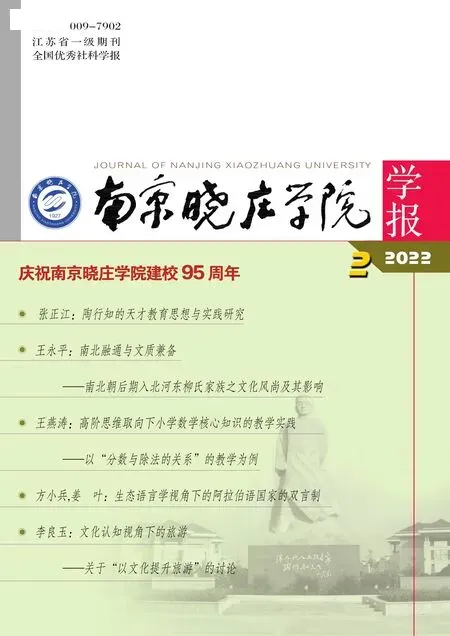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阿拉伯语国家的双言制
方小兵,姜 叶
(1.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2.南京大学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根据《语言学名词》,双言制(diglossia)又称“双言现象”或“双语体”,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普遍使用严格区分社会功能的两种不同语言或某一语言的两种变体的状态”(1)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语言不断发展、进化甚至分化形成了双言制(diglossia),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语言特征及面临的问题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时,双言制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会产生反作用。这种语言及其变体和语言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分别体现了该言语社区的系统性和动态性。而生态语言学将语言环境隐喻成生态环境,强调语言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和系统性。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生态视角的语言研究成为了一种新的学术思考。(2)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影响语言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越来越多,双言生态是否和谐关键在于其动态性及系统性能否持续。因此,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究双言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本文首先对双言制的研究进行概述,然后探讨阿拉伯语国家双言制的产生机制与演进状况,并基于国内外对阿拉伯语国家语言状况的考察,从语言生态的动态性、系统性出发,通过论述高、低级变体在阿拉伯语国家中的起源、生存、演变及特点,进一步探究阿拉伯语国家双言制的发展过程及其与语言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为阿拉伯语国家双言现象研究提供新思路。
一、 双言制研究综述
“双言制”一词由美国语言学家弗格森(Ferguson)最先提出。弗格森认为“双言”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存在于言语社区中的特殊双语现象,其中除了一种语言的基本方言(可能包括一种标准变体和几种区域性标准变体)外,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高度规范的(往往是语法更复杂的)古典变体(即高级变体)。其中,高级变体一般运用在写作及正式口语中,低级变体则出现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因此,双言制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语体(即高级语体和低级语体)不均衡地分担该语言的社会功能。”(3)Ferguson, C. A. Diglossia. Word, 1959(15).
由于高、低级变体各自功能的严格区分,双言现象表现为高级语码和方言语码在言语社区中处于明显的互补分布状态。弗格森从语言的功能角度出发,研究了双言制的四个典型案例:阿拉伯语、希腊语、瑞士德语以及海地的法语和克里奥尔语,都包含了适用于正式场合的高级变体以及非正式场合的低级变体。自此,“双言制”引起了西方语言学家的广泛关注,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甘柏兹(Gumperz)从社会阶层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双言社区”,对双言制的研究起到了过渡作用。(4)Gumperz, J. J. Types of Linguistic Communitie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62(1).之后,费什曼(Fishman)突破了弗格森的理论局限,他指出存在于同一言语社区的两种变体未必属于同种语言,例如巴拉圭双言社区中存在的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就不属于同一种语言。(5)Fishman, J. A. 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 Diglossia with and Without Bilingu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67(2).双言制的新定义大大扩展了双言制的内涵。特鲁吉尔(Trudgill)总结了弗格森和费什曼的观点,指出“双言制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标准化,并存在同个言语社区的两个不同种类的语言各自具有明确的社会功能。”(6)Trudgill, Peter.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don: Penguin, 2000.霍金斯(Hawkins)提出了“连续双言制”的概念,认为双言社会从局部(个体说话人)和整体上来看是连续的。(7)Hawkins, P. Diglossia Revisited.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83(3).在此基础上,奥尔(Auer)提出了存在于高级变体与低级变体之间的中介变体,进一步发展了连续双言制。(8)Auer, P. Dialect vs. Standard: A Typology of Scenarios in Europe. Berlin: De Gruyter, 2011.
除了定义的不断丰富,双言制的分类也受到了语言学家的广泛关注,包括“狭义双言制”(弗格森定义)和“广义双言制”(费什曼定义);“语内双言制”和“语外双言制”;“面向语言使用(use)的双言制”及“面向语言使用者(user)的双言制”,等等。(9)尹小荣:《双言制理论的演变:概念、类别和模型》,《语言规划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66-71页。徐大明在新加坡的华人社区进行了实证调查,并提出了“后双言制”(post-diglossia)的概念:曾经是双言制的社区,因社会变迁,对于变体适合于何种交际功能,社区成员的意见已发生分化。(10)徐大明:《言语社区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2004年第1期。
从现有资料看来,双言制研究存在三个视角:一是以弗格森为代表的“功能作用论”,即两种变体的存在是为了承担不同的社会分工,有各自明确的社会功能;二是以凯耶(Kaye)为代表的“情景语境论”,即两种变体的采用取决于不同的情境,有重叠的可能。(11)Kaye. Remarks on Diglossia in Arabic: Well-defined vs. Ill-defined. Linguistics, 1972(81).凯耶早在1972年就否定了弗格森对两种阿拉伯语变体的定义,并指出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没有理想中那么稳定,它在语音和句法上的变化都取决于方言阿拉伯语;三是以希夫曼(Schiffman)为代表的“社会阶层论”,即两种变体专属于各自的社会阶级,与情景、功能无关。(12)Schiffman, H. Diglossia as a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In Florian Coulmas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1997.除此之外,还有部分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变体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即高级变体专属于受教育者,低级变体专属于低文化者。对此,语言学界尚未有定论。
二、 阿拉伯语国家双言制的产生机制与演进
在阿拉伯语世界中,作为宗教信仰的载体,《古兰经》中的语言被视为是古典阿拉伯语。随着时间的发展,外来文化入侵、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语言模因效应等都给古典阿拉伯语的不断变化提供了契机,最终成为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即弗格森所说的高级变体。与此相对应的低级变体则是方言阿拉伯语。其中,高级变体用于宗教布道、政治演讲、新闻播报、学校教育、书面写作等正式场合,它有特定的语法、发音等语言规则;而低级变体用于民间肥皂剧、家庭交流、日常沟通等非正式场合,儿童在日常生活(主要是家庭)中接触到的就是方言阿拉伯语,即母语为方言阿拉伯语,所以人们需要通过接受正规教育习得现代标准阿拉伯语。
(一) 阿拉伯语国家双言制的产生机制
就阿拉伯语国家的双言制而言,其产生机制主要有三个:宗教信仰、语言接触和殖民政策。
第一是宗教因素。阿拉伯语国家的双言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伊斯兰教信仰。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存在于阿拉伯语历史社会中的语言变体不仅涉及到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还有早先的古典阿拉伯语。实际上,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是其进化版本。古典阿拉伯语早在1500年前就被用于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Hijaz)地区,它原本是古莱氏部落内部的方言,后来由于其不断发展扩张,拥有了强盛的地位和威望,并占领了麦加,经过与其他部落语言的不断交流融合,古莱氏方言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基础。具体来说,古典阿拉伯语经历了前伊斯兰时代和后伊斯兰时代。前期,它记载了公元501年至600年的阿拉伯语古典诗歌,而后期它则被用来编纂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且古典阿拉伯语的语法、形态和句法是阿拉伯人在公元9世纪建立的,(13)Abdullah, L. Diglossia in the Arabic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8(3).因此可以说古典阿拉伯语专门用来编纂《古兰经》、记录诗歌和古典文学的书面语言,这一点在语言学界达成了共识。伊斯兰教将阿拉伯语(即由古典阿拉伯语演变而来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视为“完美的”语言,因此伊斯兰教的传播对于古典阿拉伯语的稳固地位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4)Horn, C. Diglossia in the Arab World—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pen Journal of Modern Linguistics, 2015(5).而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为了适应文明时代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演进的古典阿拉伯语版本,遵循古典阿拉伯语的基本语法和形态,同时也吸收了一些相对通用口语化的术语和表达方式,在书写形式上更加规范、在表达形式上更加符合时代要求。阿拉伯语高、低级变体的共存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表现为古典阿拉伯语与其他部落方言的互补分布,到现代社会则表现为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与各种方言阿拉伯语的互补分布。
第二是语言接触。双言现象是语言通过长时间的发展而催生的两种变体互补分布的状况,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双言制产生于前伊斯兰时代。这个发展过程始于公元640年阿拉伯军队从阿拉伯扩张到征服外国土地,如埃及。从动态演变的角度来看,语言接触是双言制产生的根本原因。语言接触不仅包括前、后伊斯兰时期古莱氏部落扩张与其他部落方言接触、阿拉伯军队扩张到其他地区与被征服地区方言接触,还包括了现代受经济、政策、就业等影响造成的阿拉伯语人与非阿拉伯语人之间的语言接触。古莱氏部落向外扩张,在和其他部落的方言接触中,他们互相借鉴新单词、学习各自不同的说话方式,这为地理划分层次上的各地区方言阿拉伯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之后,在伊斯兰征服时期,阿拉伯语在与其他国家的语言接触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通用简化版语言,也被认为是现代阿拉伯语口语方言的基础。近来,受经济、政策等影响,许多外国人进入阿拉伯语国家,也有不少阿拉伯人向国外移民。在这个人口双向流动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人们工作交流的需要,阿拉伯语与亚洲语言融合,又产生了新的简化口语版本,可以被称作洋泾浜语(Pidgin),增加了方言阿拉伯语的丰富多样性。
第三是西方殖民政策。西方殖民对于双言制的产生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试图控制阿拉伯经济发展的英法殖民者执行了宽松的语言政策:鼓励民众使用阿拉伯语方言。这是由于殖民者发现阿拉伯语国家的力量源泉来自于他们共同的信仰《古兰经》,而作为用来编纂《古兰经》的语言以及之后发展而来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是所有阿拉伯人“阿拉伯主义”的标志,这是他们实现殖民目标的一大障碍。所以殖民者通过大力提倡阿拉伯语国家各地区的方言,希望借此减少甚至消灭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使用,以达到摧毁穆斯林通过语言统一形成凝聚力的目的。在此过程中,阿拉伯人不仅在使用本地方言时壮大了原本方言阿拉伯语的力量,也在和英语、法语的交流融合中产生了不少新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新变体。这种削弱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历史殖民政策造成了阿拉伯语社会至今存在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与方言阿拉伯语共存的双言现象。
(二) 阿拉伯语国家双言制的动态演进
高、低级变体一直被认为是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的语体归属,但是近年来,两者不再被使用者严格区分。例如,虽然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使用方言阿拉伯语,但当他们打算在言语中表达正式或严肃话题(无论是真的还是讽刺的)时,他们偶尔会转向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反之亦然。当他们想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必要”,即采用礼貌策略时,他们会转而使用方言阿拉伯语,这些转变普遍存在,即使是在一个单独的演讲片段中。(15)Horn, C. Diglossia in the Arab World—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pen Journal of Modern Linguistics, 2015(5).在家里和女佣说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在市场上用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讲价是荒谬可笑的,甚至被当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行为。而从目的论角度出发,这两个场景中使用现代标准阿拉伯语都是为了突出个人的受教育身份,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主要身份标志”,(16)Al-Kahtany, A.H. The ‘Problem’ of Diglossia in the Arab World: An Attitudinal Study of Modern Standard Arabic and the Arabic Dialects. Al-’Arabiyya, 1997(30).尽管看似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的确存在这样的使用者。可以说过去的高、低级变体遵循严格的分布标准,但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阿拉伯人逐渐注重个人思想的表达,不再局限于两种变体的框架式应用。
从空间维度来看,整个阿拉伯语社会是一个连续体,高、低级变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它们之间存在的“中介变体”让这个语言社区保持平衡发展。在方言地图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连续体。方言阿拉伯语为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完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地方,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与其他语言的融合丰富了方言阿拉伯语的多样性,中介变体可以直观反映两者间的互相关系。在阿拉伯语国家,语言变体及语言环境不仅自身内部在变化,还在外语的冲击下相互影响,在这样持续变化的过程中,作为双言社区的独特标志,尽管由于地区差异会造成细微的发音区别,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仍保持其文字表达的特性;而有着明显发音区别的各种方言阿拉伯语也存在着保持当地表达特色的共同点。这种介于高、低级变体之间的新变体就是中介变体,它既有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书面表达规范,又有方言阿拉伯语口头表达的地方色彩。
从时间维度来看,原始文本的多样性基本上保持不变,而口语变体则没有经历语言标准化的过程,继续以“自然”的方式变化。换句话说,相较于作为书面语的高级变体的演变过程,作为口语的低级变体处于更加明显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不仅速度快、而且呈现出了语言的多样性。高级变体作为威望的象征,同时也是唯一具有文字系统的语言变体,自然有其高度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要求,任何可能会影响书写的变化都会受到严格的评估与审核,依靠官方正规编纂的方式保存下来。(17)Bassiouney, R. Arabic Sociolinguistics: Topics in Diglossia, Gender, Identity, and Politics, 2nd Edi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20.因此近1400年来,高级变体在语法、形态和基本词汇等方面几乎不变。而今后,高级变体也很有可能选择抵制文字系统的变革来维持自身的纯洁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低级变体处在高速变化中。无论是在过去,阿拉伯语社区内各地区的方言互相借鉴,还是到现在,阿拉伯语与其他国家的语言融合,只要人们利用不同的语言交流,就会不断产生新的方言阿拉伯语,在语音、词汇等方面发生变化。
三、 双言制与阿拉伯语教学
双言制的产生机制与发展对于阿拉伯语教学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阿拉伯主义”和民族主义赋予了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在阿拉伯语国家极其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语言接触和殖民政策使得方言阿拉伯语的力量不断壮大。在教育过程中,方言阿拉伯语对于学生习得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产生阻碍还是促进作用,一直存在争议。对于阿拉伯语中存在至今的双言现象,布罗什(Brosh)通过对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学生把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他们的母语一般为方言阿拉伯语),他们认为通过接受教育来掌握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方言阿拉伯语对于学习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负面效果要大于正面效果。(18)Brosh, H. Arab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Diglos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Arabic, 2015(48).而帕默尔(Palmer)认为,学生常常混淆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能够提高学生掌握及运用两种变体的熟练度,并生成适当混用不同变体的技能。(19)Palmer, J. Arabic Diglossia: Teaching Only the Standard Variety is a Disservice to Students. Arizona Working Papers in SLA & Teaching, 2007(14).
在现代阿拉伯语国家,双言现象主要表现为高级变体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低级变体方言阿拉伯语在语言社区中的功能互补分布,其中现代标准阿拉伯语需要通过正规教育习得,用于正式交流,如在新闻媒体、教育系统、宗教场合和政府演讲中,并且可以通过高度规范的书面形式保存下来,同时它也是生活在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的交流方式,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而方言阿拉伯语则是通过口头表达的形式出现在社团内部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场合,如在社交闲谈、肥皂剧、政治漫画和民间文学中,它没有具体的语音、句法规范。因此,是否存在文字形式的书面语是双言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官方语言,同时也是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之一,现代标准阿拉伯语除了作为正式交流和文学的语言之外,还常常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与阿拉伯民族联系的象征或表现之一,但是由于方言变体的存在,双言现象出现了。
长期以来,阿拉伯语国家的双言现象表现为高级变体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与低级变体方言阿拉伯语在社会中的互补分布。然而“变体不是标准的、固定的、相互排斥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重叠;他们的领域没有严格界定……他们的说话者正在形成一个社会方言连续体。”(20)Rossi, A. V. Diglossia in Persian. In Iván Szántó (ed.), ASL to Zā’id: Essays in Honour of va M. Jeremiás. Piliscsaba, 2015,pp.211-219.语言作为沟通工具一直在适应人的交往需求而不断变化,因此弗格森最初有关双言制的定义,由于一些被发现的不足,并不能全面涵盖所有的双言社区。相比之下,费什曼提出的广义双言制指出,存在于同一语言社区的两种变体未必属于同一种语言,这一观点更适用于当今的阿拉伯语社会。如今,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阿拉伯语国家的双言制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与现代交流方式的变革中。
首先,阿拉伯国家复杂的双言环境不可避免要使其教育面临一些挑战。涉及到教育领域,就要谈到高、低级变体的习得方式。方言阿拉伯语一般是各地区阿拉伯人的母语,是儿童在日常交流中习得的。而人们必须要经过正式的学校教育才能掌握词汇、语音和句法有严格规范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因此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一般被当作阿拉伯人的第二语言。因为父母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说的是方言阿拉伯语,只有在引用《古兰经》和阿拉伯古典文学、收听新闻播报、接受学校教育时才会接触到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而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与方言阿拉伯语尽管都称为阿拉伯语,但它们之间存在了语言、词汇、句法等方面的差异,所以教育过程和普通生活的脱节对于阿拉伯语国家的学生学习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有一定影响。研究发现,双言现象对儿童学习和习得阿拉伯语的能力有负面影响,尤其在写作与阅读方面表现明显;然而,教师在课堂上混合使用两种变体的教学方式被多数受教育者接受,学生在两种变体之间随意切换更能体现对阿拉伯语的熟练把握程度。由此,有学者认为混合变体有利于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学习。(21)Brosh, H. Arab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Diglos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Arabic, 2015(48).
其次,当今阿拉伯语世界语言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所谓的“电子阿拉伯语(E-Arabic)”,即用于电子通信的语言。就语言特征和功能领域而言,这种语言实际上是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的混合体。信息技术的进步为阿拉伯语国家引入了先进的电子传媒,许多阿拉伯人使用手机和社交网站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含有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叠加特色的新变体——“电子阿拉伯语”产生了,这也是被称为“阿拉伯化(Arabization)”的语言现象:用拉丁文字表示阿拉伯音,另外7个数字代表英语中不存在的阿拉伯音。(22)Sabbah, S. Is Standard Arabic Dying? Arab World English Journal, 2015(2).不少年轻人为了追求网络用语的时髦以及交谈内容的保密性,利用方言键入文字表达个人信息,而阿拉伯文字(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不用于这种形式的互动,这种新型变体体现了时代创新对于语言发展的先进要求。
最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阿拉伯语国家和其他国家为了满足贸易、政治往来、教育等需求使用通用语言——英语进行交流,由此形成了“英语化(Englishization)”的新阿拉伯语变体,这种新变体所展示的语言现象是阿拉伯语中融合了英语单词或近似英语单词发音的新词。正如贝尔(Bell)所言,用双言制中高、低级变体两个局限的标签来形容一种语言现象太过静态和单一。(23)Bell, A. The Guidebook to Sociolinguistic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14(3).事实上,阿拉伯语国家的语言现状已经从双言制过渡到多言制。
四、 语言生态视角下的阿拉伯语国家双言制
生态语言学认为,社会环境不仅是影响语言生态系统的外部因素,同时也是属于语言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内部因素。语言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具有连续性、动态性、过渡性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双言社会中的高、低级变体以及中介变体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言生态系统,它们之间的语源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都会对语言生态造成相应程度的影响。在高、低级变体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中介变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双言生态的稳定,维持了语言的系统性。除此之外,双言社会中的高、低级变体受各自社会群体、国家语言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方式,在动态中融合发展,催生新的变体或壮大低级变体的力量,并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去粗取精,这一特性与生态语言学所强调的“动态模型”不谋而合。
(一) 从动态性看双言制对语言生态的影响
从语言生态的动态性来看,一个言语社区中存在的多种语言变体都在不断演变,它们分别承担各自的功能。在阿拉伯语国家,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作为阿拉伯语的两种变体不仅在各自的功能区域内发生变化,也在相互影响中共存发展。
从语言及语言变体出发,语言变体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在各自的功能区域内不断发展,甚至颠覆弗格森对高、低级变体之间明确界限的定义。一方面,就高级变体自身的发展而言,本源于《古兰经》的古典阿拉伯语作为阿拉伯语的高级变体,为了适应时代文明的发展,在书写与口述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语法与词汇的用法,修正后的高级变体(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更加灵活变通。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比古典阿拉伯语适用的范围更加广阔,它从宗教读本延伸到学校教材、从古莱氏方言延伸到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官方语言、从高层社会的语言特权延伸到接受教育者的语言资源,确立了一个官方、正规的语言形式,打破了阶层区分,拓宽了人们接触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渠道。另一方面,就高、低级变体各自功能而言,它们严格互补分布,高级变体出现在正式场合,而低级变体出现在非正式场合。随着石油资源的发现,阿拉伯语国家与世界各国的接触增加,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开放,这一定义已经不再准确适用于如今的阿拉伯语国家。如上述例子所展现的那样,即使在政治演讲这个正式的场合中,发言人也可能为了活跃气氛而使用方言阿拉伯语;在电视肥皂剧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中,为了刻画严肃的人物形象或紧急事态,也会出现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由此可见,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的应用逐渐由适应场合向服务于说话人的目的而转变,这种随意切换显示出人们对语言的灵活运用。
在阿拉伯语言语社区中,不同语言对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是阿拉伯语国家内部语言环境的变化:各地区的方言阿拉伯语在人口流动中互相接触,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交流互动中会增加对其他方言的认识,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各自的语言表达,导致新的变体产生。各方言之间的借鉴、融合丰富了方言阿拉伯语的种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理差异较大的地区之间的交流障碍,避免了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成为阿拉伯国家跨地区的唯一交流方式。其次,语言意识的变化会壮大部分方言阿拉伯语的力量(这取决于使用该方言阿拉伯语的人数),甚至催生新的变体。一方面,在交流时,现代阿拉伯人会为了追求与众不同而不讲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或为了保证谈话内容的保密性而使用方言阿拉伯语;另一方面,习惯使用低级变体的人群为了追求高级变体所代表的高级社会阶层,可能模仿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表达方式,但是因为文化程度的限制,往往导致高、低级变体的混合新变体产生。最后,在不同国家语言政策的推动下,各阿拉伯语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新双言现象。
由于现代标准阿拉伯语靠学校教育习得,阿拉伯语国家的语言政策大都与教育相关。尽管阿拉伯语国家将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规定为官方语言,但各国的语言教育政策并不一致,这就导致外语在部分阿拉伯语国家占据重要的地位。基于宗教信仰以及保护民族文化的需要,沙特阿拉伯规定儿童在掌握一定水平的阿拉伯语后才能接受英语的辅助教学。但是部分海湾国家,例如在阿联酋,英语成为学校教学的首要语言,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只是选修课程。(24)余光武,张森,宋思琪:《“一带一路”沿线阿拉伯国家语言国情及相关建议》,《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1期。长久下来,英语和阿拉伯语融合,形成了具有英语表达特色的新方言阿拉伯语。然而一旦极力在教育体系中推崇英语势必会造成儿童对民族文化认同的丢失,同时削弱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在双言中的权威地位。因此,不同的阿拉伯语方言和其他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
(二) 从系统性看中介变体对语言生态的影响
从语言生态的系统性来看,阿拉伯语国家的双言制不能简单划分为高、低级两种变体。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中介变体的存在起到了过渡作用,使得阿拉伯语的语言生态系统环环相扣。“中介变体”这个概念由来已久,法索德(Fasold)早就指出“广义的双言制中存在关联范围内的一个中间点”,这个“中间点”就是中介变体;(25)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84.也被称为“受过教育的阿拉伯语(ESA)”。(26)Al-Mamari, H. Arabic Diglossia and Arabic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erception of Students in World Learning Oman Center. Capstone Collection, 2011.但是由于高、低级变体界限模糊,中介变体在语言学界尚未被严格定义及广泛认可。双言制不该是一个简单的二分体,而是一个具有兼容性的、不断变化的连续统一体,其中中介变体介于高、低级变体之间,同时具有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的特点,它的功能就是维护双言社区这个动态生态的平衡,从而顺理成章地从语言连续体的角度来看待阿拉伯语双言社区中变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受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影响,抛开纯正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不谈,电子通信和商业交往领域分别出现了相应的中介变体。
随着传媒技术不断更新,各种社交网站层出不穷,电子阿拉伯语成为阿拉伯语国家兴起的新型网络交流方式,它是利用方言键入文字的互动形式,具有高级变体的书面表达形式,适用于日常交流的非正式场合。这种中介变体打破了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在书面表达中独大的局面,同时展现了使用方言阿拉伯语进行社交的保密性,是阿拉伯语国家现代交流方式的一种变革。这种“取长补短”的中介变体在维护语言生态平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受石油资源的影响,世界人口为了发展商业跨国流动,阿拉伯人为了寻找工作跨地区流动,这就促进了外语和阿拉伯语及阿拉伯语方言之间的互相影响。再加上近年来阿拉伯语国家的识字率有所提升,大多数流动人口是受过教育的新精英阶层,他们不愿意使用单纯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与他人交流。相反,他们习惯于在正式场合使用带有方言特色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甚至是在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中插入外语单词。这种商业交往方式避免了外语(尤其是英语)对阿拉伯语国家双言制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双言制言语社区的稳定性。
总之,为了达到语言生态的和谐,作为阿拉伯语国家历史文化的载体,以及整个语言生态系统中不断变化且必不可少的一个中间环节,中介变体承担着连接及平衡语言连续体的两端(高级变体和低级变体)的作用,在英语难以侵占阿拉伯国家整个教育体系的背景下,阿拉伯语国家的双言现象仍会长期存在并保持相对稳定。
五、 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国家历史与文明的象征。阿拉伯语国家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宗教信仰至上的民族统一体,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其独具代表性的双言现象受到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阿拉伯语双言现象发展至今已超过了1500年,其现状、特点也超过了弗格森的定义范畴。
宗教信仰、语言接触和殖民政策是阿拉伯语国家双言制产生的几大原因。时至今日,尽管高级变体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仍然是阿拉伯民众所公认的官方语言,但其影响力已在外语的冲击,以及低级变体方言阿拉伯语的壮大过程中逐渐削弱。现在阿拉伯语的语言生态更加复杂,在教育教学、网络社交和商业交往三个领域呈现出独特的语言多变体现象。在教育体系中,将方言阿拉伯语作为母语的儿童在习得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过程中会产生混乱,这种混乱在不受外语的干扰下,实际上会有利于学生同时熟悉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在网络社交中,新兴的电子阿拉伯语是中介变体的代表,既有书写形式、也能应用于非正式场合;在商业交往中,随着语言接触与语言意识的增强,方言阿拉伯语与外语、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融合产生的中介变体满足了在正式场合用有方言特色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完成沟通的需要。
在阿拉伯语国家,受外语、阿拉伯语及其变体影响,双言制处在动态演变中,语言生态日益复杂。尽管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方言阿拉伯语在不断变化,中介变体的产生与发展将使该言语社区生态持续平衡。双言制作为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语言连续体,在高、低级变体不断发展、进化的动态演变过程中,中介变体成为了该连续体的接头,也是这个言语社区生态和谐的平衡点。高、低级变体的演变是语言生态的动态表现过程,而中介变体是维持语言生态系统性的重要部分。由此,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双言制在阿拉伯语国家将保持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