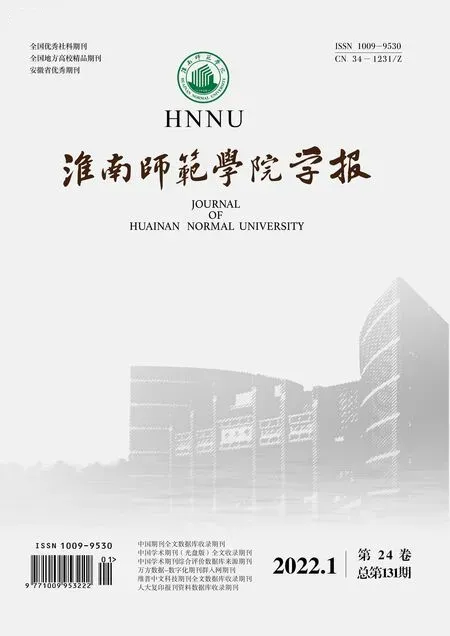淮南文化源流及其基本精神
胡焕龙
(淮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淮南文化”是“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而言,“淮河文化”也就是“淮河流域的文化”。 淮河流域位于我国中东部,西自铜柏山脉,东至东海与黄海,南北介于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之间,其总面积近27 万平方公里。 北方的黄淮平原和南方的江淮丘陵,东西向的干流与众多南北向的支流, 构成其开放而自成一格的地理单元,孕育出独特的“淮河文化”。 同时,不同的区位特征与多样的地形地貌,又使淮河流域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形态。 位于淮河中游江淮大地上的淮南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从桐柏山发源地到豫、皖交界的洪河口,为淮河上游,全长369 公里。淮河在此由丘陵,进入涡淮平原地带。 这里有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放诞潇洒的“竹林七贤”、滋阴补阳的玉液琼浆、神奇莫测的中医养生等,哺育出重生而洒脱的亳文化。
淮河下游最大的一条支流泗水,自北向南将鲁西南、皖东北、苏北连成一体。 春秋后期,孔子在泗水上游的曲阜聚徒讲学,周游列国,力图恢复“周礼”,实现“小康”。 孟子高扬“民本”与“仁政”学说,继承孔子思想精华。 儒学逐步南下,融入淮河文化有机体。 同样诞生于泗水上游的墨家学派倡导“兼爱”,为真理而战,死不旋踵。 在淮河下游的黄淮平原上,儒墨思想相映成辉。
西汉前期,在淮河中游的江淮大地上,以淮南国为载体,以寿春为核心,“淮南文化”兴起,一时间淮河中游精英荟萃,日趋成为大汉王朝的文化中心之一。“淮南”一词,自古以来具有三重内涵:一是地理概念,即广义的“淮河之南”;二是政区概念,如淮河中游先后出现的汉淮南国、 三国魏之淮南郡,唐之淮南道、宋之淮南路,以及现代的淮南市等;三是文化意义上的“淮南文化”。 它以上古淮夷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融合为底色,以道统儒,无为而治,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多元性、包融性特征,绵延至今。
纵观整个淮河文化区域,亳文化(或曰“涡淮文化”) 位于上游, 儒墨文化由齐鲁延伸至淮河中下游, 两者的文化重心皆在淮河干流以北的黄淮平原, 东西相连。 淮南文化的精华在淮河干流的中游,绵延于其南的江淮大地。 三者一南二北,隔河相望,首尾相连,呈鼎足之势,构成“淮河文化”的整体蓝图。
淮南地方文化研究随着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而正式起步。 90 年代皖北学者“淮河文化”概念的提出,推动了学术界对淮南地方文化研究的自觉与深入。淮南文化研究作为淮河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淮南地方学者奉献出数量可观且颇具学术价值的成果。
对于淮南地方文化的研究,部分成果着眼于历史与文化具体事项的梳理与阐释,这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 在此基础上,我们超越外在纷繁表象的具体阐释,以整体性、宏观性视野,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探求淮南文化有机结构、价值坐标及其历史演变轨迹,对其进行内在的、学理性研究,则是更具实质性的工作。 系统考察淮南文化的源流与变迁轨迹,由此进一步考察其有机构成、基本特征与内在精神(核心价值系统)等,应该是文化研究由外在考察逐步深入,进行学理性研究的必要工作。 不仅对于淮南文化是这样,对于淮河文化研究,乃至对于民族文化研究,亦应如此。因此,文章尝试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特定理论工具,考察淮南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轨迹、 基本特征及其精神图谱,对“淮南文化”进行本体性研究,以期使淮南地方文化研究不断深入。
一、淮南文化源流
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既深受外在历史环境的影响,也受文化有机体内在结构的制约。 其中大、小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成为最重要的内在因素。 文化大传统高居于庙堂与学堂之上,多以思想学说、政治理念、法律法规、社会伦理等形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精英文化形态,处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 文化小传统来自田野,来自乡村生活,是以风调雨顺、家族繁衍、乡风民俗为主题的民间文化形态。 两者的相互作用,内在地影响着特定文化的基本风貌与历史走向。 因此,除却远古至春秋战国的漫长形成期,所谓“淮南文化”,实际上先后呈现出汉淮南国古典文化、近世淮南民间文化和现代淮南文化三种历史形态。汉淮南国文化是以《淮南子》为思想架构的精英文化与楚地民间文化完美结合的形态。近世民间文化是唐宋以降淮河文化大传统衰落后,淮河流域民间社会生活式样的结晶,在质朴粗犷的外在形式下蕴含着道家人生哲学。 现代淮南文化形态,正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处在历史的建构过程之中。 汉淮南国时期是整个“淮南文化”发展历程中的“轴心时期”,它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淮南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基本精神,是现如今建设现代淮南文化不可替代的传统文化资源[1]。
(一)渊源:夷文化底色下的多元文化融汇
约六千至七千年前,中国历史进入神话与传说时代。 在这个充满血与火、蕴育发明创造的激情与活力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体开始凝结,最终融合为炎黄、东夷、苗蛮三大部落集团。
炎黄集团又称为华夏集团,“这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2](P40)。 炎、黄集团起源于我国西北部黄土高原的渭水流域,分别在姬水和姜水一带成长壮大。 他们互为婚姻,沿黄河两岸向东进入中原,后与东夷集团的蚩尤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最终黄帝擒杀蚩尤。 华夏集团势力占据中原和今山东一带,淮河流域开始沐浴中原文明的曙光。
东夷集团地域“北至山东北部,最盛时也或者能达到山东的北部全境。 西至河南的东部,西南至河南的极南部。 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海”[2](P56)。 它主要由太皞(太昊)、少皞(少昊)和蚩尤等众多部落组成。夷人以太阳和海鸟为图腾,也被称为“鸟夷”。一些部落南迁,进入皖北平原,依据各大水系而居,建立了英、六、蓼、江、钟离及群舒等小国,也被称为“淮夷”。“淮夷各部落带来了图腾、神话、礼仪、仁性等东方文化因素,江淮大地上浸润了浓郁的夷文化底色。 ”[3](P7,10)
以“三苗”为主体民族的苗蛮集团,活动范围大致在淮河以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苗蛮集团在文化上不与中原认同。尧舜时代,南北战争旷日持久,这促进了南北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西周至春秋时期,在苗蛮文化沃土之上,荆楚文化崛起。 它以南方浓郁的原始文化精神与中原礼乐文明相对峙,成为淮南文化大、小传统的渊源。战国至秦汉,以寿春为中心舞台,这种原始文化精神的原始浪漫与北方理性精神的有机融合,凝结为淮南文化的基本结构与精神谱系。
(二)孕育:春秋战国蔡楚文化的合流
蔡国地处今豫皖交界地带,历史可追溯到西周初年,始祖为文王之子蔡叔度。由于战乱,蔡国由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一路迁徙至下菜(今安徽省凤台县)。从沿途大量的出土文物来看,蔡国南迁东下的过程, 也是在淮河流域一路撒播中原文明的过程。
蔡国文化的主要构成,一是故地上蔡的上古土著文化,一是新兴的西周礼乐文化。就前者,考古工作者在上蔡故地发掘出非常密集的古代遗址82处,其中西周以前的遗址42 处,较鲜明地体现出从远古到商周时期的中原文化特征。上蔡土著文化与姬周文化的融合,形成独特的蔡文化。 蔡国的礼仪制度代表了中原礼乐文化精粹。 1955 年在寿县发掘的蔡昭侯墓出土文物总数580 件。富有特色的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车器等四大类,充分展现了中原礼乐文明风貌[4]。
在约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楚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逐步“华夏化”趋势。但楚文化结构始终是大传统(中原礼乐文明)与小传统(荆楚先古民风)的相互渗透,相得益彰。 汉《淮南子》那“道治天下”的理性精神与文化内涵丰富的神话世界的有机融合,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艺术再现。
从物质到精神,有学者把楚文化的主要成就归纳为冶金、织帛、髹漆、道家哲学、浪漫主义文学和艺术等六个方面,成为后世汉淮南国独特的文化资源[5]。 而漫长历史凝结的楚文化精神气质,同样影响着后世淮南文化的精神风貌,其具体表现为:
1.积极进取,坚韧不拔。 一部楚国历史,就是楚人文化精神的写照。 楚人在早年屡遭歧视,然筚路蓝缕,开创基业。 强大后积极北进,争霸中原;虽为秦灭,然“楚虽三户,亡秦必楚”[6](P680)。楚人终灭秦而开创汉祚。这种顽强进取精神,既有文明时代北方理性精神中的坚忍不拔(大传统),也有源自自身原始时代生命本能与宗教迷狂凝成的蛮野剽悍(小传统)。
2.开放吸纳,勇于创新。 楚人的民族构成颇为复杂,因而在楚国,很少有中原各国“华夷之辨”一类的种族歧视与文化偏见。 楚国社会海纳百川,积极吸纳中原的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成果,且同时包融巴、蜀、越、吴的民间文化。当地的民谣、方言等与社会上层公族音乐艺术相配合,孕育出楚国艺术的瑰宝——楚辞。其青铜器融合南北,形成楚式风格。其冶炼、纺织与漆饰技术,更是吸纳、融汇自各国。这种开放包融、不拘一格的文化精神,在淮河中游一马平川的江淮大地上,得以充分展现。
3.浪漫情怀,幻想人生。 西周至春秋时期,我国北方人文精神兴起,理性精神高扬,“事鬼敬神而远之”成为当时社会上下普遍的思想理念。但在楚国,原始宗教氛围仍弥漫于社会生活中。屈原的《离骚》带有一种浪漫与哲学互补式的想象,其《九歌》是民间古代仪式乐歌的再创造,浪漫的想象世界弥漫于楚国人民的精神生活。
4.不拘礼法,率性而为。 楚人身处南方偏远蛮荒之地,长期遭受中原华夏文明的歧视,形成强烈的屈辱感与自我意识,进而形成叛逆、张扬、率性而为的民族精神,蛮野的血性让楚人敢作敢为。 政治上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与当时的华夏文明世界分庭抗礼;宫廷内弑篡频仍,国境外灭国无数。 此外,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凝结成楚文化绚丽奇伟的个性主义气质。
上述种种,成为数百年后汉淮南国的基本文化基因,也全面影响了汉文化的有机构成、思想倾向与精神气质。
(三)辉煌:淮南国文化成就
大汉王朝建立后, 高祖刘邦采取黄老治国学说,无为而治,逐步恢复和发展生产。 经“文景之治”,至武帝时代,大汉王朝走向强盛。 与京畿地区相对应,作为东方文化中心,淮南国文化也逐步走向辉煌:以刘安为代表的庞大文人队伍,成为淮南国文化“大传统”的创造群体;以“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淮南子》为核心,凝结出足以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体系,代表了中华民族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成果。《淮南子》对董氏政治哲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完善与补充作用,在与董氏儒学冲突与互补的辩证关系中,成为汉王朝文化大传统的有机构成。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淮南子》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族哲学多元融合的历史成果,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淮南国文化是整个淮南文化发展历程中的“轴心时期”。
刘安在位四十三年,是淮南国学术事业和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淮南》内书,即我们今天看到的《淮南子》。 它以道家思想为核心,有机融合儒、法、阴阳、兵、农等诸家思想,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体现出淮南文化博大、开放、多元、形上的风格。
淮南国文学创作渊源于楚国辞赋,据《汉书·艺文志》 记载,“《淮南王赋》 八十三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大多失传、散佚。透过残存的篇章,我们仍能深刻体悟到淮南国文学的楚风汉韵,感受淮南文化潇洒浪漫的精神风貌。此外,长袖善舞的“淮南舞”、以融中原与楚地风格为一体的青铜艺术及陶瓷艺术等也都走向成熟,显示出鲜明的多元交汇、以楚风为宗的特点。 它们与博大精深的哲学、绚丽飘逸的文学等,共同筑成淮南文化多姿多彩的哲思—审美精神文化园地。 相传为刘安发明的豆腐,质地细腻柔嫩,成为浪漫文人修身养性与民间社会纯真质朴的文化象征。
(四)蜕变:战乱与灾害中民间文化的兴起
汉武帝十九年(前122 年),汉王朝在淮南国复置九江郡,治所寿春。但连绵不断的战争、水患等天灾人祸, 使淮南地区不再成为地方经济与文化中心, 文化精英阶层失去政治与社会依托而流散,主流文化(大传统)因失去创造主体与文化土壤,逐步衰落。 以风调雨顺、家族兴旺、升官发财、祈福禳灾为主题的民间文化渐渐成长,一枝独秀。 纯朴粗犷的民风、热烈奔放而细腻传神的民间艺术,日趋成为近世“淮南文化”的新面孔,它从精神内涵到外在形态都使人生发“沧海桑田”之叹。
三国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寿春地区成为兵家争夺之地。隋唐时期,国家一统,经济繁荣。然此时,国家政治中心在中原,经济文化中心却在“江南”,扬州代替寿春成为淮河流域地方经济文化中心。京杭大运河开通后, 寿春地区被进一步边缘化、“乡村化”。以民风民俗、民间文艺、乞讨艺术等为表征,淮南文化的精神品格由士人“大传统”向民间“小传统”发生整体性历史蜕变。
两宋时期,寿春地区成为宋、金对峙的前线。此时期以乞讨为宗旨的民间艺术“花鼓灯”、凤阳花鼓等走向成熟,成为淮南地区及淮河流域具有象征性的民间艺术奇葩。元代以降,民族压迫严酷,淮河流域饥民遍地,民间乞讨艺术格外兴盛。 明朝多次发生黄河决堤及夺淮入海的大水灾,灾后流域常常赤地千里。
清朝前期,朝廷加强对淮河流域的治理与赈灾工作,寿春一带呈现出相对安定的局面。然而,近千年的文化颓势难以改变,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淮南文化的振兴,有待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总而言之,在文化有机体中(不管是民族文化、区域文化还是地方文化), 大传统对小传统的积极引领与规范,大、小传统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文化健康发展、繁荣兴盛的标志。大传统的衰落,意味着文化有机体创造性、现实超越性及其诗意品格的丧失,意味着“文化精神”(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民族精神)的丧失,此可视为文化衰落的重要标志。随着淮南国的消失及后世延绵不断的天灾人祸,近世淮南文化乃至整个淮河文化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五)“现代淮南文化”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淮南地方文化开始发生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历史性蜕变。 它一方面以“传统”身份,融汇于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之中,同时又作为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全面参与“现代淮南文化”的历史性构建。 “现代淮南文化”将以崭新的精神大厦、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 呈现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中。重建大传统、优化小传统,铸造现代型淮南文化模式,是新时代“淮南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所谓重建大传统,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坐标,继承和改造淮南文化传统肌体中仍具现代意义的思想文化成果,使之成为现代淮南文化主流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从而实现“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一言以蔽之,在民族文化全面复兴时代背景下, 铸造淮南地方文化的价值座标。所谓优化小传统,就是在新时代文化大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规范之下,对在恶劣生存环境中陷入粗俗、愚昧的民间文化进行思想与美学的升华,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大传统之核心价值观铸造其灵魂、以现代社会文明生活方式及道德观建设其良风美俗、抢救民间工艺、繁荣民间艺术;以传统之“礼”维系民俗风情、以现代之“法”建立道德理性,以形成健康、和美的乡村与社区文化样式。 大、小传统高度和谐,良性互动,现代形态的“淮南文化”,便应该呈现出其新时代的风采。
现代淮南文化与传统淮南文化在经济基础上有着本质性差异:前者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建立在家族封闭型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行模式,高科技对社会生产、对个人日常生活方式的全面渗透,人与人之间全新的关系模式,对人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审美理想、行为方式等,都会产生全方位的、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在基本内涵与外在形态上,现代淮南文化与传统、古典形态的“淮南文化”将呈现出更深刻的本质性差异。 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淮南文化”将迎来又一次,即现代化的“沧海桑田”。
二、淮南文化基本特征
文化的外在基本特征与内在基本精神,都是该文化历史发展、 变迁之路及存在形态的最终凝结。相对而言,文化基本特征具有外在性、客观性及一定的历史变异性。 内在精神则是特定文化的灵魂,核心价值系统所在,具有鲜明的现实超越性与历史延续性,因而,由历史发展变迁考察到基本特征的把握再到内在基本精神的凝结,应是文化研究逐步深入的一般理路。
作为淮河文化的有机组成,淮南文化既体现出淮河文化的一般特征,又显示出其独特的存在形态与风貌。在儒道互补思想的大格局下,道治天下、开放包容、柔以为进、无为而有为,是淮南文化基本特质与内在精神的体现。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出淮南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独特的区位与全面的融合性
公元前203 年,刘邦划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为淮南国,封英布为淮南王。 其范围在今安徽省境内淮河以南,包括今江西省全境,西延至河南东部, 总面积为30 多万平方公里。 英布谋反被灭后,淮南国国土被一分为三,分别建淮南国、庐江国、衡山国。 刘长、刘安父子先后为新淮南国王,新淮南国仅领九江一郡之地。 范围在 “今之安徽中部,以今之寿县、淮南市、蚌埠、临淮关乃至江苏扬州等地区沿淮一带向南推展,接近长江北岸”[3](P19),古寿春地区始终是其核心之地,而此地正是传说时代淮夷各部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区,也是三大民族集团碰撞与交汇的“十字路口”。中国各地文明的种子通过各部落联盟“东征”“南迁”与“北上”,以战争、杂居与通婚形式播撒在这片土地上,也因此奠定了此地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与融合性特征。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中国文化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并根据代表性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及其类型的差异,提出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①。
苏秉琦先生认为,考古学上的这六大文化区自形成以来,就处于持续而全面的相互影响、由多元走向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大考古文化区域除了北方文化区,其余5 个或在黄河流域(中原区、东方区),或在长江流域(东南区、西南区、南方区),几乎四面合围,把淮河流域紧紧围裹在中间,其相互间的文化互动可想而知。 苏先生强调,其中的中原区(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青莲岗—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呈倒三角态势,主导着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互渗,按照这一视角,淮河流域处于这倒三角形的中心地带,因而,三方“以苏鲁豫皖四省邻境地区为纽带之一”[7](P79-81)进行互动互融。 纵观全国各地其它地区,难以找到像淮河流域这样被五大文化区域“四面合围”的地方,这一典型的“文化十字路口”地位,某种程度上使淮河流域成为中国各区域文化交流的“集散地”。 其中,以古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方文化,以其地理位置上更典型的“通衢”特征,成为文化集散地区的“交通要道”,从而体现出其突出的开放性、融汇性特征。
(二)多元的人文荟萃
作为淮河文化的有机构成,淮南文化吸纳着四面八方的营养,形成多元一体的人文精神内涵。 它以夷文化为底色,蕴寓东方的神话、图腾与仁性色彩,兼具潇洒浪漫、崇尚个性与自由的情怀。它浸润于沿淮东下的老庄文化精神,道家哲学最终成为其核心精神,“天人合一”“自然无为”, 成为其精神运动的最高境界。 同时,它全面吸收齐鲁之风带来的礼乐文明,在道家自然无为底色上积极进取,描绘治国安邦的蓝图,最终凝结在“以道为宗”、儒道互补的思想大格局之下。 身置楚文化摇篮,南国方士与北方“诸子”在此会面,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在此碰撞。 人文精神与宗教情怀的完美融汇,酝酿出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养生文化与神仙文化。“仙人”逍遥于此岸与彼岸,是最自由、最完满的个体生命形式,“得道成仙”成为人们憧憬的最高人生境界。 刘安士人群体的故事及其编著的《淮南子》,可谓中国神仙文化集中而富有诗意的展现。 总之,融通此岸与彼岸,追求个体生命的完美与永恒,享受现实世界的诗意与浪漫,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立足现实人生而追求精神超越的人生哲学与宗教精神。
(三)包融的哲学精神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易》作为中华文化的“群经之首”,是远古中国各民族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在从西周到春秋的所谓“轴心时代”,思想家们对远古文明进行了深刻反思,从中汲取精华,各自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至秦汉天下一统,思想智慧的大融合已是历史的必然。 先有《吕氏春秋》的探索,“儒道互补”“外儒内法”成为时尚,再有董仲舒兼融诸家、神学化的大一统儒学体系。 与此相呼应的,是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 作为淮南国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淮南子》 以道家哲学为本体,有机融合阴阳、儒、墨、法、神仙等各家思想,全面探讨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根本关系。《淮南子》代表了淮南文化的最高成就, 彰显着淮南文化综合、博大、包融、形上的精神品格。
(四)大传统非主流之文化地位
上文已述,大传统指由社会文化精英和权力阶层共同创造的以思想学说、政治理想、社会制度等为基本形式的主流文化、官方文化形态,与社会下层自发形成的民间文化(小传统)相对应。 在远古“英雄纷争”时代,“淮南”地区以蛮、夷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在不断进逼的华夏势力面前,始终是被征服和被贬抑的对象。 周初至春秋时期,“夷”在华夏文明面前已成为落后与愚昧的象征。 春秋战国以后,“儒道互补”成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基本格局,作为淮南及淮河文化核心价值系统的道家哲学,其时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四大显学”(儒道墨法)之一,有着深厚的思想传统与广泛的社会基础,是诸子百家中唯一能够与儒家思想哲学体系并驾齐驱的精英文化。 但它始终又以反传统的“在野”姿态,与庙堂背景的儒学相竞争,大多在“儒道互补”大格局中处于“补充”地位,即大传统思想谱系中的非主流地位。淮河流域被纳入楚国势力范围后,这里成为与北方正统文化对应的前沿,“淮南文化”最终以楚文化为坐标,与北方正统文化互动,成为大传统中的非主流、非正统文化。 在大一统帝国文化逐渐形成的西汉时期,“无为”长期成为汉王朝治国之策,窦太后推崇黄老之学,《淮南子》也深受汉武帝的喜爱。 然而在思想的角逐中,博大精深的《淮南子》备受冷落,终被逐出庙堂,董仲舒神学化儒学体系占据了汉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地位。
三、淮南文化基本精神
每种文化,都是诸多文化元素围绕其共同的基本精神或核心价值系统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外在具体文化元素都在不同层面,不同侧面,体现着该文化的基本精神或核心价值。文化基本精神是在其外在基本特质基础上进一步内化、凝结而成的核心价值系统,是该文化的灵魂所在。 文化基本精神一旦凝结而成,由于其稳固的价值座标而使其具有突出的自足性与现实超越性。不管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它都将作为稳固的“传统”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尊奉而一代又一代地延传下去。中华文化精神是这样,淮南文化精神亦是如此。 面对文化遗产,我们通常所谓的“批判”、所谓要“继承与发扬”的,主要就是“文化传统”,即文化的内在精神与价值系统,这也是今天我们由表象到本质,最终要着力发掘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传统”的原因所在,文章在此对淮南文化内在精神进行归纳。
(一)以道统万,追求超越
汉淮南国地处淮河中游的江淮之间,承受西北道家哲学精神,领略南方楚地原始文化精神的浪漫情思,形成以道为宗、追求超越的形而上品格。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最先以“道”的概念建构自己的哲学本体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与人类社会的本源,它无形无象而化生宇宙万物, 因而只有领悟大道,才能认知宇宙万物;拘泥于纷繁复杂的具体表象是舍本逐末,只能离大道越来越远。 刘安及其合作者继承这种超越精神编撰的《淮南子》“更凸显‘太上之道’的绝对优先意味,并将其置于天、地、人之自然法则与生存本原之上, 作为思路起点与价值依据。 在《淮南子》看来,‘道’不仅是一切的本原及其合理性依据,也是宇宙间一切的支配性力量,甚至还隐隐是有人格与意志的神灵, 它贯穿了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三大领域,无论鬼神还是人类,无论幽冥还是人间,‘道’ 都昭示了必须遵循的法则”[8](P245)。在《淮南子·要略》中,刘安阐发其哲学的主旨为“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把握大道以统御天下,沟通万物,而“非循一己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于物,而不与世推移也”。 他认为,我们在生活中应不被纷繁的表象所迷惑,不被具体的现实关系所拘束,不被一时一地的得失所困扰,而是要力求把握根本、掌握规律,明确方向,从大局出发,在大境界上处理各种关系,化解各类矛盾,凡事不争先而求最终的胜利。 在现如今浮躁的时代氛围中,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哲思与智慧正是我们最为珍贵的文化传统。
(二)以博为怀,海纳百川
淮河流域地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东西流向的主干与众多南北流向的支流、辽阔的淮北平原与平缓的江淮丘陵,使淮河流域成为中国典型的东西南北区域文化尤其是南北文化交汇的历史舞台与集散地。 淮南文化以道家思想为核心,有机容纳儒家礼乐精神、法家法治理念、墨家之实践精神以及阴阳五行之运动变化学说等。比起淮北平原上的两个地域文化——上游的道家文化与下游泗水区域南下的儒墨文化,淮南文化更为典型地体现融“百家”于一身的特点,更为鲜明地表现出多元、广博、海纳百川而又自成一体的淮河文化特征。 它既有形上之大道,又有形下之万物;既有理性之哲思,又有生命之冲动;既有北方之严谨肃穆,又有南方之浪漫率性。 不论是抽象哲思还是安邦治国,抑或生活之理,无不充分体现这种多元一体、海纳百川的文化特质,以致于《汉书·艺文志》视《淮南子》在思想构成上为杂家。 一部淮河/淮南文化的发展变迁史,就是持续不断的多元交汇与有机体系生成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与成长于相对较为封闭安宁的自然环境中的徽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以文化主题的明确性、文化结构的稳固性及文化精神的保守性为鲜明特色,而思想的开放性、有机体的包融性与灵动性,则是平原文化的总体特性。
(三)以逸为宗,创新制胜
“逸”并非懒散无事、不思进取,而是自觉遵循客观规律,顺应自然法则。在此前提下,人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韧性进取,最终创新制胜,这种文化特性与淮水的顺势婉转及平原的通达明澈有内在贯通之处。 它渊源于老庄的“无为”,至《淮南子》则进一步突出“无为”与“有为”的辩证关系,凝结为淮南精英文化基本品格之一。
在中国哲学史上,《易经》的辩证思想与“五行”相生相克学说,都包含着顺应自然与社会规律则无往而不胜的思想。 至《道德经》则发展为“无为”理论。 “无为”即“无违”:君主以“无为”治国,圣贤以“无为”济世,庶众以“无为”谋生,最终“无为而无不为”。
毋庸讳言,老庄的“无为”哲学过多强调了人对客观规律和对“大道”的顺应,而相对忽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考察。《淮南子》则对“无为”与有所作为的辩证关系作了较为合理而公允的论述:“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惠,可谓无为矣。”[9](P814)“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于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10](P1124—1125),即不以个人主观意志凌驾“自然之道”之上,事成则归功于天道自然之大法则而不自矜。 神农教民播种五谷,结束了人们茹草饮水的野人生活,且遍尝百草为民治病,解除民众疾病之害;尧处置讙兜、三苗、共工、鲧四凶,维护了政治稳定;舜教人民建造屋室,使人们有了栖身之所;大禹决江疏河,平治水土,勘察与划定九州,平定四夷千八百国,使华夏一统,让人民安居乐业;商汤攻夏、伐无道、诛暴君,改朝换代,开创历史新纪元……种种千古功业,皆为自然之道的具体体现,“无为”的历史成果。[11](P63-64)而类似以火烤干水井、引淮水上山等行为,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有为”行为。 《淮南子》以大量篇幅,详细论述了“无为”原则下实现千古事功、造福人民的范例。 以“逸”为宗,“无为”中的奋发进取、“因循”下的创新制胜,成为淮南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
(四)以退为进,以柔克刚
如果说“无为而无不为”体现出道家哲学文化内涵的科学精神,那么“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则体现出道家文化把握大局、顺势婉转,追求终胜与完胜的阴柔文化气质。相对于儒家入世进取与担当精神,墨家的身体力行、义不旋踵的侠义行为,法家唯法是依、刻薄寡恩的刚性性格,淮南文化以“水”为尚,以柔为宗,以不争、无为、静观、体道为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抱雄守雌、无为而无不为”的大境界。中华文化的柔性精神,主要体现在淮河中上游道家哲学的柔性精神上。“柔”绝不是消极的软弱退让,而是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下遵循采用合理优化生存与发展模式的最高原则,其中蕴含着睿智的大局观、时势观、发展观与变易观,蕴涵着“天之道”与“人之道”的辩证关系,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最高生存智慧。
四、结 语
综上所论, 本文既对淮南地方文化的历史源流、外在特征与内在精神三个方面(或三层面)分别进行考察,同时还试图借此研究架构以探讨淮南地方文化(包括更高层次的文化,如区域文化之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民族文化之中华文化等)研究的学术路径。在文化研究视域中,三者既是并列关系,更是由表及里、从具体到一般的逐步深入关系。
文化源流,是特定文化的萌芽、成长、壮大、成型的历史过程,往往能够显示其特定的历史演变轨迹。 文化的发展变迁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具体的外在作用力,如战争、自然灾害、政治状况、民族迁徙等,其内在因素则取决于文化内在结构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大传统渊源于小传统母体, 最终又对小传统进行强有力的统摄、规范与引领。大、小传统之间良性互动与否,决定着该文化的精神风貌及其历史兴衰。 因此,文化的历史变迁并非无序的,而是有理可循的。 以此为考察视角, 文章认为淮南地方文化经历了远古萌芽期、春秋战国孕育期、 汉淮南国形成与辉煌期、 近世蜕变期和当今的现代转型期几个历史阶段, 先后呈现出西汉早期的古典文化、 近世民间文化、当今正在建构中的现代淮南文化三种形态。 这样,所谓的 “淮南文化” 才能以鲜活而具体的历史面目在我们面前活起来、 有序地动起来, 而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
文化的基本特征(或外在特征),是该文化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某些本质性、规律性的凝结,在特定的侧面上可以体现出该文化有机体的一般性意义,表现出该文化相对稳定的存在形态、社会功能与精神气质。这种文化基本特征往往形成于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与外在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使它往往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又呈现出某种变异性,但变异却不离其宗。 因此,文化基本特征作为文化肌体形而下的某些实质性、规律性凝结,是外在纷杂现象通向文化内在精神结构(价值谱系)的桥梁或纽带。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只有把握了某种文化的外在特征,对该文化的研究才能真正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具一般性与本质性的文化特性不断内化,凝结成人们稳固的文化心态,再经思想家的提炼与升华,形成思想学说、精神坐标与价值尺度。 这种抽象化、精神内化、价值化的过程,就是该文化内在精神坐标、价值谱系凝结的过程。 “文化精神” 作为该文化的灵魂或“神经中枢”,统摄着整个文化有机体,最终形成该文化特定的“文化模式”。 民族文化是这样,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地域文化也是这样。特定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谱系)一旦形成,便表现出强烈的自足性与历史超越性,它一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规范着现实社会生活,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同时又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超越时代变迁,以自身的内在逻辑代代相传, 凝成具有绝对权威性的思想力量,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对之坚信不疑,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传统”。
作为超越时代、稳固自足、极具权威性乃至神圣性的思想力量,文化传统渗透到人们精神生活的每个细胞,规范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好的传统引领社会进步,造福于广大民众,僵化落伍的坏传统则压抑着人们的创造活力, 易造成社会的停滞与僵化。因此,历史上任何文化革新运动,归根结底都是文化革命的先驱们根据时代需要,对自身这份精神文化遗产——文化传统进行重新审视的实践结果,其后或继承发扬,或改造批判,以凝结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传统,而当今我们对淮南地方文化遗产的研究亦应如此。
注 释:
①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上六大文化区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主要文化遗址有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 青铜文化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赵宝沟文化、后红山文化等);(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主要文化遗址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3)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仰韶文化遗址为代表,还有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庙底沟文化等等);(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主要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5) 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主要有屈家岭文化、 三星堆文化等);(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见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