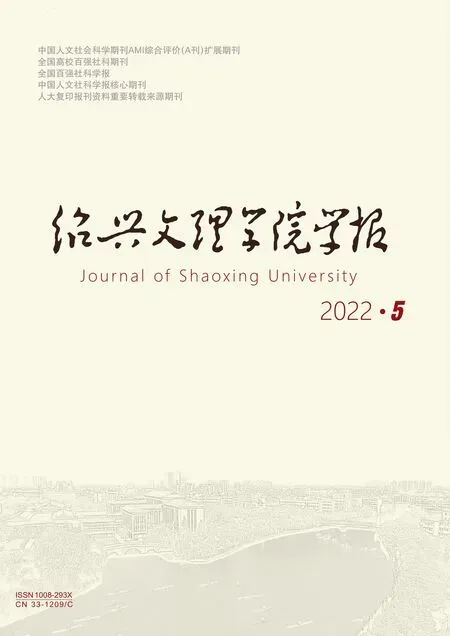葛洪由儒入道及其道家思想特色
陈颖聪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专上学院,香港 九龙 999077)
对葛洪的研究,论者多关注他的丹鼎之术而定位为“内神仙外儒术的道教思想”[1],近来不少研究者又多持“儒道互渗”之说。这些说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以把握葛洪思想的核心。本文试从葛洪思想的前后变化及其基本特点研究葛洪思想的性质及历史价值。
一、葛洪的前期思想
葛洪前期的思想主要反映在《抱朴子·外篇》中。《自叙》称,因父亲早逝,家境贫困,“不早见督以书史”[2]652,“不得早涉艺文”[2]653,“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2]655。葛洪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学说,不但以“忝为儒者之末”[2]668自负,而且表示“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2]710,这时的葛洪颇有把儒学发扬光大的抱负。
(一)政治观
葛洪前期的政治观主要表现为对玄学清谈的批判:“(林宗)无救于世道之陵迟,无解于天民之憔悴也。”[2]474“(弥衡)言行轻人,密愿荣显,是以高游凤林,不能幽翳蒿莱;然修己驳刺,迷而不觉。故开口见憎,举足蹈祸。赉如此之伎俩,亦何理容于天下而得其死哉!”[2]488
葛洪认为,玄学清谈的根本弊病是脱离社会,对社会、百姓缺少关心,谈玄者表面上装得清高,孤芳自赏,实际上却是自我标榜,互相吹嘘,以此求名求利。
鲍敬言是“无君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2]493,“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意也”[2]507,人间一切灾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有了“君主”的缘故。葛洪则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予以深刻揭露:“贵贱有章,则慕赏畏罚;势齐力均,则争夺靡惮。是以有圣人作,受命自天,或结罟以畋渔,或赡辰而钻燧,或尝卉以选粒,或构宇以仰蔽。备物致用,去害兴利,百姓欣载,奉而尊之,君臣之道于是乎生,安有诈愚凌弱之理。”[2]516“久而无君,噍类尽矣。”[2]522
葛洪所坚持的是,有德有才者为圣、为君,带领百姓创造新生活,君道的确立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明的标志。葛洪又坚持在社会生活中必须要有纪律约束,否则必争讼不已,天下大乱;确立君道是发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秩序的保证,所谓“靡所宗统,则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网疏犹漏,可都无网乎!”[2]564葛洪批判“无君论”,目的显然是要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
对于君主,葛洪亦有具体要求。他认为,君主必须成为万民表率,“未有上好谦而下慢,主贱宝而俗贫”[2]334,“率俗以身,则不言而化”[2]337。他又强调,在君主之治中必须“仁”“刑”兼施:“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3]330“仁”与“刑”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至于两者的关系,他从两个层次上作出说明。
从根本的方面说,施行“仁”政是最终目的,所以“刑为仁佐”[3]330,必须“贵仁”,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定义。然而,葛洪又认为不能过度宣扬“仁”,为“仁”必须有“刑法”作保证:“故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3]344他清醒地看到,当前社会现实所急需的是要有强大的“刑法”整治不正的风气:“刑之为物,国之神器,君所自执,不可假人。”[3]346“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措刑……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俗儒徒闻周以仁兴,秦以严亡,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3]361-364葛洪对“刑法”的认识未离开两汉以来儒者对“王霸”之道的贯彻。
葛洪早期的政治思想明显与两汉时“礼表法里”思想相呼应,表现出积极用世的愿望。
(二)人性论和人才观
在人性论方面,葛洪没有专门论述,但他曾说:“勋、华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于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恶不染于三仁。”[2]298这是传统的“性三品”说,然而现实又使他认识到:“敢为此者(笔者按:指以力残害别人),必非笃顽也,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3]613他认为,人性固然有天生之差别,但起作用的则是后天对“情”的修养,如“冠盖”之家自应是“上品”者,但若不修养其情,一旦放失,就会沦落为“恶”。所以他告诫人们:“是以小善虽无大益,而不可不为;细恶虽无近祸,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纵欲,而不与天下共其乐,故有忧莫之恤也。”[3]240
魏晋时,社会动荡导致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相当普遍,门阀地位的变更直接动摇着人性“上”“下”品“不移”的观念。正是面对这一社会现实,葛洪对人性的“三品说”作出了新的思考和修正。他一方面承认有上智下愚之别,另一方面更强调后天的社会生活与个人修养可使“智愚”“善恶”之性发生改变,于是他提出了名与实必须相符的见解:“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闇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华,不可以祖祢量卫、霍也。”[2]287“肤表或不可以论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2]296葛洪强调人的智、愚、善、恶不能凭其表象而判断,他以“情”说“性”,强调“情”必须得到掌控,不能因贪求荣利而积恶成习,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这个前提下,葛洪指出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夫学者所以澄清性理,箕扬埃秽,雕锻矿璞,砻炼屯钝,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仰观俯察于是乎在,人事王道于是乎备,进可以为国,退可以保己。”[3]111学习不但可以使人的性理、情怀得到陶冶,得到改变,更是关乎王道之治、国计民生的大事,至于学习的内容则主要是儒家经典。他认为,秦所以二世而亡,汉以后所以社会混乱,均是由于儒学得不到重视的结果。因此,“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3]173,应是首要之事。
在葛洪之时经学已经表现出自身严重的不足,政治、经济、学术已处于非变革不可的时期,他的儒学主张尽管难以为世人接受,但不可否认,他强调后天学习对立德立品的重要性,认为“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3]117,“进德修业,温故知新”[3]124,“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3]132,无疑是对魏晋森严的门阀制度的大胆挑战。他认为,用人要谨防“德薄位高”者[3]423,这些人妒贤忌能,唯利是图,于国计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主张人尽其才,唯才是用,“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矣”[3]309。他甚至要求国君带头摈弃门阀之见,“不吝金璧,不远千里,不惮屈己,不耻卑辞,而以致贤为首务,得士为重宝,举之者受上赏,蔽之者为窃位”[3]325。他告诉君主,要打破一切世俗偏见,不分远近、贵贱,唯贤是用,营造出人君以招贤用材为己任,人臣凤兴夜寐、竭心尽力以奉公的政治气氛,才可能出现隆平盛世。
葛洪的“人性论”和“人才观”是对传统儒学的发挥,颇具进取精神。然而,在玄学向两汉经学挑战的历史大潮下,年轻的葛洪不但不可能使历史逆转,而且极有可能被历史大潮淹没,在中晚年以后,他的思想转向了道家玄学。
二、葛洪的后期思想
葛洪生活在玄学盛行之世,严峻的现实使他对“儒”“道”关系作了深入思考,后期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栖居罗浮以后。
(一)由儒入道
葛洪后期对儒、道的认识,《抱朴子内篇·明本》明确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4]184,两者是“本”与“末”的关系。葛洪从上古自然无为而治,然后生发出帝王崇尚“礼”“法”之治的历史演变,指出:“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4]138又根据《老子》“道”既是万物之始又是万物之母,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点,认为“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4]185。“道”是万化之源,是引导人类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根本理论。葛洪认为,儒、墨、名、法等学派虽各有长短,但对宇宙万物始生、始成的认识均十分欠缺。例如,他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4]184,道家之说“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4]184。因此,所谓“本”“末”关系就是宇宙自然为根本,以及把这个根本应用于事事物物的关系。道家取其本,儒者用其末。
葛洪又说:“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4]139他认为,道与儒的不同,简言之表现为“难”与“易”差异。儒者事事皆有章可循,有书可据,出处语默均有定则,一般人容易了解和执行,这是其方便之处。儒家强调凡事必须要有典籍条文作为根据,但“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4]140,对儒家的典章若略有闪失,极有可能被视为铸成大错。由此可知,儒家理论看似方便,实际上却是隐藏危机,难以放心施行;而道家不受经典、人事所束缚,只需静修其气,循道而行,功夫由己不由物,自我主宰,这是十分简单、明白的要求,但要进入“道”的境界则要摒弃一切个人名利、荣辱及人事往还,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4]139。总的说来,儒者多为典章,乃至势位、名利等外物牵掣;道者惟需抱朴守一、自我约束,故从己之“道”易而难进其境,依人之“儒”难却易知其说,于是葛洪选择了从“道”而不依“儒”。
此外,葛洪还对儒、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出具体的分析和选择:“故道之兴也,则三五垂拱而有余焉;道之衰也,则叔代驰骛而不足焉。夫唯有余,故无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严而奸繁,黎庶怨于下,皇灵怒于上。”[4]186
他认为,循道家“无为”“不争”之道,则整个社会均在大自然的规律中运作,不断趋向与自然和谐。离开这自然的和谐,社会便会产生“怨”“怒”,所谓“法令明而盗贼多,盟约数而叛乱甚”[4]186,他因此得出结论:“道德丧而儒墨重矣,由此观之,儒道之先后可得定矣。”[4]186那么,在这个时期,葛洪是否舍儒而不用呢?答案又是否定的:“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尊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问伯阳,愿比老彭;又自以知鱼鸟而不识龙,喻老氏于龙,盖其心服之辞,非空言也。”[4]138
显然,葛洪并未全盘否定儒者之说。他认为儒家学说还是有可取之处,这就是移风易俗的社会责任,但葛洪终究认为孔子对老氏是心悦诚服的。
(二)对“玄”与“气”的认识
道家关于宇宙本源的“玄”与“气”是整部《内篇》展开的依据,葛洪通过对它的分析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什么叫作“玄”?《畅玄》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眜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4]1
宇宙自然、人间万物的本源是“玄”,它涵盖并衍生宇宙间的一切,虽不可见知其形,不可真知其质,但它却影响着宇宙万物,参与宇宙万物的生长变化。可见在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上,葛洪已不满足于孔子儒家天地生万物的理论,要寻求比天地层次更高的宇宙本源。这种思维取向正是来自于对《老子》“道”本体说的思考。
《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5]73。老子视“无”作天地之始,视“有”为万物之母,而“无”与“有”均同出于“玄”,也就是“道”(1)“两者即谓有与无,有无实同出于道”,“‘玄之又玄’谓道”。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6]。显然,这个“道”统摄着“无”与“有”,所谓“无”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指天地未开、混沌之时,万物处于醖酿而尚未成形之际。《老子》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5]233“一”乃天地未开之混沌状态;“二”乃天地已分,即阴即阳;“三”乃阴、阳及阴阳之和合,于是而有万物,万物必具阴阳,阴阳又必以和谐状态处于万物之中[5]234-235。对《老子》学说的理解,尽管学术界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其所论的“道”与后来所说的“玄”是相当的,所以道家的学说亦可称之为“玄学”。葛洪的“玄”正是对《老子》关于“道”的描述:“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4]2,即是说,“道”必于内在修养而达到“微妙玄通,深不可识”[5]129的境界才能显现其真谛。若其情为外物所惑,不能守“无为”“无欲”之德,必遭“败”与“失”,这与《老子》所谓“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5]188“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5]212,并无本质差异,唯《老子》把这叫作“复归于朴”[5]183“朴散则为器”[5]183,葛洪则称之曰“用之者神”“凡言道者,上至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4]185,这个“朴”或“神”是万物生生变化的本体。
《老子》重视“一”,葛洪同样亦重视“一”:“道起于一,其贵无偶”[4]323,又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4]323。葛洪所说的“一”其实就是《老子》“道生一”的“一”,有时他又把这个“一”叫作“玄一”或“真一”[4]324-325。葛洪重视“一”固然是道家思想的承传,但更重要的是,在《老子》思想体系中,“一”乃“道”在“阴阳”相生中的必然过程,主要表现为分阴分阳而互相对待的“气”,这个气充满宇宙,关系着人与万物的生生死死。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养生,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4]114
作为宇宙万物生生变化的本体,“玄”或“道”是至高无上的境界;在具体人、物当中,“气”则占有至为重要的位置。“气”不但主理人、物的生生,更可以驱邪役物,延年益寿。这就是包括葛洪在内的道家主张通过养气而达延年益寿的根据。
(三)因探求生命之真而误信神仙的存在
葛洪没有否定神仙的存在,甚至认为凡人通过不懈的努力也可成仙。这个认识当然是错误的,然而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笔者认为,对葛洪神仙之说,只是用“方术”或宗教宣传去解释[4]序言7是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的。道家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7]。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永远也不可能对客观世界有全面彻底的认识,凭其有限的知识而断定客观世界中孰有孰无,极可能是错误且危险的判断。对“神仙”之是否存在的认识,亦如是。葛洪指出:“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4]12
针对“无神仙”之说,他认为“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4]21。其立论的根据是客观世界无所不有,现在认为不存在的东西只是受认识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认识它而已;一旦我们取得相应的认识能力,获得认识的机会,原来认为不存在的东西就可能被认识,被掌握[4]12。葛洪这个估计颇能鼓励人们去了解客观世界,去探索未知领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处于比较粗糙、幼稚的阶段,葛洪“神仙”之说表现出在今天看来比较愚昧甚至是相当可笑的想法,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和谅解。
研究“神仙”“长生不老”之道,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然而葛洪却是旗帜鲜明地提倡科学(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反对迷信。他指出:“祭祷之事无益也,当恃我之不可侵也,无恃鬼神之不侵我也。”[4]177他揭露“巫祝小人妄说祸祟”骗取钱财的伎俩;主张通过养气健身,施用药石,达到消灾治病,拯救死亡的目的[4]172,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延年益寿。所以他又说:“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4]14葛洪对仙道的探求更多的是对人体保健,尤其是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可能性的研究。
他指出,世上的物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创造出新的物质,他举例:“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4]22所谓“铸作之”者,大概即是冶炼的方法。不唯“冶炼”可创造出世上本无的“水精碗”,而且“化铅”可生产出“黄丹”与“胡粉”,甚至可以通过驴与马的交配产出新的品属“骡”[4]22。根据这样的一些科技成果,葛洪相信只要不懈努力,什么奇迹都可能产生,甚至使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之药也可以炼成。
葛洪关于“神仙”“延年益寿”之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带有探索自然、了解人生奥秘的进取精神,然而最终却走进了追求仙人长生不老的误区。这固然是由于他对养生之道执着的追求,在理论指导上又未尽成熟所致。在浩瀚的宇宙中,未知见的东西不一定不存在,但也不一定就是必然已存在着的东西。葛洪却错误地认定了虽未知见“仙人”,但却或是存在的,于是就偏离了其理论的出发点,把对自然界客观的探索,衍变为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可能的逻辑错误。在葛洪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生命,人们只粗知其生,却不知其所以死;况且人之本性乃喜生而恶死,还不懂得一生一死、新陈代谢是宇宙的必然规律,是一切生命,包括人类自身发展、完善的必由之道,于是造成他从狭隘的感情和偏颇的认识去追求违背自然规律的长生,于是越陷越深。这应该说是时代的局限,也是葛洪的悲剧。
(四)对葛洪“神仙”“长生说”的再认识
葛洪关于“长生”之说,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对此,笔者准备多作一些正面研究。
葛洪懂得要寻求“长生”之道,首先要了解人为什么会死。他认为:“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夫逝者无反期,既朽无生理。”[4]110这固然是“形神相离”说的继续发挥,但他把“身劳”与“气竭”视作生命衰亡的原因,且认为生物一旦死亡则不可复生,无疑是正确的。他又说:“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4]112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对“长生”之道进行了不懈研究:“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4]114
通过“养气”来调节身心健康是传统养生之道,不但道家持此见,孟子更有养浩然之气的名言[8],即如韩非子也认为“是以死生气禀焉”[9]。可见,在传统认识中,“养气”是养生必不可少的条件与过程,葛洪则是从道家立场丰富了这个理论。他认为,要真正做到“养气”,必须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有清静的环境,远离凡俗之腥膻;二是必须为善不倦,不可喧哗而合污秽。他指出:“凡俗之闻见,明灵为之不降,仙药为之不成。”[4]187这显然是道家的“清心寡欲”说。同时,他认为当时的所谓名流只知酒醉歌舞,不知真正养生:“世人饱食终日,复未必能勤儒墨之业,治进德之务,但共逍遥遨游以尽年月。其所营也非荣则利,或飞苍走黄于中原,或留连杯觞以羹沸,或以美女荒沉丝竹,或耽沦绮纨,或控弦以弊筋骨,或博奕以弃功夫。闻至道之言而如醉,睹道论而昼睡。有身不修,动之死地,不肯求问养生之法。”[4]73这无疑是对以“清谈”为名、以身居“清流”为时尚,事实上却是穷奢极欲的混浊社会风气的公开指责和反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葛洪认为对“长生”的探求不应把“成仙”视作唯一目的,而应是为了“长寿”。“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4]53他希望能自足地过好每一天,做到“止家而不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他所表达的是能在世上活着总胜于在天上当神仙,可见其“长生”之道的最高境界是活着而不是“升仙”。“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4]53
葛洪认为,替别人排忧解难是为道者起码的道德行为,这种道德的修养比个人的“长生”“成仙”更为重要。“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4]53“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4]53
社会道德的培养不能光靠单纯说教或行政命令,只有建立在普遍、自觉的需要上,才有可能成为自觉的行动。葛洪以人们普遍关心的“生”“死”话题切入,提出“为善”“不为恶”,多为他人排忧解难等等道德要求,姑不论其出发点如何,其客观效果都是使人在“生”与“死”的选择中有自觉的道德要求。
在修炼学仙的问题上,葛洪说:“是以历览在昔得仙道者,多贫贱之士,非势位之人。”[4]19他认为历来权贵者多唯利是图,利欲熏心,根本不具备修炼仙道、延年益寿的条件。在道德品格的修养上,权势者远远比不上贫贱之士,这显然是对当时森严的门阀制度和“上智下愚不移”传统思想的大胆挑战。
葛洪对“长生之道”的追求,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可笑的,但他却是力求用当时所可接受的态度和方法去寻求答案。他认为,史书均有载神仙事,前人是不会胡乱编造的[4]46,他完全相信了前人的记载:“(刘向)所撰《列仙传》,仙人七十有余。诚无其事妄造,何为乎?”[4]16显然,这是对古人的记载缺乏分析,是盲从的表现,但却给了他探索“长生之道”的信念。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古人之说作为终点,他的注意力主要是用在以下两个方面:
他注意从对身边事事物物的观察中得到启发,作出推论。例如,他从“五谷”这些普通的食物能维持人的生命而联想到若有比“五谷”优良得多的“上品之神药”,则能维持人的生命“必万倍于五谷”;从“铜青涂脚,入水不腐”联想到服食金丹则可“沾洽荣卫”,使人长寿[4]71。也就是说,可以从改善人的饮食结构入手获得健康长寿的效果。
他又观察到“龟有不死之法”[4]48,其法是“道引”“食气”之术,“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4]51等等,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延长物体的寿命,因而他认为人的寿命亦可仿此而收到效果。这些方法虽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却给葛洪以启发与思考。事实证明,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不断改善生存环境和饮食结构,在科学的保养中人的寿命得到了延长。当然,葛洪希望人可以最终达到“不死”,这是不切实际的、非科学的想法,是时代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但他提出“若可止家而不死,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的理想,对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勉励人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葛洪由儒入道并由道而生发出对生命的思考,反映出儒家对当世生命的重视与道家对保养长生的追求,这两种思想构成了葛洪长生之道的特色,显现出科学思想的萌芽,但因其夹杂着不少带有天方夜谭式的幻想,而这种幻想又多为方术之士所利用,因而长期以来得不到健康发展。这不但是葛洪的历史悲剧,也是古代中国科学研究得不到健康发展的悲剧。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从这悲剧中发现其积极的、带有科学倾向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正确的方向上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天年的颐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