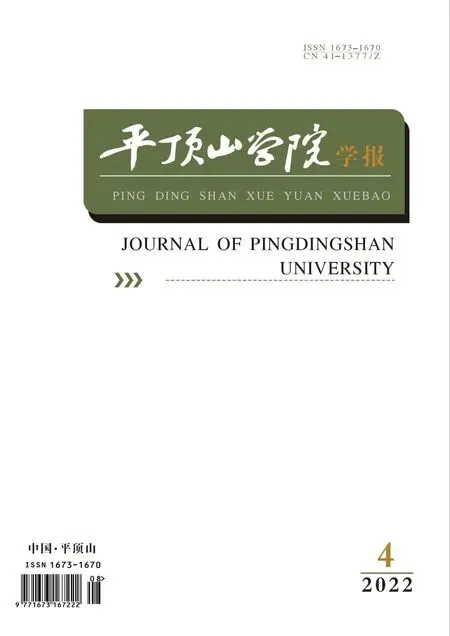从日本内阁文库藏叶宪祖杂剧看南杂剧之新变
隋雪纯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杂剧艺术在元代形成高峰后,至明代尤其中晚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南曲影响力逐步扩大和文人创作群体地位日益得到凸显,产生“南杂剧”(1)“南杂剧”首见于万历时胡文焕《群英类选》“南之杂剧”类,收程士廉《戴王访雪》和徐渭《玉禅师》,两者均用南北合套曲。吕天成《曲品》中亦有“不作传奇而南剧,传奇而作南剧者”一类,列举并品评徐渭《四声猿》、汪道昆《大雅堂杂剧》。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专列“南杂剧的出现”一章,将其作为与“北杂剧”对举的概念提出,意指明代兼用南北曲或专用南曲的戏曲形式。徐子方先生指出南杂剧“真正形成明中后期的杂剧独特面貌”,“在体制上创作出有别于元代及明初北杂剧,并为时代大多数作家所认同的模式”。狭义的南杂剧即由四折南曲构成的杂剧,与“北四折”相对;而广义则为包括南曲、北曲和南北合套曲在内的短杂剧,并指出以广义概念更为合宜。本文亦用其广义。的剧体形式,并在体制、内容、思想等诸方面具有新的时代特点。日本红叶山文库旧藏、现藏于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明代杂剧《易水歌》《三义记》《渭塘梦》《琴心雅调》,乃为明代杂剧的重要珍本,然目前对此少有专题研究。笔者拟以上述四种明代杂剧为基本对象,通过考述其作者及版本情况,以对其文本的具体分析为基础,考察叶宪祖杂剧的互文性与改编等叙事特色,并研究叶宪祖为代表的明代中晚期南杂剧的发展面貌、思想肌理及艺术新变,以就正于方家。
一、版本及作者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杂剧四种均为明万历刊本,版式相同,单边,无鱼尾,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宾白双行。仅《易水歌》题“槲园居士著”,且扉页钤有“飞鸣馆”“谭月主人”朱印,其余不署撰者姓名。“槲园居士”,据黄宗羲《外舅广西按察使六桐叶公墓志铭》,“槲园”为叶宪祖填词别号[1]。傅芸子先生《东京观书记》中首先对内阁文库所藏此四种杂剧有所关注和介绍;然其仅根据题款确认《易水歌》之作者为叶宪祖,虽指出《三义记》《渭塘梦》等“版式与《易水歌》相同”[2],但并未确证其撰者姓名。后叶德均先生首先指出后三剧亦为叶宪祖所作[3],黄仕忠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上述四种杂剧原应为一帙[4]。根据笔者考察,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此四种杂剧均见于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叶宪祖”名下,且《剧品》所陈述的情节梗概、回目与之均相合,此亦可作为叶宪祖为作者之一证。
叶宪祖为明嘉靖人,生平见于《明史》《浙江通志》《绍兴府志》。叶宪祖所撰戏曲共三十种,其中传奇六种,今存《金锁记》《鸾鎞记》;杂剧二十四种,除本文所涉及的四部以外,还有《骂座记》《寒衣记》《团花凤》《北邙说法》《四艳记》等尚存于世。此外,《明史·艺文志》还载有其所著《大易玉匙》,明代许运鹏辑其作品《青锦园文集选》五卷,存天启刻本残卷。日藏此四种杂剧,《琴心雅调》《三义记》《渭塘梦》均为海内外孤本,但传世书目和剧评类文献均有著录:
《三义记》,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题作“《三义成姻》南北四折”[5],清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乐府家之三”亦存目。《渭塘梦》,亦见于《远山堂剧品》,《奕庆藏书楼书目》“乐府家之三”记之,用南曲,凡四折。《琴心雅调》,分上下两卷,每卷四折,不题撰者姓名。《远山堂剧品》著录此书并记“南八折”,著者叶宪祖;吕天成《曲品》卷下论陈济之所著传奇时提及“吾友叶美度有《琴心雅调》八卷”;《奕庆藏书楼书目》《重订海曲目》和《曲录》亦载此书。
《易水歌》,《远山堂剧品》著录叶宪祖作品有“《易水离情》南北四折”,《盛明杂剧》[6]卷十亦录有此剧全文。首先,从时间先后看,现存《盛明杂剧》最早为崇祯时刊刻,内阁文库本为万历刊本,时间上更为早出。其次,从文本对比看,内阁文库本有段首开场白叙全剧梗概及作者旨归,为《盛明杂剧》本所无,为该本独特价值的重要表现之一。最后,内阁文库本的人物布设更为详细,如燕太子“金冠蟒衣”、樊将军“冠带”等。此外,内阁文库本每折下均标有“用某韵”,为《盛明杂剧》本所无。又“我两人自去罢”一句,内阁文库本“我”作“俺”,与言说者高渐离在文本中其余宾白自指的称谓方式一致,应以此为当。更重要的是,《易水歌》与《盛明杂剧》相较,讹误较少。如“颇好游侠,读书击剑”一句,《盛明杂剧》本“击剑”作“击筑”,按文意有徐夫人赠利刃以助之刺秦一节,合文中又述及“与善击筑的高渐离”,故当为“击剑”非“击筑”;又“把樊於期首级撇出宫门”一句,《盛明杂剧》本“撇”作“撒”,根据文意应以前者为当。由此可见内阁文库本应较《盛明杂剧》本更接近作品的原貌。
综上,内阁文库所藏四种明代杂剧应均为叶宪祖所作,三种未标著者的杂剧当与《易水歌》原为一书,盖在流传保存过程中散离,故除《易水歌》当为第一编外,其余顺序无法确知。又国内传世文献中《三义记》《渭塘梦》《琴心雅调》仅存目,作品文本均已亡佚。曾永义先生论明杂剧之分期及特点颇为详切,然至论《渭塘梦》则云:“仅万历间有刻本,日本内阁文库庋藏,一时无从觅读。”[7]422《古本戏曲丛刊》编印多种传世善本珍贵椠,然“像国内已无传本而流入东瀛者,如叶宪祖的《渭塘梦》《琴心雅调》《三义成姻》均系海内孤本,还未能收录进去”[8]。笔者即意在详考此四种杂剧文本,通过校考其与国内传世文献、原始文本的互文与改编关系,反映明代南杂剧的发展特点及叶宪祖等明代文人之精神风貌。
二、内阁文库所藏四种杂剧的跨文体互文性
杂剧多有本事出处,并在汲取前代题材类型、人物塑造和叙事方式等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在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及不同文体之间形成“互文性”[9]。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四种杂剧的题材特色在于均来自史传或小说,并经由叶宪祖进行重新组织并加以艺术润色而成杂剧。根据其作品取材来源,可分为两点:
(一)本于历史而演绎之
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四种杂剧中,《易水歌》和《琴心雅调》均本于史传而铺陈展演。
《易水歌》以荆轲刺秦为本事,除了着力表现荆轲的智勇双全的“矫矫英姿”,还同时塑造了与荆卿“情属投胶,谊称刎颈”的樊於期、“盛壮之时,颇不让人”的田光等一批英雄群像。通过“死者生之,败者成之”的方式,力图展现“荆卿挟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即事败身死,犹足为千古快事”,祁彪佳因此称叶宪祖为荆卿之“知己”。《琴心雅调》本于司马长卿与卓文君之事,本事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西京杂记》。该杂剧对以往戏曲小说作品的突破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即由片段式转为“全记体”。杂剧正体,一般以四折为主,然《琴心雅调》则八折,分上下两卷,《远山堂剧品》释云:“玩其局段,是全记体,故必八折。”《琴心雅调》的篇幅长度是由其采取“全记体”的结构方式决定的。相对于前代同题材作品而言,叶宪祖此剧较全面地展现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识、相许、相离到重会的过程,对史传及前代文学创作中的相关作品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借鉴吸收:
杂剧第一折“挑琴”(论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相如奏《凤求凰》引得卓文君倾心)、第三折“涤器”(两人从成都至临邛开酒铺、当垆涤器)、第五折“献赋”(记司马相如作天子游猎之赋,拜文园令兼中郎将)以及第七折“交欢”(卓王孙与程郑二人拜贺相如)均本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九折“重聚”(文君作《白头吟》自绝心恨之时,长卿衣锦归来,二人欢聚)中卓文君作《白头吟》事初见于《西京杂记》“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10]。卓文君私会相如事,《史记》中仅有“文君夜亡奔相如”七字。《琴心雅调》情节大体与明宁献王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多有重合,然后者仍保持四折体例,第二折与《琴心雅调》第一、二折,第三折与《琴心雅调》第三、五折,第四折与《琴心雅调》第七折基本一致。《琴心雅调》第二折“奔凤”(论卓文君私出闺房至长卿行馆)盖出自话本小说《风月瑞仙亭》卓文君夜至相如所在瑞仙亭,与之“同赏月,饮三杯”[11]的情节;第四折“题桥”(叙长卿欲上长安献赋求用,与文君在升仙桥相别)、第六折“还乡”(司马长卿重过升仙桥,实现当初“题此桥柱,云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的誓言)盖出于杂剧《升仙桥相如题柱》。由此可见,叶宪祖将既有的史料和相关作品进行了整合和剪裁,遂成此剧。
叶宪祖的“全记体”杂剧创作结构不取杂剧惯用的片段式的呈现方式,对于杂剧“折惟四”“但摭一事颠倒始末,其境促”的规定有所突破,向“备述一人始终”[12]的传奇靠拢。虽然增加了折数和情节,然囿于杂剧篇幅的限制,相应使每折内容减少,但整体的表现容量仍有所增加,在更长的时空广度内呈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悲欢分合,用宾白如“娘子,自你家君分财之后,归家聚首,将及一年”、唱词如“【步步娇】宦味侵寻年来倦,几见青丝变”等作为折与折之间的转接过渡,展现纵向时间发展变化。
叶宪祖其他杂剧亦多有基于史实而改编者,如《鸳鸯寺冥勘陈玄礼》本于《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本传,展现“马嵬埋玉”之“千古幽恨”;《巧配阎越娘》中的人物郭史为五代间霸主能臣,而叶宪祖传以新声;另如《骂座记》演窦婴及灌夫事,见《史记》卷一百零七、《汉书》卷五十二本传等,均说明藉史以展演生发,乃为叶宪祖杂剧的重要题材来源方式。
(二)改编明人小说
叶宪祖杂剧创作亦多取材于同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杂剧孤本《三义记》《渭塘梦》均本于明人小说而改之。《三义记》应本于嘉靖间小说《刘方三义传》(夕川老人《花影集》),主人公名姓和主要情节均一致;《渭塘梦》之故事情节,最早见于明瞿佑《剪灯新话》卷二《渭塘奇遇记》王生与酒肆主之女梦中相会,佚名《王文秀渭塘奇遇记》(见《元明杂剧》)、王元寿《异梦记》与之情节相仿。
叶宪祖的其他作品亦多对小说有所取用,如《会香衫》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死生缘》即《金明池吴倩逢爱爱》,《丹桂钿合》本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素梅玉蟾》本于《二刻拍案惊奇》之“莽儿郎惊散新莺燕,龙香女认合玉蟾蜍”等。由此可见明代杂剧、传奇、小说等诸文体的互文关系及相互影响。
三、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杂剧四种的改编与创新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杂剧四种的改编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情节增改
叶宪祖杂剧与史传、小说等不同文体形成互文,但并不直接全部承袭既有文本,而是有意识进行情节重塑和调整。情节修改的直接动因来自叶宪祖的部分杂剧取材直接来自史传小说,需要配合舞台展演的需要。黄宗羲称其“花晨月夕,征歌按拍。一词脱稿,即令伶人习之,刻日呈伎”。叶宪祖“改编式”戏曲创作相比其原始素材,能够展现出其重视舞台表演的一面。如《渭塘梦》与其所本《剪灯新话》卷二《渭塘奇遇记》相比,体现出作者对人物出场方式的有意设计。率先出场的并非剧作主人公,而是“家住横塘渭水漥,醉乡深处做生涯”的店小二,通过其口述“有个贾员外,家赀富足。我小二领得他些本钱,便赁他两间门房,开个小酒店度日”,引出贾员外,为贾姝子出场铺垫;同时,“住居又幽雅,铺面又斯文”酒肆场景的设立为王仲麟与贾姝子见面亦提供了地点准备。这种以丑角上场插科打诨式自语的方式,能够聚焦画面,有助于剧作表演过程中的吸引力和趣味性,强化舞台效果。
与《渭塘梦》情节相近的有同出于明代的《王文秀渭塘奇遇记》(存孤本《元明杂剧》),演王文秀、卢玉香渭塘相悦,分别后于梦中定终身。涉及王、卢梦中相见的叙述较为简略,仅为“是夜遂梦至肆中,入门数重,直抵舍后,始至女室”,但无“梦游神”情节。实际上,该情节为叶宪祖《渭塘梦》对原作创作式改编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杂剧题目将“奇遇记”改为“梦”,可以见出有意突出梦境情节描写。题目正名即云“做小买卖的是店小二,结好姻缘的是梦游神”。梦游神在全部情节回目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杂剧并不直接写贾姝子与王仲麟梦中欢会,而是先设置梦游神、二鬼“勾魂”“摄魄”,并在第二折“梦聚”中率先出场。王、贾二人的姻缘正由于梦游神牵引才得以实现,后贾员外和魏妪觉察屋中异样,剧本同时展现鬼神与人间两界中不同角色的反应,设置梦游神和二鬼引导贾、王相会的始终,人物“急上”“推门嚷”“惊下”“复睡”“醒”等复杂多样的动作表现、紧张的情节发展和鲜明的戏剧冲突使画面更为充实丰富。在演员安排方面,使二鬼又同时一扮贾员外、一扮魏妪,充分根据角色“在场”的必要性调动分配演员,显示出作者对舞台设计灵活性的充分把握。另外如《三义记》虽以刘方和刘奇的情缘为主线,但开篇并不直接引入刘奇,而是在第一折述梅香试图勾引女扮男装的刘方,小厮又欲求爱于梅香的情节。并在第四折又照应以梅香自云:“我梅香只道二哥是个汉子,有心去惹他,谁知却是一个女儿。今与大哥做了一对,教我又好恼,又好笑。”颇有谐谑之感。
叶宪祖的杂剧创作虽然大量基于既有史实或文学作品,但乃为根据原故事框架进行进一步加工和虚构,且表现出较为明确的主动创作意识。这突出表现在《易水歌》开场白中,作者自道欲令观众“须教四座莫凄然”,“凭余夺得天工巧,壮士生还作剑仙”;且文末云:“撮出个壮士生还莫当做谎。”展现出较为明确的以虚构补益现实的观念。同时在结局方面,该剧将荆轲功败身死改为“荣归易水八方名畅”,且使秦王求饶道“使臣饶了寡人之命,寡人无不听从”,荆轲令其不再弄干戈、争强斗胜,悉返诸侯之侵地;最终与“仙班故友”王子晋同入仙界。给慷慨“壮士”以“剑仙”的结局,作者以“天工巧”的语言重新编排组织,有意与史传中的荆轲之结局形成背离,转悲剧为喜剧。叶宪祖其他戏曲如《金翠襄衣记》之于瞿佑《翠翠传》、《金锁记》之于关汉卿《窦娥冤》,亦均将结局改为团圆。此种以心统史、消解悲剧的行为得到了部分明代选本家和文评家的肯定,如祁彪佳将此剧列入“雅品”;《盛明杂剧》王玑评曰:“剑侠原诗剑仙,此下转奇而诞,觉更胜腐史一筹矣。”[6]然其虽稍快人意,但悲剧的庄严感与余情反丧失,故郑振铎先生评云:“子晋吹着笙,轲随之而去,这却是完全蛇足的故事。”[13]
另外此剧细节的处理亦见出作者对文本的重新构思意识。如荆轲刺秦中有关“利匕首”的记载,《史记·刺客列传》仅有“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14],叙述较简;然《易水歌》则将此情节改为剑客徐夫人“闻荆卿欲求利刃,特来相送”,且“常言宝剑赠与烈士,哪里要价”,说罢拂衣而去,且文末揭示徐夫人与田光、高渐离诸人均为上界剑仙,其出场均是为助荆轲成事。这使荆轲刺秦具有了“神助”的必然性。还有如《三义记》将《刘方三义传》中刘叟、刘媪去世后,刘方、刘奇和诗,刘方委婉道出实为女子,二人遂自成亲的情节改为刘奇见刘方题诗后,与刘媪商议,由刘媪问明实情,且终由刘叟、刘媪主婚成亲,“夫妇永不离,爹娘长自在”。使姻缘之喜更添一层天伦之乐,加强了剧作结局的圆满性。
(二)情节构思与剪裁
相对于明代传奇多用双线结构、更容易表现宏大题材,杂剧更为精简短小。叶宪祖杂剧在情节布设方面体现出艺术构思和匠心,通过详略剪裁、设置贯穿情节线索等方式,使中心突出,绘事写情亦能尽肖,从而“借四折为寓言”[15],心事感触具化入其中。
《易水歌》共四折,并不直接从荆轲刺秦之事入手,而是从荆轲与高渐离于酒肆畅饮倾诉“待时藏器佯狂游世”的英雄之志、遇田光奉燕太子之名请荆轲共谋秦而起笔。前两折围绕荆轲与高渐离、田光酒庐对谈,通过荆轲“江湖漂泊市井追随,逃名溷俗,纵酒忘机,喜来时,唱几曲短长歌,闷来时,洒几点英雄泪”等自白,塑造其飞扬才气、激烈衷肠。同时通过荆轲与燕太子金台饮宴,先后得徐夫人剑、樊於期头等,为刺秦造势。剧本第三折扣剧目“易水歌”题,全写荆轲“今日驱车辞易水,提刀向函关”,高渐离、燕太子丹前来送别之场景。第四折写刺秦之事则情节相对简单且紧凑。
《琴心雅调》虽多至八折,但每折均有一个中心情节,其他情节则作删削或略述。如第一折即从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起笔,相对于杂剧《卓文君私奔相如》第一折从相如“负着琴剑,去寻个出身”[16]开始叙述,中心情节更为突出,枝蔓较少。另如第三折“涤器”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被程郑眼见:“原来是大家子女露行藏,堪怜此劣相。我便对卓兄说知……小厮带马,到卓员外家里去。”而至第七折“交欢”,卓王孙宾白云“卓王孙为因女儿私奔长卿,当垆卖酒,甚是发恼。亏了程兄劝解,与他些小妆奁,不曾许他见面”,方将《史记》中“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一段补叙出。另外如司马相如在献赋得官之后的仕途及政绩,剧作并未直接展现,而是通过如“长卿致身青云之上”(王吉)、“不想长卿如今做了朝廷近臣,持节出使”(卓王孙)、“昨日闻他已为天子近臣,持节使蜀,甚是荣显”(卓文君)等人物宾白侧笔写出,使剧作详略得当,以中心事件为主,同时能兼顾细部呈现。《三义记》亦采取类似的处理方式,在其所本《刘方三义传》中,按照自然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刘叟收养刘方、刘奇之事,然叶宪祖之杂剧则将刘叟收养刘方作为前情,直接以刘方“改换衣装,抛离乡土”自叙开篇,戏剧化的情节有效提升了剧本本身的生动性和情节的吸引力。
此外,叶宪祖的才子佳人题材戏曲采用富有特色的物事意象联结全篇,如《琴心雅调》中的“琴”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结情之物,《渭塘梦》中的“梦”则为全剧情节发展的核心。青木正儿指出:“以物件维系姻缘事,此派盖出于《荆钗记》,至叶宪祖诸作造其极矣。”[17]在叶宪祖其他戏曲作品中,亦多用此法,如《鸾篦记》先后作为杜羔与赵文姝姻缘的聘物、赵文姝与鱼玄机友谊的信物、鱼玄机与温庭筠爱情的见证。其副末开场云:“看一对鸾篦分合,总关多少情踪。”《四艳记》即《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桂钿合》《素梅玉蟾》中石生题纨扇、章生拾绣符、权生买钿合、凤生赠玉蟾蜍,亦是以信物绾合才子佳人。祁彪佳称叶宪祖改编比原作“头绪甚繁而约之于一剧,而不觉其促”,认为其功在“情语婉转,言尽而态有余”,实则为对原故事的合理剪裁、叙述详略合宜之结果。
(三)转换叙述角度
叶宪祖在处理既有文本与杂剧创作的关系时,对叙事角度亦有所创新调整。如《剪灯新话》所录《渭塘奇遇记》从王生的角度叙事,写初见酒肆主之女而“怏怏登舟,如有所失”,以及夜至酒肆主之女室所见葡萄架、凿池、小木鹤、玉箫、金花笺等陈设,并最终与现实中重返酒肆时所见相印证,以为神契。而《渭塘梦》则主要聚焦于贾姝子一方的见闻与情感,从透过绣帘暗觑王仲麟饮酒“偶睹此郎,不觉情动”,到梦游神使其“况值秋夜萧条,甚样睡魔神,到得我眼皮来也”,“一时昏倦起来,不免强睡则个”。两人相会之梦被父母惊醒,发现“指上失了金环,掌中却有一个扇坠”,并自道“这相思病准准的要害了也”,到“病煞娇儿骨似柴”,以及最终王仲麟重过此地收租时“得谐凤卜,同飞冠盖”。尤其是第二、三折,由贾姝子完成大段唱白,表现女子“轻合轻离喜复嗔”的爱情心理。又如《琴心雅调》在行文过程中,多次从卓文君的情感与心理的角度出发进行刻画,如第二折“我想来不如私奔长卿,顿偿相爱之思,兼遂终身之托”,第四折道“长卿,长卿,何薄情至此!我今想他一回,又怨他一回,自怨一回,又自伤一回,真好难为情也”,到作《白头吟》以自绝的“含羞,自怨尤”之情等,均充分洞察女子的心灵世界,挖掘女子的叙述视角,为叶宪祖杂剧的改编提供了更大的再创作空间。
四、由叶宪祖的杂剧改编看明代文人南杂剧之新变
叶宪祖杂剧体现出的互文性及其别出机杼的改编方式正体现出明代中后期文人南杂剧的特色。明代杂剧经过明初转为消遣性的宫廷娱乐后,以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和十三年(1448)朱有燉、朱权去世为分界,明代杂剧结束了由御用文人、宫廷艺人和贵族藩王独擅的局面,在明代中后期进一步由贵族化向文人化过渡[18],“文人南杂剧”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通过叶宪祖杂剧的改编,可知明代文人南杂剧具有以下特征:
(一)体制南化
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四种杂剧,均对严格意义上的元杂剧体制有所突破和改变。首先,在音乐方面,四种剧本均不用北曲,《渭塘梦》《琴心雅调》用南曲,《易水歌》《三义记》兼用南北合套。其次,在篇幅方面,元人杂剧止于四折,或加楔子[19]25;而叶宪祖《琴心雅调》多至八折,分上下两卷。在形制方面更为自由,《琴心雅调》将折目列于卷首,正文无回目名称;《渭塘梦》每折均有标题;然《易水歌》《三义记》则每折无名称。最后,叶宪祖创作的文人南杂剧突破了“一人主唱”的传统体制,轮唱与合唱兼有。如《琴心雅调》第一折三段唱词,依次为生(司马相如)、外(王吉)轮流独唱与净(卓王孙)、末(程郑)合唱。多样的演唱形式增加了舞台的丰富性,也使不同人物的性格能够更加充分地展开。《三义记》《渭塘梦》均以合唱作为剧作的尾声,众声和谐齐发,更有助加强“大团圆”结局的感染力。
(二)剧本案头化、文章化
元杂剧作者生活阶层和文化教育水平不甚高,多半有做子弟的本领,偶倡优而不辞;而至明代,原本的庶民之戏曲,移入古典文学修养较高的贵族和士大夫之手[7]85。叶宪祖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又先后任工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四川顺庆知府、广西按察使等。作为士大夫阶层,其杂剧创作与改编带有较为鲜明的案头化、文章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取材方面,本乎史传和文人小说。《易水歌》中荆轲不负刺秦使命,“荣归易水,八方名扬”;《琴心雅调》中的“当今才子”司马相如得文君为妻,并实现“圣主贤臣会合风云共”的志业,致身青云之上;《三义记》中刘方、刘奇同为“两个傅粉的郎咏絮的才,完成了锦片前程大”,终成眷属;《渭塘梦》中的王仲麟秀才“家本高门,素饶风度”,且有“华笔梦江淹”“青山供谢朓”之才情。可见叶宪祖所取用的题材以士人为主要书写对象,着重关注士人的爱情生活与功业理想。
其次,杂剧在宾白中插入诗词。如《渭塘梦》第二折“梦聚”中,贾姝子化用李煜《相见欢》。又如《琴心雅调》第二折“奔凤”中,生(司马相如)宾白引《诗经》表现自己对卓文君的盼望:“曾奈一时不得到来,教我好生盼望。真个‘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第八折“重聚”,卓文君引《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有助于烘托作品的氛围,同时调节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节奏。《易水歌》中,先吟诗后自报家门,成为人物出场的标准范式。其插入南朝鲍照,唐代王维、李颀、王昌龄、王建、贾岛,宋代苏轼等的作品,使杂剧文本构成内部跨文本互文性,有助于唤起读者对原诗词的记忆,从而拓展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四维空间[20]。叶宪祖多根据人物性格和遭际而用诗摘引,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形象塑造和情节暗示等作用。同时,将名诗作契合剧情的改编,更能与意境融合无间,表情达意简洁宛转。如《易水歌》中酒保上场化用王维《少年行》,并将原诗“新丰美酒斗十千”之“新丰”改为“金台”,与第二折燕太子请荆轲在“缥缈层台,势凌空列星堪摘”的金台饮宴情节相照应;“咸阳游侠多少年”之“咸阳”改为“幽州”,与燕国地理位置一致,能映衬烘托杂剧侠义慷慨的氛围,见出作者的独出心裁。
叶宪祖杂剧中往往有隽语,穿插安置在人物宾白唱词中。这实则蕴含了作者对于世态人情的理解,亦藏有作者的感喟与襟怀。如《琴心雅调》卓王孙云“俗情皆慕势,肉眼岂知人”,司马相如谓“大丈夫志气应非小”,“羡为龙扬鬐沆漭,欲抟鹏奋翮扶摇”。《三义记》刘叟宾白“人心却如面,岂得两相同”。《剧说》云叶宪祖《鸾篦记》“借贾岛以发二十余年公车之苦”,这固然是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的表达,同时亦是作者心志的抒发。
(三)守伦常中求“情”
在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诸杂剧中,《渭塘梦》之“情”得到尤其突出的表现。王仲麟和贾姝子“一面情缘,百年姻契”,两人隔帘相望而暗生情愫,因情动而梦中相会,贾姝子为“无端情绪,扰人方寸”所困而“染成一病,没情没绪,如醉如痴”,最终因情终成眷属。贾姝子自云:“想我二人情缘深重,致此异事。”
叶宪祖对“情”的重视,或来自汤显祖的影响。汤显祖颇为重情,《牡丹亭》作者题词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其自道:“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又云:“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21]将情作为作品生发的动因,并以为有情则“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将情置于“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22]的地位加以推重。《渭塘梦》颇有模仿传奇《牡丹亭》的痕迹。生旦情缘,均全在一梦。在情节方面,亦同将婚配之事设置为神祇之命。贾姝子与王仲麟由梦神主婚配,颇同于《牡丹亭》中南安府后花园花神主柳梦梅、杜丽娘二人情事。在角色方面,两剧中的女子均为痴情所困,《牡丹亭》中杜丽娘因“害的是春前病”而“一搦身形”,“好看惜女儿身命,少不的人向秋风病骨轻”;贾姝子为情相思成病,形容枯槁。姝子因见仲麟而病除,丽娘因寻梦梅复生。
对角色真“情”的追求,有助于对心灵世界的挖掘,展现更加丰富的性格侧面,从而使叶宪祖所塑造的人物言语举止更合乎情性本色。如同为女子,《琴心雅调》中的卓文君、《渭塘梦》中的贾姝子、《三义记》中的刘方和梅香,身份性格迥异,故语气行事也各有特点。卓文君为端庄闺秀而勇敢追求爱情:“我想来不如私奔长卿,顿偿相爱之思,兼遂终身之托。”贾姝子为矜羞碧玉,自谓“奴在深闺娇养,似柔枝新长”,梦中见到王仲麟,则“腼腆羞认”。刘方假扮为男子,故用词更为豪放:“要做木兰女替父从军,却恨严亲去世;便学得苏蕙姬回文织锦,难教夫婿封侯。”梅香为佣人,追求感情大胆泼辣,对倾慕的“二哥”则云“如今深秋天气,倒得我来和你相陪才好”,对小厮则道“不是癞蛤蟆想天鹅肉吃么”,爱恨喜怒颇为分明。不同类型的角色“密约之情,宛然如见”。
需要指出的是,叶宪祖还受到吴江派沈璟的影响。吕天成评其戏曲创作:“景趣新逸,且守韵甚严,当是词隐(沈璟)高足。”而沈璟戏曲“命意皆主风世”[23],多蕴以伦理教化和惩劝内涵。这使叶宪祖杂剧虽然体认“情”之生发与存在的合理性,但其以伦理秩序为必要前提。就内阁文库所藏杂剧四种而言,《琴心雅调》程郑对司马、卓氏当垆涤器的评价是“大家子女露行藏,堪怜此劣相”;《三义记》中刘方、刘奇之结情终须“爹妈如此玉成”而能成就良缘;《渭塘梦》王仲麟与贾姝子虽梦中幽会,然两人之好,得于梦游神主婚配,“百年夫妇明朝定,一段姻缘天上来”。且剧中魏妪还取笑自己的女儿“难教官法饶人,当做先奸后娶”,可见两人私下相会于礼法定然有违,托之于梦境,真假相生,方暂成立。
叶宪祖杂剧重“情”置于伦理秩序之下的特点,还表现在将“情”的宣发与教化相结合,部分杂剧突出伦理教化或惩劝风世的主题。如《易水歌》结局仙人王子晋云:“荆卿还不晓得,燕太子宿世有恩于你,数当报效。”将荆轲刺秦的义勇行为解释为现世轮回和因果报应;另外如《琴心雅调》虽采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之事,但不取《西京杂记》所记“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衣裘贳酒’”等,而道“事君子终身倚仗,操箕帚妇随夫唱。才郎自合登卿相,暂贫窘君何悒怏”,将人物意识中的卿相利禄、夫妇伦常观念放大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个性和表现力。王国维先生论云:“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为元人所独擅。”[19]85思想主旨的平板化、整饬化导致情节设置失于牵合,从而无法恢复元杂剧“写人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的境界。
实际上,伦理秩序辖制内追求“情”的特点,实则反映出以叶宪祖为代表的明代中晚期文人面对自身命运浮沉与国家社稷之忧的双重精神困境。《明史》载叶宪祖睹魏忠贤建生祠,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而被魏削籍,其行耿介磊落可见。又作《捶钱赋》,通过“非幼非壮、不范不模,违错刀之金饰,类綖环薄肤”的“劣钱”之“不才见弃”命运,抒发“余乃喟然太息,有感斯人一经废置,复进无因”的人生感受,并曰:“吾所愿者……使夫成毁,一好丑齐,尔各适其用。”叶宪祖从自身关切至士人的整体命运,亦见出其幽愤悲切的精神状态,以及担当天下道义的情怀。叶宪祖杂剧中以梦神成就一面情缘、助荆轲完成刺秦大任并登临仙界等改编,将“前程远大”与“洞房春色”在杂剧中实现两全,并通过人物之心与口,宣泄精神,挥洒情致。与此同时,经世人伦、修齐治平的轨范又在另一方面使叶宪祖牵引着张扬的人性与飞扬的精神适应伦理的“正途”,也由此导致叶宪祖“情”的表现最终回归于伦理秩序的合理性,回归“夫妻不离,爹娘自在,金榜题名”的普遍结局范式。
五、结语
通过对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宪祖所作杂剧《易水歌》与孤本《三义记》《渭塘梦》《琴心雅调》的考察,可知叶宪祖杂剧取材的特点:辑采史传而重构之,体现出叶宪祖的主动创作意识和创造力。其将明人小说搬演至舞台,可见明代小说文体对于戏曲的重要影响。其杂剧创作体现出明代中晚期文人杂剧体制南化,剧本案头化、文章化等特质;形式上的古与今、风格上的雅与俗、内容上的情与理,共同构成明中叶以后文艺发展的内在动力[24];此三组特点亦同时并渗透于叶宪祖作品文本之中。通过叶宪祖杂剧的互文性与改编,可以见出明代小说、杂剧、传奇等多种文体的互动与生成关系与跨文体的叙事传统,并可窥见中晚明时期文人在伦理规制下,以通过南杂剧的创作实现对“情”的追求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