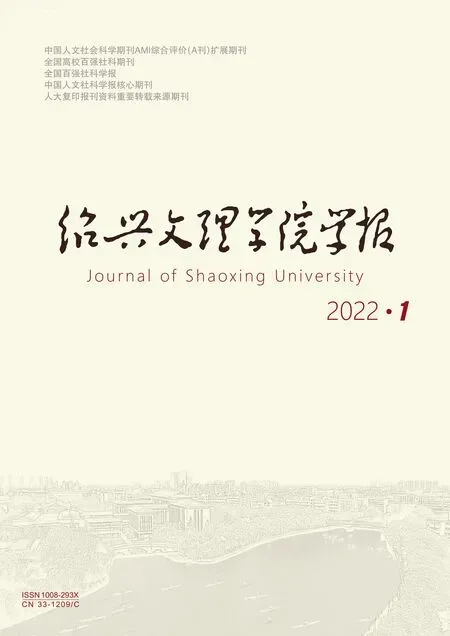张裕钊、吴汝纶交游考论
李松荣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又字至父(甫),安徽桐城人。学界对二人的单独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但关于二人的交游情况,却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从《吴汝纶全集》《张裕钊文集》《桐城吴先生年谱》《尺牍续编》《中国学报》等文集、年谱、报刊中辑得二人交往书信83篇及诗文十余篇,借助这些原始文献,试图较为清晰地还原张吴二人的交游脉络以及交流过程中由于性格相近、志趣相投而形成的较为相近甚或趋同的文学、学术、教育思想。
一、张、吴二人交游的基本脉络
(一)初识曾幕(1868)
曾国藩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1]13442张裕钊、吴汝纶的相识,也因曾国藩而起。同为曾门的优秀弟子,两人常常从曾国藩的言谈中听到对对方的称赞。但由于年龄的差距,两人并没同时在曾国藩幕府任职。同治七年(1868),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因想念在鄂城书局供职的门人张裕钊,特意写信让他买舟东下到金陵一聚。而此时吴汝纶正在曾幕任职,于是,两人终于相见了。张裕钊在给吴汝纶父母亲六十岁大寿的寿序中回忆了他们初次见面的场景:“裕钊往者则闻桐城吴侍读至甫善为文,常欲一识之,不可得。同治七年秋来江宁,乃晤至甫相国曾公使署,索其文读之,诚辨博英伟,气逸发不可衔控。”[2]70吴汝纶在日记中也写道:“九月朔阅张廉卿文。廉卿湖北武昌县人,名裕钊。所为文多劲悍生炼,无恬俗之病,近今能手也。”[3]8可见,两人一见面就以文事互相推许,颇有惺惺相惜之感。第一次见面以后,由于吴汝纶要回乡省亲,就于该年九月十四日离开了金陵。十月十二日,回到金陵的第二天,吴汝纶就与张裕钊相约秉烛夜谈,共论文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夜与张廉卿久谈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其谓‘气脉即主意贯注处’,言最切当。又谓‘为文大要四事,意、格、辞、气而已’。”[4]289事隔三日后,又在日记中写道:“与张廉卿、方存翁夜话,畅言文章,兼及经史。”[4]289张吴这期间的频密交往,持续到该年的十一月份,因为曾国藩要北上出任直隶总督,吴汝纶也跟随北上,而张裕钊则返回鄂城。从此二人天各一方,只能以书信互通,探讨文事。
(二)再晤金陵(1869—1882)
张吴二人于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分别以后,吴汝纶随曾国藩北上处理天津教案等事,直到同治九年(1870)底才回乡度岁,而张裕钊这段时间仍供职于鄂州书局。这期间他们由于南北相隔,又各自行程不定,杂事繁多,所以现存的交往书信仅有一封全面阐述张裕钊文学思想的《答吴至甫书》。
到了同治十年(1871),张裕钊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在金陵凤池书院谋得一教席,在此间开始了长达11年的执教生涯。而此年二月,吴汝纶正好准备从家乡出发,携同家人往深州任职。于是他在北上的途中先赶往金陵拜见了曾国藩和张裕钊。他在日记中写道:“至凤池书院,与廉卿留连竟日,鬯论文字。”[4]289之后,他北上深州,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官宦生活,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他因父亲吴育泉逝世才扶丧南归。这两年间张吴二人是否会面或者互通音信,由于文献不足,已经无法考证了。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至光绪元年(1875)七月,吴汝纶在苏州巡抚张树声幕府任职,期间曾请张裕钊为他的父亲作了篇墓志铭。光绪元年七月十四日,吴汝纶因母亲逝世,回乡治丧。居乡期间,作诗荐同乡马其昶拜于张裕钊门下,诗云:“张子濡大笔,淋漓坐小阁。……吾徒有马生,暗室夜求烛。若令扫公门,籍湜倘可续。”[5]398张裕钊收到来信后,立刻以诗答之:“君才霄汉上,璀璨五云阁。……枝道得奇宝,遗我不顾俗。一见为眼明,鼌采昭炳烛。”[2]299从这两首赠答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吴对对方人格和文学成就的敬仰以及对人才的珍惜,从此以后,张吴二人开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合作。
光绪二年(1876)五月,吴汝纶由家乡北上天津,期间又先绕道金陵探访张裕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留七日,读廉卿近著文,视前益奇。留凤池书院,与之盘桓连日,临别尚依依也。”[4]290从这“盘桓连日,临别尚依依”的依恋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几年的交往,张吴二人已经成为性格相契、志同道合的知心好友。
光绪四年(1878),吴汝纶因回乡营葬父母,路过金陵又拜访了张裕钊。并且作有《北征别张廉卿即送其东游》[6]7二首,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汝纶对张裕钊的为人和性格都非常了解,认为他的为人和文章可与汉代的扬雄相媲美,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之把酒论文。
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七年(1881),吴汝纶一直在北方任职,而张裕钊则在金陵执教。这期间两人仍然保持通信,但由于文献不足,他们这段时间的交往已无从考证。
直到光绪八年(1882),时任冀州知州的吴汝纶因张謇的推荐,拟聘当时正在给张裕钊当助手的范当世主冀州信都书院讲席,于是写信给张裕钊,请求张裕钊让范当世“遨游张吴之间”[3]32。这时的张裕钊已经辞去了凤池书院院长的职务,心中难免郁郁不得志,于是在给吴汝纶的回信中透露了他心中的愤懑和对友人的思念。可惜,此封信件没有保留下来,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信中所附的两首诗歌,来了解当时张吴二人的交往。这两首诗,第一首主要是因吴汝纶的来信“每有论文语”[2]342,所以有感而发,指出当世贤愚不分,牛骥同槽。第二首主要表达对当时举世混浊的批评和对高尚人格的坚守,特别是“茫茫人海劳天问,渺渺予怀独子悲”[2]342这两句,更是道出了作者与友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度契合。吴汝纶在光绪八年(1882)十月三日给张裕钊的回信中,对这两首诗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他说:“前接手示,并惠诗二律,气格高妙,魄力雄伟,数百年无此等。盖山谷、遗山以后,不见替人久矣。”(1)此信《吴汝纶全集》未收录,系笔者查阅比对民国年间吴闿生编的《尺牍续编》发现。《尺牍续编》共四卷,刻本,所收信件三百多封,部分未收入《吴汝纶全集》。关于《尺牍续编》的编撰情况,笔者将另撰专文进行探讨。此信中说:“前闻张季直言及鄂中修志,执事主裁范君应留相助。弟谓轮船往来最便,南北可以两兼,敝处笔墨及尊处皆无须镇日相守,季直谓当以此意转达”。查《桐城吴先生年谱》可知吴汝纶写给张季直的信在光绪八年(1882)七月十七日,则可知此信也作于光绪八年,又信中已标明作于“十月三日”。则此信应作于光绪八年十月三日。
光绪八年年末,因黄彭年离任,莲池书院一直缺新院长,吴汝纶就向李鸿章推荐了张裕钊。吴汝纶在该年十二月十四日给张謇的信中说:“近日李相、振帅同意聘请廉老都讲莲池,廉若不来,鄙人尚拟自媒,倘得此席,吾可终老矣。廉老处弟亦有函劝驾,渠来亦吾所深愿,此二策者将必有一可。”[3]33从信中我们可知,吴汝纶在光绪八年末又给张裕钊写了一封信,劝他北来出任莲池书院院长,只是此信现已散佚。在与张謇的这封信的末尾,还有一段按语:“濂亭自是主讲莲池书院,明年四月到馆。”[3]33从此,张吴二人同处一省,相距只有数百里,相聚与书信往来自然更加频繁。
(三)保冀深交(1883—1887)
这段时期是张吴二人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张吴二人交往的信件据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有83封,其中有66封都是作于这段时期。而且由于保定和冀州两地相距不过数百里,所以这5年里,他们几乎每年都相聚一次,每次欢聚少则数日,多则连旬,内容多是畅论经史或诗文唱和。下面依照时间的顺序,将他们这5年的交往做一番梳理。
光绪九年(1883),张裕钊从水路北上保定莲池书院任职,途中,他写下了《舟中杂咏》《舟赴天津计日与至甫相见》等诗歌来描写沿途的景色和表达自己的心境。其中《舟赴天津计日与至甫相见》这一首,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迫切希望与友人相见的心情。诗曰:“淀水东流去,羁愁相与长。夙心怀旧侣,暮气动新凉。一鸟飞寒水,数家明夕阳。晚来无限思,葭菼自苍苍。”[2]356-357诗意简洁,明白如画,但情真意切,情景交融,把对友人的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光绪十年(1884),张吴二人交往的信件达15封。这15封信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件:其一,这一年吴汝纶因官署中失盗,心中郁郁不乐,在张裕钊的多番劝导和鼓励下,才重新收拾心情,最后成功破获盗案。其二,吴汝纶把门下弟子贺涛介绍给张裕钊,张裕钊欢喜无比,次年来信回复说:“松坡,深感阁下遗我奇宝。”[2]467其三,在张裕钊的帮助下,范当世终于答应吴汝纶的邀请,于次年到冀州任教。
光绪十一年(1885),仅张裕钊写给吴汝纶的信件就有10封,而且期间还相聚两次。第一次相聚是在该年的一二月间,张裕钊由保定往冀州探望吴汝纶。在光绪十年(1884)九月十一日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弟块独居此,孤陋寡闻,寂寥少欢。足下又不得一来,明岁新正无事,拟灯节前后膏车秣马,径诣尊处,为一握手之欢,藉得尽豁积悃,如奉赠拙诗所谓‘剧饮狂谈碎百忧’者。足下闻之,当为大快邪!”[2]481在随后给吴汝纶写的几封信中,张裕钊又不断与吴汝纶商量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最后终于有了年初的冀州之行。从冀州回来以后,张裕钊非常高兴,写信邀请吴汝纶到莲池书院做客。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十三日给吴汝纶的信中说:“欢聚连旬,极快。闻阁下论古抉摘杳微处,使人智识增倍,尤为得未曾有。阁下来此,当更一极论也。”[2]465该年十二月,在张裕钊的多番催促下,吴汝纶最终携范当世到保定莲池书院做客。范当世在《燕南并辔》小序中写道:“余自冀州同挚父先生就廉卿先生于保定,车中困顿,舍之乘马,先生亦乘马,并辔相语,不知晓寒。”[7]114但是,这次师徒三人的欢聚并不长久,张裕钊在该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吴汝纶的信中感叹道:“此特造物妒我两人,不欲使久欢聚耳。不知我辈何所开罪,而造化小儿乃颠倒之若此。”[2]470-471
这一年张吴二人的交往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该年九月吴汝纶作了《李刚介诔》和《书符命后》两篇文章寄去请张裕钊批评斧正,而张裕钊在该年十月也作了《南宫学记》请吴汝纶指正。其二是该年吴汝纶还作了《依韵奉酬廉卿》[5]406二首,这两首诗对张裕钊用文自娱的生活态度非常欣赏,诗中说国家多事,当用行舍藏,可自己却未能决然隐去,远不如张裕钊之芥视一切。作者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张裕钊一样,决然隐退,从此娱文垂钓,不问世事。
光绪十二年(1886),张吴二人的交往信件更是高达16封。这一年的信件,主要讨论三件事:第一,劝范当世续娶。第二,探讨文学和学术。主要讨论为文时要注意的“声音之道”,《郊祀歌》的作者归属问题,以及与《易》有关的学术问题。第三,人才培养探讨。该年吴汝纶在州试中录取了神童李刚己,对李褒奖甚多,而张裕钊针锋相对地提出“大抵人才生之难,成之尤难”(2)此信《张裕钊诗文集》未收录,由笔者辑自民国年间创办的报刊《中国学报》第二期《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抄》,可参见拙文《张裕钊书札辑补》,《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8年第3期。的人才培养观。此外,在该年的中秋之后,吴汝纶又携范当世到保定做客,期间他们主要探讨与《易》有关的学术问题。但对于志趣相投的张吴二人来说,再长的相聚也是短暂的,张裕钊在该年十月十六日给吴的回信就说:“日者快接名论,一豁素襟,然终恨匆匆判襼,未能极畅耳。”[2]478
光绪十三年(1887),是张吴二人学术交流最为频繁的一年。该年二人往来书信达25封,超过他们5年交往书信的三分之一。而这一年讨论的文学和学术问题也特别多,按时间顺序大致归纳如下:正月至三月主要讨论与《易》相关的学术问题;四月至八月的书信主要讨论《禹贡》“三江”问题和《韩宏碑》《董晋状》是否有谀墓之嫌等问题;九月至十二月的书信主要讨论为文如何达到“顺成和动,自然入妙”[2]460的境界和《楚辞》某些篇章的作者归属问题。
(四)津门诀别(1888—1894)
光绪十四年(1888)是张裕钊在莲池书院任教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两人交往的书信有11封,前半年的书信主要还是讨论为文如何达到“顺成和动,自然入妙”的境界和《楚辞》某些篇章的作者归属问题。后半年的书信则主要商讨张裕钊的南归(3)关于张裕钊南归的原因请参见拙文《“枝蔓相萦结,恋嫪不可改”——张裕钊与莲池书院师生间的情谊》,《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和吴汝纶到天津送行等事情。这年十月,吴汝纶携同贺涛赶往天津送张裕钊乘船南归,并作《送张廉卿序》送别老友。文章第一段以往日张吴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为切入点,指出历史上“不枉实而谀人”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困顿不堪,以及他们的作品“往往诡辞谬称谲变以自乱”[5]73的原因。第二段回忆了张裕钊北来5年双方交往的情形,以及张南归的原因和自己对张的依依不舍之情。文中以深情写实的笔法叙述了五年来两人交往的点滴和对石友离去的不舍:“吾与之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每如此……独吾离石友,无以考道问业,疑无问,得无告,于其归不能无怏怏也。”[5]73而对于张裕钊南归的原因,却以曲笔书之,说张裕钊在北的这5年多,“自李相国已下皆尊师之”,张的南归,是因为湖北大吏走币相聘。其实,正如笔者在《“枝蔓相萦结,恋嫪不可改”——张裕钊与莲池书院师生间的情谊》指出的那样,张裕钊的辞席南归完全是迫于李鸿章的压力。吴汝纶对个中的内情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立场,他也只能“诡辞谬称谲变以自乱”,这也是他在文章第一段大篇幅称赞孙况、扬雄的真实意图,他希望后世了解内情的读者,能够读书而自得之,读懂他这篇文章所蕴涵的微言大义。其实,作为李鸿章的门生兼下属,吴汝纶对于李鸿章为一己之私迫使张裕钊辞席南归一事,更多的是无奈又无助。一边是师尊兼上司,一边是多年的文章知己,他能怎么办呢?或许,这篇赠序就是一种立场的表达。或许,只有像张裕钊这样的文章知己,才能读懂吴汝纶这篇赠序中所蕴涵的微言大义,也只有吴汝纶这位个性耿直,淡于仕宦的石友,才能真正理解张裕钊决然南归的原因。
光绪十五年(1889),张裕钊回到了家乡武昌,执教于武昌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十七年(1891),张辞去江汉书院讲席,改教于鹿门书院;十八年(1892)秋,由长子张沆迎至西安养老;二十年(1894)正月十四日卒于西安寓所,葬于宋儒张载墓旁。而吴汝纶在张裕钊辞席南归后,因机缘巧合接替了张裕钊的教席,从此开始了在莲池书院长达14年的教学生涯。在张裕钊离开莲池书院至其逝世的6年间,由于张裕钊行程不定,辗转南北,所以张吴之间通信不多。现能搜集到的书信只有两封。第一封是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十五日,吴汝纶到莲池书院任教后写给张裕钊的回信,主要向张介绍莲池书院的发展情况。第二封是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十日,张裕钊在鹿门书院任教时写给吴汝纶的,信件除了向吴叙述近况外,也表达了对老友强烈的思念之情:“与阁下相去益远,遂致书问阙然,然恋嫪之私,何日忘之?”[2]488
其实,吴汝纶也时刻关注着张裕钊的近况,竭尽所能帮助张裕钊寻找稳定而又报酬优厚的教席。这从他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二十六日写给两位友人的信件中就能看出来:“今武昌张廉卿,海内硕儒也……弟昨谋之南中旧游,意欲纠合十余人,人出百余金,延此公入皖,以为乡里后进师表,则文章之传,当复有寄。”[8]61-62“张廉卿之文,必传于后,今世人不知之,后世必有扬子云能知之也。今人多讲口耳之学,故自与为异趋耳。文章自有真传,廉卿死,则《广陵散》绝矣,区区之意,所为必欲罗而致之皖中也。”[8]63从这两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张吴之间深厚的友谊以及吴汝纶对张裕钊无私的帮助,为了给友人找工作,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人际关系,对于张裕钊的为人为文,也总是赞誉不绝。
光绪二十年(1894),在得知张裕钊逝世的消息后,吴汝纶悲痛万分,本想写篇祭文悼念好友,可是过了不久,贺涛就把写好的《祭廉卿先生文》寄来请他评点。吴汝纶觉得贺作“矜练缜密,气甚遒迈”[8]97,堪称祭文中的能品,自己再作一篇意义已不大,所以就搁笔不写了。但在张逝世后的第二年,当马其昶拿着收集成册的《张裕钊尺牍》请吴汝纶题字时,吴汝纶还是抑制不住对亡友的思念,写下《题马通白所藏张廉卿尺牍册子》一文以纪之。文章前半部分记述了二人交往的一个片段:吴汝纶认为张裕钊“书即工,世不求,无所托以久,身死而迹灭矣”[5]114,而张裕钊却想到“沉碑凿壁”以应对,并俏皮地反问道:“子且奈我何!”通过简单勾勒回顾二人交往的趣事,表现了对亡友无尽的思念。文章后半部分睹物思人,认为老友“所著文章与所作书具在”,无俟于沉碑凿壁也能传世行远。斯人已逝,自己只能对其书札“时时展对,以释吾思”[5]115,就像匠石失去郢人,庄周失去惠施一样,那种失去挚友的悲痛与无奈,或许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深切体悟到。
通过以上一番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张吴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相识、相交,并非依靠金钱或名利来维系。他们能够成为终生不渝的石友,固然是因为性格相近——都是那样的刚介不俗、淡于仕宦、安贫乐道,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志趣相投,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学、学术、教育思想。
二、张、吴二人的文学、学术、教育思想
(一)文学:宗于桐城,有所变而后大
张裕钊、吴汝纶都曾师事曾国藩,虽问学有先后,但文学思想均深受曾国藩影响。宗于桐城,又不囿于桐城,实现“有所变而后大”,是后期桐城派论文的一大特色。从宗于桐城来讲,论文从“声音证入”,强调讽诵、熟读之功可以说是桐城派学文的不二法门。从刘大櫆的《论文偶记》,到姚鼐的《与陈硕士》,再到曾国藩的《谕纪泽》,所强调的都是声响和诵读在学文中的重要性。张裕钊在《复黎莼斋》中说:“至甫亦屡以文相质,其所不足者,亦是声响不能尽合。弟每报书以为盖坐讽诵之功未至,但多熟读,久之自尔动合自然。(原注:以所见如曾文正,所闻如刘海峰、姚惜抱、梅伯言,盖莫不专精讽诵,是其明征。)”(4)此信《张裕钊诗文集》未收录,由笔者辑自民国年间创办的报刊《中国学报》第三期《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抄》,可参见拙文《张裕钊书札辑补》,《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8年第3期。张裕钊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一方面是自己在学习与创作过程中的个人体悟,一方面则是对桐城先辈为文经验的总结。所以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件中,屡屡强调的也是声响与诵读:“昔朱子谓韩退之用尽一生精力,全在声响上著工夫。匪独退之,自六经、诸子、《史》、《汉》,以至唐、宋诸大家,无不皆然。近惟我文正师深识此秘耳。”[2]476“要而言之,曰声调而已矣,熟读而已矣。”[2]484而吴汝纶对于张裕钊的意见,也深表认同:“昨接来示,于文章之事深怀诱进之意,至为感佩。”[9]可以说,张吴二人在为文强调声响和诵读这一点,是有共识的,这是他们对桐城先辈为文之法的一种传承。但在宗于桐城的同时,对于桐城文偏于孱弱的弊病,他们又有所突破和扬弃。而这种突破和扬弃,也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形成的。
桐城古文发展到曾国藩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行文单薄、规模狭小、萎弱颓靡等弊端。曾国藩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桐城古文,主张打破方苞所定下的“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10]890的为文禁忌,在古文创作中“参以两汉古赋”。张裕钊和吴汝纶为文的思想都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曾对张裕钊说:“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11]934吴汝纶在《与姚仲实》中对曾国藩主张参以汉赋的做法大加赞赏,他说:“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8]51-52除了在古文创作中参以汉赋,曾国藩还提出了“为文全在气盛”[12]的口号。这一论断也得到张吴二人的认同。吴汝纶在给张裕钊的信中说:“窃尝以意求之,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为抗队、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申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机势之自然,非必有意于其间,而故无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气之未充者也,执事以为然乎?”[8]36张裕钊在接到来信不久后就回复:“足下所谓:‘才无论刚柔,气之既昌,则无之而不合。’此诚洞微之论。”[2]477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张吴二人在文学思想方面深受曾国藩影响。而曾氏主张以“汉赋”和“气盛”来挽救桐城派孱弱文风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对雄奇雅健文风的宗尚。所以张吴二人,总体上也是倾向推崇以司马迁、扬雄、韩愈等为首的雄奇雅健之文。张吴二人的这种倾向,也影响了后来的莲池学子,可以说,在曾、张、吴三人的影响下,整个后期桐城派都呈现出对马、扬、韩雄奇雅健文风的追求。
(二)学术:调和汉宋,因文以求其意
张吴二人的学术思想也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曾氏是清末主张调和汉宋的代表人物。他在《复夏弢甫》中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11]1576张裕钊在《与锺子勤书》中,对曾国藩调和汉宋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发,他说:“夫学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之以考证,虽其说甚美,而训故、制度之失其实,则于经岂有当焉?故裕钊常以为,道与器相备,而后天下之理得。”[2]86吴汝纶对于汉宋两家,也采取兼容并取的态度。他在《答黎莼斋》中论及他的两部经学著作《易说》《尚书故》时说:“近十年来,自揣不能为文,乃遁而说经,成《书》《易》二种。说《书》,用近世汉学家体制……其说《易》,则用宋元人说经体,亦以训诂文字为主,其私立异说尤多,盖自汉至今,无所不采,而亦无所不扫。”[8]100-101
张吴二人在对汉宋两家采取兼容并取态度的同时,对两家的弊病也非常清楚。张裕钊说:“盖自康、雍、乾、嘉以来,经学号为极盛,非独远轶前明,抑亦有唐而后所未有也。然患在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而反以诋訾宋贤,自立标帜,号曰‘汉学’,天下承风,相师为贤,君子病焉。近乃复有一二笃志之士,稍求宋儒之遗绪,推阐大义,而不溺于纤小之习。然或专从事于义理,而一切屏弃考证,为不足道。蒙又非之。”[2]86吴汝纶说:“我朝儒者鄙弃其说,一以汉人为归,可谓宏伟矣,唯意见用事,于汉则委曲弥缝,于宋则吹毛求疵,又其甚者,据贾、马、许、郑而上讥迁《史》,蒙窃未之敢信。”[8]616所以张吴两人,对于前辈学者的著述,往往采取一种“无所不采,而亦无所不扫”的开放态度,也正因为这样,他们能在汉宋二家之外,开拓出一条“因文以求其意”[4]1141的新道路。下面以二人讨论《禹贡》中的“三江”问题为例,来看看他们怎样“因文以求其意”。
张吴二人讨论《尚书·禹贡》中的“三江”问题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是年三月,张裕钊以“《禹贡》三江考”为题,让莲池书院的考生写一篇作文,但是对于考生们的答卷,张裕钊感到“颇乏称意者”,于是自己作了一篇,并在该年四月十日寄去请吴汝纶指正。吴汝纶回信表示不太赞同张文的观点,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半年的笔墨官司。关于这场辩论的具体内容,由于涉及许多繁复的经学问题,再加上篇幅过长,笔者不再赘述。但是,从他们辩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二人在探讨经学问题时,往往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切入,下面仅引两小段以作说明:
适与《禹贡》“东迤北”之文合,其严于辞也若是。……所称郑康成及国朝汉学家故皆不知文者,为此说诚无足怪。知文如姚惜抱及足下,亦从而和之,诚愚之所未解也。[2]249-250
执事所好者,经之文也,请更以其文决之。……执事以为古人之文固必如是乎?……康成固不知文,何至自汉以来无一人知文,知文者乃独一魏默深也![5]65-66
在这两段文字中,无论是张致信吴,还是吴对张的回复,均以《禹贡》经文文本的行文用词或结构特点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和解决经学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最后对对方的质问,也往往归结为是否“知文”,是否能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经文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吴汝纶在给王晋卿的信中,把这种治经的方法说得更为清楚:“乾嘉以来,训诂大明,至以之说经,则往往泥于最古之诂,而忘于此经文势不能合也;然则训诂虽通,于文章尚不能得,又况周情孔思邪!”[8]616在他看来,治经之法,首在通文,只有深于文事,对经文的行文用词和结构特点有深入把握,才能真正读懂经文的微言大义。
张吴二人共同培养的弟子贺涛对这种治经的方法有过非常精彩的总结,他说:“(先生)于古人书,率以文衡之,以谓文者,精神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则辞之轻重缓急离合失其宜,而不能得其要领,或悖其旨而旁趋。又尝言:‘古人著书,未有无所为而漫言理道者。’故治群经子史,必因文以求其意,于古今众说,无所不采,亦无所不扫。”[4]1141
“率以文衡之”“因文以求其意”“无所不采,亦无所不扫”恰恰道出了张吴二人治学的特色,这种治学方法,也影响着整整几代莲池学子。
(三)教育:反对科举,重视人才培养
张吴二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但他们却深知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戕害。张裕钊说:“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士方其束发受书,则一意致力于此。……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其人能瞋目攘臂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言而已矣。乌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乂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2]279-280张裕钊认为,科举制度到了近代,已成为阻碍人才发展的绊脚石,根本选拔不出真正的人才,沉溺于科举的士子大多满口仁义道德而没有真才实学,这样下去只会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吴汝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比张裕钊更加激烈,他说:“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8]194“时文复用,窃谓于取士无甚损益,于长育人才实有妨碍。”[8]216“吾谓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8]365在同时代的文人中,当康有为还在说“科举不能骤废”,张之洞仍坚持“科举与学校并存”的时候,吴汝纶已明确举起了废科举、重学校、兴人才的大旗。可以说,在反对科举的道路上,张吴二人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张裕钊、吴汝纶都深切认识到,要改变国势颓靡、人才凋敝的境况,首要在“得人”。“夫穷天下古今尊主芘民,批患折难之要,一言以蔽之曰:‘得人而已矣!’”[2]219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得人”呢?张吴认为,“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2]279;“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西学未兴,人才不出”,“学校不兴,人才不出”[8]365-366。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张吴二人逐渐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而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当科举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时候,就应该坚决推翻它,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建立起新的培养制度,大兴学堂,引进西学。张裕钊在莲池书院接收日本留学生,劝导好友黎庶昌大胆走出国门,去了解西方的情况;吴汝纶在莲池书院创办东、西学堂,亲赴日本考察学制,在家乡桐城创建新式中学堂,这些都可看作是他们在培养人才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转变。这些教育理念以及对科举和人才的看法,无疑也体现在对莲池学子的培养上。
从同治七年(1868)张吴二人定交,到光绪二十年(1894)张裕钊逝世,二人交往长达26年,现存的交往书信多达83篇,另外还有酬唱诗文十余篇。我们不难发现,在古代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书信往来依然是晚清文人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当然,面对面交流探讨,更能促进友谊的增长。特别是张裕钊在莲池书院任教,吴汝纶在冀州当官期间,是二人交往最频繁的一段时期。这期间,不仅留存的交往诗文书信最多,当面交流探讨的机会也最多。他们在畅论经史和诗文唱和的过程中,逐渐对对方的思想性格、学术观点有更深入的了解,继而成为“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的石友,于是在文学、学术、教育思想上也日渐趋同。而他们二人又相继执掌莲池书院将近20年,这种趋同的文学、学术和教育思想,必定会对前来求学的莲池学子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也扩大了后期桐城派在北方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