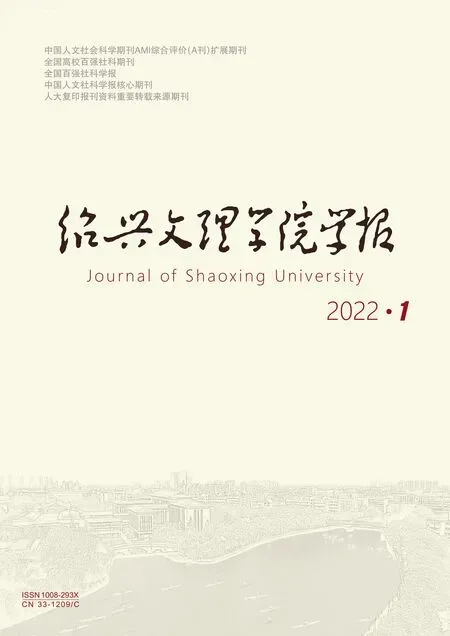守旧与弄潮:晚清文学家族的复杂横切面
成丹彤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晚清文学介于古代与现代文学之间,相比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其并未引起传统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忽视的背后可能是观念的偏狭,更可能是方法的局限,古典文学常用的文献考证或是知人论世都难以找到合适的焦距来处理晚清文学的复杂面貌。于是,在有意无意的冷淡中,时间序列上紧密联系的文学现象,在研究畛域中却划江自治。然而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也在提醒研究者需要“瞻前顾后”的视角。如何理解晚清作家的旧体文学与新小说创作?如何在新变局下理解传统士大夫创作转变的逻辑?如何看待新的媒介下的旧体诗文?这些问题需要不断转换视角才能予以解释。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目光是向前看[1]导论,然而顺着因果链条往上,研究者还能继续发问——晚清文学又是因何而来?晚清文学的革新因素与传统文学有什么关系?在外部冲击下,传统文学内部是否能生发出新鲜的力量?
魏爱莲的新作《小说之家:詹熙、詹垲兄弟与晚清新女性》(FICTION’SFAMILY:ZhanXi,ZhanKai,andtheBusinessofWomeninLate-QingChina,2016)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此书2016年出版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20年由陈畅涌翻译成中文与国内读者见面。魏爱莲长期关注明清女性研究,如《美人与书》(TheBeautyandtheBook:WomenandFic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2006)关注18—19世纪的女性小说写作,与方秀洁合编的《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TheInnerQuartersandBeyond:WomenWritersfromMingThroughQing,2010)探讨明清女性写作与闺阁的内部经验。而《小说之家》涉及晚清衢州詹氏一家两代人,讲述从父母到子女、从长子到三子的文学转变历程,借此来描绘晚清文学家族的图景。与前作相比,《小说之家》采用了家族文学的视角,而其对女性话题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性别意识成为詹氏家族文学传承中的DNA,研究也正是以此为线索展开。
“小说之家”就指衢州詹氏家族,詹嗣曾、王庆棣夫妇是传统的文人,而他们的子女处在帝国末期新小说兴起的浪潮中。晚清风云变幻之际的两代人,其代际差异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世家大族。詹氏夫妇创作传统旧体文学,写作与牟利无关,作品的传播也在交际圈内部。而詹氏兄弟主要投入小说创作,主题与改良女性有关,他们的创作在新式出版物中牟利,也拥有更广阔的读者群。
詹氏家族中,詹嗣曾、王庆棣夫妇分别有旧体诗文集《扫云仙馆诗钞》和《织云楼诗词集》;长子詹熙有改良小说《花柳深情传》等;三子詹垲有《幸楼诗文集》,有狭邪笔记《柔乡韵史》《花史》《花史续编》,也有改良小说《中国新女豪》《女子权》等。这些作品中思想资源差异巨大,体现出外部环境剧烈变化下两代人的张力,但魏爱莲更要发掘的是其中的联系,她的核心问题是坚持旧体文学的父母如何影响儿子狭邪笔记和新小说的创作?传统文学体裁对晚清文学的生成有什么影响?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怎么被贯彻于其中的?他们对这种题材的热衷有什么原因,而表现于文学中又有什么差异?为什么这个传统家庭会产生两位改良小说家?而最根本的追问是,传统中国文学向现代文学迈进的过程中,有哪些自发性的动力,而作为个体如何体现转型期的复杂?
一、家族的视角与母教的可能
魏爱莲解释“小说之家”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有四位作者的詹氏家族,家庭作为一个文学场域,文学创作构成了家族群像式的脉络,她试图基于詹嗣曾、王庆棣的作品来理解詹氏兄弟的作品;第二是长子詹熙小说《花柳深情传》中魏氏家族故事;第三是三子詹垲的创作集合,多种文体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体现着共同的主题。
“家”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亦是与之相适的研究方法。此外,“家”本身是关于新旧文学的比喻,是魏爱莲看待文学之变的视角。詹氏二兄弟无疑受到了新思想的冲击,而魏关注的是他们的文学家庭为晚清小说的写作做出了什么准备土壤,更大的企图则是寻找中国文学的内在理路和内部创造性。面对外来冲击时,传统文学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180度转向,传统文人思想中最能松动转向的部分,正是来自古典文化所赋予他们的灵活性。其内部的创造力,可以让他们在西潮涌来时,创作出能与之回应甚至抗辩的文学,而不只是在“冲击—反应”模式中一昧模仿西学。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很难不看成是旧体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的喻体,传承中自然存在突变与差异,但暗线的继承关系也往往不容忽略。
从魏爱莲的研究路径来看,这个视角也是她研究逻辑上的必然转向。她从明清文学入手,关注了女性在此间大量的创作。而这本书是她关注领域的延伸,也是打破古代帝国与近代化中国时间分期的尝试。
魏爱莲认为“家”对两个儿子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母教”。她观察到母亲王庆棣擅长创作旧体文学,从中表达自我感受,家人对此非常开放和包容,王庆棣成长的环境有赖于父亲、兄长、丈夫等男性亲人的支持。凭借家人的帮助,她还在现代媒介《申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三首诗词。有文化的家庭氛围成为家族成员关注女性生存的土壤。而友好的家庭氛围、具有创作热情的母亲与她的作品,都是对詹氏兄弟的另一种母教。
明清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母教在家学中的重要地位,父亲或科考为官或出门谋生,子女教育依托母亲的言传身教(1)徐雁平《课读图与文学传承中的母教》(《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269页)中对此文化现象有精彩解释。这里的母教群体有有文化水平的母亲,也有不识字的母亲,文化精粹显示在母亲待人接物上并以此传递下来。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中第四章“常州女学与阳湖文派”专门论述女学与母教,而女学本身就具有地域性和家族性的特点。。魏爱莲慧眼独具,发现这种母教本身就具有内在转化性。不同于传统蒙学培养,母亲自身的创作行为与生命经历就是一种教育,蕴含了传统可转化为现代价值的潜力。这种发现要与明清文学研究对照,才能显示其独特之处。前人总结明清女学兴起的三大要素:“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王庆棣的家人正好聚集了“名父”“才士”与“令子”。母教留下的记忆,展示在子女为其写作的年谱、行略等回忆文中,成为他们文学中极具温情与才华的部分。与之相似,于晚清詹氏家族而言,母亲晚年的失意促使了两兄弟在改良小说中为女性发声,时代风气通过家庭影响了两兄弟接受新思想的路径,他们在新小说写作中树立了与母亲命运完全不同的各式新女性。从闺秀作家到晚清文学中的进步女性,人物与创作者,母亲与儿子,生命经验与创作经验融汇为一体。母亲的人生变成儿子的书写经验,并借写作小说的改良作用,真实地推动女性命运的改善。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魏爱莲并未以更可靠的文献来论证,因此予人以猜想演绎之感。其实,这样的证据就在詹氏两兄弟所写的书中,如詹垲的《花柳深情传》《柔乡韵史》中都保留了大量青楼女子的诗歌,对女性的才华都尤为注重,对女性作品的认识,很明显受到母亲杰出才华与发表作品的影响。
当然除了文本上的证据,魏爱莲更多注意到他们的关于女性的社会实践:詹熙在衢州推动女子教育,成为女子小学的校董,提倡男女平等;其子詹麟来创设天足会,所募集的资金兴办女学;女儿詹雁来在女学任教,成为女权同盟会的创会成员。连绵三代人对于女性改良的关注,就是传统母教在外来冲击中产生的新转向。
这些与女性有关的创作与社会实践被视为近代化的社会思潮和小说“改良群治”影响下的产物,魏爱莲试图从家族历史角度寻找其中的草蛇灰线。而在具体的论述中,魏所提供的证据并未能显示这种家庭氛围与母教影响的强劲,事实上它们的作用也极其有限,家族给子女带来的潜意识只是提供了接受现代思潮的背景,而根本性的转向因素仍是西潮冲击与社会变革(2)明清思想研究者对明清母教与晚清女性主义的关系也多有关注,如熊秉真认为“当中国进入了变动的近现代时期,当我们看到被男性个体支持的‘女性主义者’观点变成中国社会政治论坛上的清楚力量时,就不难了解这是一个根植于晚清中国社会旧的心理作用下的现象。”(熊秉真《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载吕妙芬主编《明清思想与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6页)然而这种情感联系与心理作用只有在晚清社会背景下才得以产生改良女性的变革力量。。家族的视角和母教的影响,对詹氏家族何以生发如此丰富的创作解释力是有限的。
二、即时性
在最后的结论中,魏爱莲承认“家庭是一个极其狭隘的研究范畴,此书的很多方面很明显没有局限在这个框架内”[2]288。在第三四章她涉及晚清小说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关系,运用细致的文本分析对比詹熙和詹垲的作品差异,以及詹垲作品内部的变化。两人都相信小说改造社会的作用,针对当下的变化与问题而发,因而具有很强的即时性。在两兄弟的创作中,这种“即时性”其一是指他们有意记录时下的热潮与新闻事件,其二是他们的作品倾向迎合当时的需求与思潮,因而无意中成为当时人心态变迁、思想嬗变的即时记录。
晚清小说的“即时性”,如王德威所言“面对日渐紧迫的社会与政治危机,晚清作家倾向于记录刚刚才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对当下每一刻飞逝的时光紧张的凝视,以及他们迫切想要铭刻眼下经验的冲动,都可由其作品的题目看出来”[1]50。无论是外部世界的即时经验和内心的快速转变,都能在小说中迅速被记录下来,这是晚清文学区别于古典小说的特点。不再是陈陈相因的主题,更非从史书中取来的人物形象,代之以敏捷的时事反应与对当下乐此不疲的记载,因此魏爱莲认为“詹垲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经历及流畅的写作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比实际所见更广的时空全景”[2]136。
詹熙1897年完成的《花柳深情传》,是晚清最早的一批白话章回小说。主题是社会改革,本身就是针对社会当下问题而作。两年后,更名为《除三害》——又将其视作对傅兰雅“时新小说竞赛”的回应。詹垲的作品自发生长,狭邪笔记《柔乡韵史》《花史》《花史续编》都是妓女小传,尤其是《柔乡韵史》如实记录了当时风月场的妓女传奇。之后的《花史续编》增添的内容是《柔乡韵史》问世9年以来发生的社会事件。此外,狭邪笔记除了妓女个人生活外,还专注于男性友人与她们的关系,上海变幻不居的名利场日常也被记载其中。
另一方面,从《柔乡韵史》到《花史》《花史续编》中有许多暗藏的转向。《柔乡韵史》将男性作为受众,注重娱乐感官和情感方面,展示妓女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嫖客指南”。之后的《花史续编》序中却自称更关心具有闺秀气质的妓女,更加突出慈善与爱国主题。写作风格也由风趣向说教转变,开始激发妓女改变困境的奋斗精神,以德行为导向,注重塑造典型人物。詹垲的狭邪笔记从传统的品鉴女性到启发闺秀,妓女从书写和品鉴的对象变为积极女性事业的参与者,甚至妓女成为闺秀的榜样。这些转变的背后正是对女性思潮兴起的即时反应,也是其思想上转变的记录。
魏爱莲在这点上极富有创见地将詹垲的社论与其狭邪笔记和小说对读,发现三者都有共同的核心主题——改良社会,都是对当时社会的即时反应。“与狭邪笔记类似,小说也是在詹垲预设了阅读与通过改良作品启发读者的背景下创作的”[2]179。詹垲对创作背景的即时反应,使得其不同体裁的作品具有互文性,如狭邪笔记与小说之间产生了互文,对慈善办学、职业教育持有相似观点,正是詹垲当时最为关切的时事问题的记录。
第五章“作为记者的詹垲”对这种突出的即时性特点做出了解释,詹垲曾为上海和北京《商务报》供稿,写作社论的职业要求使他对当时的迫切问题极为敏感。最为奇妙的一点是,詹垲在社论中虽从未提及女性事务,而对照文本,其中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小说、笔记中涉及政治经济问题的部分,与社论的基本观点一致,是詹垲同一时期思考的产物,只是以不同文体文风表现出来。而且出现了社论向小说渗透的现象,或可谓之“小说的社论化”。如《中国新女豪》开场两篇社论文字设定了小说的叙事框架,小说情节围绕社论提出的目标而展开。此外,小说中还不时穿插社论性的文字,女主人公被社论影响思想。社论中的观点奠定了改良小说中探讨女性工作的合理性,在创作小说时,詹垲也在坚守自己作为社论作者的立场。而从时间线上来说,小说是面向未来时间线,而社论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改造宣言。
魏爱莲已经注意到晚清小说对当下即时的反应,这种反应以对未来的想象呈现出来。这样的小说与当时文人的社会改良社论有一致性,但小说中包含了更多的复杂因素,正如魏爱莲所分析的,“詹垲是随着时代自我发展的”[2]257,小说中的激进色彩是有所转变的,而且也不能完全按照社论的逻辑叙述,它仍然按照书中人物的逻辑展开,所遭遇的可能性也远远超出了社论的容量。
三、“弄潮儿”式的边缘知识人
如果我们打破家族文学视角的限制,其实还能有更多发现。魏爱莲《小说之家》中注意到了詹氏子女的职业,明显不同于父亲科举为官的传统知识分子道路。可惜并未向此继续挖掘,其实职业与身份的变动与他们的创作有很大关系。1882年詹熙名列会试的副榜,而13年后,他写了《花柳深情传》,将“科举”列为三害之一。后来的生涯又是做艺术品商人,又是做卖字文人,总体来说以经济利益主导。最后回到衢州创办学校当校长,同时又在衢州政界任职。何以解释如此不同于父辈的人生遭际呢?这些思想转变如何在内心取得和谐呢?同样詹垲也考中了秀才,之后做过记者,也刊登过广告,卖字赚润笔费为生。兄弟二人既像传统文人一样,在年少时博取科举功名,又都经历了职业转型,在大都市游走,以卖文写字来谋生,接触近代媒介,并且把文化与商业结合起来。詹氏二兄弟的经历,正是当时无数传统知识分子面临的巨变,科举士大夫所期许的“学而优则仕”与记者、艺术品商人之间的剧烈职业规划变动,我们很难不去问,这种千古未有之变局如何在个人意识中被理解?如何被个体平滑消化?身份、职业规划、个体生存价值如何在传统价值与新冲击之间取得平衡?
葛兆光在徽商詹鸣铎的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序言中提到“边缘知识人”群体,认为他们在晚清社会中的作用中是灵活地转变,没有太多负担的“投机”,趋时而上。他们是不够有坚守的“弄潮儿”,思想上容易松动和转型,同时又带有旧文人的知识资源和趣味。西潮冲击下的思想松动与传统文化所给予的文化底色,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其间的矛盾、对抗、共存最先发生在这些人的头脑与生命经验中。因为社会思想的转型可能正是从思想不那么纯粹坚固的群体开始,相比于传统精英士大夫的操守与价值信仰,他们更能灵活调整思想,或是为了谋生,或是为了顺应时风[3]4。
从詹氏兄弟的职业经历中,我们也容易发现他们确实具有小知识分子应时转化身份的特点,而且紧追时代的潮流,相比保守的传统学者,他们的灵活变动具有更多社会变革上的意义,“一些边缘知识人却有着‘咸鱼翻身’的欲望和‘浑水摸鱼’的手段,常常超越社会流动的常规,反而追求‘在传统外变’,这几乎成了晚清民初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3]3。在这个层次上,两兄弟的作品中既有传统文人的一面,如在狭邪笔记中品鉴青楼女子,也有积极参与社会,改善女性地位的一面。启迪世人的小说家和狭邪笔记的创作者,双重身份集于他们一身,晚清乃至五四之后的现代化,最早可能是从这一部分人开始的。
魏爱莲在分析詹垲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复杂性,“一个周旋于风月场的上海通形象显然与《汉口中西报》社论作者的身份不符”[2]259。两种身份和形象背后是两种知识资源,狭邪笔记更多借鉴李渔、袁枚等传统才子的趣味,一面赏玩妓女,品评“花榜”,而另一面又去突出德才兼备的妓女,关注其中闺秀气质的妓女,具有了改良女性的使命感。很难说,这里面的矛盾究竟是作者的复杂性使然,还是存在追赶潮流的投机心理。总之,从其多样性的作品思想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小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有着传统雅士趣味又对女性怀着同情,对当时的风潮又有体察的谋生文人。
詹垲的作品因为其趋时又成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梢。他有《幸楼诗文集》,与人合著过《全球进化史列传》,擅长写小品文,曾刊登广告可以替人写寿文、祭文、碑志,作序、传、记、跋、楹联、诗、词,传统文化变成可以谋生的商业资源,包括狭邪笔记、小说,混合以当时女性改良的思潮,成为典型的时代热点。在含混的文体表达之间,在东西拼凑的思想资源之间,这些小知识分子或出于利益或出于理想,在大众社会层面推动社会向近代化转型。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4]12可谓是传统中国理想士大夫的典范。与之对比,詹氏兄弟面对传统文化衰落之时,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青松之志,也因此更加灵活机动:在复杂夹缝中求生存、谋福利,文化体现在他们身上更多是可利用的资源,他们作为小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拼凑中跌跌撞撞走向近代化,以商机和利润为动力,在复杂的心态中促进女性改良和社会变革。虽然如詹氏兄弟之类的文人,在史书中未能留下浓墨重彩的笔墨,但作为促进社会变化的合力,同样参与了风气更新和社会启蒙。
《小说之家》所关注的詹氏家族,作为一个横切面体现了晚清文学图景的复杂性,作为喧哗中的低音,显示了晚清文学所开创的可能性,既与传统文化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又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促进了新变。魏爱莲采用家族视角更多解释前者,而材料本身所暗含的复杂性绝不会仅限于此,还在期待着更多视野的重新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