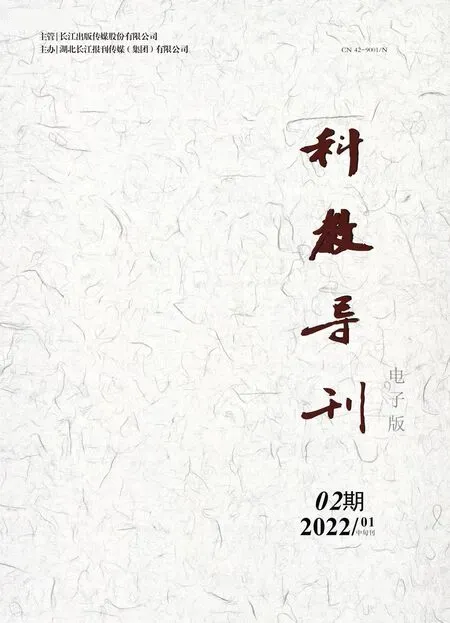“爱是蔚蓝色的信念”—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研究
林艺佳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1 道德焦虑
与一般故事片导演从影经历不同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从洛兹电影学校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拍摄纪录片。他曾在毕业论文中提到对纪录片的看法:“纪录片是一种比剧情片更伟大的艺术形式,因为我觉得,生活本就比我聪明,它创造的东西比我所想出来的要更有趣。”生活中存在的真实性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钟情于纪录片的原因,却也成为他离开的纪录片的原因。一是因为他逐渐发觉纪录片很难表达真正的真实,当摄像机离拍摄主体越近,拍摄主体就会化藏的越深,比如人们会在哭泣的时候关起门来。
但当基耶斯洛夫斯基拍到人们“真实的眼泪”,才使得他下定决心离开纪录片领域。在他眼中自己是没有权利去拍摄这些“真实的眼泪”,在他眼中个人的私密生活虽然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但他会因为打扰到人们独自享受这些私密的个人化的瞬间而内疚。他对于纪录片导演身份赋予他的这种在权力体系中处于高位的凝视的权利感到愧疚,甚至觉得自己滥用了这种权利。他表示那种时刻“自己像处在一个没有边界的王国里”,所以他宁愿用甘油刺激出演员虚假的眼泪,也不愿意承担看到真实的眼泪后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谴责。在他最后一部影片《蓝白红三部曲之红》中,兼职模特瓦伦蒂娜在摄影师的要求下为摆出悲伤的表情而去想悲伤的事情,而后这张照片被放大成海报贴在街道上可以被所有人观看,也是他对这种处于高位的凝视的谴责。
基耶斯洛夫斯基就一向有着这种高度的道德焦虑感,对于他而言在别人出口指责前,他就因自己产生的负罪感和内疚感而难以生活。我们知道当时波兰制片厂体系中,电影人是很难生存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如同其他导演一样去了法国,而后加入法国国籍。但是这次无奈中的决定,成为身为波兰人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心里难以过去的坎,在《机遇之歌》里威特克的三段人生中,前两段都没能搭上去往巴黎的飞机,第三段在去坐上去往巴黎的飞机的时候飞机失事。甚至在《白》中卡洛在巴黎失去的财产、性功能、爱等等全部的一切,都只有在他回到波兰之后才能找回来。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跟过去自己的决定过不去,甚至到最后选择留在医疗水平远远低于巴黎的祖国做心脏手术,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国家的偿还。
2 神秘主义与宿命论
基耶斯洛夫斯基所有电影中的主人公都被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感深深笼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文艺复兴起教给人类的对抗精神,自由意志,其实全是命运早已写就的样子。因此在他的电影中总会出现一个类似上帝一样的角色,在《两生花》里那个写了剧本,给维罗妮卡寄东西的人,他像掌控木偶一样一步步操控着维罗妮卡的人生。《红》中老法官给瓦伦蒂娜指引去做轮船,因而瓦伦蒂娜遇到了年轻法官。而年轻法官与老法官经历的高度相似性,无法不让人觉得老法官在将瓦伦蒂娜一步步牵引着走向年轻法官。在《白》的开头处卡洛藏身的行李箱在行李传送带上按照既定的传送轨道被运输,我们就知道卡洛的一生,在巴黎失去一切也好,在波兰重新获得一切也好,甚至是最后在海难中得救,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既定道路。
所有的巧合和机遇只是命运的伪装,而看似人的自由选择只是往生命的既定结局处迈进了一步。但基耶斯洛夫斯基意不仅在说明生命注定无情地奔向死亡,而是通过既定的命运和结局告诉我们“人生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生命是件礼物”而我们需要珍视。
在这种悲观主义之的宿命论下,基耶斯洛夫斯基还信赖生活中存在的非理性的感性层面的神秘主义。在《两生花》中让人相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灵魂的另一半,《蓝》中朱莉走到街上听到流浪汉在演奏自己和死去丈夫创作的音乐。迈克尔在尝试数次后小球终于站在了底座上,而下一秒朱莉与家人就发生车祸等等,基耶斯洛夫斯基眼中世界的关联太过神秘,每个人之间关联不是呈现线状而是网状的,每一个事物之间都有若有似无的联系,而他信赖心灵的某种感应。这种相信与人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紧密相连的观点,与现今西方以海德格尔为首的哲学家们所提倡的“万物相通”观点不谋而合。
3 爱的信念——《三色》
3.1 如果有自由
《蓝白红之蓝》是关于自由的讨论。提到自由我们一定会想到的是一种不受拘束,自主生命的状态。在影片的一开始,一场车祸就赐给了朱莉这种自由:从此她不再是母亲、妻子、著名作曲家的妻子,虽失去一切,但因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基耶斯洛斯基在采访中也曾说:“如果不考虑亲人的丧失,你无法想象更自由的人生。”在他的眼中,自由对应着囚禁,我们为了有所归依,常自愿为爱情友情亲情囚禁,从而付出自由,因而自由是以丧失为前提的。
但是朱莉并没有获得自由,她无法选择地被记忆和悲伤的情感囚禁。我始终觉得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很会把人类心里无法言说的情感用影像表现出来的人。他在片中未曾让女人痛哭过,但朱莉看似正常运行的生活画面中会突然涌进一片蓝色,在这片蓝色中画面内的一切都不可见。与蓝色一样,与朱莉的悲伤如影随形的还有朱莉与丈夫一起创造的那首曲子,朱莉拼尽全力想要逃离一切,甚至毁掉了自己和丈夫创作的谱子,但是在街头流浪者突然演奏出一模一样音符的时候,再次被死死的囚禁住。
朱莉为了逃离这一切,与丈夫的合作伙伴在家中上床,用表演式的方式告诉自己你可以忘记他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紧接着第二天,朱莉走出家门的时候用拳头在墙上划,这种触目惊心的痛,让观众知道即便肉体上的背叛已成为事实,她也无法自由选择忘记。弗洛伊德有一个观点称“悼亡不是为了在纪念和怀念而是为了杀死死者,只有让他们真正的死去,幸存者才能幸存。”随时间流逝,画面中的悲伤不再是大面积流入的蓝色而变成了蓝色吊灯,它存在前景或背景或成为女人脸上蓝色的光斑,伴随着音乐存在于女人生活的每一处。
朱莉真正获得自由的时刻是见到丈夫的情妇,并看到她怀了丈夫的孩子。之前一切对美好婚姻的记忆和幻象就在这一刻全部被打碎,朱莉最后的拥有被剥夺,由此才收获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影片最后一个画面,玻璃窗上不再只映照出女人的脸,窗外的景象也慢慢出现,朱莉也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记忆情感的囚禁。但朱莉转而投入奥利维尔的爱情中,可见朱莉追求的和想要的本就矛盾,就像爱和自由永远是悖论,人能有多自由呢?我们不过是为爱甘愿被囚禁。
3.2 如果能平等
波兰有句谚语:没有真的平等,只有更平等。《蓝白红之白》中探讨的就是有关平等的故事。这里的平等关系除了之前提到在法国和波兰两个民族之间的,就是卡洛和妻子多米尼克之间关于爱中的平等关系。多米尼克对卡洛的需求在生理层面上更多,所以会在卡洛性功能丧失的时候,多米尼克对他的态度是彻底的嫌弃,甚至将他扫地出门。但卡洛对妻子的爱是从精神到肉体的,从爱产生的那一刻,追求在这段关系里达到平等就是个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卡洛在巴黎苦苦哀求妻子的时候,卡洛卑微到了极点,于是卡洛选择回到波兰重新开始。
当卡洛因为自己一步步积累的财富而获得越来越多自信的时候,他开始惊心设计来报复多米尼克,这种当我能得到一切的时候我还是要约束你的状态,在体现出卡洛的变态的同时,将卡洛对妻子的爱体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传递出一种浪漫的追求和渴望。卡洛选择复仇的方式是自毁的,他不惜让自己的社会身份死亡来找多米尼克对她进行惩罚。最值得讽刺的是卡洛重新又偷窥视角看多米尼克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还爱着多米尼克,越是变态的观看视角就越是爱。即使卡洛变得多金,即使将多米尼克送入监狱,在这段关系里卡洛因为爱着对方始终是不平等,人永远没有办法在爱情中扯平。但到了影片的最后一幕,多米尼克向卡洛传递出自己的爱,二人间终于达到了平等,虽然一个在监狱内,一个在监狱外,但那一瞬间他们彼此需要。
其实平等本就是一种不可能的语境,它与人类的本性相对,真正的平等只有在集中营中会出现,但基耶斯洛夫斯基给出了我们另一个答案:爱存在的瞬间,你我平等。
4 结语
综上,我们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中看到一个有强烈道德感的、悲观的信奉某种神秘主义和电影哲人。
尽管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在我的作品里,爱总是与原则相对,爱产生两难境地,爱带来苦楚,有了爱,没了爱,我们都无法生活。”但是他在他近乎绝望的悲观世界中给观众和他自己留下了唯一信仰的出口:在无法选择无法把握只能依浪而行的绝望人生中,只有爱才能将我们带离这片虚无的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