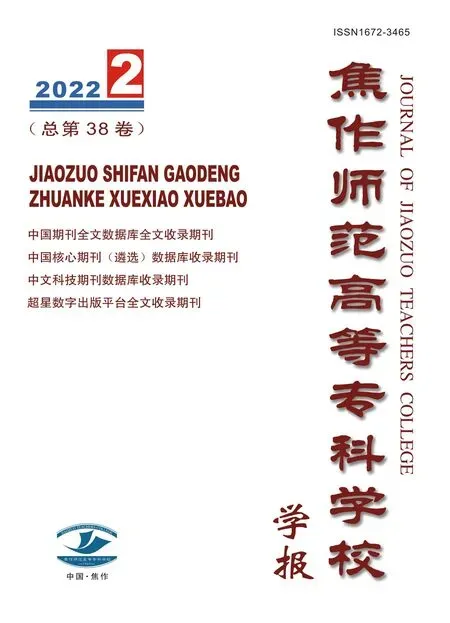从《左传》看春秋时期赋诗活动的演变趋势
王胜柃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赋诗活动是春秋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断章取义”是当时运用《诗》的一种惯例和普遍原则,即仅取诗的部分意义或比喻义、引申义。先秦文献中记载赋诗的典籍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语》和《左传》,但《左传》《国语》记载的赋诗并非都可以称为“赋诗断章”,因为“它是指宴饮朝聘之际,主人、宾客为表己意而自选诗之特赋,不包括造篇及例赋。例赋用诗的意义是固定的,无以更改,而特赋诗之意义则可以突破诗歌原有的仪式义,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作出当下的理解,这就是卢蒲癸所说的‘余取所求’”[2]。以此为标准,《左传》《国语》共有赋诗32场。《诗》被用作国家外事酬应,或被官僚、士大夫们用以赞美、讽刺、规劝和请求等。赋诗既是一种文化活动,又是一种有效的外交和人际交往手段,多发生在“聘”“盟”“会”“成”等多种场合。在《左传》《国语》记载的赋诗事例中,赋诗者的身份主要是诸侯、卿大夫和上卿。
目前,学界对《左传》《国语》中赋诗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赋诗的概念与特点、赋诗的功用、赋诗的文化内涵、赋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方面。比如张宇恕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质疑》[3]、刘丽文的《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4]、郑彬的《春秋用〈诗〉及其社会功用研究》[5]等都对赋诗的概念与活动规则进行了论述;关雯的《周代礼典的美学解读》[6]和孙敏的《〈左传〉、〈国语〉赋诗、引诗研究》[7]等概括了赋诗在政治、外交和言志等方面的功能;过常宝的《春秋赋诗及“断章取义”》[8]、刘丽文的《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9]等剖析了赋诗中体现出来的礼仪、制度、风俗、精神等文化内容;刘生良的《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10]、毛振华的《〈左传〉赋诗研究》[11]等对赋诗的后世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学界对于赋诗活动演变的研究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屈园的《〈左传〉赋〈诗〉考论》[12]、毛振华《〈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13]、刘生良《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14]、李炳海《春秋后期引诗、赋诗、说诗的样态及走向》[15]、韦春喜《歌诗·赋诗·引诗·说诗——先秦时期〈诗经〉接受观念的演变》[16]、周秉高《论“赋诗断章”的发展轨迹》[17]。以上关于赋诗活动演变的研究,多集中于讨论赋诗活动的兴衰历程,而对其兴衰过程中的具体演变趋势则是少有论及,即使偶有提及,也显得简略、笼统而零散,没有详细而全面地揭示出赋诗活动的具体演变趋势。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着重论述赋诗活动在兴衰过程中呈现出的几种演变趋势。
一、仪礼性削弱,实用性增强
赋诗是一种用来亲和四方来宾的外交礼仪活动,有固定的用诗、用乐之礼仪规范。赋诗活动的前期十分强调仪礼规范,而到赋诗活动的兴盛期,人们对于仪式规范逐渐不那么在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形式上由繁入简。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仪式本身,而是注重通过赋诗达到言志、观志、讽谏、达意等实用性的目的。赋诗的仪礼性被削弱,实用性增强。
前期的赋诗活动十分遵守礼仪规范。首先,赋诗活动中的诸侯僭礼行为常受到抵制。如文公四年(前623),卫宁武子到鲁国聘问,文公和他一起饮宴,并为他赋《湛露》及《彤弓》,宁武子不辞谢也不答赋,这是不合于礼的,于是文公便“使行人私焉”,宁武子对曰:“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1)本文关于赋诗的事例均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以下不再一一标注。原来宁武子以为他赋错了,《湛露》为周王宴诸侯的诗,《彤弓》为周王宴赏有功诸侯的诗,鲁文公赋之,皆不合于礼,所以宁武子不辞不答。其次,诸侯在赋诗之后通常要进行拜礼。拜礼有“拜”和“降拜”,同级别的宾主双方通常是“拜”。如文公三年(前624),晋国人请求改订盟约。因曾对文公无礼,此次晋襄公设飨礼招待文公,放下大国身段向其示好,并赋《小雅·菁菁者莪》。晋襄公借诗首章中的“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一句,将鲁文公比作君子,庄叔领会了晋襄公的示好意图,马上“以公降,拜”表示感谢,“晋侯降,辞。登,成拜”,双方十分客气。又如文公十三年(前614),鲁文公如晋寻盟,归途中郑伯宴请文公于棐,赋诗请平于晋,当季文子赋《采薇》之四章暗示答应请求时,“郑伯拜,公答拜”。“降拜”是一种更为谦恭的礼节,即降阶再拜,如秦伯设宴招待重耳,重耳赋《河水》,秦伯赋《六月》相答,赵衰赶紧让重耳降阶而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在“赋诗断章”前期,赋诗的主宾双方十分遵守礼节,甚是客气。前期赋诗共有6场,只有2场没有行拜礼,可见前期赋诗活动对仪礼规范的重视。
到了赋诗活动的兴盛期,人们不再关注仪式自身,而是注重通过赋诗达到实用性目的,仪礼性被削弱。这时,人们对诸侯僭礼行为已习以为常,没有任何抵制和批评。如上文提到的文公四年卫宁武子到鲁国聘问,鲁文公赋诗不合于礼,宁武子便不辞不答以抵制。但襄公八年(前565),晋范宣子聘问鲁国,襄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武子赋《彤弓》,显然不合于礼,但范宣子坦然接受并不以为失礼。滥用礼乐的例证还有鲁国叔孙豹访问晋国,晋侯款待他时使用了天子享元侯之礼,这显然超出了礼乐等级。除此之外,来而不往非礼也,赋《诗》讲究礼尚往来,拜谢之后,还应答赋,否则就会被视为无礼。前期赋诗 6 场,有 2 场没有回应,一次是文公四年,卫宁武子到鲁国聘问,此次宁武子不作答是因为对方不合礼仪。另一次是文公七年(前620),先蔑前往秦国迎接公子雍,他的同僚荀林父再三劝阻,先蔑不肯听从,于是荀林父赋《大雅·板》第三章进行讽喻,先蔑没有赋诗回应。到了中后期,赋诗不回应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对不答赋的现象也习以为常。中后期赋诗共有26次,有18次无回应,并且18次无答赋中,仅有一次遭到了抵制,可见中后期对仪礼的忽视。另外,不行拜礼也已经司空见惯,中后期赋诗26场,行拜礼的只有5次。由此可见,相比于前期,人们对于仪式规范不那么在意了,而是旨在通过赋诗达到言志、观志、讽谏、达意等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目的。
二、群体性削弱,个体性凸显
前期的赋诗活动往往是双方一唱一和甚至是多人多轮对答,具有群体性特征。赋诗活动后期,单向赋诗占据主流地位,赋诗不再遵循严格的仪礼要求而成为某一方的单独表达。各自独立的赋诗言志使赋诗行为的群体性被削弱,个体性被凸显出来。
首先,在前期,赋诗多是有往有来,而且有的赋诗活动会有多轮的双方对答。如文公十三年,郑穆公与鲁文公于棐地饮宴时,子家和季文子就进行了两次对答:子家赋《鸿雁》,季文子回应《四月》;子家赋《载驰》,季文子又回应《采薇》。又如《国语·晋语四》记载,秦伯设宴招待重耳,首先是秦穆公赋 《采菽》,重耳回应《黍苗》;再是秦穆公赋 《鸠飞》,重耳回应《河水》;最后秦穆公赋 《六月》。赋诗活动共经历了两个半回合。 进入中后期,赋诗唱和次数明显减少,甚至变成赋诗一方的单独表达,群体性被削弱。中后期赋诗共26次,单方赋诗就有18次,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如襄公十四年(前559),诸侯跟随晋国进攻秦国。到达泾水,军队不肯渡河,叔向与叔孙穆子相见,穆子对叔向赋了《匏有苦叶》一诗,叔向马上回去准备了渡船。可能因为情况紧急,叔向没有赋诗回应。又如襄公十九年(前554),齐国与晋国讲和,在大隧结盟,穆叔进见叔向,赋《载驰》第四章。叔向没有赋诗回应。再如昭公元年(前541),郑简公设享礼宴请赵文子、叔孙豹和曹大夫,子皮向赵文子通告宴请的时间,赵文子赋《瓠叶》,子皮也没有赋诗回应。可见赋诗已成为某一方的单独表达。
其次,在一般情况下,赋诗主要用于诸侯和贵族之间的交际活动,在此基础上,与个人志意有关的“言志”“观志”的赋诗出现了。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在垂陇设宴招待赵武,赵武让七子赋诗言志。子展赋《召南·草虫》,以君子称赵武,意为自己忧虑国事而信任晋国,赵武谦虚地说“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鄘风·鹑之贲贲》,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两句,较为直接地怨刺君上。子西赋《小雅·黍苗》四章,把赵孟比作周贤臣召伯,赞美他在弭兵之盟中的功劳。赵孟谦逊地说一切成功应归之于晋君。子产赋《小雅·隰桑》,以诗中“既见君子,其乐如何”一句,表达相见的喜悦,表示愿尽心侍奉晋国。子大叔赋《郑风·野有蔓草》,表示自己与赵武初次见面,深感荣幸。印段赋《唐风·蟋蟀》,公孙段赋《小雅·桑扈》都是称赞赵武能尽礼文。通过观察七子在赋诗活动中的表现,赵武对七人的人品、志向作出了评论,并预测了他们的命运。他首先批评伯有“志诬其上”,认为他不会有好下场。他最欣赏子展和印段,认为子展身居高位却谦恭礼让,是人民的主人;印段享乐时懂得节制,是保住家族的当家人。这次赋诗活动,明确地提出了“《诗》以言志”的观点,这是对“诗言志”观念的又一表述,即将诗作为个人志意的表达,并不是发生在诗的创作中,而是发生在诗的应用和阐释活动中。这里的“《诗》以言志”用以直接抒发怀抱和展示风采,展示了赋诗者的个性。赋诗成为“言志”和“观志”的个体行为,个人好恶、意图、感激、憎恨、逢迎和嘲讽等,都可以通过温文尔雅的赋《诗》表达出来,赋诗活动的个体性便凸显出来了。
三、政治性削弱,审美娱乐性凸显
在“赋诗断章”的中后期,参加活动的客方有时不再通过赋诗以达到谈判、劝谏、请求、示好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是作为观赏者出现,赋诗的审美娱乐性凸显。
如昭公十六年(前526),郑国的六卿在郊外为韩宣子饯行,韩宣子邀请六人赋诗以察看他们的志向和郑国政治动向。子齹第一个赋诗,他赋《野有蔓草》,借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两句,表示初见贵宾,深感荣幸;子产赋《郑风·羔裘》,借诗中“彼其之子,邦之彦分”两句,赞美宣子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子太叔赋《褰裳》,取诗中“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两句,暗示宣子要善待郑国,否则将另投他人;子游赋《风雨》,借诗中“既见君子,云胡不夷”两句,表示见到宣子,郑国就心安了;子旗赋《有女同车》,借诗中“淘美且都”赞美客人仪表不凡;子柳赋《萚兮》,取“倡予和女”一句,表示宣子提倡在先,自己将和而从之。赋诗结束后,韩宣子赋《我将》,取诗中“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几句,表示要畏惧天威,平定天下。这场赋诗活动成为展示郑诗的一场文化盛宴,韩宣子则成为这场艺术表演的观众。对比上次赵武在郑国的赋诗,这次赋诗活动更为和睦融洽。郑六卿采用的几乎都是爱情诗,以情爱喻国家亲善,显得更加风流文雅,借助《诗》本义带来许多审美体验。通过郑六卿所赋之诗,韩宣子领会了郑国想与晋国交好的愿望,故而满心欢喜地说“皆昵燕好也”。赋诗把外交活动文明化、艺术化,其所引用之《诗》和通过赋诗来表达的情感内容具有一种艺术特质和审美特性。政治家在片言之间,微言相感、吐纳成文,这种外交辞令充分体现了对审美形式的追求。
另外,赋诗者运用诗文的象征意义,通过隐喻的方式传达志意,可以调动起听者丰富的联想与想象,进而使其产生审美感受。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麇》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郑简公设享礼宴请赵孟、叔孙豹和曹大夫,叔孙豹赋《 鹊巢》,借“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将赵文子比为鹊,自己比为鸠,希望得到赵文子的庇护,免于被杀。赵孟连忙以“武不堪也”作为辞谢。叔孙豹又赋《采蘩》,诗中有“于以采蘩?于沼之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句,以蘩菜喻鲁,以公侯喻晋,表示鲁愿意为晋效命。子皮赋《野有死麕》的最后一章,曰:“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子皮以此喻赵文子抚爱诸侯,以礼相加。赵孟立即心领神会,于是赋《棠棣》,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句,言兄弟之国相亲。 与观乐不同的是,观志依据的是诗的文字意义,因为赋诗的惯例是只取诗的部分意义或引申义,所以相当于把诗文当成“隐语”,用其象征意义、通过隐喻的方式传达赋诗者的志意或隐秘动机,不为《诗》本义所束缚,这样可以调动起听者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以及审美享受。这种隐喻的方式充分挖掘出了诗的无限韵味,使效果更加形象生动。总的来说,“赋诗言志”实际上是借用他人之诗来为自己“代言”,用这种方式美化、修饰语言,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审美化,凸显了赋诗的审美性。
四、结语
赋诗言志是一种具有神圣性、权威性、身份性的言说方式,这种特殊言说方式具有委婉性和含蓄性,容易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能够有效地避免很多直接言说可能带来的正面冲突,有利于双方统一意见和缓解矛盾,也显示了卿大夫的学识修养。最早的赋诗活动发生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文公、成公时期有少量的赋诗活动,襄公、昭公时代达到鼎盛,定公、哀公时代走向衰落。《左传》中的赋诗活动除了有兴衰变化,还呈现出三种演变趋势:仪礼性削弱,实用性增强;群体性削弱,个体性凸显;政治性削弱,审美娱乐性凸显。“赋诗言志”广泛盛行于春秋各国的交际场合,但是到了战国,礼乐文化土崩瓦解,春秋卿大夫委婉含蓄、温文尔雅的诗赋外交辞令,便被战国策士们气势磅礴、恣肆汪洋的说辞言论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