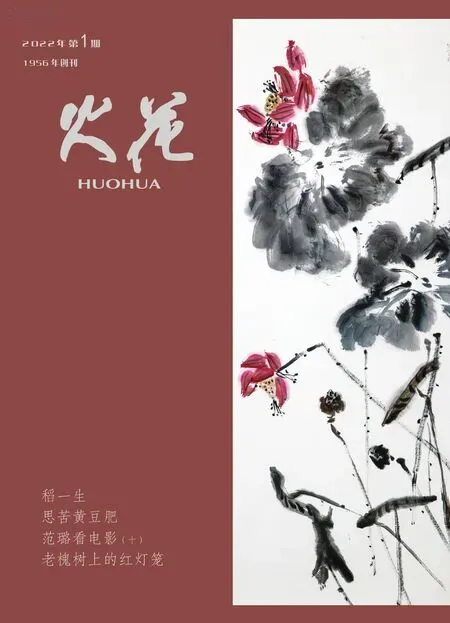荒原之夜
陶诗秀
秦箭
2月14日晚,接到“110”的通知,我们刑警队立即出警。
事故地点位于石板路至电报路方向的双白段。我们刑警队到达现场时看到,两辆车应该是发生碰撞后,同时冲下公路南侧。两辆车分别是奔腾阳光轿车和奔腾商务车,均受损严重。
黑色奔腾轿车的后备箱撞在一棵树上,车后体扭曲变形。商务车歪停在公路下的缓坡上,驾驶员侧的车门是打开的。
看起来是交通事故,但“110”称有人报警,所以交警和我们刑警队都赶了过来。车毁人消失,找不到受伤人员,驾驶员不见踪影,也找不到报案人。这茫茫荒原上,发生过什么事?蹊跷。
我们刑警队到达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以后,立即展开现场勘查,有了惊人的发现。
阳光轿车被挤在两棵树中间,后备箱的门因受挤压裂开,露出十公分左右的缝隙。我们的警员打着手电,透过缝隙往里看,似乎有一条类似人腿的物体。
“想办法打开后备箱!”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具尸体,完全没有生命迹象。
把尸体从后备箱移出,法医周民上来做初步鉴定。
“男性,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双手被捆绑,胸部有锐器创口,头部有多处钝器打击伤……显然不是死于交通事故。”
周民粗略察看一遍,得出了结论。即使不是法医,也能看得出是凶杀。
他是谁?车主还是乘客?跟这起交通事故有什么关系?
“秦队,在轿车里发现了这个。”警员朱丁递过来一本行车证。我翻开一看,轿车车主名叫唐孝果,证件发放地为河北。
周民对比了死者与行车证上的照片:“应该是他。”
“这么说,车祸之后,车主死在自己的后备箱?”我更不懂了,回头吩咐朱丁:“立刻让局里查找唐孝果的信息,最好找到近期的照片。另外,仔细搜查两辆车内部。”
在商务车大开的车门边,有一串步幅比较大的足迹,杂草上有明显的踩踏痕迹,显示商务车车主在车祸发生后,慌张离开了驾驶位置。
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没在现场?
“报案人联系上了吗?”
“他目前在距离现场西侧五里路的一个村子,打了几十遍电话,才打通他的手机。”朱丁正在手机地图上定位。
我们马上赶往村子,十多分钟后到达。报案人曹铁男正躺在村里的医务室输液。
曹铁男
“我是报案人,也是商务车的车主。”不等警察多问,我抢先告诉他们。
“你受了什么伤吗?”警察拿眼看我输液吊瓶上的标签。
“别看了,葡萄糖。没受伤,可是真他妈折寿,我要压压惊……”
“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事故?这哪儿是事故!纯粹是谋杀!我是受害者。”
“从头说,到底怎么回事?”单眼皮、姓秦的警官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
“昨天,我去太白山郊游,下山晚了,在山下的小饭店吃了饭,晚上八九点吧,往回走的。
“在双白路段,我发现有两辆车紧跟着我,离我越来越近。我加大油门,试图甩掉他们。但他们玩命地追我,就像警匪片里一样,一左一右夹击着,‘哐哐’撞我的车,把我往公路下逼。”
一想到那情形,我仍心有余悸,抓起水杯大口喝水。
“你认识那两辆车吗?你有没有想到他们会是谁?”后面站着的警察问。
“不认识!我熟人朋友太多了,平时说话、做事一个不小心,难免得罪个把人。谁知道哪个孙子记了仇,跟我狭路相逢,分外眼红。”我意犹未尽,滔滔不绝,“……为了躲避这两辆车,我拼命踩油门,车撞得火星四溅。我也是急了,心想跟你们拼了。我不能白死,死也要带走你们给我垫背。带一个走够本,带两个赚一个。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来不及报警和求助,只想快点开到附近的村落……被两辆车夹击着行驶了十多分钟后,意外发生了,有一辆车的保险杠和我的保险杠挂上了,我的方向盘失灵了。两辆车一起冲下公路。
“我的车体积大、重量大,落地颠了几下稳住了。另一辆车被甩得打了个转,着地后在地上转了三圈,卷着尘土扬起一股旋风,最后撞树上了。
“那风猛啊!跟龙卷风差不多……我在第一时间弃车逃跑。在逃离现场几十米时,我听到了枪声。”
“什么?有枪声!”秦警官提高了嗓门,紧张了。警察也没见过世面,郊外是大片牧区,有猎枪的人多了。
“枪一响,我吓得魂飞魄散,死命狂奔,一口气跑到附近的村庄。
“要没有那股‘龙卷风’,我就跑不掉了,他肯定能打着我。”
冷不丁儿秦警官问道:“你的车里还有别的人吗?”
秦箭
口若悬河、绘声绘色的曹铁男突然吞吞吐吐起来:“我被吓坏了,一辈子没见过那阵势,简直是仓皇逃命……”
“还有别人在你车上吗?”
“我逃进这个村子才想起来,我的同伴还在车里……”他往后撸撸头发,手停在后颈脖处。
“你自己跑,把他留在车上了?”
“那时什么都顾不上了!晚一秒就没命了!”
“你后来见过他吗?打过他手机吗?或者有没有可能,他跟你一样跑到这个村子来?”
“没有,没联系。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他毫无愧色地说。
“他叫什么名字?把他的手机号给我!”
“王旦凤。”
“女的?你跟她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他嗫嚅着,“也就是普通朋友……”
“请你好好回忆一下,你逃离之后,有没有看见或听见她的什么动静?”
他双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没什么了,我脑仁疼,啥都想不起来……”
“现在我告诉你,在现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女性的痕迹,没见到人,也没有与女性相关的物件。但是,在与你相撞的轿车后备箱,我们找到了一具男性尸体。这是一桩刑事案,你务必配合我们调查。”我面无表情,含威不露。
“我好像——”他犹豫再三,支支吾吾,“——远远地听到她的尖叫声,夜里,在野外,声音特别清楚,好像是她从车里被拉出来了。”
“请把她的手机号给我!她家的地址、电话?”
我的直觉告诉我,曹铁男的陈述可能属实。现场商务车门外的那串足迹正是奔往村庄方向,与他的叙述一致。关于与王旦凤的关系,他可能撒谎了。道德评判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我在心里还是忍不住鄙视了他一下。这个叫王旦凤的女人凶多吉少了。
搜证警员将曹铁男的鞋印留了样,以供与现场的鞋印对比。
“先派一个人看着他。”我吩咐朱丁。
回到警局是凌晨三点半,召开第一次侦查会议。我将调查的情况梳理后,简单汇报给局领导和全体警员:“按照商务车主曹铁男的供述,曹铁男和王旦凤晚上八九点驾车从青龙山回来。在去往电报路方向的石板路双白段,遭遇劫匪的两辆车追击,曹铁男有幸逃脱,而王旦凤很可能被劫持了。
“可以确定,劫匪驾驶的两辆车之一属于唐孝果。唐孝果在这起人为车祸发生之前已经遇害,尸体藏在事故现场被撞坏的、他自己车的后备箱。”
留守值班的女警员陈萍汇报:“通过河北警方,找到唐孝果的家属。家属称,唐孝果已从河北外出半个月左右。对比尸体与河北警方发来的唐孝果照片,死者极有可能是唐孝果本人。”
河北警方效率挺高。谢了,河北的同行们。
朱丁接下去说:“整理现场带回的物证,车内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票据,反映了唐孝果出发离开河北的时间、到达我省境内的时间。根据唐孝果行车的路线,他是在2月14日进入本地区境内。据家属说,他是在2月14日下午突然联系不上的。”
我说:“本案已确定是刑事案件,至于作案动机,可以排除仇杀和情杀。唐孝果的失联有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然后被杀人灭口。被害人车上和身上都没有发现现金、银行卡、手机等私人物品。”
有人提出异议:“据此就定性为财杀,是不是为时过早?有些嫌犯有反侦查意识,会做些手脚,掩盖真实动机。再说,死者身上有多处锐器伤,一般仇杀才会形成这种伤口,会不会是他的仇人从河北跟踪过来……”
陈萍说:“我向家属打听过,唐孝果做服装生意很多年了,一向和气生财,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他们觉得不应该是仇杀。”
“商务车的情况呢?”局长问,“被劫持的受害人有线索吗?”
陈萍说:“拨打了曹铁男提供的手机号码,一直关机。‘110’没有接到任何叫王旦凤的女人的报案或求救。已打通曹铁男提供的住宅电话,证实王旦凤确有其人。她家人说她2月14日早上离家后———据说是和朋友郊游了,就没回家,处于失联状态。她的家人万分焦急,正要报警。现在,我们有人每隔十分钟打一次她的手机。”
“根据目前证据,暂时定性为抢劫案。”局长下了结论,“先按照这个方向侦查吧!技术部马上调取唐孝果进入本地区的监控录像,查找他是在哪里出现意外的。”
散会。
局长叫住我:“明天安排人跑一趟河北,提取他直系亲属的生物检材,要百分百确定唐孝果就是案发现场的死者。”
六点了,我疲倦至极,在会议室的沙发上倒头便睡。
“秦队!秦队!王旦凤的手机打通了!”陈萍摇醒了我。
“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她说的是什么。一看墙上的钟,才睡五分钟,可是睡得真香啊!
王旦凤
“他说的都是实话。”我说,警察赶来的速度之快,出乎我的意料。在电话里他们再三确认我的安全,我第一次有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感觉。
“他弃车逃跑后,我还没反应过来,就有几个人拿着棒子和枪站在车外。”现在,我想到那个人就觉得恶心,连他名字都不想提,“他们打开车门,抓着我的衣服把我拉下车,一直拽着我朝公路走。”
“总共几个人?”单眼皮、特工脸的警官问,他可能是头儿。
我说话时,一个年轻警官拿着笔在本子上“唰唰”记录,另一个警官拿着小型摄像机在拍摄。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我,像聚光灯一样,我有点不安。
“……四个。”我说。
“然后呢?”
“然后,他们把我拉进公路上的一辆轿车,我的皮包、手机都被搜走了。”
“他们的相貌、身材什么样?口音是哪里的?”
“……太黑,没看清……他们戴着口罩……南方口音……”
“南方口音?南方哪里?”
“……不知道,就是南方的……”我低下头,“我很害怕,车上有凶器,我九死一生,脑子根本不够用。”
“什么凶器?”
“枪。”我说,“他们让我老实点,不要喊叫,叫也没用。他们还说,他们身上都背着几条人命,不怕玩命。”
“他们带你去了哪儿?”
“没走公路,是土路和砂石路,一路颠簸。”
“方向呢,哪个方向?”
“没有灯,看不见,不知道方向。”
“从事故发生地点往哪边走的?往电报路走,还是回塘坊镇?”
“……没去电报路,我记得车掉了个头……”
“最后停在哪里?”单眼皮警官催问道。
“……好像经过了一个加油站,又走了一阵,进了一个院子。院里有两间砖平房,他们把车停下,叫我下车。有一个人把屋子的锁撬开,所有人都进了屋……”
“然后呢?”单眼皮警官耐着性子问。我听其他警察叫他“秦队”,这么年轻就当了刑警队长,果然有一股精锐之气。
“其中三个人商量着继续寻找目标‘干一票’,带着枪开车走了,留下一个人看着我。”
“后来呢?”
我抿了抿嘴唇,欲言又止。
秦警官拿来一瓶矿泉水:“别紧张,慢慢讲。只要你安全,我们就不怕了。”
“……看守我的这个人显得很疲惫,过一会儿就躺在炕上,让我坐在他旁边,叫我别想逃跑,说我一动他就会知道……”我一边喝着水,一边慢慢说,语调尽量正常自然,“……没多久,他睡着了……过了一个小时,我确认他已经睡熟,院子里也没有人,这是我逃脱的好时机……
“屋子的门被锁上了,不锁我也不敢从前面院子出去,我怕迎面碰见那几个人。我看见后屋有个小窗户,就轻轻站起来,确定他没有任何反应后,小心翼翼打开后窗跳出去……
“我一口气跑了很远,一直跑到加油站。万幸我逃出来之前,偷回自己的皮包,我用手机给朋友打了电话,她和男朋友开车来把我送回了家。”
“你还记得去平房的路线吗?”
“不记得,我吓坏了,四周一片漆黑,我不能确定院子的具体位置。”
秦箭
“她‘不能确定院子的具体位置’,这句话她倒说得很确定。”我在车上对朱丁说。
陈萍跟王旦凤上了另一辆车。王旦凤慢腾腾的,好像事不关己似地漠然。
案发72小时是破案的黄金时间,她不是警察,已经死里逃生,她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天亮前抓住嫌犯,一旦让他们逃脱,再想抓他们,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根据王旦凤的描述,从事故现场过了塘坊镇就是加油站。我们知道了大致方向,一路飞奔,沿公路找到了那个加油站。再走一截,看见了那个小院。同来的塘坊镇派出所警察说,那是个废弃的养殖场。
“准备抓捕!”天快亮了,必须加快行动。
特警先包围了院子。因为嫌犯持枪,临时抽调了特警协助抓捕。我和朱丁跳墙进去,拿着手电一扫,感觉不妙。院子里空荡荡,是不是王旦凤的逃跑已打草惊蛇?
慢着!我碰一下朱丁,抬下巴示意他看院子东北角,那儿安静地停着一辆面包车。
我们悄声趋近,驾驶员位置的玻璃已破碎,用手电往里照,车座上有血迹。我们来不及细看,确定车里没人,迅速挪到屋边。
门上挂着锁,但是听见里面有若隐若现的鼾声!
我一拉锁,发现并没有按死,于是把锁摘掉,轻手轻脚推开了一条缝,侧身进去,外屋没有人。我推开里屋门,黑暗中看见炕上躺着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就不劳动特警了。我用电筒朝外晃了一个圆圈,几个刑警悄没声息地进来。
炕上的人似乎被惊醒,感觉到了什么,抬起身:“谁呀?”
我们四五个人一起扑上去:“别动!警察!不许动!”
“叫什么名字?”几个人一起喝问。
“李大清。”
“李大清,你被捕了。”
在炕上,枕头边有四颗猎枪的子弹壳。在院里养殖棚舍里,也发现了几颗子弹,自制的半成品。
李大清
不可能动!几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的脑袋,告诉我“别动”,那还动啥啊?不可能动。
这一天迟早会来,自从跟他干上,我时刻准备着。
警察把我提溜起来,按在炕沿上:“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知道。”我一点不害怕,相反,踏实了。
“说!”
“撞车了呗。”
“好好说话!说老实话,不然你我都麻烦。”一个单眼皮的警察慢悠悠地说,我记得他那双细长的眼睛,他是灯亮后我看到的第一个人。
“咱是良民,不找麻烦,想知道什么尽管问。”
“一共几个人?”
“四个。”
“叫什么名字?”
“……小赵、小钱、小孙,不太熟,网上认识的南方人。”
“你叫小李是吧?”我旁边按着我的警察用胳膊肘杵了我的肩膀一下,显然不欣赏我的玩笑。
到了公安局,我已经准备好和盘托出,本来也没打算死抗到底。
“只有两个人。”
“这个态度就对了,你以为我们刑警是吃干饭的?”用胳膊肘杵过我的朱警官厉声说,“车祸现场根本没有那么多脚印,院子里也没有四个人的脚印。”
“是我开的车,撞了一辆商务车,我们两辆车一起翻到公路下边的田野。都是牛海让我干的,我听命于他,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单眼皮秦警官问:“牛海是谁?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他是我表连襟,他老婆和我老婆是表姊妹,就那么认识了。”
“他让你干什么了?”
“他让我把那个女的拽下来,送到公路上的车里去。”
朱警官敲了一下桌子:“说主要的,别避重就轻。你可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你开的阳光轿车里有一具尸体。”
“跟我没关系,我可没杀他——你得让我从头说起……”
“从头说,我们听着呢!再提醒你一次,好好说话。”秦警官抱起了胳膊。
“两个多月前,牛海找到我,让我跟他出去做事,挣点大钱。我后来才知道,他所说的挣大钱就是抢劫。
“我这人从小到大遵纪守法,以前上学连一堂课都没旷过。稀里糊涂跟他做完第一起,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跟他说,从今往后别找我了,这回的事我也全当不知道。
“但他这个人狠哪!黏上了就别想甩掉。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他把电话给我掐断了,手机卡给我抠了。不让我拿电话、不让我回家,说我要是不听他的,他就把我干的事告诉我家里,还报告公安局。他说他坐牢无所谓,他反正什么都不在乎。
“杀那个唐孝果的时候,打得那叫一个惨。我都瞅不下去,躲一边了,不敢看,等于是活活打死。他这人心狠手辣,说不杀人灭口,后患无穷。
“2月14号那天,刚打死了唐孝果,又碰到一辆商务车。他盯上了,说开商务车的肯定有钱。
“他让我超车到前面,再踩煞车,往商务车前毂辘上撞。不曾想,我的保险杠跟商务车的保险杠挂在一起,两辆车都开到沟里去了……”
我一五一十回忆着,女警官走笔如飞在记录。
秦箭
这李大清真蠢,原本端正清白的一个人,这么轻易就被人带上歪门邪道。
根据李大清的供述,确定了牛海现在所开轿车的车型和颜色,很快调出相关监控录像,一路追踪,发现牛海已经逃出本市辖区。
持枪、驾车、命案在逃,牛海是一个危险份子,极有可能狗急跳墙。案情重大,必须立即展开对牛海的抓捕。技术部继续追踪牛海的行车轨迹,其他人做好抓捕的准备。任务布置下去,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像是扣子扣错了眼、鞋子穿反了一样别扭。
“王旦凤在撒谎。”我终于找到了疙瘩所在,“我们必须要再询问王旦凤一次。”
刚要出门,技术部刑警兴奋地冲进来报告:“有牛海的消息了,他在客运港。”
抓捕小组立刻出发去码头。
根据当地警方的资料,牛海在一家小旅馆。我们部署警力包围了小旅馆。当地警方陪同小旅馆经理,向我们指出牛海所在的房间:2楼208号。
我们在走廊听见208房里有鼾声。在最紧张的抓捕时刻,我还是差点笑了出来。这两名嫌犯不愧为亲戚,鼾声都一模一样。
朱丁用一根细铁丝伸进门缝,慢慢移动里面的插销。
“拉住门把手。”他停住了。
我拉着门把手,听见“咔哒”一声,用力一推,门开了。我们一拥而进。
“叫什么名字?”
“轻点,我胳膊快断了。”
“叫什么名字?快说!”
“牛海。”
“抓的就是你!”
牛海
警察真可笑,这么多人来抓我一个。前面两个、后面两个为我保驾,一左一右俩大个儿架着我的胳膊下楼,这小破旅馆的窄楼梯根本容不下三个人并排!
他们把我像麻袋一样塞进车里。得,算我栽了,如今我也变成菜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
左右两个“保镖”又紧紧夹着我的胳膊,两人用脚踩着我的脚背。你们怎么不拿铆钉把我铆在车上?
后面一个警察抓着我的头发,压低声音在我耳边发问:“干了些什么?自己说吧!”
他们这是要趁热打铁,抓捕时趁人乱了阵脚,要第一手口供。
“你别让我活动开!你要让我活动开,我就一头撞死,我没脸活了。”我扭动着身子,想为自己争得更多的空间。
“抢了几次?”两边的警察紧紧压着我,不让动。
“四次。大丈夫敢作敢当,四次。”
“杀了几人?”
“三个。”
两边警察找到合适位置,让我坐得舒服一点。
“继续说,别停下,都怎么干的?”后面的警察却仍不放松,追着问,“时间、地点、和谁干的?”
“说来话长……”
“那就长话短说!”
“去年十一月,长春,我自己,抢了辆轿车,人给弄死了。一月,在长岭,和李大清抢了个面包车司机,把他杀了。最后这一次,抢了个河北人,人打死了……”
“抢劫动机?”
“钱呗!抢劫还能为什么?”
“为什么那会儿那么缺钱?你平时以什么谋生?”
“赌博,以赌博为生。行了,爷们儿,你不就怕我不‘坦白从宽’吗?我坦白,全都坦白,今晚先让我好好睡个安稳觉成吗?明儿个再说。”
“行,算你是个爷们儿,别忘了自己的话,咱们明天接着聊。”
嘿哟!我算什么爷们儿?作为劫匪,真没脸活了,两次在女人跟前马失前蹄。
前四次抢劫唯一一次失手,就是遇上女人。明明制服了那个小娘们儿,竟在去银行取钱的路上被她溜了。这回,又是李大清这个熊孩子放了那个女人,招来警察。
女人太可怕,真不能招她们。我算是认栽了。
秦箭
这牛海事儿真多,一觉醒来,吃了早饭,还要求先理发刮脸,才来接受审讯。
“我欠了人家三十万。本来想赚一点,不料运气太差,赌输了,债主三天两头来找我。”捯饬一番,他倒不像抓捕时看起来那么狼狈猥琐了。
“什么时候开始赌博的?”
“去年底,十二月。”
“为什么杀人?”
“我跟李大清事先商量好,完事后不能留活口,李大清也同意。”
十二月开始赌博,十一月就抢劫杀人了。李大清是去年底才跟他干的。
杀了三个人还毫无悔意,死刑就是为这样的人准备的。
“那为什么没杀王旦凤?”
“我倒是想弄死她,李大清想放了她,俺俩吵吵起来了。”
“李大清为什么想放了她?”我有点惊讶了。
“他看上她了呗。李大清先翻她的包,看见她的身份证,发现他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就唠起嗑来,挺有缘分。
“那女人也不是一般人,被李大清拿枪顶着,居然能面不改色跟他闲聊,说他长得像她的龙凤胎弟弟,他俩长得是有点像——夫妻相。后来两人谈笑风生,我几次对李大清使眼色,让他动手,他都假装没看见。”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王旦凤获救后既不马上报警,也不积极配合警方。
李大清
跟王旦凤的谈话让我突然清醒过来。在遇到她之前,我都麻木了。
跟着牛海这两个月,只觉得自己变成衣冠禽兽,不明白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这时候,我拿王旦凤的眼光看自己,都不能相信这就是我。我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我怎么像个丧家犬惶惶不可终日?以前虽然没多少钱,日子还是过得安稳。现在我连家都不敢回,看见警察就躲。我小时候写作文,不是说长大想当警察的嘛!
牛海执意要杀王旦凤。我说:“哥,我跟你东奔西跑这些日子,做下的这些事,把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我没找你要过什么,今天一个晚上,你能给我吧?我只找你要一个晚上。”
牛海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我知道这是默许了。
我们把车开到常去的废弃小院,牛海带着枪开车走了,说他再出去转转,去找别的目标。临走前警告我,兄弟,别被女人毁了,咱们有咱们的规矩,不能坏了规矩,别让我回来再费劲。
我已经打定主意,这件事上,我不会听他的。
王旦凤
我一直跟看守我的李大清聊天,他挺好说话的。如果不是在夜里、在这人烟稀少的荒原上,而是在学校、单位,我应该能很快和他成为朋友。
“看在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份儿上,能不杀我吗?”我必须在他的老大回来前逃出去。如果那家伙回来,我就命悬一线了。
“我不会杀你,我也不会让他杀你。”他说得很坚定。
真讽刺,我的命运在情人节这天,有了几个大逆转。先是甜蜜幸福地接受了曹铁男的求婚,海誓山盟至死不渝,以为他就是我这辈子的真命天子。没想到,几个小时后的生死关头,他竟弃我而去,自顾逃命了。
本以为在劫难逃,不死也会惨遭蹂躏,却碰到一个特别的劫匪,让我在对人性失去信心时,忽然又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真遗憾,我们怎么会在这样的场合认识。”我说的是真心话。
“是啊!要是我们上了同一所学校,说不定会在一个班。那我刚才拉开车门时就会说,好久没见,请你吃饭呗。”
我笑了,他也笑了。我跟他盘腿坐在炕上,聊得挺投机,这哪像劫匪和人质?
“你懂八卦吗?男女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话,八字的前六字相同,但男女性别不同,大运是相反的。”
“你的意思是,我是劫匪、你是被劫的,所以相反。”
“我的意思是,我是受难的、你是来救我的。”
他竟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对不起,刚才吓着你了吧?”
“不是说了吗,这就是缘分。”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了,“你结婚了吗?”
“结了。”
“挺爱你老婆的?”
“一般吧!能过日子。”他反问,“你结婚了吗?”
“没有,也不想结。”
“不想结?”他坏坏一笑,“那今晚那个男的是谁?你不至于说那是你的同事,是普通朋友吧。”
“我就是今晚才不想结婚的。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们出现,我就准备嫁给他了。人哪,真不知道谁是披着狼皮的羊,谁是披着羊皮的狼。”
“我是披着狼皮的羊,今晚我指定放你走。”
“放我走了,你老大回来,你怎么办?他不是说,不能坏了规矩吗?”
“放心吧,没事。”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走吧!别跟他干了,逮着了要判刑的。”我真的有些替他担心了,想到他的老大,我还是觉得要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你快走吧!别管我了。后面有个小窗户,跳出去往加油站方向跑。”
他跳下炕,把先前抢走的东西还给我:“这是你的皮包和手机,不过你的钱都被他拿走了。”
他掏出两张票子给我,“这儿有两百块,你拿着,路上以防万一。千万别搭男人的车!”
我站起来,却迈不开脚步。他又找出一件黑色的大外套:“你的羽绒服是白色的,夜里太显眼。把我的衣服套在外面,别嫌脏啊!”
他把外套披在我身上,推我:“走啊!”
我眼泪滚落,一把抱住他……
秦箭
朱丁看着王旦凤的背影:“要对她提起诉讼吗?她毕竟对警方做了伪证。”
我沉吟一下:“算了吧!她也是受害人,心理上受了刺激。”
朱丁还是一脑门问号:“弄不明白这王旦凤到底怎么回事,来三四回了吧?哪有人质替劫匪求情的?”
“不奇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什么呀?”
陈萍拿笔敲敲朱丁脑袋:“嘿!你这个人,咱们不是在同一个教室,听同一个老师讲过吗?1973年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人质对劫匪产生感情,拒绝与警察合作。人质之一还爱上了劫匪,在他服刑期间嫁给了他。”
“我发现,只要涉及谈情说爱,你的记性就特别好!”朱丁回应。
牛海
说什么都没用了。老话说养儿能防老,父亲是儿子最好的靠山。我给不了我儿子什么了,也给父母带来那么大伤害。你们体会不了我的心情……
李大清
我没有非分之想。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我知道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王旦凤
警察,他们除了破案抓人,啥都不懂。
秦箭
王旦凤根本没有龙凤胎弟弟,她倒是有超出常人的机智冷静。
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情人节吧?
幸好她与曹铁男分手了。
唐孝果
我死得太冤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