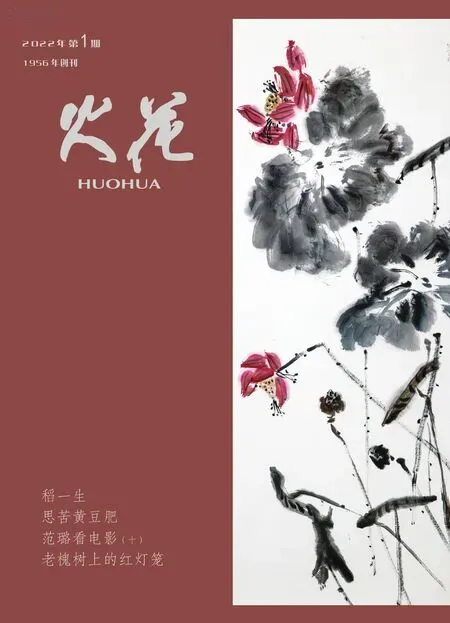老槐树上的红灯笼
荆卓然
山风携带着猪、牛、羊和鱼肉特有的香味,东家出来、西家进去地串门。几条平日里过惯了清汤寡水日子的柴狗,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享受好伙食的日子,已经近到了离鼻子只有一厘米距离的诱惑。它们那埋藏着雷霆与闪电的眼睛,这段时间看见陌生人也多了几分温柔。尤其是它们那蓬蓬松松像旗帜一样翘着的尾巴,摇晃起来风情万种、春风浩荡,昭示着天下太平、人寿年丰、合家欢聚的喜庆。
村口的老槐树下,聚集着几位老年人。农事不忙的时候他们就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唠些家长里短,一边时不时将目光投向曲曲弯弯进村的道路,已经成了一个如同电脑主机自带的固定程序,即使是格式化也无法消除的习惯。
离老槐树不远处有一座小庙。庙前的青石台阶上,坐着一位胸前戴着望远镜的男人。村里所有的小男孩,他都称呼为“超超”。大人们都这样嘱咐孩子:你聂爷爷(聂大爷)……叫你超超,你一定要答应住。你要是不答应,回来没有你的饭吃,还要打你的屁股。孩子们都很听话,男人叫他们超超,他们就高声应答:“哎!”
男人名叫聂志国。他的儿子聂超超在一次公务活动中不幸牺牲了。
老槐树下的人们谈论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的话题,杜钢牛在树上遥望着进村的山路。
“钢牛,发现情况了吗?”张大伟仰头问。要不是自己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腿脚不方便,他早就亲自爬到树上,亲眼眺望那条脐带一样的乡路了。
是的,这条乡路就是一条脐带。石槽村祖祖辈辈的人,都离不开这条脐带。他们都在这条脐带的滋养下酸甜苦辣、生老病死,演绎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张大伟在等待儿子归来,然后爷儿俩好好地喝上一壶自家酿造的美酒。
“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莫说是五六尺高的人看不见个影子,就是连一只狗也瞧不见。”在石槽村村口老槐树的树杈上,正在向远处张望的杜钢牛有气无力答道。在杜钢牛的眼睛里,恨不能把曲曲弯弯的小路揉搓成一条法力无边的绳子,把“坏蛋”捆回来过个团圆年。
老槐树据说是明朝年间,老祖宗们从洪洞县移民过来的时候,带着槐树幼苗栽在村口的。老槐树就是先辈对于故乡的一种念想,也是石槽村人祖籍在洪洞县的一个标志。
老槐树上先前还住着几窝喜鹊,后来由于年年春节前有村民爬上来眺望亲人,喜鹊觉得安全受到了威胁,就迁居到其它树上去了。只剩下几个树枝搭建的鸟窝,多少年了,依然风雨不倒,宣誓着喜鹊对于这棵老槐树拥有的产权。
老槐树上还留着许多伤痕,有子弹留下的齿痕,有火焰留下的烧痕,有雷电留下的吻痕。老槐树的树芯基本已经被虫子掏空了,据听说有人见里边曾经盘踞着一条蟒蛇,专门靠偷猎落在树上的鸟类为食。后来蟒蛇的恶行引发了上苍的震怒,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执法的雷公“咔嚓”一声放出一道闪电的法器,将蟒蛇拦腰斩杀为两段,总算是为鸟类除了一个巨大的祸害。
好在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老槐树虽然没有树芯了,但血脉畅通的、坚韧厚实的树皮还在。老槐树依然年年春华秋实,活得枝繁叶茂、鸟鸣繁华的。
杜钢牛的儿子乳名叫“坏蛋”。不用问,“坏蛋”这个另类的乳名,一方面显示了儿子小时候是个捣蛋鬼,二方面饱含着父母对儿子的宠爱。这里有个习俗,儿女的乳名起得越难听,阎王爷越不待见,儿女的成活率越高。所以村子里的老年人中类似粪锅、狗屎、泼小、泼妮等很不文雅的乳名,随便一拾掇就能满满当当地装一卡车。
有人掐指计算过,“坏蛋”已经三年没有回来过年了。今年要是再不回来过年,怕是杜钢牛就要崩溃了。别人家都是团团圆圆、红红火火地过大年,自己家却冷冷清清、冷锅冷灶的。没有儿孙膝前腰后绕,你说他杜钢牛过的这是个什么年啊?
每到春节前,石槽村村口的老槐树下就会聚集一群留守老人和孩子,外号人称“9961”部队。他们天天吃罢早饭就开始聚集在树下,伸长脖子向远方的仅能单行一辆小车的小路遥望,隐隐约约看见一个黑影过来了,大家就激动起来,揣测着这位是谁家的孩子。他们恨不能变成长颈鹿,好更早更方便地看见孩子们回家的身影。
有人说,咱中国人太注重传宗接代,太关注孩子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其实全球包括几乎所有动物在内的生物,不注重后代的动物少之又少。假如家里没有孩子身前身后“捣蛋”,如同一个人走在前方没有半丝光亮,面前最多只是点着一支蜡烛的路上。蜡烛的光亮灭了,人也就灭了。而我们假如有后代,一代代传承下去,几千年、几万年……之后,另一个版本的你、升级换代的你,依然活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上。
老槐树上的“哨兵”,一旦发现有人回来,立刻就会告诉树下所有的“长颈鹿”。有时候即使认出是谁家的孩子回来了,他也故意要说看不清是谁回来了,让大家心里的光亮都来一次充电的机会。
常常是黑影往村口移动,老人和孩子们向黑影移动,然后认出是自家孩子的人,像运动场上的百米冲刺一样,向孩子扑过去。他们先接过孩子手里的大包小包,然后亲亲热热一起向家里走去。
其余人的面部表情逐渐晴转多云,口里说着俺秀秀、俺欢欢、俺晨晨估计也快回来了,心里却空落落地没有一个准信。
该回来的总是要回来的。在老槐树下等待亲人的人,快过年以前,刚开始呈现的是加法模式,等待的人逐渐增多。越是接近年关时节,呈现出的却是减法模式,等待的人一天天减少着。
随着回家过年人口的逐渐增加,村子里的炊烟也逐渐多了些扑鼻的香气。树下等待的老人们,却觉得那炊烟是自己烧焦的心冒出来的。有的老人甚至放出了狠话:龟儿,龟孙们今年要是胆敢不回来过年,我就和他们断绝关系,从此后石头是石头树是树,不认他们了。我活着,家是住活人的房子;我死了,家就是现成的坟墓。有本事,他们等我死了也不要回来,大河有源头,小草也有条根根,人走得再远还能忘了祖宗?说归说,骂归骂,埋怨的时候面部表情再凶神恶煞般可止小儿夜哭,儿子、女儿、孙子、外孙们千里迢迢回来了,马上就变成了海纳百川、春光明媚的菩萨,欢天喜地领着孩子们回家,杀鸡宰羊地为孩子们改善着伙食,满脸憋不住的笑容里,哪里还有半点乌云密布的气象。
按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通讯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是石槽村实在是太偏僻了,偏僻到你拿着放大镜在本市的地图上寻找,才能勉勉强强看到一个针眼大的黑点,标注着石槽村三个有气无力的汉字。十万大山挡住了外边的风光,也挡住了他们连接世界和亲情的手机信号。
村里为数不多的几部座机,由于山风肆虐经常断线,刚开始电信公司还给维修一下,后来觉得维修成本太大,加上村子和邻村合并后,村委会办公地点设在了相对繁华一些的邻村,电信公司就不给石槽村维修电话线路了。
村子合并后,村名改为了邻村的名称,但石槽村的村民们在嘴巴和心里还是称自己是石槽村人。他们认为改村名如同男子到女方家当倒插门女婿,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张大伟忽然想起了父亲当年爬到老槐树上侦查敌情的事情。
张大伟的父亲,当年是一名游击队员。为了防止日本鬼子偷袭,村子里常年派人在老槐树上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通知村民们转移。张大伟没有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老槐树上又设上了“岗哨”。只是这次瞭望的不是敌人,而是连通着自己内心山河的亲人。
张大伟儿子的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某某市财通四海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相”。实际上剥掉那个夸张的外壳,张晓相只是个骑着电动三轮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捡废品兼收废品的劳动者。每年春节前是“公司”生意的黄金期,市民们收拾房间的卫生,顺便会扔掉许多可以卖钱的废旧物品,张晓相哪里会舍得这个时机,所以张大伟总是失望。
杜钢牛望远处望得心烦了,脖子疼了,就开始扯着嗓子唱歌。歌声翻过一座座山梁,传出去很远很远。
哎嗨嗨哎嗨哎嗨啊
嗨嗨哎啊,
羊肚肚手巾哟,
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容易啊,
拉话话难。
你在那圪梁哟,
我在个沟。
咱们拉不上那话呀就招一招手,
瞭见那个村村哟,
瞭不见个你,
泪蛋蛋就洒在了沙蒿蒿林。
“啪啪啪啪……”一阵掌声从不远处传来。聂志国穿着一身泛白的消防制服,拍着手掌走了过来。
聂志国因公牺牲的宝贝儿子聂超超,从小就生得虎头虎脑招人喜爱,是村里新婚妇女心中的“样品”,都希望自己将来也能生个这种版式的儿子,抱回娘家接受父母和邻里上下的检阅。大学毕业后,暂时没有就业的聂超超,经过报名、体检、政审等一系列程序后,光荣参军。聂超超穿上那一身军装,显得高大威武、英气逼人。父亲母亲的脸上一年四季都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服役期满转业后,聂超超为了兼顾和大学时期就恋爱至今的女友娜娜,主动要求组织安排他到市消防总队工作。但是超超在一次抢救森林大火的行动中,风向忽然发生了逆转,本来他和几位战友已经突围出火圈了,但是为了抢救被火围困的战友,他重新返回火场,不幸光荣牺牲,只为父母留下几张帅帅的军装照片和扯心扯肺的思念。
失去儿子后,聂志国先是戒掉了持续数十年的烟瘾。据听说他儿子聂超超扑救的那场森林大火,就是因为一位山民无意乱扔的一枚没有熄灭的烟头引发的。由于思念儿子过度,聂志国后来就逐渐变得有点疯疯癫癫的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成天戴着一个望远镜,向远方眺望。他说戴上望远镜就可以望见儿子超超。聂志国说得很认真,别人听了心中不免一阵唏嘘。
聂志国来到老槐树下,破天荒地解下望远镜来递给杜钢牛,说:“钢牛,戴上望远镜看看俺家超超走到哪里了?往年的这个时间他早就回来,坐在家里吃他妈妈包的韭菜猪肉馅扁食呢。俺家的扁食那才叫个香呢,白面是自己家地里靠农家肥长大的,韭菜是自己家地窖里生的黄牙韭菜,猪肉是五花肉剁的,外边看白玉包翡翠,咬一口满嘴流香油……”聂志国在村里当过民办教师,还爱好文学,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杜钢牛不喜欢听聂志国自家夸奖自家老婆的手艺多么精。他老伴儿做的饺子外形像元宝珠光宝气,内里猪肉蔬菜蘑菇大团圆,尚未入口已经香气扑鼻,那才叫真正的皇家气派落户民间餐桌呢。但是他从来不在外边宣传老伴的手艺,只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吃在胃里。他像猴子一样嘶溜一声溜下树来,接过望远镜,手脚并用又爬上了老槐树。平时,这架望远镜是聂志国的心爱之物,谁也甭想摸一下。他害怕自己动作稍一迟缓,聂志国改变了主意,这望远镜就用不成了。
那次,聂志国好奇心极强的表弟杨老虎,执意要看看聂志国手里的望远镜到底能不能看见聂超超。结果他的手还没有挨到望远镜的表皮,就被聂志国狠狠地打了一下。
杨老虎的儿子杨牛小,在市里开火锅店发财后,让原配夫人留在村里照顾公婆,自己在市里包了个十八九岁的漂亮女服务员逍遥快活。原配夫人如何能咽下这口鸟气,一个人南下打工,至今没有任何音信。好在两个孩子都在县里的寄宿制学校上学,不用杨老虎和妻子操心。儿子和媳妇夫妻分居、分离,倒也没有让平静的生活掀起惊天的浪涛来。
杨老虎发誓这辈子不再见这个孽子。结果,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带着两个放寒假归来的孙子,来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开始张望儿子的身影。
杨老虎摸了摸被聂志国袭击过的手,夸张地放在嘴巴边哈了几口气,说:“志国,这几天这只手本来有点麻,结果让你这一巴掌‘啪’地一下子就给治好了。我看你是成了聂大仙了,今后可以开个诊疗所,给我们看个头疼脑热了,谢谢你啊!”
大家哈哈大笑。
去年春节前,杨老虎的儿子杨牛小是开着私家车回来的。车子到了村口,牛小一打开车门,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就抱着一个孩子钻了出来。
杨老虎一看孩子那四方脸、粗短腿的相貌,就知道是自家的品种,抱着孩子就流下了眼泪。他说,儿子不亲,儿子勾搭的女人更不亲,但小孙子是杨家的骨血,小孙子没有错,小孙子是亲的呀!
杨老虎今年春节前,提前半月就惦记上孙子了,每天没事就坐在老槐树下,眺望着进村的道路,想象着小孙子是胖了,还是瘦了。
杜钢牛戴着望远镜往远处一望,视野果然开阔了许多。他知道自己家的“坏蛋”春节是不会回来的,因为或许在回家路上的火车站、汽车站乃至家的周围,会有几双眼睛盯着疑似“坏蛋”的每一个人。前几年,“坏蛋”为了给女朋友家筹集彩礼钱,一时糊涂借了高利贷,从此后就陷入了一个无底洞中。截止目前,先前借的5万元,已经利滚利达到了60余万元。其中还不包括已经还了的15万元,有些民间高利贷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啊!
“坏蛋”现在带着妻子四处躲避,每一个地方打工都不会超过三个月。前些时候,他带着怀孕的妻子晚上“潜伏”回家,和父母吃了一顿团圆饭,次日天还没有放亮,就又偷偷离开了村子。临走,杜钢牛将家里仅存的一千来块钱偷偷塞到儿媳妇的手里。儿媳妇推了几次,看公公婆婆坚定的眼神,只好含泪收下了。
杜钢牛的肩头扛了一把闪闪发亮的锄头,老伴的手里拿了一把连夜重新开了刃的镰刀,送了儿子和儿媳妇十几里地。如果遇到讨债的,杜钢牛就计划和他们拼命。如果自己的性命能够换来儿子全家一生的平安,他也认了。人活着为了啥,不就是图个子孙团圆、平平安安吗?
明明白白知道刚走不久的儿子不会回来过年,杜钢牛还是装模作样在村口瞭望儿子。他要用行动告诉讨债者的“卧底”一个错误的信息:“坏蛋”确实失踪三年了。
是的,最近每到晚上,杜钢牛家的院门外、房顶上就会出现身份不明的人。他们渴盼“坏蛋”能够回家过年,然后抓住他,让他还钱。
他们还自己发明了一种让欠债人还钱的方式,那就是将欠债者“抵押”到私挖滥采者的黑煤窑里打工,欠债者什么时候把钱还清了,什么时候才可以获得人身自由。
虽然心中有一长串担心,但是杜钢牛打心眼里渴盼儿子能够再次回来,全家平平安安、和和美美、热热闹闹地在一起,悬挂红灯笼、张贴春联、给祖宗上香、包饺子、喝烧酒……过一个团圆年。
眼看着时间就到了年三十的晚上了,老槐树下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老人。他们觉得自己的脚下已经生出了根须,常常等到很晚才回家,失望的脸上堆满了无奈和凄苦。
有人说,县里的村村通公路工程,让回村的路多了好几个岔道,这黑漆漆的晚上,万一孩子们回来,找不见路可咋办啊?张大伟说,咱是不是应该往树上挂上一个大红灯笼,在灯笼上写上石槽村,这样孩子们晚上回来的话,远远就可以看到大红灯笼,远远就可以望见石槽村。大家一听,我的奶奶呀!高手在民间,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立刻就有人回家连夜糊了一个大红灯笼,懂电工技术的杜钢牛专门从村委会扯出一路电线来,一盏像母亲等待儿子熬红了的眼睛般的红灯笼造型的路灯,就这样顺利地在老槐树上诞生了。
挂红灯笼的地方,抗战时期挂着一口铁钟。放哨的民兵发现鬼子来了,就一边手执一根火柱拼命敲打铁钟,向村民们报警,一边大声呼喊“狼来了!狼来了!”,催促村民赶紧转移。同时,这急促、激昂的钟声,也给了日本鬼子一个警告———豺狼们,小心着点,我们知道你们来了。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等待你们、犒劳你们的,只有大刀、长矛和猎枪。
按理说,日本鬼子听到钟声,应该加快进村的步伐,在老百姓没有完全转移出去以前进入村庄,然后伸出魔爪开始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实际上当日本鬼子暴露了行踪的时候,看见离村子很近了,好像三步并作两步,几秒时间就可以进入村子了。实际上农村的道路很特殊,非常善于欺骗外人的眼睛,往往是你看见村庄近在眼前,实际上远在天边,没有半小时四十分是根本进不了村子的。从发现日本鬼子的行踪到鬼子进入村庄的这段时间,老百姓完全有较为充足的时间,藏好粮食,牵着牲畜,藏到地形复杂的大山深处去。
在石槽村,日本鬼子吃过一次这样的亏。那次他们听见老槐树上的钟声有人敲响了,领头的赶紧抽出指挥刀,“呀唧唧!”剑指石槽村,发出了冲锋的命令。结果等他们气喘如牛冲进村子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小时之后的事情了。正当鬼子们喘气未定、连枪也端不稳的时候,村里负责掩护村民撤退的民兵们的土枪土炮,已经开始在制高点发言了,打了鬼子兵们一个措手不及。最后鬼子兵只好报复性地烧了数十间民房,抬着七八具尸体灰眉土脸地狼狈而逃。
当年挂铁钟的地方,现在挂上了大红灯笼,挂上了一颗平安果,挂上了父母对儿女的思念与渴盼。大红灯笼是父母想念儿女回家的心脏啊!红彤彤、热腾腾,散发着光与热,散发着亲人的气味。
村里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家的儿女陆陆续续都回来过年了。几位一直没有接到儿女的老人们,开始给自己找理由、找台阶。大家有的说儿子工作忙,估计正月十五回来闹元宵;有的说女儿没有买下火车票,过了交通高峰期,估计就回来了。
张大伟和几位老人,正要趁夜色没有完全淹没道路时,回家做饭睡觉,忽然,远处出现了汽车的灯光,光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许多老人的心房和笑容。车子还没有开到老槐树下,已经被迎上来的老人们截在了半路。大家看清了,车子里坐着的是张大伟的儿子———“某某市财通四海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相”同志。
张大伟患小儿麻痹症的腿好像忽然康复了,他上去拉开儿子借来的汽车的车门,说:“我就知道你要回来的嘛!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嘛!你要是不回来的话,让我这个年咋活呀!”
张晓相下车给大家每人发了一支香烟,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想年后竞选村委会主任,再想办法接通村里的通信网络。他说咱村水质、空气等自然条件好,没有污染,要在村里开个农家乐,一边伺候他爹张大伟,一边养家糊口,一边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张大伟拍了一把儿子的屁股,快不要吹牛了,你这点本事爹还不知道?
张晓相说,爹呀!俺这不是吹牛,俺在城里一边收废品,一边琢磨咱村的事情。成与不成咱可以试试呀!总不能守着这破烂的房子,穷一辈子呀!咱村要是再不发展,等你们这辈子的老人都走了,整个村子也就等于报废了。
几位老人听着有理,说:“对呀!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口尝一尝。过了年村委会换届,咱就选年轻点的愿意回村干的人试试。”
大家拥着张晓相刚要回村,远处又隐隐约约有了车灯的光芒。一辆依维柯汽车穿透浓浓的夜色,一直开到了村口。
车子内坐着七八名身着火焰蓝制服的小伙子,一下车就打听聂志国家的住址。
这些小伙子是聂志国儿子聂超超生前的同事。今年,他们放弃了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机会,留足值班人员后,昼夜兼程从一千多公里的驻地赶来为聂志国夫妻拜年。进入乡村小路岔道的时候,由于没有无线信号,车子的自动导航系统失灵,幸亏挂在老槐树上的红灯笼为他们导航,一颗颗激动的心脏,才顺利来到了石槽村。
张大伟忽然感觉自己产生了幻觉。当年,他的父亲在这里放哨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望见远处出现了一支举着火把的队伍,他以为是日本鬼子又来了,赶紧通知老乡们转移到了大山上。结果,这支队伍进村之后,没有出现过去那种四处烧房子、杀鸡、杀猪……的暴行,而是就像一阵轻风进入了村庄。后来村长派了几个胆子大的男青年,悄悄摸回村庄一看,进入村子的原来是一支八路军队伍。这些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老百姓不在家,他们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进老百姓的家门,背靠背坐在村子的大街小巷里,除了几个流动岗哨外,全部炒面就着白开水,草草吃了几口饭就进入了梦乡。
村长一听原来是咱自己打鬼子的队伍来了,立刻招呼大家赶紧回村,赶紧家家生火做饭,犒劳八路军战士。那天晚上,村子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家家户户做出最好的食品招待八路军战士们。有的人家甚至还从院子里挖出珍藏着的“女儿红”酒,让战士们喝。人家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把身家性命都贴上了,咱给人家吃点饭、喝点酒、杀只鸡,还不应该吗?
妻子和儿子、儿媳妇、孙子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孤寡老人杨广来,含泪说,我老了,没有办法为妻子和孩子们报仇雪恨了,八路军战士为咱报家仇国恨,告别家乡,离妻别子,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呀!
老百姓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他们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与感恩。
记得那天晚上,战士们的喊声响彻云霄:“为杨老伯全家报仇,为全中国百姓报仇!”气壮山河的喊声,震得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个不停。
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七八十年以后,又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年三十晚上来到了石槽村。
早就有人快步跑进村子,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人。大家不约而同,从不同的方向向聂志国家聚集。
聂志国两口子听到这个信息,一时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站在大门外,等待着这群可爱的亲人。他们一个左手搓右手,一个一个劲地往下拽衣服的前襟。
小伙子们来到聂志国家门口,领头的借着大红灯笼的光芒,透过这中间站着两位老人、四周站着众多父老乡亲的队形,一下子就找到了他们要寻找的主角。
“稍息!立正!敬礼!”随着一声口令,小伙子们动作整齐划一,齐声叫到:“爸爸!妈妈!过年好!”
然后,泪水如瀑布在灯光中闪闪发亮。
不知道谁从家里拿来了花炮,噼噼啪啪的花炮声,点燃了石槽村的快乐。
聂志国疯疯癫癫的迹象一点也没有了。他和妻子的双手在衣服上擦了好几遍,同时伸出颤巍巍的双手,分别握住站在最前边的小伙子的左手和右手,招呼道:“孩子们,快进家,快进家,爸爸妈妈给你们煮扁食吃。咱家的扁食那才叫个香呢,白面是自己家地里靠农家肥长大的,韭菜是自己家地窖里生的黄牙韭菜,猪肉是五花肉剁的,外边看白玉包翡翠,咬一口满嘴流香油……俺超超可喜欢吃呢,一顿能吃五六十个。”
杜钢牛跑回家拿来了自家做的红烧肉,后边跟着端着一大篦子元宝饺子的老伴。张大伟回家为孩子们端来了新出锅的黄米糕,杨老虎回家现炒了一大锅冒着热气、散发着香气的猪肉过油肉,杨广来的外甥将女儿女婿带来的好酒和好烟拿了出来。
聂志国满脸都是大红灯笼的红光。火红的灯笼映红了小院子的吉祥,红红的灯笼在欢快的花炮声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
忽然,村口又传来了汽车的鸣笛声。这次从车里下来的是一位女士。女士的怀里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一步一步向聂志国家走来。
有人认出来了,女士是聂超超的未婚女友娜娜。
聂超超牺牲前,娜娜来过几次石槽村。面容姣好、身材窈窕、文文雅雅、开口必笑的娜娜,为石槽村人留下了青石上刻字般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石槽村人把娜娜当成了全村人的未婚媳妇。娜娜和聂超超走到谁家,都是满满的阳光般的笑脸,甜到心窝里的话语。娜娜来到石槽村,每天都有人家排着队请她和聂超超吃饭,煮油糕、枣介糕、莜麦面推窝窝、土鸡蛋卤拉面、韭菜饺子、土公鸡炖蘑菇……乡亲们恨不能掏出心肺肝脾来招待这天生的一对。娜娜说,她好想变成猪八戒,把乡亲们的美食与深情厚意都装到肚子里去。
聂超超牺牲后,娜娜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她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烈士生下了这个遗腹子,并在年三十夜让父亲开着车,沿着公路的大脐带,接通乡村的小脐带,将她和孩子送了回来。
聂志国的妻子抱着孙子,泣不成声。这孩子虎头虎脑,目光比十五的月亮还暖人,活脱脱一个缩微的、新版的儿子聂超超啊!尤其是孩子见到他们的时候,那摄人心魄的一笑,两口子有了醉酒的感觉。
聂志国以为这一切发生在梦中,他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看来不是在做梦。他觉得这样还是有点像做梦,又顺手在老伴的胳膊上掐了一下。老伴“哎哟”一声,亲昵地打了一下他的手。
聂志国伸出粗糙的双手,紧紧地、狠狠地握住娜娜父亲的双手,一声“亲家!”,立刻就泪如倾盆大雨。
聂超超生前的同事们,目睹了这暖人的戏剧性的一幕。他们再次嘴和口令———稍息!立正!敬礼!齐声喊:“嫂子!嫂子!亲亲的嫂子!”
大红灯笼映照下的娜娜,脸色分外喜庆、温暖,那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泪花,汇聚成了村里那脉流淌了数千年的小溪。
村里那几条柴狗,也跟着主人来到了聂志国家的大门外。它们蹦蹦跳跳戏耍着,生机勃勃的尾巴摇摇摆摆,打扫着内心集聚了一年的尘埃。
没有人理会,杜钢牛忽然失踪去了什么地方。
忽然,杜钢牛那原生态的民歌声,从村口大槐树上传了回来。歌声乘着大红灯笼的光芒,温暖了山村的夜色与寒冷。
正月里来是新年,
家家户户挂红灯。
老爷高堂饮美酒,
娃子炕上翻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