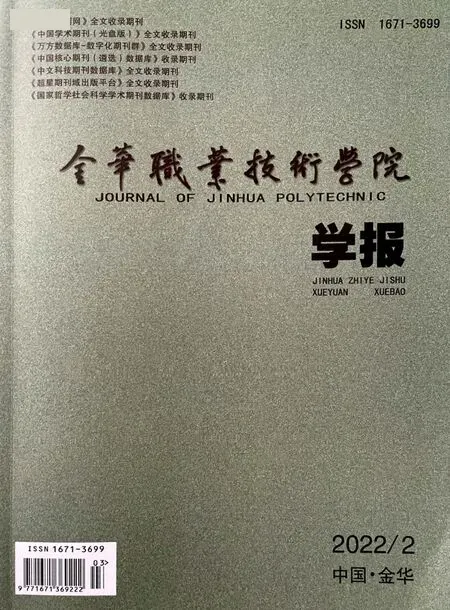沈从文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生命伦理
陈全丽
(西南大学,重庆 400700)
现代文学中充斥着大量“疾病”话语。例如,鲁迅“弃医从文”,打通了医学与文学对人类共有的治疗功能;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身患某种疾病,且疾病不止是他们生理上的表现,甚至成为一种人格气质。相比之下,虽然沈从文并不是一名以疾病书写或“疾病情结”著称的作家,但他在小说世界中对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书写态度和所表现的生命意蕴已经构成一个整体的城乡对照下的病态与健康的对比。本文并非是要探讨沈从文对城乡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而是聚焦于沈从文笔下具体的疾病书写。其小说的文本《八骏图》《三三》《夫妇》等中的人物都患有明确的病症,且这些疾病既是文本中一个具体符号,也可能隐含更深刻的内涵——城乡对疾病的不同态度透露出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疾患认知和生命伦理所发生的转变和冲突。而在对疾病的书写中,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对疾病的修辞化使用以及对疾病、死亡和生命的理解,所指向的正是他对人类生命的严肃思考和伦理关怀。
一、城里人与乡下人:疾病成为群体身份认同的标志
小说《三三》讲述了一个城里人到湘西苗区的一个堡子里去养病的故事。城里人的出现引起当地乡民的关注和想象,乡民对城里人所患疾病的看法及对他养病中种种奇怪行为的猜想和不理解,表现出城乡间的隔膜,女主人公三三去宋家时,听到了乡间妇人们对城里人的讨论:
“……他们养病倒稀奇,说是养病,日夜睡在廊下风里让风吹,……脸儿白得如闺女,见了人就笑,……谁说是总爷的亲戚,总爷见他那种恭敬的样子,你还不见到。福音堂洋人还怕他,他要媳妇有多少!”
“谁知道是什么病?横顺成天吃那些甜甜的药,在床上躺着,到城里是享福,到乡里也是享福。老庚说,害第三等的病,又说是痨病,说也说不清楚。谁清楚城里人那些病名字。依我想,城里人欢喜害病,所以病的名字也特别多,我们不能因害病耽搁事情,所以除打摆子就只发烧肚泻,别的名字的病,也就从不到乡下来。”
另外一个妇人因为生过瘰疬,不大悦服宋家妇人无端的话,就说:“我不是城里人,可是也害城里人的病。”
“你舅妈是城里人!”
“舅妈关我什么事?”
“你文雅得像城里人,所以才生疡子!”[1]18
这段对话很有趣,第一段是对城里人跑到乡下养病的讨论,养病的方式怪显得城里人也很怪。乡下人认为城里人形体消瘦,白得像闺女,明显和乡下人的形象不一样。在谈论中,大家想象着他的身份,认为他肯定不愁媳妇。在乡里娶媳妇,婚丧嫁娶等,是很重要的事,因此婚嫁更是乡间谈论家长里短的重要话题。紧接着这些对话中又透露出一个更有趣的观念——城里的人爱生病,并且有很多病的名目,乡下人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病人或调养自己,所以就生些简单的病,更不需要精心养病。在他们看来,有些病是专属于城里人的,某一种疾病甚至能够成为身份的区别,将城里人和乡下人区分开来,病的种类也就成为了乡下人对群体身份的区别和认同。很明显,乡下人把痨病(肺结核)当作城里人的专属,因为结核病患者的病容多是苍白、柔弱和文雅的,这是城里人才能有的形象气质。
从病理学上看,痨病,也就是结核病,常见的是肺结核。且它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慢性疾病,不受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在1943年发明链霉素之前,肺结核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会直接导致死亡[2]。在真正病因结核菌被发现之前,肺结核被视为一种因长期过劳而引发的疾病,因此中医上又称之为“肺痨”或“劳瘵”。小说中将其描述为“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飕飕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事物”[3]15。因此,从生活环境和经济状况来看,痨病并不是一种专属于城里人的疾病,它更与贫苦相联系。对于一个病恹恹、身形消瘦、穷愁潦倒的人,民间还有一个忌讳的称呼:“痨病鬼”。可见,中国民间虽对痨病有一定认识,但更多的是对其无法被治愈和恐怖传染性的恐惧。
但在《三三》中,我们却看不到人们对痨病的恐惧,反而看到他们以好奇的心理打量病人的病容和养病方式。而且,这个病人并不是穷苦、可怜、狼狈之人,而是一个在城里和乡下都过着舒适生活的城里人。疾病不但没有减损他的风姿,反而令他与乡下人健壮、豪爽甚至粗鲁的形象显得格外不同,因此在乡人眼中这个城里人虽然处处古怪但外形是美的。这样的审美认知显然受到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前期创造社浪漫思想的影响,其根源可追溯到西方十八世纪中叶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想。结核病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身份或个性的象征,“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十九世纪礼仪的标志”[3]27。结核病病人的病容和死亡甚至被浪漫化和美化,患结核病的梭罗于1852年写道:“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3]17“这种将结核病浪漫化的风气在西欧以及日本盛行一时,使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创造社的作家深受影响。”[3]27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肺结核脱离了恐怖色彩,成为一种“灵魂病”“个性病”“天才病”,且生病的姿态也被审美化。“多数病症都不可能与美结缘,总是跟形体的损伤和丑陋相联系,惟有身材消瘦、脸孔白皙的肺结核病人,不但形体尚能保持原有的美,苍白的脸容所泛起的淡淡红晕甚至会更有一种风韵。”[4]从三三以及乡人们对城里人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沈从文也受了这种审美倾向的影响。
乡下人将疾病作为区分群体身份的标志,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在医疗病理知识方面的缺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偏狭的排外心理,尤其是在面对城里人时,他们处处要做出区分,以显示城市与乡村的不同,从而表现出“我们”乡下人不会得那种病的优越感。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更体现出一种文化观念的错位,城里人虽然来到了乡间,但从未走进乡间的伦理秩序,始终显得格格不入。城里人带着城里的病来到乡间,又因病死去,好像仅仅给乡下人看到了城里人的样本,却并没有促成双方互相了解,甚至产生更深的隔膜。故事结尾处,城里人死了,许多人都在说这个白脸人的一切,但事实上这些人与这城里人并没有什么熟识。
二、疾病与健康:城乡对立视野中的伦理指向
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疾病和病态似乎成了城市文明的代名词,城里人丧失了生命活力,人性欲望被压抑,生理和心理都朝着病态的方向发展,而乡下人总是自然、健康、活泼,时刻展现出勇气和血性。《绅士的太太》中,有位绅士患了脑瘫;《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来到风景优美的青岛大学,把自己住的房子称为“天然疗养院”[5]205,并且诊断甲、乙、丙等教授都是病人。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病的病症进行了生动勾勒,城里人虽然有文化知识,但被那些道德教条和身份束缚,以至于在面对人类真实的人情、人性时要装模作样,在精神、心理、身体的压抑中变得精神分裂。沈从文在题记中写道:“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是一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5]195
相比城里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患有疾病,作为乡下人的三三表现得活泼天真,在母亲身边,说的也都是母亲听得懂的话,“那些凡是母亲不明白的,差不多都在溪边说的”[1]15。她在溪边对着鸭子和鱼说话,与自然生灵合作无间、无话不谈。再如《边城》中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6];傩送和天宝都有着湘西苗地男子的勇敢、豪爽、诚实和热情;祖父常年坚守渡船,固执得只求心安理得;船总顺顺待人慷慨仁义、大方洒脱;水手在水上做活吃饭,把命交给水和老天;就连歌女也坚守着一份鲜明的爱憎和义利观念。这些都体现出沈从文在与城市对峙凝眸中所倾心和自持的健康、和谐、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对比中,我们很容易得出“城市-疾病”“乡村-健康”的关联,这已成为对沈从文小说中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书写的共识。肯定者认为这是沈从文以“一种健康醇厚、富于生命气息的视角,透见到现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人性的荒谬与缺失”[4]84;否定者则认为这是沈从文因都市生活受挫,“依靠对湘西和对都市的双重建构而对其自卑进行了补偿和超越”[7]。然而,笔者认为,沈从文笔下的城乡对峙以及它们身上对应的疾病或健康的文化内涵,是更深层地表现出城里人和乡下人所持有的不同生命伦理观,因此他们无法互相理解,甚至在文化错位中视对方是奇异景观。
虽然疾病可以成为群体身份认同的标志,但是疾病的细菌感染并不会区分人的身份。我们可以说某种环境下更容易得什么病,但疾病本身对人类是一视同仁的,不存在城里人喜爱得病或者本就是病态的,而乡下人就与疾病无缘。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之所以会形成城里人是病态的而乡下人是健康的认知,除了沈从文自己的爱憎情感和对文明的反思之外,最核心的原因是城乡对疾病的不同认知。疾病损耗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活进程和日常生活感觉,甚至直面死亡,因此,从生病到死亡是人类生存的大话题,关系着城乡不同的生命观念和伦理秩序。
对待疾病,城里人接受的是现代医学知识和医疗观念,认为生病是身体机能的病变,通过医生的治疗就可以令身体痊愈。西方医学被传教士带进中国,改变的不只是医疗的工具和技术,更是一整套对待生命的思维模式。现代西医改变了中国人对身体的认知,借助科学仪器,身体被清晰地展现为一幅图像,让医生和病人清晰地看到身体机理的变化。由于治疗慢性病或者精神、心理上的疾病,可能需要去一个脱离日常生活压力、环境优美的地方疗养,因此,我们看到《八骏图》中的达士先生去到了美丽的海边;《三三》中的城里人专门到乡下养病;《夫妇》中的璜住到村里,希望借助乡间的清静把神经衰弱症治好。
然而,西医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理念进入传统乡土中国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思想传播的困境。最先取得成效的是风气开放的大城市,而社会关系和伦理结构都具有稳定性的乡村则面临较大困难。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湖南湘西苗区,那里的人们虽对城市充满想象,但依然坚守自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作为早期西医传教士的胡美医生,在长沙城内开办了第一家私人诊所。有一次,他接待了一位病情十分严重的病人,经过多番治疗,病人的病情反而愈加恶化,在诊所工作的一名当地苦力出于对同乡心理的了解,建议胡美医生把病人送回家。胡美医生对此很难接受,因为他知道这个病人被送回那个糟糕的环境后会有怎样的后果。按照现在的观念去看,若是病人在诊所死亡,可能会砸了诊所的招牌,甚至可能因家属的不理解而引发医闹。但当胡美将自己的苦闷告诉国文老师后,得到的解答是在乡民的生活中灵魂回到居留地是最重要的,因为“身体就像一个‘栖息的楼阁’,等待着灵魂的返回”,若是死亡发生在家庭以外,就会让漫游的灵魂找不到身体停留的场所[8]。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乡土中国对生命的理解。乡下人并不是不会生病,而是他们对待疾病、死亡没有那么惧怕。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信仰虽然有些功利性但总的倾向是“敬天畏神”。古代生命哲学认为,人的生命不是肉体和精神的分裂而是形神合一,强调的是内部身心与外界万物的协调一致。疾病不是外物入侵身体的敌人而是生命运转的不协调,而医者的职责就是调整生命的节奏,帮助病人重新回到和谐的生命轨道上。在古人的生命智慧中,生命最重要的不是生和死,死不是生命的消亡,而是生命状态的转化。人体生命与自然生命协调一致则个人的物质生命有涯,但在宇宙万物的运动中,生命是“生生不息”的繁衍。具体表现在“人的生命延续上即为‘男女’,而将阴阳、天地、男女比类联系起来,就以血缘的传承弥补‘人’的个体生命的短暂”[9]。所以,在《三三》中,人们对城里人患病的关注,远不如其婚姻或者家庭关系更能引起兴趣,而且有关婚姻嫁娶,包括三三的婚姻之事的谈论和想象始终贯穿在文本之中。《八骏图》中的教授们,因为精神意识和人性欲望的分裂,心理的压抑和病态造成了身体机能的萎靡。
另外,沈从文描写的乡土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他的老家湖南凤凰,那里虽是汉族、苗族、土家族的聚集地,但在文化上又以苗族文化为主。“苗族尊敬自然与生命的文化行为背后,有其特定的生命伦理与‘神性产权’观。这套观念认为‘万类有命、万命共尊、万物共荣,神灵才是一切资源的终极管护者与拥有者’。”在苗族的医药文化中,“巫医结合”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而选择“‘巫医结合’这种治疗模式,主要是受到苗族对生命神性认知的引导。这种生命神性认为,生命不只是一部由各个器官构成的‘精密机器’,而是‘肉体和灵魂’的共生形式”[10]。与之相反的西医思想是在生物学、物理学等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形成的,主张把人的身体和灵魂区分开。现代医学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部“精密机器”而疾病是外部侵入的干扰因素,治疗过程就是通过破坏身体达到祛除病源的目的,从而令身体痊愈。因此,城里人对待生病的态度是改善,乡下人对待疾病甚至死亡的态度更多的是接受。
由于医疗服务措施的建立和完善改变了中国民间传统的医患伦理关系,因此病人愿意脱离熟悉的家庭亲缘的保护和照料,把自己委托给陌生的医务人员。《三三》中,乡下人并不能理解那个白帽白袍的女人以护士身份服侍病人,觉得花钱请一个陌生女人来照顾病人是不可靠的,甚至猜测她是“城里人的少奶奶,或者小姨太太”。作者在此处展现了两套不同的伦理观念,表现出中国传统乡间民众在面对违背自身日常伦理秩序的行为和观念时,习惯于按照自身经验去合理化接受。将生病的身体委托给专业的医生及护理人员,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西医传教士带进中国的。很明显,城里人接受的正是这一套医患伦理——花钱请专业的护理人员照顾自己,请城里的医生为自己看病,并且到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疗养。但这样对待疾病的方式和其中的伦理关系明显不被乡下人所接受。
三、疗救与病亡:重构生命伦理的理想与反思
在《三三》《八骏图》《夫妇》当中,病人要么是身处自然乡村中,要么去到风景优美的海边,其目的都是脱离原有的世俗压力,在清静闲适、人性淳朴的环境中治病。然而,《三三》中,患病的城里人最终还是死了;《八骏图》中,达士先生刚去时是以医者的身份自居,还为其他教授做了诊断:“这些人虽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便是一种心灵上的欲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5]206只不过这位有着救治他人愿望的疾病诊断者在病态的环境中渐渐成为那些人的同伴;《夫妇》中,城里人璜认为到乡间生活是一场闹剧,最终还是考虑回城里。可见,自然风景的美好、乡间自然人性的淳朴都无法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虽有论者认为这是因城里人的都市病和种种恶习已经病入膏肓,大自然的灵药也不能挽救城里人的病亡[4]81-85,但除了强调沈从文针对城乡不同的情感态度和批评话语之外,我们也应该理性分析城乡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这样才能更好理解沈从文的生命伦理观,不然单说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对自然人性的赞美就会显得僵硬和空洞。
城里人和乡下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与自然的关系非常亲密。在苗族文化中,自然处处是神灵的造化,万物有灵。因此,沈从文笔下的乡间儿女在与自然相处时并没有区分物我的界限,例如,对于三三的事,鱼甚至比三三的母亲知道的多。沈从文对生命有独到的理解,其理想的生命伦理中有明显的泛神论倾向,“一个人过于爱有生的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11]。
城里人泛指那些生活在都市,在地理空间上与自然山水相隔离,并且受现代文化思想影响的个体。从空间上来看,城市的建构已经把人从自然万物的生息中抽离,城市生活更多的是一种规划的生活和制造的生活。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强调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强调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因此,在城里人眼中,风景是他们观照、欣赏的对象。物我彼此分离,人在加强自身主体性的同时,自然的灵性和神性也就消失殆尽,自然成为人类取用的材料,风景也成了生活的装点。
由于这两种自然伦理关系存在本质不同,纵使沈从文笔下的城里人希望借助大自然的调和来疗养身心,但他们从未真正走进自然,也从未走进乡间的伦理秩序中。所以无论是乡下人看城里人,还是城里人看乡下人,彼此都是神秘而陌生的存在。小说《三三》是以三三这个乡间女孩的视角展开的,那个城里人一直没有姓名,似乎总是很神秘,只看得到他的神态、穿着等外部表现,对他的身世经历则一概不知。《夫妇》是以城里人璜的视角看乡下人,他认为乡下人对年轻夫妇的处理是卑劣的、守旧的、不可理喻的。“地方风景虽美,乡下人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他预备明后天进城。”[12]同样是城里人到乡下去养病,但因为观看的视角不同,其展现出来的人物就有如此大的变化。
沈从文通过疾病来描写城市文明和乡村社会的碰撞,不单单是为了揭露都市的病症和怀念乡下的淳朴健康,更是为了展示与生命的对话。一方面,他从乡下来到城市,感受到的是不安和卑微,虽想融入都市社会,但在都市里体会到的是生活的压迫、冷漠的人事关系以及受金钱掌控的价值观念,这些都让他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血脉里,记忆中,故乡的风情和民族原始的人性和神性在呼唤他,让他不至于在都市的漩涡中迷失自己。因此,创作对于沈从文而言,既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也是在城乡边缘进行对自身生命价值的确证和对生命伦理的重新建构。
所谓重构生命伦理,其实就是沈从文在身份转换和人生体悟中对生命思考的深化。一方面,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13]但是来到城里的沈从文成为了作家沈从文,在城市这样一个重物质而对灵魂不屑一顾的环境,他始终保留着从乡间带来的那份对生命灵性的敬畏和信奉。因此沈从文对都市的疾病书写,不只是为了揭露社会弊病,更是为了关注生命存在形式。他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14]沈从文认为:“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15]在沈从文眼中,城里人一旦生病就是生命凝固,就像一潭死水,只能走向发臭和枯竭。而乡下人即使生病也是与自然神灵居住在一起,他们的生命是活跃的。另一方面,沈从文在回顾乡土时并非纯粹是一名乡土田园的歌者,而是从现代理性精神出发,反思乡土伦理中的不合理之处。如乡民在璜眼中是蒙昧和卑劣的;《萧萧》中萧萧对自己悲剧命运是不自觉的。可见,“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他所拥有的现代理性,使他已经实现了对自己曾置身其中的乡下人的超越。”[16]
沈从文在都市中既体会了“毁碎于一种病的发展中”[17]的痛苦和挣扎,也接受了现代理性知识和精神的洗礼,再结合自己血脉中对生命神性的感受,必然会使他自己的生命观和追求生命伦理的理想得以重新整合和建构。沈从文对都市和城里人的疾病书写,实际上是对都市中人性的扭曲、生命价值的失落、肉体和精神的衰弱的写照。在世界文学中,许多作家目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和腐朽,转而去尚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民族那里,寻找野性的生命强力和不被现代秩序和观念束缚的人性自然和生命自由,以求对现代人性异化的揭露和反省,并且希望为现代文明注入原始的生命力。虽然这样的疗救方式有丰富的文学传统,但是沈从文沿着这条路为城市病找寻治病良方时发现了城乡两套文化观念和伦理思想的碰撞。沈从文以城乡边缘人的身份,用现代理性精神和民族自然神性观照城市和乡村时,看到的是都市的病症和乡村的蒙昧。可见,沈从文在重整自己生命伦理思想的这条路上是在不断思索和反省的。虽然早期城市和乡村题材小说的创作隐含沈从文在城市生活中受挫,因而在故乡回忆中确立了自身精神优越感的心理,带有鲜明的爱憎。作为一名对生命倾心的作家,沈从文在创作中留下了自己对生命价值、人性尊严的不断追寻和反思的踪迹。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