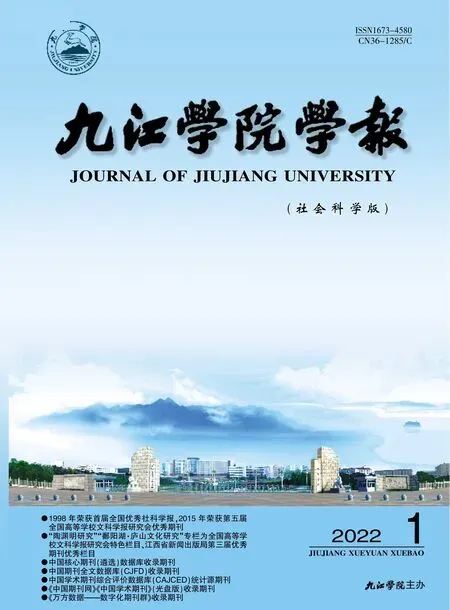陶渊明的存在主义身份辨析
余贝贝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陶渊明是中国东晋时期的田园诗人,他向往自然的生活,吟诵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归园田居》)的隐逸志趣;他写下了《桃花源记》,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个理想世界的蓝图;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的人生选择成为士大夫的楷模。20世纪80年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海德格尔为首的存在主义传入中国。学术界意识到了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于是陶渊明又有了存在主义的身份。
一、问题提出:陶渊明的存在主义身份
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是首位发现海德格尔和陶渊明之哲理关联的学者,他在1991年主张:陶渊明诗中的哲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都可以归纳为“超然”的哲学,[2]即一个“无”字。1998年,戴建业也以存在论的视角看待陶渊明诗歌中体现的人生之“真”,他认为“这里的‘真’不是逻辑上的‘真’,而是‘存在者状态上’的‘真’”[3]。后来的学者沿着两位先生的思路,纷纷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去阐释陶渊明。诸如陶渊明的“羁鸟”“池鱼”是对人生之“烦”的隐喻[4]、给自己写挽歌是对死亡的沉思[5]、坚持躬耕田园是达到“本己本真”的方式[6]。诚如这些学者所说,陶渊明的人生哲理观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有相似性,但事实上,陶渊明和存在主义之间是“形似而神不似”的。
首先,海德格尔所说的“本己本真”的状态,陶渊明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所说的“本己本真”指的是作为在世存在的此在“畏”于死亡而脱离“常人”状态,主动走向超越、自由的本真状态。一方面,陶渊明一生从未放弃过出仕的想法,所以他依旧是“常人”的、“烦”的状态。正如袁行霈所说“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7]。陶渊明写作的“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8],都表明他积极抓住机遇去做官。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抵达本己本真的方式是“超越”死亡,而陶渊明并不完全如此。从陶渊明的生平来看,他的父亲,外祖父,妹妹,两个从弟都早逝,陶渊明深感于此,十分珍爱自己的生命,且他归隐的直接原因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9]。正似鲁迅先生总结的那般:陶潜总不能超出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及的。[10]
其次,海德格尔的“存在”和陶渊明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观在概念范畴上不相当。“存在”指的是世间万物“在”的整体根据和本源,拥有形而上学的哲学意味。陶渊明以诗歌传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只是哲理性的思考,它既没有经过逻辑的推理论证,也不具备概括万物生存之源的哲思。陶诗共有四处提及自然:神辨自然以释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渐进自然。这四处表明陶诗的“自然”是自在的、自由的,[11]指的是人返回山林田园、躬耕于自然、无求于世俗的天性自由。
最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建立在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之上,他试图以存在为核心建构超越主客体二分的现代哲学。而陶渊明诗歌哲理的根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他希冀以田园为载体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显然,主客二分哲学、天人合一哲学正是海德格尔与陶渊明的文化土壤差别。再者,两者面对的现实也不一样。海德格尔面对的是西方理性占据统治地位,自然和人都出现危机的状况,他从古希腊哲学反拨理性对自然造成的伤害,恢复自然和人平等“存在”的地位。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和海德格尔的时代不一样,现代性的危机没有发生在陶渊明的眼前,他不必以此为导向溯源性地询问,且其真正的生发契机是陶渊明自己的难酬人生境遇。
总而言之,陶渊明诗赋中传达出的哲理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性、本质上是不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形似而神不似”的现象?这是本文接下来探讨的重点。
二、陶渊明存在主义身份的误解之因
(一)陶渊明隐逸形象的接受
隐逸之思、对生死的感悟构成了陶渊明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之间的关联。实际上,陶渊明的这两个主要特征只不过是六朝以后的读者“接受”的陶渊明。换而言之,后世读者加工出的“隐逸”陶渊明是陶渊明被误解为存在主义的主要因素。
沈约是第一位承认陶渊明隐士风骨之人。在沈约主持编纂的《宋书·隐逸传》中,他对陶渊明的诗文仅评价以“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12]。相反地,沈约大书陶渊明不肯屈仕刘裕王朝而归隐的行为。显然,沈约非常重视陶渊明归隐中透露出的气节。同时代的文坛重将兼陶渊明好友颜延之在陶渊明死后写作《陶征士诔》[13]也进一步丰满了陶渊明的隐士形象。他称其为“南岳之幽居者也”,且对其文章仅道“学非称师,文取旨达”之言。总之,和陶渊明同时期之人对其诗歌褒奖言语甚少,更偏重其归隐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意趣高洁和坚贞人格。
爰及隋唐,陶渊明的隐逸诗歌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然不出隐士之名。隋朝沿袭了六朝时的隐士看法。唐初,据《南史·隐逸传》所言,“若夫陶潜之徒,或仕不求闻,退不讥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斯并向时隐沦之徒欤。”[14]可见,陶渊明在唐初还是隐士的代表,甚至是隐士之首。盛唐及中唐之人仍以“隐逸”看待陶渊明,正如李白“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15]。
陶渊明隐逸形象的真正完成者是宋朝的苏轼。被贬黄州的苏轼写道“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鏊糟陂里陶靖节,如何?”[16]显然,正是在陶渊明充满闲趣的隐士身份中,苏轼找到了仕与隐之间的平衡。由此,苏轼将自己的个体生命意识转接到了陶渊明的形象中,将陶渊明打造成为一个士大夫归隐田园的理想形象。最终,在仕与隐里纠结的真实陶渊明渐渐模糊。
李泽厚认为“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17]。以清人方东树对陶渊明的品评看,他认为,“庄以放旷,屈以穷愁……阮公似屈兼似经,渊明似庄兼似道,此皆不得仅以诗人目之”[18]。此言直接将陶渊明确证为涵咏老、庄的隐逸。
从根本上来看,苏化的陶渊明源于中国文人特有的仕与隐的精神。儒家渴望在历史现实中实现个人的价值,道家渴望脱离一切禁锢,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没有任何的文人能逃离“兼济天下”的使命,也没有任何人能摆脱“逍遥游”的渴望。两者共同涵养、撕扯着中国的士大夫。他们仕途无望便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想象着个人的绝对自由。因此,仕与隐的精神“神”化了真实的陶渊明,令他被误解为“存在主义者”。
(二)晚清以来的强制性阐释
正如前所说,陶渊明没有真正达到海德格尔的本己本真状态。那么他被误解为能够和海德格尔对话的“超越万物的道家式”思想究竟是怎么确定的?答案是晚晴知识分子的“以西释中”。
启迪民智的一代先驱者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站在破除封建的立场上,以挣脱儒家束缚、恢复人之“主体”为目标。他们开始以西方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历史流变,也正因为这股“以西释中”的势力,陶渊明成了一个道家式的、超越般的主体。
晚清时期首先以西方视角重审陶渊明的当属梁启超,他不赞同传统儒家视野下陶渊明归隐之因的“忠愤说”,相反地,他认为陶渊明归隐“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浑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19]。朱自清进一步从陶改“渊明”为“潜”佐证了梁启超的说法,并认为其改名缘于“泽于道家者深”[20]的哲学趋向。“潜”一字为“隐也”,“龙潜于渊,得其所之象。人得其所,可以无咎”[21]。陈寅恪又深一步地将陶渊明定义为“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22],因为他虽不薄周、孔,但并不干世求进;虽承阮、刘“任自然”之遗风,却又不同于阮、刘之放浪形骸、别学神仙。总之,从梁启超,经朱自清,最后至陈寅恪,陶渊明被正式解读成超越性的道家象征。
同时,陶渊明在美学上也被阐释为西方式的“静穆”。朱光潜认为“古希腊人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23]。“神不静穆,尤为未至也”[24],可见“神”字正是静穆的关键。与朱光潜的观点相反,鲁迅认为陶渊明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其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25],其实他们“心里是很苦的”。陶渊明少时写作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都足以证明他的“不飘逸”。
综合以上三方面来看,从晚晴一直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塑造的陶渊明的三幅面孔和真实的陶渊明都有所出入。出入之因是时代语境影响读者的接受。此时的语境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以坚持超越面孔的渊明是为了挣脱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坚持静穆面孔的渊明是为了挣脱传统儒家的温柔敦厚美学、坚持金刚怒目面孔的渊明是为了反拨过度反抗儒家束缚。正是源于这样的语境需要,所以真正的“陶渊明”已死。
将陶渊明“以西释中”化的做法,究其根本是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建构一直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完成,西方的“无功利、无目的”的审美是评判的基础。所以五四以后中国的学者受西方启迪,以这一“美”的观点去重新审视中国文论。诗意归隐的陶渊明似乎成为了救命的稻草,学者将其美化为审美性的人生智者,好似就证明了中国文坛也有西方一样的自由精神。这种做法正如张祥龙先生所言“这不仅足以窒息中国思想的本来活力,而且会使得任何真实意义上的对话都无法实现”[26]。
(三)道家的文化渊源
陶渊明和海德格尔之所以容易产生相似性联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两者共同的道家文化渊源。海德格尔曾阅读并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认为其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思”;作为魏晋之人的陶渊明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的“神与物游”观在陶渊明和海德格尔那里都能找到证据。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7],可见在老子眼中,天、地、人、自然四者之间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观点,他将天、人之间对立,明确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28],但这其中并不是为了完全放弃人为,而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回归自然。这一自然观在美学上体现为“神与物游”。即作为个体的“我”以投向自然为方式获得感性生命和精神的绝对自由。此时“我”并不凭借外物,遨游于天地之间,自由地舒展自我。这正是“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29]。如此这般的结果是人与自然绝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关系。
道家的“神与物游”的思想是海德格尔和陶渊明共同的思想渊源,其直接影响了陶渊明田园诗透露出来的天地人和谐共存的美感,又启发了海德格尔解构西方形而上学和阐述“无蔽”。
正如朱光潜所说,“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之间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普云周流,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徜徉自得”[30]。陶诗中的我与田园之间的交融达到了一种天地人和谐交融的状态。“从海德格尔这一思想形成时期所受的关键性影响来看,它极有可能来自以老庄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道家思想”[31]。诚如此言,海德格尔所言的“让……如其所是地显现”和庄子所言的“玄同”有内在的学理相通性。而且,海德格尔描述的“无蔽”状态也和道家的“神与物游”智慧有关。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此在者的人在艺术作品“世界”展露出的澄明之境与“大地”的“敞开”之间发现了艺术作品的本源。[32]也正是在澄明的世界与敞开的大地之间,人显示了自身作为无蔽状态的存在——存在如其所是的自行显现。显然这和道家所言的“自然天成”的美一致。
然而,理论渊源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陶渊明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汲取诸如古希腊哲学、希伯来精神、禅宗、儒家等思想的过程中融合而成自身的独特性。正是融合过程中的择取和思辨,造成了陶渊明和海德格尔的差异:陶渊明吸纳孔子强调人之作用的自然观,并将它和道家的相互交融形成特殊的天地人观;海德格尔接受了希伯来的“神性”智慧,将其发展为天地人神四者共处的所在。这一差异不仅是二者形似而神不似的关键,也是陶渊明不是存在主义者的确证。
陶渊明究竟归属道家还是儒家?历来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无论哪一种归属都限制了陶诗哲思的伟大。真正伟大的诗人不可能拾人牙慧,而是在充分汲取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独创性,是以“不可执一端而非其他”[33]。陶渊明少时受儒学影响,因而儒学和道家截然不同的天人观念也影响了陶渊明的诗文,所以,陶渊明儒道兼通地发展了自身独特的天地人的美学观。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34],显然,孔子赞赏自然,加之他“吾与点也”的智慧都能看出其审美地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不同于道家全然复归自然的做法,孔子强调人积极地复归自然。陶渊明称孔子为“先师”,认为“先师遗训,余岂之坠”,还将“吾与点也”化为自己的诗句“春服既成,景物斯和”。恰如刘熙载所言“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35]。
孔子强调人之作用的天人观、道家的人无我地投向自然之措都影响了陶渊明。陶渊明兼收并蓄地发展出自身的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天、地、人观。以《归园田居》组诗来看,无论是麦苗稀疏的苦楚,还是登高所见感触到的荒凉,这些都是“我”与自然所生发的情绪和感触——这是主体作用于自然的体现。如春日暖阳下入室的微风,这“天、地、人的生命生机显发,就是真,就是一副天、地、人生命自然朗现的画面”[36],也因此才形成了陶诗平淡又丰腴的诗境。
“在重视生命、顺应自然规律方面,继承商周思想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各分支之间是相通的,儒道两家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方式和角度上有所区别而已”[37]。所以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的“道”之精神。陶渊明诗文的哲学闪光点的范式是中华文化的“道”之内核。海德格尔就算是对道家感兴趣,但其对儒学了解不深,因而并不可能全然地理解中国的“道”。这正是陶渊明和海德格尔“神”不似的关键,也是陶渊明异质于存在主义之处。
海德格尔受西方另一文化源头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在天、地、人之中加入了“神”的维度。海德格尔所说的“神”不是后来基督教所言的道成肉身的上帝,而指的是由语言召唤出的神性。“存在的本性发生也需要诸神”[38],它成为此在本真力量的保证。
海德格尔用天-地-人-神四者一同游戏达成物与世界的统一。天、地、人、神四者之间的游戏相互生成、相互传递,“于是,万物和世界相互统一。正是在此统一中生成了内在性”[39]。这一内在性令物与世界显现自身如何生成,达至物是世界的物、世界是物的世界。因此,正是用神性的力量,海德格尔完成了本己本真的言说。
这种神性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决然没有。道只是一种创生天地万物的自然性而非神秘性的力量,所以道家和儒家没有一个精神意义上的上帝,他们用以替代宗教的伦理精神不具备神性的超验性。另外,“与‘道’不同,神圣者不是本然的自然本身;神圣者外在于衍生万物的‘道’,既不在时间之中,也不在自然时间之中”[40]。中国的“道”中没有这种非时间性的存在,因此,陶渊明的诗文中绝不可能出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神性。这遂成为海德格尔和陶渊明之间绝对的异质性。
总而言之,陶渊明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不同折射出了中西方之间在“道”与“神性”两种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其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和追寻的两种方式。人类的好奇是相通的,是中西方共同的智慧。
三、结语
一般而言,陶渊明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之间跨越了千年的时间、万里的空间,强行比较容易落入诟病之中。然而,如果仅仅以事实联系来看待中西之间的思想成果,实际上限制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不妨以中西方对真理的共同探寻作为比较的前提。人类的好奇是共通的,以此共通性来打破中西文化不可通性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