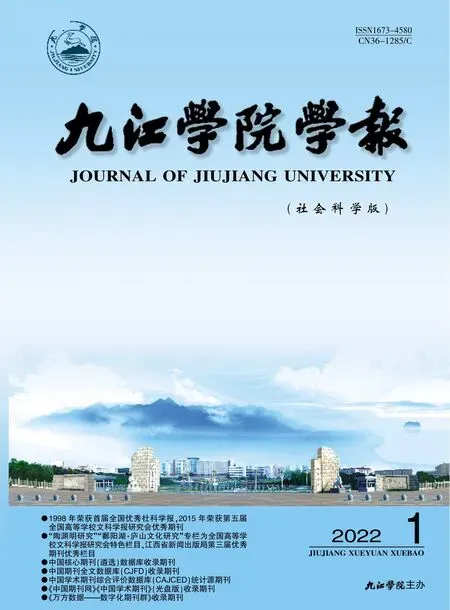空间文学视阈下《老残游记》空间结构探析*
彭淑慧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空间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人类生存与文学创作的重要维度。二十世纪以来,空间理论作为“文学转向”背景下显著的理论成果,在各文学领域表现出极强的活跃性和影响力。《老残游记》作为游记体小说,其对游踪的交代和景物描写方面的特点历来为人们所关注,而从空间角度切入对其空间结构本身进行研究,学术界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将打破游记体小说线性的、水平向度的研究,从多维的空间角度切入,探究其真实空间书写中的人性价值、虚拟空间幻设背后的空间重构愿望,进而通过老残几次耐人寻味的“哭泣”和“题壁”现象,走入作家的心理空间,力图对《老残游记》的空间结构进行全方位把握,为文本研究提供全新视点。
一、真实空间
胡适曾说“《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1],并进一步称赞其“前无古人”,这种评价极高,但也当之无愧,小说作者不仅为我们贡献了“大明湖游记”“桃花山遇虎”等大篇幅既令人应接不暇又富有层次动感的视觉盛宴,连黄河结冰、雪月交晖等景象的描写也能于细微处见精神。这一个个精彩、生动、富有个性的现实空间,成为构建起《老残游记》空间大厦的基石。
(一)风物志物——自然空间的高度还原
《老残游记》所涉故事,除二集后三回之外,其余皆叙老残在山东的所见所闻。游记体小说的情节主要在旅途中展开,因而自然少不了花大笔墨对真实空间中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等进行描绘。陈平原先生曾指出:“在游记式小说中,景物描写则几乎毫无例外是因旅人的足迹与眼睛而依次出现。最典型的是《老残游记》中的游大明湖与《剑腥录》中的观超山梅花。”[2]书中老残游览大明湖的整段描写如行云流水,我们跟随老残的脚步和目光,移步换景,“既不提前也不落后,既不贪多也不减少,不但写出了明湖景致,更写出了老残游湖的情致。”[3]试看最精彩的千佛山倒影一段:“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其中对分明如画的山间楼宇、镜子似澄浄的湖面、粉红绒毯般的芦苇花等大面积的空间铺排,如同神笔一支,顿时绘就天地;油漆剥蚀后的斑驳、松柏间丹枫的明艳、斜阳沾染水汽的氤氲,空间细节的处理更是精到细腻、动人心魄。除了高超的自然空间结构艺术之外,这段文字中对于景点名称叙述的确定性,以及对方位把控的准确性也值得注意。比如从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老残从鹊华桥边上船,经过历下亭,来到铁公祠,望向对面的千佛山,进铁公享堂转了一圈仍旧上船,从历下亭的后面返回鹊华桥畔的游览经过。也可以在方位词的引导中得知老残先向北,后向西,再向南,最后向东的圆圈游览轨迹。
通观《老残游记》,其对于自然空间的地理还原和真实记录比比皆是,这里不多做赘述,其间所记叙山东五府的地理风貌,与黄河在山东所流经的府县和刘鹗在山东治黄经历的地域皆能够基本对应,光绪十一年,黄河水患下移,山东巡抚张耀咨调刘鹗到山东作幕宾,任黄河下游提调,帮办治黄工程,赢得很大声誉,后来被山东巡抚福润保送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在艰难繁重的测绘过程中,刘鹗走遍了山东大小州县,可想而知其对整日相对的黄河两岸的风光和世情已谙熟于心。《老残游记》中山东风物的还原度和游踪的清晰度大概就得益于刘鹗这几年到任山东的经历,同时也印证了小说的写实性。
(二)人居宜人——居室空间的人性写照
在空间诗学理论的提出者巴拉什看来,空间不仅具备容纳作用,更具有人性价值。他在《空间的诗学》中将家宅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内心空间形象进行分析,突出了家宅代表内心深处回忆和梦想的空间特质。《老残游记》中有几处家宅居室的描写非常精彩,其中以桃花山玙姑洞房最令人难忘。玙姑是作者重笔墨刻画的一位光辉的女性形象,她涉猎广泛、思想深刻,并且艺术造诣极高,无论是鼓瑟、吹角,还是奏弹箜篌,均令闻者忘归,如梦如醉。
小说对玙姑居室有一段完整的描写:“这洞不过有两间房大,朝外半截窗台,上面安着窗户,其余三面俱斩平雪白。……洞里陈设甚简,有几张树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八小的不匀,又都是磨得绢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圆,随势制成。东壁横了一张枯槎独睡榻子……榻北立了一个曲尺形书架,放了许多书,都是草订,不曾切过书头的。双夜明珠中间挂了几件乐器,有两张瑟。”[4]虽然简陋、仄狭,但居室首先具有抵抗外界侵扰的保护力量,具有身躯与灵魂的庇护功能。此外,居室更是屋主人心灵的表达与呈现。正如巴拉什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到:“它们不仅有实证方面的保护价值,还有与此相连的想象价值,……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他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5]玙姑以洞为居、枯槎为榻,坐具是树根打磨的、几案是古藤天生的,家具皆不强求,随势制成,不点灯烛,明珠照夜,以琴瑟为友、以书策为伴,皆得以见出玙姑对居住环境道法得心、循性自然的营造理念。后文又提到,申子平纳罕夜明珠究竟何为,才发现是玙姑用螺蚌壳作壁,内置油池,用棉花线卷成灯芯,千层纸做成灯筒,制成的“夜明珠”,又得知她以晒干的蓑草劈丝和麻织毯、云母粉和红胶泥涂壁,既御潮又避寒气,更见其洞悉物性、注重生活的妙心慧性。
可见,空间确实有利于人物的形象化展现,“对空间与人物性格关系的洞悉与否,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创造性的标志之一”。[6]在居室空间中,自我与空间平等对话、相互慰藉,空间被赋予人性价值,主人也在诗意观照的空间中找寻自身确定性,因而主体体验过程即居住过程,也就萦绕着幸福感。如同巴拉什认为家宅、鸟巢、贝壳等等都是幸福的空间,玙姑浑然天成又精心营造的洞房已分明成为屋主人诗意的栖身之所,玙姑的生命形象也因为空间化而变得更加确定和坚固。
二、虚拟空间
文学空间与真实空间不同,它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代表人们知觉与期望的空间,因而往往带有幻想的成分。《老残游记》的两篇序言,一以“有灵当哭”为论断、一以“人生如梦”为核心,这可以理解为刘鹗创作的目的或缘起,但通过梦境的甬道,进入小说的虚拟空间大厦,便可以发现作者在现实世界中无路可去而在空间拓展中寻找出口的尝试。
(一)梦境空间
二集自序开篇便问到,“人生如梦尔,人生果如梦乎?”后通过对蜉蝣子、灵椿子等未果的询问,最后经过昭明和杳冥一系列比喻和反问,证实了人生百年倏忽而过,皆如虚幻不可复得,故知人生如梦,此言不虚。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红楼梦》的梦境主题,曹雪芹所写之事皆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众生万象“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皆如太虚幻境,“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最后只剩“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同样以梦喻人生,但从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刘鹗的“人生如梦”观与曹雪芹并不相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表现出的是一种物象实空、欲念实虚的悲观态度,而刘鹗确认为虽然人生如梦,但梦中之人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固无法使之暂留,而其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业,固历劫而不可以忘者也。夫此如梦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既不能忘,而此五十年间之梦,亦未尝不有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亦同此而不忘也。”[7]也正因为这些不能忘的惊喜和悲歌,才有了《老残游记二集》。
小说一共出现四次梦境描写,除去自序,分别出现在一集第一回、二集第四回和第七回,其中涉及到梦境空间的是老残的“沉船之梦”和“地狱之梦”。
第一回里,老残梦见他和文章伯、德慧生去登蓬莱阁观日出,突然发现远处一只大船在风浪中行驶。通过对大船及船上人物语言、行动的描写,刘鹗将晚清社会的黑暗、苦难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原来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无一处没有伤痕。”[8]这艘风雨中的大船充满着象征意味,船中空间的设置正对应着清政府的行政机制。“船主象征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楼下四人是指四个内阁军机大臣,二十三四丈是指当时的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六枝桅杆指当时清政府吏户礼兵刑工六部”[9]等等。而对于颠沛流离、饥寒落魄、无枝可依的人民,刘鹗则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千古兴亡,危船一梦”,刘鹗用他如椽巨笔幻设了一艘艺术的大船,通过大船空间的展现,向我们剖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愤恨和无奈,同时这场梦也是刘鹗试图划小船介入大船空间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思想的表白。
(二)地狱空间
小说中第二次梦境空间的展开则发生在老残在淮安城探望姊丈高维时,一日老残在银汉浮槎中看《大圆绝经》,看到月轮西斜,一落枕便睡着了,进而转入对地狱空间的描绘。“地狱”的概念大约在西汉时就已随印度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原冥界观念逐渐融合,其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常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老残游记》中的地狱书写也是如此,但如果说小说中梦境空间是对现实世界的投射,那地狱空间则更多带有现实规训的意义。
试看小说对阎王殿空间的描述:“大甬道也是石头铺的,与阳间宫殿一般,……上丹墀仿佛是十级。走到殿门中间,却又是五级。……从西面阶级上去,见这台子也是三道阶路。上了阶,就看见阎罗天子坐在正中公案上,头上戴的冕旒,身上着的古衣冠,白面黑须,于十分庄严中却带几分和蔼气象。”[10]下文又继续交代了阎王下问案的五神及其分管和轮值情况,以及办公当差的空间陈设。地狱空间中的阎罗殿映射的其实是现实中清政府的宫殿,阎罗王则映射当朝皇帝,它是地狱空间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衣冠华丽、肃穆隆重,神圣中带着几分和气,当值的五神则映射了清朝衙门坐堂时的模样,这一套从上到下的完整的官僚体系,大致便是模仿现实中清朝的官僚体系而设的。
二集第八回中对地狱的刑具和惩罚机制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不仅对油锅、磨子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刑具和行刑方式冷静客观地加以交代,并且还以问对的形式将治罪的依据告知读者。以地狱空间为媒介,刘鹗方得以将自己的善恶果报观念以及内心深处的隐痛和盘托出。刑罚系统大体遵循因果报应原则,生前作恶越多,下地狱后所受的刑罚便越重,相反如果生前多做善事,死后也会受到优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了生前言语罪恶的严重性,一句话就可能毁一个人、杀一个人,若再将恶业演说,其罪恶便比恒河之沙还重。因此在地狱中,生前犯下口过之人所受的刑罚极其严重。针对口过的刑款说道出了刘鹗的心声,他曾积极投身实业,亲自开办工厂,并提出学习外国技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但拳拳爱国之心却被有些人认为是汉奸行为,更因奸人巧言令色而遭流放,最后抱憾而终。因此在小说中,刘鹗就是要通过对地狱空间的设计来惩罚那些奸佞狡诈、花言巧语的口过之人,从而结构一个规训世道的虚幻空间,以排解心中的幽愤。
三、心理空间
文学空间不同于文学中的空间,文学中的空间即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空间,它是一种或直接或隐晦地包含着真实意义的局部形象,而文学空间则是一个更为整体的概念,它充溢着人们的生命和情感,是文心共鸣的乐章,顺着文本空间的音符,我们便能够走进人心的殿堂。
(一)心理空间的系统性
从空间角度来看,作家对艺术空间的拓展越充分,越有利于情感的释放。正如贝多芬在音乐中体会出精神空间的自由而有序:“精神的精神,弥漫在整个空间。……凌驾于各种抗衡思想的极限;你从混沌之中建立起了壮丽的秩序。”因而作家往往会通过搭建完整有序的形而上的“心理王国”来拓宽文本的空间维度,提高作品的思想境界。心理空间的系统性则表现在,面对现实空间,会主动反映和创造;而面对思维空间,则表现出统摄性和开放性,能够不断寻求空间出口、克服内心矛盾,进而不断实现对思维空间的拓展。
从上文对《老残游记》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结构的解读中已能够看出刘鹗对现实世界或写实或隐喻,以及为释放内心、寻找现实出口而进行的虚拟空间构建。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小说中直接表露的对拓展空间的向往中考察作者心理空间的系统性。小说以“游记”为名,没有空间拓展的愿望和实践自然称不上“游”,作者不仅借老残之步履遍游山东,甚至在阴间还借老残之口一抒远游之愿:“我的主意,今天案子结了,我就过江。先游天台雁宕,随后由福建到广东,看五岭的形势,访大庾岭的梅花,再到桂林去看青绿山水。上峨嵋。上北,顺太行转到西岳,小住几天,回到中岳嵩山。……过瀚海,上昆仑,在昆仑山上最高的所在结个茅屋,住两年再打主意。”[11]他认为做鬼的五种快乐其一便是可以无牵无挂、遨游八极。对人来说,如此上天入地的空间游览显然不切实际,但也不是所有鬼都有这般空间拓展的愿望,梁海舟受到老残邀请便只是摇头说“做不到”,这是内部驱动力不同的缘故。正如诺瓦里斯曾表达过同老残类似的愿望,“我们渴望在宇宙中遨游”,而且他认为宇宙同时也在我们心中:“我们并不了解精神的深度。秘密的道路通往内部。永恒同它的世界,过去和未来在我们身心中”[12]正是这种强烈的内驱力,激发着并自我确定着外部力量,使其在尘世生活中丰富、完满,且剩余的、喷出边际的力量将继续着异世界的空间拓展。
(二)心理空间的文本“代言”
心理空间的系统性使小说文本空间得以开拓,但在其系统内部又有多个灵活运作的“单元”,正如杨匡汉在《缪斯的空间》中说道:“(心理空间)包括思维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意识的显露成分与隐藏成分。……成为一种基于诗人的气质、人格、个性之上的完整的、流动的、有序的网络思维的凝聚。”[13]对这些“单元”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对作家心理空间的还原。《老残游记》中,主人公老残曾三度落泪、三度题壁,从眼泪和诗句的敞口中我们便可以对作家的心理空间做一番探寻。
1. 不以哭泣为哭泣
《老残游记》实际是刘鹗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一同漂泊摇曳、一同寻找出路的哭泣之作。“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实际上小说的自叙全围绕哭泣在写,可见是作者抒发其身世、家国、社会、种教之痛的产物,同时也是作者希望读者能够痛定思痛进而崛起的理性之光。
小说中老残第一次落泪发生在第十二回,老残动身回省城,路过齐河县在小店暂住,正逢雪月交晖,想起古人的风雪句,转而想到国家时运,“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14]这一次是国家之泪。刘鹗写作《老残游记》之时,正逢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大清朝棋局已残,内部更是混乱腐朽,国家危亡,摇摇欲坠。老残落泪,也是整个中华民族落泪;紧接着第二次落泪发生在第十三回,老残见良家女孩翠环无奈落入倡门,联想到其悲惨处境,越想越难过,“老残此刻攲在炕上,心里想着:‘这都是人家好儿女,父母养他的时候,不知费了几多的精神,历了无穷的辛苦。……就糊里糊涂将女儿卖到这门户人家,被鸨儿残酷,有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境界。’……又是愤怒,又是伤心,不觉眼睛角里也自有点潮丝丝的起来了。”[15]这一次是人民之泪。他总是关心着人民,把别人家的孩子想作是自己的孩子,把别人的遭遇想作是自己的遭遇,为其苦难而忧愁伤心。老残的泪,也晶莹地反射着所有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哀痛;第三次落泪是在《二集》中老残面对自己“尸首”流下的,“心里明白,点头道:‘此刻站着的是真我,那床上睡的就是我的尸首了。’不觉也堕了两点眼泪,对那尸首说道:‘今天屈你冷落半夜,明早就有多少人来哭你,我此刻就要少陪你了。’”[16]这一次是身世之哭。却比上两次少了些悲痛,多了些洒脱。可见对于生死,刘鹗并不执着,他将国家和人民看得更重,对于悲哀的自身境遇,只需要两点泪来寄托罢了。
在“有灵当哭”的自叙中,作者将哭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痴儿呆女之属无力的哭泣,一类是城崩杞妇这般有力的哭泣,有力的哭泣中又分为“以哭泣为哭泣者”和“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并以后者为力劲行远。显然小说中老残的三次哭泣是刘鹗为“不以哭泣为哭泣”塑造的范本。但以哭来发泄情感并不是作者的目的,正如他并不会因死亡而万分痛苦一样。看似多愁善感的背后是复杂而深厚的理性之思,他希望读者可以通过泪水的窗口进入整个社会心灵的空间,感受到觉醒的力量。
2. 心中事看墙上书
刘鹗先生在将自身经历倾注在老残身上的同时,也试图将其理想化。小说中的老残,是行世良医,对症下药、能治百病;他是治河良才,身体力行、精通奇法;他情趣高雅,博览群书、通音识曲;他游离于官场外却始终爱民为民、上下求索。虽然在现实中刘鹗在不懈的救国尝试中郁郁而终,但他的生命在老残身上延续至今,老残提笔挥就的诗句,仍然在客店的墙壁上墨香不散,启迪着每一颗行经驻足的心。
如上所言老残艺术修养极高,我们可以注意到,不论自然空间还是人文空间,小说中只要出现对联、匾额、屏风等等,老残都会将上面的题字看个仔细。因此小说中常有诗句穿插出现,其中有几次老残自己“题壁”的情节值得我们关注。一次发生在第六回,在晚清酷吏玉贤虐民害民、逼民为盗,而百姓却怒不敢言之后,深有感触,遂从枕头匣内取出笔砚来,在墙上题诗一首,“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处处鸺鹤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17]讽刺其只计较个人得失,残害百姓,血腥酷虐。还有一次发生在第八回老残到东昌府寻书的经历之后,想到这一带大藏书家只将书关锁在大箱子内,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族中人亦不能得见,于是闷闷不乐,提起笔来,在墙上题一绝道:“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嬛饱蠹鱼!”[18]讽刺其藏书不读,徒饰门面,并且自私自利,不肯实用利民。
作者为何要刻画老残写诗的情节?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因为刘鹗要将心灵空间字字珠玑地展现出来,那为什么选择题壁呢?岳飞为了收拾山河朝天阙,谭嗣同为了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刘鹗为了让这泣血之言明晃晃、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让书里书外的读者通过一笔一画的敞口进入作者的心理空间,从而起到呼吁、启迪的效用。
四、结语
《老残游记》以其丰富的地理文化信息、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显示着独特的风格与追求。其崇尚科学的实用精神、兼收并济的人生哲学、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寓言性的时局分析,都在小说空间结构的布置中逐层展现出来。不同时代、不同传统的作家都在文学作品中创造自己的空间,以容纳跃动的生命,在人们普遍关注“诗意的栖居”的今天,空间文学对于文学研究无疑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对于《老残游记》空间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感性与理性相互融合、效应与启发高度契合的心理空间有更直观的认识,这对把握小说本身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神性与人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