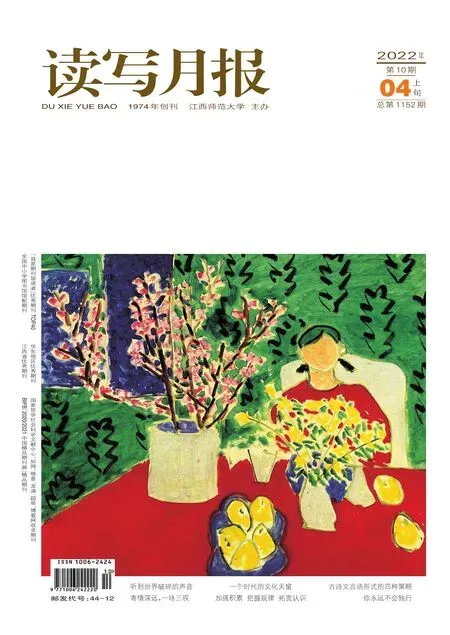听到世界破碎的声音
——读《长夜行》有感
邓敏
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长篇小说《长夜行》颇具颠覆性,颠覆了我以往从其他作品中获得的对历史、对世界的认知。
有关一战题材的作品很多,有对战争进行冷静反思的,有反映战火纷飞中小人物的遭遇和命运突变的,也有抒发家国情怀、兄弟情谊的,比如《战马》。但带有自传色彩的《长夜行》完全放弃了那些对于战争的正面和宏大的叙事。小说主人公巴尔达米,一个二十岁的医学院小伙子,跟同伴开玩笑跑进队伍里,后来稀里糊涂地上了战场,成了一战的亲历者。这位憎恶战争、时时刻刻想着逃亡的下士,他的眼中没有威武的上司,没有英雄,更没有热血澎湃,而是满心的恐惧、失望、厌弃和逃离……他用自黑和黑化的方式抨击一切,嘲讽所有人——上尉、中尉、预备役军人、平民、市长、德国军人、护士……描写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杀人,混乱,疲乏,侦察任务,火光冲天,灯火通明却一片死寂的城市,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甚至没有对敌人的憎恨,也许还私心里希望被敌人俘获。因为当了俘虏,对个体而言,战争就结束了。那些“爱国主义的道德的价值,被词语拔高……但它们在被我们的害怕和自私战胜之后,在被纯粹的真理战胜之后,就立刻变得朦朦胧胧”,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另一种战争,一种脱离了国家主义的个体眼中的战争,一种充斥着狂热、虚伪和谎言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主人的战马带着浮华的马镫重获自由,它们可以去找敌方的马匹交朋友;但人不行,只能偶尔相遇,远远躲着,或者干掉对方的几个新骑兵。战争让所有人变成了刽子手、杀人狂魔,那些原本是商店职员、文职人员、厨师、赛马手的人在战场上吹嘘自己杀人的本事,战争狂的上司像跟死神签订过合同似的,不断将自己的士兵送往对方的炮口。这是一场杀人的游戏,十月的冰雹里包着炮弹和子弹的馅儿,和平时期像天鹅绒一样温柔的夜也变成了无情围捕野兽的猎场,天空充斥着杀戮的气息。战场,农村,城市,到处都是无恶不作只会杀人的疯子,“只要活上一天就去杀人,或者被人开膛破肚,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战争让人惊慌失措、受尽折磨和欺骗,只能指望在恐惧、侮辱和厌恶中死去,用死来摆脱劳累、痛苦和噩梦。战争让生命失去了活着的尊严和意义,更没有未来。“谁谈论未来谁就是混蛋,重要的是现在”。士兵们在没有未来、不知下一秒是死还是活的战争里以偷东西为乐,甚至用欺骗的方式向一位痛失儿子的老太太要钱。
战争泯灭人性,让人狂热、丧失生命意义。胆小、自私的巴尔达米甚至希望自己的车队遭遇袭击,被炸得粉碎、烧得精光,这样他就可以免去劳累、痛苦。死亡是终极性的逃避。战争,让原本难以置信的墨西哥印第安人部落杀人求雨的残暴传闻,成了眼前的事实,让主人公意识到他就是那个下贱的待宰的牺牲品,从而体悟出一套“不去杀人,就会被人杀”的杀人哲学。
在这个杀人充斥一切的世界里,年轻的巴尔达米渐渐丧失了人性,湮灭了同情、友爱、关怀这些人类美好的情感。他冷冰冰地注视着一户平民陷于孩子被德国人用刺刀捅死的痛苦,并平静地与这户人家做着五法郎的交易,甚至为了这个付出的五法郎而发出诅咒“希望他们统统死光”。
还有从美国来的国际红十字会护士洛拉,作者对她的描述以及她与主人公及其他男人的肉欲关系,也颠覆了我在《奥斯曼中尉》中所看到的冲破宗教、种族阻隔的崇高而伟大的爱情。《长夜行》里有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吗?巴尔达米交往过很多女人,但有一个是真正纯洁的爱情吗?好像没有。爱情是这个丑陋、虚无、黑暗世界的奢侈品,作者也一定觉得这样的世界不配有爱情。这个世界有的只是欲望,是攀过一个个肉体却扬手空中、什么也抓不住的空虚,令人恶心的空虚和懦弱。
胆小怕事、贪生怕死、具有被害妄想症的巴尔达米逃离战场,逃离精神病院,从法国逃到非洲殖民地。这里的非洲也全然不是《走出非洲》里伤感交汇着壮丽的非洲。它彻底撕去了殖民者温情脉脉的遮羞布,“想到殖民地去脱胎换骨”的巴尔达米迎来的却是同胞的排挤和迫害,非洲大陆也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热毒的瘴气,殖民大暴君们的贪婪和残暴,黑人的被压榨、受暴虐和愚昧……所以,作者说“在人世间死去只有两条道路,即肥胖之路和消瘦之路”,富人大腹便便,穷人骨瘦如柴,但最终他们都通向死亡。
洛拉开启了主人公美洲新大陆的朝圣之梦,但她也彻底使巴尔达米的救赎之梦幻灭。美国,赤裸裸的金钱之乡、物欲之邦,人成了工业社会的一个零件,机器在不断吞噬着人的灵魂。最终,巴尔达米又逃回了一战后的法国。法国巴黎一改《情归巴黎》里面浪漫之都的形象,而成为病态、歇斯底里、流血流脓的贫民窟,又一个死亡的集中营。
世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珐琅,我们在很多作品里看到它绮丽梦幻的一面,但它的斑斓光彩在《长夜行》里一不小心被打碎。在漫漫黑夜中,我听到一声刺耳的炸裂声,于是世界碎裂成一块块比黑夜还要晦暗的碎片。
听到世界破碎的声音,这种尖利、刺耳的声音提醒我们:世界有晴天朗日下明媚动人的一面,它也有长夜漫漫中阴暗、丑陋、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不仅要看到世界的美好向善,也要了解人间的卑劣疾苦。完整认知世界,才能让我们更有能力和力量去体察社会、审视自我。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正如《长夜行》,对死亡魅力的着迷与恐惧,对罪恶深渊的媚惑与憎恶,对逃离之旅的想象与厌倦,从战火中的欧洲大陆到非洲殖民地,从机器制造业发达的冷漠美国到病态压抑的法国巴黎,巴尔达米每到一处都颠覆着以往我对它的认知,它在破坏,它疯狂砸碎这个世界的粉饰,让你看清世界的样子,让你看见它白天的模样,同时也能想象它黑夜的情形;让你在光明中意识到影子的存在,温热里想到还有寒凉,安宁富足的另一面是动荡饥饿,欢声笑语的背后也有愁容满面……坚强、美好、活着和软弱、丑陋、死亡犹如镜子的两面,希望我们都能照一照,甚至有时更要提醒自己:看到世界的另一面,听到破碎心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