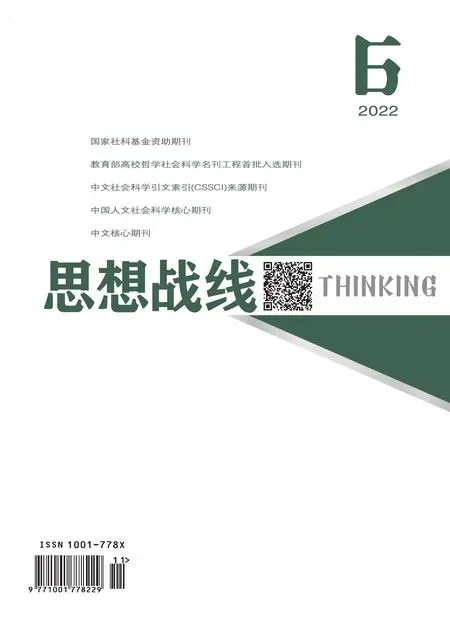“华夷之辨”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逻辑
——基于中国古代文化安全思想的研究
龙 潇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关于中原汉人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如何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种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习近平同志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用“总体国家安全观”(2)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16个领域。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页。进行审视,“华夷之辨”可以看做是中国古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策略。“文化安全”指一个国家的各种文化元素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并具备维系这种状态之稳定性与连续性的能力。(3)参见龙 潇《中华法系的文化安全智慧——以价值观为中心的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从文化安全的角度考量,“华夷之辨”强调在对外文化交往中,要防止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不良冲击、注重用先进文化去影响其他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交流融合与一体发展,以提振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增强文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于此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蕴。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在无数次的磨合中得以融合成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中华文化亦在无数次的碰撞中,得以凝练成融华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精华于一炉的文化共同体,从而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延续数千年不绝的文化奇迹。也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百余年前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就指出:“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留存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4)[英]罗 素:《中国问题》,秦 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64页。
一、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安全思想的“华夷之辨”析义
“华夷之辨”是春秋时出现的一个政治文化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经由《春秋》及其三传(《公羊传》《左传》《谷梁传》),以及历代儒士群体的阐发,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也是历代政权处理不同族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华夷之辨”的研究成果虽不断涌现,(5)有学者统计,截止2020年前,相关研究仅专著就有215部,论文更是不可胜计。参见韩婧芳《“华夷之辨”综述》,《内蒙古电大学刊》2020年第1期。但多从政治史、民族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切入,而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挖掘“华夷之辨”思想所蕴含的文化安全智慧,既是一种学术新视角,又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早在西周,就已经出现了“华夏”的概念。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自号华夏,成为当时的主干民族”。(6)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19~120页。“夷”则泛指居处于华夏周边的其他民族。“中国戎夷,五方之民”,(7)阮 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96页。即华夏居中,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各有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到了春秋时期,“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8)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僖公》,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3页。四夷威逼华夏的势头愈猛,华夷杂处的局面愈烈。“终春秋之世,戎狄之患,无时或无”。(9)陈 致:《夷夏新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正是在这一激荡不已的冲突与融合的时代潮流中,“华夷之辨”的思想应运而生,强调防止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威胁与破坏。考察春秋战国以降到汉唐明清的历史可知,“华”“夷”在更多的场域是作为文化概念来使用的。正如学者顾立雅所说:“所谓‘华夏’概念的基准自古以来都是文化上的。中国人有其独特的生活,独特的实践文化体系,或冠之以‘礼’。合乎这种生活方式的族群,则称为‘中华民族’。”(10)Herrlee G.Creel,Origins of the Statecraft,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197.因而“华夷之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维护中华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体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是典型的对外文化安全思想。凡其理论价值有三。
(一)“严夷夏之防”:华夷之辨重在文化之“防”
“华夷之辨”首先是要辨明华与夷在种族血缘、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上的不同。但“辨”不是目的,其目的是为了“防”,即“严夷夏之防”,防止夷狄对华夏的威胁、破坏,由此凸显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味。最初的“华夷之辨”,是对夷狄全面设防。“《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11)《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29页。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征战不断、民族迁徙频仍,华夷杂处成为客观现实,此时再强调华与夷的种族和地理区分已失去了客观条件,维护华夏文化不被破坏便成了最后一道防线。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考察,文化包括外显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指一个国家和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衣食住行模式等;价值观念则指民众对该国政权组织、法律制度、伦理道德等的认知态度。不同国家和族际之间的军事行动,可以使地理疆域很快发生变易,却难以改变疆域上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华夷之辨”更准确地讲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夷夏之防”思想,(12)张星久教授认为:“在这些研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华夷之辨’的三个方面的标准或三层基本含义中,‘华’、‘夷’之间的种族之分、居住区域上的内外之别相对比较次要,而文化标准亦即是否认同、实行华夏礼乐文化,才是辨别‘华’、‘夷’更根本、更重要的标准。”参见张星久《政治情境中的“华夷之辨”——秦汉以后“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与意义生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具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功能。
第一,在华夷文化交流中,为辨识文化的整体发展程度提供思想工具。《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13)阮 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64页。从文化显性层面的生活方式来看,“华”已进入农耕文明阶段,“夷”尚处于游牧、渔猎或采集文明阶段。“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14)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卷五《王制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8页。从文化潜在层面的价值观念来看,华夏依靠礼乐政刑培育起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价值观体系,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夷狄则大都依赖民族习惯进行粗放式管理,崇尚武力征服。秦穆公与由余的一段对话正好反映了这种差别,“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15)《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2页。既然如此,就要防止夷狄文化对华夏文化造成冲击。齐国管仲北御山戎、西击狄族,确保华夏子民“束发右衽”的生活方式不被外来文化破坏。对此孔子大为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6)阮 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57页。这显然是基于国家文化安全所发出的议论。
第二,在华夷文化碰撞中,为抵御外来文化的威胁与破坏提供理论武器。对抛弃华夏礼义而采用夷礼的文化行为,“华夷之辨”思想会给予强烈批判。如杞国(今河南杞县)本为华夏正宗,在杞成公(?~公元前637年)、杞桓公(公元前637年~前567年)时,“而迫於东夷,风俗杂坏,言语衣服有时而夷”。(17)阮 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55页。受东夷影响,抛弃了华夏文化,改用夷礼,对华夏文化安全造成威胁。孔子作《春秋》时,将杞成公、杞桓公直接称作“杞子”。(18)阮 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54页。杞国国君的爵位本来是“伯”,将其贬称为“子”,表达了对杞国“以夷乱华”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后来杞桓公迫于中原诸侯对他的贱视,又舍弃了夷礼,孔子在《春秋》中便称其为“杞伯”。杜预注文对此解释说:“复称伯,舍夷礼。”(19)阮 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18页。表达了对杞国回归华夏文化正统的肯定性评价。
(二)“用夏变夷”:“华夷之辨”要在文化之“变”
在频繁的族际交往中,“华夷之辨”不但主张要防止外来文化的不良冲击,还关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可能发生的改变,并力图引领文化变化的正确方向:即要用先进文化去影响其他文化,以期增强华夏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当然,也要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增强其凝聚力。这样的思想,对提升华夏文化的综合实力、维护古代国家文化安全大有裨益。
一方面,注重用华夏先进文化去影响夷狄的文化。先秦时期的华夏文化比之夷狄文化在整体上具有先进性,所以在防止夷狄文化对华夏文化形成冲击的同时,还要注重用华夏先进文化去影响夷狄。这就是《孟子·滕文公上》中所说:“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20)孟子的主张发端于孔子的言论。《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想到九夷之地居住,有人不理解他为何要到不开化的地方去。孔子回答说:君子住在那里,怎么还会鄙陋呢?参见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十《子罕第九·十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4页。由此可见先秦儒家对华夏文化保持着自信,坚信华夏文化能够引领夷狄向文明进化。如春秋时东方的徐戎是东夷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曾数次联合淮夷等抗周,后因受华夏文化影响,进而依附诸夏。公元前645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21)阮 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18页。徐戎在文化上向华夏靠近,引起南方荆楚的不满,以致兴兵攻伐。(22)公元前706年,楚武王讨伐随国。《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5页。但在强大的华夏文化的熏染下,久而久之,荆楚文化便融入到华夏文化之中,楚人也因崇尚中原礼乐文化而变成华夏的一员。正如董仲舒所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2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第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徐戎、楚人由夷入夏的进程,为孔孟“用夏变夷”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观念支撑,而用夏变夷思想诞生后,又反过来为华夏文化影响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留意吸收外来夷狄文化中的精华。“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4)韩 愈撰,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有学者认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公羊传》对孔孟夷夏观的发展。“《公羊传》的夷夏之辨思想,从思想渊源来讲,是导源于先秦孔孟的夷夏观念。其一是重视宣扬‘异内外’的思想,也就是要严夷夏之别。其二,《公羊传》对夷狄仰慕、遵守礼义者则‘中国之’。其三,《公羊传》对中国违背礼义者以‘夷狄之’,这与先秦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夷夏观相比,则是一个重要发展。”参见汪高鑫《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笔者以为,“进于中国”就是“变夷入夏”。概有二义:一是人,夷狄之人因学习尊奉华夏文化而变为华夏之民;二是文,夷狄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华夷交往中能够被华夏所吸收,变成华夏之文,从而使中华文化更具凝聚力和安全性。先秦时期在文化上“变夷入夏”的典范,当推赵武灵王(公元前340年~前295年)“胡服骑射”的改革,(25)《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08页。不但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加强,也为文化上的“变夷入夏”提供了有益尝试。它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总体上“四夷”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华夏,但其文化中也有值得华夏族学习的优点和长处。华夷之间的文化互鉴,才是提升文化实力、维护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三)“王者无外”:“华夷之辨”旨在文化之“合”
“王者无外”是《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主张,语见《隐公元年》《僖公二十四年》。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中考察,其义是指帝王当以天下为一家,不应将夷狄排除在外,而应将其与华夏视为一体。正如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逸民》中说:“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26)葛 洪:《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二《逸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101页。王者无外是对“华夷之辨”前两种理论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严夷夏之防”强调的是防止外来夷狄文化对本土华夏文化的冲击;“用夏变夷”强调的是用华夏先进文化去改变夷狄文化;那么,“王者无外”则是要淡化差别而求同存异,强调的是一体,只要信奉华夏文化者,其与华夏族是一体的,再无本土和外来之分之别,都是王者治下的一员。
“王者无外”作为“华夷之辨”中的高级理论形态,在后世公羊学中得到了不断的阐释而日趋完善。董仲舒是将《公羊传》发展成为公羊学的关键人物,他在论夷夏关系时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2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仁义法第二十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的观点,正是对“王者无外”的继承与发展。在他看来,夷与夏可分为中国、大夷、小夷三类,按照“《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2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第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的标准,不管夏与夷,其行为违背了礼义,就得“夷狄之”;无论大夷、小夷,其行为符合礼义,就得“中国之”。对于那些经过“用夏变夷”过程,进而仰慕华夏文化、遵守礼义道德的夷狄,应当充分给予肯定,当以中国之民一体相待。因为“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29)《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08页。天下之人都是君王的臣民,夷狄自然也不例外。
东汉末年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将“王者无外”解释为“王者以天下为家”,(30)阮 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73页。从而将这一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他提出自己的“三世”说,认为夷狄在这三世中是不断进步发展的:在“衰乱”世,诸夏尚未统一,无所谓夷夏之分;到“升平”世,夷狄已“可得殊”,(31)阮 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988页。这才有了夷夏之辨;再到“太平”世,夷狄通过学习华夏文化而不断进化,与诸夏没有太大区别,自当一体待之。“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32)阮 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74页。此时的华与夷,不论地域的远近、族群的大小,彼此都一样,夷狄也能与华夏享受同等待遇而加官晋爵,这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一统社会。何休的这一设想在他那个时代虽然并不现实,但后世的历史进程却证明了这一思想的重要价值,不同民族之所以能在不断的冲突融合中得以凝聚成中华民族,不同文化之所以能在不断的交流碰撞中得以发展为中华文化,与王者无外的理论不无关系。
综上可知,“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文化安全思想,为中国古代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在辨明华与夷之文化差别的基础上,主张“严夷夏之防”,防止本土文化受到冲击与破坏,维护华夏文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主张“用夏变夷”,既要用先进文化去影响其他文化,又注意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积极元素,提升华夏文化的影响力和开放性;主张“王者无外”,推动华夏文化与经改造后的夷狄文化共存共荣,共同构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这些思想特征使中华文化在长久的历史时期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且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秦汉以降的国家对外文化安全建设实践,正是在“华夷之辨”思想指导下展开的。
二、“华夷之辨”在汉人王朝的文化安全建设中的实践逻辑
中国历史进入秦汉时期后,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权统治格局,先秦的华夏族经过与周边夷狄的交流融合,发展成此时的汉民族;汉民族经魏晋南北朝与周边胡人的交流融合,又发展为隋唐时虎虎有生气的汉民族。中华民族正是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3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的民族大家庭。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往中,无论是中原的汉人王朝,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会用“华夷之辨”作为思想指导,以制定其对外文化交流政策,以期达到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目的。历史上汉人王朝对“华夷之辨”三种理论的运用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因时间、对象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理论作为指导。大体包括三种情形。
(一)对严重威胁汉人王朝文化安全的民族,多采“严夷夏之防”理论
秦汉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帝制国家,中原核心地带以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为主体,周边还散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其中北方、西北、东北的匈奴、西羌、东胡,以及西域诸族,尚处于草原游牧文明时代,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冲突最为激烈,而匈奴更是他们中间的典型代表,成为严重威胁中原政权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劲敌。
对于匈奴,秦朝采用了严格的“夷夏之防”策略。《汉书·西域上》云:“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34)《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后汉书·鲜卑列传》载:“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35)《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鲜卑》,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92页。可见,秦朝筑长城的意义在于“界中国”“别内外”“异殊俗”:华夷之间以万里长城为界,既防止军事上的越界入侵,又防止文化上的冲突破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察,长城无疑是秦朝维护国家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设施,同时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外显标识,是受“华夷之辨”中“严夷夏之防”理论影响的产物。故有学者指出:“至秦始皇筑长城,就从地理上将华与夷分开,华处长城内,夷狄处长城外,‘华夷之辨’自此成定式。”(36)李治亭:《“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的理论对决——〈大义觉迷录〉解读》,《历史档案》2021年第2期。
秦汉时对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夷狄之所以采用“严夷夏之防”的策略,乃因双方的文化差异太大。华夏定居的农耕文明与夷狄逐水草而栖的游牧生活相较,价值观冲突十分明显。比如,夷狄因地处苦寒,不得不向周边争夺生存资源,故而崇拜武勇杀伐,不尚礼义道德。《战国策·魏策三》称戎狄“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又因征战需要,盛行重青壮而贱老弱的风气,“贱长贵壮,俗尚气力”。(37)刘 安编,刘文典撰,冯 逸、乔 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一《原道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页。“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38)《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9页。这与华夏族注重礼义道德、提倡尊老爱幼的价值观迥异其趣。再如,夷狄为促进人口繁衍,流行收继婚。“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39)《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9页。这在重视人伦道德的汉人看来,为国家礼法所不容。
由于当时北方夷狄文化在整体上迥异于南方华夏大汉的文化,故秦汉对其采用“严夷夏之防”的策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秦汉对北方的文化策略也并非只有“防”这一手,间或还会使用“用夏变夷”之策。比如汉朝的“和亲”,“以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40)《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引导其仰慕华夏农耕文明的灿烂成果;通过派儒生辩士前往宣讲礼义道德,引发其对中原礼让仁爱风气的向往之情,逐渐改变匈奴喜好攻战的风俗。虽然终西汉之世,“用夏变夷”的文化政策对匈奴并未取得显著成效,但却对东汉时南匈奴内附并逐渐汉化起到了文化浸润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沿袭了秦汉时的对外文化策略,对北方民族采用“严夷夏之防”为主、“用夏变夷”为辅的路数。如曹操对南迁匈奴,使用镇抚并施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对不服管治者进行征讨,对为己所用者进行安抚,并将汾晋一带的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使匈奴豪右与其统辖的部民彼此分离,削弱其实力,目的就在一个“防”字。西晋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41)《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3页。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南迁如潮的局势,江统提出“戎晋不杂”的论调,(42)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卷二《江统·徙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1页。主张将夷狄迁回故地,更在于“防”。到宋齐梁陈偏安政权时,为了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正统,仍然要在文化之“防”上做文章。“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43)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117~118页。梳理这一脉络可知,“华夷之辨”思想在汉魏六朝文化建设实践中的运用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对北方更偏重使用其中的“严夷夏之防”理论。
(二)对难以危及汉人王朝文化安全的民族,则采“用夏变夷”理论
与对北方的策略不同,秦汉以降的汉族政权对南方各少数民族大都采取“用夏变夷”的理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44)《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朝鲜》,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68页。以指导对外文化交流的实践。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指东南及南方的“百越”(又称“百粤”)群体,支属繁多,包括瓯越、于越、闽越、南越等;西南地区的“西南夷”群体,分布在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45)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7页。《史记》中有专门的《西南夷列传》。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南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也各有不同。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早已注意到这种差异:“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46)阮 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第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29页。既然南方少数民族“舒缓”,对华夏文化难以造成严重威胁,故中原汉族政权对其采取“用夏变夷”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主要从如下两条路径贯彻落实。
第一,设置郡县,广施礼乐政刑教化。秦汉时期在南方诸夷地区广泛设置郡县,推动南方诸夷的华夏化。在秦汉史料中,设置了郡县的地区往往被称作“徼内”,未设的则称“徼外”。(47)《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81页。对徼内诸夷所在的郡县,中央政府要派具有儒学背景的官员前往治理。这些官员既是当地的父母官,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十分重视用华夏文化去教化当地民众。如西汉文翁(公元前187~前110年)任蜀郡太守,刚上任时,便采取多种措施来助推“用夏变夷”政策的落实。既将本地人送到京师长安“受业博士,或学律令”。(48)《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文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5页。又在当地兴办学校“文翁石室”,(49)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第三十二《学校礼通故·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54页。“县邑吏民见而荣之”,(50)《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文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6页。纷纷送子弟前来求学。对此班固著《汉书》评价说:“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51)《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文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6页。又如,东汉张翕(公元89~105年),任越嶲郡太守,在当地普施仁政,“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52)《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西南夷·邛都》,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3页。朝廷命官在南方诸夷郡县实施礼乐政刑教化,大大加强了当地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第二,加强交流,扩大华夏文化影响。对于徼外诸夷,比邻郡县的汉人官吏往往会利用“文而化之”的方法,去扩大华夏文化的影响,以吸引他们前来归附。如西汉元帝时期,王尊担任益州刺史,辖区附近颇多夷人,“尊居部二岁,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53)《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王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29页。又如东汉前期的郑纯,任益州西部都尉,“纯独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叹”。(54)阮 元:《揅经室集》续集卷八《文选楼诗存第十五·丁亥·宿永昌池馆流泉树石湛然清华名之曰小兰津并诗示镇府诸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44页。散居在洱海周围和澜沧江两岸的哀牢夷对他十分仰慕敬佩,最终一致决定“举国归汉”。可见,在南方少数民族华夏化的过程中,作为儒者的循吏于地方推行儒家教化的同时,也在践行着华夏文化传播的时代使命。如果说徼内诸夷华夏化的进程是这样的:政治归属——身份转换——文化认同,即先设置郡县,实现诸夷的政治归属和身份转换,再用文化进行同化,使其转化成真正的华夏子民。那么,徼外诸夷华夏化的进程则刚好相反:文化认同——身份转换——政治归属,即先用文化进行影响,使其向往先进的华夏文化,进而主动要求设置郡县,变成汉族政权治下的编户齐民。
汉人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用设置郡县、加强交流的方法推行“用夏变夷”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早在汉武帝时就露出端倪。“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55)《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77页。可见此时的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已经有了价值认同。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仍然沿袭“用夏变夷”之策,大大加速了当地族群的华夏化进程。由此可以看到“用夏变夷”对促进民族融合的巨大理论功能,而不同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又反过来大大增强了汉人王朝维护文化安全的能力。
(三)当汉人王朝的文化实力十分强大时,则采用“王者无外”的理论
“华夷之辨”思想在秦汉魏晋南朝的实践运用,基本上是“严夷夏之防”与“用夏变夷”这两种理论交互使用。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做法,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汉族政权处理夷夏关系的总体趋势是帝国向北方划定疆界,“严夷夏之防”;向南方则是设郡县、施教化,以“用夏变夷”推动南方诸夷的“华夏化”。及至唐朝,国力已达到帝制时代的鼎盛时期,“华夷之辨”中“王者无外”的理论才得以运用于实践。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56)《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为保证这一文化策略顺利展开,唐王朝采取了多种措施。在政权建设上,于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推行汉文化。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下诏:“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5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第一百七十《帝王部(一百七十)来远》,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90页。据统计,唐朝的羁縻州多达856个,涉及边疆地区的突厥、回鹘、党项、吐谷浑、奚、契丹、靺鞨、高句丽、羌,以及西域、西南、岭南各族。在法律适用上,对周边少数民族在“因其本俗”的前提下,统一适用国家的律令格式,积极推行汉法。如贞观四年(630年)突厥突利可汗率部降唐,唐在其所领部落设置顺州,任突利为顺州都督。唐太宗告诫突利说:“当须依我国法,齐整所部。如违,当获重罪。”(58)杜 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边防十三·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412~5413页。在教育制度上,鼓励周边少数民族和四邻蕃夷学习汉文化,允许其参加国家统一实施的科举考试,并形成“宾贡进士”制度,与“国子进士”“乡贡进士”区别开来。如朝鲜的崔致远(857年~?)、日本的阿倍仲麻吕(698~771年)等,都在唐朝考上进士并任职为官。东汉何休关于“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设想,至此已不再是空想,而变成了现实。
通过这种种举措,华与夷的区别界限被淡化,大家同为大唐子民,适用同样的法律,学习同样的文化,享受同样的对待。正如盛唐诗人杜甫在《夔州歌》之三中所咏唱的那样:“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唐宣宗时,大食人(今阿拉伯人)李彦升参加科举考试且一举及第,引起汉人士大夫争议。进士陈黯为批判这种陈腐观念,专门写了《华心》一文,强调“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59)董 诰:《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陈黯·华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86页。只要有向往礼义的态度和行为,夷狄就变成了华夏。昭宗时进士程晏写《内夷檄》,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60)董 诰:《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一《程晏·内夷檄》,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650页。只要推崇仁义忠信的中华文化,就不能再视之为夷狄。
唐朝“爱之如一”的对外文化政策是践行“王者无外”理论的结果,其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华夷的界限,不再纠结于二者的不同。只要认同华夏文化,“慕仁义、行礼乐”,“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61)董 诰:《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一《程晏·内夷檄》,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650页。夷就是华。将“华”的范围无限地扩大,便能将周边的“夷”不断纳入华的范畴,在加强民族融合的同时,更使中华文化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发展成为以华夏文化为主干、熔各少数民族文化精华于一炉的文化复合联结体,中华文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样的文化就像大江大河,既流淌不息,又不断汇入沿途支流而变得澎湃浩大,具有超强的凝聚力和包容性,同时也具备了强大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
三、“华夷之辨”在少数民族政权文化安全建设中的实践逻辑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为数众多,综合起来分析,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与华夏王朝并立的政权;一类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君临天下的大一统政权。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政权,为了更好地解决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大都采用汉人提出的“华夷之辨”思想作为指导,并非照搬,而是有选择地汲取。因为他们多是从周边地区崛起,要入主中原就必须突破而不是应用“夷夏之防”理论。一旦建立起与汉族并立的政权,就会选择“用夏变夷”做理论武器,倡导“纳之华夏”“以夷入夏”;及至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大王朝时,便会选择“王者无外”为价值指引,宣扬“中国之道”“华夷一家”,积极学习推广汉文化,培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价值观体系,使之成为本国多民族的共同信仰,从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维护文化安全。
(一)“夷夏并尊”的少数民族政权对“用夏变夷”理论的运用
“夷夏并尊”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出现在两个大的历史时段。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时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公元304~439年),包括“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等十六国”。(62)永 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二 载记类存目·十六国考镜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89页。南北朝时北方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二是五代两宋时期,北方出现了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政权运用“用夏变夷”理论做指导,践行“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路,(63)韩 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原道》,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页。积极学习汉文化,推动自身的汉化进程,他们“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64)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仁宗·庆历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41页。使本国文化实力大为提升,为本国国家安全提供了文化保障。
第一,争夺文化正统,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一个政权的存在必须是名正言顺的,才具有正统地位,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而为国家正名,争夺正统地位,单靠武力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从文化上入手。
首先,从国号上争正统。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南方汉族政权自然要在文化上对他们发起攻势,指责他们的君长是“僭号称帝”,(65)《晋书》卷四《帝纪第四·惠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4页。所建立的国家是伪政权,并以“克复神州”“中兴晋室”(66)郭 璞:《郭弘农集》卷一,山西:三晋出版社,2018年,第8页,第68页。为旗帜,号召南北各族民众服从自己的统治,抵制诸夷政权的统治。针对这种舆论攻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打起了文化战。如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前赵(304~329年),便以匈奴祖先曾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作为理由,定国号为“汉”,打的是恢复汉室的名义,从舆论上为其入主中原提供合法性支撑。再如南北朝时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原来国号为“代”,后改称为“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67)魏 收:《魏书》卷二十四《列传第十二·崔玄伯》,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1页。这里的魏当指三国曹魏。之所以做如此改变,是因为大汉的“命”被曹魏所“革”,曹魏的“命”又为西晋所“革”,西晋的“命”又被十六国所“革”,现在北魏又统一了北方,革了十六国的命,自然该以神州上国“魏”为国号,传承的正是华夏文化的正统。
其次,从地盘上争正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通过使用武力占领中原地区之后,就会从文化上论证其正统性。依照“华夷之辨”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路,中国即指华夏文化的正统,既已入驻中原之地,自然是正宗中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就明确地说:“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68)魏 收:《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四之一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44页。正因为北魏占据了中原地区,虽为鲜卑族所建立,后世学者杨奂也主张视北魏为“正统”,“舍刘宋取元魏何也,痛诸夏之无主也。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69)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鲁斋学案补遗·雪斋学侣·文宪杨紫阳先生奂·正统八例总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353页。又如两宋时北方的金朝政权,也因占据了中原之地,无不以文化正统自居。“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有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70)王 恽:《王恽全集汇校》卷第一百《玉堂嘉话卷之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57页。正因为有了文化正统的观念,也赋予了金人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金将完颜陈和尚与蒙古军作战,失败被俘,不屈而死。金人将士莫不感叹地说:“中国百数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71)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第二十七《碑铭表志碣·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491页。
第二,学习华夏先进文化,为政权的稳定性提供制度保障。魏晋南北朝或两宋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大都处于原始部落时代,要使自己走向先进、文明,服务于统治中原的需要,就只能仰仗“用夏变夷”的理论功用,积极学习汉文化,在政治上推进封建化,建立起以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法制上推行“汉法”,仿照中华法系中的律令典章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386~534年)为例,其作为南北朝时与南方对峙的第一个王朝,早期还保留着鲜卑皇族拓跋部的辫发习俗,在政治法制上也不发达。在“雅好读书”的孝文帝(467~499年)即位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政治上学习汉人官职,完成封建化进程,尤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史称“故变时法,远遵古典,班制俸禄,改更刑书”。(72)《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页。这里所说的“古典”,即汉法的典章刑制,并邀请汉儒与律学博士制定颁行《太和律》(495年),其编纂体例和主要内容融汇了汉、魏、晋以来的立法成果和儒家法律思想,获得了“齐之以法,示之以礼”(73)《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七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7页。的美誉。
北魏之后经长期探索而至北齐,少数民族政权在立法上进入了一个新高度。由渤海著名律学世家封述主持编撰的《北齐律》(564年),史称“法令明审,科条简要”,(74)《隋书》卷二十五《志第二十 刑法》,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06页。无论是体例、篇目、罪名,还是刑制、法例,都趋于定型,成为隋唐法制的主要来源。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建设,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是“北优于南”;(75)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六《北齐律考》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93页。法史学家程树德先生也指出:“盖唐律与齐律,篇目虽有分合,而沿其十二篇之旧;刑名虽有增损,而沿其五等之旧;十恶名称,虽有歧出,而沿其重罪十条之旧。”(76)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六《北齐律考》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91页。由此可见,中华法系的时空演变脉络,在秦汉魏晋之后,不是经由南方的汉人士族政权传承,而是经由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传承到隋唐,从而形成一套对亚洲诸多国家影响深远的法文化体系。故尔,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律文化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内容,对维护中华文化的稳定,进而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一统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对“王者无外”理论的运用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1~1368年)、满族建立的清朝(1636~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统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地域之大,甚至远超以前的汉族王朝。《元史》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77)《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45页。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其版图更是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面积。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之中,民族成分更加复杂,既有本族人,又有汉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之人,彼此价值观差异大,文化冲突在所难免。这样的矛盾是无法用蒙古铁骑和八旗金戈来解决的,只能靠文化,而其自身的文化又难以担此重任。所以无论元朝还是清朝,都选择了“华夷之辨”中“王者无外”理论,来解决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首先,论证文化正统,为政权合法性筑牢理论基石。如果说前面的“夷夏并尊”型少数民族政权是在与汉人王朝争夺文化正统,那么此时的一统天下型政权,在政治、军事上已经没有了对手,就不存在与谁争正统的问题。但其面临国内知识界对政权合法性发出的质疑论调,是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廓清的。如南宋遗民、元代儒士郑思肖(1241~1318年)在其所撰《心史》中认为,北魏拓跋氏虽采用了中国的礼乐文物,但也是“夷狄行中国事”,是“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78)曾枣庄,刘 琳主编:《全宋文》第三百六十册卷八三三五《郑思肖五·古今正统大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借古讽今地隐斥蒙元政权并非正流。针对这样的言论,必须从思想上“正名”,才能助力于政权稳固。元初名儒郝经(1223~1275年)的言论颇具代表性:“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79)郝 经:《陵川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2页。元初另一位著名学者杨奂(1188~1255年)也用“道”来论夷夏关系:“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80)杨 奂:《还山遗稿》卷上《正统八例总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8页。元朝虽为蒙古人所立,但推行的却是华夏文化。如元世祖忽必烈,“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81)《元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7页。既然元朝习的是儒学、行的是汉法、立的是汉制,所存载的就是中国之道,就是王道。道之所在,正是文化正统之所在。
清朝对文化正统的论证力度更大,甚至有皇帝出场发声。一代名儒吕留良(1629~1683年)不承认清朝政权的正统地位,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82)雍正编纂,张万钧、薛予生编译:《大义觉迷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第116~118页。影响了一大批儒学士子。湖南儒生曾静信奉其说,著《知几录》《知新录》,传播反清言论。针对曾静的论点,雍正帝与之展开了辩论,进行了驳斥。曾静运用的是“华夷之辨”中“严夷夏之防”的理论,并且是其中以种族、地缘辨华夷而非以文化论夷夏的偏见,早已被历史所抛弃,在清朝已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际,徒显落后与狭隘。雍正运用的则是“华夷之辨”中“王者无外”的理论,更适合当时大一统格局的时代需求。通过对曾静种族论和地缘论的批驳,雍正最后说:“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8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资料》第四辑《大义觉迷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页、第29页、第8页、第55页、第4~5页。“华夷一家”正是对“王者无外”最好的诠释,将“华夷之辨”思想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此时此刻,执意区分华夷不过是“妄判中外”进而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谬论,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在王者治下,无论华夏还是夷狄,大家都是一家的;这个大家庭就是正统,没有必要在家庭成员中再分出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以此,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亦以此。
其次,推崇礼义道德,为国民凝练统一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8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页。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构建了一套古代的道德观念体系,古人常谓之“礼义道德”。正如唐朝皇甫湜所说:“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85)董 诰:《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皇甫湜 二·东晋元魏正闰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31页。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是因为有一整套礼义道德观念。古代以礼义道德为名的价值观体系,包揽了忠孝节悌仁礼信廉等各种德目,这样的观念外显于经史子集、典章文物、庠校庙堂等物质载体之上,对内植根于芸芸众生心灵之中。当绝大多数人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这些观念,做到心往一处想时,文化的凝聚力便发挥出来了,这对消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此,一统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莫不热衷于推崇礼义道德,以培育国民统一的价值观。
元朝在建立统一政权之后便形成了“必行汉法乃可长久”(86)许 衡:《鲁斋遗书》卷一四《郡人何瑭题河内祠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3页。的共识。这里的“汉法”,不仅仅指法律,也指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需遵循汉人的办法来设计建设。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大元通制》,承袭了唐宋律典中五刑、五服、十恶、八议等内容,体现了“遵用汉法”的立法原则;在教育制度上,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更将其确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为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提供了保障。据《元史·许衡传》载,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地方官学已达二万四千四百余所,遍及天南海北,甚至是边疆郊野,程朱之学“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87)《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列传第四十五·许衡》,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28页。儒家的伦常标准和道德观念已为元朝子民广泛认同。
清朝康熙帝三十年(1691年),下诏决定对长城不再修理、驻兵,长城已不再是“夷夏之防”的物理界限,而只是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后又宣称:“朕君临天下,无分内外,视同一体。”(88)《清实录》第五册,《圣祖仁皇帝实录(二)》卷一百九十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2页。凡清朝治下之人,不再以种族、地缘分夷夏,“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89)《清实录》第八册,《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96页。用统一的礼乐文化进行教养,用统一的政令刑法进行治理。在“华夷一家”思想指导下,此时的中华文化已不再是单一的华夏文化或汉文化,而是融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精华于一体的大文化系统,形成了“以德化民,以刑弼教”(90)《清实录》第四册,《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九十四《康熙二十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7页。的文化安全运行机制。“教”指“五常之教”,(91)阮 元:《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5页。《尚书正义》释为“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9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宋代朱熹进而将其扩充为“三纲五常”。用道德观念教化万民,用法律制度来帮助道德教化的推广与普及,在德礼与政刑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凝练成清廷宇内不同民族共同遵行且稳固不变的价值观,产生了“久道成化,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93)《清史稿》卷八《本纪八 圣祖本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5页。的良好效果,展示出强大的保障文化安全的功能。
四、结 语
假如把国家安全比做一座大厦,那么政治、军事、经济等就像钢筋、砖木一样是硬件,文化则像水泥、砂浆一样是软件。正是有了软件,才能将各种不同的硬件黏合在一起,凝聚成牢固的建筑体,由此可见文化对国家安全的意义至关重要。“华夷之辨”作为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安全思想,包含“严夷夏之防”“用夏变夷”和“王者无外”这三种理论形态,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为秦汉以后的汉人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安全建设实践提供了有力指导,在防止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用先进文化影响落后文化、促进不同文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中华文化融聚成一个“多元一体”的大文化系统:以华夏文化为主体、融少数民族文化精华于一炉,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且五千年传承不绝的文化奇观,与华夷之辨的思想不无关系。这样的思想智慧,对今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开展文化安全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