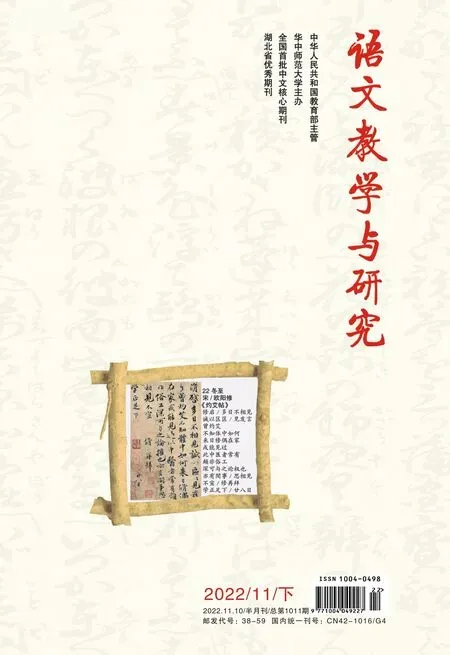鲁迅与易卜生之比较研究
◎肖国武
鲁迅的同窗好友许寿裳曾称赞鲁迅是介绍域外弱小国家文学的先驱,并非是夸大之辞。在其早期论文中,就大力介绍过众多的外国作家作品,包括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1]此论文是鲁迅留学日本弃医从文后在东京研究文学期间所作,是其初步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受到西方文学思想影响后当时思想状况的记录,而鲁迅爱易卜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及,“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2]
1918年《新青年》杂志出了易卜生专号,译载了他的三个剧本:《玩偶之家》《人民公敌》和《小艾友夫》,同时另一个进步杂志《新潮》译载易卜生的又一名剧《群鬼》。鲁迅主张道:“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3]此时的鲁迅对于易卜生推崇备至以致到了崇拜的地步。后来在谈到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出刊易卜生专号由来时指出:“我想,也还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得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4]足以说明此时鲁迅与易卜生的思想已达到某些方面的一致,两位文化巨人实现了思想的对接。更明显的是,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提出“娜拉走后怎样?”似乎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两年后,鲁迅写了小说《伤逝》。凡此表明,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然而当两位文化巨人站在一起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
一、相近的时代背景——历史的抉择
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相继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领导的维新改良,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革命运动,推翻了千年帝制,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担负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中国的现实政治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使中国仍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中国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的是重大的历史选择。
北欧国家挪威虽位于边陲之地,但西欧的社会思想动态对它并不隔绝,无论是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和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还是十九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上发生的革命运动,对其社会都产生过冲击。挪威虽然远比英法等国落后,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也日渐发展起来。十九世纪正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其历史任务一方面反对封建主义,另一方面也在批判资产阶级罪恶,同时处于社会转型期。
二、相同的社会态度——反叛与改造
在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进程时,鲁迅曾说:“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5]正如在《一件小事》中所表现的,以劳动者的高尚品质及高大形象来批判小资产阶级,以手中的笔作为解剖刀,解剖社会的毒疮,而更多的是无情的解剖自己思想中的恶疾。蜕变是痛苦的,选择却是坚决的。而对孱弱的国家,愚弱的国民,认为“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改变他们的精神”。[6]
易卜生于1850年参加工人和学生的革命运动,做革命宣传工作,而在此之前,即法国革命爆发时,就写了一个反抗专制暴政题材的剧本《凯替来恩》。他在回忆中写道:“在伟大的国际暴风雨咆哮声中,我也同我所处的那个小社会——由于环境和生活条件而困处其中的小社会打起仗来。”究其根由,相同的反抗思想都源于不幸的生活遭遇,而最为关键的则是对当时所处社会的清醒认识。谈到改造问题时,他在1885年的一次演说中说:“现在的欧洲,正准备着改造社会关系;这种改造,主要是要解决工人和妇女前途的问题。我等着这个改造,我为这个改造而兴奋,我愿意用我终生的一切力量为这个改造而行动。”[7]
背叛、批判、反抗与改造,构成了鲁迅和易卜生对黑暗社会的基本态度。
三、相似的个人处境——孤独
鲁迅对黑暗统治和邪恶势力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对中国民众的落后与愚昧的态度也是众所周知的。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8]他的启蒙主义立场使他不可能与大众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致或者打成一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不是由于对民众的冷漠,而恰恰是由于对民众的热爱。正因为爱之深切,才对其弱点不能容忍,发出毫不留情的猛烈的批判。这样使他走上了既无权威可依,也无大众可靠的异常孤独的道路。
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高涨的年代,易卜生曾短暂地参与政治活动,不久即对政治冷淡,同时也与革命民众越离越远;又因不满本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政府对普奥联军第二次侵略丹麦的中产政策,怀着失望和愤怒离开了祖国,长期侨居国外,心境是凄凉而孤寂的。在《人民公敌》中,借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之口发出感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真切地反映出作者在当时具体情况下的激愤情绪和孤独处境。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称易卜生为“欧洲的最愤怒的人”。鲁迅一面推崇易卜生的斗争精神,一面也指出他的孤独处境,“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又说“……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9]易卜生即以孤独的斗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四、共同的创作题材——妇女问题
纵观鲁迅一生的小说创作及所关注的问题,可归结为三大类型:(一)农村社会和农民题材;(二)知识分子题材;(三)妇女问题题材。其中有些作品是多题材相重叠,以《伤逝》最为典型。妇女问题是鲁迅始终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除在小说里有所表现,于大量的杂文中也多有论及,如《记念刘和珍君》《女人未必多说谎》等篇。鲁迅关注此问题,缘于千百年来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与压制,他站在反封建的高度加以阐述,同时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输入,使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妇女问题,从个体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因为妇女解放是人的解放、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易卜生创作了一系列内容深刻的“社会问题剧”,这些作品触及了当时的政治、宗教、道德、法律、家庭、妇女和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问题,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易卜生关于妇女和家庭问题的见解,集中体现在五四时期介绍的三个剧本《玩偶之家》《小艾友夫》和《群鬼》,以及后来的《海上夫人》,在批判资产阶级罪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提出了妇女解放这一重要社会问题。妇女问题也是易卜生一生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
但是,审视两位文化巨人的整体特征,我们更多地是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一、易卜生的矛盾与悲哀
易卜生是一个陷入深重矛盾的人物,他虽然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批判的锋芒涉及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却始终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标榜“自我”,进行所谓“个人精神的反叛”,他说:“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一时会促使你把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唯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东西,而把其他的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要把这信看作是我的兽性的一种表露。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10]但他对什么是“人的本质”却不是很清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来说,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存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易卜生认识不到这一点,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不能进入新的思想境界,始终没能突破资产阶级立场,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年代,而挪威不是一个阶级斗争不够充分和深入的社会。易卜生的这一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其作品之中。《布朗德》的主人公布朗德牧师痛恨现存制度,追求崇高理想,要求理想和实际生活的绝对一致。他的处世格言是“要么全部,要么全无(All or nothing)”。由于他的理想缺乏明确的内容,更没有实现理想的切实途径和手段,决定了他的事业不可能成功。布朗德的失败在于他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理想家,这一形象的最终结局正是易卜生思想矛盾的真实写照。
由于挪威和全欧社会冲突日趋尖锐,帮助易卜生明确了立场,使他用现实主义方法写作。但他仍远离政治,远离无产阶级。正是这样,易卜生无法摆脱思想上的矛盾,不能随着时代前进而进入共产主义阵营。到九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日益过渡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充斥反动思想,易卜生的创作与思想也遭遇到了危机。由于看不到改变丑恶现实的途径,致使他作品的批判力量有所减弱,悲观主义情绪也变得浓厚起来,作品往往带有神秘色彩。他终于在一八九一年回国,向挪威的资产阶级社会伸手妥协。此时他的名声虽然已响誉国内外,却表现也极大的悲哀与无奈。
易卜生距离现代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很遥远,他未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去反对资本主义的。德国文艺评论家费兰茨·梅林曾这样说:“易卜生再怎样伟大,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诗人;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并且必然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于本阶级的没落便看不见,也不能看见任何解救的办法。”其悲观的根源在于立足于资产阶级而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没有得到发展,以致于最终停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二、鲁迅的斗争与飞跃
“五四”时期的中国已进入尖锐的阶级斗争时代,实际的社会变革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历史问题。在这种历史境况下,任何一个敢于直面社会、热爱人民并力图以艺术改造人生、社会的作家都是要从具体的社会变革中获得特定的内容,以此重新来理解和诠释“人的解放”的时代内涵。人们无论对《伤逝》等小说主题做怎样的解释,物质因素在涓生与子君离异的悲剧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自始至终,鲁迅都在密切地关注物质现实,在艰难的探索之后最终选择了斗争,在斗争中,超前思想在发展。
鲁迅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也曾有过暂时的悲观、失望与彷徨,这是他思想矛盾尖锐到极点时的表征,随着矛盾的解决促成了他思想的跃进。鲁迅思想的每一进步表现,在时代推动下都不断得到发扬,其根本原因是他所处的时代虽同属社会转型期却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鲁迅主要活动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新时代,中国有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给他以极大影响。鲁迅积极支持并参加这一运动,以致后来与党组织有了直接的极为密切的联系,成为党领导下的一名自觉的战士,走入了无产阶级阵营,其思想获得了质的飞跃。
三、鲁迅对易卜生的超越
鲁迅看重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对易卜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越来越不满意。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称赞过这种反叛,那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在言论上和创作上批判它了,并且指出易卜生最后还是妥协了:“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易卜生终究伸出和睦之手,“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11]
而鲁迅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解决了易卜生终生不能解决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就越过易卜生,突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相信无产阶级才有将来,勇敢地参加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洪流中来,成为共产主义者。鲁迅以封建阶级的叛逆在长为工农斗争的战士,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抗发展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斗争,从革命民主主义提升到共产主义,实现了对易卜生,也是对时代的伟大超越。
注释:
[1]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六.《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第3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第1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11]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