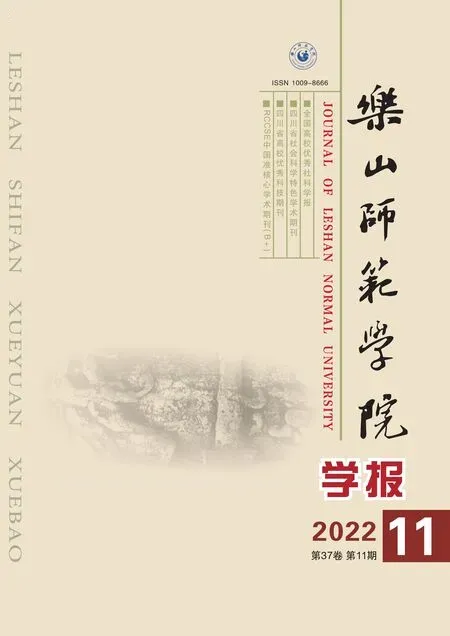断根、恋乡与纠缠
——新时期乡土文学中农裔知识分子的乡土心态研究
李 松,何 恋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a.文学与传媒学院;b.软件工程学院,重庆 合川401520)
农裔知识分子(以下简称“农知”)指的是通过知识由农村走向城市、完成了由农村身份向城市身份转换的人。乡土中国的集体无意识塑造了他们的农民性人格,而现代教育则帮助他们建构了知识分子人格(现代化人格),这二重人格的不断拉扯铸就了“农知”的双重文化色彩。拥有双重文化色彩的他们,深受乡土作家的欢迎,成为了乡土小说中除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外的第三类重要写作对象。
纵观新文学百年历史,对“农知”的书写集中在城乡关系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现代性进程中,“农知”的伦理取向和乡村情感也在逐渐分化。本文借助“农知”的乡村情感这一视角,力图通过分类研究和社会文化解读廓清城乡关系变迁、作家心态转变以及乡土文学最新的发展面貌,并以此为重要窗口窥视社会文化心理和时代弊病。
一、农裔知识分子的三种书写模式
“乡土经验书写的出现,其实就是启蒙主义思想的一个产物。”[1]“农知”便作为启蒙的载体,伴随着乡土小说一起诞生。鲁迅率先在小说中以“返乡”视角塑造了魏连殳和吕纬甫两位“农知”形象,自此,“农知”成为了乡土小说的常客。之后许钦文、师陀和萧红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创作,都是寄寓城市的“农知”怀乡情绪的流露。在政治意识高涨的十七年时期,“农知”在文本中消失,并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在高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离场、城乡关系松动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农知”再次在小说中出现。及至当下,在“城乡间性”“城镇中国”和“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下,“农知”书写再次成为不可忽视的潮流。从以《人生》(路遥)、《浮躁》(贾平凹)、《无土时代》(赵本夫)等为代表的虚构写作到以《中国在梁庄》(梁鸿)、《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王磊光)和《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黄灯)等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农知”谱系。随着谱系的不断丰富,主题也从单一的“怀乡”变得多元,“农知”形象被注入了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依据对“农知”书写侧重点的不同,新时期乡土文学中的“农知”书写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一是乡下人进城模式。“农知”进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乡下人进城”的具体化表达,除开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和进城务工的普通农民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承担了批判现代性和怀念乡土中国的叙事任务。此类创作重点关注“农知”融入城市的艰难,刻画他们在城市语境中的苦难遭遇、伦理碰撞、阶级鸿沟和妥协退让等,从而凸显城乡差距。《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中的涂自强虽然通过高考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是他无法跨越阶级的鸿沟,先后经历爱情失意、毕业即失业等,最终因肺癌死在异乡;《雨把烟打湿了》(须一瓜)中的蔡水清借助婚姻留在了城市,但与妻子在家庭地位方面的不对等,造成了他主体性的衰落,在无法融入城市的困扰中毫无悔意地杀死了那个看起来像自己的出租车司机。这一类“农知”行走在城市的边缘,以一个敲门人的姿态叩问进入城市的方式,但始终无法被城市接纳。
二是“他者”模式。此类创作认为,“乡下人”不过只是“农知”们的一种外在身份表示,作家更关心是他们作为“城市人格”或“知识分子”的一面。通过人性异化、物欲贪恋和灰色生活等关键词,表达知识分子主体性衰落这一主题。《风雅颂》中的杨科和《桃李》中的邵景文都是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表达,《婉的大学》中由农村考上大学的婉因为无权无势也在人性和物欲中苦苦挣扎。
三是乡土情感模式。此类写作虽然涉及城乡差异,但作者的侧重点不在于表现“农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问题,而在于关注他们的乡村情感态度:是在城忘乡,还是在城望乡?此类模式自许钦文、师陀的“自叙传”开始,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的新时期再次焕发生机并一直延伸到当下。作家在塑造这类形象时总是将其置于“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主流、隐性的文化批判和“返乡”的文学母题中,并借助作为文化隐喻的女性形象来加以演绎。相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对现代性决绝的批判不同,浸淫了多种文化的“农知”流露出了较为斑杂的价值取向。依据他们的乡村态度与最终选择,“农知”的乡村情感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断根型,表现为在巨大的城乡差距面前对生养了自己的故乡的主动舍弃与决绝背离;(2)恋乡型,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始终热爱着乡土;(3)纠缠型,纠缠型介于断根型和恋乡型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乡村情感追求与价值取舍。在城乡关系剧变的当下,相较于前二者,“农知”的乡村情感态度更值得研究。
二、断根型地之子:文化转型期的决裂
断根,斩断自己根植在乡土上的根,是向养育了自己的农村的主动舍离与抛弃。这种舍弃既体现在空间位置上的逃离农村奔向城市,也体现在心灵情感上的挣脱农村拥抱城市。
断根型地之子集中出现在时代变革初始期,同时也是城乡关系松动的时期。在“归来—离去—归来”的行为模式中,农民性逐渐让位于知识分子性,“农村人”身份成为他们迫切想要摆脱的枷锁。“读大学的最大坏处就是使我这个20岁没出过山沟的农村小子认识到外面世界的意义,我不知道回家还有什么意义”[2]。断根型地之子以“在村思城”和“在城忘乡”为主要表现形式,其共同点在于:在城市,他们游刃有余;在农村,他们举步维艰。例如高加林(《人生》)和夏风(《秦腔》)。
高加林,生活在城市与农村对立关系刚刚缓和的新时期初期,是新时期第一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断根型地之子。高加林的人生观中隐含了一个观点:农村没有出路。他不安于农村,自由于城市。虽然刘巧珍在某种程度上稀释了高加林对乡村生活的厌恶,但发自内心的对农村的忽视仍是高加林农村观的主导面。这一方面体现在他的阅读上,“高加林的阅读、知识、才华和集体劳动、经济发展农村现代化建设完全不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体现在他不参与农村事务上,“卫生革命”事件中高加林在撒完漂白粉后就消失了,这是“高加林为代表的农村青年对领导和维护乡村共同体的主动放弃”。[3]他将自己凌驾于农村之上,就是为了远离农村,可以预见的是单纯的乡土文明已经很难唤回沐浴并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高加林。入城后,他像换了个人一样,不再是返乡时的无奈、悲愤和绝望,取而代之的是兴奋、自由和激动。他无情地抛弃了乡土女孩刘巧珍转而与城市姑娘黄亚萍结合;咖啡、电影院和游泳馆等极具城市印记的现代化产物成为了高加林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我们承认刘巧珍和黄亚萍分别代表了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那么在高加林的选择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乡土是失意无奈的退守地,而城市才是最终的价值指向。
在农村举步维艰与在城市如鱼得水的强烈比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决然的断根型地之子,但高加林不是孤例。夏风,一个处于城市化进程浪潮不可阻挡的21世纪初期的农村新一代知识青年,成为我们理解《秦腔》主旨和窥视农村现状的重要载体。夏风生活在城市化进程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多年的省城生活磨平了他农民性的一面,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性的一面。贾平凹在小说中用具体可感的秦腔和白雪作为乡土文明的指代,那么夏风对秦腔和白雪的疏离与抛弃则暴露了他真实的乡村观。“我就烦秦腔”是夏风同乡土的诀别;为了断根,他甚至逼迫白雪堕胎。可见夏风在“文化断根”的道路上比高加林更进一步,他主动、直接、彻底、完全地忘却了乡村,成为了完全断根的现代都市人。
“农村竭尽全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都是对农村生活最彻底的背叛者。”[4]断根型地之子渴求逃离农村。然而,这种渴求越迫切,他们的农民身份却越发凸显。《生命册》中的吴志鹏代他们发出了“怎么就扒不掉‘农民’这身皮”[5]的感叹。断根型地之子活跃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这是社会文化急遽转型时期,也是农村与城市关系最为微妙和松懈的时候。在城与乡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在“关于自身精神、文化血缘的指认”[6]中,断根的地之子们不约而同地将逃离农村走向城市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
作家抓住了时代的脉络展现了“农知”在大变革语境中的个人选择,如果单纯从时代——每个人在时代变革浪潮中都可以依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做出选择——的角度考虑,“农知”的选择无可厚非,本文也不以“土地”为核心做出价值评判。
三、恋乡型地之子:时代弊病的调和
恋乡,顾名思义是对故乡的眷恋、怀念与思念。恋乡型地之子体现出“人在城市、心系乡村”的“回望式”特点,他们内心深处的“乡愁机制”一旦被触发,就会呈现出怀乡恋乡的情感指向。如果说断根型地之子总是出现在时代变革浪潮的初始期,那恋乡型地之子则出现在时代变革浪潮的高潮期。《浮躁》写于《人生》四年后的1985年,《无土时代》写于《秦腔》四年后的2008年,甚至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有此类人物(孙少平)的书写。
(一)作为反思存在的恋乡型
恋乡型地之子由来久已,“农知”出身的京派作家就是此类形象的源头。萧乾在《给自己的信》中说:“虽然你是地道的城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相望却都寄在乡野。”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废名也将乡村看成最终的精神归宿。这一时期的作家对乡村的怀念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现实怀念和虚构创作。现实怀念(《父亲的花园》《果园城记》和《呼兰河传》)通过回忆、书信等非虚构创作表达流浪心态;虚构创作(《边城》《桥》和《竹林的故事》)通过建构理想世界表达恋乡情感。
“农知”出身的作家虽怀念乡土,但他们的创作却很少触及“农知”这一类人物,他们的恋乡体现在对农民而非“农知”的书写中。如沈从文尽管创作了不少知识分子形象,但他笔下的城市人却极少有正面形象,他们的出现不过是为了反衬湘西世界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有论者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仅仅由其小说文本‘客观’地显现出来,并且还在作家小说中‘乡’与‘市’的对立性形象的设置秒回和情感价值取向上特别地显现出来。”[7]沈从文们的乡土情感可以简单概括为“对乡土的爱与对城市的恨”,这既是时代的局限也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借助城乡人物的对比突出恋乡的主题。
“乡土的概念可以视为现代性反思的概念,是以情感的及形象的方式表达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或反动,但它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人们才会把乡土强调到重要的地步,才会试图关怀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市或现代对抗。”[8]如果这种对抗是发生在饱浸现代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上不是更能反证乡村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吗?因此,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人物群逐渐扩大,作家对乡土的赞颂不再单纯依靠农民为核心对象,而是将视野延伸到“农知”形象,并逐渐成为表达恋乡情感的“核武器”。思乡主角从农民到“农知”的转变,是乡土中国转向城市中国的注脚,也是乡土情怀自下而上、由农村人向城里人的扩展。
(二)《浮躁》与《无土时代》:时代弊病的调和
《浮躁》与《人生》都是以主角的记者身份进行“返乡—离乡—返乡”的叙事,但金狗做出了与高加林截然不同的选择。部队复员后金狗扎根农村,带领村民打通了仙游川到白石寨的水上交通,发家致富;站在村民一边抗衡乡村霸主田中正。步入城市后,金狗没有像高加林那样热烈拥抱和贪恋现代文明的成果。他不甘于只做“党和政府的喉舌”,他更愿做农民(因为他自己就是农民出身)的喉舌。为此,他扳倒了弄虚作假的东阳县委书记;不畏权势,大胆地披露“州深有限公司”;在对待作为文化隐喻的女性的态度上,金狗对指代农村的小水和指代城市的石华的态度是积极的,对“不城不乡”的英英则是有意的疏离和拒绝。归来、离去、再归来的金狗,没有高加林的悲苦和绝望,这要归因于金狗对乡村的情感态度和对自身身份的坚强认定。金狗对其乡土身份有着清醒的体认,他“骄傲于其知识者的农民气质,‘乡下人’本色。以‘乡下人’表明文化归属”[9]。有论者认为:“这一体认更夹杂着对自我不乡村不都市又乡村又都市的尴尬身份的难以言说的酸楚,这其中更隐含着对自己无法摆脱乡村故土影子完全蜕变为都市知识分子的无奈和痛苦”。[10]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也不免片面,因为金狗从来就没有将融入城市、抛却农民身份当成自己的最终目的,也更没有为两重身份的交织而困惑。综观整部小说,拥有农民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金狗的情感归属坚定地指向了一点:虽然在城市生活过,但金狗属于农村。
同贾平凹一样,赵本夫也在着重探析“农知”的乡村情感。《无土时代》同时塑造了农民和“农知”两类钟情于土地的人物,这是乡土小说中难得的存在。《无土时代》的文学史意义还在于其第一次明确展示了“农知”对乡土文明的呼唤和对现代性的拒绝。
“石陀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人,展现的是怀乡病和人格分裂……对都市现代文明的反抗和颠覆”[11]。“现代都市人”是石陀的显性身份,“原始有巢氏”是石陀的隐性身份。作为高级出版社总编,他不遗余力地为胸怀“大地情结”但得不到读者认可的柴门出版文集;下雨不打伞就是为了淋雨;办公室里,皮质的沙发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自制的木梯;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了办公室里的“有巢氏”;住在破旧的城中村是因为这里有生活气息;半夜拿着锤子妄图敲碎城市的柏油马路;年复一年的提出“拆除高楼,扒开水泥地,让人脚踏实地,让树木花草自由地生长”的提案等,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进行审视,石陀的行为不免荒诞和可笑。而正是在这荒诞中,我们看到了以石陀为代表的“农知”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表现为对“土地近乎变态的迷恋”,对传统甚至是原始生活方式的依恋,进而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背离和毁坏。
农业文明的记忆深深印在金狗和石陀们的脑海中,乡土中国的集体无意识是他们无法消除的底色(他们压根也没有想过消除),生活场域的变化没有改变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反而更能激发他们自觉地向乡土文明靠拢。从叙事意义上说,“农知”较普通农民更具理性色彩和现代性眼光,以他们为视角切入更能在单一的以农民为书写对象的创作中传达出更为丰富的思想。叙事视角的转变不仅彰显了作家视野的拓展,更表明了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时代心理对作家的影响。
四、纠缠型地之子:复杂心志的展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知”的乡村态度属于非爱即恨的二元对立,似乎除此之外就找不到第三种情感。实际上,纠缠型的情感状态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它游离于恋乡与断根之间很少被人重视,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形成潮流。
乡村情感追求与价值取舍呈现出复杂指向的纠缠型介于断根型和恋乡型之间,以他们为写作对象的文本通常带有忧郁悲伤的情感基调。在启蒙意识消退、无奈感笼罩的背景下,作家在过去/现在、回忆/当下、心理/现实间吟唱出一曲乡土与心灵的挽歌。纠缠型地之子有三个特征:一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城市文化;二是乡土社会保留了他们的童年记忆,使他们对乡村持积极态度,故事往往从他们的回乡开始写起;三是处于对农村现状的不满、无奈(这与断根型的不满与无奈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与无法改变间的纠缠中,随着各种矛盾不断演变,他们对乡村的态度就从一开始的新奇和眷恋慢慢变成了无奈或逃离。对纠缠型地之子的书写主要涉及到“人种退化”“伦理崩塌”“城乡差距过大”和“农村未来发展”等文化学和社会学问题。当发现现实与记忆的乡土存在差距时,恋乡与怨乡的矛盾情感就会产生。
纠缠型的文本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虚构型小说写作,如“恋乡与怨乡两个冲突着情结”[12]的《白狗秋千架》《外省书》等;另一类是流行于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如《中国在梁庄》(梁鸿)、《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王磊光)和《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黄灯)等。两种类型的创作都指向了对社会进程中农村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思考。但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破败不堪现状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当下以“非虚构写作”为载体的“返乡”叙事中。
(一)虚构性文本中的纠缠型
“从90年代开始到2002年前后,贾平凹的文学视点从乡村转向城市,对物质文明所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生命力委顿进行深刻省思”[13]。21世纪,贾平凹的作品不再有20世纪80年代那种对乡土社会的歌唱和未来发展的期盼,转而以一种“文化反思”介入乡土,《高老庄》就是一部反映“农知”纠缠心态的杰作。子路凭借努力成为了大学教授,现代教育和生存场域的变化让子路在情感上更加认同都市文化,同菊娃离婚可以看成他为融入都市所做的努力。与高加林、夏风不同的是,子路对城市的拥抱不是通过“断根”进行的,乡土文化仍然在他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扮演了“诗意的栖居地”的角色。与金狗一样,进可成为城里人,退可成为乡下人的子路一旦回乡,其知识分子性便让位于农民性,不讲卫生和小气等(虽然是陋习但也是农村真实的一面)缺点被唤醒。子路携带着大量的乡村经验进入他想象的乡土,但随着乡村生活的深入,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在文化传统的衰败中、在高老庄的愚昧落后中、在农村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种退化的语境中,子路意识到,记忆中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存在巨大的差距,于是他对乡土的眷恋就转化为一种更为复杂和纠缠的情感。与金狗对自身农民身份的坚定认同不同,子路的根虽然在高老庄,但是他的归属却是模糊的,他始终在知识分子身份与农民身份间挣扎徘徊,在精神属性上他既不属于城市文化,也不属于乡村文化。
生活在城市的“农知”们,试图重新回归乡土却未被接纳,种种矛盾让他们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种身份间拉扯,虽然没有造成“进不去的城和退不回的乡”的处境,但对乡土的爱与恨始终纠缠着他们。《外省书》(张炜)中的史柯发现自己无法融入进京城后退守故乡,但是故乡已无法接纳这个满口京味儿的“外省人”,他在“回与回不去”间纠缠;《人心不古》中的退休校长贺世普一心想把现代法治观念引入乡村,但最终只能是失败的逃离,这是“改变与无法改变”间的纠缠。
(二)“非虚构写作”视野下的纠缠型
乡土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并不是新事物,早在乡土文学诞生的早期,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和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充盈着“留恋和告别”色彩的写作就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但是囿于作品中“农知”色彩的单薄性和时代的局限性,“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直到近年,以“返乡”为叙事模式的“非虚构写作”才成为乡土写作的一大热点。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开始,《出梁庄记》《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等以“现实”和“真实”为核心理念进入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
“非虚构写作”的切入视角是城乡审视。作者和评论家们先后指出“尽管返乡书写呈现的是农村,但农村作为问题呈现,和城市经验提供的视角密不可分”[14],“(返乡写作)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乡村社会发展进程,对城乡二元化结构下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呈现和思考”。[15]“非虚构写作”无一例外都是在对比的框架下开展的:记忆里的乡村是美丽的,是多数人的精神载体,而当下的乡村是苦涩的,因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伤痕累累。“最近几年,我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16]叙述者担心的东西很多,如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成长、文化伦理的失衡和环境的破坏等,虽然这些早已被小说家们反复论述。在完成“向后看”的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性审视后,叙述者们虽然希望通过他们的呼唤让社会“关注他们在现代性转型中的伤痛和眼泪”,进而“在城乡的关系结构中理解乡村的命运,在城市的空间结构、经验烛照中回望乡村”[17],但是作家们仍在“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的悲观情调下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体现了“农知”们既忧虑乡村的现状,又不知如何改变;既呼唤改变,又迷惘无助的爱与无奈的纠缠。
纠缠型地之子的书写既是对乡土的文化学考察,更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下城乡对立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是因为城乡差距和户籍制度等的隐形限制,不存在是因为城乡间的交流和沟通前所未有的便捷。正是在“有和无”的对立中,“纠缠”才能被发现。但是,交通和通讯的便捷并不能消除现代城市人的乡愁,现代人的乡愁也早已不再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的空间距离,而是回不去的心理距离。纠缠心态的书写不是结束了乡愁,而是开创了以全民“怀乡”为表现形式的“现代性乡愁”风潮。
五、结语:农裔知识分子的未来走向
新时代的中国,城乡关系的松动拔出了横跨在城乡间的栅栏,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农村人员向城市的流动。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突破63%,城市人口也已超过了9亿。在涌入城市的群体中,“农知”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尤其在当下,“农知”的数量有了几何级别的增加。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每一次变动都会“促使乡土文学在题材、价值取向和美学形态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18]。城乡关系的变化中,“农知”的身份开始模糊,“农知”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及走向会是怎样的呢?
一种可能是“农知”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向往的生活》等综艺和以“李子柒”为代表的表现乡土内容的自媒体视频的热播,吸引了大量来自城市阶层的关注。“城市土著并没有把城市作为自己乡愁情感中思念的对象,他们想象中的故乡仍然是乡村化的,是儿时记忆中的城市中特有的乡村元素或者说本土文化,而不是相似度极高的高楼大厦、共同设施或者消费行为”[19]。如果我们承认乡愁作为一种指向自然和乡野的情感,是人类血液中自带的文化基因,那么,也许农裔知识分子已然在无声中内化为了城裔知识分子,和全民一齐被卷进以怀念自然和乡野为表现形式的现代性乡愁风潮中了。另一种则截然相反,如《七叶一枝花》中的湘渝、《花腰祭石》中的高山石和《理想照耀中国》中的雷金玉等,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记住乡愁和乡村大有可为的大背景下,在责任意识和恋乡情感的指引下返乡创业,逐渐成为生在农村、学在城市、一生奉献农村的新时代农裔知识分子,甚至可能因此开创新时代返乡文学的创作潮流,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