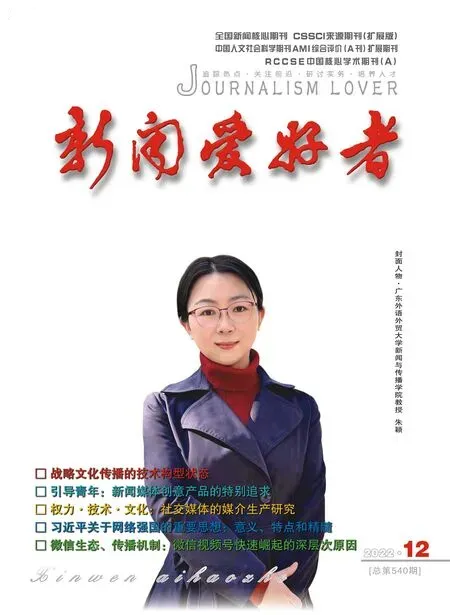东方特色:钱锺书杨绛编辑风格论
□敖慧仙 宋立民
1998 年钱锺书去世后,英国《泰晤士报》报道:“Qian taught at various universities,and worked as an editor on journals including The China Critic,Tsinghua Weekly,and the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从而把“文化昆仑”钱锺书1938 年回国后的文化贡献拓展到教书和编辑方面。
钱锺书的编辑生涯包括中英文刊物《清华周刊》《英国文化丛书》《文学研究》《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报刊和大型丛书,及《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等个人文集等。 而杨绛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老圃遗文辑》《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全集》《钱锺书手稿集 中文笔记》等的编纂,为杨荫杭和钱锺书研究、国学研究、中外文化研究,提供了独树一帜的视角和方法,凝聚着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郭沫若说:“鲁迅先生无心做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1]同理,无心做编辑的钱杨夫妇,在自己“无意间”的编辑生涯里,树起编辑思想的高标。 钱锺书杨绛的编辑活动——无论是编辑古籍、书刊,为他人和自己作序跋, 还是评价他人编选自己的文字所表现出的编辑思想,有以下特点:
一、草成与“文改”的统一
无论后人如何评论, 钱锺书对自己的文字很少满意过。 细考《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的成书过程,他不无“草成”的痕迹。 在1948 年出版的《谈艺录·序补记》中提及:“周振甫、华元龙二君于失字破体,悉心雠正;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底下短书,重劳心力,尤所感愧。 ”[2]在《管锥编·序》中,他再次诚谢:“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3]盖因周振甫任钱锺书学术专著编辑,难度非一般编辑可胜任。 钱锺书学识渊博、贯通中外,其学术专著皆由其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而他的读书笔记素以“自己看懂”为原则,属于“随记”“备忘”之类,记下来的时候并没有一一校对原文。 钱锺书常凭借博闻强识做 “感悟式评点”,在笔记里“草成”,导致著作出版之际,需要责编一一核对原文,工作量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为此,钱氏学术专著的责编还需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解析必要的技术问题。 钱锺书反复感谢周振甫先生,对于自己当初未打算出版的“草成”之作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然而,当随感笔记需变成著作出版,钱锺书立马变成咬文嚼字的老学究。 钱锺书戏称自己为 “文改公”,他对作品里任何不满意的细节或错误皆零容忍。比照他不少著作在各个时期的版本,“他大大小小做的修改都可以让后人写本版本勘定的书出来”。[4]为此,张明亮对《围城》的初刊本、晨光各版本、新版各次印刷本,做了反复的对校比,他辑录出钱锺书全部异动之处,即经钱锺书修改过的文字共计512 条,从而出版了学术专著《钱锺书修改〈围城〉》。 钱锺书秉持一以贯之的“需多改,莫过改”的严谨态度,即使已出版的著作亦不断修订,补订内容亦可成书,如《管锥编》第五册和《谈艺录》下编。
而作为编辑的杨绛, 亦始终坚持一丝不苟的信念。 八十余岁,她不满意已完成的20 章小说,悉数删去。 九十八岁开始创作最后一部小说 《洗澡之后》,103 岁高龄出版,其间几易其稿和书名。 责编胡真才回忆,“《洗澡之后》单行本出版后,先生照样细看一遍,并勾画出了十多处她做了修改的字句,如去掉了第二部第四章结尾的最后一整段文字,将‘吃了一顿夜饭’改为‘吃了一顿晚饭’等;此外,她还纠正了一个错字,将‘他的脸都生光了’中的错字‘生’更正为‘丢’”[5]。 杨绛一如既往认真严谨的态度让人钦敬。103 岁之际《杨绛全集》出版,她不厌其烦地修订,即便是备受好评的文章,她也一丝不苟地从头检视,细微到“大娘‘呜——噜噜噜噜噜’……”(《干校六记》)唤狗的方式,杨绛都反复斟酌,更改为“大娘‘狗’一声喊……”。 《杨绛文集》中,喜剧《弄真成假》多次错印为《弄假成真》,《杨绛全集》出版时亦一一修正,诸多细节修订比比皆是。
文本的编辑需细致而严谨, 求真务实为一切之首。 钱锺书与杨绛坚持草成与“文改”统一的编辑理念,从而保证了作品的优质出版。
二、坚辞与辑选的统一
钱锺书杨绛夫妇性情淡泊、专心著述,他们既不愿意扬名立万,也不提倡别人研究他们的作品。 无独有偶,他们的编辑理念相互渗透,具有不趋时不媚俗的独立理念和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
钱锺书对个人著作出版或重版极其严苛。 《谈艺录》初版于1948 年,是钱锺书以札记形式写成的一部文学评论。 他曾对朋友说,“此余三十五岁时作,少年气盛,语多鲁莽,故不愿重印”。 直到1984 年,中华书局才得以出版《谈艺录》(增订本),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
钱锺书在“增订本”引言中说:“暨乎《管锥编》问世,中华数接读者来函,以《谈艺录》罕购为言,因申前请。 固辞不获,乃稍删润原书,存为上编,而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 ”[6]钱锺书视个人著作的出版或再版为细水长流的工作,精雕细琢严谨认真。 知夫莫若妻,杨绛曾回忆,钱锺书“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 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7]因此,钱锺书的作品向来只是单独出版,没有合成所谓意义上的《集》,这是钱锺书对出版文集的见解和立场,他有自己严格的准则。
无疑, 钱锺书的编辑理念对杨绛的编辑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长期的学术和婚姻生活,钱杨夫妇的学术理念亦得以互相影响和渗透。2004 年出版《杨绛文集》时,她制定了“四删一留”标准:“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 文章扬人之恶,也删。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 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8]编辑综合涵养的高低和编辑理念的差异, 决定着编辑活动能否顺利进行,也决定着作品品质的优劣。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她(指杨绛)跨东西方两种文明之上,角色多重且各有建树,是许多后辈学人无法企及的”。[9]钱锺书杨绛夫妇皆如此。
三、勘误与借力的统一
由于手抄、刻板印刷等历史原因,古书的讹误相当严重。 勘误成为古籍编辑的重中之重。
与勘误者发现大错“深恶痛绝”不同,钱锺书一边指出古籍的明显错误——尤其是平素并不为人注意的校点错误,一边充分肯定“始作俑者”不可取代的成绩。 这种“宽大为怀”的编辑态度,来自于学养的深厚,也实在是仅限于古籍的编辑,是后来者很难克绍箕裘的。 钱锺书举僧显忠的诗被名家刘辰翁等名家“判”给了王安石、宋代别集“从前面的部分钞得多,从后面的部分钞得很草率”的通病、《宋诗抄》的“许多小序也引人误会”、《宋诗纪事》 开错了书名又删改原诗等,批评得十分中肯。 此后总结说:“我们未必可以轻心大意,完全信任吴之振、厉鹗等人的正确和周密,一概不再去看他们看过的书。 不过,没有他们的著作,我们的研究就要困难得多。 不说别的,他们至少开出了一张宋代诗人的详细名单, 指示了无数探讨的线索,这就省掉我们不少心力,值得我们深深感谢。 ”[10]
年过八旬,杨绛通过日本学者中岛壁、小野信而和国内学者范旭仑复印的七十年前父亲散见旧报刊的文字,编辑出版了45 万字的《老圃遗文辑》,编辑过程之艰苦难以备述。 由于旧报纸上字迹模糊,誊清煞费工夫……苦的是模糊的芝麻点儿细字, 太小看不清,放大了更难认;一面查书,一面对着模糊的芝麻点儿反复比拟,仔细琢磨,大非易事。[11]且杨荫杭古典功底深厚,深谙训诂小学,熟悉多国语言,往往下笔酣畅淋漓,引经据典,易造成标点的谬误。 她力求准确,根据底稿逐字辨证,并与钱锺书遍查书刊解除疑难,才最终辑录出版了《老圃遗文辑》,从而再现20 世纪20 年代的社会风貌和老圃先生的文学风采,从中可窥杨绛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勘误辨别的编辑能力。
而杨绛在编辑《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时,由于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遇到瓶颈。 而恰好翻译《围城》的德国学者莫芝宜佳博士来华,杨绛就借助她的力量完成178 册、3.4 万多页外文笔记的编排。20 世纪80 年代,计算机在中国尚未盛行,而钱锺书远见卓识, 亲自指导并参与筹建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室, 此举对古籍数据库建设和数字人文研究意义重大。 同时他借助栾贵明等年轻助手的力量,运用计算机的文献检索功能,完成《〈宋诗纪事〉补正》等的庞大编排工作。
钱锺书和杨绛用自己的编辑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称职的编辑,一方面需要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提炼精华; 另一方面更有必要借助旁人之力求事半功倍,发现他人的长处而用之,古今编辑同理。
四、钩沉与发微的统一
作为编辑的钱锺书,是钩沉与发微的专家。 1962年《文学评论》首期的《通感》一文,之所以在学术界“吹皱一池春水”,一大原因就是其探幽发微的功夫。文章从“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切入,步步深入,最终振聋发聩。 这种独特的专业态度和方法论运用在编辑实务上,就是于精微处见真知。 例如他为晚清文献学家谭献的《复堂日记续录》作序,不仅通读21册日记,而且从曾文正、翁文恭,到李莼客、王壬秋的日记特点,到谭氏虚怀若谷“多褒少贬,微词申旨”的特点,骈散齐下,概括简明扼要,堪为后世编辑楷模。
“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六十三载相濡以沫的人生历程,使得杨绛十分熟悉《围城》《管锥编》等著作的来源出处、成书过程与内涵。杨绛为夫君撰写序跋,不扬不抑,不卑不亢,只是据事纪实,客观点评,钱锺书读后亦承认没有失真。 她陆续写下饱含深情的文字——《记钱锺书与〈围城〉》《〈宋诗纪事〉补正序》《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钱锺书手稿集〉序》等文字,据实向读者披露钱锺书著作的成书背景,也为学术界研究钱锺书提供第一手材料。 毋庸置疑,无人能及杨绛资历为钱锺书作传并任其著作编辑。杨绛作为钱锺书著作的编辑,其“钩沉”意识倍加鲜明。因此,杨绛作为编辑的一大特色, 就是赓续了钱锺书的钩沉与发微的编辑理念。 “钱锺书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 杨绛如许评价,与其是在赞许丈夫,不如说作为编辑的杨绛在“吃透作者”。
钱锺书常常翻阅笔记,把精彩片段与杨绛分享,当初的“著述分享”和“编前会”不经意间成为杨绛编辑工作的依据。 夫君对于中外典籍的钩沉与妻子对于往昔生活的回忆融为一体, 是所有钱氏著作的编辑们不可奢望的特权。 因此,无论是一般人认为“艰涩难懂” 的钱锺书手稿, 还是父亲遗落旧报刊的文字,杨绛的编排常常似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杨绛编辑夫君手稿的全过程, 彰显钱锺书的心迹心影和学术思想。 而作为七万余页“天书”般的钱锺书手稿的编辑,杨绛无疑历经艰难险阻。 其一,钱锺书阅读面极广,且通晓多门外语,他的手稿常古今中外思想交互参考引证,极难把握。 其二,钱锺书熟读深思历朝典籍, 文化昆仑的渊博在学术细分时代让人惊叹。 但钱锺书手稿往往率性而成,从浩渺的学术笔记中梳理出目录,何其困难。 其三,数百册手稿颠沛流离,几经劫后重生,有些已难以辨析。 再者,杨绛编辑手稿之际已近九旬高龄, 艰巨的任务加之年老体衰使其备受考验和折磨。 但如她引用16 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的名言:“欣赏艺术, 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对困难的克服,方能成就艺术的高度。 杨绛深知钱锺书手稿的学术价值,也本着对挚爱生命的虔诚守护,终能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完成宏大的手稿编辑。
可见,在个人文集和亲人遗著的编辑出版中,钱杨夫妇统筹全局的综合性特色与钩沉发微的国学特色相得益彰。
总之, 普通的编辑学原理已经无法涵盖钱杨夫妇的编辑活动, 他们的编辑理念像章鱼的触角伸进了诗学、语言学、古文字学、古籍整理学、训诂学等。他们用自己的编辑实践, 证明了优秀的中西比较文化的编辑,首先需要的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她可以暂时不顾忌面面俱到的“系统理论”,但是一定要有对于局部与细节的真知灼见——从而开启一个 “大文化编辑”或者“东方编辑文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