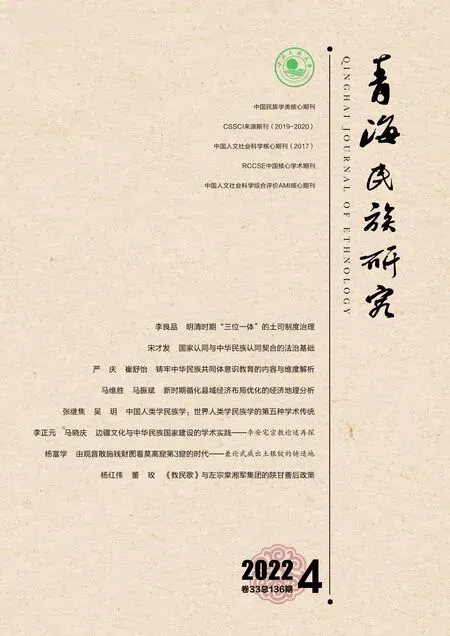长征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三维方式研究
詹全友 张文灿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一般而言,都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行为实践先于概念,尽管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这一名称,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这项事业却是与19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同时起步的”[1]。从发生学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已开始。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情(情感)→意(意志)→行(行为)受知(认知)的支配,而准确且全面的认知或理性认知,是理性情感→理性意志→理性行为的先导。长征时期,鉴于双方(红军将士与党政工作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众)相互了解极少甚至有误解的实际情况,用何种方式解决双方尤其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理性认知、进而形成理性情感→理性意志→理性行为的问题,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棘手问题。于此,中国共产党努力克服一切困难,采取言传身教而以身教为主、“漫灌”和“滴灌”而以“滴灌”宣传教育为主、纵向和横向而以横向宣传教育为主等三维方法和形式,对内对外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主要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红军教育、社会教育予以呈现),推进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走深走实。大多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红军,或主动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予以支持,为党和红军赢得长征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以后有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和新时代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提供重要借鉴。
一、言传与身教而以身教为主
言传身教,即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主体通过言语和行为示范开展宣传教育,既强调口头传授、文字和图画宣传,又注重以身作则、时时处处为宣传教育客体着想。言传与身教遵循了感官协同规律,两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并不是主次不分,在言传与身教中,身教无疑显得更为重要。身教更生动、直观,不受语言、文字、时间、空间、客体素养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更方便语言不通、不识字的人理解与效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政治实践中逐步成长为具有主导性力量的政治组织,已形成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进而体现为动员型政治的实践面向。[2]长征时期,“群众最主要的是要观其行。红军的实际行动是最好的宣传。所以,红军战士在长征中,处处向群众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按规定办事,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还处处为群众谋利益”[3]。因此,既需言传,更要身教。只有为各族群众谋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获得他们的真心拥护与积极支持。
一是发布训令、指示、通令、布告进行宣传教育。这也是党和红军使用的主要宣传教育方式。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文件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于1934年11月29日发布的《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原件月份不详,从内容判断当在6月左右)19日出台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等。1936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还发布《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对回民教育进行了具体部署:如“红军进到回民区域,必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另附),并在部队中作广泛的解释,各级政治机关首先必须经常检查与督促执行,如有违犯应给以纪律制裁”。“在打汉人的土豪中,要注意没收的主要部分要分发给当地的不分汉回的穷苦群众”,公平公正地对待各族穷苦大众。[4]
二是党和红军领导人亲自进行宣传教育。这是长征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一大特色。如1935年1月12日毛泽东同朱德等领导参加遵义全县民众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述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5]。党和红军领导人采取的这种方式,既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也更易得到各族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三是通过《红星》报进行广泛宣传。《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红星》报针对的对象是广大红军将士,先后发表《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第14期)、《实现总政治部提出的四大号召》(第17期)等一系列文章,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紧密团结各族群众,为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统一思想认识起了重大作用。
身教而言。“群众常常不听我们所说的好听的话,他们首先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6]。长征时期,党和红军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不仅言行一致,而且“行”比“说”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毛泽东、朱德更是以身作则,为广大红军将士树立了榜样。1934年12月下旬,红军从贵州黎平出发向黄平进军途中,毛泽东在村旁见一位老年妇女因冻饿而倒卧路旁,当得知为当地农妇时,立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又从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还让警卫员拿出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并送给她。老妇连连道谢。[7]1936年4月初,朱德一到四川炉霍,首先派指战员会同爱国上层人士带领翻译分头上山寻找、规劝藏胞回家安居。群众回来后,又立即赈济贫困群众600余户,治病疗伤达2000人。其次,为抢农时,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带头种地。没有种子就拿红军紧缺的口粮作种子,没有耕牛红军就自己拉犁,没有工具就用红军的小铁铲。耕地近4万亩,并为群众看管、饲养牲畜上万头。[8]得到当地藏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
在回答“红2、6军团的政治工作干部是怎样发挥政治工作威力”的问题时,长征中一直担任红2军团第6师政治委员的廖汉生的话颇具代表性,他总结为“做三个模范”:“第一条,打仗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条,多扩充些红军战士,尽量少损失,少跑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条,严守纪律,不违犯政策,即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9]
广大红军将士即使战事再紧张、条件再艰苦,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即便寒冬腊月,大多数部队都住在屋檐下或露宿街头、路旁,避免惊扰群众。即使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抢光装备、衣服甚至牺牲,也绝不还手。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少数民族群众。1934年11月,红军路过湖南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家中,见其家徒四壁,临走时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她。徐解秀感动地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党,并把党当成自己人。[10]
与此同时,红军各纪律检查小组还经常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如损坏群众的东西是否赔付、购买群众的东西是否付钱、部队从宿营的村庄走后坚持上门板没有和捆稻草没有等。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绝不损害群众的任何利益。云贵川地区广泛流传着一首“赔锅”的诗歌,便是对红军纪律严明的一个真实写照。大意是,“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世凯’(银元),赔你一只好铁锅”。红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云贵川等省的群众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红军真是穷人的大恩人。[11]
二、“漫灌”和“滴灌”而以“滴灌”宣传教育为主
“漫灌”宣传教育重“面”(所有合法的策略、所有人),“滴灌”宣传教育重“点”(有效策略、客体具体)。两种形式各有优劣,如果一起使用、双管齐下,可以起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之功效。长征时期,党和红军的“漫灌”宣传教育,就是使用能够想到的所有合法策略对所有人进行宣传教育,力争广种多收、厚收。“滴灌”宣传教育就是精准施策,针对不同的民族(如瑶族、苗族、回族、蒙古族等)、群体(如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等)、个体(如羌族土司安登榜、彝族家支头人小叶丹、藏人领袖格达活佛等)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力倡功效最大化。坚持“漫灌”和“滴灌”相结合而以“滴灌”宣传教育为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照顾“面”又更看重“点”的理念,也是推进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入行的关键一招。
(一)“漫灌”宣传教育
“漫灌”宣传教育主要特点有四:使用能够想到的所有合法策略、客体是所有人、针对宣传教育客体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以及成本极其低廉,甚至没有成本。如写标语,只要有石灰或锅烟即可。“漫灌”教育,一般在两种情况使用较多,一是宣传教育客体由于听信谣言以及“污名化”宣传而躲避山林,无法找到宣传教育客体。二是由于战事频繁、停留时间极短,没有时间开展“滴灌”宣传教育。“漫灌”宣传教育的方法主要有写(贴)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组织联欢会等。
写(贴)标语、布告时,凡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材料、载体均得到充分利用。早在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就非常看重标语的宣传教育价值,不仅把标语列为第一个宣传教育方式,而且对其内容、宣传技术、书写方式等作出严格规定,逐步使其科学化、规范化。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第5期刊登的《健全连队中的宣传工作》中,就大力加强连队的群众宣传工作,并积极倡导开展书写标语的竞赛活动,“把我们的一切标语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斗争”。同时还提出了书写标语的具体数量、材料、位置,凡是会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l—10条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笔、石灰、石块书写”,墙壁都要写满标语。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之前,就提前准备了针对广西的宣传标语。红三军团进入后,宣传队立即在灌阳文市镇唐济荣家外墙上书写12条标语。迄今,在桂北发现红军留下的标语超过100条。主要内容有:“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红军是为着工农自己利益求解放而打仗!”“红军绝对保护瑶民!”[12]红军全部进入民族地区后,在各地都留下许多书写、錾刻、张贴、散发的标语、布告。书写和錾刻的标语都是就地取材,如书写标语口号时,使用材料有锅烟、红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垩土等。书写和錾刻标语选择的处所,在农区村镇多是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牌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均属醒目之处。为使标语留存时间长,红四方面军各军、师还成立錾字队,专门从事革命标语的书写与錾刻工作。在森林地带,红军还因势利导地创造了“树标”,即选择路旁的大树,在树干上用刀剥下一块树皮,再将标语口号刻、写于树干。这种“树标”在松潘县的毛儿盖、茂县的松坪沟和黑水的小黑水最为多见,至今仍然可见。在牧区草地,红军则使用小石块在草地上镶嵌成标语。在靠近白区一带,凡在河道较宽、水流量大的地方,如汶川等地,红军就用木板写上标语、文告投入岷江,木板顺流漂下,借此进行宣传教育。[13]
长征时期,召开群众大会是党和红军必用的宣传教育方式。红军每攻克一地,都会召开群众大会,对各族群众进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宣传教育。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不受时间、地点、人员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且开会的时间可长可短、参与人数可多可少。红二方面军宣传员陈靖回忆道:宣传员“要调查和没收土豪财物,召开群众大会和扩大红军。这三件事是每天必须做,而且必须做出成果来的”[14]。
如果说开会是一种由上到下的单向宣传教育方法,那么组织联欢会则是一种双向快乐互动的形式。1935年5月,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颁布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指出:“多多组织少数民族劳苦群众和红色战士与汉族工农的联欢大会。”[15]在军民联欢会中,常常演出歌舞、川剧、活报剧等,教育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其产生的效果,斯诺略带夸张地评价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16]
(二)“滴灌”宣传教育
“滴灌”宣传教育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讲究针对性,即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客体存在的特殊性问题采取具体对策,使其逐渐消除疑惧心理,愿意接受、主动接受、心情愉悦的接受,明白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亲人。二是注重实效性,即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做实做细,使其产生最佳效果。
“滴灌”宣传教育策略之一是尽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表演形式等,以提升亲和力。如1935年5月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颁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要求“准备大批的宣传品,顶好翻译成回藏蒙人的文字”[17]。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文件,也尽量采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便于少数民族阅读。通过学习、吸纳、借鉴和创新,红军创作出许多深受少数民族群众喜欢的舞蹈形式,密切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滴灌”宣传教育策略之二是谈话、座谈等。1935年5月19日,在四川西昌县锅盖梁(今西宁)地区,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临行前,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仅不会打我们,反而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18]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途经宁夏兴隆镇回族聚居村单家集,当晚就在清真寺北厢房向阿訇马德海阐明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以及尊重回族习俗等政策,留下了著名的革命佳话——“单家集夜话”。
“滴灌”宣传教育策略之三是极其注意运用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策略引导各族群众提高认识。1936年2月初,红二军团第六师突破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袭占黔西县城。几天后,在黔西东北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土豪劣绅的罪恶,由没收委员会没收其不义之财,当场分发给“干人”(那里的贫苦百姓被形象称为“干人”),有的人一时不敢要,就派战士在夜晚把粮食、衣物送上门去,启发他们:“天底下还是穷人多,老财少,你看看哪个力量大?”鼓起他们的斗争勇气。各伙食单位还用没收来的钱粮办起酒席,请“干人”们免费分享胜利果实。宣传队则搭起台子,演活报剧,唱花鼓,唱山歌。经过这些形式简单、内容实际的宣传教育,“干人”们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组织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在此基础上,又启发他们: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可他们上面还有乡长、区长、县长,还有一级一级的衙门,直到那个全国最大的衙门——国民党反动政府;这里的“干人”翻身了,可其他地方的“干人”还在受苦,全国还有千千万万的“干人”……就这样,由打倒某个土豪劣绅联系到要打倒整个反动统治阶级,由夺取某个战斗的胜利联系到要夺取全国的胜利,由建立某个苏维埃政权联系到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大同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他们的革命理想就逐步树立起来了。[19]使少数民族群众从报家仇、报族恨,逐步认识到报国恨才是最重要的;从争取个人解放、家庭解放、本民族解放,逐步认识到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全国人民解放才是最重要的;从观望徘徊、各自为战到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各个少数民族逐渐认识到,民族团结不仅是各个少数民族自身家支、本民族内部的团结,也不仅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三、纵向和横向而以横向宣传教育为主
纵向宣传教育,或称垂直宣传教育,即从上到下宣传教育,是红军内部宣传教育的一种形式(党和红军领导人→党政工作者和红军其他将士)。横向宣传教育,或称水平宣传教育,以党和红军这个宣传教育主体为主,也高度重视其他主体的作用,形成两个多元多向、各有优势的宣传教育链:一是党和红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众,这是宣传教育主客体的直接对接。二是党和红军→通司(翻译)→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少数民族群众,这是宣传教育主客体的间接对接。纵向宣传教育与横向宣传教育相结合,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相互衔接的、自动延伸的、开放的宣传教育链,以汇聚各方积极力量、形成尽可能多的主体一起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合力。同时,以横向宣传教育为主,突出了宣传教育客体的指向性、重要性、目的性,对于推进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入脑入心入行具有重要作用。
(一)纵向宣传教育
长征时期,由于党和红军是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民族地区,许多红军将士对少数民族情况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和省委其他同志进入川西北后,就感到对“少数民族情况是无知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20]。因此,首要任务是自己努力掌握和学习少数民族知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中国共产党不仅第一次提出要全面开展少数民族情况调查,而且开展了许多扎实的调研工作。《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就是在全面弄清苗族、瑶族情况的基础上完成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再次强调:“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这个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等。”[21]为此,每到一个地方之前,都会派出侦察员对该地各个方面的情况如人员构成、风俗习惯等进行彻底摸底,以便准确把握当地的情况,为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党中央还号召广大红军将士努力学习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如到达甘肃、宁夏回族聚居区时,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于1936年5月24日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应以团为单位成立回民工作团,研究回民的生活习惯及对回民的政策与方法,并须学会几句回语,每个战斗员至少使之见回民能说撒哇布(再见谢谢),使回民群众知道在红军中有很多的回民,更加拥护红军”[22]。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星》报于1935年7月10日刊登《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的社论就强调:“我们部队中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的上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动的来参加这个工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口号是: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更是首次指出:“在许多其他问题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23]打铁尚需自身硬,只有每个党政工作者和全体红军将士首先学好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才不会沦为空谈、流于形式。
在实践中,党和红军内部自上而下宣传教育的顺序是:党和红军领导人→党政工作者和红军其他将士。1934年12月上旬在强过湘江后,毛泽东就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入苗族区,苗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汉民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进入苗族区以后,又给警卫人员讲党的民族政策”[24]。1936年4月初,朱德一到四川炉霍,不仅立即给红军指战员作出四项纪律规定,而且要求大家教育红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见土地无人耕种,第二天就召开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他指出,“我们帮助藏胞种好地,就是做了一件实际的群众工作。我们虽然不久就要离开这里,但是我们要把党的影响、红军的影响留下,让它像种籽一样在藏族同胞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25]。在毛泽东和朱德影响下,党和红军从上到下,每个人既是宣传教育的客体(被育),又是宣传教育的主体(育人),初步形成了全员育人的格局。
(二)横向宣传教育
一是党和红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众。1934年11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发布的《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指出:“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须不疲倦的解释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众的敌人,瑶民与中国劳苦民众是兄弟,所以联合起来协力同心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而奋斗。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瑶民等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26]从中指出瑶族劳苦群众与汉族劳苦群众是兄弟、有共同的敌人。还首次明确提出:“在瑶民中间共产主义的宣传是必要的,共产党在瑶民中间应该不断的吸收最觉悟的与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在瑶民中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且在一切实际斗争中,以共产主义的教育,教育所有的瑶民群众,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瑶民的民众得到最后的解放!”[27]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指出:“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动员他们帮助红军,反对刘文辉及当地的汉族统治者。 ”[28]
为了贯彻落实上述政策精神,红军进入民族地区后,不仅全体将士都负有宣传教育工作的使命,而且还设有专门的宣传组织和机构,从制度上予以保证。师、军以上的政治部都设有宣传部,团政治处设有宣传科。师以上单位设有宣传队甚至剧团,军以上政治部还设有地方工作部和地方工作队。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上游地区之前,就着手组织调查研究川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情况。“军、师政治部之下增设少数民族委员会,由政治部主任、组织科长、党委书记、地方工作队的人共同组成,吸收当地先进的回、羌等族战士参加。师、团政治处之下增设少数民族组,由政治处主任、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共同组成”[29]。他们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各种途径,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
二是党和红军→通司→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少数民族群众。基本程序是:党和红军首先做好通司的工作,然后让其说服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再通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做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即采取“熟人的熟人”拓展方法。在实践中还存在两种具体情况:党和红军→通司→少数民族群众;党和红军→通晓汉语或汉文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少数民族群众。
争取并借助通司进行宣传教育。进入民族地区后,红军除努力学习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对通司的作用十分重视。1935年5月上旬,有关部门就指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干部必读》西北特刊第二期,1935年5月5日出版):“为着将我们的政纲、政策深入回、番民群众中,首先要将‘通司’(能翻译回、番文字语言的人)请来,我们要大大优待多给工资(照优待专门家条例),使他们好好的正确的为我们翻译(如果没有翻译,彼此说话都不懂,工作不能进行)。”因此,红军每到一地都努力物色一些人员作通司,这些“通司大多是本地、本民族中通晓汉语或汉文的人,也有少数外地久留民族地区,通晓藏语、羌语的汉人。他们熟悉当地的自然、地理,人文等各方面情况,既可以担任通司又可以充当向导,在协助红军进行群众宣传动员等工作中,发挥了特定的重要作用”[30]。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进入川西以后,选聘了两名通司(一名藏族喇嘛当藏文翻译、一名回族阿訇当回文翻译),主要负责翻译党和红军的布告、捷报等工作,以便藏族、回族群众及时了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据刘瑞龙回忆,他们和红军关系非常融洽,工作积极、勤奋,很快成了宣传工作的积极分子,为省委开展宣传做了大量工作。[31]
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借助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红军提倡民族平等团结,也包含争取开明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因此,在严厉打击反动的少数民族上层时,也积极争取进步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通过他们的威望去影响和教育少数民族群众。《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在首次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苗族、瑶族上层阶层特点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待苗族、瑶族上层人士的政策:一是“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二是“我们并不放弃在一切实际的斗争中批评他们的动摇犹豫与不坚决,推动更左的革命分子走上领导的地位,团结他们在我们的周围,并从他们中间吸收共产党党员”。[32]这不仅成为长征时期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基本方针,而且也对后来相关政策的制订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征时期,红军在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效显著。1935年5月,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并帮助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鸡支队。在红军帮助下,丹巴县巴旺村头人马骏(藏族,藏名:麻孜·阿布)成立藏民独立师。时任藏民独立师副师长的金世柏在《忆红军藏民独立师》写道:“在同马师长朝夕相处中,我们彼此尊重,感情十分融洽。马师长为人诚恳朴实,很重感情,深受战士们的拥戴。我曾跟他一道多次下连队检查工作。每到一地,他都给部队讲:要拥护共产党,听红军的话,要遵守纪律。话虽那么几句,但很起作用。”[33]1936年,红三十军所部进驻甘孜县白利土司官寨时,白利土司家寺庙主持活佛格达见红军秋毫无犯、保护寺庙和群众利益,感慨地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的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34]格达活佛更加坚定了永远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并于1950年为西藏和平解放舍命奔波,谱写了可歌可泣、民族大团结的感人篇章。
四、结 语
科学知识中,新术语产生的一般规律是先有其实其义,而后才以专名附之。长征时期,虽然尚未出现“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概念,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在民族地区首次大规模的实践。通过采取主次兼顾的言传身教、“漫灌”+“滴灌”、纵向+横向等三维宣传教育方式,既保证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的有效性,也充分调动了每个主客体自我教育的积极性;既为党和红军赢得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和促进了党的民族理论的形成,也为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
首先,长征时期,尽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的环境极其恶劣,但中国共产党仍然秉承初心使命的理念,紧紧围绕长征时期的总目标总任务,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尽最大努力挤出时间,在对民族地区进行较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实施三维宣传教育方式。这种立体宣传教育方式的显著特点是,既兼顾“面”(社会教育),更关注“点”(干部教育、党员教育、红军教育),不留任何死角。以点带面,以面促点,主次分明,统筹兼顾,共同达成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目的。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往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方式的继承,更是创新。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践,除继续努力提供越来越优良的物质环境和精神食粮外,也应当注意各种方式的兼容性、互补性、实效性。坚持点面结合、相互促进,大力弘扬长征精神,进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汇聚磅礴力量。
其次,在言传+身教而以后者为主的宣传教育中,党和红军通过言语图文和行为示范等方式,让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众通过听言、观行,具体可感地认识到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意义,传颂着“半条被子”“赔锅”等佳话。新时代,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践中,我们应当继续既要注意言传,也更需关注身教,惟其如此,才能激发各族群众参与其中的自觉性、主动性。
再次,在“漫灌”+“滴灌”而以后者为主的宣传教育中,党和红军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出发,以“漫灌”解决普遍性问题,以“滴灌”解决特殊性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践,也应当继续坚持“漫灌”+“滴灌”而以后者为主的宣传教育,既不能偏废一个,也不能主次不分。就学生而言,要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家庭等情况产生的问题,既要采取“漫灌”方式保证全覆盖,更要采取“滴灌”的方式精准施策,把解决普遍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实践效果。
最后,在纵向+横向而以后者为主的宣传教育中,党和红军充分把握联系观、系统观。一方面,通过纵向宣传教育联系党和红军领导人、党政工作者和红军其他将士,通过横向宣传教育联系各种各样的客体;另一方面,以横向宣传教育为主,突出宣传教育客体的特殊性、目的性。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践,同样应当既需注意纵向宣传教育,也更要注重横向宣传教育。只有首先做细做扎实这两个宣传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践才有底气、正气,才能既有效保证纵向宣传教育的效果,也是做好做细做扎实横向宣传教育的前提条件。
——宣教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