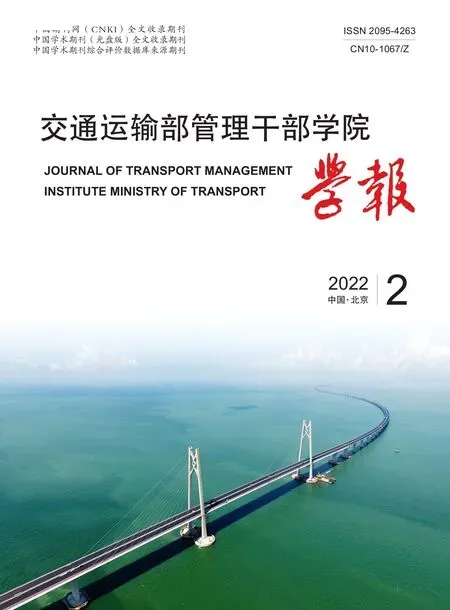信息形式主义与智能官僚主义的治理方略探析
张 桢
(中共开封市委党校,河南 开封 475001)
随着5G时代的全面到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数字治理应运而生并改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式和逻辑。然而,随着各种政务新平台和政务APP的泛滥,信息技术的正面效应被不断消解,“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在线上悄然出现,成为一种隐形的线上“四风”。在新形势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哪些新变种?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持续解决新型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笔者将结合当下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并提出解决基层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的治理路径,以求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信息形式主义与智能官僚主义的“新变种”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为社会治理的高质量发展赋能。“两微一端”虽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标配”,但由此形成的全天候、留痕打卡的治理模式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基层干部每天紧盯各个“微信工作群”,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办公群已成为“晒调研走访里程”“晒摆拍”“晒加班”的“秀场”,年终突击的学习培训让基层干部逐渐形成“打卡第一,留痕走人”的形式主义工作作风。
(一)“痕迹体”
随着政务信息化、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的新型形式主义。各种手机客户端和微信群成了基层部门随时随地布置、开展、汇报工作的重要载体,“开不完的会”变成了“刷不完的屏”。工作落实变成了微信群里的“@所有人”,过去“面对面”变成了现在的“头像对头像”。有的地方过分强调痕迹化管理,要求图文并茂地全过程记录工作,“打卡”“留痕”已经日渐成为工作中的必要环节。“精致留痕”成为应付各种检查的“捷径”和“妙招”;每日打卡、“列队”回复、事事留痕的情况已较为普遍,甚至出现开一次会更换多次电子屏,做一次现场调研要更换几次衣服的现象。驻村干部要求在微信群“发送位置”“共享实时位置”,利用位置软件将自己的位置固定在村里。年终考核前,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文字资料,疲于在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留痕”。“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往往一人应对多个部门,技术更新不仅没有化繁为简,反而消耗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成为新的负担。上级领导滥用“打卡”“留痕”代替管理。“千条线”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蜻蜓点水、敷衍了事在所难免,严重损伤了上下级之间的信任。
(二)“网红体”
随着数字治理的普及,熟练掌握多种网络媒体的应用技能已经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媒介素养。利用各种新媒体为实际工作进行宣传和造势,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手段。然而,个别党员干部将网络作为秀场,甚至利用“直播带货”作秀,刷“政绩”,以此显示自己的“亲民”作风;员工充当网络水军为领导集体点赞,齐呼“领导好帅”。表面上是网红经济,实际上却是利用新媒体制造“政绩泡沫”。有的地方为了显示领导“直播带货”的网红效应,甚至搞“虚假下单”、重复签约,只顾流量、销量乐观,背后却用数据造假来掩盖“亏本赚吆喝”的真相。这种背离初心、盲目跟风的现象披上新的科技外衣后变成典型的信息形式主义,严重损害政治生态,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让原本尚未解决的问题变得“网上加难”。
(三)“僵尸体”
数字治理的初衷是让社会治理更高效、更快捷,然而当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联姻后就变成懒政、怠政。“技术赋能”变成了“技术负能”。在一些政府网站或公众号上,群众要么无法反映问题,要么反映问题无人回应。有些部门利用自动回复软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简单敷衍。让政务服务网站或公众号成为一种“僵尸”式存在。另外,个别服务部门变成了“电子衙门”,打着数字化、信息化的旗号,要求所有服务内容必须“网络”申报,让很多不会使用网络或者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办事无“门”。一些正常办理的业务,借口网络或系统问题不办理,“管卡压”变成了“推拖绕”。部分政务平台滞留在走形式阶段,上线时间超过1年,政府部门依旧回答“还在建设,无法正常使用”,让数字治理改革变成互联网治理面子工程。
(四)“碎片体”
数字治理本应是整体性治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治理形式,强调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重新整合政府职能,打造一站式、无缝隙的公共服务体系。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形成功能碎片化、任务碎片化、管理碎片化的“碎片体”。各政务APP之间缺乏统筹规划,一部手机甚至装有十几个政务应用平台,涉及党建、城管、扫黑除恶、基层治理等多项内容。各平台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不能统一和共享数据,导致公众需要在多个APP上办理类似业务,造成一线工作人员在多个平台重复录入相同数据、重复处理相同数据和后台程序,分析人员无法掌握全面数据。而各类APP、工作群、微信公众号的签到打卡、分享点赞、下载量、浏览量、推送文章量又成为基层政府对工作人员的重要考核指标,增加基层工作人员负担,大大降低基层工作的执行力。
二、信息形式主义与智能官僚主义的危害
(一)服务公众变成“面子工程”
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改进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公众满意度是数字治理改革的初衷。但是在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的蔓延下,真作为、真办事变成了“轰轰烈烈走过场”“干得好不如晒得好”的面子工程,过度追求高大上的噱头和数字化的官场作秀。这种“脱实向虚”和“庸政懒政”的作风虚耗了信息办公平台的投入,程序繁琐、内容繁多的数据报表和各类考核化简为繁,造成行政资源浪费。领导遥控指挥基层干部,基层干部隔空开展工作,大量的“群上安排、群上指导、群上培训”让基层干部成了“云上干部”“牵线木偶”。虽然布置工作的速度提高了,但缺少与群众面对面的温度,造成民情不明、民情不查,对群众的呼声失去了回应能力。
(二)公权力“内卷”
“内卷”是一种陀螺式的死循环,无论是个体,还是某个组织、行业,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会如同车入泥潭,难以自拔。在“万物皆可卷”的当下,重“痕”轻“绩”的检查考核使得一些地方的基层工作陷入公权力“内卷”的怪圈。究其根源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如果任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毫无意义的精益求精”“被动应付工作”等“内卷”现象扩散,就也会受到影响会挫伤基层干部积极性,使得责任感缺失、政绩观错位、想干事的人干不了事、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搁置,甚至基层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会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得不到保障。
(三)“减负”变成“加正”
数字治理的目标是提高基层政府工作效率、创造更方便更快捷的公共服务,而部分地区反映的“成效”却恰恰相反。花样繁多的APP和微信公众号、应接不暇的微信群让基层公务员应接不暇,工作负担不断加剧,影响日常工作开展。有些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手机上安装的各种政务APP和微信公众号多达70个。大量工作需要在手机上完成,眼睛不停盯着手机,基层工作人员没有时间深入基层。另外,甚至个别学习、走访、宣传的APP要求“强制下载”,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数字治理塑造的服务型政府形象大打折扣。有些领导干部的工作变成每天在电脑或手机上“复制+粘贴”上级指令到微信群,基层治理水平出现倒退现象。
(四)暗藏“微腐败”风险
微信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秀场,也藏着“微腐败”的风险和隐患。出现在领导朋友圈里的古玩字画、花鸟虫鱼成为下属投其所好的重要依据。正是所谓“不怕领导有原则,就怕领导无爱好”。下属趁机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些微信工作群频繁出现“抢红包”大战,背后甚至隐藏着拉票贿选。这些“微腐败”现象在新的媒介形式下滋生蔓延,严重影响政治生态。
三、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存在一定的普遍性,严重制约数字治理发展质量和效能。探究其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与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和责任感缺失有直接关系,同时也反映出制度改革与治理方式的深层次问题。
(一)主观原因: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责任感缺失
主观上的错误行为来源于思想认知的偏差。这些“唯痕”“唯形”的工作作风源自于领导干部政绩观的偏离和责任感的缺失。政绩来源于为人民服务,来源于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满足群众的具体诉求,而不是追求各项数据的达标,更不是为了迎合上级领导而不惜造假。一旦脱离群众,政绩就无从谈起。“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强调的不是“印”和“痕”,而是“踏”和“抓”的力度和成效。欺上瞒下、无中生有、摆谱抓痕不仅与数字治理过程的精细化要求背道而驰,也必将在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群众之间筑起“高墙”,使得群众呼声无法上传、政策措施无法切实落地。痕迹管理在实践操作中事与愿违的重要原因在于混淆了手段和目的,把监管方式错误地看做行为结果。面对工作和考核首先考虑上级怎么看、看到了什么,把心思花在“照片、定位、记录”上,确保把作秀结果精准推送给上级领导。对待工作不负责、不担当,留痕不留心,工作作风不实,责任感严重缺失。不仅贻误工作、劳民伤财,而且背离党性,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二)客观原因:压力型体制下的负面激励
“压力型体制”是一种“一元化”的纵向运行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数量化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1]。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集目标制定权、考核权、奖惩权于一身。面对这种“一票否决”制的绝对权威,下级政府必须无条件服从,形成了“唯上主义”的官场逻辑。对基层干部而言,仅仅是命令执行者,而职位升迁和权力赋予都来自上级,形成“想要立足,必须讨好上级”的“唯上是从”思维。因此,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很难成为影响行为导向的根本准则。
由于近年来各项监督考核工作不断加强,干部真抓实干、积极进取的工作干劲受到激发,但也滋生了落实工作“层层加码”“层层拔高”的工作倾向。为了向上级表现自己的工作能力,给下级制定的标准层层拔高,压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传导,逐渐形成职责与评估压力的“漏斗效应”:层级越低,任务越重,评估压力越大。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层层加码,增加了官僚体制纵向的紧张感。基层政府在目标层面受到上级压力的约束,在过程层面则较少受到约束和审核;目标责任通常以量化指标的形式呈现,操作化较强的问责制成为每一级政府或部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作为“参赛选手”进入“晋升锦标赛”的基层干部为避免自己被淘汰出局,用高昂的成本搜集缺乏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信息来实现短期目标。因此,在推广数字治理的改革进程中,为了服从上级要求建立的治理平台广泛存在,与数字治理的公民导向相违背,既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也不能提高服务质量。
第一,规范“群头”制度。群头是独立于横漂公会,不受公会制约,如果把群头作为公会管理的一部分,不但化妆师公会实际对其有了法定的约束力,还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演员管理有。此外,由于群头的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参差不齐,对其实行相应的培训和考核机制也是极其必要的。
(三)制度原因: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异化
从基层实践看,基层工作要应付种类繁多的会议文件,重复机械的检查考核,并且越来越套路化、机械化,重痕迹轻效果,给基层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各类表格,而工作的实质——服务民众却被忽视,造成了普遍的目标替代问题。虽然各地区各部门存在各自的考核机制,但政出多门,重复考核、多头考核的现象屡见不鲜,考核制度不健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因此很难达到集成高效的考核效果。上级往往为了在各种排名中获得优势,通常对各项考核指标“层层加码”。目前各级考核存在考核面过于宽泛、考核重点散乱、考核指标过多、考核重点不突出、考核内容脱离基层工作实际等问题。而考核体系的设计不够科学,考核机制过于形式化,很难对干部起到激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部门不考虑基层实际情况,布置工作随意性强,必然出现智能官僚主义的倾向。基层工作人员为了不被上级部门问责,只能用形式主义来应付。而责任心强、工作作风踏实的干部却无法客观准确的展示自己的工作成绩,工作积极性被严重挫伤。虽然指标化、数量化的考核有助于引导基层注意力分配,但同时又造成了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不能用一个个简单的数字所代替。因此,只有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的出现。
四、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的治理策略
技术本身是为了更高效快捷的解决实际问题。尽管数字治理引发一些问题,但其基础和内涵在于提供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来重新协调利益,缓和冲突并促成合作,所以技术特别是数字治理技术的进步并不应止于科技手段的革新,更在于如何通过技术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付诸实践,让基层数字治理切实落地,推动政府实现良政善治的运作模式。
(一)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干部选拔标准
防止和整治新型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需站在讲政治、讲党性、讲理想信念的高度,要想标本兼治,必须深挖思想和利益根源。整治和防止这种新型的线上四风,必须纠正干部错位的政绩观和价值观。政绩观与个人的理想信念和自身修养有密切关系,由个人的人生观、权利观直接决定,也与上级的选人用人导向和干部管理制度有密切联系。上级“重痕迹、轻结果”的错误导向,已经对干部的考核任用产生了负面影响。上级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对干部理想信念、工作作风以及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把具备正确政绩观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风向标,不以形式论英雄,优先选拔德才兼备、作风扎实、敢于担当、对党忠诚的干部。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面形式看到实际内容。提拔重用工作扎实、实绩突出的干部,让作风浮夸、搞数字造假、利用新媒体大造声势的干部得不到提拔和晋升,才能有效遏制新型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二)构建多元化协作治理体系
构建多元协作治理体系,即鼓励非政府机构和普通个体参与基层数字治理,不仅可以缓解基层政府工作压力,而且可以有效防止信息碎片化、僵尸化现象的出现。民间社会机构、企业甚至普通公众共同参与基层数字治理,可以有效利用各具特色的优势资源,实现治理主体的互补互助。
目前,我国互联网治理系统已经充分彰显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各级网信办与企业和社会形成良性互动的常态协作机制。网信办整合网络宣传、舆论引导以及网络安全等职能,通过网络平台为公众提供管理、监督和参与互动的机会;科研机构向网信办、互联网企业提供政策建议;企业运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网民和社会组织发挥监督和自治的社会功能。该多元化协作治理体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仅增强了社会治理有效性,而且极大减轻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建立数字治理集约观,政务平台或APP应尽量做到简洁便利易操作,杜绝盲目建设,控制后期运行和维护成本。
同时,需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考量平台建设的边界和连通问题,避免重复交叉性建设,不断弥补技术漏洞,减少基层工作压力,杜绝网上数据造假行为。加强“人机”和“人际”多向互动沟通,建立包容友好的“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3]。让“数字治理”和“传统治理”达到平衡,既要充分做好面对面服务,又要提高数字治理的效率与水平。
(三)构建科学高效的立体化考评体系
改变原有的考评方式,构建立体化考评体系,将自我考评、专家评审、公众打分等因素融入综合考评系统,兼顾各类型各机构考评的差异化。在数字治理改革过程中,既要关注改革结果,同时也要重视改革过程,从根本上扭转因上级考核压力而奉行形式主义的基层政府运作机理。
针对信息形式主义与智能官僚主义,一是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针对工作任务交叉与条块分割模糊的现象,要尽最大努力消除和拆解。防止技术滥用,杜绝文山会海,杜绝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二是建立重“实效”轻“痕迹”的考评机制,减少形式权重,增加绩效比例。同时,监督干部网上行为,开展广泛的行政监督、技术监督以及民主监督。以此规范干部网络行为,建立干部网络行为责任制度,对不当网络行为敢于追责问责。
五、结语
克服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特别是要防范和查处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长效化”[4]。在长期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坚持用发展的方法建立持续治理新型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长效机制。切忌因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影响基层正常的工作内容。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处理民生问题,把工作落到实处,形成常态化和长效化的治理机制,并进一步形成系统治理合力,将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实践工作走实走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