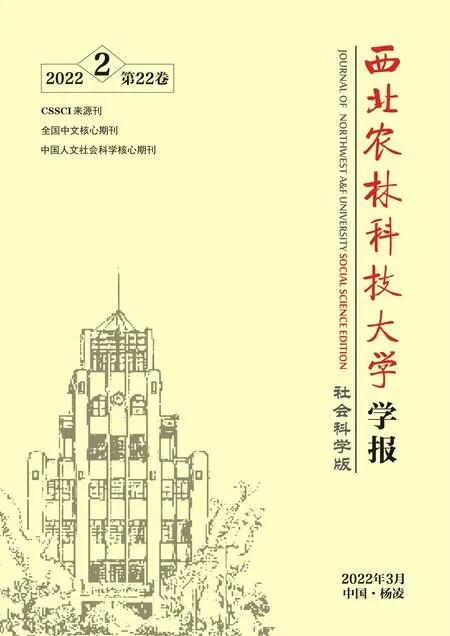森林文化价值的法制表达与《森林法》的文化担当
吴普侠,崔彩贤
(1.陕西省林业科学院,西安 710082;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1],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引用的经典名句。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可持续发展理论”“两山理论”与“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论”等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和方向遵循。2015年发布的《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年)》指出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进一步阐明“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20年《民法典》“绿色原则”的确立将绿色文化的价值理念深刻融入到当代的法制体系。2021年3月12日,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的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上,项目总负责人江泽慧指出:“森林在为美好生活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同时,还提供了约为3.10万亿元的文化价值”[2]。由此可见,森林文化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绿色原则”的重要载体。因此,当代《森林法》的文化价值担当尤为重要。
一、森林文化价值构成与森林价值的多维统一
(一)森林文化价值的构成
森林(林木)具有其独立、多样的文化内涵。学术界对森林(林木)文化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述,或对森林文化进行总体性研究,或对特种树木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更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基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方面,森林文化以森林为背景或载体;另一方面,森林文化体现了森林的人化[3]。政策制度层面对森林文化的规定局限于某些特殊的领域或片面的具象化,如关于古树名木的规定、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论述等。一般认为森林文化是人类认识和使用森林资源过程中形成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包括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其构成见表1。

表1 森林文化价值的构成
(二)森林价值的多维统一
森林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形成了森林价值的统一体系,各价值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更是一种互促共进的关系。
《森林法》总则第一条突出强调了森林的生态价值,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与新战略,立法技术和立法质量也进一步提升。但随着国际国内社会的巨变和转型,国家和民族文化成为国际竞争和国内发展的源动力和方向标。森林文化所具有的国家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等特征要求我们不仅应从社会层面进行宣传和教育,同时也应注重森林文化价值制度层面的规制与引领作用,加强国家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
本文特别强调森林文化价值对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推动和提升作用。一方面,森林文化价值引导经济生产活动。森林文化产品主要满足人们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需求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森林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更多的森林文化形态,森林公园、国家公园、自然景观、林下经济等已经发展成大众文化,成为现代城乡居民休闲、娱乐、康养、疗愈的重要载体、空间和场域,是新时代森林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这种沉浸式消费的意义和快感,成为文化消费产业的营销对象,大众对森林文化价值的需要决定新生的森林经济活动方向,受众对于森林文化价值的认同和满足是森林文化经济活动成功的前提。因此,文化价值成为经济活动策划的核心,较高的文化价值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森林文化价值促进生态价值的实现。森林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净化空气、提供氧气、消除噪声、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生态价值是人类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所总结和凝练一种价值体现。生态学家沃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4]事实上,森林的文化价值对森林生态价值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森林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一种互为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制度规制的层面也应统一和协调。
二、森林文化价值法制表达的历史脉络
(一)古代习惯法的启蒙
人类文明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文明,人类的农耕文明是在挤压森林空间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人类农耕时期对于森林这个神秘的“故居”仍然心存敬畏与感恩。从中国森林法则的发展历史来看,古代虽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典法则,但关于森林及森林文化的价值在历代律令中很早就有了认识与体现。夏朝《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吕氏春秋·孝行览》中的《义赏》篇规定“ 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寡人之于国也》规定“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太祖颁布诏令对造林、护林有功的奖赏进行了规定。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实践中,特别是在律令中,体现着平衡、节制、有序、适度、内敛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理应促进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的现代转型[5]。
(二)近代对森林法则的漠视
工业革命带来的转变使中国走上了一条谋求快速发展的道路,此时的森林法则着重对森林的经济利用进行规范,旨在更高效地利用林木进行社会财富的积累。光绪二十三年(1897),光绪帝以世界潮流所趋,督促各地发展农林事业,下诏谕云:“桑麻丝茶等项,均为民间大利所在。督饬地方官,各就土物所宜,悉心劝办,以浚利源。”于是设专官、兴学校倡办林业[6]。与此同时,对森林资源的消耗和攫取也导致生态危机接踵而至,因此人们便开始重视森林的生态保护,相关立法也从注重其经济效益转换为保护森林生态功能下的经济利用。1914年,北洋政府公布我国第一部《森林法》,从此中国揭开了依法治林的序幕,并涉及到了“保安林”的保护、奖励与责罚等,强调了森林的生态效益[7]。但该阶段战乱频发,严重掣肘相关法律的实施,最终多落为一纸空文。可见,近代以来森林文化在法则中受到了冷落与漠视,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仍未被彻底发掘,因此,人们对于森林的保护仅限于在法律强制力约束下的补偿与修正,而非在森林文化价值理念指导下主动保育。
(三)现代《森林法》的复兴
新中国成立后,稳定的社会环境给予文化蓬勃发展的土壤,中国森林文化研究逐渐繁荣,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如党双忍[8]、苏祖荣[9]、郭风平[10]、樊宝敏[11]等。此时的森林文化研究已经由传统的感性欣赏转化为科学的理性分析,并呈现出细分学科的发展态势,生态伦理学、生态道德、生态文学等概念相继提出,对人与森林和谐共生的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然而这种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对立法的影响甚微,森林法重心仍然在平衡森林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上。1998年特大洪水和沙尘暴引发人们对森林资源配置模式的思考,以往被忽略的森林文化价值重新回到立法者的视野。1998年修正的森林法除在经济、生态价值维度对森林资源进行规制外,还将森林的文化价值纳入其中,着重保护古树名木和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并对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体现了该时期对森林文化价值的认识与重视,并引发各个层级及各省市对该类对象的专门立法。随着自然保护区体系建立,森林公园、森林休闲旅游、森林康养、森林疗愈等的出现,森林文化的价值更加凸显。2019年修订的《森林法》使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表述立法目的,虽未明确肯定森林文化价值的重要地位,但森林文化价值对立法的影响已经有所体现,这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本范式。同时《森林法》规定:“在不影响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发展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从森林基本法层面为森林文化价值的发挥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森林法》文化价值法制表达的时代必然与优化路径
(一)《森林法》文化价值法制表达的时代必然
后工业化、后城镇化时代,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转变,人们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森林法制的价值体系应进一步拓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及本土性,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相关法制的精神中应当被固定和倡导。
同时,在基本法中对森林价值进行均衡规定的立法模式也为域外实践所采纳。韩国2005年出台的《森林文化·休养法》强调充分发挥森林多种功能,鼓励建立自然休养林、自然观察教育林、风景林来满足人们对森林的多元愿望[12]。英国1967年制定的《森林法》规定,应保护具有特别感价值的植物群;对于在果园、花园、教堂墓地或公共休憩用地上种植或生长的果树或树木,委员会不得随意处置,因为该类林木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法律有必要对其进行严格保护[13]。这些国家通过科学的立法让森林文化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文化本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分散立法既不能穷尽森林文化所有形态,苛求立法事无巨细的制定包罗万象的森林文化,实为立法不能承受之重。立法本就是一个将繁杂社会现象浓缩只言片语的过程,既然无法做到巨细无遗的涵盖所有文化形态,在基本法中明确引入森林文化价值,通过上位法来宏观指导下位法的实施就更为必要。
(二)《森林法》文化价值法制表达的优化路径
1.森林法则的人本气息应进一步加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秩序、社会矛盾及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时代转向。习总书记的引典“观俗立法则治”,以及他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与思想,无不体现着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发掘与传承,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法制发展提出了新方向与新遵循。同时著名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指出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富裕阶段时,人们便更加注重求知需求、审美需求等精神层次的满足,在不断丰盈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来实现自我价值。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社会文明的跨越式进步也带动着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森林作为具有疗愈、观赏等独特价值的生态体,其所孕育的既传统又现代的优秀文化愈发得到人们的重视与实践。在此背景下,立法理念的成熟与适度转向也成时代必然。法制从来不是冷冰冰的说教,它是人类创造的唯一驾驭和规制人类行为的科学,它从人类思想行为中产生并最终走向并运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不可避免的要融入人类丰富的人本气息。
2.森林法制理论价值体系需进一步拓展。学界一般将森林资源的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三者共同构成了森林的价值体系,以此种森林价值体系为基础而制定的《森林法》条文中更多强调了森林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对森林的文化价值有所忽视。如前文所述,森林资源三种价值之间关系密切,互促互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对森林资源的利用着重于其经济价值,过度索取的恶果又让政策制定者注意力转移到生态价值上,法律制定与修改也呈现出这一变化趋势。进入新时代,随着国际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和需求的变化和转向,政策制定者的顶层设计不断强调文化价值的重要性,突出扩大文化价值的引领作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应适时跟进。在森林法律体系的基本法《森林法》中明确森林文化价值的地位和作用,对森林文化价值进行适度规定,不仅可以优化立法结构,同时也可以避免森林价值理论的体系缺陷,让森林价值体系在法则中全面体现,将生态文明观彻底融入森林基本法中。
3.森林价值体系在《森林法》中应进一步统合。全面检视涉及森林文化价值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呈现出规章制度独立规定、分散式立法、下位法更为具体、基本法缺失较为突出的分布态势和特征。2011年实施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以及2016年修订的《森林公园管理办法》都对森林文化价值中森林旅游这一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2016年北京市实施的《森林文化基地建设指导原则》通过森林文化基地建设推动森林疗养、森林体验、森林教育的开展。2020年2月1日实施的《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了文化传承的原则等。这种态势和特征与以往我国对人与森林关系认识的局限性有关,缺乏对森林文化价值的重视,加上我国森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现状,致使各部门在规范制定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利益博弈,种种因素最终形成了森林文化价值在森林法中的弱势地位。立法中对森林文化价值没有明确规定,政府缺乏发展森林文化价值的制度基础,法官缺少援引法条保护森林文化的制度依据,因此,在《森林法》中进一步统合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四、《森林法》文化价值担当的基本策略
《森林法》是实现森林文化价值的最优规范载体,应合理建构法律条文以表达森林文化应有的价值定位。《森林法》应明确确立森林文化价值的核心地位,更有效的从制度层面发挥森林文化价值,引领法律其他价值的实现。《森林法》应采取“总则明确规定+分则相对细化”的立法模式和技术,将森林文化价值扩充至基础地位,以保障《森林法》立法逻辑的自洽性、价值方向的全面性与总分则内容的协调性,实现对森林资源的整体性保护[14]。
(一)总则明确规定
为更高效地发挥森林文化价值的作用,构建价值维度间的协调关系,可将森林的文化价值在《森林法》中予以“总则化”表述。总则与分则是共通规定与特别规定的关系,其中总则部分扮演着双重角色,即指导与补充分则[15],因此,森林文化价值的“总则化”不仅在价值方向上发挥着引领性作用,注重解决《森林法》中的共性问题,还对具体条款的适用起到补漏性作用。据此,应结合现行《森林法》总则结构进行完善。
森林文化价值的总则化,首先可以对《森林法》立法方向进行引导,改变以往忽视森林文化价值的观念,确立森林文化价值的重要地位。总则可从宏观角度回答《森林法》中的基本问题,有利于分则更明晰地规定森林文化价值相关具体问题。其次可以补充分则中遗漏或不明确的条款,起到兜底补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的总则不仅对本法分则有指导作用,对于下位法涉及到森林文化及其价值的部分均可以进行有效回应,增强了森林法律体系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这样规定,一方面契合了“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立法目的,落实“突出森林主导功能、发挥多种功能”的价值期待,明晰森林文化价值的立法定位;另一方面在立法层面理顺了生态、经济及文化价值的逻辑关系,优化了森林价值体系,也为森林文化的现实需求提供了规范依据,完善了森林法律体系,更大限度地保护森林生态并满足人民大众的各种需求。
《森林法》总则部分以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责任主体及相关权利义务为立法的技术路线,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了各主体对森林资源保护所应承担的宣传教育及知识普及义务,间接彰显出人文林业的教化功能,因此,若将森林文化价值纳入总则之中,第十二条可明确“推动森林文化建设”的指导性义务,落实森林资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期待,给予其相应的法律地位,实现森林生态、经济、文化价值的协调共存。除明确其价值定位之外,对于相关措施的规范设计也应在总则中予以落实,第五条对于森林生态保护及林业发展所投入的资金支持也可涉及森林文化领域。同时,第十三条规定的表彰、奖励同样也应给予在森林文化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组织或个人。通过对该三条法律规范内容的扩展,森林的文化价值在总则中得到了合理表达,且实现了将其“总则化”的调整目的。
(二)分则相对细化
分则特别规定的适用应与总则保持协调统一,因此森林文化价值这一抽象表述可适当通过分则的具体条款予以阐释与落实。
《森林法》第四十条“对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的保护”以及第四十二条有关“森林城市和美丽家园建设”的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森林的文化价值,但其条款内容更侧重于森林保护与造林绿化,除此之外,分则部分对于森林文化价值的规定鲜有体现,可见涉及森林文化价值的法律规范并没有得到系统地表达。从立法逻辑来看,若要在分则中对森林的文化价值进行相对细化规定,可将其编入第六章“经营管理”之中,该章将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类,首先对公益林的概念、区域划定及管理主体进行了规定,在此之后,第四十九条从生态和经济价值角度明确了公益林的用途、经营方式及经营理念,同样对商品林也进行了类似的立法设计。由此可见,该章是保护森林生态及经济效益的立法,但森林文化效益的缺失,其条文设计并不能完全实现立法价值。通过在分则中的补充规定,将森林文化价值内涵融入《森林法》之中,既是对总则总括性规定的呼应,又保持了分则价值体系的平衡,矫正了价值体系在分则中的失衡。
《森林法》是基于森林价值体系构建的森林资源配置的基本法。在我国,森林文化法制化源远流长,中国森林法则的发展历程为森林文化的法制化提供了历史依据。同时“可持续发展理论”“两山理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论”为森林文化的法制化提供了宽厚的理论基础。《森林法》作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需要在调整“人林共生关系”时为公众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16],通过对相关权利义务的调整使人们建立对森林资源的文化价值认同,从而在思想根源上引导人们自主、自发地重视森林的保育与修复,加强公众保护森林的参与度,以提高林业的社会贡献力和公众的文化自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