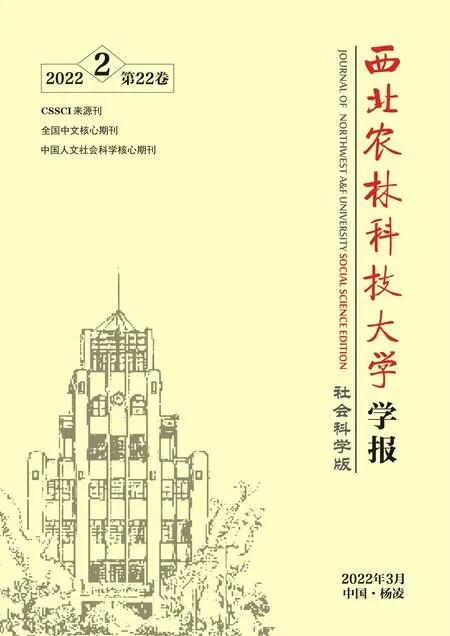《中华农学会报》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
郭建新,惠富平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南京 210095)
《中华农学会报》(以下简称《会报》)是民国时期中华农学会的机关刊物,曾用名《中华农学会丛刊》《中华农林会报》,1918年12月创办,1948年11月停刊,是民国时期办刊时间最长和最重要的农学期刊,反映出现代农学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的过程。著名农学家过探先、周清、顾复、曾济宽、陈嵘、梁希、沈宗瀚、胡昌炽、陈鸿佑等人先后担任该刊主编,编辑队伍也是群英荟萃。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会报》办刊之路艰难曲折,但坚持走到终点并保证了学术质量,充分发挥了其农业科技传播作用,其中包含了很多成功经验与有益启示。可惜迄今学界以《会报》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很匮乏,能检索到的论文仅寥寥数篇。为此,本文以全套《会报》资料为基础,探讨该刊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业科技变革中所发挥的重要媒介作用,以便加深对中国现代农学与农业发展的认识。
一、《会报》办刊背景与历程
《会报》内容丰富,办刊历史持续而完整,在近代农业科技传播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还全面反映出民国时期的农学研究以及农业发展水平,在当时林林总总的农学期刊中首屈一指,影响深远。
(一)办刊时代背景
清末民国初期,面对中国农业衰败落后的境况,许多有识之士学习西方先进农业科技,发展中国农业,兴农救国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政府设立各种农业管理机构、颁行一系列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组建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农业科研机构,并向国外选派大量农科留学生;各地还纷纷设立农学团体,创办新型农业学校及农事试验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孙中山强调:“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1]实业家张謇曾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2]教育家章士钊认为:中国的政治现状已令人绝望,“而以地大物博之关系,比较的惟有农业尚可救国。”[3]棉业专家穆藕初认为:“实业中占中心势力者莫如农,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4]在农业救国风气的影响下,许多有志青年及赴外留学生选择学习农科。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潮流,民间学习西方科技的热情日益高涨。与此相适应,在政府、科教机构和科学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相关出版传媒事业迅速发展,科技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社会对现代农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加之期刊这一新媒体形式的知识传播功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促使一批以译介和传播现代西方现代农业科技为主体内容的专业性农学期刊相继问世。
1896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农学会”,是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农学学术组织,该会以“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源”为宗旨,刊行《农学报》,在清末近代农学引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农学报》以农学社团为核心的办刊模式,也为近代农学期刊的创办提供了样板。20世纪初,农业报刊杂志的重要性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盖学堂既难遍立,教育不能普及,全靠农报风行,开通民智”[5],各地农业机关及农学社团创办的农学刊物逐渐增多。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等组建的中国科学社在美国创办《科学》杂志,过探先、邹秉文、秉志等社员成为科学社最早的农科研究发起人。1918年,《科学》迁回国内,在中国首创中文横排方式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之一。
1917年1月,由中国最早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等发起组织成立“中华农学会”,并在上海江苏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其宗旨是“研究学术,图农业之发挥;普及知识,求农事之改进”,会所在南京市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见图1)。中华农学会创立后,充分认识到会刊对于组织和传扬农学的重要作用,标志着《会报》的正式问世。

图1 中华农学会南京会所(1)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华农学会报》,1931年,第84期。 图2 《中华农学会报》刊影(2)图片来源:大成老旧刊数据库和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二)刊物创办与发展历程
在民国时期建立的科学社团中,中华农学会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农学社团。中华农学会从清末以来各地创办报刊的实践活动中受到启发,将刊行会报奉为首要事业,所谓“事业之发轫,首在会报之刊行”[6]4。
1918年12月,中华农学会经过了近4个月的筹备,创办发行《中华农学会丛刊》(见图2)。《中华农学会丛刊》出版四册以后,农学会经济拮据,于是决定与中华森林学会共同办刊,会刊自第五册起更名为《中华农林会报》,规定年出6册。不久,中华农学会与中华森林会分道扬镳,不再合办会刊。1920年10月,中华农学会会刊再次更名为《中华农学会报》,并长期沿用。另外,经学会第三次年会商议,《会报》年出月刊10册,专刊2册。月刊“注重一般之农学,发表研究、调查,鼓吹舆论,促进农林事业为主”[7];专刊则“专就农界上重要之问题,应时势之需要而研究发表之”[7]。1920年10月至1922年9月,《会报》共出版2卷24册。从第3卷起,《会报》专刊的出版时间不再固定,只在有特别著述时才临时增刊。1924年,受江浙战争的影响,农学会辗转苏杭,《会报》暂时休刊。
1925年,中华农学会迁至上海。同年11月,在上海会员的共同努力下《会报》继续发刊,出版第48期(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局趋于稳定,但学会办刊经费不足,只得将《会报》委托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因限于该局规例,《会报》名称又改回当初的《中华农学会丛刊》[6]7。1927年2月-1929年2月,《丛刊》以双月刊的形式共计发行14期。1929年4月(第67期),中华农学会与中华书局签订的印刷合同期满,收回会刊发行权,恢复会报旧名。
1930年,中华农学会迁回南京。自第72期起,《会报》改为月刊。截止1937年8月,《会报》共计出版92期(到第72期第163期),其中专号32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农学会辗转西迁,《会报》暂时休刊。1938年8月,《会报》衔接以往期数编印,复刊之第一册(续前为第164期)在重庆出版。重庆虽处大后方,但日军飞机频繁轰炸,依然影响《会报》出版发行。据1940年2月11日会报编辑报告:“去岁渝市屡遭轰炸,而承印本会会报之京华印书馆工厂奉令疏散,未能按期出版,只发行167期1期,以致留存文稿甚多。”[8]1941年冬,日军侵占上海,“会报同蒙浩劫者,计有3期(174、175、176)之多,作者心血,读者期待,尽付烽烟”[9]。
1946年7月,中华农学会总部由重庆迁回南京,因交通困难、房屋破蔽待修,编辑工作受到影响,《会报》不能如期付印[10]。1947年,“工料飞涨,为经济所限”[11],会刊仅出版了第184、185两期。1948年12月,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衰亡,中华农学会决定《会报》暂停编行,并最终停刊。截至1948年11月,《会报》前后共计出刊190期。
《中华农学会报》从1918年12月创办,到1948年11月停刊,历经艰难,坚持了整整30年,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和承载了近代中国农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还催生了大量相关的地方性及专题性农业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会报》又通过《作物学报》等期刊得以新生。
二、记录近代中国农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
20世纪以来,西方农业科技成果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并扩展开来。在各种传播媒介中,农学期刊成为农业科技知识交流与扩散的主要载体。从一定程度上说,《会报》作为民国时期的代表性农学期刊,是中国农业科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记录者,各个农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演变历史都可以从其栏目设置、内容安排及文章选取中找到依据。
据统计,《会报》自创刊至终刊总计开设74个栏目。按栏目类型划分,可分为学术类(论说、学艺等)、调查类(调查、研究调查)、报告类(报告、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译介类(译述、译著等)、计划建议类(计划、计划书等)、书评类(书报介绍、新书介绍、书籍介绍)、纪事类(本会纪事、纪事等)、杂录类(附录、杂纂等)、文艺类(文苑、游记、小说)、新闻通讯类(农事新闻、农界时事录等)、图片类(照相、插图)、资料类(参考资料)以及其他类(读者论坛、农民常识等)。从以上栏目类型可以看出,《会报》兼顾知识性、理论性和应用性三大方面,呈现出内容覆盖面广、层次多样的格局,基本能够紧扣办刊宗旨研究农学革新、农业促进和农村建设。对各大类所包含的具体栏目加以统计,可知这些栏目设置的起止时间各不相同,相互间保持着继起和并存的关系。其中有38个栏目仅设置1次,5个栏目设置2次,3个栏目设置3次,可看作是非常设栏目,而出现4次及以上的栏目则可看作是常设栏目。本文仅将常设栏目名称及其出现次数加以整理,见表1。

表1 《中华农学会报》常设栏目种类表
从上述栏目设置的起止时间和名称变化来看,不少栏目是异名同义,刊载的文章内容相对稳定,既体现出明确的传承性,又有一定的创新性。其栏目传承性主要体现在常设栏目保持连续不变。例如,“论说”“学艺”“专载”自设置后,分别是1~47期、1~22期以及11~47期的常设栏目,反映它们属于《会报》的主打栏目,这有利于保持刊文内容的稳定性以及读者订阅的持续性。还有些栏目虽然是间断开设,但延续时间较长。例如,始于第1期的“调查”栏目,从1918年12月到1948年9月间共断续出现58次。栏目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会报》主编与时俱进,变更或策划了一些新栏目,并多次对外发布通告宣扬“刷新”(3)例如,《中华农学会报》第35期至第42期、第44期以及第52期均刊载有中华农学会刷新该刊的通告。。例如,1923年设置的“论著”栏目由“论说”“著述”两个相关性比较强的栏目合并而来,学理性的文章、演讲稿等均可收录在内。自1926年起农学会开始与国民党政府密切合作,栏目建设上对农村组织、农村社会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上述栏目所承载的农业科技内容非常丰富。

表2 《中华农学会报》各科文章数量
据统计,《会报》办刊30年共刊载的论文2 072篇。再依据《中华农学会报第一期至第一百五十五期总索引》以学科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将《会报》刊载文章的内容属性归纳为15个门类,统计出各学科文章的数量(见表2)。《会报》着眼于“大农学”概念,刊文内容范围广泛,层次多样,基本涵盖了现代农学的各个方面,并见证和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农学发展的特征:(1)作物、林学、农业化学等学科刊文数量较多,且体裁形式多样,内容则经历了由译介为主到本土试验研究为主,以及研究内容逐趋系统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近代农业及农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以作物学文章为例,1937年之前发表的文章中,译文占据较高比例(37%),而1937年之后的文章则主要为中国学者自撰文章,译文比例仅为2.04%。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中国作物学是在西方作物学理论的引领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作物学界在1937年以后已经不再将从西方引进理论作为主要任务,而是开始投入到具体的研究、创造工作中。(2)抗日战争期间,《会报》关于西部大后方的调查、研究文章显著增加,体现出中国农学发展的时代特点。抗战期间,随着科研机构和团体的纷纷内迁,学者们结合战时需要,因地制宜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农业展开课题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例如:1930-1933年,赵连芳在国立中央大学昆山稻作试验场开展了一系列水稻育种技术试验,创立的一套育种法被全国各水稻育种试验场广泛采用,论文《水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也在《会报》及时发表;1932-1941年,金陵大学农学院组织在四川金堂、江津、南充等地开展柑橘果实贮藏及病虫害防治研究,俞大绂、陈锡鑫、胡昌炽等人的系列试验及调研成果相继在《会报》刊载;1941年,梁希在西南地区的调查研究中写成《川西(峨眉、峨边)木材之物理性》《中国十四省油桐种子分析》《桐油抽提试验》,堪称中国林产化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在作物学文章中,作物遗传育种备受关注,相关文章数量达162篇,占作物学刊文总量的42.74%,其他如栽培和田间试验、作物通论、调查和生物统计方面的文章也相对较多;作物学研究以水稻、小麦、棉花为重点,时见试验场的最新实验报告和研究成果;对于西方作物学理论的引介及本土实践探讨,贯穿于《会报》整个生命历程,为中国作物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会报》刊载的林学文章数量位居第二,且前沿性强,森林知识传播也很受重视;林学文章涉及的树种往往与战时军需品的生产密切相关,体现出林学为抗战服务的特点。早期的林学文章以现状调查和技术介绍为主,之后理论性逐渐增强,反映出中国林业科技的本土化进程。
三、西方农学引进桥梁与中国农学宣传窗口
在近代中国农学转型的重要时期,《会报》代表了当时中国农学期刊的最高水平,成为西方先进农业科技引进的重要桥梁及向外介绍中国农业的窗口,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国际书刊交换活动中。
《会报》的创办人员大都来自江浙地区,又曾在欧美、日本留学,故一开始就很重视译介和刊载西方现代农学成果,以便洋为中用,振兴中国农业。据统计,“三十年间所出版的190期《中华农学会报》中,有译作305篇”[12]。虽然《会报》后来以发表本土的农业试验和调查研究成果为主,译文数量有逐步减少之势,但是这种重视西方农学译介的传统却一直延续到1937年。《会报》所选录的译文选题丰富、内容多样,且目的性强,涉及农学各个分支学科。例如,作物学方面:顾复译《种艺研究之新题目》,潘简良译《农作物产量之育种》,卢守耕译《野生稻与栽培稻杂种之性状观察》,冯泽芳译《印度棉之染色体数目》。蚕桑方面:夏振铎译《论家蚕后天之免疫》,胡鸿均译《蚕卵人工孵化之原理(预报)》。林学方面:曾济宽译《森林植物带之分布与果树栽培带之分布》,林刚译《洋槐造林之价值》。农业化学方面:李承忠译《农产物之化学性质》,陈方济译《中国之食粮问题与酒类》。园艺方面:胡昌炽译《日本果树园艺之过去与将来》,陈梦熊译《中国果树及蔬菜园艺之杂感》。译者多接受过现代农学教育且精通外语,从而保障了译文的质量。《会报》刊载的国外农学论著,可以为中国农业科技人员提供及时有效的试验研究指导,推动中国本土农学发展的进程。
尤其是这些译文选择以“实用济世”为初衷,针对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并紧跟国外农学研究的新步伐,具有“补充中国学术研究不足”的特点。汪和耕《栽培森林之利益》前言中讲述:“按此篇系前青岛林务官德人哈司氏所著,关于森林利益,言之綦详,深可引起一般重林观念。而于德国林业经济之状况,以及我国急宜振兴林业之策略,尤为致意,所论各节,颇有见地,故不厌其陈而移译之。”[13]沈宗瀚《选种为改良棉业之捷径》篇首亦言:“近数年来,政府商界提倡美棉不遗余力,试验棉场相继设立者日见增多。农人感于棉价之高,提倡之力,改栽棉花者亦日多,此诚可佳之景象。然参观各场,大都一场栽培美棉十数种或四五种,所产棉子即供次年栽植之用,品种日渐退化,当谓美棉不适中土,殊不知试验品种与选种宜分别行之,否则花粉杂交,品种劣变,自然之势。古氏O.F.Cook为美国棉业育种专家,去年曾来吾邦,此篇系彼名著,论育种选种之法甚详,译之以饷国内业棉诸君子。”[14]周长信摘译《稻之一般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一文时提到:“此篇译自理学博士木原均及长尾正人共著禾谷类の细胞遗传学中,此书系1933年11月出版,材料极为新鲜,且有相当价值。”[15]以中国农业实际需求为目的,精心选译的西人论著,显然有利于当时中国农学与农业的进步。
除过译介西方农学论著之外,《会报》有些文章写作时还大量引用外文资料并标明出处。这既属于学术规范,也是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学习和吸收西方农学的重要表现。例如,卢守耕的《印度型稻与日本型稻之比较研究》一文,引用了23种文献,其中英文7种,日文9种;管相桓等人的《栽培稻多颖性变异之观察》在文后共计列举了12种参考文献,全部为英文资料。
同时,《会报》积极发挥其沟通中外农业的媒介功能,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农学的窗口。中华农学会一直追求国际化的办刊理念,《会报》后期更是遵循国际贯例,在第64期、第174期中专门设置英文目录,第175期、第185期又增加了英文摘要。《会报》仿照西方学术杂志办刊体例的做法收到显著效果,使其很早便进入了西方科学界的视野。1933年,德国种畜社通过与中华农学会互相交换杂志,了解到中华农学会“对于振兴中国农业,尤其对于畜牧之改良非常努力”,该社成员在致函中华农学会的信中还特别提到:“《中华农学会报》系以中文印行,敝社同人不识贵国文字,至以为憾。惟第一〇八期载有振兴中国全国农业计划英文译文一篇,藉知贵国对于发展本国农作物及畜产品之生产甚为注意,无任愉快”。[16]特别是在抗战军兴后,中华农学会与英美大使馆商定,按期交换各自的农业研究最新成绩与进展:“凡彼国有最新之研究成绩,按期交由本会代发国内各农业机关、学校、及专家,以便参考。而我国内农业研究进展情形,亦随时摘要译成英文送请该两国大使馆转送各该国内农业机关、学校、及专家”[17]22。随之,1943-1947年出版的第175期至第185期《会报》中,各期卷首均有英文摘要。中华农学会负责人在报告1943年度学会编辑工作情形时指出:“本年度仅能出版两期(175期、176期),深以为憾,惟有两事颇足自慰者,一为内容充实,本年度刊行之两期会报,其内容均系会友精心结构之作,发刊后,深得各方之好评。一为与国外交换,本两期会报之各篇大作,均附有英文摘要,每期并抽印单行本100份,分送英美大使馆请其转赠各该国农科大学及农学专家参考。英美两大使馆均甚表欢迎。故本会报今后不仅在国内取得崇高地位,即在国外亦有其学术价值矣。”[17]15
此外,《会报》还专门刊登启事,向国外选送学术价值较高的稿件,宣扬中国的科研成果。对此,主编梁希曾作过注解:“抑欧化东渐以来,国内杂志林立,而农学独寥若晨星,从未有继续十八年,连绵百五十五期,累积一千万言如本报者,本会拥此有历史之月刊,岂独敝帚足以自珍而已?海内外欲知中国农学之演进,欲识中国农业之掌故,欲察中国农政之推移者,寻绎本报,未始不可得一大概,然则本报之关系于中国农界,亦不得谓小也。”[18]表达出其开放办刊、向世界推介中国农学的思想。
四、农业科技传播与交流的学术平台
在民国时期,兼具图书和报纸之优点的农学期刊是农业科技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首选媒介,也是其进行农业信息传播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会报》及时刊载中外农学研究成果,努力构建农学知识学习与信息交换平台,拉近会员间的时空距离,不但为全国各地的读者及农学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知识营养,而且通过成果发表与交流,为其科研创新及学术成长创造了条件,较好地实现了“发扬农学,交换智识”[19]的功能。许多读者也正是受到《会报》相关论著的启发,获得了学术突破。
著名农学家沈宗瀚在回忆其本人学术生涯起步时的经历称:“余于民九冬起,开始农学著作,然自审学识浅陋,乃自调查报告及译述棉业名著入手,多于民九(1920年)至民十一年(1922年)之中华农学会会报发表。”[20](1921-1923年)有会员在阅读了《中华农学会丛刊》第1期登载的《滁县珠龙桥镇桐漆调查》一文后,主动与作者谢先进联系,交流桐子脱壳的方法,并向其介绍了四川桐油外壳剥脱及利用的方法,后来作者据此法又写成了《油桐种实脱皮及其利用法》一文[21]。1932年吴觉农发表的论文中,说明他引用了《会报》第100期杜修昌《米价问题之一斑》关于粳米价格季节变化的资料[22]。梁希读完《会报》刊载的《广东试行兵工造林第一年之纪述》和《一九三三年美国林业之新设施》等文章后,写成《读凌傅二氏文书后》,再刊于《会报》,对中国林业的发展充满希望,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讨论。郑乃涛在写作《鱼藤及其经济价值》之前,遍览《会报》中关于害虫药物防治的文章,发现了该领域研究的薄弱之处,从而形成了新的课题:“我国南部所产植物中,有名鱼藤者,含有剧烈之杀虫成分,目前各国已认为最佳之杀虫剂原料。东邻及美国曾下精细之研究,而反观我国对此植物之探讨尚不多闻。爰搜集材料,草成斯篇,聊作初步之介绍。”[23]王绶1948年从大豆遗传实验中发现了一个花斑隐性基因,此成果一经《会报》发表,即受到国内外农学界重视,被国际大豆基因命名委员会定名为“Riri”,也激发了后人对大豆育种的探索。
《会报》还凭借其媒介优势出版专刊,结合时代需求,有意识地组织专题性学术讨论,发表相关学术成果,促进农业科技知识的交流与创新。《会报》先后围绕蚕丝、稻作、农业教育、茶叶、除螟、植物病虫害等13个主题发行专刊,引导会员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解决农业发展中遭遇的难题。20世纪20年代,中华农学会提倡棉业、小麦的改良,《会报》刊登《选种为改良棉业之捷径》《江苏淮徐海棉作之现在与将来》《中棉之研究》《中棉之形态及分类》《改良小麦之管见》等一系列文章,有力地支持了两种作物的改良与生产[24]。30年代政府推行农村复兴运动,《会报》刊发了《农村复兴运动与农村经济之发展》《改造农业教育救国之商榷》《农村复兴运动声中村有林之研究》等文章,其中包含了相关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1933年底刊行的《植物病虫害专号》序言:“今之为政者,亦鉴于连年各地蝗蝻螟螣及稻瘟麦奴等为害之烈,既渐企遵总理遗训,实行‘用国家的大力量来消除害虫’。则邦人士当亦亟欲一觇年来治病虫害学者之研究成绩,爰我会有此专号之刊。”[25]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加速开发大后方农业”,《会报》从服务抗战出发,发表一批有关西南地区农业研究的文章,如《云南出产木棉之价值》《四川重要林木生长之研究》。
《会报》的学术交流平台作用,获得很多农学家的赞誉。据吕增耕回忆,茶叶专家吴觉农曾向其推荐该刊:“1936年笔者在上海报考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检验员,第一次见到了吴老,当时他问我读些什么书,我回答读一些农业技术方面的书,他说还要读些活的书,如《农学会报》《中国农村月刊》。”[26]尤其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农学专题刊行策略,最为农学家看重。据吴觉农回忆:“由于这样的《专刊》的内容比较集中,并能各就学术问题抒发己见,因此,刊行以来,深受读者欢迎。”[27]水稻专家柯象寅也说:“我对本会的各项,最感兴趣的是《中华农学会报》,特别是第114期‘作物育种专号’(1933年7月号)。这期刊载的有赵连芳:水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肖辅:棉作田间技术研究;沈宗瀚:高粱育种法;孙逢吉:绿麻田间技术研究;李先闻:人工引变与育种;涂治:抗病育种和丁颖的‘广东的野生稻和育成的新种’等。作者都是当时的专家、教授。这些论文为我国作物育种科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尤其是水稻田间试验技术,沿用至今。这是一本好书,一本珍贵的书,是本会重大贡献之一。我的一本,历经动乱,都未丢弃,珍藏至今。”[28]
学术交流切磋推动了科技发明和革新,“科学工作者只有通过相互交流和研讨,才能使糊涂的观念得到澄清,片面的思想得到修正,散乱的概念得到整理,不足的知识得到补充,创造性的火花得到触发,从而建立起智力协作的关系”[29]。《会报》学术传播与交流的媒介功能,在农学家的科研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农业科技应用与推广的期刊媒介
《会报》属于农学期刊,也是一种方便快捷、受众面广的新型农业信息传播媒介。在民国时期强调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相结合的社会背景下,《会报》的农业技术宣传推广方式也有一定特点及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其农业新品种及实用技术介绍、农用物资与农业书刊推销广告刊登等方面。
第一,《会报》介绍的耕作栽培和饲养繁育方法,意在普及与推广切实易行的农业生产技术。民国时期,不少农学家注意到《会报》在农业技术推广和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积极投稿以实现其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孙恩麐《美棉栽培简法》即有推广美棉栽培之目的:“美棉优于华棉,人尽知之,然近日吾人试种美棉,每遭失败,致后起者,裹足不敢前,余甚惑焉。……今更撰此美棉栽培简法,公诸同志,俾吾人栽培美棉之得其道,而实行促进美棉之推广也。”[30]谢先进在《会报》发表《除虫菊之栽培及其利用》《除虫菊粉制蚊香法》《除虫菊栽培须知》等文章之后,除虫菊种子销量大增。《会报》上刊载的一则除虫菊种子购买预约广告反映了这一事实:“除虫菊为农业上日用上驱虫妙品,向特日人输入每年约三百万金,漏卮之巨可胜叹也。先进前在本刊发表关于此菊栽培利用等法,函询购种者纷纷,因未先事预备留种,致分配不匀。”[31]又如,1926年的《除螟专刊》登载的各种螟虫驱除方法,“为昧于施用人造肥料致遭巨大损失者之南针”[32]。其他如《日本驱除螟虫之方法》《五倍子人工繁殖法》《甘蓝栽培法》,也重在技术推广,帮助民众发展生产。

图3 德商硫酸铔广告(4)《中华农学会报》,1937年,第55期。
第二,《会报》凭借其信息传播优势,刊登良种、化肥等销售广告,客观上起到了农业技术推广作用。《会报》发行范围广,信息传播速度快,拥有稳定的涉农读者群体,具有开展相关广告经营的优势,所以在该刊投放广告的农业公司数量众多,如南京兴农公司、浙江生生公司、云野林业公司、三星牛乳公司、南沙林牧公司、江西利生林垦公司、上海三友化学肥料公司、爱礼司洋行以及三井洋行等。这些公司主要经营优良果木、蔬菜、畜牧品种及新式肥料,具有现代企业的性质,它们有意识地运用先进的销售策略,选择《会报》作为宣传载体,既拓宽了产品销售渠道,又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以江苏浦东模范农林场的广告为例:“本场精选作物、森林种子,果树、蚕桑、蔬菜、花卉种苗,农林、蚕业、养蜂用具,并代办外洋种子、苗木、农具、农书及一切农用物品,品种优良,定价低廉,如蒙各界光顾,不胜欢迎。”[33]这则广告作为一种信息源,吸引人们去了解或购买其作物苗木良种及新农具,也有利于农业技术推广。再以化肥宣传推销为例,化肥进入中国初期,农民不相信其肥田效果,不愿意购买和使用。为了打开化肥销路,商家通过各种手段予以推销,其中包括在《会报》等各种期刊杂志上大量登载化肥广告(见图3)。如上海爱礼司洋行刊登于《会报》的化肥广告宣称,其狮马牌和合肥田粉与市上一般肥田粉大不相同,氮磷钾三要素俱全,且成分充足,用法简单,视土壤及作物种类而别,干撒或化水灌溉皆可。并承诺该化肥不含有毒质,不伤人畜,适宜于各种作物,施用日久不坏土壤,用以壅田,生育完美,收获增多[34]。又如日本三井洋行的化肥广告宣称,其生产的双龙牌配合肥料“系按泥土之性质及植物之种类配合窒素磷酸加里三要素而成”,且日本产肥田粉具有“肥效既大且极美观,包装品质无虞损坏”等的优点。[35]这样的广告难免溢美夸大之词,但也确实对化肥推广起到了一定作用:“近以化学肥料,商行利用广告宣传之故,人造肥料且有凌驾天然肥料之势焉。”[36]大量广告宣传改变了人们对化肥的排斥心理,使得其购买和使用量大为增加。

图4 中华农业函授学校招生广告(5)《中华农学会报》,1924年,第47期。
第三,《会报》刊登的农业类图书杂志广告及农业学校招生广告,间接推动了农业科技文化及教育的普及与推广。《会报》创刊后与中华书局、中国科学社等诸多书局、报刊社建立了业务往来,并刊登相当数量的书报广告。在《会报》刊登的图书广告有:《农学实验法讲义》《堆肥新编》《森林管理学》《森林保护学》《测量学详解》《农业教育》等;刊登的杂志广告有:《科学》《农林新报》《醒农》《农事月刊》《新农业》《劝业丛报》《博物学会杂志》《法政学报》《北京民生月刊》等(见图4)。例如,《湖南实业杂志》的广告声称:“本杂志之特色:材料宏富,调查确实,议论精当,宗旨纯正。……定阅本杂志者之利益:研究学问者读之,可以输入最新科学之知识。留心时事者读之,可以洞悉国内外实业之状况。”[37]上海新学会社出版的《林政学》《实用森林学》《造林学本论》等林学丛书打出的广告为:“有志林业者必备之参考书。”[38]《会报》的读者群体具备较高科学文化素养,以上书刊的内容多与农业及实业有关,符合这些书刊广告对目标受众的要求,从而提高了传播效果。另外,金陵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中华农业函授学校等农业类院校都曾借助《会报》发布相关招生信息,如《金陵大学蚕桑特科招考简章》《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招考棉林科职工班学生简章》《函授养蜂招生》等。这些消息随着《会报》的发行而广为传布,有利于增进农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并促进社会各界对农业教育的了解。
六、小 结
在民国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会报》数易其名,编辑出版也屡经坎坷,但仍坚持刊行30年,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农学期刊及科技期刊典范。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传统农学向现代农学转型的关键时期,《会报》很好地实现了其农业科技传媒功能,对中国近代农学及农业的发展演变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今人应进一步关注其农业历史资料价值及办刊经验教训,以推进中国近代农学与农业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