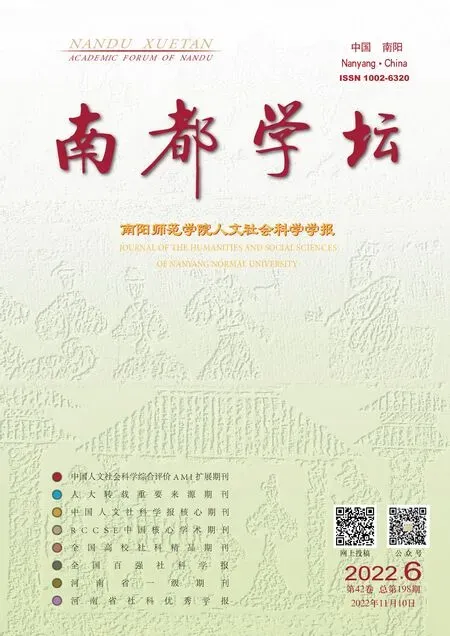王献唐日记等文献佐证甲骨文发现新说
——再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及“刘鹗发现说”
任 光 宇
(成都市龙泉驿区 龙华社区,四川 成都 610100)
笔者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1]中(下简称《新论》),论证提出了“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的学术新说,其主要内容可总结为: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应只有“王懿荣发现说”与“刘鹗发现说”可议(“古董商/农民发现说”仅为“行为意义发现”,“王襄孟定生发现说”因缺乏“学术发现”所必要的、及时的“学术鉴定”难以成立)。“刘说”具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吃药发现说”尚不宜入正史[1]1。然而笔者看到李勇慧的论文《再论甲骨文发现始末》(2016年6月)[2],以及《王献唐年谱长编》(2017)、《王献唐著述考》(2014),还有其他多种来源提供的史料文献和相关评述,为百年来流传极广的“吃药发现甲骨文说”从传说进入学术史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王刘联合发现甲骨文说”“刘鹗开启甲骨文考释说”“刘鹗发现说”等新说议题提供了有力的新文献证据支持,故有必要以本文作出进一步的多方面辨析论证。
一、李勇慧发现王献唐日记中记载的“甲骨文发现始末”
李勇慧《再论甲骨文发现始末》(为行文方便,下文有时简称《李文》)[2],披露了民国时期山东文史大家王献唐在其“尘封近80年的尚未公开面世、尚未出版的《王献唐日记》”中,写下了一篇《记甲骨发现始末》的珍贵短文,记载了“王懿荣甥孙周汉光”向王献唐当面口述的“亲见刘鹗为王懿荣医病并首先发现从鹤年堂药店购买之甲骨上刻有文字之经过”(下简称《唐记》),其内容与学界争论至今的甲骨文发现之“10余种说法皆不相同”。
经笔者查阅,获知此一重要史料最早是由李勇慧在准备博士论文、整理王献唐后人提供的资料时发现,并先后公布于《王献唐研究》(博士论文,2011年)(1)参见李勇慧《王献唐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380、440页。李勇慧在正文前的论文摘要中特别写道:“本文并以王献唐为主线,通过《王献唐日记》、师友书札等反映史实之考证,溯源析流,纵横比较,左右参证……本文还纠正或是补充学界的一些错误甚至是片面的认识,有些问题或看似与其没有直接关联,如胡适关于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时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945年日本在济南的受降时间等。”(论文第2页)另在其《一代传人王献唐》(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的前言里,李勇慧再次发表了相同表述(见该书第16页)。[3]、《王献唐著述考》(2014年)[4]、《王献唐年谱长编》(2017年)[5]。这条相当可靠的文献史料,无疑应该成为影响并修正“甲骨文发现学术史”的一个重要发现,引发相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进一步研讨。遗憾的是,相关日记的研究仍很欠缺。
李勇慧论文《再论甲骨文发现始末》为递交于2013年12月底举办的“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究会议”的参会论文,纸质发表于2016年6月出版的该会议论文集。故将其中有关甲骨文发现的新史料和评述转引如下:
(《李文》先对王献唐及其日记做了如下背景介绍:)“王献唐(1896—1960),山东日照人,原名凤管,改名管,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是“远绍乾嘉诸儒,近承清末名宿,益之以科学观念,辅之以实地勘查,集目录、版本、校雠、训诂、名家于一身,熔文字、声韵、器物、古史之学为一炉”的大家学者,“被著名学者张政烺、夏鼐誉为‘山东近三百年来罕见的学者’”。“尚未公开面世、尚未出版的《王献唐日记》”现存“八种四十九册”,其“内容体例、写作笔法,与‘晚清四大日记’之一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颇为类似,所记内容包括:治学札记、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是王献唐一生最重要时期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寻知求识、友朋往来等的真实记录”。
(关键段落:)“在现存《王献唐日记》第六种《五灯精舍日记》中,有《记甲骨发现始末》一篇,文曰:‘安阳殷墟之甲骨,初时土人得之,多售于药商,为药中龙骨,发现之人皆知为王廉生。日昨,周汉光来访,谈及此事,彼时适在王氏寓中居住,廉生其外祖也。廉生染病卧床,刘铁云深知医药,延之诊视,从鹤年堂药店购归药后,铁云正在王氏室中坐谈,见即取而检视,内有龙骨一味,纸启翻检,忽见残片上刻有文字,历视数片皆然,惊告廉生。廉生从病床扶起,相对研求,以为古文字,灯下执玩,不知病尚在身也。时知为鹤年堂物,即夜派人往问,云从河南购来,尚有一大袋未研碎,廉生乃倾袋得之。后复派范贾至安阳大事搜罗,数千年淹没之殷墟文字从而发现矣。’”
“该稿写于1935年12月28日,现为手稿本,从未刊行。文中所记史料来源,乃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甥孙、烟台周汉光(字允溥)口述。王献唐《五灯精舍日记》(1935年12月27日)记曰:‘允傅来访,五时半偕至东鲁饭庄晚饭,饭后同访坚叔,九时回家。’次日,王献唐于该日记中作《记甲骨发现始末》,记载了周汉光亲自向王献唐谈及其寓外祖王懿荣家时,亲见刘鹗为王懿荣医病并首先发现从鹤年堂药店购买之甲骨上刻有文字之经过。”
李勇慧并在文中有评述,现转引、再附笔者新注评于【】内如下。
第一,刘鹗为王懿荣医病时首先发现王懿荣用作药材的“龙骨”上刻有文字并告知王懿荣。【评:此关键点准确到位。《唐记》此处原文为“廉生染病卧床,刘铁云深知医药,延之诊视”,据此,一则“夫人染病”等传说可以休矣;二则印证了刘鹗“深知医药”的史实(详论见后),于是“王懿荣生病自诊、自开药方”“刘鹗寓居王宅”或“拜访巧遇”等说法也可休矣。而注意到是刘鹗先发现甲骨刻字后“惊告廉生”则更加重要,因笔者还曾在《新论》文中提出过刘鹗可能更早开始收集甲骨文的线索,详论见本文第五部分。】
第二,经王懿荣与刘鹗“相对研求”,共同发现这些文字是古文字。【评:《李文》这个“共同发现”的判断,与笔者提出的“王刘联合发现说”不谋而合。《唐记》原文为“廉生从病床扶起,相对研求,以为古文字,灯下执玩,不知病尚在身也”,不仅符合一个当事人对亲见场景的描述,也为“中国学者发现鉴定甲骨文”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细节。】
第三,王懿荣用作药材的“龙骨”来自北平鹤年堂中药店。【评:出自“汐翁”等人的、甲骨来自“达仁堂”之类的不明京城街市方位的误说,和在此一问题上的诸多争论都可以休矣。】
第四,王懿荣在京城吃中药期间发现甲骨文后,又派文物商贩至安阳购买“龙骨”,该商人姓范,名字不详。【评:合情合理,也与明义士、罗振常的记载大致相同(详论见第四部分)。】
此乃甲骨文发现的通行说法“王懿荣在京城吃中药发现说”的又一史料佐证。但与通行说法不同的是,谈到刘鹗在发现甲骨文中的重要作用。周汉光作为王懿荣的亲属之一,不避谈刘鹗在甲骨文发现中的作用,为“刘鹗发现甲骨文说”提供证据,值得甲骨文研究者注意。而王懿荣哲嗣王汉章在其1931年发表的《殷墟甲骨纪略》一文中,未提刘鹗。【评:李勇慧这段评论难能可贵。不但王懿荣亲属周汉光在甲骨学已成显学的1935年如实道出当年实情十分难得,而且李勇慧有关新史料和评述,也体现了学术首重求真的高度专业素质。】
虽然周汉光是亲历者,但所述值得深入探究者亦有以下四点。
第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时,周汉光多大年纪?是否亲见该事,还是听长辈或王懿荣后人转述?【评:看来李勇慧也未查到周汉光的年龄、文化程度等生平详情(且周汉光的字,《李文》中说是“字允溥”,但随后所引《唐记》则为“允傅来访”,待考),这也是笔者试图反复查找而未得的重要信息。但周是亲眼“目睹”、而非“转述”则无可置疑,前有《唐记》的“周汉光来访谈及此事,彼时适在王氏寓中居住”的明确文字,后有蒋逸雪“方有龙骨,其甥周汉光检视”的错忆或错记(详见第二部分),都明确指出了周是在场的目击者。】第二,事情发生在1899年,距周汉光1935年向王献唐叙述此事时事情已过去了36年的时间,当时的真实记忆是否还在?【评: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亲历者正式忆述,情节具体、合理,且被文史大家郑重及时记载,加本文后面提及的多种旁证,故出大错的可能很小。】第三,王懿荣是周汉光的外祖父,从法律角度上说周汉光不具有为王懿荣作证的资质,但周汉光所述又肯定了刘鹗在发现甲骨文中的作用。【评:此论与前评论相似,并借鉴了现代法律常规对证人资格的要求,不仅十分重要,也值得史学界重视以提升科学论证质量。】第四,从王文中所记事件经过来看,周汉光所述与汐翁《龟甲文》最为接近。【评:并且还与琉璃厂古董商及明义士记载大致相同。但《唐记》的可信度和重要性,与“汐翁文”不可同日而语(详见第二部分)。】
二、《唐记》具有合理性,并佐证“王刘联合发现说”
在笔者看来,李勇慧发现的这一新文献史料、即《唐记》所载的这篇《记甲骨发现始末》,应是自甲骨文发现至少120年以来、在刘鹗《铁云藏龟·自序》之后,关于“中国甲骨文学术发现”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最珍贵、最可信、最合理的史料文献。下面就此三方面论述如下。
1.其珍贵性在于:在可能性最大的“甲骨文学术发现”现场——北京王懿荣宅(尚有其他可能,详后)、已知具学识的三位目击者中,王懿荣、刘鹗二人去世过早且至今都未见有任何记录此一事件的文字留存(虽然有迹象是王氏口头告知了相关古董商、刘鹗告知了个别好友,详后),故周汉光的即使是36年之后的此一口述回忆笔录,极有可能就已成为存世至今的、关于此一重要历史性事件的唯一目击记载。
2.其高度的可靠性/可信性在于:之前关于甲骨文发现的各种说法,基本上都来自早年估人和古董店商们的口耳相传,或经过学者、文人对这些传说的转录,甚至是加入了演绎、想象的误记(详后)。但《唐记》这段文字记载,不但叙述者周汉光是现场目击人、和王懿荣的亲属家人(虽生平待考,但祭酒门庭的甥孙至少也应是读书人),而且关键的记载者是专业素养和信誉度都极高的王献唐(忆述如有疑点,应会当面问清),文字记录时间也是谈话后仅一天,时期也处于王献唐39岁的盛年期。再加上此一文献是以原始日记手稿的性质存世,是在几无扰动、未加编纂的难得状态下保存至今。再从其实际内容来看,虽然具体细节丰富,但没有夸张、想象之类的词语和硬伤。金石考古学家的严谨信誉加持,使其可靠性和可信度明显高于以往各种性质的史料(详后)。
两三年前笔者也曾读到过蒋逸雪于1944年发表的《〈老残游记〉考证》[6],但仅注意到其前言有回忆王献唐在重庆畅谈《老残游记》“悬泻不竭”的记载。此次从《李文》中意外看到,蒋逸雪居然在同一篇长文的结尾还讲到了王献唐也曾谈及甲骨文发现(2)参见《老残游记考证》第73页”余论“部分,蒋逸雪相关全文为:“藏龟之拓,影响于近世学术尤巨。初,懿荣居京师,妻黄氏病,方有龙骨,其甥周汉光检视,乃有刻纹之甲片,不与常质同,命仆持问铺。回言无误,此药新由河南安阳运到,货极地道。闻于懿荣,懿荣亦疑不能释,亲往同仁堂(药铺名)查询。其所谓龙骨者,其形大小不一,上皆有刻纹,间合数小片成一大片,而形似龟板,其文字更若意义之可寻者,虽不能悉识,而断为古代书契无疑。乃罄同仁堂所有以归,并嘱代向安阳搜购,后亦续有所得。此汉光亲为献唐先生言者。”[6]73。但读后对这段文字可靠性的感觉,却与“汐翁文”类似。如李勇慧在其前述论文中指出:“蒋文与王文又有三点不同。第一,生病的人。蒋文是王妻黄氏,王文是王懿荣。第二,首先发现甲骨上有文字的人。蒋文是周汉光,王文是刘鹗。第三,购买龙骨的药店。蒋文是同仁堂,王文是鹤年堂。”[2]351蒋文虽也写明“此汉光亲为献唐先生言者”,但对比之下,内容错讹之大令人瞠目——除《李文》指出的上面三点之外,尚有其甥孙“(周)命仆持问铺”“懿荣亦疑不能释,亲往……查询”“谓龙骨者……上皆有刻纹”的不合情理之处,故其可靠性、合理性明显逊于《唐记》。究其缘由,王言于蒋时(1941)已距周言王时(1935)隔了五六年,于是凭记忆的闲谈比之当年的及时笔录就可能有意或无意出错;加蒋氏在聊天时又可能听错,之后在不很相关的文章中(该文主写《老残游记》、且蒋所记“吃药说”与刘鹗无关)写入时又可能忆错、记错。可见,如果不是直接、认真并及时记载的文字,仅凭记忆的二、三手笔记之类,即使是在学者文人之间的流转也难免各种大小讹误,更何谈在学养为人、处事风格都不可同日而语的商贾和三教九流之间!
综合而言,由于这篇忆述者、记载人、保存形式、文字内容都几近无可挑剔的史料文献的发现,长久以来基于道听途说的、归类于“非学术论作”[7]3的“吃药发现甲骨文”传奇故事,今日应可升级蝶变为中国甲骨文发现学术史的核心内容。
3.《唐记》内含的重要合理性在于:此一文献没有明显违背已知史实、或不合逻辑情理之处,并为“王刘联合发现甲骨文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刘鹗不再仅仅是因为最早公开出版了对甲骨文的鉴定、著录、考释/研究、和在《时报》上及时发布了“甲骨文发现公告”等确凿文字而无愧于“甲骨文联合发现人”之一[1]7、和笔者《1904年中国甲骨文发现公告之再发现》(3)参见任光宇《1904年中国甲骨文发现公告之再发现》,《文化与传播》2019年第5期,第72-78页。该论文经逐日比对、分析,详实确证了刘鹗率先在1904年7月至1905年1月借助上海现代媒体《时报》,以具里程碑意义的自撰告白《三代文字》121次向世人宣告了“甲骨文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原本有欠完整和确凿的中国甲骨文发现学术史应由此得到重要改观。[8],如今根据新史料中诸如“铁云正在王氏室中坐谈,见即取而检视,内有龙骨一味,纸启翻检,忽见残片上刻有文字,历视数片皆然,惊告廉生”的细节,他更是第一位亲眼注意到“带字龙骨”——即甲骨文的中国学人,并且由于“廉生从病床扶起,相对研求,以为古文字”,他无疑还是参与最早甲骨文鉴定行为的两位学人之一。另一方面能够互相印证的,是“廉生染病卧床,刘铁云深知医药,延之诊视”的明确文字,有力佐证了刘鹗当年的医术和医名——关注过刘鹗的学者多只知他早年曾经尝试行医,但因“门可罗雀”告终;殊不知近年又有《刘鹗年谱长编》收入的数条来自《盛宣怀档案》(下简称《盛档》)的新史料(4)参见刘德隆、刘瑀《刘鹗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7-318页、及328-331页,有多处转引自《盛宣怀档案》的、与刘鹗医术相关的原始文献资料。所引为盛宣怀讲解中西医高下的信函中,尚有诸如“外国医学自哈斐(哈维)创言回血管而后,形体始烛其微,医学始有要领”“中华医理虽优,而学者无人, 药物多伪, 行之殊欺, 似此尽失先圣辨症用药之理,安能与泰西争能”之类的高见,更有“不必鄙西医而不言,不必弃华医而不论,中西皆可取也”的明智结论,与百多年后今日中国“中西医结合互补”的方针高度相似。[9],证明刘鹗不但深谙中医、对西医也有相当独到的见解,且医术颇得当时已是朝廷重臣的盛宣怀(1844—1916)的信任。例一,“《盛档》第078210号”记录了刘鹗在1896年10月(九月十八日)因得知盛宣怀“示洋药可以速効,并欲亲试多时,以较中外优劣”而致函盛氏,分析讲解了中医和西医各自的优劣。该信长达1400余字,且多有明察精到之论,如“医者当学古圣气化、标本之理,操之渐熟,兼看泰西所译之书(如《形体阐微》《割疮全书》《医学入门》《万国本草》-原注),细究其真,默会贯通,出医自有把握,不必效欺世术误人误己也”等,最后医嘱盛氏“大人身任枢机,不惟千万人属望,实为中国千万世风气转移,似不宜身试未达之药,以较区区医药之所宜”。例二,刘鹗还曾正式出任“津海关”官医多年(待详考),在上盛宣怀禀中明言:“屡奉面谕,谓中国医学日废,理法尽弛……惟以数年荫庇,教养多方,所诊各衙署、各税关、各公馆,数年来幸无陨越。从此奋发黾勉,实力实心,或不至有负大人期望”。同时,他还论述西方医保经验并建议借鉴:“伏念泰西诸国,凡商董诸人,皆有医生保险,公司又设施医、施药等所,原以备时病、济穷苦;义至详,法至善也。伏查招商、电报两局,历年筹赈捐各项抚恤亦可谓恩义周至,第(但?)局中司事、小工、穷苦等人及轮船到岸遇有猝发等病尚无预备”(《盛档》第015117号)。随后他又为招商、电报两局建议拟出了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机构现代医疗保障条例《施诊章程》七条(5)刘鹗所撰《施诊章程》事无巨细,拟“造福并非牟利”“施诊不论贫苦远近”,惠及上海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下所有员工及眷属,应是中国向西方借鉴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早期尝试。查盛宣怀于1885—1886年即任招商局督办、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开始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监督;1896年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被授予“专折奏事特权”,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授太常寺少卿衔;1897年12月补授大理寺少卿衔。[9]329。例三,刘鹗于1897年6月30日曾“奉盛宣怀之命”赴汉阳为鄂省铁厂总办郑观应(1842—1921)出诊,数日后向盛氏详细汇报了“昨呈一禀,谅已赐阅。今晨再诊,郑总办清恙”,及“兹已拟用温通重大之剂,大约数剂可以病退”[9]331等语(《盛档》060437-1、063474号)(6)来源同上注《刘鹗年谱长编》,第331页。刘鹗致盛宣怀相关郑观应的第一函未见;第二函除上文中所引,尚有“惟不能酣睡,闻声即醒云云。细诊脉象,右手稍起,左手尚是细软异常”“各友皆有湿病,近日辄发。袁景升更甚……”等。第三函中,还有“入夜实不能寐,皆系白日烦扰之故。伊意中定欲返沪静养一月……如再发喘嗽,用温恐伤阴分,用清又难驱湿。且脉已经细弱。正气自廿余日病后已觉大亏,似非静养不可” 云云(《盛档》第063474号)。郑观应,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理论家、实业家、教育家,名著有《盛世危言》《易言》等。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同年入股轮船招商局。1881年后出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蛰伏著书后在1893年再任招商局帮办,1896年被张之洞委任为汉阳铁厂总办,1897年正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
综上所述,有原始文献证明刘鹗于1896—1897年间曾应邀为当朝重臣盛宣怀、能员学者郑观应看病开药。由此相推,两年后的1899年,王懿荣祭酒“染病卧床”之际因刘鹗“深知医药”邀其诊视,就极为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在《新论》论文中,笔者已运用预设前提的方法多方论证提出了甲骨文发现的“王刘联合发现说”:“就算王-孟(王襄-孟定生)在1900年或更早收购了少量甲骨,也无任何原始证据证明他们在1903年《铁云藏龟》出版之前及时、正确鉴定出了甲骨文的年代和意义,只有反证。而要确立甲骨文的发现,前述三项现代科学发现必要条件不可或缺……多项原始证据各自独立,相互印证、互洽,形成了一条完整、坚实的证据链。因此,全面、严格来讲,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并正确将其鉴定诠释为中华文明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古文字,且及时借现代出版媒体多次向世人宣示这一重大发现的人,是刘鹗。” “间接证据最多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而不涉及鉴定甲骨文……将历史、国情、情感因素综合迭加起来,‘王懿荣发现说’至今能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传播,其来有自,情有可原。而联系到本文开头所述、即有确凿实物加正确诠释才能获得完整的发现人资格。可见最好的两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将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发现事件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1]4-6
现有了李勇慧对《唐文》的发现,有了甲骨文发现现场目击证人的口述和史学大家王献唐记载,甲骨文发现新说“王刘联合发现说”又得到了有力可靠的新佐证,“刘鹗应为甲骨文发现人之一”的论据已可说是铁证如山。此新证、新说如可获学术界论证认可,中国甲骨文发现学术史就更可以“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解决”,中国学人也“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为何“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1]6。
另外,笔者又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一篇待出新书的书摘,作者殷作斌先生在其中披露了一条前所未见的甲骨文发现过程信息,特摘录如下:“笔者曾祖父殷高良(1851—1914)是私塾先生,其从教学馆距名震江淮的兼职中医师刘鹗在淮安的常住地(即今‘刘鹗故居’)不远,他认识刘鹗和罗振玉亲家俩……殷高良还常求刘鹗看病。殷高良在留下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大意,因原件由当校长的家兄殷作超保管,毁于‘文革’,原文和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予问及藏龟刷龟文事,铁云先生侃侃而谈。言他己亥年惊闻恩师文敏公回乡料理完其弟丧事回京身子不适,急往探望把脉开方,他发现其家人自鹤年堂抓来的中药中,龙骨上有契文,甚觉奇怪,即呈恩师,文敏公亦惊奇。翌日,文敏公备轿亲往药店一探究竟,遂作出向京师药肆广为高价收购“带契文龙骨”的决定。后有范姓估觅得十二版送王府,恩师推断是篆籀之前的殷商占卜文字。庚子岁范姓估、赵姓估又陆续挟千余片,文敏公均厚价留之。详加研究。时义和拳乱起,文敏公怕有失,密运部分宝贝藏淮安,嘱铁云先生代为保管。文敏公殉难后,壬寅年,其哲嗣翰甫(汉辅)售所臧,清公夙债,龟板千余片,铁云先生悉得之,遂据此成《铁云藏龟》,成书过程中,得亲家罗振玉大助。’后来笔者发现笔者曾祖殷高良遗存所记与淮安民间传说甚合。可见,1931年北平《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汐翁《龟甲文》所记为真。”(7)殷作斌《关于定发现甲骨文为四个并列第一人的建议》见“京兰传媒”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7日推送。此文主张“王、刘、孟、王襄” 并列发现甲骨文。文末附有说明“本文由作者待出版全一册专著《殷代史·卷一〈考古学揭示的殷代文明〉·第一章〈殷代系统的文字——甲骨文〉》的部分内容节选压缩而成”,其作者简介是:殷作斌,1941 年生,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南禄乡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曾任工程师、厂长、并任教于淮阴工学院等院校。退休后从事中华殷商传承文化的研究工作,有《殷代史六辨》《朐阳殷氏宗谱》等著作。据《殷代史六辩》导言,其曾祖殷高良字显祖;其长兄文革中因 “遭批斗恐吓,连同高良祖留下的许多手抄本家史研究文稿和书法作品都付之一炬了”。[10]
笔者注意到,此文至少又提供了四个新的相关说法,值得继续追究:一是在淮安也有“殷高良常求刘鹗看病”;二是,刘鹗是主动地为王懿荣看病,“己亥年惊闻恩师文敏公回乡料理完其弟丧事回京身子不适,急往探望把脉开方”;三是在王家初见甲骨后,“文敏公备轿亲往药店一探究竟”;四是可能性较小的新说法,“义和拳乱起,文敏公怕有失,密运部分宝贝藏淮安,嘱铁云先生代为保管。”但十分可惜的是,此一珍贵原始文献的原件未能保存下来,经后人“忆述”的内容可靠性大减,凭回忆写下的内容难免会受到各种近现代甲骨学进展相关信息的影响,否则此“殷高良日记”将可与“王献唐日记文献”并肩而列,成为一项新发现的重要文献证据。然而,它至少仍可作为又一条独立于前述各条史料的新信息,再一次佐证了“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
三、明义士、方法敛等多处来源史料的相关考析
在以往多篇论文中笔者已反复强调:凡涉及“学术发现”,正确且及时的“学术鉴定”就成为发现的关键前提,不可或缺。“甲骨文发现”和“敦煌遗书发现”正是近代两项典型的重大学术发现,但因事件都发生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加之证据的缺乏及“爱国”的环境影响,导致中外几代学者专家对此一“关键前提”有意无意的忽视、错解或语焉不详,并由此造成此两个领域中百年以来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学术史重大遗案。
如“刘鹗最早准确鉴定、并考释甲骨文”这一基于原始确证《铁云藏龟》的事实,至今仍得不到学术界的公认,中国学界主流结论仍然是完全根据推测的“王懿荣鉴定了甲骨文”。除严一萍(1912—1987)曾有诸如“知其所重而定为殷人之物者,刘氏也”[11]、“识甲骨文字,当以刘铁云为第一人”[12]等明确论断外(8)参见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8年版。《新论》中的相关引述尚有:“严一萍更有明确论断……在‘释字与识字’一章中明确指出:‘研究甲骨,首重文字……识甲骨文字,当以刘铁云为第一人……刘氏不以甲骨文为业,只是举例而已。’”,在较著名的甲骨学史著作中,笔者仅见《中国甲骨学史》中稍有质疑:“说他(王懿荣)那时已知‘为商代卜骨’,在未确定出土地点及究明卜辞内容之前,恐难做到,应是溢美之词”;但同时自相矛盾、语义含混、莫名其妙地断言:“王懿荣首先认识甲骨文,这一点该是无可怀疑的。至于他怎样认出甲骨文的,那是次要的问题。”[13]
加拿大汉学家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1885—1957)应是早期收藏甲骨文实物最多的人(9)据《王宇信序》(载方辉著《明义士和他的藏品》,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相关文字为:“明义士以驻安阳传教之便,近水楼台,自1914年起就在小屯村收集甲骨文和其他古代文物,先后收集甲骨达5万片,成为一位最大的甲骨收藏家。”,也是最早记载并出版甲骨文发现过程的外籍学者。李学勤在一篇序文中说:“在这样丰富的藏品基础上,明义士对甲骨研究创获颇多,对殷商世系的探讨尤有见地,在甲骨学界早有公论”;“他手募的甲骨著录《殷墟卜辞》,1917年于上海出版,久已成为珍本。只有书的序言,有译文登在1928年《东方杂志》上”[14]1。笔者查到了这篇《东方杂志》所载《殷墟卜辞序》译文(题为《殷墟龟甲文字发掘的经过》),其中的相关文字为:“十五年前,有中国考古家王姓者,在北京杂货店买龙骨以为医药之用,于此等龙骨碎片中,其一刻有极精小之文字,其文字与向所藏之古钟鼎文字甚相类,因问其所由来,商人亦不知所以对,王乃独携其宝物以去,秘密察验焉。此可谓发明殷虚骨甲卜辞之第一人也。”[15]在1933年写成的《甲骨研究》中,明义士再记:“余既找到正处,又屡次向范氏和小屯人打听,又得以下的小史。今按事实略说一下……按范氏一九一四年所言:一八九九(己亥光绪二十五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字廉生谥文敏公)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10)见明义士《甲骨研究》(1933年版),齐鲁书社1996年誊抄影印本,第8页。在本书第12-13页,尚有明义士对美国宣教士方法廉(敛)1906年9月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初时文字》(又译《中国古代文字考》)第30页内容的转引:“一八九九年,(河南省)卫辉府附近,古朝歌城故址,有古物出现。(此即潍县范氏在山东不言正地殷虚,特言朝歌城。)据说发掘三千件。商人先到业京,遇义和团之乱,乃带古物到(山东)潍县,将一部分留存城中某贾手中。此人与著者相识,告了他,也借给他看,其余带往上海(或别处,售归刘铁云道台,这位学者用他本国(中)的文字著了一部书,并将他所有的标本墨拓八百片石印插入书中。” 虽然方氏将《铁》书所收录的甲骨拓本1058片错记为800片,但这是笔者所见外国人对《铁云藏龟》最早的文字记录。日本林泰辅自述的初见《铁》书日期为“1909年8月的二三年前”,故推断应比方氏稍晚,详见笔者2019年著《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以下为行文方便,有时会简称《新探》)。[16-17]
以上明氏记录中的“王买药发现甲骨文说”,应是范估或其他古董商由王懿荣告知的转述(详后),现已得周汉光亲见过程记载为证;但“可谓发明殷墟骨甲卜辞之第一人”和“王廉生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的结论,则缺乏当时没有、其后也未曾出现的确凿证据,仅可能是根据王氏声誉和他高价收购甲骨等信息所做的推断。有着现代土木工程学和神学背景的明义士[14]5由于历史机遇在甲骨考古上颇有创获,但在“甲骨文发现人”的判断上,也有不够严谨、轻信传言之误。
《东方杂志》所载明氏《殷墟卜辞序》译文的前端,笔者尚发现有一段“记者”关于甲骨文发现的介绍按语,措辞则比较严谨:“河南洹曲一带,在光绪庚子以前,便常有龟甲文碎片发见。当时得之者如下:王懿荣等虽颇引为宝贵,惟尚未能辨其文义。逮后转入丹徒刘氏之手,始有《铁云藏龟》之刊行。未几上虞罗振玉和海宁王国维等出,考释甲文事业乃大盛。”[15]43此“王懿荣等虽颇引为宝贵,惟尚未能辨其文义”一语,应更可反映当时的学界和传媒界尚未受干扰、只以公开出版物为凭的合理看法。
笔者尚在同期《东方杂志》中,查到另一篇著名学者闻宥(1901—1985)所作的甲骨文考证长文(11)参见闻宥《殷墟文字孽乳研究》,载1928年《东方杂志》第25卷第三号,第53页。同年闻氏尚在《民铎杂志》9卷5号发表了一篇“甲骨文的过去与将来”,笔者惜未查看到原文。查闻宥(1901—1985),字在宥,号野鹤,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县)人。先入震旦大学进修,后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工作,再后历任中山大学文史科副教授、教授,青岛大学、燕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等职。1952年后再任四川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直到逝世。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联邦德国德意志东方文学会会员。[18],开篇有更专业的表述:“安阳卜文既出世,为此学者凡数家:丹徒刘氏铁云,瑞安孙氏仲颂,筚路蓝缕,首启山林,犹未能洞悉幽隠也;上虞罗氏叔蕴,海宁王氏静安继之,训释文字,疏证史实,名篇巨制,络释贡世,而后此一学也,卓然成一新天地。”[18]53可见闻宥以学者的严谨,也将首先著录研究甲骨文的刘鹗明确列为第一位“为此学者”,而只字未见列入王懿荣。
除《新论》中提到的“早期只有董作宾、胡厚宣1937年的《甲骨年表》”等曾提及“刘鹗发现说”之外,1951年《科学通讯》对甲骨文发现和早期研究的表述为:“自清季该地(小屯村)滨洹河农田中,即常有甲骨发现。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甲骨文字始为丹徒刘鹗、福山王懿荣所注意。一九○三年,刘鹗以所藏甲骨文字选拓千余片为《铁云藏龟》六册。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等,相继都有著作发表,对于考证殷代帝系社会礼制古文字等方面,颇多创获,殷墟甲骨文字遂大显于世。”[19]可见1951年初的中国甲骨文研究权威机构,至少还把刘鹗与王懿荣并列、甚至放在之前,作为首先“注意”甲骨文的学人。
另据美国传教士学者方法敛(Frank H.Chalfant,1862—1914)于1906年9月在美国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字考》(英文)[20],和郅晓娜2011年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的方法敛致金璋书信140多通(12)参见郅晓娜《金璋甲骨的收藏始末》,《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4 月;第364页。书信内容反映了方氏虽然因缺乏中国古董知识被骗购买了不少赝品,但更可看出他对研究甲骨认真执着、竭尽全力的献身精神。[21],方氏早于林泰辅、罗振玉、孙诒让(孙诒让著《契文举例》虽作于1904年但在13年后的1917年才公开发表),已在著作中记有“据刘铁云说,公布龟骨刻辞,他实为当今第一人。他认为龟骨文字比现存所有铭文都更古老”,和“刘铁云认为‘虺父’是卜人的神秘称谓”等甲骨文考释探讨[20]253,255。在随后1907—1912年间的多通书信里,方氏又至少二十余次提及刘鹗,并多次详细讨论了《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考释得失,诸如:“他怀疑□=问(小图片显示为[现释甲骨文‘贞’]-笔者注),而我怀疑假设的‘问’的不常见的形式”“刘氏还说‘复’是‘第三次询问’,但我们没有在骨片上发现不断贞问”“‘巳’的许多形式也是有趣的,很奇怪,他们都被刘铁云忽视了”等等(13)参见苗双《方法敛的甲骨收藏和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5月,第73、100、106页。另值得注意和待考的是,此文的第三章尚逐一“列出了方法敛讨论研究过的163 个甲骨文字”,“考释正确”的107个,“有误”的56个。如考证基本准确,则方法敛作为一位初学中国古文字的外国文字学者,也应被列为与林泰辅至少同时的、在甲骨文研究初期一度对中国学者形成实际挑战的外国学者,虽然当时罗和方二人自己都并不知晓。(详见任光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笔者还发现,在苗文第56、67页的方氏书信中,他不但基本准确记录了《铁》书包含1057片甲骨,而且还具体记载了他如何得到《铁》书:“关于龟甲刻辞,刘铁云著录的书目全称为《铁云藏龟》,六本,还有四本为《铁云藏陶》。1904—1905 在上海出版。我是从作者刘铁云的一个朋友那里获取了这本书的,这个朋友以为这部书是不出售的。我认为作者在北京,更适合叫做‘Liu Tao T’ai(“刘道台”的音译-任光宇注)。”[22]73,100,106。这些都可与孙诒让在《契文举例》中多处讨论《铁》书中刘鹗的甲骨文考释的事实相并列,作为第三方原始证据,佐证笔者在《新论》中提出的另一新说:“刘鹗自序全文凡1467字,此类探讨具体辨识的考释文字至少有777字,占全文的53%,即一半还多”;“刘、孙、罗、王、董在研究方法上一脉相承”;“故笔者认为,谈甲骨文考释研究,言罗不能弃孙,说孙不可忘刘。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应被确立为迄今世界上最早考释并成功破译断识甲骨文的论文,并凭借此一开创性工作,刘鹗领衔罗振玉和吴昌绶,一同率先拉开了甲骨学史中‘考释研究甲骨文’的序幕。”[1]8-10
四、“王说”中“吃药发现说”和“经古董商发现说”的来源辨析
恭借吕伟达先生《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始末》一文[23](下简称《吕文》)所做的总结罗列,“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说”可再分为“王懿荣吃药发现说”和“古董商先送甲骨给王懿荣说”两大类,共有相关近/现/当代文献来源至少19条[23]7-9,其中“吃药说”来源七条,“估人说”来源十二条。
所列“吃药说”第一个来源就是著名的汐翁短文《龟甲文》(载1931年7月5日北平《华北日报·华北画刊》),此文加上标点不到330字,所描绘的发现场景与王献唐的日记记载大至情节相同。但其明显的转述加传说的随笔性质、加内容出现多处讹误,已如李学勤教授专文所指出:错别字四五处、将事件日期误说为1898年、刘鹗当时并非借住王懿荣宅、北京菜市口无“达仁堂”药店、五千余片甲骨并非都买自药店、外籍研究人只提“法日”未提“美英加”等,故此文此说一直被李学勤等诸多学者专家裁定为“离奇而不符合事实”(14)参见前注李学勤《汐翁〈龟甲文〉与甲骨文的发现》第1-3页。《龟甲文》全文为:“光绪戊成年。丹徒刘铁云。鹗。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文敏懿荣私弟。文敏病痁。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到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搰地得之。辇载衒粥。取直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惟药肆买之。云云。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计五千余板。文敏于次年殉难。铁云以被劾。戌新疆。遇赦归。到癸卯岁。乃以龟甲文之完好者千版。付石印行世。名日铁云藏龟。此般虚甲骨文字发见之原由也。藏龟行世。瑞安孙仲客先生。以数月之力。尽为之考释。箸契文举例一书。甲辰书成。于是学者始加以研治。今则甲骨日出不穷。治之者亦不乏人。法日二邦。皆有专门研究者。为我国古代文化上之一重大事件。世人所当注意也。”[7]。现在从“刘鹗在王宅先从龙骨上看到甲骨文”等主要情节无误来看,笔者推测此文应来自刘鹗的某位间接的、非住京城的朋友,也可能是刘鹗天津密友方若(字药雨,1869—1954)的朋友:方若是参与刘鹗多种收藏(包括甲骨文,更多是古钱币)的多年密友,刘初收甲骨时难免会亲口相告真实的发现过程。而非京城的朋友很容易把刘鹗曾经借住另一位宝(熙)祭酒的府第(15)参见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5页所引“陆树藩救济日记”:1900年“十月初四日到大甜水井与铁云畅谈(按铁云先生当时在京住东城大甜水井宝熙宅)”。错记为王祭酒府第,更易搞错北京药店的字号和方位。不太可能是刘鹗的直接好友,是因为作者把刘1908遣戍、1909死在新疆的史实说成了“戌新疆,遇赦归”再出《铁云藏龟》的齐东野语。其他的一些错误,也应是因为这位化名的“汐翁”者对甲骨研究较外行、且是从转述者听来之后再撰述之故。
《吕文》所列其他支持“吃药说”的第2条(明义士)、第4条(赵汝珍)、第5条(陈重远)、和第6条(沈念乐)的所说所记,都可能是王懿荣生前向个别古董商透露(范估、孙秋帆(16)经查孙秋帆(1859—1931),名桂澄。光绪五年(1879)进京参加已卯科顺天乡试而落选。经叔父孙虞臣推荐他进入琉璃厂名店清秘阁学徒。1884年后开始做翰林院、国子监学者藏家的古玩生意,1904开办 “式古斋”。曾于民国初期出任第二任京师古玩商会会长,积极运作合资购回国宝重器毛公鼎。可能是最早的亲聆者)、然后在业内口耳辗转相传的故事。第3条所引的罗振常语,笔者未能在《洹洛访古游记》中查到,如确有,也应是同一来源。第7条中的王宏立先生有云:“公(懿荣)生前与家祖父往来较近,因家伯父与王汉甫(崇烈)亦系良好弟兄。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因病发现‘龙骨’上的文字……”不知此王氏是否与王懿荣同族,如是的话则也可能追溯到前述目睹发现的王懿荣甥孙周汉光。于是可归纳出“吃药说”共三个来源,恰是分别来自刘鹗、王懿荣、周汉光这三位仅有的亲历者,他们早期大致的可能传播路径分别为:刘鹗-方药雨/殷氏/某友-“汐翁”;王懿荣-范/孙/京城古董商-明义士/罗振常;周汉光-王氏亲属(+王献唐-蒋逸雪)。
《吕文》所列支持“估人说”的十二条文献,来源都应可追溯到第2条的刘鹗《铁云藏龟·自序》(第5条的罗振常所述[24]5-7也应来自范估+《铁云藏龟》(17)罗振常在《洹洛访古游记》中的开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第一天即宣统三年(1911)二月十五日所记的文字中,就有“叔兄(指罗振玉,字叔蕴)……时方治贞卜文字,初据丹徒刘氏铁云藏龟,继复加搜求”;第二天(十六日)准备开赴安阳,又记有“遂收拾行箧,携《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册”;而罗振玉在《殷》书自序中也写有“文敏殉国难,所藏悉归丹徒刘氏。又翌年,始传至江南”。,且估人自然要说自己最先“发现”甲骨文;且因《洹洛访古游记》迟至1936年才公开发表,故影响小且晚)。因《铁云藏龟》是1903年最早由发现当事人刘鹗自行编撰、出版印刷,且同时刊有罗振玉、吴昌绶两位学者的序言(18)关于《铁云藏龟》最早版本是否同时刊载了刘、罗、吴三序,或只有刘自序等情况,尚难以确定,存疑待考;初步探讨参见任光宇《新论甲骨文的发现、研究与〈铁云藏龟〉》,《练祁研古——上海练祁古文字研究中心集刊(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28页。吴序提及了“铁云先生获古龟甲刻文逾五千片,精择千品纂为一编,以印本见饷”等,而罗序中的相关文字只有“至光绪己亥而古龟古骨乃出焉”。再则,罗、吴两序内容都可说是 “引古籍考证前所未见的甲骨应为周之前占卜所用”的专业论文,并无具体的甲骨文字考释。,故在当时具有最高的可靠性和权威性,遂被其后至今的几乎所有主流学者采信、引用,其影响之大之广,也已被无数史料和著作所印证(但影响主要来自不包括刘鹗自序的《铁云藏龟》(19)“很多学者从未见过该(自)序全文或从未仔细通读”,是《铁云藏龟》至今仅被定性为“著录”的主要原因之一,详见《新论》第四章,第8-9页。)。第1条的《潍县志》等地方文献虽也比较可靠,但基本都曾在二十至四十年代被各地方志编纂学者,根据包括《铁云藏龟》的最新出版资料修改更新。
笔者的《新论》中经过简单论证,曾明确主张多数现当代主流学者认同的“经古董商发现说”:“长久以来广泛宣传的‘王懿荣生病吃药发现甲骨文说’,其源头实际上只是报刊短文和民初流传于北京琉璃厂的坊间传闻,王家后人也没有认同,不宜用作信史写入甲骨学正史中,进而在各类媒体中传播。此说最多只可作为一种假说,包括刘鹗是王懿荣门生、先于王氏或在王宅同时发现甲骨文,也仅来自传闻和后辈的口耳相传(自刘蕙孙等),尚未见原始记录确证。”[1]7然而,由于本文前述李勇慧发现的王献唐记载,可靠的“原始记录确证”现已明确出现,故笔者也必须根据“确凿证据第一”的历史研究原则,改弦更张转以主张“王刘从中药中一起发现甲骨文说”。
至于此“吃药发现说”的最大疑点,既“作为甲骨文发现的当事人或当事人之一,刘鹗为何不在《铁云藏龟》自序中直言不讳道出发现的真实过程?”容笔者在下一章中继续探讨。
五、“刘鹗发现说”的线索分析和蠡测推断
如李学勤教授在前述的评汐翁专文中所质疑:“如果说王懿荣买龙骨一事尚有可疑的话,汐翁《龟甲文》的叙述就更为离奇了。按该文所说,龟板上的文字是刘鹗首先发现,是刘鹗拿给王懿荣看的。这一过程,完全不见于刘鹗本人1903年的《铁云藏龟·自序》,也没有其他任何材料依据。”[7]2王宇信也曾断言:“报纸专好猎奇以哗众取宠。一篇满是错误时间和错误地点的小文,本不足训……虽然刘鹗记王懿荣始购甲骨之年较一八九九年迟后一年,但并没有宣称他本人是甲骨的第一个购藏者。”[25]“我们认为,还应以学者早年记载为是。王懿荣收购甲骨,刘铁云《铁云藏龟》自序中曾有言及,恐非‘齐东野语’。”[26]这些质疑可以说在甲骨学界和史学界极具权威代表性,更是百年来“吃中药发现甲骨文说”难以被学术界公认接受的主要原因。从其重要性和复杂性来讲,也可谓是中国甲骨文学术史乃至中国近代学术史中的重大谜题之一。
本文前四部分的内容,尤其是对“李勇慧发现王献唐记载周汉光亲见甲骨文发现经过史料”的详细介绍和对其珍贵性、可信性、合理性的分析论证,应已基本解决李教授上述质疑中“买龙骨”的“没有其他任何材料依据”部分。但对于如果“文字是刘鹗首先发现,是刘(鹗)拿给王懿荣看的”,为何“这一过程,完全不见于刘鹗本人1903年的《铁云藏龟·自序》”的更大质疑,笔者的确也未发现可靠的直接证据来解答,只能根据几条相关的线索、加《新论》和另一篇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中所作的分析[17]22-35,尝试给出初步的蠡测推断。这些已有线索和尚待“小心求证”的“大胆设想”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重要线索和可能的真相、动机和原因、另外一种的可能,分别探讨如下。
1.重要线索的考证及推断:现存刘鹗日记中的“人为缺页”极可能与“甲骨文发现过程真相”有关。关于这条重线索笔者已在2018年《新论》一文中有简短提及:“本来刘鹗初次见到或购藏甲骨文的时间理应(比1902年11月5日)更早,至少要早上几天,但记录恰缺,据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27]记载:‘壬寅十月日记初一至初四日数页,被人扯去,内容不详。但从初五日记刷龟及初七日记王汉甫取款事推测,购让王氏藏龟,即是在十月初几天以内的事。’(20)见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01页。刘蕙孙(1909—1996)为(刘鹗第四子/罗振玉长婿)刘大绅的长子,早年曾随罗振玉、王国维、刘大绅寓居日本、上海、天津、北平,并曾留学日本。之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马衡专攻金石考古,再后任教于北平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建国后任福建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有《中国文化史稿》《刘蕙孙周易讲义》《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铁云诗存》《刘蕙孙论学文集》等。[27]101这个疑案很值得日后继续追究。”[1]6近来笔者再查《刘鹗集(上)》(2007)中编者刘德隆对《壬寅日记》所作的说明,有:“本日记根据刘鹗手书《抱残守缺斋·壬寅日记》原稿过录、标点……其中多有缺页”,其后列出了七月十四日(农历,下同)、九月初四、十月初一共三处出现的缺页[28]714;笔者又查新出版的影印版刘鹗《抱残守缺斋日记》(2018)[29],壬寅年十月初一至初四(10/30-11/3)四天的日记确实缺失;并且,九月二十九日(1902年10月30日)与十月初五日(11月4日)的两页之间,确有明显可见的、被撕去一两页后的残存页根痕迹!(21)参见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影印+逐页释文版),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54页。惜日记原本上没有页码,故无法断定确切的失页页数。(日记手写本原件现存编者处)[29]154再翻看同年七月、九月的另两处影印缺页之处,却没有类似的痕迹。这说明七、九两月日记中的缺页还有可能是因保存不当、装订不牢而脱落丢失,但十月初的四天内容缺页,则可肯定是有意的人为所致。
对此疑案笔者的分析推断是:刘鹗本来在此四天中的某日从王汉甫处买回了第一批甲骨,于是自然在当天日记里记下此事,并回忆了自己初见甲骨的情形——即三年多前(1899年夏)在王懿荣府第从中药龙骨中发现甲骨文的过程,具体内容应与前述周汉光所讲基本相同。在之后三、五天的十月初六日(1902年11月5日)刘鹗第一次得空仔细研究所获甲骨,于是就有了当天日记中的“迄今所见我国甲骨文史上明确记录甲骨文字的第一次文字记录”(22)此结论引自刘德隆《试论刘鹗对甲骨学的贡献》,1987年11月提交“首届刘鹗与《老残游记》研讨会”;后刊于《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第53页;再后收入刘德隆《刘鹗散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诸如“甲骨文发现”的任何重大历史结论,最重要依据应只能是确凿的原始文献,没有的话则只能是推断、假说。刘此文的论证和结论尚有:“陈梦家所引刘鹗日记的日期并非1901、实为1902年”,刘鹗“收藏甲骨当在6490片以上”,“刘鹗是最早考释甲骨文的学者”,“刘鹗对于甲骨学的贡献应给予充分肯定”等。[30]):“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23)同前注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第155页,随后一天日记中尚有“夜作《说龟》数则”,见第156页。[29]155,156但在之后,在刘鹗开始墨拓甲骨、准备出版《铁云藏龟》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于某“特定”考虑(详后),刘鹗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或在1903年初刘鹗携甲骨拓片到上海面晤罗振玉(24)关于罗振玉何时初见甲骨,笔者已在《新论》第六节“罗振玉‘1901年初见甲骨说‘应予更正”中再次论证,结论是罗氏不太可能早于1902年尾得到甲骨拓片(除非刘鹗在1902年尾得到王懿荣甲骨之前已发现并收藏了甲骨、又曾将拓片邮寄罗氏)。罗琨、刘德隆等学者也早已考证、否定了“罗振玉1901年见甲骨说”,究其来源只是罗氏的误忆、和刘鹗相关日记在1936年《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上最初发表时错将1902年标为了1901(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沿用了此日记的错误日期)。但长久以来,仍有不少学者持续相信、引用此误说,包括王宇信在《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2页等)及《甲骨学发展1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268页等)中,仍持续多次沿用此误说。并专门讨论之后,他们共同决定:隐瞒“刘鹗先于王懿荣见到、并一同发现甲骨文”的事实,在今后著作中都共同改持“王懿荣率先经古董商收藏甲骨说”。其后为持续隐瞒“吃药说”真相,在1908年刘鹗被捕、发配之前的某日,刘鹗自己特地将有相关记载内容的日记页全部撕去了(也存在刘鹗预先交代,或罗振玉在刘鹗去世后交代刘大绅撕去日记的可能)。
2.隐瞒真相的动机/原因。根据已有的线索,笔者推测刘鹗,或刘、罗一起,如此决定的主要动机和考虑是:为使三千多年“神物”的“古脆骨甲”避免“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罗振玉《前编》序中语),并在当时“特定境遇”下为使甲骨文发现得到中国学界和社会尽快的认同、保护、研究,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布此一重大学术发现的发现人为当时金石学权威学者加最高学术官员王懿荣。这个当时“特定境遇”的含义,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重要因素:社会状况、科举出身、学术水平。
如笔者在《新论》和《新探》论文中所指出,虽然刘鹗很早就开始收藏和研究金石,“罗氏于1917年对二十年前的回忆,亦明言:‘少好古器,贫不能致。三十(1896)客春申江(上海)……亡友丹徒刘君铁云有同好,聚古器数十……每风日晴好,辄往就观,相与摩弄或手自拓墨,不知门外有红尘也”[1]12,但在“1903年末出版《铁云藏龟》对甲骨文进行鉴定和初步考释之后,刘鹗自己并没有再接再厉,罗振玉也没能给予及时的学术跟进。除了风雨飘摇、烽烟四起的环境及个人事业、仕途、谋生等因素造成的干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人都颇具自知之明,他们在期待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科举制度培养的传统中国学者中,有卧虎藏龙之‘四方君子……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刘鹗《三代文字》告白中语)”,深信“斯书(《铁云藏龟》)既出,必有博识如束广微者为之考释阐明之,故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序》中语)“清朝科举大约三年一科,全国平均每次就能考出满腹经纶的几百个举人、一百来名进士。而刘鹗和罗振玉的出身仅是秀才级别,没能中举,遑论进士。虽然晚清时的科举出身已不能代表真学问的高低,甚至对新学还有消极影响,但在学术领域里,传统的出身观念给刘鹗、罗振玉的无形压力仍是不容忽视的。回望当年,即使身为新学领军人物的严复(1854—1921),在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后、甚至在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前后,仍执着回乡四次赶考(皆落第),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佐证。”[17]22-23
之后发生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刘、罗当年如此考虑绝非杞人忧天。《铁》书和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的自序虽都声明是“王懿荣首先发现了甲骨文”,但发表后仍“被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如章太炎、康有为等断然否定;日本汉学界的主力东京学者群、古玩家赵汝珍等也都认为甲骨文是逐利之徒的伪造。章太炎不但有诸如‘国土可卖,何有文字’的冷嘲热讽,更有诸如‘《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等学术否定,并贬斥刘鹗、罗振玉为‘非贞信之人’”;章太炎甚至还在《与罗振玉书》的公开信檄文中,“不但痛贬保皇派罗振玉的学术水平‘固当绝远’‘延缘远人以为声誉’,捎带表示了对‘孙仲容大儒’的不满,更将日本汉学界的新老学者几乎逐个点名训斥、嘲弄,可谓睥睨群雄,气势如虹。”好在罗振玉不为所动择善笃行,“扎实的学术成果源源而出”;后再加王国维的百尺竿头,才在1920年前后确立了“罗王之学”在世界范围的甲骨学上“二骑绝尘”的辉煌[17]23。
但在甲骨文发现之初,毋庸置疑王懿荣在声誉地位和学术水平上遥遥领先。如胡适曾经指出的:“古书有种种作伪的理由。第一……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轻,不见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31]王懿荣虽不是古人,但属学术名人、强人,故可预期如宣称“甲骨文的发现鉴定”始于王懿荣,其公信力、可信度、影响力都会大幅提升。这个预期虽因风雨飘摇的环境在初期未见大的成效,但在其后的百余年里,就不出所料地被几代学者公认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的事实所证明。
较具代表性的,如前述《吕文》[23]10、和近年张淑贤的博士论文《晚清国子监祭酒研究》中,都有一段几近相同的表述:“在发现鉴定甲骨文前,王懿荣已写有大量金石方面的著作。如《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六朝存石目》《福山金石残稿》《古泉精拓本》《石渠瓦斋藏瓦》等研究金石文字著述达30 余种。因身处京师,王懿荣与陈介祺、潘祖荫、赵之谦、吴式芬、缪荃孙、翁同龢、盛昱、张之洞、阎敬铭、张荫桓、刘鹗(此处且存疑-笔者注)等人,切磋金石文字之学的书信往来非常频繁,多至500 余封。”(25)张淑贤《晚清国子监祭酒研究》,黑龙江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0-131页。笔者尚未见王懿荣与刘鹗交往有任何确切的文字记录,故且存疑待考,也望见者告知。[32]然张文也提到“山东籍祭酒王懿荣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坚守,对戊戌变法的抵制”的史实,这不但造成了他对甲骨文发现“命秘其事”(王国维语)的守旧态度和行为,也应是他未及时留下甲骨文相关文字记录的重要原因(26)另据此论文“原国子监南学肄业生”陈曾佑曾在王懿荣麾下共事。在笔者另一论文《评议》(见末页注)中,此人在1906年任甘肃提学时因未能及时保护抢救敦煌遗书,后被学界责为“可耻甚矣”(第14页)。。《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未说王懿荣与甲骨文相关,但也肯定了他“与潍县陈编修介祺商订古文书疏往还不绝。潘文勤暨熟翁尚书咸推之为博学多识。于书无所不窥,而于篆籀奇字尤善悟……至购买书画古器,即典衣质物不惜,故官日崇而贫日甚”。然此书中还专门说到了王懿荣的著述:“所著率未就,仅《天壤阁杂记》一卷载江氏《灵鹣阁丛书》中。奏稿若干卷,别刊。”(27)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925);夏祖尧校点,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82页。另据本书后的“重印说明”:书中“各家的‘生平著作,无论已刊未刊,必尽载其中’”;“本书(1925年)出版前,曾经章太炎校订。”[33]282这与前述《吕文》和上述张文的王生前“已著/写有研究金石文字著述达30 余种”似有不合,实情应是王懿荣仅是“写有”了那些文稿,却仍依旧习未能将它们及时公开出版(28)另据唐桂艳《王懿荣刻书事迹钩沉》(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四期,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15页),王懿荣生前尚刻有自著“朱卷”/科举试卷八种,及1900年4月开刻、殉难后才完成、但未能正常印行的《四家馆课》一书,王为四位作者(王懿荣、张之洞、盛昱、樊增祥)之一。。
无论如何,可以推断,刘、罗在自己著作里都不提“在王宅药中发现甲骨文”的真相,主要是基于刘罗科举出身低、学术声誉和水平尚差、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考虑,应是比较合理的推测。且刘鹗既然在《铁云藏龟》中隐瞒“发现甲骨文”的实际详情,自然也无法道出如何与王懿荣一起“鉴定甲骨文”的具体情况,只能在自序中用切实的考证作出并宣告了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的最早学术鉴定。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王懿荣才是甲骨文的最早、真正或主要的准确鉴定者。因此在这一点上暂不细究(今后如无新资料也仍然难以确定),学术界如能尽快先做出“王刘一起发现鉴定甲骨文”、暨“王刘联合发现甲骨文”的裁决,仍完全不失为是一个真实、合理、公正、同时比现行推断说法严谨得多的学术结论。
刘鹗也可能曾经打算,在“甲骨文发现”被学界认定、引发重视、成为显学之后再公布发现过程真相也不迟。但不料《铁云藏龟》出版多年,特别是他的《三代文字》暨“甲骨文发现公告”长篇告白在文化界新锐报纸《时报》刊登了一百多次[8]74之后,预期的轰动和研究却迟迟未能出现(虽然已知仅有的回应、孙诒让的接力研究《契文举例》也可能及时寄给了刘鹗,但他曾否见到、回应,尚存疑待考[34]),直至1909年他以遣犯之身暴亡于边陲新疆。而可能知道真相的罗振玉,在1910年惊悉日本学者做了领先的甲骨研究、随即快马加鞭以“一剑封喉”(29)关于“罗振玉研究研究甲骨文缘起“真相的考辩、和罗振玉“一剑封喉”、王国维“再剑封喉”的论证详情,可参见《新探》第五、六章,第28-30页。开启罗王之学之际和之后,当事人老友刘鹗已身在黄泉,也就没有很大必要节外生枝、再去向公众费力揭示解说历史真相了。
3.尚有线索指向另一种可能:“刘鹗早年独自发现甲骨文说。”对此笔者在《新论》中也略有提及:“‘刘鹗发现说’至少还有两个辅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说法,尚未见学界关注。一是……(30)《新论》第二章提及了另一个“王懿荣去世后刘鹗在王家屋角再发现甲骨文”说,来自刘蕙孙《甲骨聚散琐忆》-《刘蕙孙论学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第365页)。另在刘蕙孙逝世前一年出版的《〈老残游记〉补编》中也重复了同一种说法,仅是将放置甲骨处“墙角“改成了”架上“(载《老残游记 全编》,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35页)。现因“王刘由龙骨同时发现说”已可坐实,故推测刘蕙孙所记似应为罗振玉/刘大绅为隐瞒真相的另一种说法。。另一种较弱参证,是刘鹗家族三代家仆李贵有‘刘鹗在河南(1888至1893年-原注;更可能是1897至1898年-笔者今注(31)笔者近期注意到,刘鹗于1888—1893在河南山东治河期间发现甲骨文的可能性比较小,较大可能为1897—1898在山西和河南,运作英国福公司与晋丰、豫丰公司合作开矿修铁路期间。刘鹗有著名诗句“百年经济起关西“等作于1897年夏秋间的山西,而晋抚胡聘之在10月25日批准的《晋丰公司与福公司办矿合同》中议定的“开办孟平泽潞诸属矿务”中的泽、潞二府[9]335,今查处于山西与河南交界地,邻近安阳。1898年6月光绪帝又批准刘鹗策划的《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的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前后他曾否亲身赴焦作/豫北待考。另据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的《民间影像(第八辑)》载《1898,一位美国工程师的山西之行》[35]图文,美国矿师威廉·肖克利(1855—1925)“热衷摄影……在中国前后有三年,期间到各地勘测和旅游,到过北京、上海、山西、内蒙古、河南”;“1898年他被任命为英国福公司(The Peking Syndicate Ltd)在山西的总负责人,对山西南部的煤铁矿和冶铁业进行了长达三个半月的细致勘测”;并附有照片“轿中的刘鹗和一旁站着的意大利人萨比奥内”[35]12和其它照片二十多张。刘鹗当时任福公司中方经理,与资方英意人交往频繁,但照片中人与刘鹗相貌相差较大,存疑待考(目前已发现这些照片都应来源于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的影像资源数据库,链接:https://archives.lib.duke.edu/catalog/shockleywilliamh)。再则,胡厚宣尚在1950年的著作中提及何天行、卫聚贤曾转述马衡所言,军人赵守钰在山西离石县造路时挖出过甲骨文并赠送了样品;但胡厚宣之后再向马衡调查核实时,二人都认为赵言甲骨出自山西“并不可信”[36]。[36])从中药龙骨中发现甲骨文’的说法,由刘氏后人刘德馨转述。但因讲述者无学识、与后辈闲聊很可能记错年代,更因为没发现刘鹗自己的相关文字记录,故只能将其中一些场景,如刘鹗曾关注龙骨药渣、曾去药店调查收购等,作为一个独立于‘汐翁说’的参考资料。”[1]5如今有了本文前述的周汉光所述王献唐所记可靠史料,因传闻转述而带有缺陷的“汐翁文”就可成为独立于“王献唐文”的第二方证据,而上述的“刘德馨转述李贵所言”虽也因仆人闲聊的错记而有缺陷,也有着可作为独立于前两项证据的第三方辅证线索的参考价值。
此一“大胆设想”之说如能在今后被可靠的史料“小心求证”,则甲骨文发现过程就又可能成为:刘鹗因精通医道、不时为患者开方子早已遇到过“龙骨”这味药,且在19世纪末期河南一带药铺出售的“龙骨”上发现了疑似古文字刻画,以他所具备的金石学学识随即判定这应是“史籀以前文字”,并开始注意收集,只是在洋务繁忙中未及细究。随后恰在1899年夏遇到了为王懿荣诊病、开药的机会,便特意在所开药方中包括了这味“龙骨”,于是就发生了在王宅再次“巧遇”带字龙骨、并与王懿荣一起当场鉴定甲骨文、亦暨“周汉光忆述王献唐所记”的1899年“王刘联合发现甲骨文”的历史性事件。
早于1899年发现甲骨文的线索,还有胡厚宣以专文《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讨论的“蒋玄佁发现陈寅生跋记胡石查所拓1894年甲骨文拓片”。可惜原始物证未能面世,蒋文亦未曾发表,故胡厚宣认为陈氏“所记年月可能就不像考据家那样确切……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证明……(胡石查在)1894年,已经辨认出了甲骨文字,并且已有收藏”[37](32)详情参见杨末君《陈寅生与甲骨文——陈寅生收藏过甲骨,年代不一定比王懿荣晚》,《艺术中国》2020年第12期,第77-83页。胡厚宣《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载《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993年10月出版;笔者未能找到全文,引文转引自杨末君文。胡石查(1831—1902),名义赞、字叔襄,1872年举人,古钱、金石鉴藏家,精墨拓,与潘祖荫、吴大瀓、王懿荣等都有交往。陈寅生(1830—1912),名麟炳,北京琉璃厂铜刻名家、古董商。。此事也应予以继续追究,然可能较大的情况应是:带字甲骨虽然确曾在庚子年前的京城收藏小圈子中秘传,但旧派文人“秘藏私赏”的传统陋习导致了当事人们沉浸于自得其乐,没能及时研究并留下确切记载、更没能及时出版公之于众,遂使他们与此一重大的“现代学术发现”失之交臂。
六、结语
如笔者在《新论》绪言中所说:“甲骨文的横空出世已被列为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首,甲骨学的兴起也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这一重大发现,恰巧发生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故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难免混杂着某些传统观念习俗和一些非科学论断。尤其是关于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的历史,不少关键环节上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处于悬案状态。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界面前,在甲骨先驱尽瘁而逝一个世纪之后,在“新时代”领导人给予特殊重视、亟需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这笔糊涂账的延续越发显得与时代脱节,也与今日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相失谐。”[1]1
从另一方面来看,“甲骨学已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唯一的、从发现创立到发展壮大都由中国人主导并持续领先的、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现代学术领域”[17]33。故对于这一重要领域学术史的任何新说、修正,也应由中国学者作出慎重讨论、辩证、裁断,达成共识并公之于世界学林。因此,综合本文前几章所述,笔者在此谨向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甲骨学界提出如下初步建议。
1.针对前述李勇慧发现的、周汉光见证王献唐记载的“甲骨文发现现场情况”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合理性,尽快组织学者专家及时做出专业验证、鉴定,正式列入中国甲骨文发现学术史。
2.将《新论》及本论文提出的“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连同“刘鹗开启甲骨文考释暨‘甲骨学’说”“1904年《三代文字》告白暨《中国甲骨文发现公告》具有中国近代学术转型里程碑意义”等相关议题(33)《新论》除提出“王刘联合发现甲骨文说”外,其它新说和议题尚有“1904年多次刊登于《时报》的刘鹗《三代文字》告白应确立为‘中国甲骨文发现公告‘、并具有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里程碑意义”(参见论文 [21]);“《铁云藏龟·自序》应确立为最早成功鉴定和考释甲骨文的论文、暨甲骨学的开端”;“罗振玉’1901年见甲骨说‘应予明确否定”;“对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应予质疑”;“建议1899至1928年的‘甲骨学草创期’应更名为‘甲骨学的开创奠基期‘”等。,作为系列正式研究新课题立项(在此也借机就另一领域的重要学术新说——“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之‘叶昌炽裴景福联合发现说’”一并提出相同的立项建议),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展开相关论辩、论证,并对连带的诸多“存疑待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求尽早、尽可能彻底解决百年以来留存于“甲骨学”“敦煌学”等举世瞩目学术领域中的重大疑题悬案,以期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实质性推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