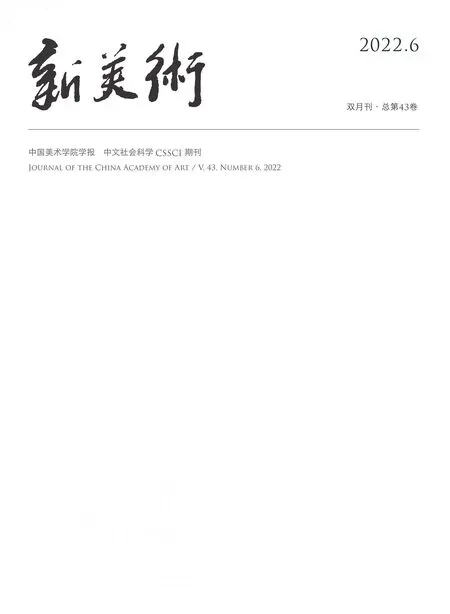郭宗昌《金石史》乾隆以前刊本考
王文超
关中学者郭宗昌(?—1652)所著《金石史》为明末清初极重要的金石学著作。《金石史》明末有抄本流传,所见最早刊本康熙二年(1662)的付梓缘于郭宗昌晚年同乡挚友王弘撰与刘泽溥的帮助。
王弘撰(1622—1702),陕西华阴人,字文修,又字无异,号太华山史、鹿马山人、山翁、丽农老人、天山丈人等,其居又称砥斋、待庵。康熙十七年时荐博学鸿儒,病辞不就,与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禛等诸多名士交善,康熙初被誉为“关中生气之领袖”1[清]颜光敏,《颜氏家藏尺牍附姓氏考》,《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 册,第57 页。。刘泽溥,生卒年不详,字润生,顺治九年(1652)进士,与王弘撰有“姻友”2王弘撰为刘泽溥母亲去世曾作《刘氏葬礼记附诗》,称“姻友刘君泽溥”。在二人通信中,亦提及“前奉面言,弟即如约,而亲家乃不尔,岂信于朋友者然耶?”[清]王弘撰,孙学功点校整理,《王弘撰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6、919 页。关系。
一 《金石史》康熙二年本相关问题考
《金石史》在明末至清初顺治间有稿本流传,惜郭宗昌逝后其家人并未有保存。刘泽溥言:“入都从民部张尔唯饮,言及《金石史》之亡也,而张公曰‘吾能存之’。亟观之乃习见本也。”3[明]郭宗昌,《金石史》,《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第39 册,第465 页。此当是流传常见抄本。张学曾,明末清初画家,字尔唯,号约庵,山阴人,与曹溶、孙承泽、周亮工等友善,周亮工《读画录》中有小传。4[清]周亮工,《读画录》,《周亮工全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 册,第103、104 页。北京慈觉寺(旧称金刚寺)顺治十年(1653)立有《金刚寺次略记碑》,今存北京石刻博物馆,张尔唯书并篆额,时在京任户部清史司员外郎,可知书法风格与官方制度的倡导相契合。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有载:
江贯道《长江万里图》张尔唯学曾所藏。顺治甲午赴苏州太守任,孙北海、龚孝升、曹秋岳三先生偕王元照(王鉴)、王文孙(按:有作荪,即王鹏冲,其藏长垣本《华山庙碑》)于都门宴别。各出所藏名迹相较,诸公欲裂而分之。尔唯大有窘色,北海集古句戏之曰:“剪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一座绝倒。5[清]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7 页。
张尔唯顺治十一年(1654)赴苏州任知府前一直居北京,与孙承泽交往颇深,《庚子销夏录》同样有此宴别相关记载。6孙承泽相关记载在《庚子销夏记》中“巨然《林汀远渚图》”条。[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1 册,第22 页。刘泽溥亦有言与张尔唯相聚饮的前因:
辛卯仲冬,余别入都,壬辰初夏闻先生殁,痛苦数日。夜归,吊于家,哭于墓,即问遗书,其小阮能藏之,唯《金石史》亡矣。益深余恸。甲午又入都,从民部张尔唯饮,言及《金石史》之亡也。7同注3。
壬辰初夏即顺治九年,先生是对郭宗昌的尊称,知其逝,返乡奔丧。辛卯、甲午,分别为顺治八年(1651)、十一年。两年后刘泽溥入京,知张尔唯处有《金石史》后连抄二十日,赶在其赴任苏州前完成。8赵阳阳,《四库提要订正两则》,见《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年5月,总第195 期,第78 页中言郭宗昌稿本极为稀见,进而断定“来濬见到的《金石史》当是康熙二年刊本”,与其第77 页提到的“即如馆臣所论,则来濬此书也可能撰于清初顺治十七年《庚子销夏记》成书之前”矛盾,《庚子销夏记》作于顺治年间,与来濬见到《金石史》是康熙二年。
(一)王弘嘉、田薰、王弘撰同订康熙二年本
刘泽溥在北京二十日抄毕的本子被王弘撰在康熙二年携至南京刊刻,除此康熙二年本外,乾隆以后仍有几种重刻本传世。9郑璐硕士论文《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研究:兼论“关中金石圈”的形成及影响》,第三章第一节“《金石史》的版本和校勘”中以《四库》本对比《昭代丛书》与《知不足斋丛书本》有34 条的差异,以《四库》版本问题最多。惜未用康熙二年本,清代刻本的编撰体例源头即失去了,反而使些问题更加含混了。见郑璐,《明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研究:兼论“关中金石圈”的形成及影响》,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34—37 页。赵阳阳《明代书学文献研究》中有讨论“《四库全书》本之所出”指出四库本漏刻的诸多问题,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27 页。吉林大学藏康熙二年本《金石史》一册与诸多公藏单位公布的康熙二年本不同。此为上海画家张龢旧藏,封面有小篆“金石史”,落款“关中郭宗昌著,王弘撰山史刻。甲申秋七月得于海上,石园居士记”。此应是1944年张龢署签,钤印两枚,上白文“张”,下朱文“石园”。函套为后配。是书现为“金镶玉”式,纵27.7 厘米、半页横15.7 厘米,衬纸较原书上端出1.8 厘米,下端出1.4 厘米,原书尺寸可知为纵24.5 厘米、半页横15.7 厘米。其中数页有渗墨和墨色偏淡现象,后几页略有损泐,已作薄托修补。张龢善书画装裱,极可能是亲自修整为“金镶玉”样式,以便于保护原书。
今研究《金石史》者大都未寓目康熙二年本。我们现在看乾隆后的诸多版本在刊刻形式上与康熙二年本有较大区别,皆是依此校订后重刻而非复刻。吉大本首页“关中郭宗昌胤伯著”下有“王弘嘉玉质、田薰虞南、王弘撰无异,仝订”10郭宗昌,《金石史》,康熙二年刻本,叶一正。行文中吉大康熙二年本,皆简称吉大本。。此后所传诸本中均无此信息。首为王弘撰“序”,每半页六行,行十二字,手写楷书刻版(图1),康熙二年以后刻本皆王弘撰序为“金石史序”;吉大本刘泽溥作“金石史序”及之后的正文皆为略扁宋体,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图2)。此意已明,刘泽溥抄录稿本当为《金石史》作序,王弘撰笃于友情,加刘泽溥抄录之功,合此二事为“序”,而不言“《金石史》序”。另,吉大本未见有牌记、目录、递藏者批注等信息。

图1 吉大藏康熙二年本手写上版序

图2 吉大藏康熙二年本刘泽溥《金石史序》
同订信息中王弘嘉为弘撰三兄,字玉质,善诗文,通墨翰。弘撰年幼随父侍读时与三兄一起,而弘撰多有“狎邪之行”,亦是弘嘉杖勉规劝。弘嘉殁后,弘撰曾有言:“予自三兄逝后,无日不怆然于中,且自警自惧。故于庚戌元旦谨告先灵,凡一切逾分违理事,必不敢为,所以养身,非独自励,亦望我子弟共识此意也。”11[清]王弘撰,孙学功点校整理,《王弘撰集》,第955—957、558 页。《砥斋集》“三兄遗札跋”条又载:
予三兄云隐先生于读书学道之余,颇留心墨翰,虽规模古人,而得之天授者多。此其随笔残札,所谓不经意之书。从子宣(按:据康熙八年本《砥斋集》校,应为“宜宣”)装潢珍藏,请予题其后,志殊可取。12同注11,第832 页。
弘撰善书,精鉴赏,为侄子宜宣所藏三兄手札作跋,言“得之天授”方是理解弘嘉书法的笔性佳。
王弘撰、王弘嘉、田薰三人中,弘嘉、弘撰善书,二人俱为郭宗昌旧藏《华山庙碑》作跋,弘嘉以小楷为之,与此手写刻版序言书风极为接近。由图3 可与图1 对比,可见弘嘉同订《金石史》的功绩应是手书弘撰序。

图3 王弘嘉跋郭宗昌旧藏《华山庙碑》
田薰,字虞南,号雪崖,陕西高陵人,弘撰挚友。康熙九年弘撰游高陵时住田薰“汲古阁”,且拾得文徵明残卷,历五年“以还旧观”。13王弘撰所记在田薰处历五年而把文徵明画卷复得十之七八,看似雅事而弘撰言“此事虽小,可以喻大”。[清]王弘撰,《砥斋集》,见《王弘撰集》,第876 页。友情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弘撰《贺田雪崖进士序》中言:“戊戌,南宫之有试也。……于是,雪崖在白云司者五阅月,而始得以例假归,则取道华下,遍访诸故旧,为十日之饮。”14同注11,第791 页。序中同时记述了甲申之变二人相知相交同患难的友情,然田薰取得顺治戊午科(1658)二甲八十名,以假归乡,遍访故交,弘撰相伴十日。15弘撰书田薰父母合葬墓志铭,述及田薰甲申之变时与母避乱于华山谷中,与弘撰结邻,朝夕相处。同注11,第938 页。
田薰康熙元年任江宁府推官时为王弘撰在南京出版《砥斋集》,王弘撰子宜辅《刻砥斋集记》中言:“家大人读书之暇,间作诗古文词。癸卯(1663),田雪崖先生为刻之白门,曰《砥斋集》,文才数十篇,无诗。己酉春(1669),大人有昌平之行,携入都,汪苕文先生为作序,云刻之京师,实非也。”16同注11,第781 页。癸卯即康熙二年,白门即南京。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福建金石学者林佶手抄有《尧峰文抄》传世。汪琬《砥斋集》序中言:“王子既与予定交因出是集示予。”17[清]汪琬,《尧峰文钞》,《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277 册,第6 页。请序时王弘撰应与汪琬刚刚定交,而初刻文数十篇,无诗,康熙八年再版时已十二卷,序跋、碑铭、游记、传赞等体例完备,但仍无诗选录。汪琬康熙八年为《砥斋集》作的序,王弘撰并未使用,仅有同乡南廷铉序。18赵俪生亦言《砥斋集》的序仅见《尧峰文抄》,认为“此文(汪琬序)臭味,与山史迥乎不同,宜乎其不以刻入,而另倩渭南南鼎甫(廷铉)为之也”。赵俪生,《顾亭林与王山史》第二章〈王山史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第149 页。王弘撰刊刻《金石史》时,田薰正在南京为其出版《砥斋集》,亦或通过田薰联络《金石史》出版的可能性极大。
(二)王弘撰与周亮工的一封信
王猷定(1589—1662)康熙元年卒于杭州旅次,周亮工旋即为其《四照堂集》付梓,传为士林佳话。19王猷定,《四照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 册,第1、2 页。《赖古堂集》中卷十三亦收录《王于一遗稿序》,未有周亮工所写序言时间。见[清]周亮工,《赖古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36—541 页。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别号很多,最为人常称者为栎园雅署,时人多称其“栎园先生”。周亮工出身出版世家,所刊行小说在明末已有盛名。赖古堂便是其家族出版机构之一,亦有遥连堂20刘乾,〈试谈周亮工遥连堂所刻书〉,载《文物》1983年第9 期,第82—86 页。文中引杜浚与亮工通信,为黄济叔所注六书付梓请托之事,亦提及亮工为王猷定刻书之义事,以说明亮工热心为人刻书。、南京大业堂21明代万历间金陵周希旦、周如山的书坊名。相关刊刻书籍可参看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 页。、醉耕堂22陆林,〈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 期,第123 页。、苏州白水书坊等出版机构。
在王弘撰与周亮工交往过程中,有一封信札极为重要。信中既表达对周亮工出版逝友文集的崇敬,亦有牵涉《金石史》问题。现录信文如下:
《金石史》,皆胤伯所自藏秦、汉以来金石之文,各有评跋,卓然独得,绝不随人悲笑,行文亦自蕴雅可喜。弘撰浅学寡闻,窃谓可与《集古》《金石》二录,并传不朽。他著述甚多,其后人既不能为之广播流传,而友朋中又力不及此,弘撰每以此自恨,旋自愧也。先生为王于一刊《四照堂集》,凡有与于斯文者,无不感之欲涕。岂但于一衔环地下哉?今之世如先生者几人乎?殊可叹也。闻已扬帆,不及走饯,翘首江天,我劳如何。23[清]王弘撰,《砥斋集》,见《王弘撰集》,第921 页。
《清史列传》载:“康熙元年,部议复亮公佥事道职,起补山东青州海防道。”24《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20 册,第6575 页。康熙二年初前往山东,由沂水穆陵关入青州,同年十月已有山东沿海东巡之行。返程至城阳有《十月廿六日城阳寄冠五》四首,第四首后附注:“予以今春取道秣陵入青,随巡东海复逶迤由此返。”25周亮工,《赖古堂集》,第311、312 页。另,第309 页有周亮工前往青州途中《抵邗关迟汪舟次兼示吴野人》诗。其并不想前往青州任此职,乃是身不由己,其中之孤独、失落的心理状态正如诗云:“北去非吾意,依违痛定身。无风吹老热,待尔拂衰尘。”王弘撰〈《金石史》序〉言:“癸卯春,予来金陵。”26同注23,第878 页。信当是作于到南京后,此时已知周亮工前往山东,二人未及见面。
翻检王弘撰与周亮工相关文献,最突出的除此封信外,便是王弘撰为周亮工藏画作题跋,似二人交集并不多。27同注23,第833 页。薛龙春先生提供其于故宫抄录一封周亮工致王弘撰信札,从信文来看,周亮工见过郭宗昌为王承之《涧词》手书上版的序言。薛龙春先生认为此信应写于康熙二年启程前往青州前。从信文看亦应是故宫周亮工信在王弘撰文集中收录,时间是在得弘撰信之前,二人可能有一面之缘。王弘撰推崇《金石史》,又感慨不能广播流传,从信文看却似有意请托周亮工帮助出版,并未直言,尤其对周亮工为故友王猷定出版文集的敬仰,隐隐可见有欲效仿亮工之意。吉大本从前序手书上版及行文略显扁势的宋体字来看,品味明显高于市场流通的坊本,非厂肆商品书籍,而吉大所藏未有牌记,是否出自周亮工家族的出版机构,或周亮工联络出版并无直接证据。28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第888 页。其中“赖古堂”条列举了周亮工及其子所刻书目,未见《金石史》。此前多有研究者将《金石史》出版归于周亮工名下,皆由此信与周亮工家族经营出版引起。
正如王弘撰《山志》中有记述:“郭宛委先生,博雅君子也。与予为忘年之交。著书散佚,深可慨惜。予曏在白门,尝为刻行其《金石史》二卷。今略纪遗论,以见一斑。”29[清]王弘撰,《山志》,见《王弘撰集》,第652 页。“所纪遗论”为“有关万历援高丽抗倭事,严世藩父子轶事、王维《辋川图》,白居易《荔枝图》事、以及古器物及山林怪异诸事”30赵俪生,《顾亭林与王山史》,第149 页。。“著书散佚,深可慨惜”与同周亮工信中“弘撰每以此自恨、旋自愧也”可相印证,仍未提及请托周亮工帮助出版之事。
《金石史》康熙二年本应是刷本数量不大,这也是流传不广的原因。清初文集如,王士禛帮其兄王士禄出版《然脂集例》嘱托张潮“希惠寄三四十本,以为家藏之秘,且识雅谊也”。帮助门人张弨、林佶刊刻书籍后要求“敝门人林吉人《甘泉宫瓦图咏》,张力臣《焦山瘗鹤铭辨》《昭陵六骏图考》三书,亦求惠寄各数十册”31王士禛,《集外文遗卷》,《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第3 册,第2413、2414 页。。皆可映当时私刻本的刷本梳理数量不大,甚至不为商业性的几十本足矣。
应该说,王弘撰与田薰同在南京时《金石史》定版,此时《砥斋集》也将刊行,二书同一出版机构或田薰联络出版的可能性很大,田薰同定应源于此。钱大昕言“此书罕传”当是康熙二年本成书刷印数目不多。《金石史》缘自王弘撰笃于友情而付梓传播,乾隆以后又因王杰发现汪照旧藏本,钱大昕助推,使之再于士林中传播,多种版本陆续出现,可谓金石佳话。
二 乾隆本及以后诸版本相关问题考述
乾隆朝以来《金石史》有数种版本,较知名的分别为:源自汪启淑家藏抄本的《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第四集乾隆四十三年本、王杰据汪照家藏重刻本32汪照,字青,一字少山,嘉定人。与金陵王蓍增补周在浚《天发神谶碑考》,王杰于乾隆年间所寻《金石史》即汪照旧藏本。赵阳阳曾指出郑璐误汪少山为汪启淑,应是汪照,亦认为钱大昕作序的本子或因知不足斋本的刊刻而并未付梓。见赵阳阳,《明代书学文献研究》,第226 页。、道光十三年吴江沈氏刻《昭代丛书》本、光绪八年(1882)崇川葛氏刻《学古斋金石丛书》本等等。台湾《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中收录为《知不足斋丛书》本。33《石刻史料新编》采用《知不足斋丛书本》后附钱大昕序与《四库总目提要》,钱序乾隆丁酉(1777)为王惺园浙中刻本而作,提及“此书罕传,吾友汪子少山得故家所传,手录其副”。《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第39 册,第489、490 页。郑璐硕士论文《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研究:兼论“关中金石圈”的形成及影响》涉及比勘,以四库本、昭代丛书本、知不足斋本相较。本文所比勘与之重复处不再赘述。由此亦可见《金石史》在清代金石学鼎盛期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藏康熙二年《金石史》一册,索书号:己934 6082。托友人查询,知王弘撰序为宋体,“弘”已为“宏”,乾隆本无疑。有研究者对南京图书馆藏《金石史》描述:
南京图书馆藏康熙二年《金石史》,此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知不足斋丛书》本则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除每页行数与康熙刻本不同外,其他如每行字数、边栏、鱼尾等与康熙本全同,尤其是具体的文字,几无二致。唯宗昌之字“胤伯”,《知不足斋从书》本作“嗣伯”,康熙本作“允伯”。以讳字来看,此本当为康熙时刊刻而雍正时所印,挖改之字盖避近讳。34赵阳阳,《明代书学文献研究》,第228 页。
吉林大学亦藏有乾隆刻本《金石史》35笔者查询核对康熙本、乾隆本资料时,咨询吉大古籍部管理人员。据介绍此定为“乾隆本”,乃当时古籍部老师三十年前刚参加工作时改定,所据为避“弘”而未避讳“琰、宁”二字。,上下两册,白纸本。书封有以《曹全碑》笔法题签“金石史”三字。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上册目录首页钤朱文“高凌霨泽畬甫收藏印”;“金石史序”下钤朱文“豫生”、白文“家桐私印”两印;正文内“金石史卷上”下钤朱文“耿轩”小印。下册“金石史卷下”钤印两枚,为白文“家桐之印”、朱文“厢东居士”。原旧函套,马家桐隶书题签“金石史”,落款“乙卯元旦醒凡题”,无钤印。依题签及印章信息,此书为天津画家马家桐旧藏,后转至高凌霨。吉大乾隆本王弘撰序已改为“金石史序”,“弘”为“宏”,“胤伯”为“允伯”,王弘撰序亦非手写上版,与南图本描述一致。
校检吉大康熙二年本为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来看,南图本应与吉大藏乾隆本同,与康熙二年本无关,亦非雍正挖本,《知不足斋丛书》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黑口,无鱼尾,左右双边,亦是鲍廷博整体设计。清华大学藏本从图4、图5对比可知,与吉大所藏乾隆本的王弘撰“金石史序”第四行顶端“复”字上的边框皆有相同的小损,第一竖行倒数第三“卷”字右旁的乌丝栏亦同剥损,出自同版已无异议。另,清华本中《唐怀仁集王逸少书圣教序》后有一深蓝兼红色横截式印戳,此印迹是纸张作坊的标识,印时放到卷上结束处,未影响正文(图6)。36参见张宝三,《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载《台大中文学报》2012年第39 期。所以,吉大乾隆本、清华传康熙二年本、南图康熙二年本均为同一乾隆刻本。

图4 吉大藏乾隆本首序局部

图5 清华大学藏传为康熙二年本首序

图6 清华大学藏传为康熙二年本尾页纸厂印记
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言:“至康熙二年,其友王无异始刻是书于金陵,《四库书目》称为明人,似误。”37[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57 页。言简意赅地指出康熙二年本即是初刻本。然乾隆以后诸版本中以王杰征得汪照旧藏本,因钱大昕序颇为知名;《四库全书》本源于抄本问题较多,然诸多版本经重刻后校勘却已相对精严。
以吉大藏康熙二年本、乾隆本,与其他版本比勘,可知乾隆以后版本的精校处,择重点列述如下:
其一,康熙二年本称“《金石史》下”;乾隆以后皆为“《金石史》下卷”。
其二,康熙二年本为“郭胤伯”;乾隆本为“郭允伯”;知不足斋本为“郭嗣伯”。38同注34,第228 页。
其三,《夏衡岳赝碑》康熙二年本为“见塚而泣其先”;乾隆本作“见冢而泣其先”。第二则康熙二年本为“又”;乾隆本与知不足斋本均为“此碑”。康熙二年本“有文乍得斯人”;乾隆本为“乍得斯人”。
其四,《周武王赝铜盘铭》“阳冰遂所从得篆法抑又何也”康熙二年本与乾隆本同;知不足斋本“阳冰所从得篆法抑又何也”。
其五,《秦峄山铭》康熙二年本二则,第一则“元人摹宋张仲文本”,第二则遂改为“张文仲”(按:可知属笔误);乾隆本皆为张文仲。
其六,《汉司隶校尉鲁忠惠公惠峻碑》康熙二年本“□蚀不可读”;乾隆本“剥蚀不可读”。
其七,《汉曹景完碑》康熙二年本“攻桢中城四十日不下”;乾隆本“攻桢中城四十日”。
其八,《后魏鲁郡太守张君颂》康熙二年本“当曰笔与欧颜异也”;乾隆本“当由笔与欧颜异也”。
其九,《唐不空禅师碑》康熙二年本“其父乔之”;乾隆本“其父峤之”。
其十,《唐周公祠灵泉碑》康熙二年本“犹见下霁”;乾隆本“犹见下济”。
其十一,《唐少林寺碑》康熙二年本“崔㴶撰并书”;乾隆本“裴㴶撰并书”。
其十二,《唐大雅集王右军书吴将军碑》康熙二年本“止余□字”;四库本补为“一二十字”。
以上所知,乾隆以后诸版本明显校勘过,弥补康熙二年本不足,康熙二年本或为刊刻之误或为碑帖辨识有误,碑帖辨识之误如第十、十一条,显然乾隆以后诸本刊刻者以碑帖为依据逐字经过校勘。
三 余论
王弘撰建有“独鹤亭”,按《王山史年谱》至迟顺治十六年(1659)独鹤亭已经建好。39同注30,第136 页。鹤之由来即刘泽溥所赠。“独鹤亭”非志同道合友人,不得座谈其中,王弘撰言:
润生曏赠一鹤,弟搆一小亭居之。拟颜曰“独鹤”。此亭不肃杂宾,非吾臭味,不得座谈其中。非元亮、幼安之流,不以书此额。今以求足下,想当不拒耳。足下若自矜,谓弟仰书法之妙,则误矣。一笑。40同注11,第920 页。
此信息虽是独鹤亭书额请托郑簠,但与刘泽溥二人的情谊亦尽显。郭宗昌晚年过往最密的王弘撰、刘泽溥,自是为郭宗昌著述出版的最佳人选。41王弘撰在与郭宗昌的信中说“润生述近况”,说明弘撰和刘泽溥聊起郭氏晚年的一些情况。回顾郭宗昌《金石史》出版过程,可知康熙二年本即使在士人中流布也并非特广,王弘撰作“序”,刘泽溥作“《金石史》序”皆是各有所指。惜今所传康熙二年本未见有牌记,周亮工、周在浚父子也未有记述,应非周亮工帮助出版。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钱大昕为王杰欲在浙中刊刻的《金石史》所作序中言:“赵(崡)所著《石墨镌华》久行于世,而此书罕传。”42[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3 页。然有研究者对《金石史》诸版本中未见到钱大昕序的刊本,进而怀疑王杰刻本是否成功,实则《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三十九册中选用知不足斋丛书本的后面附有四库提要和钱大昕“郭允伯《金石史》序”刻本影印(图7),刻版明确,无再探讨必要。43同注34,第226 页。

图7 钱大昕“郭允伯《金石史》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