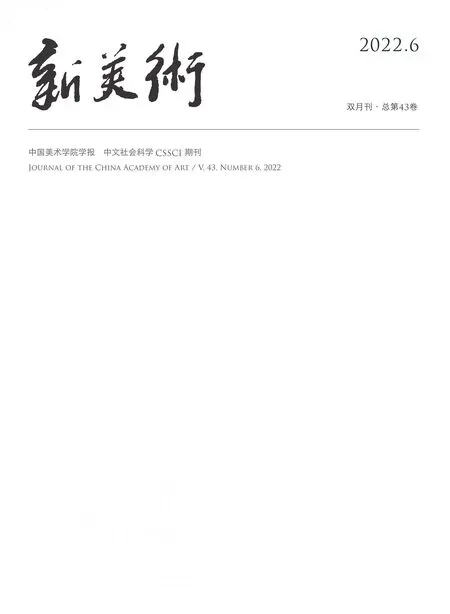十八世纪英国图书馆中的新古典主义
[英]维奇·科尔特曼
诚然,对于绅士与他的家人来说,最伟大的装饰品就是家中精美绝伦的图书馆。
——托马斯·科克,莱斯特伯爵一世,1715年
休·道格拉斯·汉密尔顿[Hugh Douglas Hamilton]在画作《诺斯特尔庄园图书馆中的罗兰爵士和温恩夫人》[Sir Rowland and Lady Winn in the Library at Nostell Priory,1767-1768](图1)中为观者展示这位英国贵族与妻子在翻修过的图书馆中的情景。正如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画作《安德鲁夫妇》[Mr.and Mrs.Andrews,1748-1749]中的麦田被视为地主阶级的象征一样,此画作中的图书馆也是贵族们精神产权的象征。图书馆中的家具代表着贵族精英们学习、旅行的阶层特权:家具由一整列排满藏书的书架墙(在此处形成了一种文学景观)和一只陈列在硕大书桌上的地球仪组成。这张书桌是由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公司以七十二英镑的价格供货的,这从侧面证明罗兰爵士赞助着当时最时尚、最昂贵的家具制造商,而放于书桌上的建筑规划图和其他建筑工具进一步表明这对贵族夫妇也是建筑赞助人。但这幅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生动体现了英国贵族对古代雕刻的趣味。图书馆里的书柜拥有长方体的柱子以及被古典雕像半身像覆盖的山墙,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古建筑的构建形式。尽管书柜上方的半身像无法辨认,但罗兰爵士身后的半身像与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位于画作最左侧的另一座半身像显然是古代艺术经典《梅迪奇维纳斯》[Medici Venus](图2)的复制品。半身像放置在由木雕牛头和叶饰花环点缀的复制品古董基座上。位于半身像的右侧是一幅粉笔画,其描绘的同样是《梅迪奇维纳斯》的头部与颈部,画像放置于椅子上并由罗兰爵士用手支撑着。

图1 Hamilton,Hugh Douglas.Sir Rowland Winn,5th Bt and his Wife Sabine Louise d’Hervart in the Library at Nostell Priory.1767-1768.100.3 cm × 125.7 cm.National Trust Collection

图2 Medici Venus.Late 2nd century B.C.-Early 1st century B.C.Parian marble,lychnite variant.153 cm.The Uffizi,Florence
虽然汉密尔顿的画作生动刻画了所有物件的细节,但它绝不仅是一幅用来罗列仿制古董装饰和家具的写实性画作,因为诺斯特尔庄园图书馆的空间和内容都被有意识地改变了。这幅画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就如由书卷组成的假门实则只是一排书架一样。虽然画作再现了由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设计的诺斯特尔庄园乡间别墅图书馆,但其所呈现的室内布置均经过艺术家巧妙的改造。比如,在真实的图书馆中,右手边的墙上并没有画中所示的两个山形墙书柜,而是只有一个(图3 右侧)。此外,引人注目的《梅迪奇维纳斯》半身像应该是与其他著名古雕像的石膏半身像放置于一处的,比如《美景楼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美景楼的安提诺斯》[Belvedere Antinous],以及沿着书柜檐口的第二座《梅迪奇维纳斯》半身像。汉密尔顿在1767—1769年间给罗兰爵士的账单上明确提到了“《梅迪奇维纳斯》半身像和两只包装箱,1.5几尼”。从1773年4月11日的一份备忘录来看,有一大批古董半身像系列直到这张画完成一段时间后才被纳入图书馆的布置方案。这份备忘录的标题为“致亚当先生的关于以下内容的信”,列出了“图书馆半身像”以及“雨水渗入副厅”和“塞林沙龙厅与其侧面的着色”等事项。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艺术家通过精心编排,将引人注目的《梅迪奇维纳斯》半身像放到了他为罗兰爵士和温恩夫人创作的图书馆双人肖像中。

图3 the Library at Nostell Priory
通过结合石膏半身像和《梅迪奇维纳斯》的粉笔画,汉密尔顿不仅描绘了这间新装修的乡间别墅图书馆,更是凸显温恩夫人作为爵士这位贵族赞助人最显眼的装饰品。罗兰爵士的法裔瑞士妻子,沃韦的萨宾·路易丝·德赫瓦特[Sabine Louise d’Hervart of Vevey]在画作中被塑造为“女性美的完美典范”,即梅迪奇维纳斯(图2):一个“不仅超越了佛罗伦萨的所有雕像,且超越了全世界所有雕塑”的形象。因此,诺斯特尔庄园图书馆的双人像绝不是一幅陈列式的或亦步亦趋的写实画作,而是一个笼罩在新古典主义图书馆再现创作中的幻想,这个幻想通过艺术家巧妙排布图书馆的仿古家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这幅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超越乡间别墅情景画的范畴。直到它在1997年成为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想象的乐趣:18世纪的英国文化》[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的封面时,突然从默默无闻的幕后走到聚光灯下。汉密尔顿为罗兰爵士和温恩夫人所作的肖像引发了人们对于图书馆空间的视觉想象,被用来与另一幅更出名的图书馆画作进行比较:那就是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所作的《威斯敏斯特帕克街7 号的查尔斯·汤利图书馆》[Charles Townley’s Library at 7,Park Street,Westminster,1781-83/98](图4)。当佐法尼创作这幅画时,汤利的古雕塑藏品是18世纪晚期伦敦的景观之一。苏菲·冯·拉罗什[Sophie von La Roche]在1786年访问首都时认为帕克街7 号是“拥有全世界最稀有、最昂贵装饰的精美绝伦的房子”。这些知名的藏品也让汤利本人名声大噪,被当时公众视为“趣味之典范”。

图4 Zoffany,Johann.Charles Townley and Friends in His Library at Park Street,Westminster.1781-1790.8.27 cm × 99.1 cm.Towneley Hall Art Gallery & Museum,Burnley
人们认为佐法尼的《查尔斯·汤利图书馆》可能是18世纪末所有呈现古典趣味的视觉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但我将佐法尼与汉密尔顿的画作放在一起研究,目的并不是讨论它们令人难忘的特质,而是将它们视作18世纪晚期图书馆兼古物收藏馆的两幅再现绘画来进行评估。这两幅画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图书馆布置及其古物收藏的不同可能性。佐法尼的《查尔斯·汤利图书馆》现藏罗马天主教绅士伦敦别墅的图书馆内。汤利的古物藏品以他大量收集的古代大理石雕塑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从罗马挖掘出土、修复并带到伦敦的。在汉密尔顿为罗兰爵士和温恩夫人所作的肖像中,温恩家位于利兹郊外的图书馆为他们的肖像画提供了背景。此画体现的是另一种古物收藏的形式:这些藏品并非从意大利远道而来的古代文物,而是英国建筑师罗伯特·亚当把古代建筑与雕塑模仿一番,并转化为室内的景象。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和艺术品收藏就被视为是汇聚智慧的宝库,它们封存并延续人类的文学和物质遗产。约翰·布里顿[John Britton]在《建筑、雕塑和绘画的统一》[The Union of Architecture,Sculpture and Painting](伦敦,1827)中就以此种文艺复兴范式描述了约翰·索恩爵士[Sir John Soane]在伦敦林肯林荫道13 号[13 Lincoln’s Inn Fields]的收藏:
对艺术家和作者来说,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必不可少的监督者、同伴、朋友。 他们是智慧的宝库;是天才们的结晶,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知识永存而留下的遗产。通过它们,我们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维特鲁威、莎士比亚进行深度交谈。我们向他们请教知识:我们在与他们的沟通中获得愉悦与满足。从他们的言语与思想中,我们认识到他们学识的进展与成果: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中,我们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经验植根于所学知识的证据。因此,图书馆和艺术品收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们将遥远国家和遥远时代的学识、才能和趣味带回“我们自己的家园和怀抱”。
艾莉森牧师[Reverend Alison]在他《论趣味的本质与原则》[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爱丁堡,1790 )中为我们阐明了18世纪晚期图书馆空间的意识形态:
古物收藏家在他的珍奇室中被旧时代的遗迹所包围,他自己似乎也穿越到很久之前的旧时代,他陶醉于生活在过去的想象中,而那个世界总让人偏心地认为比如今的世界更智慧、更美好。在这些时代的历史中,所有值得尊敬或值得称赞的事物都呈现在他的记忆中。
虽然来自各历史时期的宝物包围着艾莉森牧师所描绘的珍奇室中的古物收藏家,但查尔斯·汤利和罗兰·温恩爵士在其图书馆中被展现为不同的形象:他们周围环绕着的是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遗物和仿制品。就如古物收藏家的珍奇室一样,图书馆空间触发的是一个仅存于想象中的古典世界,但这个世界在艺术与文学作品的收藏中被赋予有迹可循的形态。
然而,关于古希腊与罗马学识、才能和趣味(如布里顿所说的)对18世纪后期现代性影响的研究是有问题的,尤其是与文学作品相关的方面。据阅读史专家说,在18世纪最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数量空前的私人图书馆涌现出来,但这些馆藏中的大部分如今已散落各处。图书馆的解体是英国乡间别墅消亡悲伤故事的一章,当时房产主们为了尽力保住他们祖先的遗产开始变卖藏品。而他们的藏书,那些曾经不可或缺的“监督者、同伴和朋友”(再次引用布里顿的话)变得可有可无而往往最早被卖掉。曾坐落于米德尔塞克斯的奥斯特利公园别墅[Osterley Park House in Middlesex]图书馆的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图5)。从1756年弗朗西斯·柴尔德[Francis Child]以两千英镑从布赖恩·费尔福克斯[Bryan Fairfox]庄园买下整个图书馆开始计算,该图书馆的藏品曾存在于世超过整整一个世纪。就像罗兰·温恩爵士在诺斯特尔庄园的图书馆一样,奥斯特利的图书馆也由亚当设计的一系列房间组成。1772年,阿涅塔·约克[Agneta Yorke]参观了这处房产,他认为图书馆是“一间迷人的房间。里面摆满了精美的书籍,亚当斯先生在装饰每一个部分时都倾注了他所有的趣味。房间是纯白色的。圆桌、书桌和椅子都是各种木材精美镶嵌而成的作品,不是亲眼所见你无法想象它们是多么的优雅,而且肯定花费了很多钱,没有一处地方让人感觉是省了钱的”。

图5 the library at Osterley Park House
除了书籍外,罗兰·温恩爵士和查尔斯·汤利爵士图书馆的所有物件随后都成为国家财产。1953年,诺斯特尔庄园被转交给英国国民信托。由建筑师罗伯特·亚当设计的一系列房间包括图书馆都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其书柜在1826年左右已磨损成类似涂画的木材。但汉密尔顿的罗兰爵士和温恩夫人的肖像已然成为那座图书馆中一件杰出的陈设,展示在奇彭代尔书桌后面的画架上(图1)。不同寻常的是此图书馆的藏书并没有散落各处,而是长期被忽视为一种文献壁纸;早在1775年,爱德华·哈伍德[Edward Harwood]在《希腊和罗马经典的各种版本概览》[A View of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Classics]中写道:“近些年来,藏书已被视为是昂贵家具的一个分类。”查尔斯·汤利于1805年去世后,他收藏的大理石雕塑以两万英镑的价格被国家整体买下并珍藏于大英博物馆。1984年沃尔弗森画廊[Wolfson Galleries]开业后,汤利的雕塑再次作为收藏品展示,还附上了佐法尼图书馆所作绘画的复制品。而原画是汤利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的私有财产,该博物馆旧址是汤利家族在兰开夏郡的家。与此同时,汤利图书馆的藏书早已散落别处,这些书籍由他的叔叔约翰·汤利[John Townley]继承,叔叔本人也是稀有书籍的收藏家,这些藏书在19世纪前后举行的多次拍卖会中以“汤利图书馆”[Biblotheca Townleiana]的名义被拍卖。1816年5月,一位金先生出售了汤利藏品中的素描、书册、印刷书籍与英国地貌书(约1291 个条目)。查尔斯·汤利图书馆有两份目录:一份来自他在白厅的家,日期显示为1771年;另一份来自威斯敏斯特,现存于曼彻斯特切瑟姆的图书馆内,未注明日期,这两份目录让我们有可能从他叔叔的销售目录中推断出图书馆的内容。只有当我们推进这项工作才能判断汤利的藏书,以及他古代文物收藏中的对开本、四开本、八开本和十二开本在多大程度上共同构建出一个文学世界,让其拥有者能够与约翰·布里顿后来所说的古希腊罗马的学识、才能,以及趣味相谈甚欢。
现在我们已勾勒了图书史领域的一些轮廓,让我们继续讨论新古典主义,把关注点从精英图书馆的同时代描绘转向其书籍,来借阅一部18世纪晚期的“经典”作品,其作者是罗兰·温恩爵士和查尔斯·汤利的同时代人之一:这部作品就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后简称《衰亡史》)的最终(第六)卷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中,吉本以“古代学识的使用和滥用”为题回顾了15世纪欧洲古典文学的复兴。根据吉本的总结,希腊和罗马文本中那些近乎完美的习语通过将野蛮人以前粗俗的举止引入“光明和科学的新世界,以及古代自由与优雅之国与社会”来感化他们。虽然这种理想化的概念影响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但吉本认为“从第一个实验开始,对古人的研究似乎就给人类思想带来了束缚,而不是插上翅膀”。通过卖力地效仿古代的思想与行为模式,现代人把自己变成了奴隶,将自己桎梏于古人的思想、言语和信仰中。虽然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拉丁文化的追随者,他们的作品端坐在我们的书架上”,但没有产生任何原创性的作品或可读性强的、带有思辨性的作品。吉本认为只有当学术的土壤“完全浸透了天上的露水”之后,古希腊与罗马的经典之作才能在意大利、而后在法国和英国激发出诗歌和小说的创作、进一步激发出“思辨和实验哲学之光”。此章以吉本关于教育和模仿的思想作为结语:“天才可以预见丰收的季节;但我们教育民族就如教育个体一样,必须锤炼其记忆,在这基础上才能开发出理性和想象的力量。艺术家在学会模仿前人的作品之前,其作品也不可能超越前人或与之相提并论。”
这段关于古代学识运用和滥用的文章,以衰亡为叙述框架,阐明了吉本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古典主义。在这里,吉本强调了古典思想的理想状态,即自由和优雅之文化被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古典主义传统所规范。互文性的实践在此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那些仿效古典模式作品的核心,在这种模式下,当代著作的作者是他们前辈著作的读者。吉本通过提醒读者拉丁效仿者占据了他们书架的这个事实,也将这段文字以及他的《衰亡史》置身于图书馆的知识和物理空间中。
这篇带有讽刺意味、语气俏皮的文章旨在回顾15世纪欧洲古典主义学习的状况,使得吉本的《衰亡史》在传统人文古典主义的框架内外都构建了自己的地位。他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本的解读将其作品置身于在以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为起源的图谱中;不过当寻找一部可读性强、具有原创性和思辨性的作品时,吉本暗示他的读者只需看看摆在他们面前的文字——那就是吉本自己写的《衰亡史》!我们需记得的是,该系列的最后两卷是吉本在洛桑“退休”期间写成的,那时他作为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的地位已得到稳固确立。这本著作在1776年2月出版第一卷,截止到3月26日已卖出了一千册,并受到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盛赞,见其致威廉·梅森[William Mason]的信:
瞧,刚刚横空出世了一部真正经典的作品: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像李维那样雄伟,也不像塔西佗那样浓缩;不像克拉伦登这样充满个性;也许也不如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苏格兰史》[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542—1603]那么深刻,但比《查理一世传》高出一千度;不像伏尔泰那样尖锐,但准确度拿捏得恰如其分;锋利与谦逊并存,像孟德斯鸠一样圆滑却又不那么拘谨。画风流畅如佛兰德斯的画,隐藏起肌肉只为自然使用,不像米开朗琪罗那样夸张以显示画家的解剖技巧;也不像约翰逊博士笔下的异类怪物那样由不同国家的小丑四肢组成。这部著作就是吉本先生的《衰亡史》。
吉本关于天才和教育的思想论述是他毕生心血的题词,有趣且带有预见性。正如沃波尔的评语所说,吉本的经典著作代表了精英阶层学习文化的文学作品,它们既是人文主义古典传统的产物,也为现代英国社会制定了一个古老故事的原始文本。 沃波尔通过文学和艺术史的比较证实了这部著作的经典地位。在任何一位绅士——比如霍勒斯·沃波尔——的图书馆里,吉本的作品都会与书架上不朽人物的作品共同出现、平起平坐,而这些书架上的作品代表了精英阶层所学所读之精华。
那么该如何利用吉本的《衰亡史》来构建我们对18世纪古典主义的解读呢?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无疑是一个更显而易见的案例,他被誉为古典复兴的英雄,其名字已然是新古典主义艺术历史运动的代名词。诚然,阅读吉本著作的艺术史学家很少在其书中读到关于视觉或考古层面的解读,虽然君士坦丁的拱门是个值得关注的例外,在书中被形容为“一个见证艺术衰亡的令人悲伤的证据”。然而,吉本在第六十六章结尾的题词可被视作是适用于18世纪晚期英国文学与唯物(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格言。他认为古典主义是一个习得的过程:“记忆必须得到锤炼,在这基础上才能开发出理性和想象的力量。艺术家在学会模仿前人作品之前,其作品也不可能超越前人或与之相提并论。”作为一个学习过程,古典主义在图书馆中被“装裱”起来:就像罗兰爵士和温恩夫人(图1)以及查尔斯·汤利(图3)的肖像一样。温克尔曼早期曾做过教师和图书管理员,他在罗马为红衣主教阿尔巴尼工作时,那儿的图书馆任凭他支配管理,但后期评论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些构建起他脑海中古代艺术百科全书的浩瀚书籍和参考书目。相较之下,吉本的古典主义在《衰亡史》的文本中均附有详细的脚注,而他那部大约有七个修订版的《回忆录》[Memoirs of My Life]既是自传,又是全面的参考书目,其中囊括了一位批判性历史学家一生的阅读。他认为收集、权衡、选择前人的思想是他的“权利”和“职责”。对于吉本来说,这项职责是通过他的图书馆实现的,他有大约六千册藏书(约1789年),被形容为“我制造历史的工具”。出于一种文学上的预见性,吉本在他早期的《论文学研究》[Essai sur l’etude de lar literature,1761]中,描绘了一位在书房中沉浸于自己思想世界的学者形象——这也成为日后的他自己:
我们跟随一个文人进入他的书房,你会看到他被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所包围;他的图书馆里收藏着各种书籍,他的思想因知识而充盈,却不会因阅读而负担过重。他环顾审视四周;书籍的作者也不会被遗忘,因为其作品可能与文人的思想有着若有若无的关系:他可能会碰巧瞥见一些意料之外而引人注目的段落,以证实批评家的发现或推翻他自己的假设。
由此,我们可以构建出吉本作为文学考古学家的形象,他探索和挖掘那些多层的、有时甚至是因时间久远已被封存的古典学识。我们再从《衰亡史》中摘录一段:
时代的混乱和真实记忆的稀缺,对试图捋顺叙述线索、保持其清晰与连贯的历史学家来说困难重重。他们周围充斥了不尽人意的历史碎片,这些碎片要么过于简洁,要么晦涩难懂,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他只能不断收集、比较、猜测:虽然他永不应该把自己的猜测归入事实,但出于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心中所蕴藏的一股激烈而又无尽的激情,在某些情况下是的确可以弥补历史素材的不足的。
吉本的图书馆相较于他的博学来说就如他的经典作品《衰亡史》一样具有纪念意义。按照上面引用的段落来看,如果说吉本是一位文学考古学家,那么他也是一位被“不完美的碎片”和文字废墟包围着的鉴藏家。在吉本对历史学家方法论的描述中,我们也可隐约捕捉到18世纪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在这个层面上,图书馆不仅成为了古代知识的宝库,更是一个能让当代人产生共鸣的实验场——吉本的书籍是他的工具,而图书馆是他的实验场。正如任何创新实验一样,吉本所做的,尤其是他新颖的方法论也遭受到一些批评。在吉本回应亨利·戴维斯[Henry Davis]对自己所谓歪曲源素材的批评时,他似乎是在有意邀请对方去看看自己在伦敦本廷克街 7 号图书馆的藏书,以此见证自己是如何在这样一种实验性环境的基础上构建历史著作的:
我不能说自己很想认识戴维斯先生。但如果他想不厌其烦地来我家看一看,那么在任何一个我不在家的下午,我的仆人会带他看看我的图书馆,他会觉得那儿的内容相当丰富,书架上都是非常实用的作家:古代的现代的、教会的世俗的,正是他们直接向我提供了我的历史素材。
对吉本著作的批评未必针对《衰亡史》文献库的内容来源。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在第四卷的扉页上猛烈抨击吉本“几乎可笑的自满情绪……你那自我感动的道德纯洁时不时从腐朽中冒出来……你高傲自大的语气,还有你对于时代索然无味的描述”。然而,贝克福德这位藏书家在1796—1797年冬天以九百五十英镑的价格买下了吉本的整座图书馆,这被看作是他作为一名藏书者最高调的壮举。本廷克街的图书馆不仅具有相当质量和数量的书籍,其室内装潢在1770年代以当时流行的所谓新古典主义风格进行了翻新而变得十分华丽,风格与罗伯特·亚当为诺斯特尔庄园和奥斯特利公园别墅所设计的类似。在1772年的一封信中,吉本描述了图书馆重新装修的方案:“爱尔兰长官今天早上和我一同参观了图书馆,先省略关于书柜的谈话细节,我们同意不要用红木。房间的墙纸将使用精细的粗绒绒纸,是浅蓝色带金色边框的,书柜会漆成白色、饰有浅色条纹:条纹既不是多立克式也不是凹凸式……而是亚当式的。”
吉本在撰写工作尚未完成前于1783年在洛桑退休,在此过程中目睹了他不可或缺的藏书是如何被搬走的;他写道,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在身边,自己将被剥夺最后几卷著作所需的陪伴与参考。虽然他也异想天开地希望“免费开放供文人使用的私人和公共图书馆”,但吉本后来吹嘘他的个人图书馆“比沃州[Pays de Vaud]的任何图书馆都好,比以前在本廷克街的图书馆更完整且更有价值”。吉本还通过订阅并保持与伦敦书商的联系不断为自己的图书馆添购新书。汉诺威公爵的图书管理员兼王子的旅伴恩斯特·兰格[Ernst Langer]在18世纪80年代描述了他访问吉本“学习宝库”及其随附书目的经历。他指出,吉本的“丰厚财富和他对一切事物的趣味、优雅的装订、书的外观等都表明了它们的价值,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早有期待的”。吉本渊博的知识唯有他浩瀚的藏书能与之相匹配——书籍本身不仅成为史料的来源,也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和精神力量的物质证据。正因如此,游客约翰·欧文[John Owen]将吉本加冕为“洛桑文学的伟大君主”;而德文郡公爵夫人则认为吉本作为一名藏书家犹如“他图书馆里最好的书”,值得大家请教。
吉本的《衰亡史》是一部为“耐心的读者”而作的文学里程碑,其出版确保了吉本图书馆的书籍永远不会完全消散在历史长河中。正如以上指出的那样,该系列的第一卷在1776年已被作为经典来看待。《衰亡史》的广度和深度让读者拥有一种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的特权(引用第一卷扉页上李维的题词),尽管这种特权是第二手的:《衰亡史》是一座微型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由吉本广泛的藏书中蕴含的文本碎片构成的,而这座微型图书馆本身就会成为一件收藏品。在吉本的一生中,它被翻译为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吉本在他的《回忆录》中几乎带有预言性地写道自己的文字“可能一百年后仍然会继续被滥用”。在《衰亡史》第六十六卷第六十六章的结尾,吉本将所谓的古典主义描述为对古代学识的使用和滥用,现在看来这种描述是多么恰当。
在我们对18世纪晚期古典主义的研究中,吉本的《衰亡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定义、一个基于教育和模仿方法论框架以及一个场所:图书馆。然而将吉本看作是18世纪古典主义代言人(可以这么说)的问题在于:这一切作为一个整体——图书馆、书籍与参考书目、《衰亡史》——都好得太令人难以置信、太不典型。吉本在1781年4月13日给继母的信中写道:“几乎每个有阅读习惯的人都购买了《衰亡史》,但很少有人真的读过它们;我发现更多的人对他们获得了一笔宝贵的消遣财富感到满意,将细读这本书与夏天、乡村、安静时光的度过相提并论。”吉本的六卷本作品是一种宝贵的消遣财富,而不是英国古典主义的构成。《宣传册》[Pamphleteer]在推荐吉本的《衰亡史》以形成一个精选的小型图书馆时写道:“他为一段历史注入了活力与乐趣,在他承担此重任之前,这段历史被埋在一堆哥特垃圾下,几乎没有人敢于触摸它,而他通过触摸它将其化废为宝。”我们需要关注吉本关于古典时期的态度而不是他文学炼金术般的历史功绩,让我们再次转向他的文学创作处女作来进一步清晰认识。在《论文学研究》(伦敦,1761)的一篇文章中,吉本明确而有力地写道:“了解古代是对古人著作的唯一真实的评论:但更必要的是某种心态的转变,这通常是了解古代的必然结果:这种心态转化为一种使古时事物为我们所知的决心,更是促使我们的思想融入于古代的事物与环境,让我们以古人的眼光看待它们。”吉本的“古人之眼”使他在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但他与许多人一样确实拥有这段话中描述的希腊和罗马古代“某种思想转变”的特征。我们需要回到与教育相关的话题来了解这种思想转变的源头来自何处。
“罗马是全世界的学校”,歌德引用了温克尔曼给弗兰克的信。对于18世纪晚期的英国旅行者来说,访问罗马的经历更像是在一所学校游学。英国公立学校的古典教育或拥有家庭私人导师的特权代表了英国小学生最早通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语言与古人相遇的经历。按照吉本《回忆录》七个版本中的一个:“一位成熟的学者可能会在威斯敏斯特(吉本的母校)或伊顿的优等生中诞生,他也许完全不了解18世纪晚期英国绅士的商务与会谈内容。但这些学校可能会认为他们所教的全部内容——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有价值的:他们将两个有价值的箱子钥匙交到一个门徒的手中。”有了这些钥匙,英国小学生们就可以打开古典图书馆的大门了。克里斯托弗·斯特雷[Christopher Stray]认为古代经典实质上作为学校的知识体系完整地体现在书籍中,尤其是在学校的教科书中。
伊顿公学档案馆中的经典教科书证实了学校对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重视,这些书共同构成了整个正式课程。这其中有托马斯·鲍尔[Thomas Bowles]的《拉丁语音简明合理的培训》[A compendious and rational institution of the Latin tongue](牛津,1740)和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的《拉丁语写作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king of Latin](第14 版,伦敦,1747)等,这让我们对学校的教育内容一目了然。詹姆斯·格林伍德[James Greenwood]的《伦敦词汇:英语和拉丁语》[The London Vocabulary,English and Latin](第18 版,伦敦,1782)是专门为小学生出版的,为了“让学习者熟悉事物以及纯粹的拉丁词汇”。1741年版的《贺拉斯的赞歌、对歌与世俗竞技会赞》[The Odes,Epodes and Carmen Seculare of Horace]将拉丁文本与英文翻译并列,同样面向小学生群体。其序言说道:“在缪斯的所有礼物中,贺拉斯的诗是最有用的,他是唯一能塑造君子的诗人。”然而贺拉斯这些“如此优秀,如此实用”的诗,这些号称能为读者提供“智慧的果实衬托出最迷人的帕纳索斯之花”的作品,也必须为了避免对年幼的读者带来不良影响而接受后期编辑。这本书的序言解释道:“没有任何翻译违背文雅或礼貌举止规则,这些内容可以呈现给最纯洁的耳朵。”因此《对歌》的第八首和第十二首诗未被翻译,而一些句子则翻译得相当模糊。在古典文学传统典型胡扯的一个生动例子中,尤文纳尔[Juvenal]的“优秀规则”(《讽刺诗》[Satires]XIV,44-45)显然证明了这些审查措施是正当的:“Nil dictum foedum visuque haec limina tangat/Intra quae puer est.”[不受猥亵或下流言语的影响/幼小男孩心灵的归属。]
罗马历史的庞大参考书目同样以接受度很高的卷册形式呈现,比如《古今名家书目精选集》[from Ancient Authors,and the Most Celebrated among the Modern](伦敦,1749)中的问答形式可读性很高。而古代地理地图集帮助小学生重温文学之旅的道路,仿若罗马创始人埃涅阿斯[Aeneas]在维吉尔[Virgil]《埃涅阿斯纪》[Aeneid]中的经历。《古典的地理》[Geographia Classica](伦敦,1712)的序言说道,这种编排使阅读古代作者变得不那么乏味,并使学生能够“合理准确地判断作者所描述的行为”。这些著作清晰展示了18世纪课堂上对希腊和罗马古代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古典教科书,包括词汇、翻译、语法和地图集当中。
相较于关注古典教育的内容,本文更关注古典教育是如何影响英国人收藏及委托创作的藏品的。斯特雷[Stray]“古典学是英国绅士风格的一部分”的理论可被提炼为一种论点,那就是18世纪的古典主义是一种受古典教育灌输的思想风格。布迪厄[Bourdieu]关于教育社会学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方法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只要通过研究那些建立和开发思想的教育体系,就能够完全理解特属于某个时期的思想风格或范式。英国公立学校的古典课程通过无休止的、仪式化的重复训练来建立并开发英国人独特的思想风格。在公立学校平均六年的时间里,男孩们每周大约有二十一小时用来解析、翻译和模仿古典作家。这些练习间接在他们思想中打上了我称之为古典主义思想风格的烙印,古典主义作为一套精心设计出来的思想程序为英国精英阶层人士提供了一种“文化体质”。因此我们与吉本《衰亡史》中所称的古典主义——对古代学问的使用和滥用——实际上是当时公立学校教育的应用技术,这是一种由精英阶层公立学校的古典课程灌输给学生并体现在教科书中的思想风格。
布迪厄提到学校在教育体系中也为学生制定游学历程。古典主义在英国公立学校系统中被打上专用的教育模式烙印后,其形态在意大利游学中得到演变。当人们一旦来到古典学的源头之处,课堂上那些隐藏的、未明说的思想风格就会变得清晰和直接。比如,在《一位游历国外的年轻画家给英国朋友的信》[Letters from a Young Painter Abroad to His Friends in England](伦敦,1750)中,詹姆斯·拉塞尔[James Russel]承认“我在威斯敏斯特阅读的诗对我在意大利常常感受到的愉悦贡献不小”。他在另一封信中指出,这是一种“在书房或教室内的人都感受不到的”愉悦。莫宁顿伯爵[Earl of Mornington]则认为如果不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旧知识”重新浮现在他脑海中,那么“穿越意大利的旅程将失去最大的乐趣”。意大利的雅游[Grand Tour]把学生从他在课堂教科书中经常读到的思想植入到真实存在的经典之域上。诺斯勋爵[Lord North]在 1753年 9月 1日至 19日写给他在伊顿公学的导师查尔斯·丹皮尔[Charles Dampier]的信中阐述了这一看法:
你知道,从托梅到那不勒斯的那条路充满了古典景观:我可以向你保证,从那不勒斯到帕埃斯图姆的那条路也同样有趣。几乎没有一个城镇、一条小溪、一座小山或一个山谷未被古代作家中提及甚至明确指出过。那些深谙其道的旅人、那些在自己的想象中已经多次踏上旅程的旅人们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著名的国度:几乎他们看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在唤起回忆或刷新自己的认知,抑或确认或抹去一些旧观念。
爱德华·吉本的雅游则代表了学生时期教育与思想启迪之旅的融合;在《回忆录》中,他回顾了自己那足以征服意大利的文学积累(指他的图书馆):
我的一切学习经历都是在为我的古典之旅做铺垫——那些拉丁诗人和历史学家、抄本、奖章和铭文、建筑规划图、罗马的地形和古物、意大利的地理以及遍布恺撒帝国的军事道路。或许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很少有旅行者能像我这般用知识全副武装,追随过汉尼拔的脚步。
吉本的《衰亡史》可解读为一场充满想象力的雅游,每一卷每一章都代表了穿越数百年罗马历史的旅程:“在几天、几小时的阅读中,六百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而古人们一生的辉煌在此转化为转瞬即逝的时刻。”精神上的历史朝圣以吉本为向导,并与实地朝圣一齐在当代罗马终结。在许多方面,意大利雅游的实际路径也可被视为一种朝圣方式,正如吉本所说“那些来自遥远的、曾经荒蛮的北国的新朝圣者们”开始追随罗马文学中不朽古人的足迹。此外,前往罗马的18世纪朝圣者也自然而然地追随中世纪朝圣者的足迹。虽然前者的目标与基督教没有太大关联,但考古朝圣的概念将西方社会的历史性构造融入了雅游。一位典型的古典游客行李中必然包括古代作家的著作,这些著作要么被带到意大利,要么在意大利获得并用来作为其向导和指南。比如,吉本图书馆里有只红木盒子,里面放着J.布林德利[J.Brindley]出版的二十四卷古典作家的著作(图6)。而尤斯塔斯牧师[Reverend Eustace]在他《一次意大利的古典之旅》[A Classical Tour through Italy](伦敦,1813)中也认同这个观点:

图6 Edward Gibbon’s travelling library.By courtesy of the Governing Body of Christ Church,Oxford
维吉尔与霍勒斯、西塞罗和李维应是所有旅行者不可或缺的精神伙伴;他们应该占据每一节车厢的每一处角落,并在每一点空闲的时间里被召唤出来以减轻旅人的疲劳、增加旅途的乐趣。与这些作者相熟或成为灵魂伴侣自然是一位古典旅行者最重要的成就。
旅行书箱的便携性无疑影响了这些经典的阅读方式。也就是说,虽然旅途中所提到的文字与和课堂上的文字一样,但其所在的真实场景与读者却因为旅行本身发生变化,从而开辟一系列全新的可能性。比如卢卡斯·佩皮斯[Lucas Pepys]医生在罗马写道,他“最近阅读了维吉尔的最后六本书,在我看来,它们以全新的面貌和视角呈现在我眼前,并在我眼前展现了真实可触的场景。未来,我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也将对阅读拉丁古典文学产生更强烈的兴趣,因为书中提到了很多我现在非常熟悉的地方”。
我们英国朝圣者在踏上雅游之前已对古代作家的文字十分熟稔,这些经典不仅规范了他们的举止行为,也使他们更了解罗马历史。老伊顿人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1751年10月12日的一封信中盛赞了古典教育的这一方面。在回复侄子用拉丁文撰写的信时,皮特很高兴听到侄子开始用希腊语阅读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并因阅读维吉尔拉丁文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他继续在信中写道:
我希望你会钟爱阅读这些作者(尤其是荷马和维吉尔)的经典。你怎么阅读他们两位都不算多:他们不仅是两位最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提供了你这个年龄所能吸收的最好的训诫:荣誉、勇气、无私、热爱真理、控制脾气、温柔和文雅的举止、人性的教训。一言以蔽之,他们代表了美德的真正含义。继续吧,我亲爱的侄子,尽你所能地饮用这些神圣的泉水:这份愉悦至少与它对我等凡人心灵无可估量的益处相当。我希望你能像维吉尔曾经那样从另一种杯子里畅饮:“Ille impier hausit spumantem pateram.”[他急切地将泛着泡沫的酒碗一饮而尽。]
塞缪尔·夏普[Samuel Sharp]在其《意大利信简》[Letters from Italy](伦敦,1766)中更简明扼要地指出:“罗马……我们从在摇篮里开始就被教导要崇拜它。”在许多方面,雅游的故事是关于这种崇拜如何形成和转变的。那些古典作家的书籍在旅行结束后回到家中成为旅行的纪念品与指南。
爱德华·吉本晚年回忆自己到达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第一印象,留下了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我的性情不太容易受到热情的影响,而我也从不认为自己会受到这种热情的影响。但在二十五年前,我无法忘记也无法表达自己第一次接近并抵达这座永恒之城时心中激起的强烈情绪。经过一个不眠之夜,我踏上了古罗马广场崇高的废墟;罗穆卢斯站立的每一处都令人难忘,塔利(西塞罗)在这里发表的演讲,恺撒在此处倒下,这些画面在我眼前立即展开,我失魂落魄并沉醉其中,过了好几天才重新恢复冷静而细致的学术调查。
吉本将他的经历描述为令人难忘而又难以言喻,其实他是通过模仿阿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冒险之旅的描述来表达初到罗马的记忆。在《衰亡史》中,吉本描述这位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他是一位准确而忠实的向导,他创作了自己时代的历史,没有让自己沉溺于通常影响当代人思想的偏见与激情。”阿米亚努斯在《晚期罗马帝国史》[Res Gestac](16.10,15)的片段中提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Constantius II]被罗马的壮观景象震撼到不知所措,这情形正如十四个世纪后的吉本一样。在图拉真的古罗马广场上,“他目瞪口呆地站着,望向他周围的巨型建筑群,在心中苦苦追寻描述此景的词汇,希望再也不会被其他世俗之人效仿”。通过引用阿米亚努斯的描述,吉本将自己抵达罗马的记忆映射到了君士坦提乌斯的记忆上。在这过程中他将自己古典化传统的格言付诸于实践,在这种传统中,艺术家在学会模仿之前不能指望超越前人的作品或与之相提并论。吉本承认自己在写下他关于罗马的这些记忆时,自己冷静而细致的理性思维完全被理想化的幻想与热情所取代。
古典朝圣者们并没有被古罗马的壮观遗迹所吓倒,他看到的不是考古意义上的景象,而是多年以来阅读古典文学后在心目中氤氲而生并赋予古代的景象。艾莉森牧师《论趣味的本质与原则》中有一段进入罗马的文章恰如其分地展示了雅游的游客们是如何在地理意义上穿越意大利,而且似乎在时间上也穿越到了古代意大利:
呈现在他面前的不是毁灭的场景、不是台伯河如何在他想象中成为浴血之池……也不是迷信如何战胜人类伟大的遗迹……而是恺撒、西塞罗和维吉尔之国。他看到的是世界之女神。他年轻时努力背诵以及成年后的研究让他熟知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这些历史现如今在这一刻全部展现在他的想象面前,呈现了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崇高而庄严的意象。
而在首都之外“你可以引用至少一百首来自贺拉斯和维吉尔不同段落的诗句”,那不勒斯的地形景观仍然充满古典的回响。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well]于 1765年 3月 19日写信给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
那不勒斯确实是一个迷人的地方;praeter omnes ridet[比一切都更让人欢喜]。我在这里待了将近三个星期并且一直在不断品味周围的古典之地。这世上怎么可能存在比拥有岛屿和与田野接壤的海湾更丰美的场景?这里是维吉尔的缪斯女神亲自创作的天选之作,古罗马的名流们在此处尽享世间无限华丽的美景与源源不断的精神与心灵之盛宴。
正如吉本对自己抵达罗马后的描述一样,博斯韦尔的信中也引用了古典文学的经典表达。这不仅包括公元前一世纪诗人贺拉斯在那不勒斯的“比一切都更让人欢喜”(《颂歌》[Odes]II.vi.13-14),还有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仿写的《贺拉斯闲谈集的第二卷第一首》[The First Satire of the Second Book of Horace](1733年首次出版)中的“理性的盛宴和灵魂的流动”[I.128]。这些引文代表了古典作家与受古典化影响的作家、受过教育的游客与他在国内读者之间的精英化对话。古典朝圣者们以古典图书馆作为他的参考书目来(重新)描绘意大利,正如他将古典文本作为向导来考察古代遗址:
我们年轻时学习古典的经历使我们能够对罗马人的情感感同身受。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个小学生只要不是对年少时接触的古典内容麻木不仁,其在情感和觉知上、甚至在语言上都变成了罗马人。这岂不是很美妙:当他在成熟的年纪抵达那个国家、看到了那些他很久以前就幻想过的场景时,必然会感到一种极不寻常的震撼与热情,在着迷于真实场景的同时其脑海中也许会浮现出更多想象。此外,意大利的风景是真正本源的古典,她与诗人和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如出一辙。
以上为尤斯塔斯牧师在《意大利古典之旅》[A Classical tour through Italy](第3 版,伦敦,1815)中的记述。这是一本吸引人们注意到每一个古代细微之处的指南。博斯韦尔建议18世纪末的同时代读者“在意大利阅读所有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作品”,而尤斯塔斯则在19世纪初建议人们预先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那么吉本在他那个时代是否已经成为英国古典朝圣者的典范——就像歌德在德国读者心目中的一样呢?托马斯·罗宾逊[Thomas Robinson]在1802年 11月 3日从罗马写给母亲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并完成学业。我在雕像、图画和宝石的鉴赏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一直努力地学习绘画……我通过观察建筑学了一些实践课,我一直在学习吉本的作品。再也不要说我来罗马是白来的了。”尤斯塔斯也引用了吉本的当代文本,他转述了《衰亡史》中的脚注并赋予其文本与古代作家同等的权威性。尤斯塔斯认为英国朝圣者在年轻时就被罗马文学文化所熏陶,他们经过多年的接触带着先入为主的理想来到了罗马。英国公立学校教育的一个悖论是:其提倡的罗马化过程——“一套深深铭刻在心中最好的罗马美德”——实际上发生在罗马之外。事实上,对罗马的第一手体验往往成为古典旅行者罗马化过程的顶峰。詹姆斯·博斯韦尔在参观完西塞罗的房子后描述自己“心中充满热情”并决定开始用拉丁语说话:“我想用罗马人自己的语言谈论罗马古物。”
科尼尔斯·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ton]在《罗马来信》[A Letter from Rome](伦敦,1741)中认为这种对古典的热情倾泻而出并不是特殊个例,而是“所有阅读和受过教育的人、追求与他们最钦佩的古代圣贤与英雄交谈乐趣的人共同拥有的”。这些已经与古人亲密无间的古典旅行者在遥远之处已经体验了意大利,而这种距离是由学校教育和期望共同营造的。罗马的雅游是一种古典朝圣形式,旅途追溯了对古意大利的崇拜之情,那里的每一处视觉景观和考古遗址都可用来指代古代的英雄、事件或文字。 在古典传统的普遍影响下,那些与古代作家长久相关联的废墟被解读为他们的工作场所、家园甚至坟墓。尤斯塔斯对那不勒斯周围的地形景观还写道:
这些地方或许从来都不是英雄成就或盛大奇事的舞台;但它们是伟人和智者的住所;它们帮助圣人沉思、唤醒诗人内心的狂喜;只要拉丁缪斯女神继续指导人类,旅行者们就会兴味盎然地参观西塞罗学院、维吉尔之墓与塔索的出生地。
然而,18世纪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如此乐于重温古迹,却在身后遭到了嘲讽。路德维希·库提乌斯[Ludwig Curtius]有云:
对于18世纪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来说,古典时期只不过是陈腐的学究研读或闲时的收藏物品;只不过是歌剧、游行和游园会的装饰背景。当然,它也可以用来提供品格或作为教育和道德说教的素材,用来启迪年轻的绅士或美化政治论文。
矛盾的是,吉本的《衰亡史》却保留了它的经典地位。这部著作在1994年最新版的序言中被评为“欧洲文学最伟大的叙事之一”。因为吉本的叙述远非过时的学究(尽管威廉·贝克福德可能不同意),本章已试图阐述18世纪的古典传统是如何成为研究对象的,而研究古典传统的目的绝非培养陈腐的学究,而是为了建立并开发一种古典教育的思想风格。英国公立学校系统灌输给学生的思想风格是古典主义并且关乎到古代学识的使用和滥用。而新古典主义并非库提乌斯所说的是收藏家闲时无聊拿来摆弄的物件或装饰背景。相反,它将这种演化而成的思想风格应用于古人留下来的物质文化之上。
在《一位游历国外的年轻画家给英国朋友的信》(伦敦,1750)中,詹姆斯·罗素描述了置身于意大利古典土壤上的愉悦之情:
我曾努力在家里试图寻找并不断回想古代杰出军事家和艺术家及其丰功伟绩。以及他们居住或休息之处的场景,以此来获得愉悦之情。在这里,我的想象犹如脱缰野马,我想象他们是如何在特定之处战斗、说话、学习或消遣娱乐的。为了更深刻地记住这些地方和古典文学中的段落,我经常尝试翻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模仿这些文字片段。这样做的结果与我总是试图模仿著名画作的结果大致相当,每一次模仿之后我都会对原作的经典与风采感到更为钦佩。
罗素有意为他的古典之旅留下深刻的印迹,他尝试翻译并模仿古代作者的相关段落。在回顾这种实为学生时代经历的过程中,他正是在训练自己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接受的古典教育所灌输的思维方式。在这封信中,罗素明确将翻译或模仿经典文本的训练与复制名画家作品的美学行为相关联。在这两种情况下,罗素的复制品都增强了原作的“风采”。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看到的那样,在收藏包括伊特鲁里亚花瓶、修复的古代雕塑和石膏模型等实体文物时,受过古典教育训练的英国贵族或绅士能够进一步“加深罗马之行与古典文学的记忆”,就如罗素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他能够将自身所受的古典教育与意大利之旅转化与演变为物质财富。我们再次来看艾莉森牧师在他《论趣味的性质与原则》中对于18世纪80年代的主导趣味,即被我们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描述:“如今主导的趣味是古典的。我们现在使用的一切都是靠模仿最近在意大利发现的那些模型而制造的;它们通过触发我们对古希腊或罗马趣味的回忆……占据了我们的想象力,这些回忆经由我们青春时期的学习与愉快的时光在我们的脑海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让我重复从布迪厄那里借来的一句话:英国公立学校的古典教育体系制定了我们的思想路线与范式。“路线”既有字面意义也有具象涵义,“路线”在之后被化为现实:英国年轻人通过亲身在意大利古典之地上体验古迹并随后将这些古迹所激发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叙述并带回英国。艾莉森牧师所描述的“占据我们思想中如此重要的地位”正是演化而成的思想风格即古典主义,它被进一步转化为物质财富、转化为新古典主义。
吉本《衰亡史》终卷(第六卷)的后续章节已为我们提供了古典主义的定义,即对古代学识的使用和滥用,接下来他讨论了对古罗马统治下“巨大而丰富宝藏”的掠夺,标题为“物质的使用与滥用”。吉本追溯了“国内外掠夺”对城市及其古老建筑的系统性破坏,从野蛮入侵者通过移除大理石等珍贵材料“在一瞬间篡夺了前几个时代积累的辛劳和财富”,到后来土著罗马人通过“呼唤宿命或迷信”来恢复其构造。让我们跟随吉本,将新古典主义的定义在接下来理解为对物质的使用与滥用。
本文译自Coltman,Viccy.“(Neo)classicism in the British library.”Fabricating the Antique :Neoclassicism in Britain,1760-180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p.1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