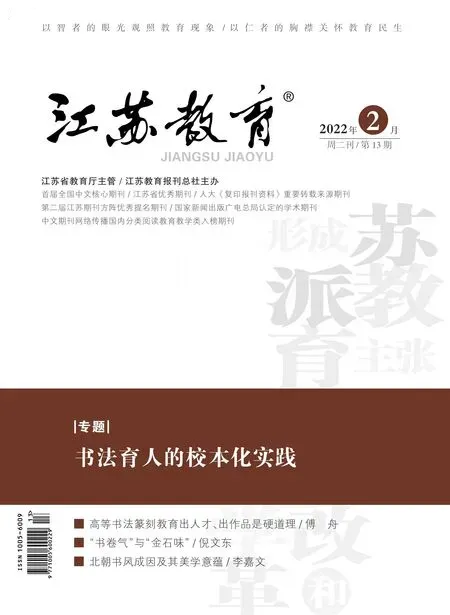新蔡葛陵楚简书写风格研究
王韬霖
《新蔡葛陵楚简》(以下简称《葛陵简》)是1985年在河南省新蔡县葛陵故城出土的战国竹简。现在对《葛陵简》的文字释读、文本内容、简牍形制、抄写年代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基础研究,已具备开展相关书法学研究的学术条件。同时,《葛陵简》由于数量大、文字多、抄手情况复杂,有助于我们整体地把握当时的书写情况。据判断,《葛陵简》抄写于战国中早期之交,这正好弥补了这一时期战国楚简的缺环,因此,对于《葛陵简》的相关书法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它上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楚简,下启战国中后期的包山简、郭店简、清华简、上博简,不仅有助于将战国楚简的书法研究形成一个更完整的序列,而且有利于梳理战国以来毛笔笔法的渊源及变化。本文拟基于《葛陵简》书法形态学的形式分析,进行相关先秦书法材料的对比研究,将《葛陵简》置于战国书法系统下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从个案研究的角度着眼,一窥先秦文字的书写情况和风格流变。
一、《葛陵简》的书写特征——书法形态学的分析
《葛陵简》系抢救性发掘,竹简出土时已因盗墓扰乱而全部残断。该简的内容多为卜筮祭祷,所以简与简的文本内容没有连续性。加之《葛陵简》数量较多,一共有1571枚竹简,这样复杂的情况导致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有多少个书手,也不确定是哪位书手写了哪几支简,这为《葛陵简》的书写风格分析增加了难度。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使我们更能突破单一书手书写习惯的局限来把握当时的整体书写情况。所以,我们先对《葛陵简》中不同风格的字迹做一个分类,分别描述其书写特征及其对笔画、字形的影响,然后对《葛陵简》的整体面貌和特点进行分析,这样能从书法形态上更好地把握《葛陵简》的书写特征。
(一)丰富多样的笔画形态
从出土的1571枚竹简来看,《葛陵简》系多个书手书写,字迹之间的特征差异明显。考古人员曾这样描述:“大部分墨迹清晰。由多人书写而成,字体或秀丽或奔放,字距或密集或稀疏,显示出不同的书写风格。”这是对于《葛陵简》书写风格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在进行下一步书写风格研究之前,还需要做一个更加细致的分类。但是,由于《葛陵简》的内容散乱,即使对那些书写风格很接近的简,我们也不能断定其由同一书手所写。以下字迹分类,主要按照笔画形态的差异来划分。
在《葛陵简》中,按笔画形态的差异,大致可以可将单字分为以下几类:






由此可见,不同的用笔方式在战国中早期的《葛陵简》就已有充分的体现,而作为日常的手写体,这样的用笔很可能是书手无意识所为,大概是由于个人生理机能的不同,在下笔的轻重、控笔的稳定性上存有着差异才形成这样千姿百态的笔画形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差异性书写背后的同一性,即《晋书·束皙传》所载“头粗尾细,似蝌蚪之蛊”的“蝌蚪文”笔法。但“蝌蚪文”笔法只能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在这一笔法系统的内部,由于书写者、书写工具材料、书写用途等因素的不同,笔画形态又有着比较细致的分化。而在战国中后期的典籍简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些不同笔法的延续,也看到了各种书写方式更加成熟、稳定的表达。
(二)方扁的字形和文字的使用
1.字形多呈方扁之势。

这样呈方扁的字势在楚文字中很常见,特别是在文书类简中,呈横势的字形有着绝对的优势。下面我们选出一些《葛陵简》中的常用字与其他楚简进行比较,这样能比较直观地看出《葛陵简》字形方扁化的特征。


表1 战国简常见字形对比
关于字势呈方扁,丛文俊先生认为“在楚系墨迹书法中,字形或纵长,或方扁,并无一定规律,或什么特别的意义。楚简帛字形或方或扁,系书写者的个性风格使然”。这是将字势的不同归因于书手的个性差异,但也有另一派学者,如三峡大学美术学教授王祖龙先生认为“楚简体势横逸宽扁,横波微露向右下回曲的出锋线条增加了通篇的律动感,实际上已有力地暗示了隶变的消息”。他还说:“如果结体上字形趋扁,直线多于弧线时,则有可能对大篆构成破坏。”这是将这些呈横势的字形看作是隶变的特征之一。现在看来,不能简单将这种现象归因于“隶变”,因为隶变的根本依据还应该落实到文字构型上。但是这样大量方扁的字形写法也不能完全归结于书手的个性差异,特别是我们不能忽视出土的楚地日常文书简中,呈方扁的字形有着绝对的优势,这样的现象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在《葛陵简》中有这么多方扁呈横势的字形呢?我推测原因有二:一是为了适应日常书写较快速的需要,二是为了使文字适应简的形制。书手在一条狭长的竹简上书写时,横方向的笔画是几乎没有限制的(因为最多也就是横跨整简),而竖方向的笔画则需要考虑上下字的空隙,所以只能较方扁化地书写。这导致在快速书写的情况下,横向的笔画干脆一笔到底,竖向的笔画则简短笔程,迅速收笔,所以在葛陵简中,我们常常看到字的两边撑满整简、上下留空的章法安排,也明显感觉到越宽的简上字势就越宽。这样的书写方式有利于保证简文单字的独立性,使字与字的空隙拉开,虽然有利于简文的识读,但是也会使字势变得方扁。可能这样的书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当时文字的形体,以至于在战国后期的楚金文和楚帛书中,字形已完全呈现方扁之势。
2.继承西周古文字的写法。

二、《葛陵简》相关对比研究——先秦文字视域下的综合考察
在战国简牍的书法研究中,相关的对比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战国文字离今天有着两千多年的距离。我们时常会对这些同属于汉字系统但是又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的古老文字有陌生感,所以研究时我们必须尽可能抓住每一个能看见的材料,将其置入战国书法研究系统中加以全面综合考察,相互对照、相互参考不同的战国文字资料,这样才能跨越时间的长河尽可能认识它们的真实面貌,理清其发展线索。
总的来说,《葛陵简》的书写质朴自然,极少修饰,姿势方扁倚侧且章法不稳定,是最接近日常书写状态的墨迹。将这些日常书写的典型文本与其他战国典籍简和同出于葛陵墓中的铭刻文字对比时,能更加真切地窥察毛笔笔法的日渐成熟和当时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与战国简牍中典籍简的比较——书写的不同状态
1.与《上博简》《郭店简》的比较。
按照文本内容和书写目的,可以把战国简帛文字材料分为自述型笔迹与非自述型笔迹。从用途上来说,战国卜筮、祭祷、文书、遣策等材料上的字迹属于自述型笔迹,而战国简帛古书上的字迹多属非自述型笔迹。所以自述型笔迹一般能准确反映当时的字体演变情况,书写较为自然,而非自述型笔迹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对抄写底本、书写用途、书手态度等因素都需要考虑。
正如前文所述,《葛陵简》中已经存在不同风格的用笔方式,而将作日常记录之用的自述型字迹《葛陵简》与作传抄古书之用的非自述型字迹《上博简》和《郭店简》相对比时,我们发现,一方面这样丰富的用笔方式在战国中后期的典籍简中能找到更清晰、成熟的表达。如下图1所示,《葛陵简》与《上博简》在笔画形态上多有暗合之处,这大概是“笔软则奇怪生焉”下的“巧合”与“偶然”。但是这些偶然性的后面正是对于毛笔性能的不断开发和用笔方式的逐渐成熟。

图1 《葛陵简》与《上博简》《郭店简》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些典籍简中也能看到在《葛陵简》中少见的明显带有美化、装饰性质的书写方式(表2)。

表2 葛陵简与不同风格典籍简的单字对比
相较来说,引笔的拉长使文字拥有了一些庄重典雅的气质,符号化的装饰则使其平添了一份图画般的美感,笔画粗细的强调让字迹更显活泼姿媚,卷曲蜿蜒的写法则赋予文字一丝曲径通幽的神秘感。这些特点的变化不仅使文字的风格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同时也在提示着我们:此时的书写不仅仅是作为一项纪录文字的技术,同时还有了表情达意的功能。书手在书写的过程中,时而正襟危坐、凝神屏息,一丝不苟;时而兴致勃勃、纵情恣肆,龙飞凤舞。在日常记录中往往不拘一格,落笔即成;而在转录典籍时,常常精意覃思、刻画入微。
2.书写水平的提高与笔法解放。
李松儒将战国时期的书写者分为实用型从业者与史官、诸子等学者,并指出这两类人都有着一定的书写能力和文化水平。春秋时期,士阶层的下移、诸子学说的传播、书写工具的进步等因素促进了社会识字能力和书写水平的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毛笔笔法的日益成熟与解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狭长细小的简牍上看这么多精彩纷呈的墨迹。《葛陵简》在战国简牍的书法研究中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坐标和参照物,日常的手写体有着较快速的书写需要,其笔墨大多数是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而典籍简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刻意的成分较多,两相参照则能有很多新发现。同时,战国墨迹书写情况的对比研究也为我们还原了书法艺术发生前的原始技术积累,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书法获得了生长的条件:人们有意识地美化文字、装饰文字,开始在文字书写的过程中主动抒发自己的情感;以竹片、木牍为主的漫长简牍历史也将要走向终点,毛笔即将迎来最适合发挥其性能的书写材料——纸;笔法也逐渐从先秦萌芽而越发成熟解放,书写由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而转向为有意识的“起行止收”。虽然此时的书写不可能完全脱离实用的功能而成为一种“纯艺术”,但是在这些简牍墨迹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个性化书写方式所传递的“人”的温度。所以到了汉代,书法艺术渐趋自觉,书法逐步摆脱了实用而走向纯美。而在这之前的先秦时代,也正如丛文俊先生所说的“春秋以后,旧秩序的崩坏,为实用书体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随之而来的,就是书写水平的提高,书体及其书法美的独立”。前文所述的这些不同书手的差异性书写,和后世的“颜筋柳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这时候的简牍书写还处于以实用为主的阶段,书写方法也没有被文人士大夫系统化、理论化地表达。但这些个性鲜明的字迹启发了后世,这些丰富多样的笔画形态成为后世书法笔法的滥觞。
(二)与同时期铭刻体的比较——文字使用的不同场景
1.与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的其他书法材料对比。
新蔡葛陵楚墓中还出土了其他有文字内容的器物,这些材料和《葛陵简》一齐起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文字使用的一个横截面。墓中出土的戈上所铸铭文有两种风格,一是典型楚系鸟虫篆的风格,字势狭长,线条蜿蜒曲折却又排布规律,但它不似蒍子倗尊缶、蔡侯产戈上铭文的明显鸟形装饰,更像是王子午鼎铭文的延续,即一种独立使用的虫书,如戈N:220、戈N:180上的铭文(见下页图2)。还有一种是接近西周金文的风格,字势不似鸟虫篆狭长,也不加修饰,如戈N:198、戈N:239上的铭文(见下页图2),这种文字应当视为当时的正体,一方面是因为其字形和西周金文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文字未因鸟虫篆化地繁缛修饰而变得晦涩难认,也没有因手写体快速抄写而变得简率,理应保留着文字最大的辨识度和正统性。可见,即使在铭刻书体中,文字的风格也会有较大的差异,鸟虫篆的文字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楚人的图腾与信仰,其背后是奇诡华丽的楚文化,而无修饰的正统文字风格则代表了秩序与规则,对称、均匀、整齐的审美趋向。

图2 葛陵楚墓出土铜戈铭文
当我们将同样书(铸)有主人名字“坪夜君”“坪夜君成”的文字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到青铜戈上的铭文与《葛陵简》上的字迹有着更加明显的风格差异(见图3)。两者的用途、制作工艺、器物和文字作者等各方面的差异都影响字迹(铭文)风格的形成。与齐整凝重的青铜器铭文相比,《葛陵简》上的文字的确更加活泼自然。在有美化性质的文字中,修长均衡仍然是人们的审美偏好,而日常手写体则顾不上这么多,方扁倚侧变成了明显特征。王祖龙先生曾指出:“(楚书法)这种大篆系统主要呈现为三种以上的书体形态……其一是正体……其二是草体……其三是美化装饰性书体……”葛陵楚墓中的文字图像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又一佐证。

图3 不同载体上的“坪夜君”与“坪夜君成”
2.手写体与铭刻体发展的不同序列。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在篆书时代,实际上并行着正篆和草篆两种样式,正篆主要适应政治集团的需要,往往受官方的规约,它的演变相对稳定;与正篆并行、通行于民间的草篆则相对活跃,是隶变的主要推手,后经过积年动态的流变,渐渐演变为秦汉时代的简牍帛书。”尽管这个观点还有待修正,但确实敏锐地指出了作为铭题礼器的铸刻文字和作为日常使用的手写体有着不同的发展序列。当我们将葛陵楚墓出土的铭文和简文分别进行历时性考察时,能清晰感受到这一点。按照学界楚系青铜器和铭文的分期研究,葛陵楚墓中出土铜戈上的铭文可以看作楚系铭文成熟期的产物,同期还有楚王舍章钟铭文、曾侯乙编钟铭文可以作为参考。这一时期的楚系铭文“逐渐形成自身特色,字体趋向修长,仰首伸脚,笔画富于变化,多波折弯曲,富有美术字体风味,以后更以鸟虫书见长……”。随着楚国国力的逐渐强盛,楚人将其强烈的文化自信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熔铸到了这奇妙诡谲的文字符号之中。楚系金文的风格演变经历了沿袭西周金文风格的继承期、风格彰显的萌芽期再到此时形成典型楚系风格的成熟期,然后到简略草率的衰落期,最终和楚国一起湮灭在历史长河里。可以说楚系铭文风格的演变史深刻反映了楚国国力的兴衰史。
而当时的手写体同样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从用笔方式上来看,如徐利明先生所指出的:“(蝌蚪文)这种形态,可上溯殷商朱书、墨书,本为一脉相承,逐步演变而来……这种形态在春秋战国的手写体中已有很大变化……‘头粗尾细’的蝌蚪意态也相应地显得比较平和了”。可见,在手写体里,“蝌蚪文”笔法作为内在线索贯穿其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成熟。从文字构型上看,如上文所说,《葛陵简》文字在这一时期仍然接续着商周文字的传统写法,与《曾侯乙竹简》《信阳楚简》上的文字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在战国中晚期,楚文字才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性特征。虽然战国晚期经过秦文字的统一,对楚文字的形体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但是楚文字中遗留的许多用笔方式仍然可见于秦汉的隶书中,并且随着文字发展的脉络一直传承到今天的楷书、行草书之中。
同时,尽管有着各自的发展线索,战国时期手写体与铭刻体也时常会有交集,如清华简《保训》篇就有着明显与铭文鸟虫篆相同的修饰符号,上博简《用曰》和《鄂君启节》在字形上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在战国后期楚系铭文与手写体也有过短暂“合流”。这样看来,铭刻体与手写体、正篆与草篆、正体与草体正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应统一地前进着,它们互相影响、交织但又保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从三代的青铜、秦汉的石刻、六朝的碑版,在后来的刻碑刻帖;从先秦的简牍、两晋南北朝的残卷,到后世的纸笺信札,这些构成了中国文字、书法史上的两条主要线索,以至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提出“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这不仅仅是“帖”与“碑”的差异,更是手写体与铭刻体辩证发展的结果。
《葛陵简》的出土为我们揭示了战国中前期日常手写体的基本面貌。随着战国简的不断出土、公布,人们越来越希望通过这些尘封已久的竹简木牍来一探当时的书写情况。虽然现在的战国书法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相关学术论文也层出不穷,但仍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如在《葛陵简》等文字图像里,能看到不同场景中,当时人们对于文字的造型、书(铸)写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导致楚文字里也存在类似秦书八体的现象?又如现有秦地和楚地出土的墨迹材料较多,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秦系文字和东方六国文字有着书写风格上的差异,那么在六国文字的内部是否也有着这样的书写差异?还有六国文字的用笔方式又是如何具体影响后世隶书、楷书和行草书的笔法?这些问题,一方面还需等待更多文字材料的出土,另一方面则需要基于现有材料进行更加细致的对比研究、更加精确的图像学分析、更加宏观的综合考察,唯有这样才能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境,早日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