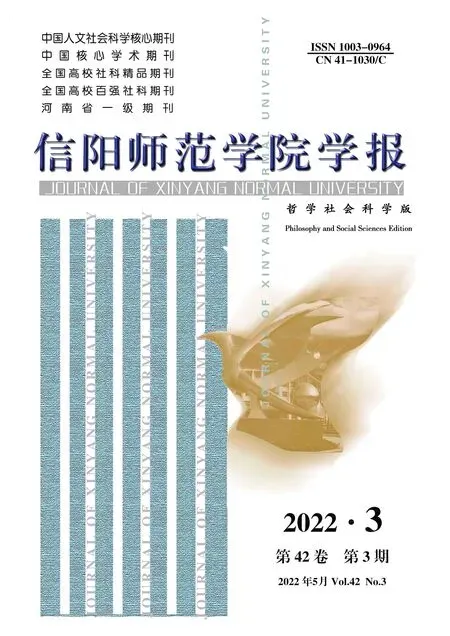评书艺术的承继与发展
——兼论英国“说书剧场”的实践
彭宏宇
(海燕出版社 儿童文学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16)
评书,又名讲书、平话、说故事等,是中国民间优秀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是我国独有的曲艺表演形式,其历史源远流长。评书艺术以其节奏的干净利落、故事与情理的交互融合、情节的跌宕起伏和语言的通俗简洁,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为了更好地呈现说书场景,先看如下描写:
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自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
那说话人五十来岁年纪,一件青布长袍早洗得褪成了蓝灰色。只听他两片梨花木板碰了几下,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羯鼓上敲起得得连声。唱道:“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1]1
这是金庸先生著名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开篇,描写的是说书先生张十五流落江南牛家村,讲评《叶三姐节烈记》而与郭啸天、杨铁心相遇的故事。这位张先生的打扮、行头,和他开讲前唱的“定场诗”,无一不是早期评书艺术的一种体现。评书艺术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一、评书的历史
评书是我国传统的曲艺表演形式之一。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里说:“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2]93根据传说,评书起源于东周时期,而周庄王姬佗是评书的祖师爷。他派遣梅、衡、胡、赵为“四大善相”奔走四方以宣传王道教化,祈求风调雨顺。据传,后世评书“北四门”即源于此。根据可以考证的史料,评书艺术“始于春秋,兴于唐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奔走天下,劝谕君王;瞽者优伶,讽喻实事。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典故和譬喻,这被认为是评书艺术的肇始。隋唐时期,“说话”这一评书艺术的雏形开始出现,不仅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也逐渐进入宫廷和寺院等“大雅之堂”。更为难得的是出现了“市人小说”“唐传奇”等脍炙人口的新型文学艺术形式,给“说话”艺术提供了可靠的文学载体。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旺发展,印度传来的佛教逐渐和中国本土思想结合,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禅宗”。到了隋唐时期,僧人为了讲经说法之便,也为了增加信众听经的兴趣,时常会在传道之时夹杂一些历史典故、民间传说乃至当朝贤臣名将的事迹,这就形成了“俗讲”。慢慢地,僧人们仿照“经变”画的形式将这些故事画成图画,编撰成册,最终形成“变文”流传民间[3]45-64。
北宋年间,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勾栏瓦舍间已有许多“说三国”和“五代史”的“说话”艺人。《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汴京人霍四究、尹常卖,“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4]108-109。到了南宋时期,“说话”艺术逐渐形成“小说”“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四家,或谓“银字儿”“铁骑儿”“讲史”“说经”四家[4]32。题材和形式开始专业化。我们常说的“宋元话本小说”,就是将宋元时期“说话”艺人讲演所用的底稿收集、记录而成。四大名著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中的故事已经在现存的宋代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三分事略》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初见端倪。这些最终成书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瑰宝——长篇章回体小说,都有着十分明显脱胎于话本的痕迹。且不说“章回体”的形制本身,就是为了方便说书人将长篇故事“分章别目”“简断截说”。单以《三国演义》为例,开篇常见“话说”“且说”“又说”,行文中间往往“有诗为证”“有诗赞曰”,一回末尾总以“且听下文分解”做结,正是不在场的叙述者——说书人存在的证据。
近代意义上评书艺术的创始人,后人多认为应是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最初评书只是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称为“弦子书”,在柳敬亭手上发扬光大。他师从莫后光,得到老师真传,擅长《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精忠岳传》。黄宗羲《柳敬亭传》记载:“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净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5]260技艺卓绝,出神入化。更为难得的是他所说过的评话,曾经由时人整理成《柳下说书》8册传世。后来,评书在晚清光绪年间传入皇宫。因皇宫唱歌多有不便,于是改说唱为“评说”,于是评书的艺术形式便基本固定下来。
二、评书的艺术特色
近代以来,因为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涌现了一大批评书艺术大家,远有双厚坪、王杰魁、连阔如,近有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这些评书艺术家不仅继承了老一辈评书艺人的传统,还各抒机杼,创作新的作品。
不仅如此,“说书人”的艺术传统仿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基因和血脉。金庸、古龙等先生以武侠为题材创作的通俗小说,便往往以说书人作为引子,上文中的张十五便是一例,古龙先生《多情剑客无情剑》中天机老人和孙小红爷孙俩也是一例。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曾说:“在我的早期作品中,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我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的早期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6]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评书”艺术经久不衰,独树一帜,更在广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心中占有特殊地位呢?笔者认为从评书的艺术特色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讲演结合
评书是一种语言艺术,和相声艺术一样,都是传统曲艺的一种。但评书更是一种表演艺术、还是舞台艺术、剧场艺术。根据英国当代著名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对戏剧的定义:“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7]3毫无疑问,传统曲艺和传统戏曲一样,都是戏剧的一种。但是,评书艺术和其他戏剧形式有明显不同,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尤其重视唱腔和身段,也不同于西方古典主义戏剧(指亚里士多德定义下的戏剧传统)注重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评书艺术是一种讲演结合兼顾两者的艺术。
讲,首先便是讲故事。在评书表演中,讲述故事情节,叙述来龙去脉,描摹人物外貌,形容自然环境,几乎全靠表演者的一张嘴。此时的表演者,是一个“出场但不介入”的存在,好像记者手中的摄影机,没有任何刻意的镜头语言,不经任何有目的的后期剪辑,只是忠实地记录——叙述着一切。但是,评书不仅讲故事,更要讲道理。每当此时,本来视域受限的描述者忽然变成了全知全能、跨越时空的叙述者。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评书表演中见识的“子曰诗云”,正因如此,讲述东汉三国故事的说书人能说出“唐代杜工部有诗赞曰”,而刚刚还在某时某地的叙述者,一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能化天涯为咫尺。这种叙述者的角色能力的切换和变化,本已十分值得玩味,可评书艺术里还有“演”的重要成分。
演,则意味着表演者在描摹主要人物心理,呈现主要戏剧矛盾冲突的时候,需要代入角色。这往往意味着从第三人称叙述转向第一人称。当叙述和表演在一个表演者身上结合,就意味着他需要不停地跳进跳出角色——自然也就意味着天然的“间离”。毫无疑问,这对表演者的要求是极高的,虽然评书表演往往不要求服装道具,对人物的塑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但一部好的评书,重要人物何止十数?如何能各得其妙,迥然而异?这就要靠评书表演者利用声音、身段、动作等方式惟妙惟肖地模仿和再现了。
(二)自由度和程式化
评书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兼具自由度和程式化。它的自由度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评书的形式十分自由。近代以来,评书多为一人于桌后坐着表演,着长衫,道具有醒木、折扇和手帕等。看似一板一眼,皆循规蹈矩。但实际上,纵观评书历史和现代发展,其形式自由度很高。一是不限人数。地方评书往往有伴奏或帮腔,我们都熟悉的袁阔成和田连元两位大师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登台表演“二人评书”《难题》,相比于同样多是两人表演的相声,评书更注重故事性和议论性,而非趣味性。二是不限器乐。这点更好理解,现代评书脱胎于“弦子书”,本身就是有伴奏的。时至今日,由于地域不同,快板、大鼓、三弦、二胡、四胡、琵琶等乐器仍然常见于各地评书表演。三是不限服装。传统评书着长衫,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评书表演者着装较为随便,如长衫、西装、中山装,乃至着便装的都屡见不鲜。
其次,评书的题材十分自由。传统评书多以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为主,但并不局限于此。尤其是当代以来,随着广播评书、电视评书的发展,言情、侦探、官场、商战甚至鬼神故事,都成了评书涉猎的内容,尽管这其中难免良莠不齐,甚至不少评书题材就是以奇情怪事为噱头博取眼球的,但题材选择之自由无须赘言。
再次,评书的表演十分自由。评书表演临场发挥的空间很大,对同一部作品的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会因为评书流派不同、师承不同、表演者不同而大相径庭,尤其是“评说”的部分,更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因为表演者的动作、神情乃至讲述时的语音语调、遣词造句,都会影响到艺术效果的表达,即使是同一位艺术家表演同一部作品,也很难保证两次演出完全一致。最初的话本,往往只有故事梗概或大纲,被称为“册子”或“梁子”。流传至今的传统评书,都有着明显的口头文学的特征,即它们都是文人个人创作和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结晶。这种流变和传播,保证了评书表演的自由度。
但是,评书艺术之所以能代代传承,源远流长,不仅在于它讲究自由度,还首先是一项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艺术。这一点与京剧等很多戏曲艺术有相通之处。评书艺术的程式化也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作为观众,我们首先感受最明显的是评书语言表述的程式化。评书并不讲究凝练,相反,更多时候追求的是铺陈和上口。比如,形容男性,一般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形容女性,则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人俊美则面如冠玉、貌比潘安;形容人威猛,则燕颔虎须、膀阔腰圆。不仅如此,评书中的武器、宝马,往往有着一个朗朗上口、云山雾罩的响亮名字。比如,评书大家们讲《说岳》,岳爷爷拿的是“沥泉蟠龙枪”;岳云用的是“八大锤”之首的“擂鼓瓮金锤”;岳雷扫北,用的是“八宝陀龙枪”。说到宝马,绝不能叫白马、黑马、红马,也不满足于白龙马、乌骓马、赤兔马,偏要叫“照夜玉狮子”“踢雪乌骓马”“赤炭火龙驹”。说到装束,那就是“凤翅紫金冠”“嵌宝狮蛮带”“雁翎黄金甲”。
其次是评书的故事结构程式化。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以“定场诗”开场,或者以一段小故事引入正题;讲述故事的场景,叫作“摆砌末”;如果介绍新出场的人物,就要跳出角色,说一段“开脸儿”,把人物的出身、来历、相貌、性格等特征做一交代;而如果需要评价、赞美人物的品德、相貌,又往往采用对仗或者骈体韵文,称作“赋赞”;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运用排比、重叠的句式和顶针、回环的手法以强化效果,是谓“垛句”或者“串口”;最后,为了吸引听众、制造悬念,往往要用“关子”和“扣子”作为基本结构,使得表演环环相扣,令人欲罢不能。
再次就是评书艺术动作的程式化。这一点最容易被观众和听众忽略,说书尽管有表演的成分,但因为条件原因并不追求惟妙惟肖、大开大合的表演。在评书艺术中常常用“帅”和“斗”概括评书表演者的动作程式。其中“帅”是指面部神情和肢体语言,包括口、手、眼、身、气等的运用;“帅”字还有另一个解释,是说书人举手投足、转身回首、左顾右盼,都要讲究美好、合度。而“斗”则指的是动作范围,在曲艺表演中演员的动作以在前后左右三步以内为宜,不能远离桌子。此外,评书表演的动作还讲究“外五行”和“内五行”,俗称十字诀。内五行是指“心、神,意、念、 候”,外五行包括“手、眼、身、法、步”。
(三)高台教化
评书作为民间传统说唱艺术的一种,和中国戏曲一样,在注重故事性和娱乐性的同时,都十分注重对百姓的教育,所谓“高台教化”。诚然,因为历史的局限,在传统评书中难免有许多糟粕内容,诸如对封建君主的愚忠,对“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的迷信,对于女性“三贞九烈”的压迫和摧残等。但评书艺术的基本格调宣扬了人性美好,弘扬了英雄正气,反映了百姓惩恶扬善的基本诉求和“善恶有报”的朴素价值观。传统书馆的门口往往一边写着谈今论古,一边是醒世良言。这正是对评书艺术内容和目的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评书是一种口头艺术,是来自于草根市井的,这也就决定了它必然有着针砭时弊、为群众发声、呼号求告的作用。
近代评书鼻祖柳敬亭的老师莫后光曾说:“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8]1057正是说评书艺术,究其实质是和儒家精神相一致的。评书艺术是中国人骨子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是中国人“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的豪迈沧桑历史观的集中体现,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士的精神。可以说,理解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就能理解为什么评书艺术经过时间考验,还能保持生命力,并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地位特殊了。
三、东学西渐谱新篇
历史的轮回耐人寻味。曾经,近代中国借鉴西方戏剧理论,系统总结了中国传统戏曲理论,改革了传统戏曲,并涌现出一批“新戏”,进而诞生了“话剧”这一概念。而中国的传统舞台艺术流传到西方后,不仅使得德国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布莱希特受到启发,相对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提出了“史诗剧”概念,更把“间离效应”从文学上拓展到了戏剧中。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评书这一中国传统民间表演形式恰好和布莱希特得自中国戏曲的舞台艺术理念十分吻合:因为其天然地要求“间离”——表演者既是叙述者又是角色——打破了剧场艺术的舞台幻觉;又因为评书艺术强调“敦风化俗”“高台教化”,这一点和布莱希特对于戏剧教育作用的追求不谋而合。他认为戏剧不能仅满足于给予观众情感刺激,更应该激起理性思辨。“史诗剧并不反对情感,它试图检验情感且不满于仅仅去刺激情感”[9]96。布莱希特的戏剧理念对英国战后戏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创立的柏林剧团曾经于1956年、1965年分别两次访问英国,将布莱希特最有名的几部作品搬上舞台。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英国开始更加注重戏剧的教育性、现实性和战斗性,戏剧应该服务人民,改变社会。在这样的思潮下,英国出现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孪生兄弟”—那就是充分继承和发扬了布莱希特戏剧理念的“说书剧场”(Story-telling Theatre)。“说书剧场”是教育戏剧(Educational Theatre)的一种形式。教育戏剧注重互动参与,寓教于乐,常常被用于青少年的读写教学,或者用来处理棘手但难以回避的话题,诸如性、毒品、种族、政治、犯罪等。“说书剧场”的概念源自英国一个名叫“共同经验”(Shared Experience)的剧团。1975年11月,该剧团提出“通过演员创造一切,而不借助任何技术效果、布景、道具、服装或化妆直接搬演故事”。如同评书一样,表演者(演员)成为演出的焦点和中心,一切故事和情节都由演员来讲述,戏剧中出现的一切角色,甚至包括自然和环境描写,都由演员来饰演和表现。表演者必须发动一切“工具”来实现剧场效果,包括但不限于自己的声音、语言、文字、肢体等。对于大多数“说书剧场”来说,舞台上不借助灯光、道具、服装、布景,只有表演者自身(有些情况下可能演员会给自己配乐)。如同评书艺术,演员既是叙述者:交代前因后果,推动情节发展,描述次要角色等等;又是表演者,在需要的时候由第三人称切换第一人称,声情并茂地进入角色。华威大学戏剧与剧场教育的两位资深教授Joe Winston和Johnathan Needlands近年来一直在努力通过说书剧场,把更多中国传统故事介绍到西方[10]。
随着时代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如以评书、相声为代表的传统曲艺和京剧及地方剧种构成的戏曲艺术在国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老艺术家纷纷谢世,优秀节目失去传承,青年一代后继乏人,广大群众不闻不问。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并相信,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形式仍然是有着生命力的,奋斗在一线的艺术家们仍然在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新鲜血液也在不停注入这些领域。比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珮瑜一方面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另一方面也通过参加综艺,探索传统戏曲和潮流的结合;郭德纲摆正了相声的位置,所谓“雅要雅得那么俗,俗要俗得那么雅”,把“笑”重新带回了剧场;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也大胆创作了《寇流兰与杜丽娘》,尝试把东西方古典的精华结合起来;评书大师刘兰芳在2020年再收新徒,76岁高龄的她仍然在为曲艺界发光发热。放眼国外,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意大利即兴喜剧(La Commedia Dell'Arte),也被当代许多表演艺术家重新挖掘,作为他们艺术表达的载体,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品,如蒂姆·罗宾斯的《自由之路》。
评书艺术针砭时弊,抑恶扬善,既在弘扬社会正气,传承中国文化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传统题材的《三侠五义》《精忠岳飞》和《白眉大侠》等;又贴近生活,反映现实,如袁阔成反映神舟七号载人航天的《飞天评书》,田连元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国企高管贪腐列传》等,其精神内核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主要依靠声音来呈现的这种简单的形式又符合当下快节奏生活的需要,可以和“听书”“直播”等新的信息传播形式相结合。我们不妨借鉴西方经验,在主动放下身段,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加积极地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与先进的传播、教育理念相结合。降低门槛,扩大受众,把经典的传承和青少年观众的教育培养结合起来。这或许是未来继承并发扬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又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