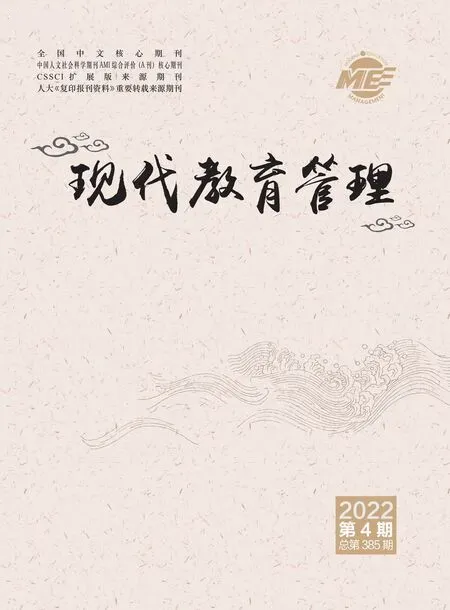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内涵及其演变①
——基于评价实践的视角
洪 茜,郭 菲,郑 湘,哈密什·科茨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现代意义的博士生教育肇始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洪堡柏林大学,旨在培养独立从事学术研究、有能力创造新知识的专业学者。此后,欧美各国纷纷在现代大学中设立博士学位,通过博士生教育培养专门的研究者和大学教授。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工业化、信息化的技术革命浪潮改变了国际竞争格局,科学技术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综合国力的贡献日益突出,率先探索、发现前沿知识,掌握核心技术对国家掌握新兴产业领域的主动权、话语权,占据战略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支撑意义。在该背景下,博士生教育对科技的贡献、在研究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得到广泛认同,博士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蓬勃发展的博士生教育也面临不同挑战和问题,包括学生流失和延期现象[1]、培养平台和导师指导水平尚待提升[2]、狭隘的培养导向未适应社会需要[3]等。如何提升博士生教育质量引起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广泛关注。然而,博士生教育质量这一抽象概念的界定仍不清晰。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何种演变趋势?未来博士生教育评价所依托的质量视角将如何转型?为探究上述问题,本研究拟基于20 世纪以来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开展背景及内容,对纷繁复杂的质量评价背后蕴含的质量内涵及其演变趋势进行提炼,并初步提出新时代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研究的崭新视角及相应评价要素。
一、学术地位:学术系统的自发追求
现代博士生教育的诞生有其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在19世纪初的德国,出于对政治解放、文化自由等理性的向往,洪堡等人发现,国家和社会的理性发展需依托于培养有理性和知识的公民,而旨在发现和分析“真理”的科学研究活动是培养该类人才的主要途径。[4]为达成这一目的,洪堡提出对大学进行改组,将纯粹的科学观念置于首要地位,将师生主要活动迁至科学探究,并在教学内容中渗透最新科研成果。[5]大学学者追求纯粹知识,博士学位则授予能驾驭原创性知识的人。[6]在洪堡理念下,教学与科研在博士生教育中实现联结统一,博士生教育承担了培养未来知识生产者与知识生产的双重职责。
19 世纪末期起,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不断深化,科学研究与博士生教育地位日益凸显。一方面,科学研究的概念开始从个人理想上升为人类的崇高职业,声望显赫。[7]另一方面,科学研究被视为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有竞争地位的手段。大学通过雇佣有志于科研的教授、获得社会慈善机构经费赞助、建立能吸引著名科学家的实验室等方式,以提升其声望等级。[8]
在该背景下,博士点享有的学术声望、资源、产出等条件在内的学术地位被视为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内涵,基于“学术地位”视角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开始兴起。该类质量评价多是学术系统自发或自愿参与的行动,目的包括帮助高校寻找高质量教员[9]、比照高校学术竞争力、为学生提供参考信息等[10]。评价设计者和实施者主要为各领域学者,呈现专业主义的特征。早期质量评价内容以学术声望(如同行对学术工作的认可度、对毕业生的认可度)为主。随着国家和区域数据库的建立和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学术资源(如科研经费、科研平台、师资、生源)、学术产出(如论文发表数量、论文被引用率)等要素也纳入了评价内容。美国自20 世纪20 年代起开展的多项博士点声誉评价是该类评价的重要代表。例如迈阿密大学校长休斯(Hughes)于1924 年针对38 所高校博士点进行的声誉评估,通过向40 至60 名杰出学者发放问卷,调查他们对受评博士点声誉的排名意见。[11]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0 年开展的博士点评估内容包括博士点的规模、毕业生特征、声望调查结果、研究支持、学术发表等情况。[12]我国于2002 年起开展的学科评估同样体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评估秉持“自愿申请、免费参评”原则,旨在帮助高校了解优势与不足、促进学科内涵建设,内容包括师资队伍、支撑平台、科研成果、科研获奖等。[13]
基于“学术地位”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与博士生教育的两大内在属性相契合,相应评价也在较大程度上符合学术系统内部成员对质量观测和提升的需求。然而,随着博士生教育与政府、产业界等外部环境交互的不断深化,同样作为重要利益相关主体的外部成员看待质量的视角可能与学术系统存在诸多差异。此外,这一视角主要指向“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客观要素,对于教育活动本身的实际过程缺乏关注。因此,单一的“学术地位”视角的局限性逐渐凸显。
二、公共效率:公共投入的必然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防发展、科技进步、社会重建、国际竞争的需求促使多国大力投资建设高等教育系统,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高等教育入学率因此不断上升。在政府投资下,高等教育升学人数增加、具有博士招生资格的机构数量不断增多、学生资助机制日益完善,博士生教育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然而,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在石油危机、福利开支过重、政府职能和规模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弊端。[14]在该背景下,吸纳私营部门管理模式、具有目标定向、绩效考核等现代管理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思潮开始在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流行,作为公共财政拨款重要对象的高等教育系统也被卷入其中。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高校在博士生毕业率、毕业年限等表现上的不尽人意进一步加剧了对博士生教育的公共资源利用效率实施问责的迫切性。
由此,公共投入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效率关系被视为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一部分,基于“公共效率”视角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开始流行。评价一般由政府或其中介机构发起,目的在于监督和促进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评价内容包括既定目标达成度、博士生毕业率、毕业年限、就业率、学术产出水平等。[15]例如,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于1986 年至2008 年间开展的研究评估实践(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评价内容包括学术人员规模、教师研究产出、研究资助途径和数量等。[16]澳大利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开展了多项相关评价,如高等教育质量署(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gency)分别于2002 年和2007 年开展的两轮院校教育质量审核,从方式(Ap⁃proach)、实施(Deployment)、结果(Results)、改善(Improvement)四个方面对教育质量进行评判。[17]为“监督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巩固并不断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18],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自2005 年起开始开展每六年一轮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定期评估。一是各学位授予单位进行自我评估并确认是否参与后续评估;二是政府组织有关专家根据明确标准对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基本状态进行评估;三是博士学位论文抽查等。[19]此外,韩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于2014 年起联合开展“博士毕业生调查”,重点对该学年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在校情况(如学费及支持来源等、期刊论文发表)、毕业规划(如出国计划、求职意向)和求职情况(如是否已经获得岗位录用、岗位类型)进行调查。[20]
基于“公共效率”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及其评价虽符合政府作为公共财政代理者对质量监督与提升的需求,但也伴随诸多争议。将私人企业管理模式运用于博士生教育,既为博士培养单位设定了明确、具体的发展目标,也要求对其目标完成情况展开绩效考核。然而,博士生教育并非固化的系统,作为创造性活动的知识生产以自由为核心属性[21],学生个体发展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固化目标不利于创设有利于知识生产和学生成长的自由环境。此外,在结果上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如毕业率提升、学术产出效率)也带有一定的急迫性和功利性。
三、市场产品:双重市场的产品需求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博士生教育的内外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首先,劳动力市场对高校“输出”的博士毕业生提出新的能力要求。一方面,随着知识生产从模式一的学科内在逻辑转向模式二的跨学科问题导向逻辑,学术劳动力市场对于科研工作者能力的要求除了相对狭隘的专业能力之外,也开始包括更广泛的跨学科和知识应用能力。[22]另一方面,随着博士毕业生就业的“外溢”,作为重要就业出口的非学术劳动力市场既关注博士毕业生在结构上是否能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也尤为重视毕业生是否掌握了非学术职业所需的沟通表达、团队合作、领导管理等可迁移能力。[23]其次,博士生作为“消费者”的属性凸显。高等教育扩张需要持久的外部支持,然而对高等教育的低公共投入回报率的担忧[24],以及将高等教育作为私人利益的定位[25]影响着政府将有限公共资金分配至高等教育预算的意愿。大学经费的下降带来研究生教育投入的减少[26],学生承担的教育成本上升,其作为教育服务产品消费者的属性加强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使得教育市场化程度加深,英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率先明确将高校列为出售教育服务的经济组织[2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于2002年提出了“出售高等教育”概念[28],这导致对学生的消费者属性的认同日益深入。此外,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扩大,博士生在年龄、民族、来源国、毕业院校、前置学位、学习基础等背景上呈现多元特征,部分学生急需在入学后接受系统课程学习。这导致欧洲等地区的博士生教育开始由原本“古老、亲密的个人关系模式”转向“更加正规的、大批量的安排”。[29]教育模式的结构化使得对教育过程的监控和评价具备了更高的可行性。[30]
在上述背景下,是否能为劳动力市场或学生消费者市场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成为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的一部分,前者为人力,后者为教育服务。基于“市场产品”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逐渐广泛流行。其中,基于“劳动力市场产品”的评价主要关注与博士毕业生有关的“结构”和“能力”要素。前者主要评价博士生毕业后的基本职业情况(如所在领域、职业类型、薪资等),通过职业结构呈现劳动力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趋势。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自1973 年起开展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31],澳大利亚2009 年起开展的“超越毕业调查”(Beyond Graduation Sur⁃vey)[32]以及从2016 年起替代它的“毕业生成果调查—纵向”(Graduate Outcomes Survey-Longitudi⁃nal)[33]均重点调查博士生毕业数年后的职业类型、工作领域、薪资水平等。后者主要评价雇主或博士毕业生自身对后者所具备职业能力的满意度,旨在分析毕业生能力是否能够满足就业单位的需求。例如,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于2007年委托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开展的“博士发展质量”调查,面向用人单位管理者开展满意度调查,具体包括对博士的业绩评价、对博士的满意度评价(如专业素质、工作业绩、人际沟通、发展潜力)、对博士后的满意度等。[34]澳大利亚2016 年起开展的雇主满意度调查(Employer Satis⁃faction Survey),从基础技能、自适应能力、协作技能、专业技术、就业能力等方面考察毕业生就业后的职业表现情况,2019 年有近4 700 名雇主参与了调查。[35]
基于“学生消费者市场产品”的评价主要关注培养单位为博士生提供教育服务的过程、教育帮助个体取得的职业成果等层面。前者主要评价在读学生或毕业生对博士项目培养过程的满意度。例如,澳大利亚于1999 年开启的研究生经历问卷(Post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主要调查学生对在读期间的导师指导、技能发展、论文考核、高校学术氛围等要素的满意度。[36]2005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开展的学术型研究生学位特别审查中,设置了研究环境、学生反馈和后续行动改进、申诉和投诉机制等直接反映学生发展需求、意见反馈渠道是否得到满足的维度。[37]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于2006年开展的博士点质量调查新设了多项涉及学生满意度的指标,例如智力环境、社会互动、研究设施等。[38]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心于2012 年起开展的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指标包括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导师指导、管理服务等。[39]后者主要评价毕业生对当前职业状态的满意度、教育在当前职业中发挥的作用等,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华盛顿大学于1997年共同组织了博士毕业十年后调查,内容包括博士毕业生职业满意度、对教育价值的评判等。[40]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自2016 年起开展涵盖本科生到博士生群体的“毕业生成果调查”(Graduate Outcomes Survey),在学生毕业15 个月后对其进行发展状态追踪[41],调查内容包括毕业生最初发展目标的实现水平,习得技能在工作中的运用水平、教育经历在当前从事工作中发挥的价值等。[42]
基于“市场产品”的博士生教育内涵及相应评价,一方面对增强博士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契合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彰显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然而,博士生教育始终无法与一般商品销售活动相等同:博士生教育保持的知识生产属性使其呈现鲜明的学术导向,遵循专业标准;而在人才培养方面,博士生教育则早已由仅培养身为学科守门人的学者,扩展至符合更广阔行业需求的知识生产和创新型人才,面向社会具有重大的人才输出责任。“市场产品”视角强调迎合市场、满足消费者需求,可能忽视博士生教育的学术导向、专业标准和社会责任,造成不良后果。首先,过度强调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结构的需求,可能导致一些实用性不强,但对人类文化的发掘和传承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以及一些当前需求不高但未来发展潜力和价值巨大的领域遭受冷遇。其次,过度强调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职业能力的需求,可能导致教育目的由发展个体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力转向帮助个体顺利就业,对博士生教育的学术导向和专业标准造成冲击。[43]此外,作为消费者的学生潜在的功利主义倾向可能使博士生教育偏重于职业能力训练而忽视严格的规范性学术训练,从而模糊学术导向和专业标准。
四、学习者发展:未来专业工作者的发展进程
作为“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另一代表,基于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则是从学习者与情境的互动关系出发,探究学习者发展的建构性进程,如外部情境支持、个体发展阶段规律、个体与外部情境的互动和参与、个体发展结果等。建构主义范式自20 世纪70 年代末起开始在教育领域受到广泛认同[44],自90 年代起博士生的建构性发展进程涌现了诸多代表性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将博士生视为未来各个专业领域的高层次从业者,博士生教育为其提供了一系列习得专业知识、技能、价值、文化的机会。例如,汀托(Tinto)提出的研究生社区(Graduate Communities)和博士生坚持(Doctoral Persistence)理论分别通过阐述个体在研究生社区中发生的学术整合(Academic Integration)和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过程,以及博士生从过渡阶段、候选资格阶段到毕业阶段的学业坚持,从而剖析了个体与教育情境的互动的类型以及不同阶段的核心特征。[45]魏德曼(Weidman)根据专业角色的融入梯度,将博士社会化过程分为预期阶段、正式阶段、非正式阶段和个人阶段,在每一阶段中,个体分别进行着不同层次的知识获取、知识投入和知识参与活动[46],并最终获得专业认同和承诺等发展成果[47]。
在上述背景下,博士生作为专业领域学习者的“增值性”发展进程及其结果成为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内涵,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开始转向“学习者发展”视角,注重考察影响博士生发展的教育情境要素是否得到积极调动、博士生在教育情境中的参与水平、专业知识能力素养的培养结果等。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2014 年开始进行的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经历调查(Graduate Student Sur⁃vey of Student Experience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以汀托的理论为依据,关注课程、研究、教学、专业发展、社会和个人生活等学生在学经历。[48]澳大利亚高校课程认证中,对于研究型硕士与博士学位的课程认证设置了额外要求,规定高等教育机构需要保障教师学生能够作为学术知识社区的成员积极参与其中,具备能够用于为学生提供政策、指导、服务、资源、支持的可用基准。[49]英国高等教育研究院(Higher Education Academy,现更名为Ad⁃vanceHE)自2007 年起开展研究生研究经历调查(Post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Survey),主要考察学生主要经历(导师指导、研究技能、资源、专业发展、发展责任、研究文化)、训练和发展机会、教学机会等。[50]2007 年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开展的“博士培养质量”调查面向博士生、博士生导师、研究生教育负责人等群体,指标包括基础和专业知识、科研能力、学位论文质量、相关学科知识、外语水平、创新能力等。[51]近年来,学者不断尝试重构院校培养和学习者参与的应有之义并设计相应质量评价。例如,科茨(Coates)等人构建了涵盖博士生入学前、学习过程、毕业后的三阶段评价框架,每一阶段分别涉及院校培养、学习者参与成长的双重行动。该框架不仅将博士生的发展阶段由传统的狭隘在学过程延展至入学前的准备和毕业后的持续发展,而且将院校和学习者在各阶段的行动对照统一起来,为提升博士生教育质量提供了参考。[52]
基于“学习者发展”的博士生教育内涵及相应评价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该视角主要将博士生视为未来的专业工作者、关注专业社区对学习者应掌握素养的要求,而一定程度忽视了教育所具有的促进个体个性化、以及将个体培养成广义社会成员的功能。
通过对多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实践的梳理,本研究发现其背后依据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经历了从学术地位、公共效率、市场产品到学习者发展的演变。各个质量内涵的形成均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然而后续内涵的诞生并非意味着前一内涵的消亡或衰落,相反,当前各质量内涵在相关利益主体的认同以及对评价实践的指引中仍然焕发相当活跃的生命力,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评价是基于多元质量视角的综合体,而非仅遵从单一视角,反映了博士生教育在时代发展中日益复杂的性质。
五、展望:“共同利益”作为新时代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
(一)“共同利益”为促进他人和社会福祉作出的努力
21 世纪以来,全球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在生态环境方面,全球变暖、能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使得全球生态环境处于继续恶化的状态。在经济发展方面,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未能在各国间公平分配,收入的不平等在扩大。[53]在国际政治方面,霸权政治、领土争端、武力战争等问题使得各国人民的安全和生活遭到潜在或直接的威胁。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仍然突出,矛盾争端时有爆发,广大人民福祉的提升,稳定和谐社会的建设仍需付出巨大努力。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重大危机,社会各阶层、经济各部门和世界各国家地区均受波及。[54]疫情深刻影响和阻碍着跨国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给诸多行业发展带来长期打击,导致各级教育的机会与过程的不平等不断扩大。人类社会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究竟如何实现?这些问题成为牵引全球关注的21世纪议题。
知识和教育被视为帮助人类化解危机、迎接未来的关键要素。知识的生产和应用是人类实施改变世界的实践的根本依托。教育则通过知识的传递,培养和塑造着能够理解和关爱他人,并运用自身知识和能力改变世界的社会成员和工作者。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 年颁布了重要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建议将知识和教育视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呼吁知识的创造及其获取、认证和使用应当是所有人的事,是社会集体努力的一部分。[55]所谓共同利益,本质上是人类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56],指向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和个人所付出的努力过程与结果,这些努力的目标在于促进广阔范围内的他人和社会的福祉。
作为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不仅培养具备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工作者,并且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承担了知识生产的核心角色,因而被期待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广泛深远的贡献。越来越多的对话和研究开始关注博士生教育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属性。例如,欧洲大学协会博士生教育理事会(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Council for Doctoral Edu⁃cation)于2019 年召开的年度会议以“博士生教育的社会层面”(The societal dimension of doctoral ed⁃ucation)为主题,参与群体包括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学术领袖、博士生项目负责人和专业人员等。会议探讨了博士生教育能在哪些层面为社会做出贡献,包括帮助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扩大跨部门人员流动和协作等。[57]此外,已有研究以博士生教育的公共或共同利益属性、博士生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等为主题,指出了相关现状和突出问题。[58]
近年来,多国对博士生教育质量的评价已尝试向共同利益的质量视角转型。例如,英国拨款委员会于2014 年起以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取代原本的研究评估实践,评价内容新增了研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并于2021 年修正了研究影响的定义,将原有的以商业合作为重点的影响扩展至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政策、卫生、社区等广阔领域中的影响。[59]2016 年我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设置了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指标,下设社会服务贡献和学科声誉两个子指标,分别用于各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贡献与特色,以及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道德水平。[60]然而,如何设计全面、恰当的评价体系存在许多挑战。
(二)基于“共同利益”视角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要素
基于“共同利益”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尚处于有待更多利益主体加入探讨和逐步认同的地位,相应质量评价也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本研究对其可能指向的具体质量评价要素进行初步展望。
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是需要在教育机会层面建立公正的招生选拔机制,并适当兼顾更广泛群体的利益。一方面,为维护教育正义,保障个体受教育权利,博士生教育单位需在招生机制中设置明确、合理、公开的录取标准,公正、可追溯的招生流程,以及畅通、有效的监督与申诉渠道。[61]另一方面,考虑到教育对于促进更广泛社会群体福祉的作用,也需适当兼顾非充分代表性群体的利益,在博士生教育机会方面给予适度支持。我国于2006 年起施行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一定程度体现了上述考量。二是学生入学后,培养单位应注重在教育过程中创设有利于不同群体全面发展的平等、关怀和包容的环境。以性别为例,以往研究发现女博士生在科研环境中可能面临想法不被朋辈认真对待、导师对女性学生期望相对较低等困境,进而造成高挫败感、高流失率等问题。[62]对此,在博士生教育的过程中需要保障平等对待不同群体,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霸权、定型观念和偏见。[63]三是无论在教育过程还是结果方面,均需要注重形成博士生身为社会成员和未来高层次专业工作者所需具备的各类素养。包括身心健康、幸福感等积极生存和生活状态;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建设全球未来的团结和责任意识等道德与价值观;以及批判思维、解决问题、信息和媒体素养等能够推动和支持社会实践和变革的能力。[64]
在知识生产及后续应用和传播方面,一是博士生教育应在帮助预防、化解事关人类福祉的挑战和风险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一方面包括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有挑战:博士生教育应放大知识生产的积极影响,在研究主题选择上更加侧重于当前社会在文化、经济、环境等层面直接或潜在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研究开展过程中注重突破地域边界,寻求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智力和资源网络联合;在研究成果应用上进一步推动成果在政府、产业界、社会的实践中得到积极应用。另一方面包括消除知识生产活动本身的风险:当前知识生产活动的速度、影响广度与幅度不断提升,其中损害人类共同利益的潜在风险可能会更加频繁而具有威胁性,博士生教育应进一步反思知识生产的利弊,从根源扎紧学术伦理教育的笼子,预防知识生产的消极影响。二是未来的博士生教育需要努力推动知识成果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开放、共享和传播。当前,由于出版商、学术界等主体的多重利益考量,研究结果、数据、方法的开放途径的缺乏或高额的费用已成为阻碍学术同行和社会大众获取和使用知识成果的关键因素,在损害知识生产活动本身的同时也削弱了知识生产带来的后续社会影响和变革。对此,博士生教育可通过对博士生发表开放获取(Open Access)型论文提供支持,鼓励博士生在开放数据平台共享研究数据和方法,运用媒体平台发布最新研究介绍等途径,促进知识成果的开放和共享,推动科学理念和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王永平教授
——陈桂蓉教授
——拜根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