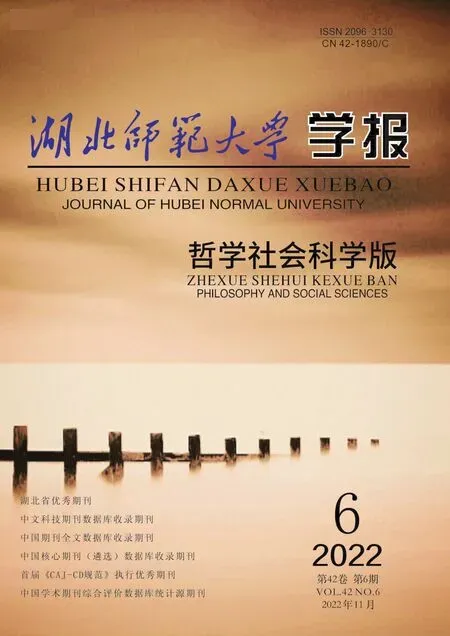《文心雕龙》的“物色论”与桐城派文论“声色观”的比较
叶当前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物色》篇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热点,位置问题、心物关系、风景与文学的关系、感物论、创作论、物与色的关系等领域均有研究。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范文澜《注》说物色犹言声色,很容易联系到桐城派的“声色”理论。然而,细读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声色”篇,发现刘勰“物色”与姚氏“声色”区别很大,故稍作比较如下。
一、物色与节物
《文选》“赋·物色”类李善注:“有物有文曰色。风虽无正色,然亦有声。《诗》注云:‘风行水上曰漪。’《易》曰:‘风行水上,涣。’涣然即有文章也。”[1]581李善理解的“物色”为偏正结构,即物的色,有形之物因有文彩而有色,无形之风因行于水上而化声为形,故亦有色。赋主铺排模状,重点在体物,《文选》“赋”的“京都”“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等类均有体物的成分在里面,只不过有些是自然景物,有些是人造景观,有的是气候节物,有的是动植物。“物色”类所选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并序)》、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等四篇,所及之物不包括江海、鸟兽等自然风景与动物,正是李善注所谓“四时所观之物色”[1]581,属于气象节物一类。
《文心雕龙·物色》开篇所及物色均为因气候变化而形成的动态节物,故谓“物色之动”,“四时之动物”,关键在“动”字上,其“物色”是指四时气候与物的动态关系下产生的“色”。如:“阳气萌”对应“玄驹步”,“阴律凝”对应“丹鸟羞”,“岁献发春”对应“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对应“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对应“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对应“矜肃之虑深”[2]693。“步”“羞”“畅”“凝”“远”“深”等都是动态词,微虫鸟兽乃至人,或行动、或情动,都因气象变化而变动。王元化《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将“物色”纳入创作论,从主客二分角度辩证分析外境与创作主体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指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须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二语互文足义。气、貌、采、声四事,指的是自然的气象和形貌。写、图、属、附四字,则指作家的模写与表现,……其意犹云: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的实践活动,在模写并表现自然的气象和形貌的时候,就以外境为材料,形成一种心物之间的融汇交流的现象,一方面心既随物以宛转,另一方面物亦与心而徘徊。”[3]90既抓住自然气象与形貌变化的关系展开阐释,又关注创作主体随物宛转的动态模写,还进一步揭示灌注主体生气的物象的文学效果,提纲挈领,直指要害,将刘勰“物色”理论推向现代文学理论的高度,尤其是“气象”一词,恰切指示了刘勰“物色”观的外延,拉近了“节物”与“物色”的距离。
潘岳《射雉赋》写“青阳告谢,朱明肇授”的四月初茎曜新、陈柯改旧、天泱泱垂云、泉涓涓吐溜、麦渐渐擢芒、雉鷕鷕朝鸲,均着眼于春夏之交的季节变换引起物象变化的动态,故徐爰注:“此以上序节物气候。”[1]416陆机《拟明月何皎皎》“踟蹰感节物”的“节物”正指明月、凉风、寒蝉等秋季物象,是独特气候影响下的独特物象[4]316。张协《洛禊赋》在铺写上巳日自然风情后总结为“美节庆之动物”[5]69,虽以三月三日为节庆,但更突出春天气象的变幻,可作节物的别解。可见“节物”是六朝固有概念,刘勰虽不用此词,但《物色》篇总结《诗经》写景物长于“以少总多”地状写节候变化下的植物、动物、天文、气象等,提出“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的观点。范《注》解释“时见犹云偶见”[2]696;吴林伯则谓“时”是“应时”的意思,“见”同现,乃“出现”的意思,以“应时出现”对译“时见”[6]896。吴氏释义似更胜。“时见”一词,抓住了物象因季节而变的动态性特点,更符合刘勰“物色”观。从这个意义上看,刘勰是熟悉“节物”概念的。
因为节物易变,所以其色难摹,体验感悟,唯在感兴。故《诗三百》篇的作者往往抓住灵光闪现的刹那,以少总多,便能情貌无遗。至于屈原《离骚》则开始触类而长,重沓舒状;司马相如等人的汉赋则丽淫而句繁,正如范《注》所谓:“状貌山川,皆连接数十百字,汉赋此类极多,所谓字必鱼贯也。”[2]696这样写作,延宕节物变幻的时间点,便只能向精细化发展,乃至近代文人“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疑作即)字而知时也”,从字里行间便可看到四时气象下的节物风貌。由少而多,由简而繁,由质而绮,节物写作虽然不断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需始终抓住气象影响下的节物展开描写。故“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2]694,尚简、更新应是节物写作的重要原则。
郭绍虞、王文生、王运熙等皆指出《时序》论述的是文学与时代(社会政治)的关系,《物色》论述的是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并同时关注到“节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王文生、郭绍虞合撰《〈文心雕龙〉再议》指出:“关于文学与现实,刘勰的贡献在于用变化发展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季节的更迭,自然的变化,通过作用于人的思想感情而影响文学创作。”[7]45王运熙则参考骆鸿凯《文心雕龙物色篇札记》列举陆机、钟嵘、萧统、萧纲、萧子显等人关于节候景物的变化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文论,证明:“南朝文人在论述文学作品(诗、赋、散文)的产生时,是多么重视节候景物的影响。”进而判断刘勰特列《物色》专篇,探讨这一理论问题,是符合时代潮流的[8]152-153。
由此可见,《文心雕龙》与《文选》的“物色”概念是一致的,刘勰“物色”所指与自然景色的范围可能不完全一致,应该是气候变化下的节物。又因《物色》篇论及节物写作方法,故似可将刘勰笔下的“物色”理解为节物的写作问题。曾大兴论述气候与文学关系时指出,刘勰、钟嵘的论述均“涉及了气候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认为刘勰所举《诗经》中的“玄驹”“丹鸟”等“物色”,“不是指一般的景物或景色,而是指随气候的变化而出现的物候”[9]85。所言甚是。而对于不受节候影响的外物,刘勰与萧统都另有分类。《情采》篇“敷写器象”、《夸饰》篇“形器易写”,其中的“器象”“形器”均为形而下者,写前者需要形文、声文、情文的统一,后者可以壮辞喻其真[5]537、608。刘永济已论《物色》与《情采》篇“虽同而实异。同者,二篇所论,皆内心与外境之关系也;异者,《情采》论敷采必准的于情,所重仍在养情;本篇论体物必妙得其要,所重乃在摛藻。”[10]162进而言之, 《情采》重在以人观物而为情造文,《物色》重在节物感人及其即兴表达。前者论创作主体入情后的写作,阐明情辞的经纬关系,因重情,故要藻采,并需处理好为情与为文的关系;后者论主体感物后的创作,阐明物辞的感发兴起关系,因重节物,故需体悟,所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景物移人情感既深,触人感兴亦速[11]324。
二、物色与功效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12]序,亦反复征引《文心雕龙》,自然熟知刘勰的文论思想。《文学研究法》在“功效”篇征引《物色》句段,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姚永朴所谓“功效”并不是指预期的贡献或效果,而是指文学可以用来干什么的问题,属于文学功能论,故其主要讨论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的关系。《文学研究法·功效》篇论文学的功效有六端,分别是论学、匡时、纪事、达情、观人、博物,即指文学可以在这个六个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在文章“达情”与“博物”两个功效上引用了《文心雕龙·物色》篇。“四曰达情”强调外物对创作主体情感的冲击与感动,再迂回到“古人性情,未有不见于文字者”,而优秀文字能够“由己及人,而使彼此之间,洞然无阂”,像汉文帝《与南越王赵佗书》、光武帝《与窦融书》那样能够“一纸定边陲”,好的文章“无论近远,放之皆准,感而遂通”[12]51,产生强烈的社会功效。姚氏论达情引《诗·七月·毛传》“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13]389,又引《物色》“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及钟嵘《诗品序》“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等大段文字,强调节物对创作主体的强大影响力。上溯经学源头,下及韩愈《送孟东野序》,看似梳理感物论,实则是关注气象节物与社会环境对创作主体的作用。一方面,四季变幻、动植有感、人心摇荡,故需要入情的文字书写表达;另一方面,反推文能达情,优秀的文字媒介可以感化读者。于是缘景动情→以情生文→由文达情便打通了,文章发生论即同于文章社会效果论,中间的文章创作过程似乎略去了。姚氏这种循环逻辑既类似钟嵘所谓直寻而获得的自然英旨,又有点像庄子目击道存而生成的文道合一,情动于衷的文章能向接受者传达出真情实感,即产生“达情”功效。
姚永朴以《尔雅》《诗》《书》《礼》《乐》与屈、宋、扬、马之词赋为博物之书,认为《文心雕龙·物色》的“诗人感物,联类不穷”一段是论述博物的文字。从字面意思看,《物色》篇列举《诗经》《离骚》、司马相如赋等模写景物的例子,呈现山水节物的样态,与姚永朴所谓的“博物”说确实有关。姚氏下引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列举河海、山岳、日月、鬼神、珠玑华实、雷霆风雨等存之编简,又引《送高闲上人序》列举“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等天地事物之变一寓于书。均从所博之物入手阐述,博观存物,便达到文学博物的目标。与“达情”可忽略写作过程不同,博物既要在宏观上“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还需要做到体物之妙、赋物之工,写出精微至境[12]54-55。《物色》篇既梳理节物的文学史,又阐明节物创作的方法原则,姚氏在“功效”篇引入此论,也是合理的。
《文学研究法》没有“物色”篇,也没有阐释节物动人的专论。然桐城派古文长于写景,桐城派文论亦有涉及物我关系的。如:姚鼐论诗本原于天地,得益于山川自然之助,其《海愚诗钞序》说:“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敦拙堂诗集序》说:“言而成节合乎天地自然之节,则言贵矣。”《左仲郛浮渡诗序》:“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余恍惚若有遇也。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14]44-49朱孝纯《罗两峰登岱诗小叙》:“天地灵秀为山水,人心灵秀为笔墨,故非笔墨不足以写山水。曰诗,曰画,此人心之灵秀与天地之灵秀相喷薄而与为融洽者也。”[15]154均从心物交融的角度阐释天地山水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桐城派传授弟子重视选本、圈点与诵读法,故论文多以文本为中心,不列景物风貌专题,自在情理之中。姚永朴将《物色》篇引入“功效”论述,亦可算权宜之法。
“物色之动,人谁获安”[2]693,古人受节物感动,无法解释其心理机能,只能以外在感性表现的手舞足蹈、长歌陈诗来表达此时的感受。钱锺书从“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分析自然与创作的关系,比古代感物说更加清晰,亦相对理性。钱先生从创作主体角度分为两大宗:“一则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二则主润饰自然,功夺造化。”前者犹如西方摹仿说与持镜照自然论,“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后者犹如西方唯美派,“此派论者不特以为艺术中造境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镕,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16]60-61两派均是主体决定自然,与物色感人仍有所区别。童庆炳阐释《物色》篇“阴阳惨舒”说时曰:“这些说法更具体细致地说明了东方的‘感应’与西方的‘反映’是不同的,‘感应’不是像反映那样忠实地复制外物,它不是镜映过程,而是在对象物的引发下的情感的对应、摇动、活跃、兴发过程,这是诗人接触到对象物之后一种比反映活动更为广阔、更为无限、更为微妙、更为神秘,同时也更具有诗意的心理活动。”[17]73从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解读《物色》篇,不失为一种合理路径,姚永朴以“达情”论物色,便入情入理了。
三、物色与声色
范文澜《文心雕龙·物色》篇注曰:“盖物色犹言声色,即《声律篇》以下诸篇总名,与《附会篇》相对而统于《总术篇》。”[2]695王运熙已驳其非,指出:“《文心雕龙》中的《声律》篇讲的是文章的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等篇,讲的是文章的色彩。虽然都讲声色,但一指自然景色,一指文章的声调色泽,二者不是一回事。”“《物色》篇的内容,是讲自然景物激发人们的创作冲动,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技巧的发展,描写景物应该注意之点等;而不是如范氏所说,是对《声律》以下讲求写作技巧诸篇的总结。”故断“范氏之说实难成立”[8]149。已厘清物色与声色的区别。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立“声色”篇,在桐城派“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个并置范畴语境下分论“声”“色”理论,属于文章声律论与润色论。显然,《文心雕龙·物色》篇虽提及“虫声”“属采附声”“黄鸟之声”“草虫之韵”等,但属于自然界的声响与文学的拟声,而不涉及文章声律问题。故刘勰“物色”与姚永朴“声色”的可比性唯在“色”这个范畴上。
姚永朴“声色”篇先论“声”再论“色”,唐文治《国文大义》设“论文之声”“论文之色”两目编排,高步瀛《文章源流》“作文之要义”下亦分立“设色”与“和声”两目。可见,“声色”一词虽然并置已久,但在文学理论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声”呈现的是声律论或声调论,“色”体现的是色泽论、设色论或润色论,与《文心雕龙》的“采”“艳”等范畴有相通之处。汪涌豪说:“‘声色’是一个并列结构的范畴,即所谓‘声响色泽’。”将两者并置追溯到鲍照《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和陆机的《文赋》[18]580。在具体解释时,汪先生仍是分为“声”与“色”两个范畴依次展开。
桐城派论文重视义理与辞章的统一,对所以为文的八个范畴虽有精粗之分,但亦能辩证分析精粗的依存关系。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说:“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19]序目26姚氏认为“文之粗者”是“文之精者”的载体,为学习的开端,不可忽视。可见,八个范畴有先后之次,而无轻重之分。刘大櫆论文以神气为最精处,以音节为稍粗处,以字句为最粗处,排出精粗次序;但粗者是精者的基础,粗者的高下决定精者的品格,故论文要重视字句音节。[20]6亦能辩证对待文章的道器关系。姚永朴论文同样既重视文章功效,又重视文章声色。《文学研究法·功效》篇旁征博引论证文学功效的具体表现时便兼及文章色泽,如:开篇引陆机《文赋》最后一段总论功效,以文章功效为第一,曰:“使为文而无功效可言,虽雕琢其辞,与《礼记·曲礼》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者何以异?与欧阳子《送徐无党南归序》所谓‘草木荣华之飘风,禽兽好音之过耳’者又何以异?”[12]47。欧阳修一文对比圣贤“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关系,旨在劝勉弟子徐无党要处理好“道”与“文”的关系,并以自警。欧阳修自谓“固亦喜为文辞”,而东阳徐生“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故要“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不能耗费一世精力于文字之间,在此语境下曰:“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21]1099-1100可见欧阳修并不是一味否定文章色泽,而是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中有主次轻重。张少康评《文赋》最后一段时也指出,“关于文章的社会功用在《文赋》中不是主要问题,而是附带论到的”[22]369,因为陆机论文提倡“缘情”与“艳”,是对儒家传统美学思想的突破。由此看来,姚永朴在论述文章功效与色泽关系时,亦只是主次轻重之别,而无重此抑彼的倾向。因而在阐述第一功效“论学”时,即指出“但文章不工,虽有此志此学,何由宣其所见,以觉当世而诏来兹?”在引用程子读张载《西铭》语、黄东发《日抄》论朱熹为文语、陆世仪《思辨录》论王阳明论学书及奏疏语后总结:“据此可见文章发挥道妙,其功效之见于论学者,固当首及之矣”[12]47-48。立志救世济世又有赖于文章之工。又如“三曰纪事”节亦曰:“此可见其文不高,不能为史;即为之,亦必不能令人传习而脍炙之也。是以退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历陈二《典》《禹贡》、大小二《雅》,以为皆由‘辞事相称,善并美具,乃号以为经’‘从始至今,莫敢指斥;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12]49姚氏强调文词对史著的重要性,并节引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证成己说。韩文其实亦强调经学著作“列之学官,置师弟子,读而讲之”的政教意义[23]607,姚永朴则略去此句,可能是有意强调经学著作的色泽而为之。由此可推,将文章的社会效益与文学性结合起来讨论,以声色服务于文章义理,是姚永朴功效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比较而言,《文心雕龙·物色》篇论节物对创作主体的冲击,更侧重情感激发。此为“物色”与“声色”的区别之一。
姚永朴的声色论是一种技巧论,其论“声”侧重于“熔铸唐宋古文家及桐城派以气势声调为要点的声律论”[24],与“因声求气”的诵读法密切相关。其论“色”则曰:“色也者,所以助文之光采,而与声相辅而行者也。其要有三:一曰炼字,二曰造句,三曰隶事。”[12]159故征引《文心雕龙·炼字》篇炼字四法、《丽辞》篇“不均”与“孤立”二病等文字讨论用字隶事之法。据此也可看出姚永朴的声色论不是文学发生论,不是感物吟志说,而是文学润色论。《声色》篇引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作文岂可废雕琢?但须清气运乎其中。功夫成就之后,信笔写出,无一字一句吃力,却无一字一句率易,清气澄流中,自然古雅有风神,乃是一家数也。”[12]161直接讲明文章不避雕琢的道理。姚永朴说:“文章色泽,犹不尽于此。广而言之,如《易》之象,《诗》之比、兴,《孟》《庄》之譬喻,扬、马之铺张,皆是。”并列举《孟子·庄暴》章“今王鼓乐于此”一段、韩愈《原毁》“尝试语于众曰”一段、李斯《谏逐客书》中间部分为例,指出李氏“即色、乐、珠、玉为喻,皆设色处也”。[12]163则将修辞手法、表达手法均纳入文章色泽论之中。从用词上看,《范围》篇用到“润色”,《声色》篇用到“色泽”“设色”等,都符合姚永朴“声色”论的用意。《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朱熹注:“修饰,谓增损之”“润色,谓加以文采也。”[25]151姚永朴所论色泽,亦是文章辞采问题,而不在于内容的增损修订。《物色》篇论述创作主体受到自然激发后的节物写作问题,涉及文章内容,至于具体怎么写的技巧,却不在本篇讨论范围。这是刘勰“物色”与姚永朴“声色”的区别之二。
至于《文心雕龙·杂文》篇“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的“声色”[2]255,则是指“七体”文章极力渲染的音乐与美色,尚没有文学理论的意义。《时序》篇“润色鸿业”应是从班固《两都赋序》引用而来,并不涉及具体文章技巧;《知音》篇“敬礼请润色”句将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润饰”改为“润色”,不知是否有意而为。但总体来说,“润色”应不是刘勰重点关注的文论范畴。他如《文心雕龙》中用到的“五色”“色糅”“色杂”“云霞雕色”“肤色”“毛色”“备色”“本色”“图色”“色资丹漆”“间色”等,均与“颜色”义相关,而不是直接用于文学作品上。刘勰不用“物色”表达文章色泽,是有其理论思考的。
四、“物色”与“声色”论的发展
《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旧题王昌龄《诗格》,多次用到“物色”一词,与《文心雕龙》“物色”论相通,亦有所发展。
“夫置意作诗”条指出作诗要以心去穿透目击之物,达到心物交融的诗境。“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卢盛江考释:“物色,自然景色。刘宋颜延之《秋胡诗》:‘日暮行采归,物色桑榆时。’刘宋鲍照《秋日诗》:‘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文心雕龙》有《物色》篇,已见前注。《文选》卷一三有‘物色’类赋,李善注”云云[26]1243-1245。卢先生所引《秋胡诗》讲的是日暮景象,鲍照《秋日诗》讲的是秋天景象,两处“物色”均指独特时段的独物风景。《诗格》在这里已明确“物色”为山林、日月、风景等,是写作的“本”;写到文章中后,物色就演变为水中之影、镜中之象。此论从虚实角度论述物色文学化的效果,非常切理。此处讲的物色,是创作主体凝心目击的独特物象,此物色经历了目击其物→心中了见→书之于纸三个阶段。此物色是与创作主体同时在场的对象,是受到彼时彼地各种外境影响的对象,具备即时性、瞬间性,是直觉的审美场,比《文心雕龙》所论“物色”在延续性上更短,感性更强。
《诗格》认为“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为高手。中手倚傍者,如‘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此皆假物色比象,力弱不堪也”。卢盛江案:“‘中手倚傍’者,为‘假物比象’。‘不相倚傍’之‘高手’,则用‘天然物色’。……‘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二句,用‘绮’比喻余霞,用‘练’比喻澄江,即所谓‘假物比象’,故为‘倚傍’。而前文所引‘方塘涵清源’等十个诗句,均为直接如实描写,即所谓‘天然物色’‘不相倚傍’。故所谓‘倚傍’,不当是指倚傍前人之作,而是指倚傍他物他色。”[26]1274-1275如此理解,高手处理物色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直寻关系,恰如《物色》篇总结《诗经》写节物那样能够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自然与心灵的关系是双融的,高手写出来诗例有“方塘涵清源,细柳夹道生”“方塘涵白水,中有凫与雁”“绿水溢金塘”“马毛缩如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青青河畔草”,“郁郁涧底松”等[26]1270;至于中手,则需要用比喻来写物象,自然与心灵是两分的,类似《物色》篇论述辞赋家写物象需要触类而长、重沓舒状一样。可见,《文心雕龙》与《诗格》论物色与文学的关系都是分层次的。
模写“物色”有一定的标准,刘勰以“简练”“新颖”与“物色尽而情有余”为准则;《诗格》重视“物色”与“意兴”的关系,以物色意兴相衬相融为好。不可“空言物色”,必须“安立其身”[26]1256,如“明月下山头,天河横戍楼”一诗,八句诗堆砌明月、山头、天河、戍楼、白云、沧江、浦沙、松风、烟霞、花鸟、芳洲等众多物象,“并是物色,无安身处,不知何事如此也”[26]1290。而意物相融时,物色纷至沓来,亦不失为好诗:“夫诗,入头即论其意,意尽则肚宽,肚宽则诗得容预。物色乱下,至尾则却收前意,节节仍须有分付。”[26]1248如“竹声先知秋”,便是物色兼意兴的好诗;“夜闻木叶落,疑是洞庭秋”“旷野饶悲风,瑟瑟黄蒿草”,则是“上句言物色,下句更重拂之体”[26]1267-1269,亦堪佳制。从诗例可见,凡因气象变化生成的物色撞击创作主体,适意而出的诗就是好诗。故其对应的景色是动态的,随气象、朝夕的变化而变化,创作过程亦是在变化中一气呵成:“昏旦景色,四时气象,皆以意排之,令有次序,令兼意说之为妙……所说景物必须好似四时者,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取用之意,用之时,必须安神净虑。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言其状,须似其景。……意欲作文,乘兴便作,若似烦即止,无令心倦。常如此运之,即兴无休歇,神终不疲。”[26]1294睹物入心、心通言状、乘兴而作的创作过程颇类《物色》篇的“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文镜秘府论》所辑旧题王昌龄《诗格》从物色与意兴关系入手讨论创作,总结出四时气色随时生意、即时入心乘兴便作的心理机制,与其意境论密切相关,将六朝以来的感物说向前推进一大步。陆机《文赋》论述这种心理机制多借助于比喻,锺嵘论述时全凭举例用事,都有所依傍;刘勰依据诗例概括出许多理论方法,但略显缠夹,没有《诗格》二分后的简略直接。《诗格》忽略写作过程,直接贯通物色、心灵、作品,又类似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论。朱光潜用王维的《鹿柴》来分析克罗齐理论,可以借来解释物色与意兴合一问题:
这诗里有情(感触)有景(意象),你能看清楚这种景,自然就能领会出这种情,这种情就只有这种景恰可表现,绝对不可换一个方式来说而仍是原来那种风味。王维在写这首诗时,他心里必有一顷刻突然见到这个“情景交融”(即情表现于景)的意境,我们读者如果真能欣赏这首诗,心里也必须如此。这一“见”——无论是由情见景或是由景见情——便是直觉,便是艺术的创造。[27]31
由此思路演绎,“物色”论便是一个审美问题,刘勰揭示自然节物与文学关系的意义可谓大矣。
桐城派古文家一直重视文章声色,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作为桐城派理论的结穴之作,既征引《文心雕龙》、韩愈文论等为我所用,又梳理桐城派诸家论述线索,成功建构起声色理论。唐文治《国文大义》下卷“论文之色”篇专论文章色泽,以日色变幻与月色明暗比喻“矞皇之色”与“寥廓凄清之色”两种最高层次的色泽,前者“惟秦汉之文,若相如、子长、扬、班始能为此色”,后者则“六朝以来,骚人词客亦能为此色”。至于华而无质的藻绘之色,为“大雅君子”不取。具体说来,《易》之文为“洁白之色”,唐虞之书为“焕乎之色”,周代之书为“郁郁之色”,《诗》多正色,韩愈文为“苍老之色”。文章之色约有五端:“津润之色”,以《左传》“周郑交质”一首与扬雄《解嘲(并序)》为例;“怪丽之色”,以“荀子《赋篇》、屈子《天问》、景差《大招》及宋玉《招魂》《大小言》、《文选·江赋》诸赋为最”,录韩愈《南海神庙碑》以见例;“绚烂之色”,备于《文选》词赋与七类,录司马相如《封禅文》为例;“平淡之色”,“以荀子《成相篇》为最”,录司马相如《难蜀父老》、韩愈《送王埙序》二文为例;“洁白之色”,从《易·系辞传》可窥一斑,录韩愈《画记》一首为示范。[28]8219-8223唐氏在梳理文章色泽嬗变史的基础上总结理论,又分门别类列举作品以论证色泽理论,较姚永朴以润色技巧为主的方法论有很大提升。
高步瀛《文章源流》“作文之要义·设色”篇引刘大櫆《论文偶记》、曾国藩《家训》卷上、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三以论“设色”,依然从用字、造句、立意、谋篇上阐释,谓“设色者又不仅在字句间,而于立意、谋篇关系甚密。要之文章一道,始则脚踏实地,终于绝迹飞行。而色空空色,又非言筌所能喻也”。设色亦因骈文、古文不同而有别,骈文“难学而易工”,古文“易学而难工”,皆因设色之法不同,“古文设色亦较骈文为难”。[29]1339-1341高氏明确“设色”为作文技法,直截了当指向桐城派文论的核心要义,在传播弘扬“声色”理论方面自有贡献。
当今学术界的“物色”研究比较丰富,“声色”阐释相对不足。大抵因为“物色”涉及文艺心理学、美学、文学创作论等领域,形而上的意味更浓一些,诠释空间更大一些;“声色”越来越倾向于创作技术论,操作性更强一些,研究空间便越来越小。
总之,《文心雕龙》“物色”论重点在于节物对人的影响上,创作主体相对被动,更接近感物论;桐城派“声色”论侧重探讨文之粗服务于文之精的问题,创作主体的主动性更强,可操作性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文学技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