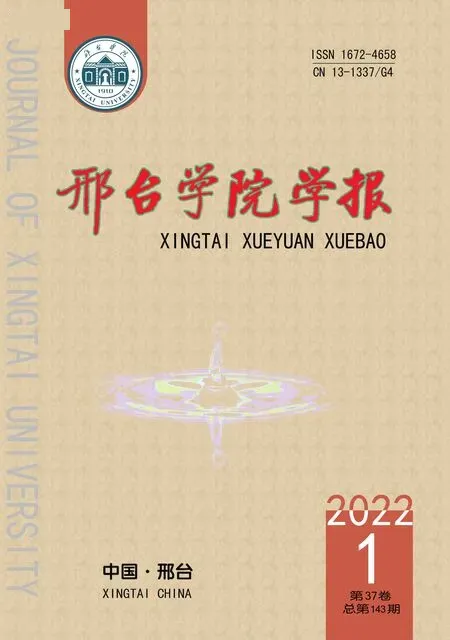苏伟贞小说叙事艺术研究
许子柱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江苏宿迁 223800)
苏伟贞的小说创作主要聚焦女性和外省人两大群体,通过对“两性、两代、两岸”的书写来表达她对历史、生活、生命的思考。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对小说叙事艺术进行探索、创新、实验,取得了较高的创作成就,长、中、短篇小说均有佳作,被誉为“小说天才”。概而言之,她的小说叙事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灵活运用叙述视角,深化对故事的认识
小说是思想的召唤,通过讲述故事来反映社会人生,但也需要借助有意味的形式才能实现。英国的亨利·詹姆斯说,依据不同的目的“叙述同一个故事可有五百万种方式”[1],叙述故事的方式往往反映了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叙事艺术的驾驭,能够体现出作家的创作风格。
苏伟贞前期的小说大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展开故事,小说《陪他一段》主叙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事,意在通过故事中的“我”作见证,讲述费敏的爱情故事;次叙事即文章的主体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按照故事时间顺次展开,主叙事与次叙事之间运用倒叙方法,使整个故事的讲述带有追述、反思的意味。叙述者“我”因是知情人,在讲述的过程中对整体事情的进展可以议论评价,如在叙述到费敏恋爱过程中只是一味付出时,评论道“果然很苦,因为费敏根本不是谈恋爱的料,她从来不知道‘要’”。这类评论性的话语使整个故事的讲述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褒贬明确。
“小说中的叙述关涉的方面很多,……第二必须选择恰当的视角,并随时调整视角的宽度和深度,以便引领读者适当地接触故事和人物;”[2]叙事视角的宽度与深度的恰当调整,可以使讲述的故事得当适当的有意遮蔽或适时显豁,增强小说的可读性。小说《旧爱》描写了程典青与三位男性之间的感情纠缠故事。故事讲述兼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故事在展开时当事人只能从自己一个侧面感知、判断、推理,使小说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感。在对同一故事的多角度切入过程中适当的安排视角宽度与深度来表现典青的情感世界,艺术手法更圆熟,更符合生活真实。1990年以后,苏伟贞在叙事艺术上进行了更多的尝试,通过对叙事频率的控制强化某一信息,对叙事者的微妙处理,控制叙事的张力,使小说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如在小说《老爸关云短》中,小说主要通过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讲述老爸流落台湾成家立业后仍一直眷恋关东老家最后返回关东的事。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却经常跳出故事叙事与读者对话(“你一定猜到我喜欢听的是我‘老孙家’老爸讲的关公、张飞、曹操……那些有名有姓中国人的故事。”“你可能猜到这是我的想法”),故事讲述时有时以童年的我为叙述者,如讲述老爸为“我们”讲三国故事时伤心痛哭的场面,真实表现孩童时的“我们”对老爸思乡时的怪异举止无法理解,让人产生“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的喟叹,但在预叙时又是以一成年人“我”的角度进行的,如“一直到老爸在我们生活中投下一块巨石,我们才知道事情发生了”。这些叙事视角的灵活调换,使小说增加了现场感和戏剧性,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文中频繁叙说三国故事(老爸反复讲述以及我不断回忆三国故事)使之在小说的旋律中回环复沓,在三国故事和老爸生活的共振中读者了解了小说人物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大向心力。
二、大胆进行心灵独语,自由展示心理世界
南帆曾说:“一个作家的成熟通常标志了一种风格的定型。这可能是一种独异的个性……;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一种隐蔽的重复,一种轻车熟路掩护之下的停滞。”[3]许多作家创作风格鲜明,但有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鲜明的创作风格也会反过来桎梏作者作品的创新,以致千作一面,陷入不断重复自己的怪圈。在小说创作中,苏伟贞总是不断进行大胆尝试,不断突破自己的原有风格,不断求新求变。一九九一年九月写完《迷途》后苏伟贞对小说创作有了进一步的反思,“我对我写的小说,也毫无把握,这一切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一年又一年努力记录改变后的观察。如果我仍具备一点点反思的能力,我不能不觉得虚假——一切都为虚构,一切都因创造而后有,一切都在写作技巧中呼吸。”因创造而后有,这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小说形式缺憾的新体悟,她决定创作更贴近心灵的小说,于是就有了《热的绝灭》、《梦书》等心灵独语类的小说。《梦书》可以说是由记梦日记连缀成篇的,作者称其为“一个梦游者以二年时间纪录下来的‘真相’文本”。这类心灵独语小说拓展或者说模糊了小说的边界,更侧重对内心世界的展示:
快天亮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以前的男友,我们在梦里交往的时间变长了,愉快地出游、说话、吃饭、买东西,我们中间从没断过,情感往后延续了下去。我们身体四周发着光。他问我关于做爱的问题及感想。这在以前我们向来没有讨论过,在延续下来的梦中情感讨论了,因为我们比以前“成熟”了。也许那时我就想问他。我们很愉快、温和的讲话,十分平静、幸福饱满。
……
情感的存在有时候不似我们想象那么有重量,反而是模模糊糊的,隔离你身边的一切,使你必须小心摸索,放弃既有规则。我仿佛听到一句偈语:“任何安排,我都无所谓。”而重新明白另一种秩序。谢谢你教我了解情感世界中的节制。
这两段梦语似是诉说又像是自语,在在流露出纯情、敏感甚至有些保守的女子关于爱情的思考与探索。第一段的核心是缺憾,“前男友”宣告了当下两人现实关系的中断,而梦中交流则直逼两人中断的缘由:梦里有,现实无。一对男女在恋爱关系中因不能顺畅地处理情欲之间的关系遂造成了现实中的劳燕纷飞的悲情结局;第二段则诉说着对情感的理解,在情感世界中自有另一种秩序,它与现实生活的既有秩序不同,两者有交叉但更有冲突,予取予求是对情感秩序的最大威胁。朱光潜曾说:“我常觉得文章只有三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这一类的文章永远是真诚朴素的。”[4]梦幻是最奔放不羁的想象,这种梦幻式的心灵独语,让想象挣脱了理性的控制,闯入一个理性思考所无法进入的世界中。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们在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愿望的一种伪装满足,是欲望的升华和隐秘的宣泄。正如袁琼琼所说:“既然外在世界如此难以适应,她于是构造书里的世界来平衡自己。”[5]苏伟贞在《梦书》中记载下了与四十岁或女人全然无关的事,只是为了缓和生命中那些“即使修伯特也无言以对”的情境。
三、巧妙变幻复调形式,在众声喧哗中丰富主旨
除了在小说边界方面进行开拓创新之外,苏伟贞感应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灵活运用一些表现手法,使小说在“讲故事”的同时借助“有意味的形式”更好地表现主题。复调小说①在苏伟贞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中不同的文类、丰富的主题和多样的线索各自都会有不同的意蕴和审美效果,如果只是单一地运用,效果不见得突出;但是,当把它们有机巧妙地组合起来运用时,就能够在彼此照应中突出主旨意蕴,就好比在一部大型交响乐演奏时,各个声部独奏效果不一定好,但是众多声部交相混响、协调配合,就能取得悦耳动听的效果,音乐主题的表现也会得到强化和突显。在苏伟贞早期的《生涯》等作品中,主要采取映衬式复调来结构小说,作者一般会安排一个主要叙事旋律,也就是有一个主调在讲述进行的故事,同时又会安排一些次要的叙事旋律来伴随或陪衬原来的主要旋律。《生涯》中的将军不仅自己再婚娶的仍是军眷女子,而且希望女儿安帼也嫁给军人,这是小说的叙事主调,在这一主调之外,作者又让女儿安帼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出了将军空自苦的执著,并且连将军的侍卫官也不再安心军营生活而是想着去学习科学知识准备去学校教书。这两种话语相互对话、缠绕,使小说旋律活跃起来,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外省人在台湾逐渐边缘化,作者用主旋律讲述军人的执著与抱负,又用另一个旋律来展现他们在台湾现实社会中日益边缘化的困苦、尴尬的处境,复调手法的运用增强了小说反映现实的立体感和深度。在小说《沉默之岛》中,作者运用的则是对位式复调手法。对位式复调就是指平行共时地表现两条叙事线索上的场景对话和事件,却又掐断了这两根线索间的一切过渡和衔接,使得两边的声部混合交叉到一起同时鸣响、共鸣,产生惊人的效果。小说设置了两套略显对称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两个晨勉出身不同,性格也截然相反。她们二人的故事穿插叙述,纠缠前行,最后两人又都怀上了丹尼的孩子,幻身的晨勉经过思想斗争,选择了堕胎,而正身的晨勉却选择嫁给了辛(另一个男人),以便给即将出生的孩子找到一个名义上的父亲。两个晨勉最大的共同之处是都在(或曾在)主动的性活动中努力“保持身体的独立”,支配她们采取生活行动的已不是她们的心灵而是她们的身体。两个晨勉不同生活世界的对位安排,扩大了人物活动的空间范围,增加了男女情爱应对的方式,从而对女性情欲作了多种可能的尝试,使小说带有了更多的思辨色彩,而不是单纯地展示女性的情欲生活,提升了小说的境界。此外,在《过站不停》、《魔术时刻》及《时光队伍》中,作者大多采用文类复调(也称文体复调)的手法结构小说,把小说、书信、散文等不同的文体种类整合在小说中,在众声喧哗中,完成文体的狂欢和主题的发展。长篇小说《时光队伍》也是这样,小说内容大致可以拆解成三部分:其一是写张德模从生病、住院到去世,夫妻二人共抗病魔,最终失败的整个过程;其二是写张德模家族从四川一路离散,不断迁移终至台湾安家的流散家族故事;其三是写张德模一年年一次次和友人不断回大陆遍游中国内地的萍踪浪迹的故事。这些是文章实线的脉络,虽然说明张德模的一生,但却无法显示一种高度,一种从时间的无涯里走来的,属于流浪者的集体命运。因此在这本书里,作者又穿插了许多虚线,诸如最后不知道流浪到哪里的北京人化石,当年带着故宫国宝在战火中流浪于西南一隅的庄尚严,还有感慨“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同样因食道癌去世的台静农,这些虚线与实线所构成的流浪族群的故事,是张德模一生的舞台背景,如今他离开了实线的人生,像是听到远方的鼓声召唤般终于走回了那从黑暗中走去的流浪者的行伍,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本书里,作者援引了许多书籍、典故,像莎士比亚的作品、《哈扎尔辞典》、《流浪者之歌》……这些内容使人像是借助一个个长篙撑过生命的浅滩,又像是从别人的故事里吐出丝线,补缀着生命巨大黑洞所可能造成的陷落。所有曾经被书写过的话语,关于生或死的体认,其实都在说明着,人没有孤独的生,没有孤独的死,所有的人都曾在流浪的路途、幽冥之河的岸边,问题是,人,究竟该活出哪一种样子?这种文类复调叙事手法的运用,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使个人经历与族群苦难关联到了一起,甚至直达人的生存方式探索的哲学高度。总之,复调叙事手法在小说中的正确运用,直接打破了小说原有的直线式叙事方式和单线发展的结构方法的限制,它把不同的主题意蕴和结构线索熔铸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意蕴场域,使得叙述视角也变成了全景式,叙述结构变为了立体式,叙述时间也因此而被重新切割和组接,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在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和艺术空间拓延,其容量得以极大地膨胀。
四、融魔幻现实于一体,增强表现的自由度
“融幻想与现实为一体”的写法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其作品往往用象征、荒诞、意识流等手法,把怪诞的人物、情节,甚至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形成魔幻和现实融为一体、魔幻而不失其真实的独特风格。当然,不管作品采用多么匪夷所思的“神奇”手段,它最根本的核心却是“真实”。“魔幻”只是外在的表现,反映“现实”才是其根本目的。苏伟贞在眷村小说《离开同方》中成功运用了魔幻叙事方法,第一人称的叙事观角因魔幻手法而拥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能够任意出入众多角色的内心世界,自由书写同方新村发生的一切人事,为读者创造出一个亦真亦幻的眷村世界:一群漂海赴台的外省人在同方新村挣扎营生,这里有着太多在失序状态中发生的人和事:李伯伯在战争中失去性能力,生活沉闷,远避外岛;田宝珣整日游走,最后竟成了戏团的主角;患有洁癖的段锦成一挨近妻子便浑身发抖,别人到他家里碰过的东西都要冲洗,最后发展到闻到有生人味就要冲洗地板;小白妹奇异的微笑,狗蛋长期的沉默,阿跳频繁地栽种花树;甚至连蔗田的大火和弥漫在同方新村的大雨和花香都有着莫名所以的怪异。这些象征、夸张、重复手法,是对现实的非常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的别具匠心地揭示,是对现实生存状态和规模的夸大,最终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现实。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同方新村一如《百年孤独》里的马康多村,是某个处于乱世的国族的缩影。”[6]
在诸多女性作家中,苏伟贞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与她的叙事艺术的不断实验和探索有关。在谈及创作时,苏伟贞曾说,目的是为了要使“生活里不能说不可说的一面,便藉由小说的方式创造出一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来弥补现实世界中的‘大洞’”,从而实现完整,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并不试图掌握话语霸权,她需要的只是多角度的表现,在这种互相映照、对话中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因为怀有这样一种“笔补造化”的愿望,追求一个完整世界的出现,苏伟贞的笔下世界往往是一种展望、设想式的图景,而较少客观的再现,这使她的创作带有某种程度的思辨色彩。苏伟贞在写作的过程中努力认识世界,进而认识自我,可以说,写作、生命、完整,对苏伟贞来说是三位一体的,而达成这一愿景的途径就是不断娴熟的叙事艺术。
注 释:
①“复调”原是音乐的概念,是多声部音乐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两种以上同时进行的旋律所组成;巴赫金首先把复调引入小说理论,把小说分为独白小说和复调小说,他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一切意义都产生在对话中,复调小说是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米兰·昆德拉在继承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复调小说理论。昆德拉从文体学中的文类角度和多线索角度出发来理解复调。巴赫金的复调和昆德拉的复调内涵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