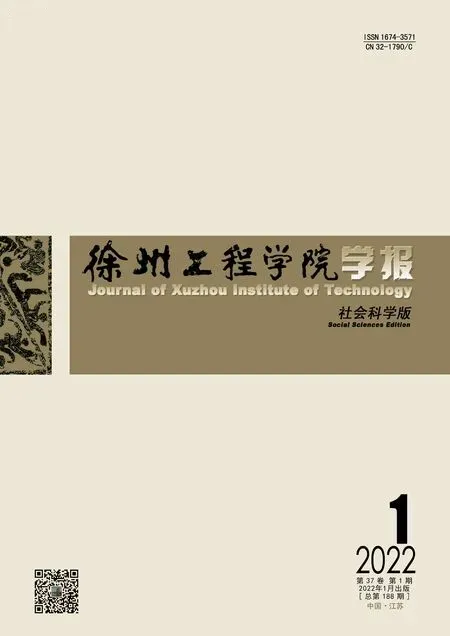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潘知常中外美学比较视域下的生命美学建构
范 藻
(成都锦城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当代美学的庐山真容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
陆游说:“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中国新世纪美学的生命大厦究竟应该如何建立?
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选择,诚如潘知常所言:“判断一种美学的理论内涵,关键不在于这种美学经常谈论什么,而在于怎样谈论。”[1]119
针对第一个问题,结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人与“美的规律”的见解,大概有三种类型的美学形态:把美作为外在于人类知识性存在的认识论美学、把美学作为表现于人类对象性活动的实践论美学和把美作为揭示人类生命存在意义的价值论美学。相较于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因其身陷知识天地和物质世界美的象牙塔而呈现的“无人”状态,的确是很难把美说清楚的。而价值论美学一定是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即“内在尺度”,即“人的尺度”来体验和思考美的,显然,生命美学就属于价值论美学,也只有它才能够呈现中国当代美学的应该有的面目;因为它选择的是跳出庐山,移步换景,才发现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奇异美景。
针对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第一个问题的延续,生命美学是如何“彩练当空舞”的?既要有“回头看”的目光,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君子人格”精神、道家文化的“欲复归根”意识,禅宗文化的“玄道妙悟”境界,还要有运用“拿来主义”的眼光,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美学到康德的唯心主义美学,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美学到海德格尔的“唯存在论”美学,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甚至还要回顾印度佛教思想对于禅宗美学的影响。面对浩如烟海的中西方的美学理论,尤其是种类繁多、流派纷呈的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天机云锦”,如何把天上的彩虹剪裁为大地的锦绣,需要的是一把思维敏捷、眼光独到和手法娴熟的“刀尺”。
借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关于治学的一个经典说法,就是哲学史家是对既往的“照着讲”,而哲学家着眼于未来不仅要“照着讲”,而且要“接着讲”。从为美学而美学的“照着讲”到为生命而美学的“接着讲”,潘知常引入现代西方审美观念提供的“多极互补”的思维观念,不但打通古今,而且融合中西,用开放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犹如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取天火”,更是像高僧玄奘一般“西天取经”,一如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样,“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2]40。不但再一次开启了新时期中外美学的全新对话,而且开始了新时代中国美学的重新建构,从而为生命美学的茁壮成长添加了新的营养。
一、否定性的思维
美学研究由于其高度的理论抽象性,在本质意义上是对鲜活灵动的审美活动感性体验的“反动”。“反者道之动”,潘知常的美学研究深谙个中三昧。所谓“否定性思维”是潘知常借西方美学之“杯酒”而浇中国美学之“块垒”的策略和思路。他在《反美学》一书中,针对实践美学的“美学局限”而提出了终结传统美学、传统艺术、传统“元叙述”,还在《美学的边缘》一书第一篇首先提出了“否定性主题”,以后又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一章就将“否定之维”作为“欧洲的动力”,在第五节予以阐述,这是对我们长期信奉的人性不是本善就是本恶的“绝对的否定”,真正的美学不是要人类在“成人”的人间道路上苦苦挣扎,而是要在“成神”的天国旅途中欣欣愉悦;不是直面黑暗而进行没完没了的抗争,而是转过身去背对黑暗,直面光明,这一“转身”就意味着脱离“人性”而进入“神性”。
他的美学不是从古希腊美学起开始研究,而是越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直接进入19世纪中叶兴起的现代主义美学。他在《生命美学论稿》第七章“从传统到现代:西方美学的重建”,独具慧眼地发现了“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转型”,即从富有普遍和全面、本质和本体、共性和共名的理性主义传统中挣脱出来,而高举个别和片段、现象和表现、个性和无名的非理性主义旗帜。他在这一章里说道:“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的两大精神性质。就其主导而言,人无疑是理性的,而就其动力方面而言,人无疑又是非理性的。”[3]147毫无疑问,这是一股发自生命本能和本源的强大动力,也可以说是“生命动力”,才有了尼采“超人”的横空出世,才有了弗洛伊德“性力”的异军突起,才有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空谷足音。正是出于对理性主义美学的否定而钟情于非理性主义美学,这肇始于19世纪上半叶登上哲学舞台的叔本华,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人,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也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继之以19世纪末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他抨击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高喊“上帝死了”,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最后是集大成者于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哲学,即存在主义的标志性人物海德格尔,关注人被理性意识长期压抑的焦虑、绝望、恐惧等病态心理和残缺人生,正话反说,以贬代褒,绝地反击式地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注重人的精神存在。
具有浓郁的非理性精神和强烈的否定性思维的叔本华、尼采和海德格尔这三位哲学家或美学家是潘知常研究西方美学,每每提到的人物,个中原因不言而明。他在《生命美学论稿》第七章的第四部分里说明了:“本书更为关注的并非西方当代美学的否定性主题的缺陷,而是它的美学意义。那么,它的美学意义何在?在我看来,就是在于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视野。”对否定性主题和思路的强调,表现出来的意义是:“对审美活动的开放性的充分展开”“对审美活动的复杂性的充分展开”“对审美活动的丰富性的充分展开。”[3]143-147这三个意义,与其说是西方美学研究的新发现,不如说是为中国美学,为中国当代生命美学提供的思路启发、视野开拓和精神资源。
如前所述,潘知常把生命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本体视界,把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主体视域,而导致其美学思考的根本转型,从静止的、沉寂的、物性的美学转向灵动的、活泼的、人性的美学,这与其说是源于先秦道家美学的“心斋坐忘”、唐代禅宗美学的“心心相印”、南宋心学美学的“心统性情”和明清世情美学的“心之元声”,不如说是受到西方美学思想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本主义生命意识的影响。他是这样总结的:
再从西方美学的发展来看,对于诗性人生以及审美与艺术的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关注也无疑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生命美学传统。也因此,从康德到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福柯、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弗洛姆等)以及现代主义美学与后现代主义美学中的诸多美学家,等等,都属于生命美学的美学一族。[4]20
西方美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是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叶催陈叶”的辩证的“否定”:古希腊的唯理主义美学家关注的是“存在本体”,而中世纪神灵主义美学家则以关注“上帝”来否定“本体”,到了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美学家又用关注“人性”来否定“上帝”,到了近代以后的浪漫主义美学家又用关注“自然”来否定“人性”,而19世纪的社会主义美学家则用关注“生活”来否定“自然”,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美学家则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注目“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基础上,终于用关注“生命”的“存在”及其意义来否定并总括历史上的所有美学思想。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已经从打开的国门中,开始建构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美学理论了:王国维的“境界”是吸收了叔本华一切生命源自于痛苦的悲剧见解;宗白华的“经验”有着明显的立普斯“移情说”的痕迹;蔡仪的“典型”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综合之体现;高尔泰的“自由”更是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新生资产阶级的精神向往;李泽厚等的“实践”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美学化;周来祥的“和谐”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学版本。
不可否认,以上种种说法因其对美的认识而贡献的思想,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当我们把美的思考从对理论本身的解释而转到对理论意义的阐发,借助“否定性思维”的引领,不得不遗憾地离开“物”的美学而转向“人”的美学:那就是作为“后实践”美学的重镇的生命美学的领军者潘知常将“美”由我们熟悉的“实践活动”,转而牢牢地锁定在“审美活动”和“生命活动”——生命的审美活动或审美的生命活动上。阎国忠在《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里是这样评说的:“潘知常从自由的生命活动出发,通过外在辨析和内在描述两个角度将审美活动界定为:自由生命的理想实现的活动;生命活动的最高价值追求的活动;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和超越的活动;是生命的澄明之境和超越之维。”[5]337诚哉斯言!
如果潘知常没有像叔本华一样强烈的生命意志,没有像尼采一样勇敢的生命力量,没有像海德格尔一样深邃的生命眼光,一句话,如果没有像他们一样的否定性思维而产生的生命反叛意识,如北岛在《回答》里高喊的:“世界,我不相信你!”那么他的生命美学就不可能枝繁叶茂,甚至还是实践美学改良版本的“后‘实践’美学”。
二、多元化的方式
潘知常“胸怀中华文化,放眼世界美学”,引进域外优质美学,尤其是西方美学,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资源,在对话中重建中国美学,体现了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一个中国美学家的责任与担当。为了中华传统美学的振衰起敝,为了中国美学的浴火重生,更是为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生命美学的傲然屹立,他借助“否定性思维”的犀利目光,分别从印度古老的佛教、西方现代的哲学和瞩目人类解放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发现并引入了可以对话,更是能够重建生命美学一股别样而独特、丰富而深邃的源头活水。
一是,印度古老佛教的启示。这是从印度佛教到中国禅宗、从佛教禅宗到生命美学的过程。佛教自东汉末进入中国,经过唐代六祖慧能的改造后,变成了具有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那么,它对中国美学带来了哪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呢?
首先,由“实体”到“空无”。这就化解了对象性思维而启示出非对象性思维,这与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哲学宣示的存在之物决定意识之思的对象性思维,有着迥然不同的旨趣。对象性思维看重外在的条件、社会的关系和现实的价值,极大地限制了生命本身所蕴含的能动性作用,让人沉迷于物理世界而忘却了精神世界,潘知常一针见血地指出:“误入了对象性思维迷宫的无家可归的人,必然是苍白、病弱、伪善、守旧和丧失个性的人。他们盲目笃信物质的极大丰富所带给人的种种幸福,盲目笃信社会进步与人类进步的正比关系,盲目笃信科学理性能够使世界透明。”[6]15去掉了对象性思维就为生命挣脱了羁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生命又一次真正地站在了“生命如何可能”本体之问的起跑线上,生命从此就可以开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用人生可能拥有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将曾经失去的天真与浪漫、鲜活与洒脱、丰富与充实、清纯与自然,全部“赎回来”了,真可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跳出五行中,不在三界外”。
其次,由“神思”到“妙悟”。如何获得丰富的审美经验,刘勰说:“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这是由有限到无限的飞跃,他进一步指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文心雕龙·神思》)跨越时空的想像和穿越情理的灵感来自作者的秉性才识,虚静的心境,深邃的思索和高度自由的内心状态。这似乎近于禅宗讲究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见性成佛,直指人心”的顿悟,其实不然,妙悟的前提是非对象形思维,而神思不论怎样的“神”和如何的“思”,都是有所依托的,这正如严羽所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辩》)潘知常论述到:“在‘神思’还是与象、经验世界相关。在‘妙悟’则已经是与境,心灵世界的相通。”[7]78由是让我们绝对而真实,并且是直接无碍地进入生命,促使个体面对浑茫世界的真正觉醒,获得了属于自己独有的经验和感悟。
最后,由“经验”到“智慧”。潘知常在《中国美学精神》第四章“美学的智慧”,开篇即说道:“中国美学的智慧诞生于儒家美学,成熟于道家美学,禅宗美学的问世标准着它的最终走向完成。”[1]119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庄子的濠梁之游、相濡以沫、白驹过隙,无一不是经验式的审美或审美式的经验。但是,禅宗美学所关注并提倡的“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东晋僧肇《涅槃无名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寥师》)、“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诸外物者,皆须臾之物”(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总的来看,禅宗美学为中国美学所带来的全新的美学智慧应该是:真正揭示出审美活动的纯粹属性、自由属性,真正把审美活动与自由之为自由完全等同起来。”[1]463这对于我们熟悉并融入血脉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使命和“闻道载道弘道”的家国情怀,无异于是一次醍醐灌顶的当头棒喝,更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命澄明。
二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引入。它表现在基督教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等上面。西方文化浩如烟海,种类繁多而博大精深,良莠不齐且启发颇多。潘知常既不是对它们作简单的介绍,也不是对它们进行一般意义的价值判断,而是围绕美学的话题,为了生命美学的建构而“洋为中用”。
中世纪的基督教美学,不论是哲学家还是神学家开启一千年中世纪有关美学最纯正的思考,尤其是圣·托马斯·阿奎那借助基督教此岸和彼岸两个世界的原理,将上帝视为最神圣而崇高的美,还是一切美的本源,将柏拉图“美本体”超验世界的追问转到了上帝视域下的“人为何”超验式的人的追问。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之所以充满神性,是因为人首先直接对应的是神而不是人,由于人是丑恶的,因此就以展现上帝的荣耀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分享了上帝的荣耀,体现为自由者与自由者的对应、从而让人以上帝之子的身份从原罪的泥淖里走出来而获得了神圣的启示、信仰的启示和爱的启示。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认作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8]51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理性意识越是高度发达,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使得人生存意义越是迷惘不解,就越是需要思考神圣与神性,越是渴望爱与被爱。潘知常说:“只要人类最为深层的‘安身立命’的困惑存在,宗教也就必然存在,基督教也必然存在。”[9]126意味着借助上帝的万能之手将人类从苦难的深渊里拯救出来。
初创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是通过对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和传媒文化的批判来实现社会学意义的审美救赎,它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广泛吸取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点,秉承浪漫主义传统,其社会批判理论以拯救人类、使人类摆脱受剥削和奴役的“异化”状态为宏旨。如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有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还有黑格尔的“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的见解,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背后的爱欲的压抑、人性的扭曲、劳动的异化等病态现象,认为应该重建艺术与审美的乌托邦,他说:“艺术的真理,就在于它能打破现存现实(或那些造成这种现实的东西)的垄断性,就在于它能确定什么东西是实在的。艺术在这种决裂中,即在它的审美形式获得的这个成果中,艺术虚构的世界,表现为真实的现实。”[10]197潘知常不但用他们的美学理论进行传媒文化的批判,指出“现代传媒的迅速撒播,使大众丧失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能力”[11]75。而且用他们的批判理论对物欲横流和人伦丧失的社会现实进行启蒙哲学的美学批判,其中“更为中国美学家所熟知的,是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沃林就曾经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先驱的本雅明的美学为‘救赎美学’,其实,他们都是‘救赎美学’,其根本目的,则是赎回‘最虔诚、最善良的人来’”[9]452。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和恩典的情怀,赎回的是人类失落已久而本应该有的自由、美好和爱。
最后,我们再看看潘知常是如何评说存在主义的。他着重从两个方面发掘出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中国美学的“道”、海德格尔的“真理”与中国美学的“真”的关系。其一,海德格尔在他的《形而上学是什么》里是这样来解说“存在”的:“存在是亲近的。但亲近的东西对人依然是最遥远的。”[12]225消解了我们熟悉的传统哲学的对象性思维,而进入非对象性思维生命本真状态。这对中国哲学而言就是“道”的追问,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庄子的“道恒无名”,其实也是对“存在”的追问。潘知常认为,“追问存在,严格说来,就是追问世界对人的意义”[12]238。从而确立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明确世界对人的意义,“正意味着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追问,对于充分人性化的世界的追问,对于栖身之地的追问”[12]238。其二,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书中说:“真理乃是对强力意志由之而得以意愿自身的那个周围区域持续的持存保证。”[13]793真理不是知识,也不是认识,而是由本体存在的意义进入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是生命存在之“真”,也是生命价值之“真”,更是生命境界之“真”,这种“真”实质上是生命的本真状态,在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的自由之中,进入非对象性和非常态化的生命境界。
三、融合式的路径
面对人类文化的浩如烟海和博大精深,潘知常广泛吸收一切有用有益的哲学、美学、艺术、传媒等理论成果,运用洋为中用的文化策略和六经注我的学术理念,超越中学为体的固有见解和西学为用的习惯做法,立足中国文化儒道释三源并流的历史,“相对于儒家美学的美在社会(仁),以及对于人与社会的和谐的关注,相对于道家美学的美在自然(道),以及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注,禅宗美学则是美在心相(心),以及对于人与自我的和谐的关注”[12]313。既继承传统又批判传统,寻找中外文化的相似之处,初步建立起了李泽厚倡导的“人类视角,中国眼光”的生命美学理论。
其一,思维方式的非对象性。
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是“隔岸观火”式的“冷眼向洋看世界”、“跳出庐山”式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它表现为“我认为如何如何”一样的主观和武断,丰富生动和多样复杂的世界被人为地“切割”成了冰冷而僵硬的“对象”,如潘知常说的“让其思考的一切,皆站在前面,对着自己而成为对象”[12]335。这种具有主客二分、心物两界和物我分明特征的思维方式,在撕裂思维对象的同时,也吞噬了思维主体;很显然,这种“对象性思维”方式于发现科学之“真”上和判别道德之“善”上功不可没,而在感受生命之“美”上则另当别论了,因为“美”和“美感”不是泾渭分明的“两张皮”,而是犹如一张纸的两个面,感受或发现它们更需要“非对象性思维”方式,走出“二元论”的泥淖和“对比性”的迷途,让我与世界、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有限与无限、存在与毁灭、天堂与地狱、上帝与子民等,凡是一切人为划分的“楚河汉界”全部变成天地混沌和有无笼统,而“直接进入这一切二分之前的同一世界”。
在消解对象性思维方面,道家美学通过主体的“恬淡、寂寞、虚无、无为”而实现与客体的圆融无碍和水乳交融,在非对象性思维的启动上毕竟有了一次良好的开端,但不幸的是它将主体自己也消解了,这不能不说道家美学离真正意义的生命美学还有一段距离。有没有既消解对象又保留主体的美学呢?那就是西方的现象学美学与中国的禅宗美学。
和中国道家讲究“返璞归真”一样,现象学也要求“本质还原”。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通过“悬置”和“加括号”的方式,要求观察者把注意力从外在事物方面转移到意识现象方面来,即把我们关于事物的种种理解全部“存而不论”,通过自有想象的方式,将经验性还原为本质性,事实性还原为可能性,所谓“目击道存”而直探本质,所谓“宏观直析”而发现可能。正如德国现象学美学家莫里茨·盖格尔说的那样:“直观是这样一种态度,人们通过这种态度就可以领会艺术作品那些以直接联系的形式存在的价值。因此,‘直观’并不是审美经验,而是审美经验的先决条件。”[14]244这与叔本华的“静观”、尼采的“沉醉”和克罗齐的“直觉”、海德格尔的“静思”等强调当下直观、看重经验和突出意向一脉相承。因为,正如美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说的那样:“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世界之间并没有隔着一个窗户,因此也不必像莱布尼兹那样隔着窗户向外眺望。实际上,人就在世界中,并且与世界息息相关。”[15]216
如果说道家美学讲究一个“无”,那么禅宗美学则突出一个“空”,而要感悟这个“空”,就需要“妙悟”。这里的“空”是“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无中生有,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虚中有实。正如那则著名的公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消解了对象性思维中我与世界的关系,而成为“我即世界即佛”,人类重新回到了“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最为根本、最为原初的非对象性思维,回到了思即妙悟。“色即空”“空即色”,大千世界之“色”和万众浮生之“空”,彼此相融,和谐相处。由是,对象与主体呈现出鱼水交融的和谐和鸢飞鱼跃的灵动,恰如张彦远所描述的:“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历代名画录》)对此,潘知常一语中的:“在中国美学,审美活动不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而是一种非对象性的活动,不是一种对于世界的把握方式或认识方式,而是一种生命的最高存在方式,不是一种美——审美的反映活动,而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肯定、自我愉悦的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动。”[1]417由此,实现了禅宗美学之“空”与生命美学之“实”的和谐对话。
其二,审美意义的反现代化。
自文艺复兴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特别是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主义哲学家尼采那句“上帝死了”,将每一个普通的生命从上帝的天国带回到了人间的大地,使一个个遥远的乡村从闭塞的穷乡僻壤走向了开放的车水马龙,在推向社会进步和追求尘世幸福的过程中,效率与效益、经济与金钱无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但是,也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句名言所批判的那样:“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有关人类生命意义的问题上,一个强调精神世界的丰富,一个看重物质世界的繁荣,反现代化就伴随着现代化一同前行。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说道:“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做的意识性防卫。”[16]16在工具理性至上和技术主义泛滥成灾的今天,反现代化不是不要现代化,而是更关注现代化背景下和时代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社会的发展前景,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人的觉醒,那么反现代化则是有关人的真正解放和精神自由的再次启蒙。
于是,进入20世纪以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进入了潘知常的视野,并纳入“生命美学谱系”进行考察,如他新近主编的“西方生命美学经典名著导读”丛书,就选入了阿多诺的《美学理论》、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梅洛-庞蒂的《眼与心》等著作。
潘知常充分肯定了他们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工业文明、意识形态、传媒文化和物化社会等戕害人类精神与心灵的弊端进行了尖锐批判所作出的贡献,其中马尔库塞针对资本主义文明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繁盛而精神空虚现象,提出了“单向度人”的概念:“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的条件下操纵这些人为的需求,这种自由的条件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工具。”[17]5在满足虚幻幸福的同时,消释精神追求和情感渴求。面对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潘知常进行了专门的批判:“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审美与艺术的自我放逐。面对社会转型,它自信而又空虚。既然追求某种价值是可疑的、虚妄的,那么,不妨‘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感觉’至上,‘潇洒’至上,于是,虚无主义的温柔乡、自慰器,也就成为它的必然归宿。”[9]422真是准确而真实、犀利而直白的批判。马尔库塞还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里的基本制度和它的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存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18]4因为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审美与人类社会在异质状态下是处于对抗的关系。如果说尼采的美学思想是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美学,那么,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则是借助对资本主义及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寻求人的现实解放的政治美学。
其三,文化批判的去乌托邦。
16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创立了旨在追求想象中的美好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其实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追寻理想社会的历程,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从庄子的“藐姑射之山”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再到吴承恩的“花果山”,更不用说基督教的“天堂”、伊斯兰教的“圣城”和佛教的“净土”,更有《圣经》里的“伊甸园”。实际上,乌托邦已经成为一种美好意愿和追求精神的象征了,然而从19世纪末尼采的“上帝死了”到20世纪中叶福科的“主体死了”,人类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陷入了“群魔乱舞”的时代,当代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感叹道:“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的时代。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它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再也不会产生。”[19]282作者还说“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果真如此吗?人类固然需要理想的招引,但不能陶醉在理想的光环下。
潘知常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二章第一节的标题就宣称:“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上了问号”,开篇即论述道:“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尼采的酒神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分别从地球、人种、历史、时空、生命、自我等方面把神——进而把人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因而也在一点点地打破这个‘模型’。”[9]119-120是的,最大的乌托邦是“上帝”,可是上帝已经死了,于是马克斯·韦伯开始了为现代世界“祛魅”的伟大工程。从上个世纪初叶,人类似乎站在世纪的尽头,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巨变”,开始了文化批判更是文化理想和模式的转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0]254这是一股来势汹涌的去乌托邦浪潮,波德莱尔1857年发表了开启象征主义文学先河的《恶之花》,1871年尼采发表了高扬生命历经痛苦而获得崇高的酒神精神的《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1900年发表了“理解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梦的解析》,伯格森1909年发表了强调“直觉是思想世界的入口”的《创造进化论》,1914年克莱夫·贝尔发表了理解现代艺术钥匙的“艺术是有意味形式”的《艺术》。从而让艺术更真切地直指人心而抵达被名缰利锁羁绊的生命深处,让美学更实在地直面现实而承担拯救正在被物欲吞噬的生命的使命。
潘知常之所以瞩目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是因为它们不仅在艺术王国颠覆了宏大叙事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在美学领域亮出了反叛传统的现代主义大旗,更是在生命意义的思考方面开辟出新的天地,这也是潘知常独特和深邃的“世界眼光”视域下文化批判的去乌托邦。
借用中国文化的语境说,它要去除那些凌空蹈虚的禅悦意识,要减少那些大象无形的老庄思维,增加“天行健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品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者风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这种看重美的现实价值,体现在著名的“伍举论美”:“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国语·楚语上》)这被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孔子发展成了“美善合一”的伦理美学思想,以“仁”为内核,“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以“礼”为表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最后是要成就光明磊落的君子人格,所谓的“君子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种文化批判的去乌托邦立意,还生动地表现在孔子的艺术观,他强调艺术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还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就是“文以载道”艺术传统的最早规定,体现为“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关怀。这与传统中国诗人们所向往的“郊寒岛瘦”、画家们所追慕的“烟寒水瘦”和书法家们所喜爱的“仙风道骨”,还有士大夫所欣赏的“吟风弄月”,生命美学与这种超然出尘的审美意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截然的不同。为此,潘知常在《中国美学精神》里盛赞“孔子沐浴着的是‘人的觉醒’的晨曦”,“是中国美学毅然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对终极价值的追问的开端”[1]59。以虚无性为特征的旧的乌托邦的逝去意味着以实有性为特征的新的乌托邦的诞生,这就是生命美学秉承的文化传统、倡导的现实关怀和承担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