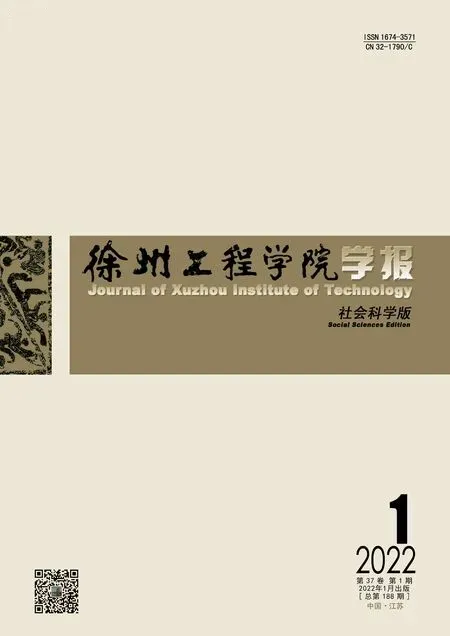从《囚笼》解读流散非裔的困境
张堂会,苏辰歆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囚笼》是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早年的创作,被收录于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集》。文章用冷静的叙事口吻展现了在非洲某沿海土地上,一位早年被迫离开家乡的青年哈米德在异乡孤寂迷茫、痛苦焦虑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对于深受西方殖民文化影响的移居地,他呈现出畏惧迷惘的心理状态,在多次尝试融入新社会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后,他对生活失去了期待与梦想,并选择用自我封闭的方式拒绝移居地的文化风俗、社会交往。然而,一位美丽女子茹基娅的出现,在他如死水般的心中激起了涟漪,使他鼓起勇气走出自构的囚笼,去外界追寻自己的幸福。但是当他走出囚笼之后,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为一名无根无家的漂泊离散者,又被禁锢在了另一个囚笼之中:陷入了痛失家园、自我认同焦虑的身份困境。
文章围绕哈米德畏惧迷茫——自我封闭——走出囚笼——再次迷茫——思归不得的过程,展现了深受西方殖民压迫的非洲民众所受的伤害以及他们身处的多重困境,抒发了他们对幸福的憧憬与追寻。主人公哈米德最后是否得到了茹基娅的爱情,古尔纳并没有给出答案,这是他对流散非裔问题的早期思索,他在后期创作中一直在为流散非裔探寻一条在异质文化夹缝中生存、重构自我身份的道路。
一、无法融入与自我封闭——流散非裔被迫移居西方殖民地后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
1948 年,古尔纳出生在位于东非大陆东海岸、印度洋西部的一座小岛——桑给巴尔岛。12至14世纪,这座小岛曾经是显赫一时的“桑给帝国”,既是印度洋贸易的中间站,也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商人贸易的聚集地。16世纪,桑给帝国灭亡,取而代之的是葡萄牙人长达150年的殖民统治。自此,桑给巴尔的土地上开始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奴隶贩卖活动。18世纪后,由于英法开拓殖民地对人力需求的不断增大,桑给巴尔因为地缘优势被迫成为奴隶贩卖转运的“大卖场”,岛上的居民长期处于被奴役与压迫的阴影之中,一批又一批本土民众背井离乡、迁徙异地,流散的痛苦是流淌在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的。直到1907年,桑给巴尔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后才真正结束了岛上人口贩卖。
在19世纪的列强瓜分狂潮中,桑给巴尔最终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为了更好地统治桑给巴尔,在当地实施了严格的种族划分与种族隔离制度,将桑给巴尔民众按种族、阶级划分为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其中阿拉伯人的地位最高,仅次于英国殖民统治者,非洲人处于最底层,“时至今日,这种历史建构模式下的桑给巴尔被描述成为处于英国和阿拉伯双重殖民之下”[1],这个政策虽然使阿拉伯人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地位,但也不得不与英国殖民者一起站在了桑给巴尔的敌对面,英国殖民者随意地将源于西方的种族范式引入非洲,最终只会导致桑给巴尔各种族之间日渐积累、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战以后,一群留学欧美归来,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上层阿拉伯知识分子率先觉醒,自发组成了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他们提出废除按种族划分的投票权,追求桑给巴尔的独立。英国殖民者觉察到了统治被动摇的危机,于是扶植了一个忠于英国政府、反对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政党:非洲—设拉子党。然而,这些政党由于内部的党派斗争和自身的软弱性在后期都出现了分化,故桑给巴尔的主流政党一直处于更迭换代之中,没有一个新兴政党掌握了压倒性的权威。直到1963 年年底,桑给巴尔正式宣告独立,民族主义党和奔巴人民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这是个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由少数阿拉伯裔统治多数非洲裔的政治结构”[1]。据资料显示,古尔纳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有阿拉伯血统,故笔者推测他的家庭应当属于这个为英国殖民者服务的少数阿拉伯裔统治阶级,这也能解释为什么1964 年桑给巴尔革命之后,他被迫流亡英国。1964年1月12日,非洲设拉子党推翻了联合政府,成立了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实行了高压政策,苏丹王族遭到镇压,土崩瓦解,反对党人士也噤若寒蝉”[1],家国的巨变使许多具有和古尔纳相似遭遇的桑给巴尔人被迫流散英美,无法归乡,陷入了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这种身处异国而产生的沧桑凝重、孤独犹疑之感是古尔纳创作的根本原因,这在他作品中人物的身上也广泛地折射出来。
(一)第一层囚笼:桑给巴尔的奴隶制以及当地对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盲目推崇
本篇小说《囚笼》应该也发生在桑给巴尔某个深受英国殖民文化影响的小岛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囚笼》很像古尔纳长篇小说《天堂》(Paradise,1994)的早期雏形,我们可以将两本书互相参照,在共性与差异性的对比中观照古尔纳思想的发展变迁。《囚笼》的主人公哈米德与《天堂》的主人公约瑟夫同样都有自小离家,受雇打工的人生经历:在12岁时,约瑟夫就被笃信穆斯林教义的父亲抵债给阿拉伯富商哈利勒(Khalil)做契约劳工。约瑟夫的父亲是阿拉伯混血,他毕生以让一位纯种的阿拉伯女子抛弃家庭与他私奔为荣。在约瑟夫幼年时,他便严格禁止约瑟夫和当地土著人一起玩,他大肆向约瑟夫宣扬阿拉伯人奉为圭臬的《古兰经》的内容,严格培养他的穆斯林习俗,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只有阿拉伯人是高人一等的。后期约瑟夫在富商哈利勒的店里打工,受尽苦楚折磨,哈利勒也每天不停地向他灌输穆斯林教义:“工作就是真主的神圣法令,允许人类为他们的邪恶赎罪”,他们都企图利用穆斯林的信仰让约瑟夫心甘情愿成为一个听话的奴隶男孩,任由他们的摆布,毫无怨言地完成工作。
在《囚笼》中,同样是自小离乡,哈米德也在小店勤勤恳恳地做了多年售货员。他日复一日地过着乏味枯燥的帮佣生活,他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异乡漂泊,远离故土,没有亲人关心,没有朋友陪伴,陌生的社会环境、风俗文化都与他原先接受的大相径庭,光怪陆离的新世界使他感到无比的恐惧与迷茫。作者在文中并没有说明哈米德早年离乡与思归不得的原因,笔者推测,哈米德应当和约瑟夫一样是被父母卖做了契约劳工,因此他说自己“一无所有”。作为一个契约劳工,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这恰好解释了文中他极度眷恋故乡却从不曾有过攒钱回乡的念头,因为他深知一朝为奴,便注定永远失去了回乡的自由与权力。桑给巴尔的奴隶制度、穆斯林教义中的糟粕部分以及当地人对于阿拉伯血统的盲目推崇,是阻隔哈米德追求幸福的第一层囚笼。
(二)第二层囚笼:西方殖民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与文化输出
面对陌生而冰冷的移居地,哈米德是没有故乡支撑的人,他只能通过努力地工作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而为移居地创造一些经济效益是他融入当地社会的唯一途径。哈米德是淳朴勤劳、善良忠厚的非洲本土人的一个典型,起早贪黑是他工作的常态:每天清晨,当最早的一批工人开始上工,他就开始营业,而直到夜晚最迟一个游荡者回家,他的小店才打烊。哈米德对于工作怀着一种极度敬业与负责的心态,并且一坚持就是十几年。这份对于工作的努力,不只是自己勤劳的本性使然,也不只是老板长期灌输穆斯林教义使然,我认为这更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途径。他试图用忙碌掩饰自己思归不得的寂寥悲伤,在异乡难以融入的孤独脆弱,他认为只要让自己充实起来,就没有时间一直处于一种自怨自怜的境地。
在为人处事上,哈米德表现地如稚童一般诚实质朴,在某些时刻甚至显得有些粗笨和痴傻。作为一个兢兢业业,有十几年工龄的老员工,他完全可以凭借多年的资历向老板索求一些福利,但是他却从来不求些什么。当被问起在店里工作这么久,是否赚了很多钱或者有私藏,哈米德只是淡淡地答道:“我一无所有,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2]41他总是默默地埋头苦干,单纯到仅仅为自己的工作熟练而感到快乐自豪:“店里忙的时候,他脚不着地,一边和顾客们插科打诨,帮他们从货架上取下各种商品,一边为自己的驾轻就熟而沾沾自喜。”[2]41
但是,老板法吉尔并没有给他相应的回报和待遇,哈米德自从十几岁来到这个新的小镇就一直在为他干活,然而法吉尔只给他提供食宿,不曾给予过分毫工资和酬劳。夜晚,哈米德露天睡在法吉尔里面的院子里,万一碰上下雨只能在店里随意收拾一块地方将就一夜。此外他还要给老人提供情绪价值,负责陪老人说话,扶他上厕所、倒夜壶……十几年的共同生活并没有使老人对哈米德更亲近一些,他从来没有把哈米德当做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因为在他的眼中,哈米德只是为自己打工的最底层的黑人劳工,不值得付出尊重与爱。古尔纳用冷峻的语言将哈米德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置于我们眼前,在字里行间读者感受不到哈米德丝毫的怨恨,他只是麻木而平静地接受着一切,连难以忍受的孤独也只是留到夜深人静的黑夜独自消化下咽,如困兽一般默默舔舐伤口。他根本不知道法吉尔对他的所作所为是非人道的,何谈反抗。古尔纳写这种近乎悲哀的麻木,意在揭示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民众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剥削与伤害。在殖民者的枪炮之下,无数普通黑人民众被相同的历史遭遇所裹挟,他们被认为是具有“动物的属性”,只要像对待牲畜一样给点吃食就可以养活,在身体上遭到了非人的残酷奴役。在精神文明与信仰上,西方殖民者将自己的侵略行为粉饰美化,用“没有殖民就没有文明进步”的说法试图掩盖自己在非洲大陆上的累累罪行。他们铺天盖地地输出西方文化,疯狂地对非洲人民进行洗脑和控制,导致非洲本土文化在外部挤压下被迫边缘化。古尔纳通过描写《囚笼》中哈米德的生活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在这股后殖民主义浪潮中,长久处于西方文化霸权语境下的非洲人民的渺小无力,哈米德只是千千万万被殖民者中的一个,还有无数的黑人正处于压迫之中而不自知。正如鲁迅曾经提到的:“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毁破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普通的底层非洲民众处于这间铁屋子之下,只能感受到无穷无尽的痛苦,但是无法说出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他们在害怕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他们只是生理性地恐惧、抗拒那些西方殖民者,却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因为无知,所以不懂是什么在根源上造成了他们的不幸,他们最终无法打破铁屋子,也无法走出囚笼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这种无知、困惑、迷茫感正是古尔纳所深深同情的,他一直试图在小说创作中为处于压迫下的非洲人和流散非裔找到一种自洽的方法。
(三)第三层囚笼:哈米德看清命运后的自我放逐
哈米德努力地工作和生活,或许也曾经对未来怀抱过希冀与憧憬,但是新的世界并没有因此而眷顾和吸纳他。他把一腔赤心剖给别人看,可真诚待人、努力工作换来的并非平等与尊重,肤色和种族决定了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永远不可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充满歧视的社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他发现自己无法改变现状,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困兽犹斗,结果是徒劳无功的。他明白只要一日不摆脱他为奴的身份,他的命运和未来就是一眼见底的稀碎狼藉。远在千里的故乡已不能复归,而新的社会又融入无门,他成为了异质社会中的“夹心人”。于是在看清一切的失望下,他最终屈服于宿命,自暴自弃地将自己封闭在这一方小店里,“独自一个人过夜,从不出门,有一年多的时间,几乎足不出户”[2]96,他选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画地为牢。
“从床上到店里只需要一分钟,他也从来不去其他地方……因为缺乏适当的锻炼,他的腿变了形。他整天都待在店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日子就这样天天过去了,一辈子都像个傻子一样被困在圈栏里。”[2]47他将自己禁锢在无形的囚笼之中,像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目的地活着,在暗无天日的小店里虚度光阴,了此残生,任由生活散发着腐臭衰颓的气息。哈米德的自我封闭是当时大环境下的个人悲剧,也是古尔纳对桑给巴尔社会一记振聋发聩的拷问:流散非裔如何才能在以种族和肤色划分等级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他呼唤人们去正视这个亟待改变的现实,一日不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一日不把西方殖民者从非洲大陆上驱赶出去,就不能完全实现国家的独立,类似哈米德的悲剧就还会不断重演。
生活上的困境或许还堪忍受,但是精神上的荒漠与无尽的孤寂则是无法消解的。哈米德逃避抗拒与外界的接触、交流,把小店视作自己唯一能够艰难存活的舒适区,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控制不住地渴望光明,“他得意地说,当售货员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过路人”[2]124,而真正失去希望的人是不会有兴致去欣赏窗外风景的。哈米德身处繁华十字路口上的热闹小店之中,他喜欢站在窗前眺望外面行色匆匆的路人,这也暗示了他心底深处仍有尚未熄灭的一丝焰芒,在烛照着通往囚笼外世界的道路。极度惧怕与极度渴望的两种情绪在他身上矛盾地交织缠绕,正因如此,美少女茹基娅的出现才会如流星一般点亮了他的天空,他一直渴望着在如死水一般庸常平淡、没有期待的生活中可以出现一位救赎他的天使。
这份突如其来的强烈爱恋使哈米德的生活有了追求与念想,也给予了他勇气去走出自构的囚笼:“一天晚上,他闩上店门,走到街上。他慢慢地朝最近的那盏路灯走去,然后又走向下一盏。令他惊讶的是,自己竟然不觉得害怕。他听到了什么动静,但仍旧目不斜视。既然不知道要去哪儿,就没必要害怕,反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么一想,心里反倒坦然了。”[2]119往日哈米德处于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小镇中,只觉得到处都是梦魇似的都市精怪,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科技与全新的社会模式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强势地闯入他的世界,不给他一丝喘息适应的机会,过度的刺激与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令他十分惧怕所在地的新社会。现在,因为明确了为什么而活的目标,哈米德拥有了走出囚笼、面对世界的底气,他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在孤苦无依地苟且生活。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时常幻想着与同为异乡人的茹基娅亲亲热热,这个罗曼蒂克的恋爱幻梦在他单调苍白的生活上撕开了一个小裂缝,洒下点点闪烁的希望。因为爱情,他滋生出了与生活、宿命对抗的非凡勇气,纵使前路茫茫,遍布荆棘与迷雾,他在惶恐之后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
古尔纳借此给予沉闷黑暗的非洲社会一丝光亮,表明非洲人民对于幸福的渴求与追寻是不会被轻易动摇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古尔纳对非洲寄托的殷切希望与终极关怀:非洲是可以被改变的,流散非裔的困境是可以被打破的。
二、自我认同的彷徨与焦虑——西方与本土文化冲突之下流散非裔的身份困境
随着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兴起,桑给巴尔岛及其群岛成为东非沿海地区发展最繁荣的一颗明珠,吸引了大批阿拉伯人、波斯设拉子人、印度人来到岛上定居与经商,他们在周边形成了重要的商业贸易圈。这些外来民族(以阿拉伯人为主)与当地黑人族裔班图人广泛地通婚,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混血民族:斯瓦希里族(Sawahil),而他们所创造的斯瓦西里文明,在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吸纳了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象征着非洲大陆上各民族文明的高度融合,让我们看到非洲文化自身包容性、国际性的发展可能,而非西方殖民作家书写文本中一味落后野蛮的形象。
与其说斯瓦西里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现象,不如说是桑给巴尔非洲人共同的身份象征。早在西方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之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同属于斯瓦希里族,斯瓦西里是桑给巴尔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19世纪后,英国殖民者接管统治了桑给巴尔,他们随意地将源于西方的种族范式引入非洲,将桑给巴尔人分为三六九等。其实,“桑给巴尔的本土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严格的种族性划分,他们共同的情感投射归属是伊斯兰文化”[1],这是当地的一种文化特色,即当地人并不以人种来划分身份。本土民众(多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与土著人的混血)都认为自身是斯瓦希里族的后裔,也被称作设拉子人。英国殖民者的种族政策使斯瓦西里族被迫进行拆解和分化,随着新的种族名称的诞生,“斯瓦西里”这个称呼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烟消云散,这意味着桑给巴尔人正在逐渐丧失自己民族宝贵的历史和记忆,也是造成哈米德身份消逝的根本原因。
桑给巴尔是东非穆斯林分布最多的地区,那里的人口几乎 99%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斯瓦西里族共同的信仰。“东非的伊斯兰教塑造了当地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并已逐渐成为个人和公共身份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1)Felicity Hand, “Untangling Stories and Healing Rifts: Abdulrazak Gurnah's ‘By the Sea’”.,然而,西方文化的输入强烈地冲击着桑给巴尔的传统教义,它们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桑给巴尔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伊斯兰文化进行解构。
《囚笼》中提到哈米德在初来小镇的时候,总是在夜晚听到令人心生惶恐的窸窣声:“夜深人静时也没有再听到那曾经让他吓破胆的窃窃私语声。现在他知道了,那声音是从长满虫豸的沼泽里传出来的。”[2]这个令他吓破胆的窃窃私语声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他是在幻听还是精神不正常地做梦,这都说明了他白天的恐惧已经延续到夜晚无意识的思想活动之中。古尔纳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笔法,对西方殖民者的形象进行颠覆与逆向书写,用沼泽中的“虫豸”象征西方殖民者,用“窃窃私语声”象征他们在文化上无形的入侵和渗透,将西方殖民文化带给非洲人民的恐慌情绪进行了具象化。
在《天堂》中,古尔纳也多次借他人之口讲述荒诞的故事,影射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冲击。约瑟夫在长达八年的商旅奔波中遇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种族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得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亲身经历和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一位印度籍机械师卡拉辛曾对他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欧洲殖民者豢养了一条巨犬,专门训练它去吃穆斯林人,“如果你了解他们愤怒的吠声,就会听到它说:‘我喜欢真主阿拉(Allah-wallahs)的肉,快给我带来穆斯林男子的肉!’”(2)James Hodapp, “Imagining Unmediated Early Swahili Narratives in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这个故事无疑是在对《古兰经》中的穆斯林神话进行解构。诸如此类的经历使约瑟夫开始质疑伊斯兰文化的神圣性和优越性,他原本是虔诚的穆斯林信徒,但是途经城市中所接触的新文化却在不停地动摇他原本的文化背景,企图解构他心中奉若圭臬的穆斯林教义,这也是西方文化与桑给巴尔当地传统文化的冲突。无数个夜晚中约瑟夫大声尖叫着从睡梦中醒来,他常常梦见自己被这只长着浓密毛发,长嘴长牙,黄色眼睛的大狗撕咬成碎片。这段经历与哈米德十分相似,他们同样频繁地在深夜做噩梦,担心黑夜下可能藏着噬人的怪物,“谁知道这黑沉沉的夜幕下隐藏着什么祸害人的东西呢?”[2]212这个梦中恶犬的形象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解释,他曾在《梦的解释》一书中提到:“人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排斥的恐惧如何通过潜意识进入意识层面,需要通过一种伪装方式,即把现实生活中困扰内心的一些情感思想转化为梦中的真实形象,这种方式叫“象征作用”。这只在约瑟夫梦中反复出现并深深困扰着他的恶犬,恰恰代表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对西方殖民者武力的恐惧,对陌生的西方文明的畏惧,对自我身份定义的彷徨焦虑。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下,穆斯林文化被解构和衬托成为野蛮、粗俗、落后的代名词。
这一点在《囚笼》的叙事中表现地非常明显,白人至上的观点在殖民地区甚嚣尘上。《囚笼》中,茹基娅在当地一家白人酒店工作,她对自己的工作地点深以为傲:“‘最好的那家,赤道酒店。’她说,‘那儿有一个游泳池,到处都铺着地毯。住的都是白人,欧洲人。也有一些印度客人,但那种荒郊野外来的、会把床单弄得臭烘烘的人一个也没有。’”[2]136由此可见,在桑给巴尔社会,人们似乎已经默认了这样的概念:西方种族代表着高贵与文明,而本土的非洲族裔则代表着低贱、野蛮、肮脏、血腥、暴力。西方殖民者把自己上升到神的位置,通过神化西方殖民文化来贬低非洲传统的穆斯林文化,使得斯瓦西里人最终失去了自己的信仰。这种与生长的母体文化进行的脐带割裂,使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下的非洲族裔产生了对于自我身份定义的困惑与自我认同的彷徨迷茫,陷入了“我是谁”的终极疑问。赛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他们既因怀乡而感伤,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一方面,这些非洲族裔对自幼接受的文化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又在新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对本土文化进行质疑和反思,在这种割裂的环境下他们成长为了矛盾的人,既不能完全认同新文化,又不能完全割舍旧文化。
“堤坝上灯光闪烁,星星点点的亮光在黑暗中连成了一线。谁住在那儿呢?他心想。他因为恐惧而浑身战栗。他不知道住在城市那端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的脑海中出现了面目可憎的强壮男人,正瞅着他放肆地大笑。光线昏暗的林中空地上,隐蔽着的影子们正候着他这个陌生人。过了一会儿,男男女女都围了上来。他听到了他们在古老的宗教仪式中沉重的脚步声,也听到了他们胜利的欢呼——因为他们敌人的鲜血正渗入被压实了的土地。他害怕住在对岸黑影里的人,不光是因为他们对他虎视眈眈,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哪儿,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2]138
这一段文字包含了大量隐晦的象征,“面目可憎的强壮男人”“星星点点的灯光”“城市那段的人”都是指拥有铁枪坚炮的西方殖民者,他们用武力迫使斯瓦西里族古老的宗教传统消弭在历史的烟尘中。为何哈米德在勇敢地走出自构的囚笼之后仍然感到难言的恐惧与迷茫?因为他发现自己是处于异质文化夹缝中的流浪人,没有故乡,也在失去历史和记忆。
三、在回忆历史中重构民族身份——古尔纳为异乡者寻根提供的道路
通过古尔纳的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回望那段时期桑给巴尔的社会历史,也明晰了导致像约瑟夫一样的阿拉伯混血、像哈米德一样的非洲土著人痛失身份的根本原因正是斯瓦西里文明的消逝。
美国评论家菲力赛提曾说:“我对古尔纳艺术的理解是:他一直有恢复斯瓦希里海岸历史的愿望,或更准确地说,恢复桑给巴尔人历史的愿望。”古尔纳自己也表示,研究人类和民族的记忆是如何运作的是解构历史叙事的迷人工具。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他大量地进行怀旧书写,试图在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中恢复记忆,重新找寻关于斯瓦西里海岸的历史、桑给巴尔人的历史,在对历史的重新发掘中,寻找自己的精神之根,获得民族意识与身份认同。
古尔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强调,自己仍有家人在桑给巴尔生活,他来自那里,那里是他的精神家园(3)Sammy Awami, “In Tanzania, Gurnah’s Nobel Prize win sparks both joy and debate”.,“海外旅居多年并未剥夺他的文化和精神之根,这一点在他的自我认同和文学创作中显露无遗”[18]。在他的作品中,关于故乡桑给巴尔的书写篇幅占比举足轻重,他的小说题材大多来源于在桑给巴尔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地点在桑给巴尔,主要人物均是桑给巴尔的原住民或者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桑给巴尔人,如《朝圣之路》(Pilgrim’sway, 1988)《赞美静默》(Admiringthesilence,1996)《海边》(Bythesea, 2001),这三部小说均讲述了桑给巴尔籍流散非裔移民英美后,在异乡深受白人歧视,无法融入社会,不被接受的苦痛迷茫。他们由于政治原因思归不得,只能反复地在对故乡的深深怀念之中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故乡”是他至关重要的写作素材,已“渗透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纤维”,为他提供不竭的创作灵感,主宰他的文学想象。恢复故乡的记忆,寻找民族之根不仅是他小说创作的宗旨,也是他经过多年思考之后,对处于异质文化夹缝中的流散非裔如何解决生存困境、精神困境、身份困境所探寻的道路。
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西方殖民较于以前变得更为荫蔽而具有欺骗性,它以类似殖民的方式推行文化霸权,严重影响了已经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格局。如果说前几个世纪盛行的殖民主义只是对非洲少数精英阶层思想的改变,那么当今世界的后殖民主义则目标更加宏大,它意在对非洲大陆全体民众思想无形的渗透及改变。面对这股浪潮,只有挖掘和还原本民族的过去,从记忆、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才能维系自己的民族身份,重新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家园”是伊斯兰文化中对“天堂”一词解释的重要元素,随着当代桑给巴尔人对种族作为身份标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广大流散非裔群体如果希望在异乡的社会中不至于飘若浮萍,必须克服西方殖民文化带来的自卑情绪,敢于正视历史,树立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从这方面来说,古尔纳虽然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后殖民主义文学家或者世界文学家,但他是真正意义上地在为世界、为人类而写作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世界主义立场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一直欣赏那种“为更大的世界而创作的人”,而非专门服务于某一国的标签作家。我们需要关注古尔纳在作品中对非洲社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理解他对西方殖民者形象进行批判、解构的逆向书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彰显非洲的主体性。这种写作倾向与主题思想对我国以及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新时代如何构建自己的民族主体性、民族意识、民族身份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