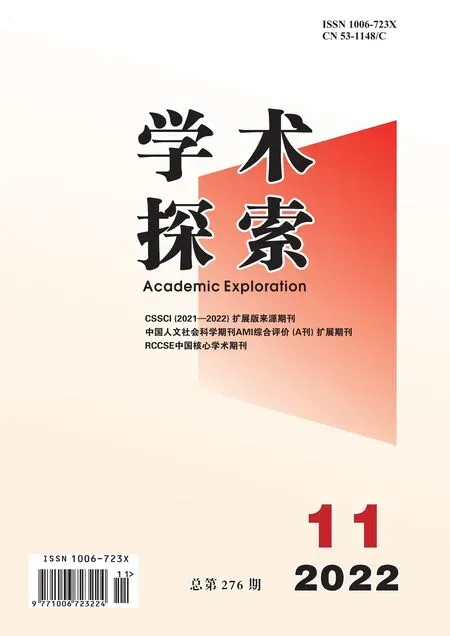“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剥离与统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
韦洪发,刘阳阳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经典著作,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马克思在《导言》中从德国现实着眼,通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法哲学批判,指出彻底的德国革命面临的重大困难——德国思想和德国现实的惊人落差,进而找到了德国解放以及人类解放的两大“工具”——德国哲学和无产阶级,指明德国解放以及人类解放的路径——依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马克思以他敏锐的眼光、严密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指出解决德国革命重大困难的关键在于“理论需要是否直接成为实践需要”,[1](P11)并进一步指出要将两者统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P11)“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10)这一经典论断是马克思对于实现“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统一的逻辑表达。厘析两者的剥离状态,解析两者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便于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在统一理论与实践中的定位,不断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境界。
一、“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剥离状态
马克思在《导言》中写到,如果按照法国的纪年,1843年的德国也不会是1789年刚刚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德国现实严重落后,自然更不会处在当代的焦点。然而,与德国现实的片面、低下保持同步的是德国思维(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抽象与超前,所以德国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思想上的超前使德国人超前于现实,直接在思想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所以马克思说,德国人是“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历史同时代人”。德国对于作为当时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进入现代国家的英法来说,是他们的“理论良心”,因为德国的国家学说描绘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未来图景,但同时反映出现代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因此,不仅德国的国家制度,而且现代国家机体本身也存在着缺陷。那么,对法哲学的批判承担了对德国政治意识形态和对现代国家机体的双重批判。这样的批判只能是通过“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实行“人的高度的革命”来实现,而这样的革命即是越过革命的多重阶梯,直接瞄准人的解放的彻底的德国革命。它的实现需要彻底的德国理论、“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在当时,德国只具备了一个条件——彻底的德国理论,即人的解放的哲学,而现实中并不具备革命的被动因素、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德国理论远超现实,早已反映出德国现实中被遮蔽的真相,它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1](P11)产生了“惊人的不一致”,即“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的剥离。
为了下文厘清“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的关系和两者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对“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的界定。“理论需要”,即德国理论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所反映的意图。“实践需要”即德国现实中所反映的诉求、所采取的行动。在应然层面上,“理论需要”是“实践需要”的理论表征和价值要求,“实践需要”是“理论需要”的实践目标和价值旨归,“理论需要”的实现,只有和“实践需要”相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能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2](P88)才能完成。
(一) “理论需要”的超前:“当代哲学同时代人”
早在马克思写作《导言》之时,德国早已经过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对宗教的辩证法批判,以及费尔巴哈对宗教的人本主义批判,证明了一个伟大真理:宗教是一种以颠倒的形式反映现实世界的意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就是“颠倒的”,宗教是人创造的,而人“就是国家,社会”。这也正是“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对宗教进行彻底的批判出发。马克思强调的德国理论——人的解放的哲学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是“此岸世界”的真理,与以往“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相区别,它已经挣脱思想世界的牢笼,扎根并融入现实生活,这种革命的哲学以哲学里的特殊战斗参与到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中。[3](P37~38)
在当时,德国的“理论需要”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德国理论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P10)即德国民众应该奋起反抗,推翻德国一切压制人的制度,使自己解放成为真正的人。这样的“理论需要”是要求“实践能力”的,可以“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但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虽然马克思以宗教改革为例承认“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但同时遗憾指出,“理论的解放”不会“正确解决问题”。然而,德国“理论需要”的超前就在于,它对彻底革命的需要并没有被德国民众广泛认识。水深火热中的德国民众没有意识到他们遭受着现实的压迫、非人的耻辱,仍在借助宗教求得精神慰藉,仍在“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1](P4)
(二) “实践需要”的落后:“不是当代的同时代人”
处在“时代错乱”中的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着现代各国的发展”,[1](P11)用思辨的德国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与“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在实践上远远没有达到现代各国的高度。德国各邦由封建贵族把持政权,推行专制统治,而且政府又突发奇想地将书报检查制度和法国九月法令相结合,所以德国悲惨地承担着旧制度的“野蛮缺陷”和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的双重缺陷,遭受着双重折磨。因此,德国成为一种具有当代政治的缺陷的特殊领域,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式的缺陷。同时,德国“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在“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当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制度正遭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尖锐批判和工人运动的猛烈冲击时,德国却在努力发展资本主义;当英、法正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时,德国正打算通过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把垄断发展到极致。可见,在英国和法国被认为是陈旧腐朽而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1](P6)正由理论向实践过渡。
同时,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历史法学派、理论政治派、实践政治派对德国现状的批判均未触及问题的中心,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历史法学派轻视历史研究,从不对经验史实进行仔细甄别。理论政治派从思辨的哲学入手,以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为批判对象,这种批判仅仅停留在思辨领域,全然不顾现实的国家和现实的人,根本没有触及德国现状。实践政治派也同样有错误,它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消灭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要求,而在于停留这个要求,即没有正确理解和处理德国法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没有将哲学归入德国现实。所以历史法学派、理论政治派、实践政治派都无法正确指明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出路。而马克思所要做的就是确立德国的人的解放哲学,将这一“理论需要”和德国“实践需要”统一,使哲学通过掌握群众转化为“实践需要”,并迸发出物质力量。
二、“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统一逻辑
德国“理论需要”与德国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正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想要弥合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9)这句话就是马克思实现“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进路。
(一)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将“理论需要”转化为“实践需要”,能够产生实现人的解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在这里“批判的武器”是指德国理论——人的解放的哲学,“物质力量”是指马克思将在后面提到的无产阶级,理论掌握群众、完成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是理论必须是彻底的。对此,马克思进一步说明:所谓彻底的理论就是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德国理论的彻底在于它是从人本身出发的。这种彻底性最早根源于对宗教的坚决废除,经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最终才确立了人的解放的哲学这样具有彻底性的德国理论。
马克思在《导言》开篇就提到,德国已经完成了宗教批判这一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批判。经过宗教批判后,宗教的虚假形象昭然若揭:正是因为人生活在“颠倒的世界”中,人的本质失去了真正的现实性,人们只能借助宗教求得精神抚慰,获得虚幻幸福。宗教批判使宗教的存在在人间声誉扫地,使人放弃幻想,使人作为理智的人思考和行动,使人面对现实。宗教批判其实就是对尘世的批判——人们要求废除宗教其实就是要求摆脱当下的悲惨境况,追求现实幸福。随后,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以宗教为精神的德国制度,即使这种制度落后于资产阶级制度,但依然要作为批判的对象。政治批判通过揭露社会各领域的“沉闷情绪”、群众受奴役和压迫的境况,使德国民众认识到实现“不可抗拒”的要求关键在自己。同时,这种批判对现代各国也具有教益,因为德国现状代表着“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这些缺陷仍困扰着现代各国。当旧制度仍旧表现为“世界权力”,自由没有成为共同的追求时,当旧制度仍表现出合理性时,这不仅是德国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剧,所以批判、消灭旧制度是必然的。但是,一方面,即使对“敷粉的发辫”——德国制度进行否定,还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资产阶级制度“打交道”,因为德国兼具封建专制制度“野蛮的缺陷”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明的缺陷”;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对德国制度进行批判,实现德国民众的解放,也无法代表全人类的解放。可见,对德国进行政治批判并不充分,也无法达到最终目的。而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这既是对德国现实的坚决否定,又是对现代国家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因为这样的思辨法哲学的现实就在莱茵河彼岸——英国、法国。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黑格尔法哲学这一“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思想形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1](P9)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1](P7)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德国和现代国家的现实或未来相联系,这种批判只能诉诸实践。或者说批判一旦上升到人的解放问题上,就超越了黑格尔法哲学,即人类的解放是现实中的实践问题。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必须重新建构新的国家哲学,这种哲学能够将哲学和现实相连,具有实践性,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将现实归入哲学,能够成为指导人类解放的“武器”。而这样彻底的理论被马克思叫作彻底的人的解放的哲学。可见,彻底的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统一的前提,只有在确保理论彻底性的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准确把握“理论需要”、精确解读“理论需要”,才能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实践需要”,真正完成两者的统一。
(二) 在“搏斗式的批判”与“揭露”中指向现实
批判宗教与德国现实,揭露“一切卑劣事物”。第一,在批判中揭露宗教本质,并转向现实批判。宗教的本质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以颠倒的形式反映现实世界,以幻想的方式反映人的本质。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对人的现实幸福的呼唤。这种批判要求撕碎伫立于现实锁链之上的宗教,不是要求服从现实,而是要人将现实连同宗教一并“扔掉”,回归“自身和自己的现实”,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实、创造未来。所以宗教批判的完结之后,就是批判现实。第二,用好批判这一武器揭露现实的卑劣。在与现实进行的斗争中,批判充当“武器”和手段,是带有激愤和“搏斗式的”,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揭露卑劣的现实——整个社会一片沉闷,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互相对立、思想奴化;揭露政府本身这一最卑劣的事物——“政府制度是靠维护一切卑劣事物为生的”。[1](P4)这种批判最关键的是打击政府——通过描述德国社会的种种羞耻、唤醒德国人民的自我意识,德国人民深刻意识到“现实压迫”和“公开耻辱”,“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1](P5)不再自欺欺人,不再俯首听命于政府和社会现实。这种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德国人民发现自己是实现自己“不可抗拒的要求”的决定性力量。
批判政治解放的不可能,指明彻底革命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无法实现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政治解放)。他指出,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的一定的阶级基于自身特殊地位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这样的阶级必定是集中“社会的一切缺陷”和整个社会的昭彰罪恶,体现着社会的普遍障碍,而且这个阶级能够“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成为“社会的总代表”,将自己的特殊要求和权利转化为整个社会本身的普遍要求和权利,并且具备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只有这样,从这个阶级解放出来才是“普遍的自我解放”。然而,德国的现状恰好相反:社会中的每个领域像一潭死水,每个阶级都没有自己革命的立场,没有革命的热情与欲望,也缺乏社会阶级代表的“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和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德国根本无法实现政治解放。他进一步指出,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P15)这个特殊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德国解放的道路必然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彻底的革命之路。
在批判和揭露中,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德国民众关注现实社会、思考生活境况、唤醒自我意识,并在找寻解放道路中指明革命之路。至此,德国民众得以掌握“理论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初步实现了“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统一,而统一的最终实现还需要依赖“物质力量”。
(三) “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
在马克思看来,对德国来说,德国解放的唯一可能实现的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为立足点”[1](P15)的普遍的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1](P16)同样在他看来,将德国“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在确立彻底理论的前提,经由批判和揭露,最终的环节就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而无产阶级能够被“思想的闪电”击中,在于“思想”的彻底和自身的特殊性。
德国解放的关键不在于目前整个无产阶级以什么作为目的,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即“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德国无产阶级诞生于市民社会,但不属于市民社会,是因工业运动兴起、社会的急剧解体尤其是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人为造成的,遭受着普遍苦难和普遍的不公正,集中体现着惨绝人寰、毫无人性的生活状况,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和“一切等级解体”,在它身上,没有特殊的权利,只有普遍的权利,也只有它有勇气大声疾呼:“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1](P13)无产阶级是这样的特殊阶级:它必须以实现社会其他领域的解放来完成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因其自身的生活状况本身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整个结构的特殊存在所形成的特殊性必然决定其在历史上有所作为,这是无可辩驳的,这一阶级天生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自己,但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
哲学和无产阶级一旦结合、相互作用,哲学将变为现实,无产阶级将“消灭自身、实现解放”。[1](P16)人的解放的哲学这样的德国理论具有实践性,能够归入现实、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变为现实。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哲学的“物质武器”,两者互为目的与手段。一旦“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结合,“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将实现统一,所产生的物质力量将推动人的解放的彻底革命的实现,人也将获得普遍解放。
三、“两种需要”重要论断对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启示
从《导言》中阐明的“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关系以及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来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把握“理论需要”,并积极推进“理论需要”向“实践需要”的转化、引导“实践需要”向“理论需要”的趋近,在实践中推动两者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一) 守正创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守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之根,是方向,是旗帜,创新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之本质,是动力,是活力,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要求和目的,共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服务。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守正为根本导向,有助于正确把握“理论需要”。“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5]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跃进,都离不开思想理论的先导作用。从文艺复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到我国历史上为救亡图存兴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充分说明超前于当时社会实践的新思想、新理论深刻改变着人类历史发展轨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万马齐喑、风雨飘摇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6]指引中国走上了康庄大道。事实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理论武器。迈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加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武装群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彻底的理论。对于这些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要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推动理论的入脑、入心,真正正确地把握、认同“理论需要”,并自觉地转化为实际行动。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社会实践总会出现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实践需要”也总是会随之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以创新为主要动力谋发展。有创新,才会在“往前发展、与时俱进”中推动“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的统一。创新源于问题,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问题意识,在问题中把握时代发展新境遇、新潮流,勇于应对时代新挑战,勇于承担时代新使命。不仅善于用理论说明、指导、解决时代新问题,更要对时代发展出现的新“实践需要”给予理论新解读,坚持在守正中创新,“在改进中加强,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7]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中,不断推进“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的统一。
(二)敢于亮剑,对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剖析和批判
彻底的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与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的坚决斗争中坚持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的。对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的批判,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所担负的重要理论使命。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空前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人们的思想阵地极易被错误思想观点侵蚀,这些错误思想观点顽固且不加以批驳不会自行消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坚定立场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公开直面、深入剖析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用好批判这一有力武器,在剖析、批判与争辩中,明确“理论需要”,修正“实践需要”,推动两者在实践中走向统一。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各种错误观点和社会思潮进行剖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4]将这些观点和思潮“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来龙去脉”,说明白“真实面目”,让真理在诘问和辩难中被学生熟知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各种错误观点和社会思潮进行批判,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辩证认识、理性分析”[5]这些观点和思潮,在批驳错误观点和思潮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防止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4]和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现象,培养和强化学生辨别是非、真假、黑白、善恶的能力,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锻炼和提高抵御错误观点和思潮的能力,激发和涵养学生的使命担当、气概与情怀。
(三)学以致用,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付诸实践见诸行动
实践是联结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中间桥梁,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最终实现“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属性之一,标明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价值实现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讲授彻底的理论与正确的观点,还要引导学生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引领人生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8](P815)理论的价值实现最终都要落实到实践上来。
当前我国正经历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实践,不仅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舞台,而且亟需科学理论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仅要求理论蓬勃发展,加快构建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要求理论先于实践,提前预见实践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指导方案。对学生来说,学习、掌握的科学理论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存在于脑袋中,也必须运用到实践中、落实到行动上,在实践中协调并促进“理论需要”与自己的“实践需要”的统一,最终在两者的统一中收获造福社会、成就自我。理论是在实践中生成并不断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活动,同样需要突出实践特性,要深入学生生动的学习和生活实践中,将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增进情感交流,激发思想共鸣,调动实践热情,增加实践体验,更加深刻地理解理论;要引导学生正确处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地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避免照抄、照搬、教条化理解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相一致,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促进人的成长成才、实现人生价值。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学生正确把握“理论需要”,在透察世界发展大势、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将个人志向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相结合,确立人生理想与抱负;要积极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引导学生在时代提供的广阔天地中,投身到火热的生活实践中,在脚踏实地地不懈奋斗中实现人生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