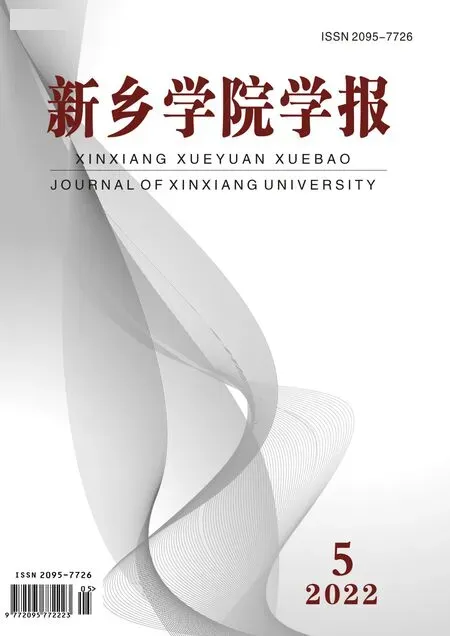论20 世纪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变革
王保先,刘丽媛
(1.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历经清末、 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时期,20世纪的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也经历了从乡村自治到单位治理的历史变迁。 从社会结构、地域空间和治理模式三个方面考察这一历史变迁, 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背景和经验, 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一、从乡村社会到单位社会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基本上就是指广大乡村。 在“皇权不下县”的制度框架下,乡村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自治状态。 传统中国治理的特点是上下分治的双轨制治理, 其治理体系由皇权控制的上层管制系统和地方族长或乡绅控制的基层管制系统两部分组成[1]。 在这一治理体系下,县官只管本地的赋税和司法纠纷, 其余的事务几乎一概交给家族或士绅来管理。 因此,帝制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相当的自治性,并且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清代延续了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乡村自治以保甲为载体、以宗族为基础、以士绅为纽带[2]。清朝末年,在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下,清政府开始学习西方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受西方自治思想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随之发生了变化, 清政府开始涉足乡村自治领域。 1908年,清政府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详细规定了城镇乡的自治区域、自治范围、自治机关、自治选举、自治监督等各项治理事宜[3]。 不过,在晚清统治者看来,推行地方自治只是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清廷认为,自治团体在地方治理中仅仅发挥了“纯粹的补充性作用”,它们管的只是地方政府没工夫管的事情,因而这种地方自治就如同传统社会士绅和官僚的分工与协作[4]366-367。 由此可见,晚清政府当时并不是要真正推行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 创立了中华民国。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推崇地方自治,继任的袁世凯在1913—1914年废除省、 县两级的自治方案,采取区、村两级的地方行政制度,即在县下设置规模大体与传统的乡相仿的行政单位——区作为基本行政单位[5]64。 这样就突破了中国社会治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首次在县以下设置基层地方政权,“皇权”下县了,区成为基层的正式行政机关,并且区的长官不是由本区自己选举, 而是由县一级政府委任[4]370。 区的下一级是村,国家权力逐渐延伸到村落,村中设置村民会、息讼会和监察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具体负责村里的行政、司法和监察等事务的管理[5]64。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村虽然名义上还具有自治权,但其实已经被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之中,国家权力开始介入乡村社会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训政后, 1928年通过了《县组织法》。 该法主要仿照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村制,在县以下设置区、乡、闾、邻等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是行政性质而不是所谓的自治组织[6]115。这种治理模式其实就是国家权力逐渐下沉到乡村, 把自然村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用保甲组织取代了乡镇、 闾、 邻等组织, 等于用官治代替自治[6]164。1934年, 国民党当局颁布 《改进地方自治原则》,把乡、镇和村划为一级[5]66。 当时蒋介石提出“新县制”,虽然国民政府1939年发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明确规定了县、乡镇自治团体的“法人”地位,但是乡镇并没有变成自治团体, 而是彻底成为县政府下面的一个“官治衙门”[6]231。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基层社会控制不断加强,乡村自治组织几乎没有自主权,乡村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下渐渐丧失了自治性, 每一个村庄、家庭甚至每一个人都被网罗在政府可控的范围之 内[7]。
除了国民党政府管理的村庄外, 这一时期的乡村还有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基层自治的实践,比如实行供给制和允许机关从事生产活动, 并且允许军政单位在中央财政体系下可以保有一部分自己的财权来筹划单位的集体利益, 这些尝试对后来新中国单位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8]。 当时的生产单位被称为“公家”,这种新的“公家”不同于传统的家庭,虽然它们有类似的功能,但是前者提供的是福利保障和安全保卫, 后者提供的是情感慰藉和安全保护[9]49。 单位和家庭的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反映了传统家庭的功能对生产单位的极大影响, 就像一个家庭对待其成员一样, 生产单位也承担了照顾单位成员的职责[9]5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基层自治实践, 极大地影响了1949年以后单位制度的正式建立。
单位是1949年后在中国普遍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和制度。 当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是通过单位这一组织进行的。在单位制下,所有的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单位,由此形成了“单位社会”[10]。国家的宏观治理架构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的三级结构。作为国家和个人的中间组织的单位, 在城市表现为工作单位,在农村表现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它们都是单位体制的组成部分[11]128。 作为国家与个人的联结点,单位在国家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时整个社会的治理可以看作一种“单位治理”, 即单位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产生了变革, 由乡村社会变为单位社会, 基层社会治理从乡村自治转为单位治理。 改革开放之后,单位体制逐渐弱化,不过由于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 单位治理模式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二、从农村到城市
清代地方治理已经利用地方的非官方组织,如地缘社区、宗族或行会等[12]。19世纪末“地方政府授权传统的城市组织承担市政府的某些工作,其模式是从某种专门的职责过渡到一种普遍的责任”[4]362。这种城市组织发挥的作用类似一种半行政组织,可见地方政府依靠非正式行政组织进行基层治理早已有之。 在1949年前的城市社会中,不仅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还存在许多传统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力量,它们勾结官府,借助帮会、师徒和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把持工厂企业[11]99。 民国时期,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同乡会、 帮会、 行会等非官方社会组织。同乡会是由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人建立起来的,这些工人依靠帮派和行会等被安排到工作场所做工[9]60。当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单位同样受传统家族关系的影响, 这表明它无法拒绝传统的强大力量, 单位体制的建立与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和社会逻辑是一致的[13]。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 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抵御侵略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正是单位治理模式起到了组织、发动民众的有效作用。而单位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城市社会中快速建立起来, 一方面是受国民党在城市建立国营企业制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单位治理模式的影响, 两者共同为1949年后单位体制在城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9]60-61。
有学者将单位制度广义地界定为 “占据主导地位的行政体制”,并在此意义上将单位制度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4]232。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国民党政府创立了一种国营企业制度, 工厂管理社区的现象出现了。 这种“工厂办社会”的模式可以说是后来“单位办社会”的早期形式[14]285。 当时,国民党政府将这些国营企业统称为单位, 这些单位为其职工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设施[14]244-245。 这种 国营企业制度, 为1949年后的城市单位制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民国时期城市的工厂企业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单位,虽然是在不一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但是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属于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并且都以生产为存在基础,以集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家庭伦理为社会关系基础[9]61。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的单位模式能够在接管城市后迅速运作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们“都以对以劳动组织为中心的社会集体的强烈认同为前提, 而且都试图供养和照顾集体成员”[9]105。 虽然1949年前的工厂企业和1949年后的工厂企业提供的具体福利有所不同,但是 “旧体制下由工作场所负责满足工人各种各样的需求延续到了新的体制下”[9]104。
作为新的社会基层组织, 新中国建立的单位取代了1949年前城市中的行会、同乡会等社会组织。 当时建立单位制度的目的在于把全国大多数人都安排到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组织中,把人们组织起来实现工业化[15]。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单一工厂制、条块分割为主要特征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16]103,单位制度在城市基本建立起来。 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第十条对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公民只有有了3种单位证明中的一种才能迁入城市, 一是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二是学校的录取证明,三是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的证明。这种户籍制度,妨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使得城市单位制度愈加固化。在农村,人口基本归属于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产队。由此,全国绝大多数人都被纳入单位之中。20世纪70年代,单位开始全面负责其成员的生活,甚至职工家属也同样享受单位福利,相当于家庭也被单位吸纳了,几乎每个人都处在单位的庇护之下, 由此造成了单位人对单位的全面 依赖[16]69-70。
总之,为了组织民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新中国通过“组织起来”和“包下来”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了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这些单位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要维护单位成员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承担许多政府职能。因此,单位成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元,发挥着联结国家和个人的重要作用。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中国基层治理的重心在地域空间上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20世纪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经历了从清末的乡村自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单位治理的历史变革。
三、从“家国同构”到“单位—国家同构”
传统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家庭, 大的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自治组织。 家长或族长拥有司法权、主婚权、财产权、人身权等家族内部事务的决定权,族长权是父权的延伸[17]。 在家族中,最注重的道德是孝,即要孝敬长辈、尊敬兄长。 封建统治者把约束家族的规范——孝转移到国家就成为忠。 皇帝就是国家的大家长,国家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家庭。在家庭中子女要对父母尽孝道, 同样在统治秩序下臣民要对君主守忠道,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结构——“家国同构”。
古代中国是“家国同构”,当代中国则是“单位—国家同构”,国家、单位与个人三者的关系表现为单位依附国家、个人依附单位,同时国家也要依赖单位来整合社会。 个人、单位、国家三者间的这种依附格局,正是传统“个人—家庭—国家”连带结构的当代变种。 也就是说,这种单位与国家的关系结构,基本上是传统家国同构的翻版[13]。 人们把单位称为“公家”, 其实是把传统的家庭私人领域拉入公共领域,在私人生活基础上组织公共生活, 传统社会的结构及其功能并没有变, 单位和家族一开始就紧密地关联着。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由家族共同体变为单位共同体, 社会结构由乡村社会变为单位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相应地由“家国同构”转变为“单位—国家同构”。
关于“单位—国家同构”的基层治理模式,大多数学者把单位看作家族的延续和变体,因为它们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比如,家庭中父为子纲的伦理在单位有所体现, 单位领导身上也有家族族长的影子[18]67-70。 单位吸收了家族的生产、分配、教育、抚育和赡养等职能,家族组织被单位取代了[19]。也就是说,单位组织仍然遵从乡土社会的行动逻辑,单位逐渐地成为一种新的家族[20]。
单位和家族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上,也体现在微观的行动上。单位治理和家族管理都具有封闭性, 当单位被赋予维系个人生活的种种权力之后, 在封闭的单位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家长制作风, 从而单位领导就像家长一样拥有了很多无形的权力。 因而,单位就像一个微型社会,单位人的行动策略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关系取向, 单位内部有着复杂的关系运作。 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依然存在于单位社会之中,甚至形成了一种单位文化,即“‘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依然是‘单位社会’中的基本结构”[18]354。 单位和家族在责任承担方面也具有某种相似性。 古代家族制度中家长或族长对外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在单位制下国家对单位、单位对个人也有一种无限责任[21]。 另外,单位和家族内部都存在上下级关系。血缘关系在家族中是第一位的,由血缘关系产生了差等关系,人与人的等级关系随着血缘亲疏的不同而不同。 在单位里上下级关系是拟定的, 即根据职位安排上下级关系。 因而单位与单位人之间不是真正平等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单位对其成员负责、成员全面依赖单位的复杂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不是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可以随便中断的, 即单位人对单位的依赖具有一种制度上的刚性。
单位不仅与传统的家族具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与乡村自治的各种治理要素有某些历史联系。 典型的乡村就是“由同质个人、核心家庭、家族以及一个或多个家族组成的村落”,它承担了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功能[22]。乡村自治的要素包括家族、士绅和保甲三个方面。 单位替代自然村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联结点之后,同样发挥了这三个方面的功能。单位除了经济职能与古代家族相似,还承接了家族的婚姻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等职能。就此而言,单位在官民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充当了国家和个人的中介,联结起了国家与个人。总之,单位治理吸纳传统乡村自治的有效要素, 同时又把它们严格限制在国家权力的管控之下,这也是单位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区别所在。20世纪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从乡村自治转变为单位治理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基层社会由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变为以工作单位为基本单元,社会结构由乡村社会变为单位社会,基层治理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基层治理的模式由“家国同构”转变为“单位—国家同构”。 这种转变,是国家权力下沉到基层社会直至完全覆盖的过程。 这个巨大的变化并非偶然, 而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从“乡土中国”到“单位中国”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