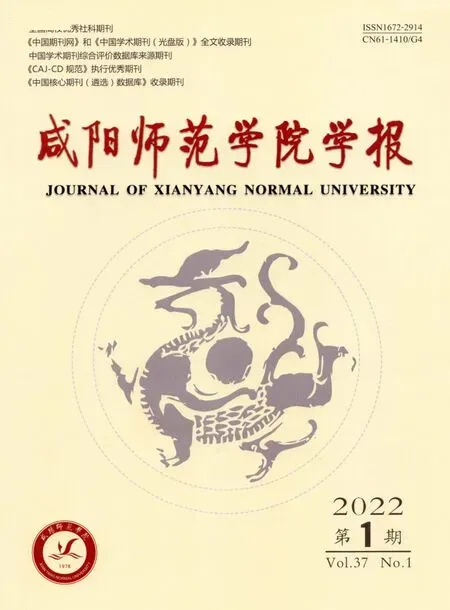贾谊无为思想探微
朱蔚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过去学界对西汉前期无为思想的研究通常着眼于当时的黄老思潮、陆贾及《淮南子》等,至于贾谊则往往阙略。实际上,贾谊对汉初无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新书·道术》当中。本文即以该篇为中心,展开对贾谊无为思想及其思想史意义的探究。
一 “无为”含义及早期问题
“无为”的概念化源于《老子》。在此当中,它与道及圣人行动关联在一起,构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圣人处无为之事”等核心主张。在先秦及随后的道家类文献中,“无为”与“自然”“道”一样都是最核心的概念。此外,随着学派间互动程度的加深,各种基于不同学术立场的无为思想也得以产生,无为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修正、补充与发展。[1]从“史”的眼光看,“无为”固然是一个随时发展的“动态范畴”;但从“思”的角度而言,不同时期的无为观念存在内涵上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通过探求“无为”一词的基本义项即可获得一定程度的揭晓。
历来关于“无为”的含义主要有两种解读:一是不为;二是不妄为。其实这两种解读在《老子》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根据,前者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47章),后者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战国中期以后,“不妄为说”被普遍接受,衍生出“因物”“循理”等主张。“不为说”虽时而招致批评,然诸子中论及“不为而成”者仍不在少数。可见,“不为”与“不妄为”均是“无为”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含义。它们是“人对自身的行为(作为与不作为)反思的结果”,[2]114蕴含着自觉精神。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无为”指向天或道时,它的确又具有无意识、无目的之含义,即无意识地为。综合以上三义,将“无为”概括为“表示没有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3]2是较为准确的。
“无为”本质上涉及对“为”之方法及原则的规定。而“为”本身所指向的范围又非常广泛,包括为学、为道、为政等等。其中,为政或君道意义上的“无为”向来是思想家们讨论的焦点。《老子》主张圣人法道之无为而实现无不为,《庄子》《韩非子》等区分主道无为与臣道有为,《吕氏春秋》强调“君道无知无为”等皆是此类。可以说,“无为”与“有为”之间的张力、矛盾是上述君道理论必然要涉及的主要问题。举例言之:在《老子》那里,圣人的“无为而治”明确排除了行动过程本身的有为,所谓“无不为”(有为)只是就行动的结果而言,老子以此协调二者;《韩非子》等以无为、有为区分君道与臣道,本意是在坚守君道无为的基础上容纳有为政治,但此举明显造成了无为与有为在君道实践上的割裂与对立。如何克服无为与有为之间这种形式上的割裂而使二者真正统合于君道实践当中,对此,先秦诸子并未给出完满的解答。此后,这一问题同样成为汉初思想家在陈述无为观点时难以绕开的难题。在《新书》卷八的《道术》一篇中,贾谊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二 《道术》与贾谊无为思想的展开
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生、贾长沙,汉初著名思想家。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贾谊年少成名,文帝初年即被召为博士,后凭借杰出的政治才能很快超迁至太中大夫,因受人谗毁而谪为长沙王太傅,数年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意外身故后亦自责而终。贾谊一生经历了巨大的起落荣辱,虽年寿不永,却也留下了众多思想篇章。此中又以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章居多,这些充分体现了他敏锐的时代问题意识及深切的现实关怀。
贾谊对文帝时期汉王朝的内外积弊皆有所认识,故而他批判时人所持的“无为”主张,认为类似的策略完全无益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是为将来更大的败乱埋下祸患。其曰:“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4]108不过,贾谊此处反对的只是“不动”或“不为”意义上的无为思想,现实当中的贾谊“颇通诸子之书”,兼采百家的广阔学术视野也令其得以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无为思想,而非仅是一味刻板地接受。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政治上的完全“不为”与“不动”,另一方面则对“无为”的君道理论予以更深入的阐发。正如潘铭基所说,贾谊政治思想之特征乃是“主有为而不废无为”。[5]30
《道术》系统呈现了贾谊的上述思想倾向。首先,关于此篇的写作背景,陶鸿庆指出,从《道术》当中的问对形式看,“当是作傅时与王问答之辞”。[4]305从内容上看,其中的确呈现了“人主”与太傅间的可能对话。另外,联系人物生平,我们亦可推知《道术》更可能是贾谊谪为长沙王太傅以后而非更早时期的作品。贾谊初仕之际便展露锋芒,时常踊跃建言,内容涉及改汉制、更秦法及列侯悉就国等。然而当时的贾谊也正因此受到周勃、灌婴等人的忌惮与排挤,后者言其“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致使其远谪长沙。从彼时政治环境看,贾谊早期的许多建言显得颇为大胆,与文帝初期优先稳固权位、安定国内的政策亦有不符之处。相比之下,《道术》一篇既主君道虚而无为,复倡温和有为之“术”,大有妥协折中的意味,与其初仕之时的奋发激进大相迥异。贾谊后为长沙王、梁怀王太傅,《道术》很可能便是其任上所作。具体写作时间虽已难考,但该篇内容主要谈论君道则是无疑。而与此前的其他思想家有所不同的是,贾谊是从“接物之道”出发的,其谓:
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诸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4]302
“所道接物也”的“道”训“由”,意为人以“道”应接事物。贾谊赋予“道”以“接物”的规定,一方面继承的是先秦儒家“道不远人”的传统,从而为后文强调“道”的人伦性与致用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此举沟通了“道”、君与“物”(事)三者,进而论道即是论君道、论具体处事规则。“道”的内涵由此充实化、致用化。
贾谊将此接物之道作本、末划分。“本”的方面谓之“虚”,指君主内在之虚静无为的接物状态,特征是精妙幽微,无预先之措置。从它与“道”的关系来看,“虚”是“道”落实于主体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是接物之道的“起点”。“末”的方面则称为“术”,指向具体事务的处置过程,体现着“动静”之理。“术”是连接“道”与“物”的桥梁,[6]21也是接物之道于外部世界的具态化。因此,在贾谊看来,“凡此皆道也”,“虚”与“术”都是“道”的展开。“道”不再是抽象难寻的存在,就在“虚”“术”及二者的现实关联当中。所谓的“虚之接物”与“术之接物”也并非是截然分立的两种接物方式,而是同一接物之道在不同层面(本、末)的展开内容。
贾谊的君道无为观就集中体现在“虚之接物”的相关论述中。其曰:
镜义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有衅和之,有端随之,物鞠其极,而以当施之,此虚之接物也。[4]302
正如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所指出的,自老庄以来,“虚”便是无为精神理想的重要体现。[7]33-34主体之“虚”往往等同于清静无为、无所秉执的内在状态,从物我关系而言则意味着主体对“物”的如实把握及从容因顺的安置。贾谊在前人基础上将无为或“虚”作为接物之道的内在总原则。他用“镜”喻与“衡”喻来说明“明主”如镜平、若衡公、虚静以接物的内在状态,不掺己意而使事物如实呈现、自然有序(“各得其所”)。随后的“明主南面而正”一句是对这种接物成效的补充说明,不过该句历来存有争议。宋代潭州本及建宁本皆作“正而”,清人卢文弨以“正而”为倒文,其说恐非。据方向东的意见,潭、建本不误,此当以“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虚而静”为句,“正而清”针对镜喻,“虚而静”则对应衡喻,[8]323其说可从。在先秦思想传统中,这种“物”(事)的自然有序性时常与君主循名责实、无为而成其功的统治理想关联在一起。贾谊发挥了这一点,认为君主之“虚”将在客观上促成事物的名实一致,并使人事得到妥当的安排。以上,“镜”“衡”之喻在整体上表明一种“以静知动”的认识途径及在合物本然意义上的“以静制动”原则,此皆体现了无为(“不妄为”)的特质。
贾谊的君道无为观既有承继于前人之处,亦有其独创的内容。若从措辞来看,贾谊论“虚之接物”一段文字固有近于《韩非子》之《饰邪》《扬权》《主道》诸篇及《申子·大体》之处,但贾谊所论述的主旨却有别于前人。他并非只停留于单纯的君道无为层面,而是旨在对无为之君道本身何以能蕴藏及进一步开展出有为之“术”做出探讨。在贾谊那里,无为(“虚”)只是接物之道的始点而非全部内容,不过,随着接物之道在现实当中的具体展开,君主的“虚”也确立了其作为“术”之“本”的地位。
三 无为与有为的统合
贾谊在《道术》当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无为与有为的综合实践何以可能”。他的观点既不像老子那样将无为与无不为分属于圣人施政的过程及结果,也不效法韩非子等人作君臣之际无为与有为的分立,而是从“道”之本末层面将二者统合于纯粹君道理论(不掺以臣道)及其实践过程。具体来说,贾谊从本末角度将接物之道划分为“虚之接物”与“术之接物”,并经由对“虚之接物”的内涵界定及“虚”“术”关系的定性而阐明了无为与有为在君道实践中的一体相关。实际上,这也是对《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理想的复归。
首先,“虚之接物”本就含有从无为向有为过渡的内在趋势。如前所述,虚静以接物的状态充分体现了无为的特质。然而现实当中的接物活动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体往往需要根据物情的变化随时做出反应与处理。贾谊认为,人主在保持如镜平、若衡公之虚静状态的同时,还须随机应变,所谓“有衅和之,有端随之,物鞠其极,而以当施之”。这当中包含了三条具体的接物准则:一是以事后的因顺式处理作为时机规定;二是主动推究源始,以事物之实情为认识基础;三是以“当”为处置原则。如果说准则一(“有衅和之,有端随之”)尚且属于无为在现实当中的延伸,那么从准则二(“物鞠其极”)开始,行为主体已然走出无为而趋向主动有为。准则三(“以当施之”)更是与主体原先“平静而处”、令物自“当”的被动姿态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它意味着行动者需事先接纳一套可以呈现是非利害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主动实现事物之“当”。从令物自“当”到“以当施之”,这些都在“虚之接物”范围之内。这也表明“虚之接物”并非只是单纯的虚静无为或者被动接物,而是兼有主动求“当”、适时作为的变通可能。
其次,贾谊将“术之接物”作为接物之道在外部世界的具体落实,以此实现接物活动的有为性。与“虚之接物”相对,贾谊列举了人主的几种“术之接物”,包括以仁、义、礼、信、公、法去感化士民,实现境内平治;注重举贤使能、固己德操、行以教训、稽验实情、明正好恶、细察事由、谨于用权,由此实现政事和畅、民心归化、树威信而少过失。[4]302-303此中既重德政教化,也兼含温和型的法(“人主法而境内轨”)、术(“密事端则人主神”)、势(“教顺而必则令行”)一类精神理念,呈现出贾谊学说兼采与调和多家之术的理论倾向。而在“术之接物”的有关论述之后,贾谊还介绍了56种“善之体”及其反面品质,认为这些也是“所谓道也”。[4]303-304这些“品善之体”的有关论述实际上可视为贾谊对接物之道所涉德行方面的补充规定,体现出其基于儒家立场的伦理关切。
最后,“术之接物”的展开以“虚之接物”为内在根据,现实当中纷繁的治理活动最终也要向虚而无为的接物总原则复归。由前可知,“虚之接物”指向主体虚静无为的内在状态及以静制动、知物本然、以当施之的原则方针,蕴含着由无为向有为过渡的内在趋势;“术之接物”则呈现为具体的事务处理或善政建设,属于有为的范畴。关键在于,“虚之接物”与“术之接物”是以“本”“末”形态而统一于人主之治理实践过程中的。“术之接物”只能是“虚之接物”基础上的具体实践,如此二者才能共享“应变无极”的实践成效。反之,倘若没有“虚之接物”作为依归,“术之接物”便只是无有所“本”的偶然施为,人主的“应变无极”也将无从谈起。《道术》篇末也说:“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圣人既能知道又能行道,也就是说,既能静态、内在地把握道的根本(“虚”),又能在具体行动(“术之接物”)中实践此根本。这表明“虚”与“术”在圣人行动中是高度一致的,而圣人之所垂范的无疑又可作为君道实践的理想归趋。此处贾谊意在提醒人主切勿只是着眼于“虚”与“术”当中的一项,而是一方面通过“虚”之涵养自然地容纳有为政治,另一方面使“术”的纷然开展亦有其归本。
总之,“虚”(无为)作为主观状态及内在的接物总原则,必须配以实践型的“术”,主体的接物活动才能完整展开。“术”作为具体而然的政治施为,需要以“虚”作为其前提与根据,否则单凭各类具态化的“术”是不可能达到“为原无屈”“应变无极”的理想效果的。经此,人主的无为与有为在接物之道的内外、本末一体性开展中实现了有效的统合。
四 结语
贾谊的上述理论是先秦两汉无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他首次从道之本末角度统合了无为与有为,克服了先秦以来关于二者在君道实践上的形式割裂;另一方面,他对无为思想的扬弃——包括对治理实践意义上之“不为”论的批判及对“虚”之为“本”的坚持,这些对于西汉前期无为思想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后来,《淮南子》一书对“无为”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便深受此影响。如《淮南子》中《主术训》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9]661《诠言训》则以“无为”为“道之体”,“执后”为“道之容”,又以“无为制有为”为“术”。[9]1030这些与贾谊本人批判时人之“不动”“不为”,在《道术》中又以主体之“虚”呈现无为,提倡以静制动的后发制物原则,及虚术一体、无为与有为相统合的君道理论皆有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