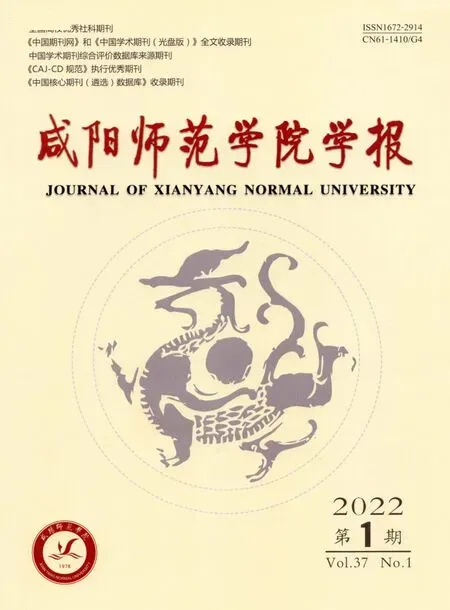易学与《史记》体例
赵继宁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创作《史记》是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1]3296说明了易学和《史记》的关联。可以说,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易学思维影响了《史记》的体例。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易学和《史记》体例的关系予以论述,并请教于大方之家。
一 “弥纶天地之道”与《史记》的百科全书性质
司马迁继承父志,完成了《史记》这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司马迁为何要把一部文史著作写成百科全书呢?这是因为易学“弥纶天地之道”的整体思维影响了司马迁。《系辞上传》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2]398-401
这段话是赞美《周易》的神奇,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而《周易》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即《周易》是以天地为准则,能够包含天地间的所有道理。“弥纶天地之道”或“《易》与天地准”,是一种天人整体易学思维,[3]7反映出《周易》是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思考的,所以《系辞传》反复强调《周易》之博大: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2]404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2]492
这种“弥纶天地之道”的易学整体思维,影响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方式和历史观,司马迁不光要研究“天人”联系,还要研究“古今”变化,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过古今之变”,如此,就决定了《史记》的百科全书性质。
首先,在“弥纶天地之道”的易学整体思维方式影响下,《史记》要“究天人之际”。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的实质就是探究“天命”和“王权更迭”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天官书》的结尾,司马迁再次提到“三五”,对此问题作了回答:
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適,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1]1351
可见,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主要手段就是《天官书》所载的星占学。《天官书》除少量属于天文科学的内容外,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为星占学内容。星占学是沟通“天人之际”的主要手段,通过占星可以达到预测“天命”的目的,即所谓“为天数者,必通三五”。这还不够,司马迁还要纵观古今历史,深入了解当前时事变化,考察其间的应验关系,这样才算真正掌握了天官这门学问,才能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除《天官书》记载的星占学可作为预测“天命”的手段外,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专门撰有《历书》《封禅书》《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集中探究“天命”。可见,司马迁要全面“究天人之际”,决定了《史记》的百科全书性质。
其次,在“弥纶天地之道”的易学整体思维方式影响下,《史记》要“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究并“贯通”古今事物和社会变化的规律。“变”是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只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规律。“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1]3292即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没有永恒存在的形体,所以才能洞悉万物的真情。“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1]1442是说事物发展到最兴盛时就会走向衰落,前一个时代发展到极限就会转变,时代风尚有时质朴无华,有时文采灿然,事物就是这样终而复始的变化。由于司马迁将《易》理“通变”哲学贯穿在《史记》中,因而他的“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实际上也体现了“弥纶天地之道”的易学整体观和系统观,具有超越表象世界而直透历史本质的内在深刻性。通观整部《史记》,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围绕三个层次全方位展开的:一是历史大势之变;二是国家兴亡之变;三是个人穷达之变。[4]36-38
在“弥纶天地之道”的易学整体思维影响下,《史记》五体完备的纪传体例,能够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从而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史记》。故唐刘知幾评论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5]35
二 “立人之道”与纪传体
《史记》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纪传体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撰述方法。《史记》人本位、为人作传的史学方法,成为后世修史遵循的制度。
《史记》以“人”为中心的撰述方法,是一种历史哲学思维的变革,标志着“人”取代“神”而成为历史的中心。对于历史的创造者到底是神还是人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人”是历史的主人,而把历史归结为“神”的创造,甚至认为人类本身也是上帝创造的,“天生烝民”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就是“神”的历史。到了西汉中期,司马迁继承了以《易传》为代表的先秦时代关于历史认识的成果,结合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创立了纪传体,从而在《史记》的史学创建中确立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之所以说《史记》创立的纪传体和《易传》有关联,是因为《易传》较早认识到“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重视人的作用。《说卦传》提出了“立人之道”的思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503意思是,从前圣人创作《周易》的时候,是要用它来顺合万物的性质和自然命运的变化规律,所以确立天的道理有阴与阳两方面,确立地的道理有柔与刚两方面,确立人的道理有仁与义两方面。《易传》明确提出要“立人之道”,即要确立天地人三才中“人”的地位,体现出了对“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重视。《系辞传》也强调“人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2]492
在“立人之道”思想的支配下,《周易》重视各层级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按照地位从高到低,将社会中的人划分为四个层级:
第一层级:圣人、天子(大君);
第二层级:王侯、臣子、公卿;
第三层级:君子、贤才;
第四层级:民。
在这些层级中,《周易》对第一层级的人,特别是“圣人”表现出特别的重视。这是因为,《周易》中的圣人,不光指《周易》的创制者,也代表古人心中贤明的君主,是和天子一样的天下管理者,如: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140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2]199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2]178
圣人能使天下人服从的原因就是重视教化,感化人心,且重视培养贤才。同时,圣人君子还能够身先士卒,具有仁德,重视生产和积聚财富,如: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2]355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2]449-450
除了重视圣人,《易传》对第三层级的人,特别是“君子”也十分重视,在《易传》中,“君子”一词常常被提起。这是因为,《周易》中的君子有着很高的道德素质,可以是辅佐天子的贤才,也可以是辅佐臣子公卿的士人。
在以《易传》“立人之道”思想为代表的先秦历史观念影响下,司马迁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创立了纪传体,从而确立了人本位,把人放在了历史的中心位置。《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都是人的传记;表是人谱;书是人事、人传。同时,受《易传》对人的层级分类的启发,《史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也将整个社会结构细分为五个层次:[6]84
第一层次:以天子帝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他们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这是本纪所记述的,与《易传》所分层级相同。
第二层次:侯王、臣子、贤圣等,这是世家所记述的,与《易传》所分层级相同。
第三层次:谋臣将相,他们中有的人在中央朝廷,有的人在诸侯王国,是第一二层次的帝王与国君的出谋划策者、政令执行者。《易传》没有此层级。
第四层次:士大夫,即《易传》所分的君子、贤才层级,他们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依附于上三个层次。其活动的多样性,丰富了社会历史的内容。
第五层次: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即《易传》所分的“民”这个层级,亦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农工商虞。
司马迁认为社会历史的形成和运转,上述五个层次的人都在起作用,五个层次形成了整个社会结构,反映了封建时代的基本社会状况。所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反映各阶层的人的历史活动,是《史记》纪传体最核心的价值所在,这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和国别体史书《国语》《战国策》所不具备的。《史记》通过纪传体来体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历史哲学,正是在《易传》“立人之道”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三 《易传》“子曰”与“太史公曰”
关于史书论赞的起源,刘知幾认为,论赞起源于《左传》“君子曰”,继而司马迁《史记》以“太史公曰”发论,置之篇末,概括一篇主旨,补充史料,而后这种体例被后世史学家所继承,“《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5]124
应该说,先秦典籍不光《左传》有“君子曰”,《国语》也有“君子曰”,如《国语》卷七《晋语一·史苏论骊姬必乱晋》篇末:“君子曰:‘知难本矣。’”[7]363这是《国语》通过“君子曰”来赞扬史苏洞察祸乱根源的能力。所以,刘知幾把《左传》定为史书论赞的唯一源头,似不妥当。《左传》成书于战国时代,和《左传》大概同时成书的《易传》中的“子曰”,也对《史记》“太史公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经笔者统计,出现于《易传》中的“子曰”共26条,其中《文言传》6 条,《系辞传》20 条。“子曰”之“子”指孔子,“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易传》一般通过“子曰”来引用孔子原话,对《易经》爻辞原文进行解释、阐发。《易传》中的“子曰”,按照格式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易经》爻辞原文在前,“子曰”在后。如: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有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2]439-440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大有》卦上九爻辞。其后以“子曰”引用孔子的话,先解释“祐”字之义,然后从“顺”“信”“尚贤”三方面来阐发该爻主旨。
第二类,“子曰”在前,《易经》爻辞原文在后。如: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2]469-471
先以“子曰”来展开议论,说明“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治国要旨,然后在结尾引用《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作为总结。
如果把《易传》“子曰”在文中的位置和作用,与《史记》“太史公曰”作一对照,可以看出,“太史公曰”是直接承继《易传》“子曰”而来的。就文中的位置而言,与《易传》“子曰”一样,“太史公曰”在文中也有前、后两种位置:绝大多数“太史公曰”居于每篇末尾,习惯称为“赞”,据统计有106 则;少部分“太史公曰”居于一篇之前,习惯称为“序”,据统计有23 则。[8]433
再从内容上看,《易传》一般先引用《易经》原文,然后以“子曰”进行议论阐发,议论往往在原文之义的基础上有更多拓展。如: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409-410
“鸣鹤在阴”等四句,为《中孚》卦九二爻辞,旨在说明人与人之间要真诚相处。“子曰”则在此义的基础上引申说明言行对于君子的重要性。《易传》“子曰”善于议论阐发的体例,影响了《史记》的“太史公曰”。就“太史公曰”的内容而言,除了于篇末对传主的一生功绩进行总结外,更多是像《易传》“子曰”一样发议论、定褒贬。如《高祖本纪赞》: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1]393-394
从字面来看,《高祖本纪赞》包含了历史循环论的色彩,但其重点在于总结夏、商、周、秦、汉的政治得失。周政“文”之敝,是说周朝等级森严的礼治使得官吏只注重形式,秦朝不思救敝,反而变本加厉依赖严刑酷法,所以二世灭亡;汉承秦之敝,把过去的弊病加以改变,顺民之俗,得以成功,这就是汉高祖的功绩。可见,《易传》“子曰”发议论、定褒贬的体式,极大地影响了《史记》“太史公曰”的形成,体现了司马迁的史识和“一家之言”。
四 结语
易学是司马迁构建其史学大厦的哲理基础,深刻影响了《史记》的体例,具体体现在:一是在“弥纶天地之道”的易学整体思维指导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过古今之变”,从而决定了《史记》的百科全书性质。二是在以《易传》“立人之道”思想为代表的先秦历史观念影响下,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从而在《史记》的史学创建中确立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三是通过《易传》“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的对照,说明“太史公曰”是承继《易传》“子曰”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