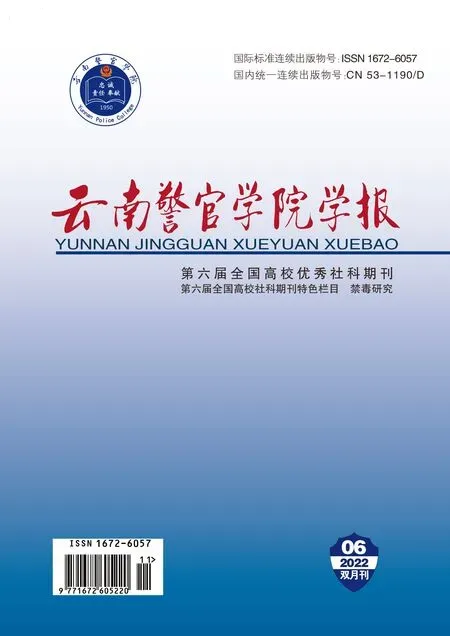中华法制文化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传承与发展
李超越
(云南省公安厅,云南·昆明 650223)
一、“礼”“刑”的起源和发展
“礼”“刑”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方式、工具,是中华民族早期规范化建设的体现,伴随着朝代更替不断演变、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
(一)“礼”的起源和发展
1.“礼”源于祭祀。农耕时代,中国古人通过祭天祈求上天眷顾,保佑风调雨顺、粮食增产、人民安康,祭祀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礼数、规矩、程序逐渐上升为统一性、标准性的操作规范,演变成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2.“礼”的演进。“礼”从早期祭祀所遵循的规矩、流程,通过演变至西周时,通过“周公制礼”,“礼”已经形成了“失礼入刑”,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机器作为保障,具有强制性、严厉性、惩罚性约束人行为的特点(即不成文的法律)。
3.“礼”的传承。“礼”逐渐演变为柔性的“法”,与道德的逐渐混同,随着封建皇权统治向民主共和制的时代更迭,完整地传承至今。“礼”文化作为中国的特殊文化的一部分,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内心中恪守的社会准则,从《清帝退位诏书》(1)“共和是人心所向、天命所归,亦予何忍因一姓之尊荣,佛兆民之好恶,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此不懿欤”。中可以发现“礼”无处不在,虽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但还是要保留皇权的最后尊严,反映了中国人做事的“体面”;在袁世凯就职誓词(2)“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委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拥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免其斯乏”。也体现着中国人依“礼”办事的“委婉”,反映出“礼”文化并没有随着封建统治的崩塌而消亡,而是随着民主共和制度的开启传承至今。
(二)“刑”的起源和发展
1.“刑”起于兵。古代行军打仗,为加强军队内部管理,防止队伍软弱涣散,提升队伍的执行力、战斗力,将“安营扎寨、攻城拔寨”中“三更做饭、四更整军、五更出发”等队伍管理、行军打仗的操作流程、工作规范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军法、军规,凡有违反者一律军法处置,督促军人对军法、军规心怀敬畏,不敢擅自违反。“大刑用甲兵”,武装镇压、军队统管,出兵打击也是以刑压制的一种体现。
2.征战之后的社会治理。“黄帝以兵定天下”。自古以来,部落间相互打仗,不断吞并,形成完整共同体,这是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起源的显著特点。夏启以来,我国各朝各代均有大一统管理华夏之地的夙愿,征战合并之后的管理,暂时由军队代管地方,军法代训地方,军警合一,军警不分,随着地方政权逐渐完善,管理规范也由军法逐渐演变为国家法律,军法处置也演变为了刑罚处置。
3.刑与法的关系。“刑”之“法也”。在古代中国,“刑”即是刚性的“法”,通常指违反秩序需要受到的惩罚、处罚手段。从夏、商、西周不成文的法(为符合统治者“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管理需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楚、郑、晋等国成文法的出现,国家治理已经从夏商周主观化和神权化发展到法制化和规范化。战国后期《法经》的出现,改刑为法,使单纯强调野蛮杀戮的刑开始向具有规范性质的法过渡,法制化由相对野蛮向相对文明发展。
二、“礼”“法”的分立和融合
中国人讲究国法、天理、人情相互统一。中华法制文明发展是“礼”治(德治)与“法”治从相互博弈到相互吸纳融合的过程。从单一的“礼”治,到单一的“法”治,再到“礼”“法”的结合,刚性的法与柔性的道德共建共治,是中华法制文化的重要特点。
(一)单一的“礼”治时期
夏商以来,“礼”涉及国家、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至西周,周天子在总结夏商崩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认为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需要由人民必须恪守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来实现。相信“礼”(人民心中恪守的准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治理手段,愈发崇尚“礼”治,认为朝代的更替是因为统治者“失德”(3)夏启有德建立了夏朝,夏桀无德,商汤有德,商纣无德,周文王周武王有德。、人民失“礼”、天神不满。“礼”治相当于往后朝代的“法”治,“礼”是积极的,防患于未然的,具有社会性、法律性和意志性,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出礼”则“入刑”,违反约定俗成的礼仪,将面临以刑处罚。
(二)单一的“法”治时期
1.早期的法治思想。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现象。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围绕“得民心、保民命、利民生”的实际,儒家(人性本善)、墨家(兼爱非攻)、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缘法而治)等学派都提出并形成了早期治理国家所遵循的思想主张。儒家荀子的两个弟子(商鞅、李斯),提出的“以法治国”“重典治乱”,形成早期“法家”以法治理国家的法治思想。战国后期,卫鞅携《法经》入秦后,得到秦孝公的赏识,迅速开展变法,使得地处雍州的小国快速发展壮大。“法”的到来,打破人们长期以来受礼压迫的束缚,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更是统治阶级统治、管理手段的迫切需要,“法家”到“法治”的思想为秦迅速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2.秦的专任法治。秦通过改革变法后,迅速崛起,一统华夏,认为万物皆可法治:一方面改法(4)法,字面解释平之如水;而律,指均布,反映的是法律的适用,要体现普遍性和统一性。为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要求刑无等级,法律适用必须做到普遍和统一,确保“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另一方面,废除儒学仁义,绝对地使用法律,法统管万物,形成专任法治现象。法多、法密、法严是秦律的主要特征,法律规定细到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5)有学者描述到,秦国的法律条文多的可以形容为“繁盛如秋荼,网密如凝脂”。。绝对专任法主义,过于强调万事皆可法治,要求无差别对待,小错大刑的重罚主义,完全抛开了儒学仁义,形成与道德对立的一种单一惩处手段,一定程度上也是秦仅过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刑罚威吓主义不仅不能完全规范人的行为,反而容易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例如:陈胜、吴广仅因“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就触犯了“失期,法当斩”的法定刑,客观上引发“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呼”的农民起义。
(三)不成文法与成文法
1.“礼”是不成文的法。自夏以来,统治者都不用成文法管理臣民,主张“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权威性和神秘性,依“礼”而治,以人们心中固有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起到约束作用,避免民众钻空子,人们才会心怀敬畏。失“礼”入“刑”行为,往往以统治阶级的标准予以认定、评判,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不成文法时期,“刑”是违反“礼”的规定之后的单纯惩处手段,“礼”是不成文的法,代表着约束;而“刑”则是违“礼”(违法)以后的惩罚手段,以刻人肌肤、断人肢体、摧毁人的生殖系统等(6)奴隶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墨”即刺面;“劓”即割鼻子;“刖”即砍右脚;“宫”不但针对男性,同时也针对女性,以“男子去其式,女子幽闭”为主要手段;“大辟”即死刑,采取腰斩、分尸等残忍手法。残忍手段进行惩罚,反映出原始、野蛮、血腥的特征。
2.成文法的出现。春秋后期,统治者意识到“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商周时期代表神权化统治的天罚神判已经遭到人民的不满和排斥,法制化统治迫在眉睫。郑(7)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晋(8)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铸刑鼎。、魏等国先后制定了成文法典,以满足统治者管理需要,实现百姓学法、遵法、用法,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素质。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9)分为盗、贼、囚、捕、杂、具6篇。,格式、体例已经初具现代法典样式(《具法》类似于现今法典的总则篇目)。成文法的出现,对中华法制文化的发展以及后续的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礼”“法”的融合
1.汉的引经注律。经过长期对秦战争、楚汉战争,刘邦显然意识到只有法治而没有德治是不行的。刘邦进入咸阳后,旋即退军灞上,提出“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以缓和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主张无为而治,试图让民众休养生息,储蓄国库,但也造成了地方势力的过于强大。武帝时期,为巩固中央集权,恢复“礼”治,以儒家思想为治国正统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引经注律、春秋决狱、秋冬行刑达到敬天、保民的目的,顺应天理,让百姓信服,“引经决狱”弥补了法律规定的局限、滞后等方面的不足,也使儒家思想迅速影响法律的实践活动,更促使了法律的儒家化。明确了自夏以来“礼”所规定的“三纲”“七出三不去”“亲亲得相首匿”等德道规范,虽然未将儒家精神修改到汉朝的《九章律》中,但引经注律的解释方法亦为后续“法律儒家化、儒家思想法律化”(10)汉朝也是“奴隶旧五刑”向“封建新五刑”过渡的关键时期,促使转变的关键人物是缇萦,缇萦上书要求替父受刑,向汉文帝上书称“残忍刑罚制度导致人死不能复生、肢体被砍了无法复长,刑罚执行完毕,想要重新回归社会,已无可能”。文帝尤为感慨,于是废除肉刑,经过文景之治,初步形成了“封建新五刑”,即“笞、仗、徒、流、死”,为隋唐时期正式确立起到推进作用。奠定了基础。
2.晋持续推动法律儒家化。司马家族本身就是儒学大士,在曹魏政权《新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泰始律》,并将《新律》中“八议”等道德规范吸纳,制定“准五服以制罪”,明确从高祖至玄孙间的道德规范。晋朝开始设律博士一职,注重法律的宣传讲解,儒学家张斐、杜预对《泰始律》进行注释,经国家审定后统一印发执行,更是将普法活动以及儒家思想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此后经过南朝、北朝的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摩擦与碰撞、实践与发展,南北各朝法制化进程呈现与时俱进、吐故纳新、兼容并蓄的繁荣景象,从《北魏律》《麟趾格》《大统式》到《北齐律》,进一步加快了法律儒家化的步伐,为隋唐法律儒家化的确立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3.隋唐的礼法融合。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年代,对推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后续朝代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也为日本《大宝律》、朝鲜《高丽律》、越南《鸿德律》等邻国法制发展提供了借鉴。不论是行政管理方面“三省六部制”,或是教育方面“科举制”的创建,隋在总结南北朝优良法制文化基础上制定了《开皇律》,为唐制定《武德律》提供了蓝本,将唐的法制文明推向了高峰。唐高宗时期颁行的《永徽律》《永徽律疏》是唐律发展到完备阶段的重要标志,为宋、元、明、清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蓝本。
4.清近代的立法。晚清(1840年之后),为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士大夫把视野投向西方世界,积极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体现了中西法律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是中国法制走向现代的重要发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尤其是日俄在我国领土上爆发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接替俄国继续侵占我国多地,非法攫取利益,慈禧太后等统治阶级愈发意识到宪政的重要性,想通过抓住君主立宪这根救命稻草,试图挽回清廷统治走向衰败。随后,派出徐世昌、绍英等人赴西方考察,试图通过效仿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破除列强侵略、山河破碎和民族起义不断的内忧外患。清近代立法,以成立法律修订馆为开端,在刑事、商事、婚姻继承等起草、施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时代进步。统治者片面的“西搬东套”,未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发展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也忽视了动荡的社会时局,晚清《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虽呈现君主立宪的初步雏形,但未取得好的实施推行效果。
三、中华法制文化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法制文明历经4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法制文化的独特性和系统性,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法制文化的完整性和典型性。与此同时,中华法制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国家法制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法制文化的独特影响力。如今,在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且具有鲜明特色的法治道路,将我国法治建设推向了新高度。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1.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领导人民用宪法、法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我国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优势所在,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传承中华优秀法制文化(“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守正创新,丰富法治实践,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推进中华法制文化继往开来、枝繁叶茂。
(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塑造文化自信之魂
1.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中华法制文化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传承与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11)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2.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提升学法用法守法水平。国无常强,亦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若则国弱。法善而不用,法亦虚器而已。即使法律制度再完美,如果无人使用和遵守,那法律制度就形同虚设,法治建设也只能是徒劳无果的。全体公民要充分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才能做到知行合一,跨越“知道”和“做到”的鸿沟,争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捍卫者与践行者,法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才能充分展现,法治治理成果才能反哺法治治理的现实需要。
(三)传承发扬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展现文化强国风采
1.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拥有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积淀了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没有中华文化,就没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既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还要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2.提升中华法治文化自信,传播中国法治故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我国法治建设在传承中国优秀法制文化基础上,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因此,应提升中华法治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故事,让世界了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伟大实践。
3.传承中华优秀法制文化,建设文化强国。中华优秀法制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因具备中华优秀法制文化的特征而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传承中华优秀法制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行稳致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