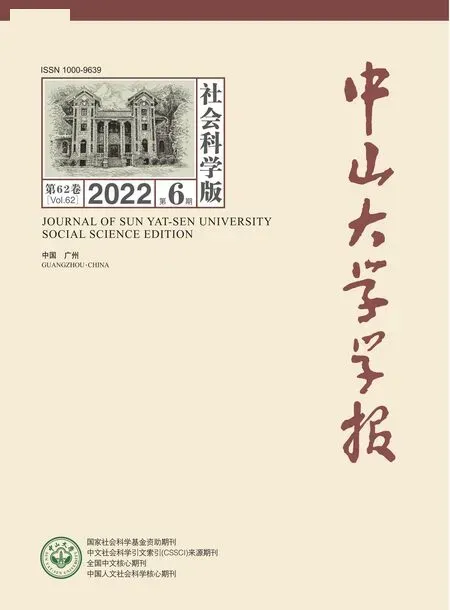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
——以严复、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的侨易背景与代际评价为中心
叶隽
如果说学术乃是高端的高深知识的表现,那么讨论知识转型则必须考虑到世俗知识、普通知识的层面。具体解释之,世俗知识是不必经过专门教育,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家庭、社会的耳口相传就能够传播并发生作用的知识。包括宗教知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世俗知识。普通知识是通过一般的教育过程来接受的知识,就是学校里可以传播的教育知识,既有一般的规训,也有普适性的常识,这是社会大众接受面最广的知识类型。高深知识指的是专门性的趋近于学术研究的专业知识。但每种知识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关。
中国的知识形式有其内在系统,譬如《汉书·艺文志》将中国古代的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或者我们也可进一步说,知识被分为六类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汉唐以来,随着佛教东渐,中国的知识系统和印度的知识系统有着一种相遇接轨的过程,最终以中国文化融化新知而获得凤凰涅槃为结局。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近五百年的相互触动、博弈和对垒过程,也仅仅是将一局大棋鏖战近乎中盘而已。到了清民之际或许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关键期,因为西方携其强势之坚船利炮取得了文化上的仿佛天然优势,其东来之势也,十分汹涌猛烈!这一进程今日仍在发展之中,我们都是“局中人”,这个过程有几个背景需要关注:其一,西方现代性的主导型地位毋庸置疑,但东方现代性有其自身的内部规律,虽始力不及,为所裹挟,但终必自省,归其本道;其二,西方内部也存在二元传统,这种二元性随着西方现代性劣势的凸显逐渐表现出来,即“秘索思”传统的一面,这正可与东方传统之主流有共谋的因子;其三,中国的儒道释多元,充分体现出东方文化的代表性,但还需进一步考察其容纳回(伊斯兰教)、耶(基督教)等的层次,如此则中西接触或可更具世界性的代表意义。
本文选择严复、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四位不同世代的精英人物,尝试对以世俗知识、普通知识、高深知识为线索的中国现代知识范式转型略做揭示。
一、“普通知识”的范式:从辜鸿铭的“非学者说”到严复的“知识译介”
虽然西方知识界乃至学术界对辜鸿铭(1857—1928)评价甚高,但更多地是出于一种思想史的意义而不是学术意义。辜鸿铭也有自知之述:“我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学者”,理由是“所谓学者,必须对他所研究的事物十分地精通。迄今为止,我虽然也做过不少研究,接触了不少事物,但在浩瀚的客观世界面前,我所得到的知识是非常浅薄的”①辜鸿铭:《什么是民主》,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311页。。但辜鸿铭所建立的知识范式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在中西对话的关系里来确定自己的位置。相比较传统的知识精英来说,他无疑有着明显优势,不仅是多年负笈欧洲,而且是幼年出国,其海外经验与同在1850年前后出生且留欧归来的那代学者如严复(1854—1921)、陈季同(1851—1905)、马建忠(1845—1900)等相比与众不同。清廷事后追认的排名中严复与他分列首席、次席,但两人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均迥异。严复留英之前已经是成年人,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幼年修习旧学,后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5年,系该校首届毕业生;1877年奉派赴英国留学,1879年归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严复是弱冠后出国,基本世界观都已形成;而辜鸿铭则不然,他虽然祖籍也是福建(同安县),但却早就随着家庭下了南洋,14岁从槟榔屿出发留英,其前期的中国知识近乎空白。
侨易效应的若干核心环节的基本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达致的一个整体张力会对个体的知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这其中主要可分为定量、变量两类因子,譬如说侨易主体(对象)所具有的生性、资本、接受能力等就是在侨易现象发生之前就已基本决定的,是属于不可更变的因素。辜鸿铭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在他14岁留英的时候②这是刘小源根据辜鸿铭的书信档案做出的考证,参见刘小源:《英租时期威海卫档案中的辜鸿铭书信》,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贰零壹贰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页。,不但其前知识几乎为空白,尤其对本土知识是相当陌生的;而且其人生观、世界观都处于待形成阶段,所以可塑性非常之强,因此英国教育阶段,不仅是爱丁堡大学的大学经验,尤其是苏格兰公学时期的基础教育,对其有着基本的规训与塑形作用。而严复则不同,他留英之际已是23岁,此前五年福州船政学堂学习经验,让他不但打下了良好的中学、西学基础,而且有助于其人生观基本成型。他自己回忆称:“不佞年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③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2页。当时福建船政学堂分前、后两堂,前者为制造学堂,以法国人长于制造舰船,乃以法为师,先学法文,故又名法国学堂;后者为驾驶学堂,以英国人海军强大,乃以英为师,先学英文,故又名英国学堂④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8页。。严复与英国的因缘可追溯至此。
侨出语境即侨出地的“前”影响同样可以左右个体知识结构。比如辜鸿铭个案中的单一殖民地背景——槟榔屿乃是大英帝国的东南亚城市。而严复一案则主要是海禁初开、变法图强的晚清时代的福建——作为沿海要地,其地方性特色鲜明。譬如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精英多出于福建,包括后来的林语堂也是福建人。闽粤一带易与南洋交通成为南洋空间的“北面边界”,像厦门大学等恐都可作此文化象征看①黄贤强认为,“南洋”是“有特殊历史含义的地理名词。如果以地理疆域而言,约等于今天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由于‘东南亚’这个地理名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因为盟军划分战区之便,才正式被启用,所以,当我们谈到战前东南亚华人时,更符合当时的称法应该是南洋华人”。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前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对厦门的意义,陈嘉庚讲得最清楚:“厦门虽居闽省南方,然与南洋关系密切,而南洋侨胞子弟多住厦门附近,以此而言,则厦门乃居适中地位,将来学生众多,大学地址必须广大,备以后扩充。”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5页。厦门确实在南方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一点也表现在西方人的相对集中上,参见李颖:《来华西方人与晚清厦门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里讲的南洋,当然是以马来群岛为中心的一种地理与文化双重认同的概念,如此则南中国的相当部分也被涵盖在内。。
侨入语境在个体知识结构形成中同样重要。比较辜鸿铭和严复二人,侨入语境大致相同而细部有差,比如对英文化适应方面,都要学习当地语言、适应学习环境、融入当地社会等。但两者留英期间,一在伦敦的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一在爱丁堡大学,教育传统不同。而且辜鸿铭在中学阶段就已经赴英,其在苏格兰公学的教育就已有绅士风格,“忆昔在苏格兰公学时,其校中游戏规则,凡合众力而搏一童者,虽是童在校中为至顽劣,胜之亦不武”②辜鸿铭:《读易草堂文集·义利辩》,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册,第228,228页。。这说明他幼时在苏格兰公学接受过教育而且颇受到影响,认为“然在英国游戏规则中,其义尚有存焉者”③辜鸿铭:《读易草堂文集·义利辩》,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册,第228,228页。,这种讲究公平、正义、平等、单打独斗的西方式的绅士教育对他影响深刻,直到多少年后,还将之举出作为例证。此期辜鸿铭虽然年纪幼小,但所接触到异邦风俗仍给他以深刻印象。严复的留英经历,首先主要是专科学院的训练,他抄录的学院考问课目包括:“一曰流凝二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④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光绪时期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5,406—407页。作为驻英公使且别具关怀的郭嵩焘,对留英船政生显然十分关心,于光绪四年正月一日接见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六名留学生,详细询问并记录下他们的读书作息日程:“每日六点钟分赴各馆听讲,礼拜一上午九点钟重学,十一点钟化学,下午三点钟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算学、格致学,下午画海道图。礼拜三上午重学,论德、法两国交战及俄、土交战事宜,下午无事。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无事。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授,受益尤多。或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⑤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光绪时期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5,406—407页。这段记录虽然体现出典型专门教育模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战史课;二是答疑课。当时距普法战争不过十年,俄土战争(1877—1878年)更是近在眼前,就已进入课堂,由此可见英国教育之注重实用的特征,其背后当然亦不无“功利思潮”的制约。答疑课则更显示出“自由教育”的模式来。诚如福州船政学堂的英籍总教习德勒塞(Tracey)所判断的那样:“以他们(指船政生)目下的学习情形,相信必能在英充分吸收高等教育的益处,而不需要太多的时间。”⑥转引自王家俭:《清末海军留英生的派遣及其影响(1876—1885)》,《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8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0页。英国教师看重的显然是英国大学教育的体制性优点,事实上,即便是专业化教育有着与传统教育背道而驰的一面,但也不乏在制度层面尽可能借鉴原有优点的方面。所以,即便严复就学于专门学院,也未必就对传统大学的体制性优点一无所获,这是我们在区分19世纪英国两种不同大学教育模式时应予以注意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郭嵩焘(1818—1891)在安排同时的方伯谦、刘步蟾等人“上水师船实习”的时候,独留严复一人继续在学院求学①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日记,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光绪时期上),第722页。严复的留英情况是很特殊的,即在同期留英军事生如方伯谦等上海军军舰实习的情况下,郭嵩焘又专门安排他在学院里延期学习一学期(半年)。为此郭曾于1878年8月3日专门致函英国海军大臣沙里斯百里(Sallsbury);8月14日,沙复函批准;8月19日,郭再复函致谢。故严复结束留学时间当在1879年6月。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778—789页。“General Correspondence”,F.O.17∕794(1878):108,转引自高增杰:《严复留英若干问题辨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有论者由此推导出严复一生思想大成的枢纽所在:“而严复由于继续留校,更进而推求西洋致富强的学问,接触到西洋重要思想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孟德斯鸠(Mountesquieu)、卢梭(Rousseau)、边沁(Bentham)、穆勒(John Mill)、达尔文(Charles Darwin)、赫胥黎(Thomas Huxley)、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著作。再以典雅深思之笔,译介给国人,终于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位启蒙大师。”②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18页。另一种表述,是严复“开始接触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等等一些使得英国思想发展进入一个‘转型时代’的维多利亚王朝时代思想家的思想”。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刘桂生等编:《严复思想新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关于这些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状况,参见Houghton,Walter E.: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187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pp.1-4。是否大师,暂不作论,但严复在留英期间,另辟蹊径,进入英国乃至西方的人文思想世界,则是不争之事实,其后由于严译名著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厥功甚伟亦所公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严复虽少有大志,亦具通识,但其启蒙思想真正成型却要在1890年代之后。从严复留英归来,到甲午战争之爆发,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严复这样谈及此段思想大进的直接诱因与思想资源:“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但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③严复:《与长子严璩书》(1894年),《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也就是说精神质变的关键点形成,不仅是因为简单的地理位移或留学经历就可以获得,而且也需要关注到多重侨易的可能性。实际上物质位移至少包括若干层面,一是最明显的地理位移;二是精神位移,即在由知识地图的虚拟文化空间的虚拟位移;三是时间位移,即在纵向的时间变动中其实也构成一种物质位移和精神质变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区分三种“位移空间”,即地理空间、虚拟空间、时像空间。有时候侨易是单纯的一种含义的位移,譬如地理位移最清晰,但往往是包含多种含义,譬如时像空间是时刻存在的,时像位移也是时时存在的,如果以精确到分秒来计算的话,一般来说时像位移的计量程度应该是大时间单位,譬如说年月。而虚拟空间的位移的重要性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我们的精神层面是一个不能简单地以“精确度”来衡量的尺度。
在严复这一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精神质变的发生有着多重刺激和影响。其中的变量因素尤其应当注意,其意则指可能由于客观环境的改变,而形成的不同的对侨易主体产生影响、刺激与生发的因素,所以留英时代固然是“种瓜得豆”,本为军事生而成就思想家的“种子”;归国之后的经历同样让其不断地“反刍自省”,甚至最终完成了思想上的“凤凰涅槃”,若非官场的不得意,恐怕也难得其译介事业的一鸣惊人。所以也需要注意侨易条件的不同要素,譬如对侨易对象的推拉力影响、返侨地的后制约因素、对大语境的同生共息能力、生性敏感度等,总之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侨易现象的形成,不可能仅是单向度的产物,而必然是在立体结构与交叉系统中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也自然会在随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得到相关的呼应,成为历史链条中难以回避的一环。
二、王国维评辜鸿铭、严复及其对高深知识的转向
对于陈季同、严复、辜鸿铭等一批上代人,王国维有什么看法?他对严复这样批评:“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入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有,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①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7页。可见对于严复这样一个知识史和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王国维不但没有回避,而且很有独到之见,甚至一针见血。那么对辜鸿铭如何?王国维曾专门撰文《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对辜鸿铭引为得意的《中庸》英译颇有发覆批评。首先,王国维肯定辜鸿铭的眼光,认为《中庸》虽“不独如《系辞》等传表儒家古代之哲学,亦古今儒家哲学之渊源也”,所以“辜氏之先译此书,亦可谓知务者矣”②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册,第125,128,126—128,135页。。虽然肯定,但却并不意味着不挑刺,旋即挑出两项“大病”,十条“以己意释经之小误”③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册,第125,128,126—128,135页。,这里仅挑一个例子略作申说。王国维说:
“中庸”虽为一种之哲学,虽视诚为宇宙人生之根本,然与西洋近世之哲学,固不相同。子思所谓诚,固非如裴希脱(Fichte)之“Ego”、解林(Schelling)之“Absolut”、海格尔(Hegel)之“Idea”、叔本华(Schopenhaue)之“Will”、哈德曼(Hartmann)之“Unconsious”也。其于思索,未必悉皆精密,而其议论,亦未必尽有界限。如执近世之哲学,以述古人之说谓弥缝古人之说则可,谓之忠于古人则恐未也……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如辜氏……之译“中”为“Our true self”,和为“Moral order”,其最著者也。余如以“性”之为Law of our being,以“道”为Moral law,亦出于求统一之弊。以吾人观之,则“道”与其谓之“Moral law”,宁谓之“Moral order”。至“性”之为“Law of our being”……不如译为“Essence of our being”or“Our true nature”之妥也……《中庸》之第一句,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外国语中之无我国“天”字之相当字,与我国语中之无“God”之相当字无以异……里雅各之译“中”为“Mean”,固无以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中”,今辜氏译“中”为“Our true self”,又何以解“君子而时中”之“中”乎!吾宁以里雅各氏之译“中”为“Mean”,犹得《中庸》一部之真意者也。④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册,第125,128,126—128,135页。
辜鸿铭西学知识虽然广博,但面对王国维,则若要说具有压倒优势恐怕也是绝难其必也。作为其貌虽旧、其学维新的王国维,所论却是处处切中要害,其对“中”的英译追问,可以说让辜鸿铭很难抵挡,后者是过于“以己注人”了。面对此类经典涉及到的共有精神财富,理应谨慎。而此处对理雅各的肯定,则尤其值得重视。其不若旁人一般去批评理氏英译之笨拙冗长,而视之为保存经典原意的一种可能途径。
那么,相比较这里的高手较技,我们要追问的当然不仅是临场发挥的“高下短长”,也还有此类人文学养相比拼的“漫长过程”。王国维日后虽然似乎颇有悔意,但却并非就文章内容而言:“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⑤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册,第125,128,126—128,135页。二十年后再回首,有些恍然若梦之感,但青年意气的王国维的考论,其实并非仅是“狂躁气矜”而已,而是自有其学理根源在。我们要拷问的则是,王国维的知识结构如何,形成过程又如何?何以能如此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辜鸿铭、严复、陈季同这代人物在中国知识界的筚路蓝缕贡献甚大,譬如辜鸿铭的英文写作、陈季同的法文写作,都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实现了文化的双向沟通功能。虽然更早的一代,譬如容闳、王韬、杨文会等已经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历程,但毕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容闳虽然已经是“留美第一人”,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但他的睁眼看世界,其主要成就也就在于派遣“留美幼童”,王韬虽与理雅各合作颇多,且曾到英国,却不通外文;杨文会(1837—1911)亦然,他曾随曾纪泽(1839—1890)、刘芝田(1827—1892)等两度出使英伦,也是不通英文的。但陈季同、严复、辜鸿铭他们相比较上代人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知识建构意识,而且都精通外语,有长期入外国大学的就读经验,亲身体验到欧洲学术的发达。再往下一代,到了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这代人就更不一样了,他们的求知意识更加自觉。蔡元培尤其意义不凡,其留德之举是有主体意识而非纯粹受委派。像梁启超、王国维也都对德国文化有所意识,但基本上以留日为主,而这种留日,更近乎旅日,因为主要不是正规地入日本大学,而带有培训留居自学性质;而从代际传递上来说,辜鸿铭、严复都多少意识到德国学术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辜鸿铭对歌德、俾斯麦的双向推崇,表现出他的知识广度和识力之深。
大致说来,王国维要晚上一代了(1870年前后出生)①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近年颇具新意者,如罗钢教授认为“意境说”乃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罗钢:《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彭玉平教授则提出“学缘”概念,对进一步探讨王国维及其同代人的知识世界颇有启发性。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他的侨易经验是有些特殊的。王国维的侨易过程中,一个核心变化是在对高深知识的自觉转向,除了经由罗振玉(1866—1940)这条线索的“入门”之外,主要与其个体的学术求知和向学自觉有关。也就是说,地理侨易有时可能仅是一种触动力和机缘,精神侨易才是根本。对这一代人来说,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都可谓一代之雄,各有其惊人之贡献,但如果就学术而论,则舍王国维之外,再不作二人之选,恐怕也是事实。
王国维的侨易经验可分为两段,一则入沪,二则留日。1898年他由父亲王乃誉陪送,赴沪求学,入《时务报》馆;随即参加东文学社(罗振玉创办)。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得以留日。1900年出发留日,12月赴东京物理学校求学,因病于1911年即返沪。但这段时间不长,实际上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即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1916年归国。这两段经历合在一处,其留日大约在五年左右。其中就在京都期间,“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②王国维:《丙辰日记》,房鑫亮编:《王国维书信日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735页。。王国维的求学虽然有海外经验,但是单向度的,既比不上辜鸿铭的英伦为点、跨越英法德,也不能与陈寅恪的周游世界相比。但作为留日一代的代表人物,王国维给我们展现出一个可以通过虚拟知识世界的精神漫游所能达到的高度。而通过日本而了解德国学术,或许是王国维那代人的优长,他是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的,且不说他对叔本华哲学的深度接受③关于王国维对叔本华思想的接受,参见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鲁迅也一样受到德国思想的影响,参见[日]伊藤虎丸:《鲁迅的早期尼采观与明治文学》,王琢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01—225页。,且看其对康德的推崇:“笃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赤日中天,烛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喑。谷可如陵,山可为薮,万岁千秋,公名不朽。”④王国维:《康德像赞》,《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1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22页。总体来说,留日学人通过留学日本而对德国文化的亲近乃至推崇,是当时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当时,“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⑤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535页。。就中国留日学人来看,因留日而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不乏其人。
三、陈寅恪论王国维及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架构
作为后来者的陈寅恪代表了高深知识在中国语境里的制度化确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当之无愧的典型和精英巨子。正是以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盖棺论定,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精神的心魄之所在:“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①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6页。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肯定,不仅是一种精神和道义的同气相应,同时也意味着在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上的高度认同。这一点在陈寅恪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表现得更为清晰: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②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248页。
可以说,在高深知识的层面上,陈寅恪给予王国维以高度评价,并以“大师巨子”相称誉,更赋予其极为厚重的载道者的角色,就不仅是简单的友朋交谊和悲惋痛惜的关系了。因为在中国学术史上,正是以陈寅恪的出现为标志,高深知识的崇高意义得到充分和全面的肯定。在经历上,陈寅恪类似辜鸿铭,只不过更加丰富,相比较共享的留德、留法背景,陈寅恪还曾留学日、美、瑞士;虽然没有留英经验,但其两度留德,对德国学术更有一种体贴入微的亲切认识。陈寅恪的优长之处,更在其国学修养和家世熏陶,这远非辜鸿铭可比;即便较之王国维也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他对王国维的态度却是高度认同,这固然与彼此在清华园中的深厚交谊有关,可如果就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史和大历史框架来看,也是就如何选择和确立传统标示典范。
对于陈寅恪这代人来说,更是英杰辈出,譬如赵元任、胡适、汤用彤、冯友兰等都是一代大家,即便是本土学者如陈垣、钱穆等,也是气象博大、卓然自立。而陈寅恪之所以在群星璀璨之中仍能耀眼夺目、众流皆伏,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最核心的或有如下几条:第一,道统意识极其明确,其治学之术明显融化西学,但载道之意更重于单纯的兴趣和求知,所以“吾侪所学关天意”并非简单的亮明志向,所以也才有对“神州士夫羞欲死”的锥心之痛,其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③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5页。,自有其立论道理,在他这里“学”“道”是相通的。第二,其游学世界固然是勇于求知、胸有成竹,妙处在更能于精神境界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以善能将西学精神之长化为己有,进行真正的创造性转化。故此他对世界学术和世界文化能有一种通达超越之认知,从而在其学术思想上初步确立了东方现代性意识之萌芽,通过具体治学方式的选择,譬如梵学选择、平章华梵和背后指向的东方意识,发展出一条在学论学的普适性关怀,这是尤其难得的。第三,有一种以生命践履理念的坚毅担当和使命感。抗战时代,困居沦陷地香港而不得不面对侵略者的威胁利诱:“回忆前在绝岛,仓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①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4页。盲目衰翁,漂泊海上,遥想故国,又是何等的坚贞守节,真可当“海上苏武”也。而将及晚年,陈寅恪又不得不重新面对新的考验,即不丧学人志节,所谓“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②吴宓1961年8月30日日记,载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60页。。这不仅表现在撰于1950年代的《给科学院的答复》中的立场③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02页。,而且尤其体现在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实践之中。悲哉,岂仅是膑足之痛、盲目之惨!身体之病痛,生存之危机,精神之煎熬,往往三位一体。正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之中,寅恪先生为我们书写出一个大写的“学人”形象。这或许也正是他敢于标示自家伦理标准的原因:为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为文“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可有裨“治道学术”④陈寅恪:《赠蒋秉南序》,《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2页。。
我曾借歌德撰《少年维特之烦恼》意,提出“文化假殉”的概念。所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此语揭示出程婴、杵臼和月照、西乡各有其归所之意义。而仁圣之殉,则更超越政治国家的俗谛之义!在我看来,作为原生代学人的王国维,与作为第一代学者代表的陈寅恪,可谓更高境界的月照、西乡。王国维不死,道统不得以最英华人物之殉;陈寅恪不生,则中国道统又如何能保存其最后之风骨?王国维死,陈寅恪生。貌似一种偶然的对待世事生命的态度和选择,然而气质似乎又孕育着时代进程与精神选择的不逆之途。如谓不信,1950年代之后陈寅恪豹隐岭南的艰难过程,或许更有可以发覆之处,诚如吴宓1961年时所记录的陈氏之言:“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尊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1961年8月30日日记)⑤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第160页。这可以见到一个坚守学术伦理维度的学人,他内心的原则立定有着怎样的精神支撑之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发端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名言,也就有了远超出区区一碑之文的深远含义!
这几点通过对王国维之死的辨析阐释得到充分展现,既明道统,更确立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架构和精神基础,乃开辟出中国现代学术的辉煌气象,而这一轨迹,又被陈寅恪自身以其生命史而延续之,虽历经磨难、生死以之而执守不变,乃产生一种极为撼动人心的力量。现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也借此高深学术与崇高精神的结合,而有了一种悲沉契阔的壮美画卷!
四、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兼论知识类型、立体系统与制度依托
本文个案对应现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过程,其横向语境也就是知识接触的文化体系交流关系,纵向语境即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横纵两方面来看,“高深知识”都是呼之欲出的,而且有着制度层面的基础。
辜鸿铭基本上可定位在普通知识层面,即是主要立足于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而非追求高深学理为标的的一种知识兴趣。即他本人并非学者式的探究,他是借助一个公共舆论空间来发声,产生社会影响力,当然其中也有文化因子和某种创造因素,但绝不是学术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创造。或者总体来说,知识创造的功能是不明显的。基本不属于高深知识的层次,亦或介于普通知识—高深知识之间的那个部分。
王国维虽在留学经验上不如辜鸿铭,但对现代学术的认同度和理解力、创造力,都远超于辜氏。比较两者的前期职业经历:辜鸿铭长期在张之洞幕府任职,是一个具有文人性质的行政官僚,虽然是幕宾性质的,但“官”的成分还是居多。而王国维则不然,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学者,虽然起步很卑微,但自得到罗振玉的帮助之后,就如虎添翼,通过西学资源的自由汲取,达到了一种相当自如的学术境界,乃能慨然陈词:“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①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02页。
陈寅恪则是个典型的留学生,虽然没有获得任何学位,但确是在欧美大学里入学听课,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对王国维的知识与学术世界和境界,有充分的理解和共鸣,同时又不仅于此,在制度层面有着更深刻的维系和关联。所以,他会在清华大学建立20周年之际撰文《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开篇即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②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明确地将大学职责和学术独立联系起来。而对大学职责和意义的关注乃至凸显,更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现代大学和学术制度所孕育的精灵儿。就现代学术制度上的开创范式而言,王国维的意义其实要弱于陈寅恪,但之所以王国维会在现代学术史上享有甚为崇高的地位,与陈寅恪借王国维之死确立中国现代学术之精神大有关系,那几篇大手笔的碑铭、书序、挽词,意义极为重大深远。
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双簧绝唱”真可谓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绝响,以二者品格之高洁、学行之纯粹,道统承担意识之坚、学问追求意识之深,而又清华相遇、忘年而交,真是难得之极。这一点在辜鸿铭那个时代基本上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代大学和学术制度都未建立。譬如北大、清华都是在1910至1920年代确立了现代大学制度,这几位也都与这种制度密切相关。但不同的是,辜鸿铭、王国维虽然分别在北大英文系、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职,但却没有发生非常密切的关联,或者说他们基本上没有融入到这个制度中去,惟有陈寅恪与这个现代学术制度是生命与共的。我们看他当时在清华任教时参与校务的积极态度,看他大力支持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的那种认真态度,就可以意识到他作为纯粹学院知识分子的纯正品格。他从客观上是认同现代的学术共同体的,也是愿意为之而付出努力的。所以我们在考察知识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考察制度因素,这是一个基本的分野,有无此制度和语境之孕育,对于学人来说其意义大不一样。
结语
个体侨易的层次借此融入到一个更高的范式侨易的层次,也就是说,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的侨易过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某个学人的个性经验,如果我们在现代中国的知识范式转型过程中来考察,那么,“高深知识”追求目标的出现,是具有共性追求的。一方面,我们意识到,就现代中国知识转型而言,有着一个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重要转折期。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它也仅是全局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即便就高深知识而言,它更接近象牙塔内,所谓“为学术而学术”可能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普适性的无用之用。其轨迹链发展也有多重可能,譬如此处的人文知识之外,还有科学知识的方向,譬如竺可桢、任鸿隽等一代科学人的出现标示的是与人文不同的路径。
可即便强调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意义,我们也会根据侨易学的原理追究其“前世今生”,考察其交叉系统和立体结构,如此即便“普通知识”之链也并非就此而绝。往前追溯,譬如曾国藩—张之洞的传统精英领袖型的知识链延续;有海外经验的如容闳、王韬、杨文会等人的系谱;周馥、王树枬、孙宝瑄等本土精英的西学认知和兴趣;乃至底层精英如刘大鹏的知识地图,都可以让我们看到知识转型过程的复杂面相。这基本上也是一种普通知识层面的东西,当然可以说是较为高等的,接近“高深知识”的那块普通知识。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这个面相,说明的是现代性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环节,就是“知识生产”成为一种为资本规训和驱动的经济形式①所谓“知识生产”,即“无论什么人的(或人引起的)任何一种活动,其目的是在一个人(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的脑子中产生、改变或肯定一种有意义的知觉、知晓、认知或意识到的任何事物”。[美]弗里茨·马克卢普著,孙耀君译:《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另外,则需考虑相关联的文化下延问题。后者更着重在文明结构三层次的器物、制度、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关系,而知识形式的范式变型则让我们看到这三层次之间资本、权力、知识之间的必然关系。如果说文化下延更多是自上而下的高端下沉,那么知识生产则更多体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低端上侵,究竟是资本驱动知识,还是知识影响社会,这似乎又进入到一个两难悖论之中。随着现代大学和学术制度的建立,“高深知识”的范式意义逐步建立起来。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一流精英对于现代学术理念的自觉服膺,以及对自由与自律的学术空间构建的诉求,是最好的对于“高深知识”范式建构的例证。
我们看这三位日后对待“学术社会”尤其是“制度依托”的态度和选择就可以更清楚些,辜鸿铭、王国维虽然进入了现代大学制度,但基本上并不太善于运用,辜氏因其老派和思维定式,而王氏则因自沉昆明湖而打断了这一进程,但他去清华主要是因了末代皇帝的圣旨;必须强调的是,陈寅恪的大成就也有赖于对现代大学和学术制度优势的运用,没有这种制度作为依托和基础,在现代商业资本社会中学者其实很难依靠单纯的“普通知识”生存,同时又保证“高深知识”的生产力。
对于资本的本质操控,是“高深知识”共同体需要更具自觉性和联合力去面对的。在个体层面的文化间转移、在共同体层面的联合之外,在文化体层面现代中国所要面临的还有文化体的转型必由之路问题,以知识范式为引,以整体性框架为依托,或为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