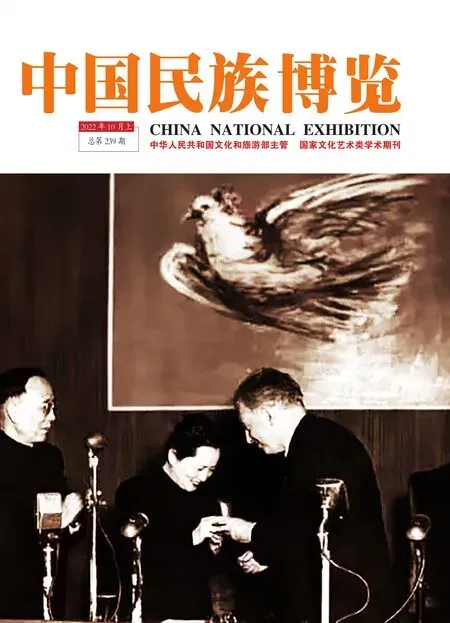女巫使人变兽题材的发展及女巫形象研究
王心怡
(湖南省湘潭大学兴湘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在中国唐代的传奇小说《河东记》中,作者薛渔思讲述了《板桥三娘子》这一故事,故事的内容主要是写唐代元和年间,一位叫赵季和的旅客在前往洛阳拜会长辈的途中,留宿在了汴州一位叫作三娘子经营的板桥店中,赵季和在这家板桥店寄宿的晚上,亲眼目睹了三娘子用奇怪的法术把面粉制作成烧饼,并把吃了烧饼的旅客全部变成驴的故事。
这个故事内容新奇,想象颇为大胆,塑造了一个可以将人变成驴的“女巫”形象,而这一故事经过诸多学者考证,并非薛渔思原创,而是有其外国源流。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就曾考证唐代“人变驴”传奇《板桥三娘子》最早源出于西方《奥德赛》中女巫基尔克使人变猪的故事,并认为其存在近东地方的民间故事来源,但并未实指。后来刘守华教授进一步考证,认为《板桥三娘子》故事的直接源头为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这一结论也在学术界被广泛认可。
关于这一故事题材,我国著名的民间故事分类学家丁乃通先生将这其列为449A【旅客变驴】型。在美国著名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存在G263【女巫施魔法或变形】,以及D100-199【将人变成动物】两类母题,而“女巫使人变兽”题材,则为两种母题情节的组合。
关于这一题材,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关注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主要聚焦在这一题材流变的考证及异同的比较上,也有的与其他相同或相似题材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并用不同的文学理论或文化理论进行解读阐释。但是鲜少有人关注这一题材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形象——“女巫”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为何会扮演此角色?本文通过借鉴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女性主义观点,结合《奥德赛》《一千零一夜》《板桥三娘子》中的相关故事情节,旨在研究“女巫使人变兽”这一题材的发展特点及女巫形象变化。
一、女性的“他者”地位
从古希腊最早的伟大作品《荷马史诗》中,我们就已在文学中窥见了男权社会的面貌,在诸神云集的奥林匹斯,宙斯作为伟大的众神首领,是一位男性神,他创造的象征着人间一切灾祸的潘多拉,是一位女性;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作为耶和华创造的最早人类祖先,夏娃只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的女人,是她诱惑了亚当偷吃禁果,从此被逐出伊甸园。
在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社会中,女性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与男性公平相对的主体。在波伏娃《第二性》的序中曾如此注释女性的“他者”地位:“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做一个自主的存在……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①”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而女性“作为整体的人,作为一种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的,人们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她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②”。
从波伏娃的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个相对于男性而确立的“第二性”,她是被动的,是次要的,是内在的,是客体的。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将士们在结束了特洛伊之战的回家途中,被美发的女巫基尔克诱惑,吃下了混有害人药物的食物被变成了猪,但最终奥德修斯凭借神的帮助和自己的勇武,成功地战胜了基尔克,解救了同伴;在《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中,巴西睦太子沉迷于与拉卜女王的欢乐,因为窥见了女王变成一只鸟与曾经爱慕的奴仆交合而差点被女王变成驴,但因为有法术更加强大的老者阿卜杜拉的帮助,巴西睦太子反将拉卜女王变成了驴;在《板桥三娘子》中,三娘子作为女巫虽有法术可将前来住宿的旅客变形,却还是被赵季和识破了法术,用掉包的方式被反变成驴。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纵使故事中的女巫有着令人恐惧的使人变兽的魔法,但最终却还是被男人们战胜,在她们身上发生的失败,似乎就象征着整个女性群体为自身主体地位而与男性对抗的失败,她们作为男性的配角,始终没有逃过作为“第二性”的“他者”地位。
二、女巫形象的特点及共同点
剑桥大学古典学者安娜丽莎曾这样谈及《奥德赛》中的女巫基尔克:“她是男性白日梦的一种:危险,性感,全身散发着异国情调,没事就朱唇半启,整日狩望着海平线上过往的船只。③”这一段话,就清晰地概括了一系列女巫使人变兽故事中女人的总特点以及男性对这些女巫的总态度——美丽但也危险。
归纳三个故事中的共同点,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故事中的女巫都具有让男人难以抵御的美貌,在《奥德赛》中,美发的基尔克既是一个女巫,也是一位女神,故事中虽未直接描写她的美貌,但通过侧面写奥德修斯的将士们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却依旧被基尔克的歌声和美貌吸引,就足以证明基尔克那让男人难以抗拒的美。包括后来奥德修斯已经救下了自己的将士并征服了基尔克之后,他的手下欧律洛科斯劝他不要被女巫迷惑继续赶路时,奥德修斯却被基尔克的美貌和华丽享乐的宫殿迷昏了头,竟思忖的是“要不要立即从大腿侧旁抽出利剑,砍下他的脑袋④”。在《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中,巴西睦太子在被警告过女王拉卜是会让年轻人变成动物的可怕魔女之后,却依旧因为拉卜的美丽而流连忘返于拉卜的宫殿,一住就是几个月,这都无疑表现了在这些女人身上难以抵御的美丽。
在这些女巫或女神身上的美貌虽然对男性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但故事中的男性对她们的态度却是矛盾的——他们既爱这美貌,也怕这美貌。这些故事中并非全部都是描写男性们被女巫的美貌迷惑而陷入情欲的陷阱,相反,男性们在一度的沉迷之后还是会恢复理智与智慧,意识到“美丽背后的危险”——男性们无法理解的魔力。于是他们抵抗这种魔力,并在尝试征服的过程中歪曲和妖魔化这种魔力,更多体现的是女人因美貌而具有“红颜祸水”的特点,以及暗示女巫的种种未知是男性在成长和超越过程中必须克服的恐惧与欲望。
除了这一女巫形象的总特点以外,三个故事中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共通之处。
首先,故事中的男性角色都是在冒险过程中遇见了一直固居于一隅的女巫。奥德修斯是在回家的冒险航行中来到了基尔克居住的艾艾埃海岛,巴西睦太子是在返回国家的过程中因为船只被海浪吹翻,在九死一生之时漂流到了女王拉卜的国土,赵季和也是在去东都洛阳拜会一位长辈的旅途中寄宿到了三娘子的旅店。这些男性无论是漂泊还是旅行,都带有着冒险的意味,在波伏娃看来,男性的地位之所以自古以来便高于女性,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他的活动往往是危险的⑤”。他们通过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对自然的探索和开拓,不断通过存在来超越生命的行为,正是他们作为主体的“超越性”体现。
而对比故事中的女巫形象,她们永远是静态、封闭地生活于自己的领地之内,从未主动地施予男性们变兽的魔法,只是通过男人好色、贪婪等弱点来达到目的和确立自己的地位,她们不是从自己的积极价值中去超越,而是被动地等待,这就体现了女性缺乏超越性的“内在性”特点。再结合人类历史的事实,原始社会往往是男性在外打猎开辟,而女性则主要负责生育和耕种,男性所冒的危险相较于女性明显要大得多,他们的价值和地位也自然更为凸显。
其次,从故事的结局中,我们都能看出,最后男性战胜了拥有魔力的女性,甚至反利用女性的魔力将其变成了驴。这个过程中,往往都有一位“先知”的指引,《奥德赛》中给予奥德修斯不会被变兽草药的是神使赫尔墨斯,《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中帮助巴西睦太子降服拉卜女王的是比拉卜更加通晓魔法的阿卜杜拉,甚至在《板桥三娘子》中,赵季和已经把三娘子变为驴之后,在行路的过程中将三娘子解救变回人形的也是一位先知老人。这些扮演“征服者”“解救者”形象的都是男性,女性甚至已经失去了自我解救的能力,只能被动地等待着被征服之后男性的解救,这些结局,都深深地渗透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思想。
除此之外,当故事中的男性在与女巫的对抗之中占上风之后,都极尽描写了女巫们做小伏低,服侍他们的情状,这也体现了男性潜意识里对女性征服和超越的欲望,哪怕面对的是拥有强大魔力的女神或者女巫。
三、女巫使人变兽情节的发展特点及产生原因
在经过了上述对“女巫使人变兽”这一题材中的特点和共同点总结之后,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题材流变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变化脉络,即从《奥德赛》到《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再到《板桥三娘子》所体现的就是女性被去神化,不断发展内在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形象在不断地向内在性发展,从最开始具有女神的神圣性,到变成统治一个国家的女妖魔,再到最终仅仅拥有魔法的旅店女老板;从奥德修斯被神使赫尔墨斯拯救,到巴西睦太子被先知老人帮助,再到赵季和自己识破女巫的诡计。女性的内在性越来越明显,反抗能力和神秘性也越来越低,而男性的超越性却不断变强。这一横跨十几个世纪的流变,正象征着女性地位不断变低变内在的历史事实。
波伏娃曾如此说:“一切神话都牵涉到一个主体,它把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投向超越的天空。⑥”其中,“主体”就是作为第一性的男性,而这种基于希望和恐惧的“超越”就创造了“女巫使人变兽”这一题材的故事。
在探索这一题材故事如何产生之前,需要先厘清故事中女巫和女神的定义与特点。首先无论是女巫还是女神,她们都是有“神力”的,这种“神力”源自于男性对女性双重性的认识,一方面,在最早的原始农耕时期,因为男性对于女性生育的不解,他们认为孩子是从某些飘浮于自然之中的祖先亡灵降落在女人体内而生的,又由于农耕迫切的劳动力需要,决定着生命延续的女人就有着晦暗不明的能力,土地和自然似乎就是女人,女人能“把祖先的亡灵召唤到自己怀里,也能让播种过的田野迸发出果实和麦穗⑦”,在这一方面,男性就把女人视为有着一定魔力和威胁的“他者”;另一方面,因为女人相对男性生理和历史原因所注定的内在性,让女人失去了主动创造的超越,因而也就只是“女性”。这种他者、女性的双重性也就侧面体现了故事中男性对女巫们既想征服,又有所惧怕的态度。
关于三个故事中的女性形象从女神到女巫的一个退化过程,主要是随着男性对女性“魔力”的逐渐理解而发生变化的。“当一个行动不是来自原动力,而是来自被动性时,它就是有魔力的。⑧”女巫和女神的神力就是来自男性对于被动性也能产生创造的不解。因为女性的“他者性”,女性的神秘被男性所崇拜,这时女性就被尊为女神;而当男性为了让社会战胜自然,让理智战胜生命时,便更重视女性的“内在性”,把似乎拥有神秘力量的女人视为女巫。从《奥德赛》到《白弟鲁·巴西腔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再到《板桥三娘子》,随着男性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男性逐渐破解了女性的神秘力量,不再惧怕其“他者性”,那么故事中的女巫也就逐渐被去神化,实现了从女神基尔克到女巫板桥三娘子的转变。
总的来说,女神是以所有成员的名义,为共同体的利益,与神灵和法律取得一致,控制和引导她所驾驭的力量;而女巫在社会之外活动,按照自己的情感,违背神和法律。⑨这一点在故事对三个女性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男性对她们态度的差异与变化,在《奥德赛》中的基尔克她身为一位古希腊的女神,在得知眼前男人是大名鼎鼎的英雄奥德修斯时便放弃了与之对抗的念头,转而与之共享欢乐甚至贴心服侍,而《白弟鲁·巴西腔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中的女王拉卜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魔头,毫无缘由地纵情享乐并把青年们统统变成动物,全文完全没有对其正面性的描写,《板桥三娘子》中的三娘子也是如此,只交代了三娘子毫无缘由地把自己旅店的住客变成驴。这种描写均突出了作者对于她们从女神到女巫形象的态度转变。
上面已经解释了女巫为什么会有魔力,以及女神到女巫形象转变的原因,但这些都是从男性角度去阐释和理解的,那女巫本身呢?她们自发性地做了哪些事情,又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这一问题,除了是上述中男性对于女性“他者性”超越和内在性要求的结果,还是女性自发反抗下的结果。波伏娃认为,女人之所以成为女巫,自身的原因是她无法融入男人的世界,因为被分开,被对立,所以要把男人带往分离的孤独和内在性的黑暗中。这一想法也与真正的史实不谋而合,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萧兵教授在研究神妓与女巫的关系中时,通过大量的中外历史事实考证,就认为“神妓的身份,是某种大神,尤其是大女神庙里的专祭女巫⑩”。这些有着美貌的女性会把自己的贞操献给神灵以求得国家安稳,往往是通过被视为神的代表的男性首领进行“破瓜”仪式来完成。后来,女性为了报复这种献祭行为,而出现了“破戒诱引”,笔者认为这种最早的“破戒诱引”行为,就是从《奥德赛》开始出现的,是女巫基尔克诱惑奥德修斯的历史原型。
以上内容就解释了女巫为什么有魔力,女神到女巫是怎样发生转变的,以及为什么故事中是由女巫来扮演坏人角色的问题。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就可以探究最后一个问题——“女巫使人变兽”这一题材是如何形成的?
这一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解决,一方面是从女性视角看,为什么要把男人变成兽;另一方面是从男性视角,为什么男性会被变成兽。
从女性视角看,我们已经知道使男人变兽是女性带有报复意味的“破戒诱引”行为,但究其根源,这种“破戒诱引”是女性在尝试突破其内在性时的一种反抗,是女巫作为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他者,通过自己内在性中具有的创造能力使男性也趋向于内在,是对自身不断被他者化、客体化排挤的反抗。在《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中,女王拉卜是不同于伊斯兰教的拜火教教徒,她的“拉卜”一名,就是阿拉伯语“教化太阳”的意思,而众所周知,太阳是阳性力量的象征,教化太阳就带有明显的反叛意味。
从男性视角看,因为女性的双重性,他们一方面想要征服女性使其永远被困于内在性的枷锁之中,服务于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惧怕和被女性身上神秘的自然之力所吸引。所以,当他们作为主体尝试占有女性而失败时,他便被不可抗地异化了,迷失了,变成了异于自身的人,沉没到致人死亡的水流之底。在《奥德赛》中,一开始被变兽的男人们便是在尝试占有女性的过程中失败而被异化成兽,后来甚至连奥德修斯也沉迷于基尔克神秘的内在性之中,直到后来勇敢的心灵重新回到奥德修斯的躯体,他继续开始了超越的征途,而故事最后交代的“不是很富有智慧”的同伴埃尔佩诺尔因沉迷于享乐没有跟随奥德修斯一起离开,最终清醒后从基尔克宅邸的屋顶跌下死去,也就象征着被女人内在性同化的结局。
四、结语
纵观“女巫使人变兽”这一题材十几个世纪以来的流变,我们既看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不可抗拒的不断内在化过程,也感受到了故事中自然流露的女性反抗意识。本文更多是从共同性和发展的过程中来研究这一题材下的女巫形象,但在不同的文本中,因为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两性观等不同,女巫形象也各有其特色。比如,《板桥三娘子》与《奥德赛》和《白弟鲁·巴西腔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中这一题材的最大区别就是缺失了“破戒诱引”的情节,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里就彻底消除了女巫“红颜祸水”的他者特点,只是因为受中国封建统治下儒家文化浸染的“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纲常影响下的结果。又如,板桥三娘子失去了基尔克和拉卜带有的女神特征,也不仅是内在性发展的结果,还涉及在不同文化中女神承担的历史使命不同之原因。
女性主义只是研究这一主题和题材的一种视角,笔者希望通过文学中的这一小小视角得以管窥女性在世界历史中不断挣扎与探索的历程,让这片被不断超越、不断书写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一片属于女性的色彩。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⑨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杭州: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③ 王梆.女巫简史:文学镜像中的女性地位[J].花城,2020(4).
④ 荷马.奥德赛[M].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⑩ 萧兵.神妓女巫和破戒诱引[J].民族艺术,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