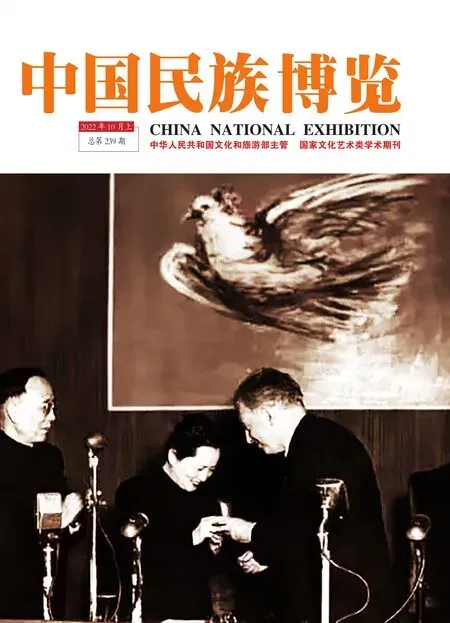电影《敦刻尔克》中人物身份对“生存”主题的表达
宿宸辰 付一方
(1.山东财经大学,山东 济南 250002;2.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2017年,上映的电影《敦刻尔克》由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影片以1940年英法联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敦刻尔克大撤退”为背景,讲述了以撤退(逃生)为核心展开的救援、保卫的一系列行动,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音效剪辑奖、最佳音响效果奖和最佳剪辑奖。导演诺兰深受希区柯克的影响,其影片中善用视听艺术,充满悬念,情节流畅生动,表现出极强的个人特色风格。从叙事上看,诺兰电影典型的叙事结构为非线性叙事和迷宫式叙事,例如,《敦刻尔克》中的三维空间和《致命魔术》中的倒序;从视听语言上看,其善用多元的镜头、深入人心的音乐和视觉奇观来深化电影主题。另外,诺兰对社会中的个人心理发展、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解决等问题十分关注,其电影作品也普遍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特征。将从战争类型片的传统形式、《敦刻尔克》的历史背景与观察视角、四种不同人物身份与主题的关联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导演是如何超越传统战争类型片,通过人物塑造充分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深刻认识和对经历者的关怀的。
一、战争类型片的传统形式
战争片类型片是电影作品在类型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战争史上重大军事行动为题材的影片,主要通过描绘战争事件、战役经过和战斗场面,展现主动或被动参与战争的人物个性,体现英雄形象,将某一重大军事行动、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以及战争的影响展示给观众。其中,反映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心灵创伤是重要的主题之一。目前,单纯表现战争的影片数量已经越来越少,影片通常会融入其他元素,从其他角度来表现战争的影响,与爱情片、历史片或传记片的融合性越来越强。战争类型片的传统戏剧形式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素材取自真实的历史背景
战争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源于历史现实。这些影片的宏观背景以历史上著名的战争为主,写实派往往从史实中的某一标志性事件出发再现当年的战争场面,基本都有据可查。“架空”派则通过放大、演绎并适度虚构其中的人物与事件,进一步展开故事情节。《敦刻尔克》耦合了这一特点,再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场景,以写实笔触深挖了历史背后的故事。
(二)通过“反战”主题展现人道主义精神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局部战争始终存在,其对生命与家园的毁灭性打击令人不忍。每一部战争片,无论是真实再现战争场面,还是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反战”几乎是每一部战争片的共同主题。在战争类型片的程式中,炮火连天的战场、对立的“正邪”双方、战火中的情感等都是经典的元素。战争的场面越惨烈,剧情的矛盾越激烈,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浓厚,越能使观众在眼泪与愤慨中强化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向往。并且,战争片总会交融着亲情、爱情、友情等内容,“真、善、美”的普世价值就像烈日下沙海里的珍珠,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
(三)史诗性与抒情性相结合
战争片因其取材战争史实,并以惨烈的场面、悲壮的基调使其具有鲜明的史诗性。然而,长时间沉浸在“战场”中,往往会使观众感到单调,甚至不适,这会严重弱化影片的故事性和深刻性。为了使整部影片更加具有张力,强化剧情深度,从而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不能从始至终都充斥着血腥、战乱、死亡等镜头,取而代之的是穿插其中的一些平缓、美好的故事情节。实现与观众情感上产生共鸣才能使观众认同影片传达的价值观和创作者的态度,所以战争片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就是“爱情”这一普世价值。
(四)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尤为鲜明
在大部分战争片中,每当战役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会出现极具自我牺牲精神、实力非凡的一号主人公英雄主义形象。他们有的为了集体利益和民族大义而不屈抗争;有的为了完成某一特殊使命,甘愿伪装与潜伏;有的能够在战争到来时,背井离乡,抛却私情。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众多经典的战争片中,英雄主义形象尤为突出。
二、《敦刻尔克》的历史背景与独特观察视角
敦刻尔克是法国西北部的港口小城,靠近比利时边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40年5月25日),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攻势下逐渐崩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英军利用各种船只,在敦刻尔克海滩组织了当时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代号“发电机计划”。虽然这项大规模撤退行动使英国及法国得以撤出了大量的部队,成功挽救了大量的人力,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了有生实力,但是英国派驻法国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这导致英国本土的地面防卫出现了严重问题。此次撤离,标志着英国势力撤出欧洲大陆,西欧除英国、瑞士和西班牙以外的主要地区都被纳粹德国占领。
通过历史背景的论述可知,“敦刻尔克”作为一场撤退战役,本身的成功却又预示着抗战的失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且,它是在敌方领导者独断专行的失误与联军的坚持和妥协中最终得以实现的,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偶然性,也具备成熟历史条件的必然性。因此,其历史评价应当分类讨论,辩证分析。从军事行动角度看,这是一场失败的战役,其影视表述也注定要脱离战争类型片“正义最终胜利,英雄俯瞰天下”的套路,而这场战役“撤退”的实质目的回避了敌我之间的天然对立,为影片场景的创新奠定了天然基础;从挽救生命的角度看,这则是一场奇迹般的成功,这也是影片对这场历史事件的认同。生存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争取活着”也是战争中人的本能。导演诺兰在接受专访时指明,这不是对战争的描绘,而是对“生存”的探讨。
总之,《敦刻尔克》以一场特殊的战役为依据,强化了英法联军内部的矛盾,高度弱化了敌我双方的矛盾,打破了“枪林弹雨”的战争场景构建模式。通过不同的人物群像突出主题,突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精神构建局限,在主题方面,超越了扁平化的“反战”窠臼,以“生存”为核心议题探讨人与战争的关系,从而表达导演对于“人们应当如何看待战争”的独特观点。对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正确理解是研究该影片的重要前提。
三、不同人物身份与主题的关联
该影片的定位是战争悬疑片,但是其中既没有枪林弹雨的激战场面,也没有形象鲜明的超级英雄。观看完整部影片,几乎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名,人们记住的更多的是军官、士兵、民间普通船员、飞行员等人物身份下的群体或群体缩影。本文将在“生存”的主题下,对等待救援的英法联军、民间救援力量、英国飞行员、隐去的敌军四中不同身份人物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导演是如何通过人物塑造充分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深刻认识和对经历者的关怀的。
(一)等待撤退的英法联军的庆幸与愧疚
影片采用了诺兰擅长的“非线性叙事”方法,构建了叙事的三个时空维度——敦刻尔克海滩上长达一周的逃亡故事,英吉利海峡中持续一天的民间救援故事,一个小时内空军飞行员空中保卫的故事,它们以“大撤退”为中心,在救援与保卫中实现交汇。这三个时空的主要人物群体各有不同身份。在敦刻尔克海滩维度,主要人物是正在执行长达一周撤退行动的英法联军。英法联军是战争的亲历者,是受战争创伤最深、求生欲望最强烈的群体。在一周的时间里,在空袭的恐惧中等待着机会,每个人都不愿意放弃生存的希望。比如,一个法国士兵换上英国军装,冒充英国人登上驱逐舰,想要前往还没有战火的英国。在影片开头一路逃跑的英国小士兵汤米最开始不愿意抛下共同逃生时结识的法国朋友,却在一波三折的求生之路上自顾不暇,无力在意其他人的生死。驱逐舰被炸沉后,一群士兵强行登上一艘海边的私人船只,在船体受枪击破损后仍不愿意放弃出海逃离的机会,努力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住弹洞,面对减轻重量的要求,没有人愿意下船重新加入等待的长队,甚至为了是否该抛弃那一名法国士兵而爆发了激烈争吵。船舱一幕,导演通过近景镜头和镜头切换展现了舱内空间的逼仄、狭小,与舱内士兵激动的情绪和混乱的动作共同作用,形成双重压力,加剧了影片氛围的紧张感和画面的混乱感,既刺激着观众的神经,又增强了战争逃亡的历史真实感。
对于参战士兵来说,能够成功撤退既是一次获得生存的机会,也是一种逃跑的行为,隐藏在这场撤退行动背后的是强大敌军的步步紧逼、联军的弱势抵抗力和战斗的失败。因此,生存于他们而言是值得庆幸的,却也是失败、愧疚的。当时,士兵们并不知道几十年后,后人将这场大撤退视为重要的转折点,而他们只是不择手段、竭尽全力地想要逃离敦刻尔克海滩,渡过海峡,活着回家。当他们坐着渔民的小船,满面油污的回到英国,还在垂头丧气猜测、担忧着,以为自己会因民众因败军的身份而被唾弃。
在这一维度,影片通过成功撒退者逃生时不顾一切和生还后不安愧疚的矛盾心理向观众传达了独特的战争观——战争的胜利究竟指什么?在这场撤退中,逃生就是博斗,生存就是胜利。站在经历过万劫不复的士兵角度,战争是没有胜者的,一场被视为伟大胜利的军事行动却是一些人没能迈过的鬼门关和一些人的劫后余生。另外,这部分故事是个人与群体界限最模糊的部分,主要通过直接塑造几个不同空间中的士兵群体展示人物形象。这种对个体的弱化和混乱感的强化,突出的是在战争面前,人脆弱和渺小的一面。
如果说在敦刻尔克海滩维度,士兵角色主要是在联军群体中得以构建,那么民间救缓力量中的船长道森和奋战到底的皇家飞行页皮特(影片中并未提及他们的名字,只是突出了他们的代表性)则是以个体的形象为主要表现形式,在三条故事线的交织中得以构建。人们能从两者形象中看利群体的背景,而两者是群体的缩影。
(二)民间救援力量的帮助与欢呼
影片结尾可以看到,多亏了大批英国民船的帮助,原本高层计划3万人的撤离才能奇迹般地变成30多万人的大撤退。民间救援力量群体被浓缩在了道森父子和助手乔治的形象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驶向交战区,在航行过程中,冒着危险靠近坠海的战机和漏油的舰船,救助了大批落难者。当一大批民船抵达敦刻尔克海滩,指挥官和副官在防波堤上眺望。副官问:“您看到了什么?”指挥官深情地说:“家。”可见,民船是这片充满绝望与焦虑的海滩的希望之船。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船被征用后,道森先生亲自驾着“月光宝石号”率先踏上了救援的道路,他说:“船长跟着船走,他儿子也去。”而在影片结尾可以看到,不仅民船征用十分顺利,而且回到英国海岸的时候,大批民众第一时间为士兵们送上食物和祝福。其中,有一位士兵说:“我们只是勉强活下来了而已。”提供食物的盲人大爷听到后说:“这就足够了。”那么,这场军事行动对于英国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返航过程中,当获救的飞行员问道森先生如何能够预判出刚刚空袭未遂的敌机能被击沉时,道森先生说:“我的儿子(开战第三周就牺牲的大儿子)也是飞行员,我知道他会保佑咱们的。”可见,这场大撤退、大逃亡不仅保存了保卫家园的有生力量,而且保护了普通民众被送上战场的孩子。
然而,战火尚未燃至英国,民众们终究不是战争的亲历者。在影片中,当士兵们坐着火车回家时还在担心遭受谴责,没想到报纸上丘吉尔的讲话已经将其定义为一场伟大的胜利,民众的欢欣鼓舞与士兵的茫然怔愣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表明,民众对生存的认识更倾向于宏观层面一股有生力量、一群年轻的孩子、一批军人获得了新生,而幸存者则实实在在经历了属于自己命运的一劫。未能获救的六七万人对于40多万大军而言只是一小部分,但对于他们本人,却是百分之百的悲剧。士兵与民众的两种反应与前文提到的士兵矛盾心理形成呼应,再次提醒人们,影片始终站在亲身经历灾难的人的角度。同时,启示着现众:不妨跳出政治家的视角和旁观者传统角度重新看待战争,欣赏或创作战争片,战争始终是沉重的而非娱乐的。这一站位也体现了导演对战争类影片创作的创新点。
(三)皇家飞行员的放弃与实现
由于战略的考量,英国只能派出三名飞行员和三架战机来保卫敦刻尔克大撤退。最终,两名飞行员落水获救,而一名飞行员皮特在燃油耗尽被迫下降的过程中仍然选择去阻击敌机,最终迫降敌占区被捕。在构建被救飞行员与环境的关系时,影片使用了交叉蒙太奇和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方法,先通过空战线维度、飞行员法雷尔的角度,看到在水面上迫降的战友挥手示意自己安全,后来通过民船救援意识到飞行员并不是在挥手,而是在从卡住的机舱内挣扎逃生,以此来体现战争的混乱与每个人视角的局限性,突出了人在战争面前的渺小。另外,最后一名飞行员对自己生存的放弃和对更多人生存的守护,是影片唯一一处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突显。影片用深冗、悲壮的配乐,逐渐拉进的镜头以及火光与海天色彩明暗的对比特别突出了他的形象,面部特写更加强了人物的英雄气质。然而,他仍然不被定位为“超级英雄”——对大撤退的保卫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功劳,他只是整个空军的一个缩影。但是,他的结局在强烈的求生氛围以外提醒了人们:面对战争的灾难,求生是一种本能,但牺牲却也无法避免。这位毅然赴死的战士与那些坚强存活的战士实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他们都向人们传达了响亮的声音:生命虽然脆弱,但同样有着它的坚持与伟大,是应当受到尊重、不允许被轻视的,无论何时都不能妄论生死。
(四)隐去的敌军
电影中很少有人提到German或者Nazi,仅仅是称为enemy(敌人),在镜头中故意隐藏了敌人的存在,造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同时也刻意淡化了传统战争片中敌我对立的关系,弱化了“正义必胜”的逻辑。这样的设计将影片视角保持在士兵的层面上,竭力忠实还原他们本身的体验——逃生,突显了影片的核心观念——站在生命的角度,战争是没有胜利的——将观众引向对“生存”的探讨。
四、结语
通过历史现实我们知道,战火蔓延到了拉芒什海峡对岸的英国,影片中塑造的所有身份人物都成了战争的亲历者。《敦刻尔克》是一部讲述“幸存者”的故事,它通过构建不同人物身份与“生存”的联系,向人们传达了“枪响之后没有赢家,唯一可以称为胜利的就是生命留存”这一对战争的深刻认识,片中的英雄,是海陆空三个时空中的角色;片中的正义,寄托于存活下来的希望。影片脱离了战争片的模式,没有鲜明的主人公,也没有敌我激战,始终站在战争亲历者的角度阐释战争,理解并包容他们的心绪,并通过营造氛围和构建环境等手法帮助观众“感同身受”,这种对战争类型片的创新,也是对遭受战争苦难的人们极具个性化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