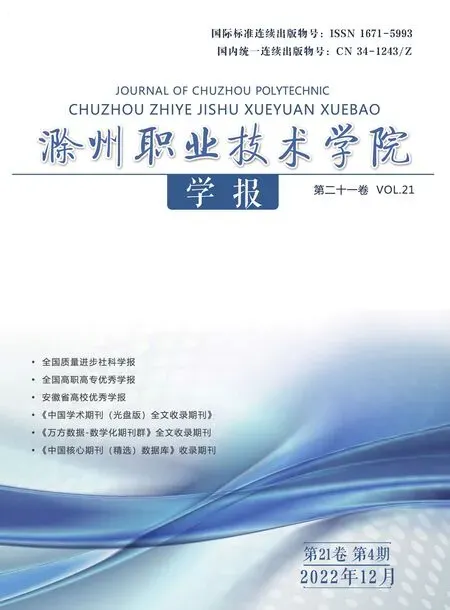对当代读经运动中读经学堂的反思
——以阅读史为视角
韩正非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1)
一、当代读经学堂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当代读经运动及读经学堂的发展脉络
当代读经运动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时任台北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系讲师王财贵率先发起。1994年,王财贵正式向社会倡导读经,此举立即获得大量拥趸,读经运动的影响也由台湾一隅扩展到全国。根据其创办的“文礼书院”的官方网站显示,迄今为止王财贵已在各地开展读经运动宣传讲座2000余次[1]。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等九位文化名宿在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以期通过建立古典幼年学校或古典班的形式来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2]。在读经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社会上以“国学班”“现代私塾”“读经学堂”等形式开办的培训机构也迎来了蓬勃发展。《2018-2024 年中国国学培训行业分析与投资决策咨询报告》显示,全国经营范围包含国学教育的相关企业已达到 4000 余家。这些培训机构的教育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全日制的课外辅导,另一类是全托寄宿制教育。全托寄宿制模式下的读经学堂所开设的课程剔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义务教育体系中的传统科目,而只开设国学经典科。并采取“包本”而不“解经”的教学方式,要求学生完整背诵经科书目,如四书五经、《弟子规》《女诫》等[3]。根据文礼书院讲师裴志广介绍,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50家学生在50人以上的读经学堂,王财贵“御定”的学堂如广东明德堂、北京千人行书院,招生的规模都在百人以上[4]。
在读经热、国学热背景下催生出的读经学堂存在非法经营、违规办学等问题,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2019年3月36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各地要认真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5]”读经学堂产业由此遭受重创。
(二)当代读经运动的研究现状
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主题检索“读经运动”,搜到相关资料95篇。主题检索“读经学堂 + 现代私塾”,搜索到146篇文章。其中有100条是以“教育理论和教育管理”“初等教育”为研究视角的教育学研究,如肖玲,成云《从现代“私塾教育”的特征谈当前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一文以教育学为视角论述读经学堂教育的多元化的价值特征并指出学校教育体制存在的不足[6]。 沈立《对当前儿童读经运动的反思》一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教育、中国基础教育现状和教育哲学三方面分析儿童读经之现象,以期将此教育运动推进到持续健康发展的“经典教育阶段”[7]。刘晓东《儿童读经能否读出道德中国》从教育学的批判视角看待儿童读经问题,呼吁以新思想、新文化推动我国儿童教育的传统立场的变革。[8]
(三)当以阅读史为视角研究读经学堂的意义
在现代教育系统的背景之下,从九年义务教育培养体系进入学堂读经的学生具有怎样的特点,他们为什么要进入学堂读经?他们的阅读的内容具体是什么,阅读方式是怎样的?这样的阅读行为对他们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相关研究多从初等教育、教育理论和教育管理等教育学领域和文化视角对读经运动进行讨论分析。鉴于此,本次研究以阅读史的研究视角为切入点,聚焦读经运动的读经学堂形象,改变以往对儿童读经运动在教育学上的研究路径,具体以阅读主体、阅读文本、阅读空间、阅读行为这四个方面为讨论内容,探究当代读经运动中读经学堂的意义、象征及影响。同时,对于补充读经运动的研究成果以及探索古典教育的发展方向有一定意义。
二、从阅读史视角对读经学堂的分析
阅读活动是一种人类的普遍行为,具有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双重性质。其要素包括谁在读、读什么、为什么读、何时读、何地读、怎样读以及读的结果和影响等,而这些要素也就成为阅读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从读经学堂的特点出发,笔者以阅读主体、阅读空间、阅读文本、阅读行为这四个要素为代表作为讨论对象,从而展开对读经学堂的阅读史研究。
(一)读经学堂的阅读主体——缺乏主体性的孩童
在被送去读经学堂学习的儿童在成绩、品行上与同龄人并无二致,而他们的家庭体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读经学童们家境宽裕,这样才能够负担学堂的高昂学费。同时,家长也具有明显的特征,他们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信任。然而在信任的同时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信任学堂培养“圣人大才”的宣传而将孩子送进避世读经、效法古制的学堂中。
从读者本身的特点而言,他们属于身体和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儿童是缺乏主体性的个体,在去学堂读经这一事件中难以发挥自主的行动和思考。相比处于无知状态中的孩童,父母的意志和意愿在儿童进学堂这一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是孩童行动的代理人和决策者,促使他们做出决策的本质在于:他们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概括性认识具体投射到了经典的阅读文本上,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让自己的孩子读经取得了认识和实践上的连贯性。然而这样的行为可看作一种伪实践,儿童真正承担了父母对阅读文本认识偏差的后果,以被动的姿态脱离了义务教育的体系,被投入到学堂教育之中。
(二)读经学堂的阅读空间——规训的空间
阅读的地点在学堂中,学堂所具备的空间属性不可忽视。福柯对于空间概念的探究使其成为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福柯指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空间化的社会,权利和规训通过空间展现,空间也由此来统治和监管人。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有学堂设在深山之中,如“深圳凤凰山上开起了上百家读经学堂”。在河北承德山中的一所学堂里也有十余名学生,他们各有一间十平米的毛坯房,并且各占山头不许相互来往[9]。还有的学堂规定学生三年不准回家,完成不了背诵任务的学生要受铁戒尺的惩罚,学生在饭前要念感恩词,长年吃素,见到客人还要九十度鞠躬问好。这些严苛的规定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强化学堂的规训功能,重塑人们想象中的学堂威严的形象。如此种种是对古代教育空间和形制的僵硬模仿,是忽视历史发展规律的极端实践。此外还有一些读经学堂与正常学校的班级并无不同,然而旧式学堂所具有的封建、严肃的气息依旧被其承袭。“学堂”这一名称之下的教学空间相比于“班级”更加强化了它对于学生规训意味。如福柯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建筑本身无所谓压迫或解放,并无所谓控制或自由,相反,它随势而定,一个空间只有在被实践与操作时才起到压迫或解放作用”[10]。这些规定也确实将一个现代的“毛坯房”塑造成了一个压迫的“学堂”形象,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学生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中规训教育的被试者。学堂空间在日常的实践中无不向学生展示着它的权力,很难想象它采用强力手段塑造出来的学生符合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空间中的控制带来交流上的闭锁,交流上的闭锁导致精神上的封闭。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要求人以更加开放灵活的态度进入生产和生活,而读经学堂的规训则是与其相背离的。空间就这样被有意识地用来锻造人、规训人,身处其中的学生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成为了被空间权利所统治的人,并且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
(三)读经学堂中的阅读文本——局限的经典文本
读经学堂所开设的课程里没有数学、英语、自然等科目,学生学习的课本是《弟子规》《大学》《论语》《孟子》等传统经典文本。首先需要厘清的关系是学堂开出的阅读文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即这些文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传统文化乃至优秀的传统文化?
以由清李毓秀创作,贾存仁修订改编的《弟子规》为例——它几乎是所有学堂开出的必学篇目。《弟子规》主要列举了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接物、处世、求学时应有的礼仪规范,受到了清廷的高度重视和推广,被誉为“开蒙养正最上乘”的读物[11]。一方面,《弟子规》中“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秉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中最广博的仁爱思想。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苟擅为,子道亏……号泣随,挞无怨”等封建愚孝的观念。《弟子规》的文本内容与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它描述的是中国封建制度下社会行为的规范,其中存在的男尊女卑、君臣等级、愚忠愚孝等思想糟粕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读经学堂中阅读文本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国学经典成为了学生阅读内容的全部来源。当代素质教育注重人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主张将个体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而单一化的经典阅读文本阅读会对学生的个性发展起到限制作用。无论经典文本中包含的是精华还是糟粕,对于不加理解的生硬背诵来说,文本都成为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僵硬的符号。
(四)读经学堂中的阅读行为——缺乏阐释的阅读
在读经学堂里儿童按照学习计划背诵与自主学习,主张“内求”,不提问、不解经。这也是王财贵所主张的“填牛”式记忆——“不求理解,只求熟读、背诵,大量背诵,该记忆的时候让他记忆,不能理解的时候不要强求理解,这才是合乎人性的教育法则。[12]”让学生自己背诵经典是读经学堂几乎唯一的教学形式和目标,这样的方式也被称为“包本”,就是让学生一章章、一本本背诵完经典书目。
阅读史研究的理论认为,书籍的生命包含三要素,分别是文本、物质形态和阅读。“文本和物质形态是为了传达意义,阅读是为了生成和获取意义,因此意义是这三要素的共同目标”[13]。意义的重要性毋需多言。读者反映批评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读者采用特定的阅读策略,会否定、认可或者改变他读到的东西,要么把这些东西吸纳进自己的知识储备,要么排斥,弃之如敝履。[14]”那么“包本”形式的阅读又存在着怎样的意义呢?面对晦涩难懂的经典,作为读者的学生在阅读中缺乏阐释这一重要的过程,也就是切断了意义生产的源头。依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而言,这是实践中的语言符号在所指与能指上被割裂。学生无法感受经典文本所包含的丰富意蕴,这些文本只成为了学生口中意义不明甚至毫无意义的音节。
王财贵认为儿童的记忆力处于黄金时期,在此时期只管记忆,而后再专注理解。这样看似“合乎人性的教育法则”静止地看待记忆与理解的关系,将二者机械的割裂而加以训练,实则是违反人性的法则。只背诵而不解经、先集中记忆再自主理解的阅读方式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在与近十位读经孩子的接触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发现学生们功底薄弱、识字量匮乏甚至难以写成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相当不安的状态,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15]”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明确地指出:“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的、死的, 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我们活的书,直接的书。[16]”这也是现代广义阅读的概念,城市、社会、经历、人物等等都成为了阅读指向的对象,人们通过对各种各样事件的阅读来增长自己的智识,建立自己的品性。单一化的阅读和固化生活体验不利于儿童建立健康完整的人格。阅读在“包本”的形式下成为了一种僵化的、机械的、静态的记忆输入,学生并不能理解文本的含义,文本也无法和学生产生真正的互动。在这样的阅读行为里,文本无法实现它的价值,读者也无法从中获益。读经学堂中暴力阅读的方式是对文本的病态阐释,这样的阅读更像是一种倒错,文本本身成为了唯一的标准,而学生以缺乏主体性的处境被迫记忆。
三、总结
读经学堂中的阅读无论是在读者、空间、文本还是阅读方式上都显示出了它的负面性。信奉学堂教育的人忽略了阅读文本和优秀传统文化逻辑上的关联性。转而采用了一种违背科学、违背理性的方式规训学生,只知模仿古制却丧失古意,这是教育的退行,阅读的失格。
国学经典文本包蕴着灿烂而悠久的民族文化,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创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当代读经运动的勃兴成功增加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唤起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是成功的。然而由读经运动催生出的读经产业却失去了人文教育精神的初心,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敛财牟利的本质。这样假古典教育之口行敛财之实的行为向社会公众传递出了消极的信息,创造出了一个有关传统文化的消极语境,儒学、传统、经典与僵化、闭锁、敛财等印象钩连起来,这是对经典文本乃至传统文化的伤害性实践。在被污名化的语境中,传统经典文本如何在公众心中重正其名,继而唤起公众对其的信任和向往,仍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