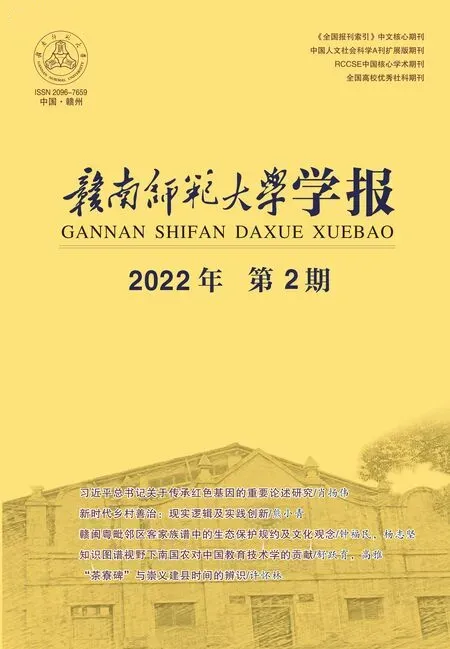褒忠崇礼:明代南赣巡抚修建儒学与祠庙研究*
张志鸿
(赣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明中前期,南赣地方社会动乱不安,剿荡不止,碍于赣闽粤湘边界区隶属不同行政区划的限制,盗贼在地方官府的追剿下往往“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且因地连各境,事无统属,彼此推调回护,以致盗贼横行肆暴,略无畏惧”,[1]1830南赣巡抚便于弘治八年应运而设,在南赣巡抚治下,南赣地区重修、新建了许多儒学、祠庙,部分现今仍有遗存。以往学者对于南赣地区儒学、祠庙的解读,多将其归于风水信仰下,与宗族、民俗等联系起来,或认为民间信仰可视作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窗口,是社会控制的体现。(1)钟俊昆:《江西客家仙娘庙会调查》,《寻根》,2010年第4期;邹春生:《“隐约的祖先”:从民间信仰看客家的族群来源——以赣南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为例》,《民俗研究》,2014年第6期;宋德剑:《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闽粤赣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晓方、温小兴:《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已有研究虽对南赣地区儒学、祠庙的类型、功能、源流、辐射范围等有相对研究,但对以南赣巡抚群体修建的儒学、祠庙并探讨其背后的历史内涵尚属少数。(2)廖祥年则讨论了曾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作为祭祀对象形成的阳明祠庙与明清赣南地方社会的关系,主要着力点在于阳明祠庙、阳明学派、赣南地方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参考廖祥年:《王阳明祠庙与明清赣南地方社会》,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本文在梳理南赣巡抚修建儒学与祠庙概况的基础上,探讨南赣巡抚修建儒学与祠庙背后与地方社会的深刻关系。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正之。
《虔台续志》《重修虔台志》为本文的基本材料,二者属明清南赣巡抚官修志书。“南赣巡抚又称‘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始设于明弘治八年。因巡抚系都察院差遣职官,而都察院由御史台发展而来,南赣巡抚驻地赣州则旧称虔州,故明代人将南赣巡抚衙门称为‘虔台’”。[2]前言2《虔台续志》分《舆地》1卷,《纪事》4卷,详述分总辖及八府一州地图与沿革、地情,纪事则各卷仿通鑑编年目,依时叙事。纪事自弘治八年,终于天启三年,同时收录王守仁等历任巡抚在任期的诗文奏章共59首(篇)。
南赣巡抚自弘治八年设置,于康熙四年最终裁撤,历经明朝中后期、清前期,其间在任共73任巡抚,嘉靖三十四年《虔台续志》、天启三年《重修虔台志》收录弘治八年至天启三年南赣巡抚55人,其中有22任南赣巡抚有新建或重修祠庙之举,共新建、重修祠庙26次之多。按照祭祀对象所宣扬的情感态度、价值理念,在儒学单列一类的前提下,亦可将祠庙分为两类:忠义祠、阳明祠。
一、儒学的修建与礼仪教化的传达
南赣巡抚建立的儒学既包括府县儒学,亦包含乡间社学,府县儒学是官办教育的主体,社学则是主要开办于乡村地区,以儒家伦理为主,向蒙童提供教育的组织形式。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社学追溯至洪武八年朱元璋的诏令“是以行教化而美风俗,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3]在这则诏令中,社学不仅是对蒙童进行儒学教化的手段,也是促进地方移风易俗的重要依托。具体到南赣地区,南赣巡抚设立期间,有建儒学举措的巡抚15任,兴建儒学15次。最早为第一任巡抚金泽于弘治九年因赣之府县学“岁久日圮,出公帑修葺之”,[4]46最后一次则是巡抚周应秋于万历四十八年因赣县儒学“为风雨朽蠹,倾塌踰年”[2]233且“附祀不专”,[2]269遂令有司重新修缮。
(一)建祠时间
在南赣巡抚建儒学的过程中,大多集中在冬春之季,15次修建儒学中有11次在冬季与春季,其余则零散分布在夏四月、秋九月。如巡抚金泽弘治九年春二月重建“赣之府县学”,秦燿任于万历十五年“冬十一月,复大庾县儒学”。[2]207
修建时间集中在冬春之季首先与巡抚到任时间以及地方形势有关。如金泽于弘治八年秋八月就任南赣巡抚,于当年冬十月督兵进剿流劫于信丰、龙南的汀漳盗寇王魁、蔡郎钢等,平叛结束,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南赣辖区的城池、书院等建设工作。弘治九年春二月,相继创建了南赣巡抚衙门、重修赣州、兴国等地的城池,设立关隘以及修建儒学。其次则与春天厉行祭祀有关,《礼记·月令》“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发展到明成祖时期,朱棣特令在南京建立帝王庙,并规定在每年分春秋两次祭祀三皇五帝等。可见,春季在祭祀的环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春行祭祀,再布行政令,已经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重要的施政环节,而社学亦是祭祀圣贤先儒的重要场所。所以在春季将祭祀场所社学和府县官学进行修缮、新建就成了当地官员很重要的一项季节性安排,也是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
(二)建祠地点
府县儒学与乡村社学一般有左庙右学的规制,而府县学又多集中在“城东南隅”,与府治并列。如金泽在重修府县儒学时即有明确表述“时赣之府县学俱在城东南隅”,[4]62万历十五年巡抚秦燿复大庾县儒学时就说“大庾县府治,旧有颛学……今议地仍旧址,文庙附府学,不必另创。”[2]207可知府县社学一般与府治相并,先贤祠则附之于社学之内。后世巡抚多沿其旧址兴建、从祀。
(三)建祠原因
1.完全新建。正德十年巡抚蒋昇“府州县官务要慎选素颇读书谨守者招局教读,不拘城市山乡,但人烟相望约有百家上下或七八十家者,可设社学二所,四五十家以下者亦设一所”,[4]128不仅详细说明了社学招生的条件“素颇读书谨守者”,也阐述了社学与时人口密度之间的大致关系,以四五十家为界增设社学;嘉靖十九年巡抚李显“先是,赣城内社学凡四,曰义泉、正蒙、镇宁、富安,至是又新建龙池书院,合为五处”。[2]99巡抚在原先没有书院、社学的地区新开社学,进而进行先儒先贤的崇祀,是儒学修建的直接原因。
2.岁久失修。岁久失修,倾颓有年是在南赣巡抚兴修儒学中占比最多的,《重修虔台志》与《虔台续志》中多次提到,如弘治年间巡抚金泽重修赣之府县学“时赣之府县学俱在城东南隅,岁久日圮”;[4]62弘治十五年韩邦问重修濂溪祠“旧有书院,岁久沦废”;[4]68正德十年巡抚蒋昇重修赣州府县儒学“赣州府县儒学复坏,乃檄下府县修葺之”[4]75等;重现地方教化,完善倾颓的府县儒学以及礼学祭祀本就是熟读圣贤书的巡抚们的正常手段,这对他们来说足够亲民。
3.不符规制。嘉靖三十一年,巡抚张烜重修信兴国县学的原因即是如此,在此之前,兴国县学经历了几次的地基迁移,后有识者认为其中建置不符合礼制,推官、县事、官师等有志于推进的士大夫群体便与时任巡抚李显商议将之进行完善“以正体制”“以遵王制”,先后规划了正殿、两庑、棂星、敬一亭、堂斋、泮池,缭以周垣,最后达到了“规模焕然,不失崇正之体”的目的。万历四十八年周应秋完善赣县儒学明伦堂亦是如此,先是“湫阨痹隘,附祀不专,厥制弗称……非所以育材彦而隆教化也”,[2]269重修之后便取得了“明兴胶序,鳞次郡国,秩祀严备,文教蔚然”[2]207的结果。上述儒学的修缮是因为之前的社学、明伦堂等并不是完全的符合礼制规定,巡抚上任之后便进行了重修,这也是儒学重修完善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资金来源
儒学的资金款项来源大多是公费,官府出资修建,此在多处均有明确表述。金泽在重修赣之府县学的资金来源是“出公帑”;万历十五年秦燿重修大余县儒学时就说得更加明确,“一切善治之费,取足于府先库贮积余,齐俸、门役、廪粮、膳夫及考试贡举诸费,有本县原编府学银数可以制回,有本府议革小溪驿廪粮过关等银可以改编,府仓额银余剩可以待用。”[2]207在动用官府存银的同时,有些巡抚也会捐献出自己的薪金进行儒学的改造,如万历三十三年李汝华重修赣县儒学时“捐金一千六百有奇,亟助成事”,[2]228万历三十九年牛应元完善赣县文昌二阁泊四周垣墙时“捐七百金以助工料,乃终厥绪”。[2]230
(五)儒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儒学的兴建不仅为地方进行了人才储备,也更加完善了国家礼法体制。这其中,更多的是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儒学礼法渗透地方的过程,也是地方士大夫、文人集体促进地方融入大一统国家的重要手段。“使知孝亲弟长、尊君亲上、为善去恶之义”[2]95“人心翕然乐趋,而童蒙小子亦知所向往矣”[4]192“重道崇儒兴起斯文之盛举也”;[2]203社学一设,地方教化一日而新,影响深远。赵克生也说“阳明社学礼教的影响极大。这种影响首先是在南赣当地, 通过童子习礼, 传播了家礼知识, 家礼得以进入民众的生活……其次, 阳明教法成为其他地区社学礼教的范本。”[5]府县儒学与乡村社学的兴修重建使得南赣地方教育逐渐趋向完善,崇儒重教之风得以重现,濂溪龟山等文脉也得到了承续,这对于改变明人印象中的南赣地方“瘴疠丛生之地”,增强地方文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二、阳明祠的修建与南赣礼教的深化
王阳明一生多次经过或停留赣州,最长的一次是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六年任职南赣巡抚时期,期间改革盐税,拣选民兵,平定三浰、横水、桶岗诸巢数十年的动乱,新建了崇义、和平、平和三个新县,使得南赣地区重新恢复了社会秩序。[6]正如明史专家方志远所说,如果说贬谪龙场开始造就中国哲学史上的王阳明,南赣汀漳巡抚的任命则造就了中国政治史上的王阳明。文化上,王阳明在赣州刊印了古本《大学》,强调仁政亲民,同时兴办了书院、社学,推行《南赣乡约》改善民风旧俗,教化南赣百姓。王阳明对赣州文武教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虔之民众对于阳明去任后的怀念以及后面逐渐修建起祭祀他的阳明祠,不论是其中对于平南赣盗的报功祠,还是彰炳道德文章,讲学修己的儒学类祠庙,都是对其恩德功绩的肯定。
《重修虔台志》和《虔台续志》记载,共4任南赣巡抚,建阳明祠5次,其中4次都是在嘉靖年间修建的,1次修建于天启年间,巡抚张烜则有两次修建阳明祠像的举措,一是嘉靖三十一年冬十月,复南安旧祠阳明王公于庾河之南,二是同年十二月,又再次修复阳明像于郁孤台。
南赣巡抚对于阳明祠的修建,大体可分成两类,一是感恩王阳明平定南赣盗乱的报功祠,一类是偏重于传承儒学道统,在南赣进行讲学活动而进行纪念的理学祠庙。报功祠有两例,一是嘉靖十三年巡抚陈察重缮阳明祠,“王阳明先生,守仁别号也。功在南赣,士民德之。祠在学宫之右,额曰报功祠”,[4]128此时,王阳明已去任南赣巡抚13年,去世6年,赣之士民念其旧恩,由之兴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和之后,巡抚陈察也相继进行了募兵、除戎器、兴社学、重修赣州城等施政举措,可以看到,修缮阳明祠是与之并举的。二是嘉靖三十一年冬十月,巡抚张烜修复南安阳明祠于旧址,在这则记载中,对于修祠的原因和过程表述地较为详细,“先是,公(阳明)督理军务,以正德丁丑岁荡平輋贼,民获宁宇,思之弗置也。岁丙戌,父老谋构公祠于学宫之右,以昭报祀。[4]172-173“荡平輋贼,民获宁宇”“以昭报祀”等侧重于阳明平乱的表达也更说明此祠偏向于报功祠的成分多一些。
对于阳明祠的修建,再有就是对于其讲学的推崇,嘉靖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巡抚张烜“有见于祠之逼于市嚣类,弗虔也”,[4]174-175于是起了重修之意,在留下的记文中,张烜提到“其为宇三进,妥濂溪神像于中堂,列二程先生于东西以配享祀,俾谒者瞻祠起敬,以知先儒论道之源,其尊礼也至矣。复于台端隙地别构一堂,每谒祠既事辄止于斯,时与诸生讲论经义恒于斯,士大夫有感而来者接礼于斯,或出师振旅凝静定计间宿于斯,公之寓于齐居以自得者亦多亦”,[4]174-175亦可知,这是对于阳明讲学的推崇,在这里,作为理学家的王阳明身份显然多于军事家。嘉靖三十四年冬十月,巡抚汪尚宁也重修了郁孤台阳明祠,“正德丁丑,王守仁移其署而增封之,下祠周程三先生,集列郡士绅讲学于斯,郁孤遂以王公望于天下。公既去,人士复其后以祠公,祠存而台毁。公来乃与游兵宪震德,檄郡邑复之。”[2]126就此观之,这次重修更多的也是对于王阳明“集列郡士绅讲学于此”的推崇。
再有一例则是对报功和教化均有表述,天启二年春三月,巡抚唐世济重修文成祠,“王文成公倡明理学,剪除祸乱,虔人食其赐而尸祝焉。伏腊近百年矣,庙且就圮至是。先查取信丰、龙南两县水面银一百四十四两四钱,命知县刘永基葺而新之,更增建堂后一带。前后约共五百余金。”[2]239平定动乱与教化是相辅相成的,平地方动乱给了百姓一个得以安居的生存环境,教化人心则是在安居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二者相互结合,不断推动着地方社会融入王朝国家的进程。
另有学者分析,报恩祠多在南安各县,讲学祠庙则多集中在府治、于都、赣县等地。且南安府阳明祠多在正德年间为感王阳明对南赣的功绩而建;嘉靖十六、十七年多有破坏,原因是嘉靖皇帝于嘉靖十六年,十七年的两次学禁;嘉靖三十年代,阳明弟子多占据庙堂,在江西任职的沈谧、刘节也响应朝廷政策,倡导地方兴建阳明祠庙,导致这时期的阳明祠庙修建达到高峰。赣州府周边地区理学风气、儒学浸润则相对南安深,王阳明多于都、会昌籍弟子,在这些地方,更多地则崇尚王阳明的学术思想。(3)相关研究参考廖祥年:《王阳明祠庙与明清赣南地方社会》,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郭晓慧:《王阳明赣南弟子研究》,赣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王阳明巡抚南赣,重建了地方基层社会,赣之官民修建、重修阳明祠庙,尊崇祭祀王阳明,既是对其治理方式的认同,也是对其学术与事功的尊崇。而阳明祠修建的官方化,又含有一个重建南赣地方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联系意义,南赣地域上建立起来的阳明祠庙,不论是表彰其事功,还是追崇其学术,都能让南赣这片文化贫瘠之地多一些阳明过化之迹,这对于王朝礼制的深化以及南赣地域的社会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
三、忠义祠的修建与“忠”的政治认同构建
南赣地区,自古便有盗贼渊薮之说,动荡不安,宋代有盐寇、虔寇、峒寇等,元明有畲民等流民问题,明清鼎革、三藩之乱等也延续、影响到南赣地区,无论是盗贼规模,还是动乱频率,都使得南赣这片土地在王朝体制的管理殊为不易,朝廷虽在此设立了行政区划,进行赋役征收等,但南赣地方对王朝国家的认同并没有达到预期地那么深切。
宋代赣南动乱较多,据黄志繁统计,据正史、方志、文集记载,择其大者而观,宋代赣南的动乱便有26起,尤以南宋初年最为频繁,而且规模、数量往往能达到数万、数十万,波及范围广。[4]43-46元代,赣南动乱大者亦有14起,但规模巨大,常常可以达到几十万之众。[7]83-85明朝时“江湖闽广边界去处,高山大谷,接岭连峰,昔人号为盗区”。[4]144据黄志繁统计,据府一级方志记载,有明一代发生在赣州地区的动乱就高达102次。[7]117-127《虔台续志》和《重修虔台志》里面记载的重修、新建忠义祠有5次,忠义祠的修建全部集中于嘉靖年间。嘉靖四十五年中,南赣巡抚一共换了28任,最短在任2个月,平均一任担任19个月,期间赣州发生动乱41次,[8]有名的有嘉靖三十年岑冈李文彪叛乱,杀龙南高砂堡民三百人,[2]118持续流劫到嘉靖三十九年。嘉靖年间赣州的动乱频繁,与南赣巡抚的施政措施之一,兴建忠义祠便形成了直接的关系,历任巡抚在保赣安民的过程中兴建、重修象征着对国家忠义,表彰将士军民的祠庙便有了现实意义。
在5次修建忠义祠的过程中,岳武穆公祠便占了2次,分别是嘉靖七年巡抚汪鋐重修和嘉靖四十五年巡抚钱桓重修。《虔台续志》和《重修虔台志》均对第一次修建有详细记载,对比两次记载,我们能发现其中有趣的地方,《重修虔台志》对第一次修祠有两处记载,第二处省略了“高宗密令岳飞尽屠虔城”中的“密”字,而《虔台续志》则直接隐去了高宗“密”令岳飞尽屠虔城,岳飞再次上书的次数,仅表述为“高宗以隆裕太后震惊之故,欲尽屠虔城。飞乃请除首恶而赦胁从,帝许之”,[4]116而在《重修虔台志》中,“以隆裕太后震惊之故,欲尽屠虔城,武穆力请止除首恶而赦胁从,请至再,帝勉从之”[2]87“帝许之”与“帝勉从之”的表达也颇具玩味。对比同一时间三版不同的修建精忠祠记载,可以试图还原的是,高宗因隆裕太后受震惊之固,密令岳飞尽屠虔城,岳飞先后两次请求除首恶而赦免胁从,最后高宗勉强同意。从这其中,我们更能体会到岳飞对于赣州人民的浩大之恩,“虔人之德武穆也更甚”[2]87矣。万历四十五年的重修则是由于“庙久倾圮”,巡抚钱桓“委赣州府通判李若素监修,易旧为新”[2]232了,这其中固然有崇敬岳飞,希望像岳武穆一般做出一番政绩,护佑一方百姓有关,也与彰表、激励前方军士奋勇杀敌,立下精神支柱密不可分了。
嘉靖八年,巡抚周用建清忠祠崇祀赵忭、文天祥。赵清献公忭、文信国公天祥都曾经担任赣州的知州,郡守,因此赣人为之立祠,春秋祭祀。在周用为重修该祠写下的祠记中,对于“清忠”有着这样的解释:“夫臣之事君,不易其介谓之清,不有其身谓之忠”,[2]266并对赵忭、文天祥的事迹、为人做了高度评价“其笃信力行类如此,是故不以辱加宠,不以退荣进,不以利妨义,不以死易生,志遂于当时,烈垂于后世,光明俊伟立乎万物之表,使人咨嗟叹息以为不可及”,[4]120赵忭谥号清献,文天祥谥号信国,这已是莫大的殊荣,再次重修翻新并为记便加深了士人百姓对“清忠”的理解,“以诏自今之吏于赣者知所尊信,俾赣之人世蒙其休泽以永其思焉”,这便有告于在盗区与政区往复的南赣之百姓忠于朝廷,南赣之官吏清廉奉公,除了军事行动上的破除山贼,更需人心教化,以便更好的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
在南赣巡抚重修的忠义祠中,还有两例祠主则是更明显地表现为抗敌御战,以表彰之的主题,嘉靖十二年春正月巡抚钱宏建忠命祠,祭祀“龙南县尹陈泰惠政及民,元延祐进士,仗义御贼战死。宏乃命立祠学宫之傍祀之”;[4]124同年冬十二月,继任巡抚唐胄表宋丘佥判祠“广东南雄府保昌县丘必明,宋德祐中任韶州佥判,元兵逼城下,必明不屈,为敌所杀。本县旧有祠,后废为社学。胄谓有司仍立祠,绰楔表之,复其子孙”。[4]126这二者都是御贼战死,为敌所杀的元时忠烈,巡抚嘉奖,彰表他们则更能直接看出对于地方治理的希冀了。
《重修虔台志》还有一则对于修建地方神灵江东庙的记载,万历十九年秋七月,巡抚汪敬民修江东庙。“照得江东之神显灵于汉,建庙于唐,尤著英爽于本朝,其护国之功甚多。本院叨抚兹土,因祈雨行香见本庙房宇圮坏,不蔽风雨,非所以妥神灵而祈鸿庇也。”[2]218可以看到,重修江东庙也是由其护国之功甚多,于是巡抚汪敬民利用原有的该庙田租重修修缮。“明初名臣宋镰《江东庙记》记载了许多江东神“石固”显灵的故事,如宋建炎三年,用阴兵吓退金兵,保护了逃亡到赣州的隆佑太后;淳佑九年,帮助监军姚希得平定安远崔文广之变等。”[9]江东庙从神职而言,也是“忠君爱国”的一种,重修江东庙亦有在南赣地方树立忠君护国的认同观之考量。
通过对以上忠义祠的分析,结合时南赣的社会状况可知,忠义祠的修建、重修目的很明确,即塑造动荡地方对于明王朝的“忠”这一政治认同。南赣巡抚设置的本意便是缉盗安民,加强社会治理,在南巡抚施政过程中,兴建、重修已有的精忠词、忠义祠等对于南赣地区的社会治理、抚盗安民便有着显著的表彰、激励作用。从《虔台续志》和《重修虔台志》中,没有找到忠义祠的修建对于地方叛乱的直接影响,但从前面学者的统计,嘉靖后包括隆庆六年、万历四十八年、天启二十二年、崇祯十七年共93年间,赣州动乱仅发生21次,[7]117-127相比嘉靖四十五年中动乱41次,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这其中固然有王朝统治日益深化,社会矛盾相对调和以及军事征剿取得成效,但在这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南赣巡抚建立忠义祠对南赣士民争好向善,止戈为犁的推动作用。
四、结语
南赣巡抚裁撤的时间距今已经356年了,“提督虔院前有古柏数十株,高可百尺,常有群鹤翔集其上,康熙四年裁缺,柏渐枯,而鹤亦去矣。”[10]忠义祠是塑造地方士民对于明王朝的“忠”的情感,儒学和阳明祠则是塑造“礼”这一儒家道德,二者是除了编户齐民、设置新县、减免赋税等政治举措之外地方融入大一统王朝的重要手段。正如吴启琳在评价王阳明在南赣地区设置新县时所说:“待上犹、大庚、南康边区贼寇平定以后,南赣巡抚王阳明便在三县适中地方着手设置新的县治并辅以巡检司,试图将国家正统权力完全地置放于原先的贼巢之中,从而实现该区由‘盗区’向‘政区’的转化。”[11]“忠义祠”构建的是政治上对于国家的归属,儒学与阳明祠构建的是文化心理上对于国家的深切认同。二者相互影响,共同体现社会治理需要下的不同侧面。在儒学与祠庙的修建过程中,南赣地方社会和明王朝的接触融合日益加深,忠义礼教渗透也日益强烈。《虔台续志》亦有云:秋月皎兮玄鹤依,章贡合兮奠清邑,[4]175俾赣之人世蒙其休泽以永其思焉![4]120
历来学者对于赣南地域融入明清大一统王朝的方式与过程都有不同程度、不同视角的探讨。王福昌、饶伟新重视生态与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刘志伟、黄志繁从国家赋役与经济视角提出无籍之徒到编户齐民的转化,重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作用;唐立宗、吴启琳则从政区沿革与传承嬗变入手讨论赣南政区变迁;肖文评、邹春生等从文教风俗出发,重视儒学教化、民间信仰在这一过程中的体现;另有王东、谢重光、温春香等人对族群这一特定群体的重要把控。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的视角延伸,将国家背景下南赣巡抚修建的儒学与祠庙中体现“忠”与“礼”的部分进行关照。儒学的不断兴修与重建,是礼学教化在地方社会的纵向传达,忠义祠、阳明祠修建群体的士绅化、官方化,蕴含着重建南赣地方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努力。从无籍之徒,化外之民到版籍之徒、编户齐民的转化,从“昔人素称盗区”到“崇儒兴起,斯文之盛举”,这是忠于王朝国家,礼于地方社会的客观表达。南赣巡抚修建儒学与祠庙,寓政治希冀于潜移默化之中,也是赣南社会历史进程与赣南社会史的一个侧面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