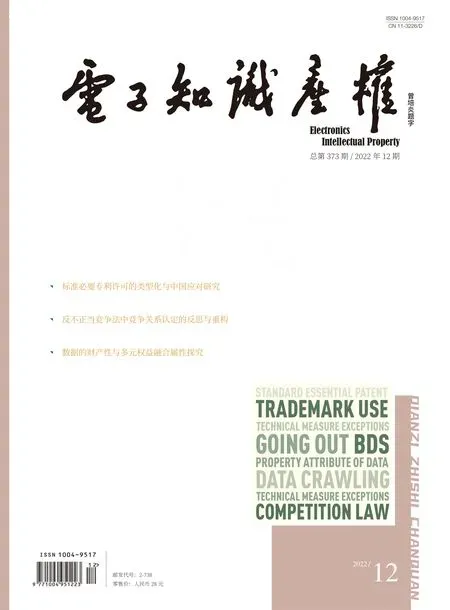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体系化分析
文 / 刘云开
一、引言
互联网、电视网、电信网“三网融合”技术的革新与普及为广播电视行业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新型法律问题,深刻影响《著作权法》中“传播权”体系内容的变动。广播组织权利制度是随“三网融合”技术发展而变动最大的著作权制度之一。2021年6 月1 日,我国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正式实施,1. 参见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1/272b72cdb759458d94c9b875350b1ab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 月31 日。意味着我国著作权法进入一个新的“解释论时代”。2020年《著作权法》对我国广播组织权利制度做出诸多调整,其中最大的调整莫过于在权利内容上为广播组织增设“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权利使广播组织对其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控制从“非交互式”领域扩展到“交互式”领域,极大扩张了广播组织权利范围。对此反对观点认为:(1)该权利既是对广播组织权“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的背离,也将严重侵蚀公有领域;2. 参见王迁:《对<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四点意见》,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9 期,第42-46页。(2)由于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制度十分完善,因此该权利存在的意义不大,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广播组织享有非专有使用权的内容和公有领域内容;3. 陈绍玲:《论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空间》,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 期,第65-74 页。(3)广播组织在播放他人制作的广播、电视的过程中没有贡献新的内容,对广播、电视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合理,该权利范围应仅限于针对广播组织自己制作并播出的广播、电视。4. 袁锋:《新技术环境下广播组织权的问题与完善——兼评最新<著作权法>第47 条》,载《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 期,第109-119 页。上述反对观点展现出一定的“规则怀疑论”倾向,且第(2)种观点与第(3)种观点所提供的最终方案截然对立。由此表明,围绕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产生的理论争议并未随《著作权法》的修订完成而消失,相反却会对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条款的适用产生障碍。法律属阐释性概念,5.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许宗英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 页。立足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条款,运用解释论方法回应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争议、范畴界定和体系衔接问题,以确保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准确适用,既是一种可行选择,更是一种迫切要求。
二、因何设权: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正当基础
(一)本土需求:广播电视节目数字化进程加快
随着数字与传媒技术的融合与革新,电视行业已经进入融合发展的快车道。我国广播机构已不再满足于使用传统的模拟传输技术向公众提供广播电视节目,而是抓住“数字赋能”的机遇,借助电视网、电信网、互联网等多种通道,以电视或网络直播、转播、点播等多种方式传播其广播电视节目,从而提升传播效率和节目收视率,便捷观众选择需求,助力广播电视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首次突破1 万亿元,其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实际创收收入9673.1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4.68%和25.43%;智能终端用户和有线电视双向数字用户逐渐增长,全国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用户超过3 亿元,互联网电视(OTT)用户数超过10 亿元。6. 参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http://www.nrta.gov.cn/art/2022/4/25/art_113_6019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 月20 日。但与此同时,随着广播电视节目“数字化分发”进程的不断加速,广播电视机构与传统的网络平台在数字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其共同的目标是网络受众及其注意力。由于公众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获取更加便捷,加之网络平台缺乏严密的监管措施,导致部分用户通过电视、网络非法录制和传播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日益严重,广播机构失去节目控制权的风险越来越大。7. 参见《广播部门目前的市场和技术趋势:导言和内容提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30/5文件,2015年6 月17 日发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法侵权人的行为严重分流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受众注意力,而广播组织者的维权成本则不断提高。8. 参见刘云开:《广播组织权客体之再辨析——兼评我国新<著作权法>第47 条》,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11期,第13 页。
然而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前,广播组织权的权利范围仅限于禁止未经其许可而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转播、录制和复制三类情形,不延及网络领域,9.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二)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侵权人将广播节目通过互联网传送到用户终端的行为十分多见,例如一些网站未经授权向公众提供体育赛事的网络直播和点播回看服务,其中既涉及广播电视节目的网络转播,也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显而易见的是,此种行为必将给广播机构的合法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广播机构的相应投资可能付诸东流。如果著作权法缺乏相应规范,广播机构和司法机关面对此种非法行为也显得无能为力。在“浙江省嘉兴华数公司与中国电信嘉兴分公司侵犯广播组织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互联网转播了涉案广播电视节目,但尚不能依据原《著作权法》的规定将该行为认定为“转播”,加之广播组织也不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无法规制被控侵权行为。10. 参见浙江生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1)嘉南知初字第24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嘉知终字第7 号民事判决书。更重要的是,当前多数广播电视盗录盗播行为都发生在网络空间,如果不将广播组织权利范围扩展到网络领域,广播组织将不能独立于著作权人而单独起诉侵权行为人,但广播机构的损失并不因此而降低。11. See Shyamkrishna Balganesh, The Social Costs of Property Rights in Broadcast (and Cable) Signals,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22: 1303, p. 1319 (2007).因而,将广播组织权的权利范围延伸至网络领域,为广播组织赋予网络转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于维护广播电视机构的投资和合法利益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二)国际动向:SCCR 拟扩张广播组织权利内容
为广播组织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既是我国维护广播电视机构合法利益、规范行业竞争秩序的实际需求,也与国际立法趋势保持一致。扩张广播组织权利内容,强化广播组织权利国际保护,这是《罗马公约》制定以来持续存在的一项国际知识产权议题。近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与邻接权委员会(SCCR)致力于制定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国际社会代表在广播组织权利保护问题上也表现出权利扩张的主张。
在1948年《伯尔尼公约》布鲁塞尔修订会议上,缔约方围绕“是否应当将版权扩展到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机构”这一议题展开讨论。随后国际社会于1961年单独缔结了《罗马公约》以保护上述主体利益。根据该条约第十三条,广播机构有权授权或禁止他人转播、录制、复制以及向公众传播其广播节目。12. Se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formers,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adopted at Rome on October 26, 1961.但《罗马公约》的实施范围极为有限:第一,它只对广播节目的“同步广播”提供保护,而不包括“延迟广播”这类核心业务;第二,它只规制传统的无线转播行为,而不规制包括有线电缆和数字广播在内的传播方式。当然这与条约制定时有线广播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缔约方未能预知广播技术发展之迅猛。第三,该条约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只有加入《伯尔尼公约》或《世界版权公约》的签署方才能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单位。1974年的《布鲁塞尔公约》是第二个保护广播组织权利的国际条约,但因为该公约旨在保护原始卫星信号的传输,而非广播信号的再次传输,导致其适用范围依然十分有限。在后来的TRIPS 协定缔结过程中,尽管有线电视技术在当时已十分普及,但其仅仅纳入了《罗马公约》的实质性条款,而未将有线广播写入TRIPS 协定。其原因在于,各缔约方主要围绕网络和数字技术给版权法带来的挑战展开讨论,而忽略了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现实。13. See Mantani Sharma, TRIP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the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Stalemate or Deliberate Ignorance?, Richmon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Vol. 24: 5, p. 19 (2018).同时TRIPS 协定被设想为“最低标准”条约,并没有更新现有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想法。14. See Laurence R. Helfer, Adjudicating Copyright Claims Under the TRIPS Agreement: The Case for a European Human Rights Analogy,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9: 357, p. 360 (1998).因此广播组织错失了扩张权利内容的机遇。
1997年,WIPO 举办“世界广播、新通信技术和知识产权研讨会”(即“马尼拉研讨会”),此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是,现有广播组织国际保护制度需要顺应广播技术的发展,有效遏制广播盗版行为。15. See WIPO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 Related Righ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WIPO Doc. SCCR/1/3, Sep. 7(1998), p. 4.1998年,WIPO 成立SCCR 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更新广播组织国际保护制度。然而从1998年至今,SCCR 已连续主持召开四十二届会议讨论制定具有现代意义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旨在应对新技术环境下的广播组织权利国际保护问题,但由于各国分歧过大,至今尚未就条约的实质性内容达成共识。《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由此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史上争议最大、难度最大、制定时间最长的条约。16. 胡开忠:《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利内容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修正的信号说”为基础》,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 期,第39 页。但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推动意义的事件是WIPO 在2006年大会上决定SCCR 应力求商定并最后确定“以信号为基础”的保护目标、具体范围和对象。17. See The WIPO Treaty on the protection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Informal Paper. Prepar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SCCR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f the SCCR at its 16th Session (March 2008), p. 2.当然在条约磋商过程中,一些代表提出了“基于权利的进路”或“基于内容的进路”。该观点认为,《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应是对《罗马公约》的更新,以弥补通信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保护差距。新的条约应当沿袭《罗马公约》,对已经存在的权利进行更新。然而反对者认为,许多国家并没有加入《罗马公约》,也没有为广播组织提供版权法意义上的保护,“基于权利的进路”将导致许多国家版权法中为广播组织机构新增“知识产权层”(layer of IP rights),由此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锁定公共领域的内容,并扼杀技术创新。18. See The WIPO Treaty On The Protection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Informal Paper. Prepar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SCCR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f the SCCR at its 16th Session (March 2008), p. 7.也有一些代表认为,应当以“防止信号盗窃”为目标导向,采取“基于信号的进路”,赋予广播机构对“载有内容的信号”所享有的权利,“有限而具体地关注保护信号免遭故意盗用或盗窃”。19.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WIPO Broadcast Treaty Provided by Certa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 and Performers' Representatives (Sept. 5, 2006), at http:// www.eff.org/IP/WIPO/broadcasting_treaty/wipo-statement-20060905.pdf (Last visited on August 24, 2022).
在网络广播领域,SCCR 最初没有计划将“网络广播”纳入条约讨论范围,决定暂时留给以后单独讨论。但在SCCR 后来召开的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认为,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广播信号的行为十分严重,新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需要增加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保护其国内广播机构的投资利益。SCCR 对此提出了三种替代解决方案,签署方可以:(1)简单地批准与广播有关的条约和有线广播;(2)批准条约并通知WIPO 总干事其选择包括对网络转播的保护;或(3)批准条约并通知总干事其选择包括对网络转播和信息网络传播的保护。20. Matthew D. Asbell, Progress on the WIPO Broadcasting and Webcasting Treaty,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4: 349, p. 353 (2006).在2022年5 月9 日—13 日举行的SCCR第四十二届会议上,SCCR 发布了最新的《经修订的产权组织广播组织条约案文草案》(以下简称《案文草案》),该《案文草案》相比于2019年的《经修订的关于定义、保护对象、所授权利以及其他问题的合并案文》(以下简称《合并文案》),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将“广播”的定义范围扩展到了“计算机网络”领域。该《案文草案》第二条规定,“广播”是指以有线或无线手段传输节目信号供公众接收。在关于该定义的解释中,《案文草案》指出,“‘广播’中不仅包括无线传输,还包括‘有线’传输。该定义由此涵盖所有传输,包括通过电缆、卫星、计算机网络和任何其他手段。因此,‘广播’的概念在本条约中是完全技术中立的。”该建议认为,不应将“网络传输”排除在“广播”定义之外,而应当明确网络传输属于广播行为。如果各成员方希望将网络传输排除在条约适用范围之外,可以通过条款保留的形式予以执行。21. See Revised Draft Text for The WIPO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Treaty, prepared by the SCCR Acting Chair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CCR Vice-Chair and facilitators. SCCR/42/3, May 9-13(2022). p. 10.笔者认为,新《案文草案》将“网络广播”纳入“广播”的范围,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一,网络作为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的重要通道,在许多国家已经相当普及,成为广播机构的重要投资场域。如果在新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中排除网络广播,将极大限缩条约的适用范围和制定意义,更甚者可能再步《罗马公约》的后尘;第二,不少国家的著作权法已经赋予广播组织网络转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条约缔结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代表肯定条约纳入网络广播的意义。
(三)域外经验: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实践
为了实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两项条约,强化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保护,欧盟于2001年通过了《信息社会中著作权和版权指令》(以下简称“《指令》”)。与目前保护广播组织的国际条约以及此前欧盟制定的广播组织权保护规定相比,该《指令》对广播组织提供的保护更加严格。首先,《指令》保护的对象不限于无线广播,同时将有线广播、卫星广播也纳入保护范围。《指令》第二条规定,广播组织就其通过无线、有线或卫星传输的广播的制品,享有授权或禁止他人复制的专有权。22. 参见《信息社会中的著作权与邻接权指令》第二条第5 款。其次,《指令》同时为广播组织规定了“提供权”,即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广播组织对其广播的固定享有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的专有权。23. 参见《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第三条第2 款(d)项。欧盟这一《指令》,及时把握住广播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扩张了广播组织权的权利范围,实现数字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力度的强化。除欧盟成员国外,瑞士等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都为广播组织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数字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提供了高标准的权利保护。如《瑞士著作权和邻接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广播组织有权通过任一媒介向公众提供其广播电视,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接收。《日本著作权法》对“无线广播组织”和“有线广播组织”均赋予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其第九十九条之二规定:“广播组织专有接收广播或者接收广播后进行有线广播,将广播内容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权利”;第一百条之4 规定:“有线广播组织专有接收有线广播并将其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权利”。
当然,域外规定对我国立法而言仅具有参考意义,是否为广播组织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应以本土需求为遵循。曾有观点认为,虽有部分发达国家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更多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自身文化产业的需要,并未将广播组织权延伸至网络领域,我国不应超越发展阶段规定这一权利。24. 参见许福忠:《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不应延伸至互联网领域》,载《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2 期,第44 页。但是将发展阶段作为我国著作权保护的标准,显得过于绝对。在没有国际强制义务的前提下,我国是否应当为广播组织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更应当关注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需求与著作权法公有领域的保护。报告显示,我国广播电视覆盖人口数居世界第一,广播影视制播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广播影视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25. 参见《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我国广播影视规模已居世界前列》,载《中国广播》2019年第8 期,第41 页。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强化广播组织权利保护,营造良好的广播电视产业生态,符合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发展实际情况。
三、以何设权: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依据
客体是界定权利的依据,是理解广播组织权不能回避的问题。广播组织权客体是广播组织权利制度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学界关于广播组织权客体的讨论激烈,集中表现为“节目说”和“信号说”之争。26. “节目说”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8 页;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 页。“信号说”则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射的“载有节目的信号”,参见王迁:《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兼析“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1 期,第 100-122 页;胡开忠:《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利内容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修正的信号说”为基础》,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 期,第39-50 页。遗憾的是,学理界和立法界对这一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我国著作权法在此次修订中也未对“节目说”和“信号说”做出明确选择,使这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解释和适用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必须正确分析广播组织权客体。
(一)反向推理:网络传播权对于界定广播组织权客体之意义
反向推理是填补规范漏洞的方法之一,适用于立法者有意或者依法律目的将法律后果仅仅适用于事实构成要件的情形,它是一种具有规范目的的评价活动。27. 舒国滢、王夏昊、雷磊:《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 页。从解释论视角看,在不明确广播组织权客体是A 还是B,由A 无法推导出规范效果C 但由B 可以推导出规范效果C 时,那么根据已经存在的C,可以对广播组织权客体属于A 还是B 进行反推。当前,广播组织权客体“节目说”“信号说”之争,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之间呈现出“内包蕴含关系”。28. “内包蕴含关系”是指特定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事实构成要件是其所规定的法律后果的必要条件,该事实构成要件已在法律规定中对所有可能产生法律后果的情形都被穷尽列举出来。换言之,有法律后果G 一定有事实构成要件F;而没有事实构成要件F,就没有法律后果G。参见舒国滢、王夏昊、雷磊:《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410 页。
权利客体是连接不同主体之间的媒介,29. 方新军:《权利客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 页。对权利客体的界定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一些学者基于“权利边界决定客体类型”的错误认知,提出广播组织应受保护的利益类型决定了其客体类型:一是“转播权”用于维护广播组织的瞬时利益,因此其客体为转瞬即逝的“广播电视信号”;二是录制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用于维护广播组织的延时利益,其客体则是具备延时性的“广播节目内容”。由此该观点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既包括“节目”又包括“信号”。30. 陈绍玲:《论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空间》,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 期,第70 页。事实上,这种广播组织权“双重客体论”的论证逻辑值得反思。首先,从体系化视角考察,广播组织的转播权、录制和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三类并列的权利,既属同一条款中的平行权利,其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必然具有一致性,否则将违反法律的体系化原则。其次,在法律逻辑上,“权利边界决定客体类型”不符合事实基础,因为权利的客体是权利设立的基础,31. 参见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 期,第36 页。客体的作用是界定权利。32. 参见梅夏英:《民法权利客体制度的体系价值及当代反思》,载《法学家》2016年第6 期,第29 页。因此权利客体是权利内容生成的依据,如果不明确法律保护的客体,就无法明确法律关系中不同主体的行为边界。质言之,广播组织者应当享有哪些权利,取决于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定位,因此更符合逻辑的研究思路是“权利客体决定权利内容和权利范围”。尽管2020年《著作权法》在处理广播组织权客体时试图搁置争议,但权利客体具有唯一性,立法者在决定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时,事实上就已明确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只是没有在法律条文中释明。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范围之内的一种情形,是对既有客观法律不明确之处的澄清。33. 陈辉:《论功能主义法律解释论的构建》,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6 期,第61 页。由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论基础是权利客体,因此根据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利内容推导广播组织权利客体,则属于法律推理功能的重要展现。相对于广播组织所享有的有线或无线转播权、复制权和录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于推导广播组织权客体而言更具有说服力:首先,“复制权”和“录制权”是《罗马公约》为广播组织设定的权利,而我国学者关于广播组织权客体的争论在《罗马公约》体系下已经存在;其次,转播权是“节目说”和“信号说”都主张的权利,因此尽管2020年《著作权法》将广播组织转播权扩展到网络转播领域,但该权利本身无助于解决广播组织权客体争议;最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此次修法中争议最大的权利,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论证基础各不相同。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基点进行“由权利到客体”的反向推导,对于解决2020年《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中广播组织权客体不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客体排除:“信号说”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相矛盾
在我国学理上,“信号说”源于SCCR 为制定《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而确立的“基于信号的进路”,也称为“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2019年,SCCR 编拟的《合并文案》将广播组织的保护对象确立为“广播组织播送的,或代表广播组织播送的,作为广播的载有节目的信号”,34. See Revised Consolidated Text on Definitions, Object of Protection, Rights to be Granted and Other Issues, SCCR/39/7, page 6.但不延及其中所载的节目。所谓“载有节目的信号”,是指通过电子手段生成、最初播送以及采用任何后续技术格式的载有节目的载体。35. See Revised Consolidated Text on Definitions, Object of Protection, Rights to be Granted and Other Issues, SCCR/39/7, page 5.2022年SCCR 拟议的最新《案文草案》将“节目信号”界定为“原始传输形式和任何后续技术格式的载有节目的电子生成载波”。我国理论界所持的“信号说”即来源于此,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SCCR 文件中的“载有节目的信号”。
然而,就“信号说”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而言,二者属于“互斥关系”。换言之,与“信号说”相对应的结论是反对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原因在于“信号”是能传播节目的电子载波,36. 参见《发送卫星传输节目信号布鲁塞尔公约》第一条。“载有节目的信号”在物理性质上是流动的,信号本身无法被固定、上传、点播和下载。37. 参见王迁:《对<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四点意见》,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9 期,第42-46 页。而信息网络传播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交互式传播”,也即公众能够将广播电视节目固定下来,上传到网络服务器中,供网络用户依其时间和地点自行点播和下载。故而根据信号传输的技术特征,“信号说”理论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本质内容相冲突,若认为广播组织权客体为“信号”,则无法得出广播组织应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结论。但也有代表认为,“广播电视信号”可以固定,但事实上能够“固定”的是信号中储存的信息,信号本身则仅具有瞬时性特征。既然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为广播组织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无论从立法论还是解释论看,都应认为我国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不是信号。
从国际立法来看,SCCR 选择“基于信号的进路”并不等同于“广播组织权客体是信号”。在《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制定之初,各国存在认知分歧,提出了“基于内容的进路”和“基于信号的进路”两种方案。38. See Lisa Mak, "Signaling" New Barriers: Implications of the WIPO Broadcasting Treaty for Public Use of Information, Hastings Commun.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30: 533, p. 540 (2008).SCCR 最终选择了后者,一方面力图有针对性地遏制信号盗窃行为,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聚焦重点问题,为条约的顺利制定积累更多共识。无论选择何种模式,对广播组织权利保护来说均只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不具有确定权利客体的功能。换言之,“基于内容的进路”和“基于信号的进路”都是强化广播组织权利保护的路径,无论选择何种路径都能够实现既定目标,至于SCCR 最终选择后者的原因,是考虑到不同国家对广播组织的保护模式存在差异,为了尽可能地缩小差异、凝聚共识、减少分歧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在将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基础上选择的方案。
除此之外,“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还面临着解释困境。信号是信息或数据的物质载体。传统的广播电视信号在法律上称为无线电频谱,而无线电频谱资源在法律属性上为物权客体,属于国家所有。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五十二条确定了无线电频谱资源的物权属性,其所有权归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我国民法学者认为,无线电频谱资源,也称为频率资源,一般指9KHz-3000GHz 频率范围内发射无线电波的无线电频率的总称,它是一种自然界存在的电磁波,是一种物质。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释义和立法解读》,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 页;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0 页。SCCR 特别强调《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保护的是“载有节目的信号”,表明并非所有的信号都受广播组织权保护,只有承载广播电视数据、图像或声音的电磁波,才是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对象。但在文义上,其案文落脚点终究是“电磁波”而非电磁波中的节目信息。如果由此认为广播组织权客体是作为物质形态的信号,将直接与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特性相违背。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国家承认“物质材料”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美国之所以通过保护“信号”的方法为广播组织提供法律保护,其原因在于美国并不承认广播组织属于版权法主体。美国学者在《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制定过程中就极力反对,认为美国加入《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将对美国版权制度产生重大转变:首先,它将促使在其版权法中加入一个新的权利主体,从而破坏美国版权法的现有结构;40. See Letter from Patrick Leahy, Chairman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and Arlen Specter, Ranking Republican Member, to Hon. Marybeth Peters, Register of Copyrights, and Hon. Jon Dudas, Director of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r. 1, 2007), at http://www.keionline.org/misc-docs/broadcast-treaty.pdf (Last visited on August 28, 2022).其次,美国学者认为此举将违反美国版权法中的“独创性”要求,因为广播机构只是传播他人创作的作品,并不由此产生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最后,赋予广播组织以若干年保护期限,也将严重阻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41. See Lisa Mak, "Signaling" New Barriers: Implications of the WIPO Broadcasting Treaty for Public Use of Information, Hastings Commun.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30: 533, p. 543-544 (2008).为解决上述担忧,后来美国成功说服SCCR 大会将条约的范围缩小到保护广播公司信号免遭盗窃所必需的条款。42. See Marlee Miller, The Broadcast Trea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ignal Piracy in North America, Business Law Brief (Am. U.), Vol. 4: 33, p. 36 (2007).由此可知,美国从最初反对制定《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到主张“基于信号的进路”,都是由美国版权法律结构和版权立法传统所决定的。与此相同的是,欧盟代表主张为广播组织纳入网络转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有其本土立法实践为支撑:一是认可广播组织的版权法主体地位,二是认可强化广播组织权利保护的必要。然而相比之下,我国学者主张以“信号”为基础设计广播组织权制度,弱化广播组织权利内容,既不符合我国立法实际,也不符合本土产业发展需求。
(三)客体确认: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以“节目说”为基础
“信号说”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难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得以证立。根据网络传播技术特性,能够在信息网络空间进行传播的,只能是某种非物质化的信息,而非信息的载体。43. 刘文杰:《互联网时代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3 期,第15 页。广播组织能够据以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基础是“非物质化的信息”,这与知识产权“客体非物质性”这一本质特性相契合。44. 参见吴汉东:《无形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 页。根据体系解释,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特定信息”与著作权人创作的作品、音像制品制作者制作的音像制品具有非同质性,否则将冲击广播组织作为独立的邻接权主体的地位。SCCR 所主张的“载有节目的信号”明确了信号中的信息——广播电视节目,即由广播或电缆传播播送者向公众提供的声音,图像序列或音像序列。45. 【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1 页。在我国,“节目说”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是因为“广播电视节目”的属性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曲解:
曲解一:认为“广播电视节目”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而非邻接权客体。46. 参见胡开忠:《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利内容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修正的信号说”为基础》,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 期,第41 页。有学者在解释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时认为,在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制度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的意义不大,对于未经许可交互式传播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广播组织者完全可以依据其与著作权人、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签订的合同,享有对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此规制侵权行为。47. 参见陈绍玲:《论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空间》,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 期,第70 页。这实际上不仅造成了“广播电视节目”和“作品”“音像制品”之间的混同,而且混淆了不同主体所付出的不同劳动,从而将广播组织通过广播行为向公众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等同于未经加工的作品、音像制品等节目素材。这种理解对广播电视节目的属性产生误读,将广播组织的劳动过程“简单化”“机械化”和“僵硬化”,否定了广播组织的劳动投入和投资价值。从广播电视节目和节目素材的关系来看,广播电台、电视台首先对被授权播出的作品、制品或者其他节目材料享有“播放权”,该权利来源于著作权人、音像制品制作者或者表演者等主体的授权许可;但是,广播组织在广播过程中,不仅需要对作品、制品或者其他节目材料进行编排,而且需要通过信号加工和传输,实现“节目素材——信息流——视听画面”的转换。公众最后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接收到的节目(包括声音与画面),包含了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劳动和技术投入,才属于广播组织的劳动成果。因此,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出来的、公众到接收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垄断利益,而不是对被授权播出的作品、制品或者其他节目材料享有垄断利益。实际上,广播电视“节目”并不等同于“节目内容”,节目内容是指被传播的作品/制品,而“节目”是广播组织对已有作品/制品的传播而产生的新的内容。48. 参见冯晓青、郝明英:《<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及权利构造——兼评<著作权法>第47 条》,载《学海》2022年第2 期,第187 页。将广播电视节目视为作品的错误在于:广播电视节目是广播组织对作品等节目、音像制品等素材加工处理的结果,是向公众传递出的节目声音和画面的组合,不具有独创性,不能将其视为作品。而广播组织对其自己制作的《动物世界》《星光大道》等作为“作品”的节目,在向公众播放之前已经存在著作权,广播组织对这些“节目”是否享有邻接权,取决于广播组织是否将“节目”中的声音和画面传递给公众。
曲解二:认为广播组织仅基于播放行为而获得邻接权保护的正当性不足。该观点认为广播组织只是作品、音像制品的机械搬运者,其对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除了添加“台标”之外,再无添加任何新内容,而广播组织对节目的播放所形成载有节目的信号,才是其获得广播组织权的依据。49. 参见王迁:《对<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四点意见》,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9 期,第42-46页。这一观点同样无视广播行为的技术属性,否认广播组织的劳动价值和经济投入。事实上,对广播组织而言,信号作为节目信息的传输载体只具有工具意义,只有信号中的信息才是投资对象。简言之,信号中立,信息有价。广播组织只是信号的利用者,但“利用信号”只是广播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尚不能称为对节目传播作出的贡献,广播组织只有运用信号将打包完成的节目信息传递到观众面前,才完成了整个投资过程。在“北京冬奥会体育赛事节目盗播行为保全”案件中,法院认定被申请人因“向公众提供冬奥会赛事节目的在线直播”而构成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其理由并非“盗窃节目信号”。50.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2)沪0115 行保1 号裁定书。同时在我国,干扰或屏蔽正常广播信号的行为,属行政违法行为而非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曲解三:认为广播组织完全能够以“非画面保护途径”获得权利保护。如有学者认为,广播组织能够以作品著作权人的身份主张自制节目的著作权保护,以录制者的身份对不构成作品或元素主张邻接权保护,以被授权人的身份对被授权节目主张合同权利。51. 袁锋:《新技术环境下广播组织权的问题与完善——兼评最新<著作权法>第47 条》,载《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 期,第109-119 页。此种观点本质上也属于对广播组织权的正当性认识不足。广播组织者当然能够基于作者身份主张自制节目的著作权保护,但此时广播组织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其权利来源于“创作作品”;而广播组织基于“传播作品”行为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邻接权,与基于创作行为获得著作权保护并不矛盾,两种行为和两种成果在法律上并不难区分。事实上,一个主体在社会关系中通常都充当着多重角色,法律不应对其社会角色设置限制。而以录制者、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之说,同属此类误解。因此,只要承认广播组织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中做出了贡献,就这个贡献而言应获得多少权利,取决于立法者的考量,立法者赋予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会引发法律逻辑困境。52. 参见张伟君:《论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关系——兼谈<著作权法>第47 条(广播组织权)的解释论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3 期,第91 页。
从技术上说,“节目”是广播组织活动的综合体,因而更接近受保护的客体。53. 【法】克洛德·科隆贝:《世界各国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基本原则:比较法研究》,高凌翰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 页。在“三网融合”背景下,公众可以利用网络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电视点播、回放观看电视节目,为了防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或录制广播电视节目后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为广播组织设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源,来自于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而最终向公众播放出来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节目声音和节目画面,这与著作权人对其作品、音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制品所享有的权利存在本质不同。按照这种“由权利到客体”的反向推导,可以论证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视节目”。
四、如何设权: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构造
以2020年《著作权法》第十七条为立足点,从解释论视角分析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有助于明确该权利的规范构造:一方面,基于该权利明确广播组织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的专有权边界;另一方面,围绕当前学界对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的“许可权”或“禁止权”性质争议,明确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许可模式。
(一)专有范畴:控制广播电视节目的交互式传播
1.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旨在规制广播电视节目“后续播放”
广播组织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专有权利,广播组织可以依据该权利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地使用。表现在行为范畴上,广播组织可以禁止他人对广播电视节目实施“交互式传播”。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赋予的“播放权”,既涵盖实时播放,包括有线和无线转播权,也涵盖后续播放,包括录制和复制后的播放以及通过信息网络进行的“交互式传播”。在《著作权法》修订之前,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人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该权利来源于WCT 第八条5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第八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和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以获得这些作品。”中的“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WCT 第八条为著作权人规定了两项权利,包括“广播权”(即该条款前半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和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和“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二者共同构成了理论意义上的“向公众传播权”。其中“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的内涵是“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以获得这些作品”。55. 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第八条后半段之规定。这是我国《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来源。此处的“信息网络”为广义上的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等各类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5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11 月26 日通过,2020年12 月23 日修正)第二条之规定。这与WCT 第八条对未来技术发展保持开放性的做法相一致。57. 参见刘银良:《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与广播权的界限》,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6 期,第101 页。信息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公共性、非同步性和交互性的特点,58. 参见【美】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网络空间的法律道德》,李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 页。其中开放性和公共性构成了“向公众传播”的基础,非同步性和交互性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区分于“广播权”的重要特征。在2020年《著作权法》中,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界限明显,二者的区分标准就是“交互式传播”与“非交互式传播”之分。
2.广播组织基于权利专有性控制广播电视节目的“交互式传播”
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著作权人的网络传播权除客体不同外,二者所规制的行为相同。在“三网融合”背景下,观众对广播电视节目的收看拥有更多自主权,人们不仅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定时收看节目,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点播、回看广播电视节目,一定程度上看,广播组织在对其播放的节目降低了主导力量;59. See Current Market and Technology Trends in the Broadcasting Sector, SCCR/30/5, page 6.此外,如果公众将非法录制或复制下来的广播电视节目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传播,不仅将给著作权人和广播组织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无法维护广播组织机构的投资利益,而且还将导致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质量日益低下的恶性循环,无益于增进社会公共福利。此即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设立的现实依据。进一步而言,广播组织权的目的在于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广播组织因播送广播节目所付出的技术性、组织性和经济性投资得到回报,因此在具体权利设置上,如果将“有线和无线转播行为”纳入广播组织权利体系,从而使广播组织能够控制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网络实时转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通过信息网络手段传播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排除在广播组织的权利控制范围之外,因为“交互式”传播使广播电视节目在网络空间中保留的时间更长、传播范围更广、受众更多,他人针对广播电视节目非法实施的“交互式”传播行为给广播组织造成的损失比“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更大。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增设信息网络传播权,意味着广播组织者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点播、回放等非交互式传播行为享有控制权,那么公众通过电视点播、回放观看的方式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落入到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涵摄范畴。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网络转播权”共同承担着规制网络环境下以“交互式传播”和“非交互式传播”方式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功能。2020年《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增设的这两项权利,对于遏制“三网融合”发展趋势下的广播电视节目盗播行为、维护广播组织机构劳动成果和投资利益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前述关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范围的“否定论”“怀疑论”“限缩论”等观点,将架空《著作权法》的现有规定,有违“有效解释原则”。60. 参见张伟君:《论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关系——兼谈<著作权法>第47 条(广播组织权)的解释论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3 期,第95 页。
(二)许可模式:对节目交互式传播的“有限许可”
1.“有权禁止”不排除广播组织对其广播电视节目享有许可权
《罗马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广播组织应当有权授权或禁止转播其广播节目”,这实际上赋予各缔约国可以采用“许可权”或者“禁止权”的模式规定广播组织权。对于广播组织权的权利性质,国际知识产权法专家存在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广播组织权的权利性质为“专有权”,包括转播、录制以及在收费场所公开传送广播的权利;61. 【法】克洛德·科隆贝:《世界各国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基本原则:比较法研究》,高凌翰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 页。而也有学者认为,授予广播组织(准许复制或向公众传播其节目)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或第三者可免去作者、表演者和制作者的授权,除非实施强制许可制。62. 【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4 页。尽管我国没有加入《罗马公约》,但根据TRIPS 协定的规定,我国需要承担《罗马公约》所规定的实体义务,而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广播组织权的规定也主要来源于这一公约。2020年《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采取“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的表述,通过行为列举的方式为广播组织规定转播权、录制和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据此,有学者认为广播组织权属于“消极的禁止权”,63. 参见王昆伦:《从我国广电实践重新审视广播组织权制度》,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年第7 期,第21 页;闫书芳:《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吗》,http://www.cipnews.com.cn/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125499,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 月31 日。只能消极地禁止他人以非法手段实施上述行为,但不具有主动许可他人转播、录制、复制或者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属性;64. 参见秦俭:《互联网环境下广播组织权与著作权的利益冲突与平衡——以“网络转播权”的利益分配为例》,载《电子知识产权》2019年第5 期,第26-36 页。或认为除非有相反的明确约定或授权,对包含他人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的广播、电视,广播组织不得复制发行、重播或许可他人播放其已经录制的包含他人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的广播、电视。65. 参见管育鹰:《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内容的综合解读》,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9 期,第3-16 页。但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回归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组织权条款,对“禁止未经其许可的行为”进行逻辑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经广播组织许可,他人可以实施某种行为,即广播组织有权许可他人实施某种行为;(2)未经广播组织许可实施某种行为,广播组织有权要求该行为人停止侵权。据此,从广播组织与广播电视节目被许可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广播组织有权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许可给他人传播。然而,《著作权法》为何不以“专有权”的形式为广播组织赋权?这是由广播组织权的生成机理所决定的,同时该机理也影响着著作权人和广播组织、其他邻接权主体、广播电视节目被许可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2.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有限许可”属性的机理及体现
《著作权法》为他人传播广播电视节目设定了义务,即禁止未经广播组织许可的转播、录制、复制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从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看,与他人所负有的义务相对应的,属于传播组织权利所及范畴。这意味着广播组织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转播权、录制和复制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组织自身可以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第三项的规定自主实施与上述权利相对应的传播行为。而从许可权的角度看,广播组织所享有的许可权属于“有限许可”。广播组织所编排和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中包括各类作品信息、不构成作品的音像制品信息以及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其他材料信息。作品、音像制品的“再现”由著作权人、音像制品制作者所垄断,由于著作权法的规定或者在先合同约定,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属于对前述作品或者音像制品的合法再现。但是,他人未经许可对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进行转播或者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既是对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广播电视节目的非法再现,也是对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作品、音像制品以及相关表演活动的非法再现。这意味着,在广播电视节目之上当然地存在着一层属于著作权人、其他邻接权主体的权利,他人对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和利用,既影响广播组织的利益,同时影响相关著作权人、其他邻接权主体的“底层权利”。但《著作权法》同时保护广播组织和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意味着重复保护,也不会产生权利边界不明的问题。由于二者的权利来源不同,即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来源于作品创作行为,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来源于作品传播或者作品加工行为,二者的劳动属性及劳动结果差异明显,由此所形成的两种权利在边界上十分清晰。只不过一些广播电视节目中包含着作品,他人对广播电视节目的利用自然包含着对该作品的利用,此时需要获得著作权人和广播组织的双重许可。这表明广播组织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许可权”,只是这种许可属于“有限许可”,具体情形包括:
情形一:若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中没有包含他人创作的作品或制作的音像制品,或该节目素材完全来自于公有领域,那么广播组织可以直接将该广播电视节目许可给他人使用;
情形二:若广播组织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中包含他人创作的作品或制作的音像制品,那么被许可人在同时获得相关著作权人、其他邻接权主体、广播组织的许可时,可以转播、录制、复制或者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视节目;
情形三:如果广播组织事先与著作权人、音像制品制作者以及表演者等主体约定,获得以“转授权”方式许可他人以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利用广播电视节目中包含的作品或制品的权利,那么被许可人可以直接依据其与广播组织之间的约定传播该广播电视节目;
情形四:如果著作权人、音像制品制作者以及表演者等主体拒绝广播组织以“转授权”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或制品,那么广播组织此时对其播放的包含他人作品或音像制品的广播电视节目仅享有“禁止权”。
上述情形表明,广播组织权利内容一定程度上受广播组织与作者或其他邻接权主体之间的协议内容影响。广播组织首先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禁止权”,在所有情形下都有权禁止他人非法利用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其次,如果广播组织基于其与作者或其他邻接权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对“底层权利”享有“转授权”的权利,那么广播机构则能够授权他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播放其广播电视节目,此时并不存在影响、限制或侵害“底层权利”的风险。我国一些学者对广播组织权利内容进行综合解读时就持此种观点。66. 例如有学者认为:“广播组织对不包含他人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的由其自己制作和播放的广播、电视,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也可许可他人以《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各种方式使用;对包含他人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的广播、电视,广播组织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以《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各种方式使用,但除非有相反的明确约定或授权,广播组织不得复制发行、重播或许可他人播放其已经录制的包含他人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的广播、电视;对未经许可使用包含他人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的广播、电视的行为,著作权人、录制者和广播组织均可请求禁止。”参见管育鹰:《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内容的综合解读》,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9 期,第3-16页。从体系上看,《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不得影响、限制或者侵害”条款就是对广播组织权“有限许可”属性的阐释。广播机构对其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自然适用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
五、权利协调: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平衡
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权利限制”属性,主要表现为该权利的行使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限制。更进一步来说,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对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限制。此外,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引入还面临着“侵蚀公有领域”的质疑,可能产生著作权法实施的制度性风险。对此有必要在相关制度之间寻求协调或化解之策。
(一)法定许可:扩展“广播组织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
1.该权利对“广播组织播放作品法定许可”的影响机理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是与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密切相关的一项制度。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67. 参见我国《著作权法》(2020)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这里的作品是指除视听作品之外的其他作品,视听作品被排除适用该制度。68. 参见我国《著作权法》(2020)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由于《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前,广播组织仅享有无线转播权,广播组织播放作品的行为属于广播行为,因此该制度也被学者称为“广播权法定许可制度”。69. 参见刘银良:《我国广播权法定许可的国际法基础暨修法路径》,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2 期,第163-180 页。从文义上分析,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是对著作权人广播权的限制,这与2020年《著作权法》实施之前广播组织所享有的“无线转播权”相对应。
广播权法定许可制度具有正当性。第一,法经济学认为,法定许可制度的优势在于降低权利流转带来的交易成本。70. 参见熊琦:《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溯源与移植反思》,载《法学》2015年第5 期,第72 页。对广播组织而言,其为制作广播电视节目需要使用数量较大的作品,但由于广播电视节目时效性强,制作周期短,广播组织通常无法及时获得著作权人许可,而只有依靠广播权法定许可方能解决所涉作品的著作权问题。71. 王昆伦:《广播电视网络同步播放中的版权问题研究》,载《中国广播》2014年第9 期,第38-40 页。第二,从著作权法所期实现的法律目标来看,广播权法定许可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打破权力垄断、保障公众信息获取权,也有助于著作权人获得合理报酬。72. 胡开忠:《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问题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载《知识产权》2013年第3 期,第3 页。第三,从国际公约视角考察,《伯尔尼公约》第十一之二条第三款规定了与广播权限制相关的临时录制事宜,可视为广播权法定许可的国际法基础。73. 刘银良:《我国广播权法定许可的国际法基础暨修法路径》,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2 期,第166 页。第四,WCT 第八条在规定“向公众传播权”时,也在第十条规定了相应的“限制与例外”,即在不影响作品正常利用,也不无理损害作者合法利益的情况下,缔约方可在立法中对作者权利规定限制或例外。74. See WIPO Copyright Treaty (adopted in Geneva on December 20, 1996), Article 10,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此即广播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基本依据。
然而与修订前的《著作权法》相比,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增设网络转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组织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控制不再局限于“非交互式传播”,并因此享有更多法定利益。那么,“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否因为2020年《著作权法》的通过而从广播权领域扩张至包括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向公众传播权”领域呢?有国外学者认为,对广播权的限制应仅限于初始无线广播行为,75. See Mihaly Ficsor, The Law of Copyright and The Internet: The 1996 WIPO Treaties,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ras. C8.05-C8.07.不适用于初始有线广播和网络直播行为,更不能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但也有观点认为,广播组织基于法律规定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自动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于广播电视节目中包含着作品,且广播组织在播放广播电视节目时无需事先获得著作权人对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许可,因此广播组织在事实上享有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由此可见,作为一项新权利,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必然对著作权法中的相关制度产生影响。如何理解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回到《著作权法》相关条文之中。
2.该权利扩张了“广播组织播放作品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
从解释论视角分析,“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否延伸至“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首先应当正确理解“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中的“播放”一词的含义。在许多国家的《著作权法》中,“播放”被界定为借助无线电波对声音或合成音像的传送;76. 【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1 页。《罗马公约》第三条f 款规定,“广播的播放”是指供公众接收的、通过无线电波对声音或音像的传播。77. 参见《罗马公约》第三条第f 款之规定。当然这种理解具有历史性,因为随着“三网融合”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节目的播放已经不再局限于“无线电波”。不过“对声音或音像的传播”作为这一概念的核心要素并没有发生变化。“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中的“播放”可以理解为“对声音或音像的传播”。
广播组织通过广播手段向公众传播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当然属于“播放”,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视节目是否属于“播放”的涵摄范畴却需要解释。从WCT 第八条以及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看,其核心要素在于“向公众提供作品”,从而使公众能够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收看或下载。尽管“提供行为”和“播放行为”都具有“传播”含义,但“提供广播电视节目”在文义上并不直接等同于“播放”。广播组织主动以数字形式将广播电视节目保存或者上传至网络服务器中,其间并没有产生“主动播放”这一事实行为。然而,广播组织传播广播电视节目的主要形式却是播放,其向公众提供广播电视节目并不是目的,只有播放广播电视节目才能吸引受众、收回成本并从中获益。就此而言,提供行为是播放行为的手段,播放其广播电视节目才是提供作品的最终目的,因此“播放行为”能够被“提供行为”所吸收,信息网络传播处于“播放”一词的涵摄范畴。质言之,信息网络传播旨在规制广播电视节目的“后续播放”问题,以信息网络方式传播广播电视节目时不可能规避播放行为,受众每通过网络点播、电视回放等途径收看广播电视节目,都包含着一次播放行为。立法者在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时,必然预想到广播电视节目的后续播放问题。由于广播组织基于法律规定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从而在事实上享有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因此,“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播放”应当做扩张解释,其既包括广播行为,也包括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上述结论可通过目的解释予以检视。有学者认为以非自愿许可名义进行的转播之所以应当是“同时进行而且不加修改”的转播,其原因是那种“录后广播”与《伯尔尼公约》中提及的“公开传播”相差甚远。78. 【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89 页。但这种理解具有历史性,非自愿许可之所以仅适用于“同步转播”,主要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而在传媒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制度要求应当有所变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目标在于减少交易成本。“有线和无线转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都是2020年《著作权法》中的广播组织权,其中“有线和无线转播权”与广播行为相对应,“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相对应。既然广播作品需要“范围广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作品,那么通过信息传播广播电视节目自然也需要以“范围广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作品”为基础。如果“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不能延伸至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广播组织将一边适用广播权法定许可制度播放作品,另一边还要与著作权人另行谈判广播电视节目的后续播放问题,这非但没有降低广播组织与著作权人之间的谈判和交易成本,甚至还将导致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被架空。
从国际立法来看,将“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延伸至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也不存在障碍。WCT 第八条在规定“向公众传播权”的同时,也根据《伯尔尼公约》第九条第二款所确定限制和例外的“三步检验法”,在其第十条规定了限制和例外条款,并将它扩大适用于所有的权利。79. WIPO. Summary of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 (1996), at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ip/wct/summary_wct.html,(Last visited on August 30, 2022).在《WCT 条约议定声明》中,各缔约国认为该“限制与例外”应继续适用并适当地延伸到数字环境中。80. 完整声明为“不言而喻,第十条的规定允许缔约各方将其国内法中依《伯尔尼公约》被认为可接受的限制与例外继续适用并适当地延伸到数字环境中。同样,这些规定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方制定对数字网络环境适宜的新的例外与限制。”See Agreed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adopted by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December 20, 1996), Agreed statement concerning Article 10.因此,将“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延伸至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与国际条约的规定并不冲突。
3.该权利的“权利限制”属性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不冲突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是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律制度,其对著作权人而言是一项权利限制制度。由于广播组织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张,其不仅是对著作权人广播权的限制,同时也是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然而,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增设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同时,还在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增设了一项规定:“电台、电视台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不得影响、限制或者侵害他人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8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那么广播组织因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造成的限制,是否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相矛盾?
从体系解释视角分析,“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属于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它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不矛盾。首先,从《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与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关系看,二者均由法律直接规定且处于平行关系,前者属于“著作权权利限制”条款,为例外性条款,后者属于“禁止限制著作权”条款,为原则性条款。根据“原则之中允许存在例外”的理念,例外应优先于原则适用。这意味着,《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行为,不受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约束,此时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应当解释为“电台、电视台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不得影响、限制或者侵害他人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其次,《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属于紧急立法的产物,如果认为广播组织因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造成的限制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相矛盾,那么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就属于对四十六条第二款的限制,这意味着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前已经存在的“广播权法定许可制度”将不复存在,这不仅动摇了我国著作权法的制度框架,也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违背。再次,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是对广播组织“行使权利”的限制,而根据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广播组织权的属性为“有限许可”权。“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并不意味着广播组织享有以“转授权”方式将广播电视节目中所包含的作品、音像制品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传播。在广播组织与被许可人的关系上,广播组织在授权他人以信息网络方式传播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时,仍然属于“有限许可”,此时被许可人还应取得著作权人、音像制品制作者以及表演者等主体的授权。因此《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主要是针对广播组织在许可他人传播广播电视节目所做出的规定,而非对其自行播放广播电视节目所做出的限制。《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可视为对四十七条第一款“禁止未经许可”表述所作出的补充和说明,旨在进一步说明广播组织权的“有限许可”属性。最后,从权利基础和权利范围来看,广播电台电视台对“节目的播放”所享有的权利,与著作权、其他相关权人对作品、音像制品、表演活动享有的权利本身就是不同的,82. 刘云开:《广播组织权客体之再辨析——兼评我国新<著作权法>第47 条》,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11 期,第27 页。《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实际上属于多余条款。即使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权利限制”属性,其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并不冲突。
4.应适当提高广播组织播放作品的付酬标准以平衡不同主体利益
目前,我国未就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发表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制定相应的付酬标准,而是在2009年11 月仅就播放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问题出台了《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8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9-11/16/content_591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8 月1 日。在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发表作品适用法定许可制度如何付费问题上,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第三十条对此做出规定,确立了“以约定报酬优先,以法定付酬标准为补充”的付酬方案。84. 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按照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由于缺失具体付酬标准,因此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发表作品主要以合同约定形式付酬。然而,由于广播组织与著作权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作者获酬权可能难以保障。85. 彭桂兵、朱雯婕:《论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的存与废——基于立法价值的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 期,第88 页。对此国务院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发表作品的付酬标准》,或者在正在修订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提供具体操作方案,明确付酬标准和救济措施,从而降低著作权人因权利限制而产生的利益损失。与此同时,“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制度”扩张适用至信息网络传播权,除限制了著作权人的广播权之外,还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造成限制,由此打破了著作权人和广播组织之间原有的利益平衡关系: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前,广播组织通过“无线转播方式”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基础是广播权的法定许可,广播组织只需按照广播作品的付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作品使用费;而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后,广播组织还能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相应地,广播组织应当按照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方式播放作品的付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作品使用费。也即,广播组织应当在原有支付作品使用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作品使用报酬,以补偿著作权人因信息网络传播权受到限制而产生的损失。尽管许多情况下,广播组织播放作品时按照使用作品的数量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在合同中以笼统的方式约定作品使用行为,但这种付酬标准多是以广播组织不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为前提的。但当广播组织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时,广播组织将从这种权利扩张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其利益基础包含着著作权人因创作作品而付出的劳动。在此情形下,广播组织应适当支付给著作权人更多作品使用费,以此实现双方利益平衡。
(二)公有领域: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侵蚀公有领域观”及回应
2020年《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增设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另一质疑是此举可能损害著作权法中的公有领域。公有领域是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领域,处于该领域的智慧成果可以为社会公众自由利用。86. 胡开忠:《知识产权法中公有领域的保护》,载《法学》2008年第8 期,第64 页。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超过保护期限的作品因进入公有领域而可以被公众自由利用。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就有学者担忧,广播组织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使广播组织对他人制作的节目,甚至是公有领域的作品在播出后获得保护期长达五十年的专有权利,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87. 王迁:《对<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四点意见》,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9 期,第44-45 页。美国学者最初反对美国加入《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谈判的原因之一,也是认为赋予广播机构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以时间期限将对版权公共领域造成限制。他们认为,这将允许广播机构通过简单播放行为对公有领域的材料获得额外权利,使公有领域的材料变为私人专有权利,这违反版权制度“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终极目标。88. See Matthew D. Asbell, Comment and Recent Development: Progress on the WIPO Broadcasting and Webcasting Treaty,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4: 349, p. 361 (2006).
上述担忧的实质是认为赋予广播组织对广播电视节目以专有权,将降低公众从公有领域中获取作品的机会。通常而言,作品、音像制品进入公有领域后,可以为公众自由获得和使用,从而实现知识传播与知识共享的立法目标。89. 参见李建华、梁九业:《我国<著作权法>中公有领域的立法构造》,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 期,第40 页。但是截至2021年底,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等播出机构2542家,90. 参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http://www.nrta.gov.cn/art/2022/4/25/art_113_6019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 月20 日。如果认为每一个广播机构在首次播放作品,甚至每一次播放作品后,都对其播放的包含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五十年的权利期限,那么公众利用该作品的空间就被大大压缩。尤其是当该作品进入公有领域,著作权人无法对该作品享有财产权利,广播组织却能够通过播放该作品而实现对包括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控制,可能会引起著作权人的不满,因此上述担忧不无道理。
对此,有学者提出协调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公有领域保护冲突的路径,认为由于邻接权依附于著作权,根据邻接权权利范围不得大于著作权权利范围的原则,当一个作品进入公有领域后,广播组织亦不得对该作品以及包含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任何垄断利益,由此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有领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种观点尽管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公有领域,但是“邻接权权利范围不得大于著作权权利范围”这一前提难以经得起推敲。邻接权尽管与作品传播密切相关,但其亦具有相对独立性,著作权法基础理论中并没有“邻接权权利范围不得大于著作权权利范围”的要求。对超过保护期限的作品而言,表演者能够通过对该作品的表演而享有表演权、音像制品制作者也能够通过录制活动享有音像制品制作者权,相应地,广播组织通过播放该作品从而对包含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广播组织权并无理论障碍,因此邻接权与著作权的权利范围不存在孰大孰小的区别。由于在大前提上存在错误,因此这一路径不具有可行性。
事实上以笔者之见,为广播组织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足以侵蚀著作权公有领域。首先,无论从产业需求还是立法实践看,应当承认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价值。广播组织在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过程中做出了相应贡献,广播电视节目中也承载着广播组织的投资利益,根据传统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应当赋予广播组织一定期限以维护其广播投资。“三网融合”背景下,广播组织者的投资向网络领域延伸,导致广播投资的增长。借助网络技术,广播电视节目的保存更加便捷、保存时间更长,广播组织的预期利益更多,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产业和立法的双重选择,不宜否定。其次,我国通过“首次播放”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期限予以限制,有助于维护著作权法中的公有领域。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12 月31 日。”这说明在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期限上,立法者强调将“广播、电视”的“首次播放”作为广播组织权保护期限的起算点。“首次播出”作为对广播组织权的时间限制,能够最大程度地预留公有领域空间,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再次,“侵蚀公有领域”的观点仍将“节目”与“节目内容”混为一谈。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从与广播机构相同的来源自由获取和使用属于共有领域的作品或材料。91. See 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 Negotiations on Broadcast Treaty Raise Concerns (Sept. 8, 2006), at http:// www.cdt.org/publications/policyposts/2006/16 (Last visited on August 24, 2022).如果认为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将限制公有领域,那么相应的,包括广播组织转播权、出版者权、表演者权、音像制品制作者权的各类邻接权也将同样面临着侵蚀公有领域的问题。92. 参见张伟君:《论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关系——兼谈<著作权法>第47 条(广播组织权)的解释论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3 期,第91 页。最后,即使面临“作品仅由广播机构保存,公众难以获取”这一极端情形时,也不应对广播机构予以苛责,这是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中缺乏“作品获取权制度”所导致的。在我国著作权法制度下,“保护版权技术措施”与“维护公众作品获取权”之间也呈现出此种紧张关系,其解决之道在于,立法者可以要求广播机构或技术措施实施者在特殊情形下向公众提供相应作品。
六、结语
2020年《著作权法》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符合“三网融合”技术发展的趋势以及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现实。本文基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梳理了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背景、客体依据、规范构造及其对著作权法中其他制度产生的影响与协调路径。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涉争议,是因广播电视节目渗入了广播组织、著作权人、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等众多主体的劳动而致,但这并不影响广播组织邻接权主体的独立性,也不影响《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正当性。可以预测,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今后的实践中不会面临较多适用困境,因而“限缩适用论”“有限适用论”等观点将不攻自破。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更重要的问题是厘清广播电视节目中所含“权利层”。通过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正确适用,将充分实现尊重广播组织的劳动价值、有效维护数字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技术投资的制度目标,同时平衡广播组织与著作权人、音像制品制作者、表演者乃至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和版权产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