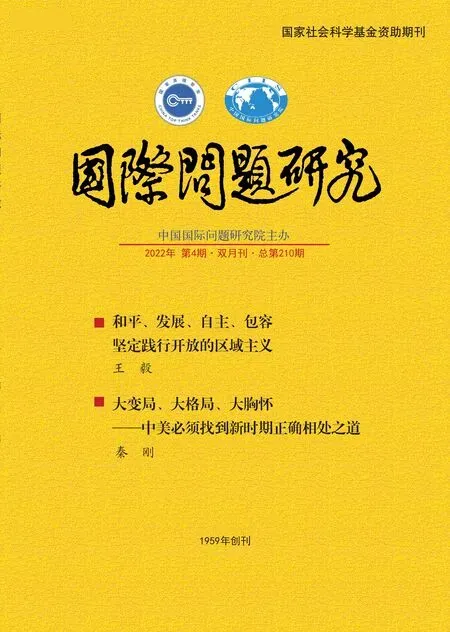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
张 帅
〔提 要〕粮食安全合作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议题。中国与对象国建立的多元伙伴关系、构建的多样化合作机制、制定的多领域合作政策、实施的多类型合作项目,为全球发展倡议在粮食安全领域的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仍面临粮食安全关联性危机频发、农企资金压力大、对象国营商环境欠佳、粮食安全合作领域失衡等诸多制约。中国需创新粮食安全合作模式,应对企业融资困境,并建立海外风险评估体系,加强危机预警。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还需构建以粮食安全为中心的系统合作机制,从粮食危机管控、数字农业、生态农业、减贫兴农等领域拓宽合作议题,助力全球粮食体系转型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自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气候极端化加剧、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全球经济疲软等多重因素叠加,削弱了全球粮食体系的韧性和弹性,以粮食安全为特征的发展赤字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中,粮食安全为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1]《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版。在全球发展倡议下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既是破解发展赤字的主要抓手,也是构建粮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还将服务于联合国2030“零饥饿”目标的实现,成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一、全球粮食安全的现实境况
粮食安全兼具安全和发展问题属性,既是以战略资源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影响地区稳定、国家安定和个人生存,也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课题,与经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密切相关。[2]张帅:《民生为先:当代中东粮食安全问题及其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5期,第149-152页。粮食安全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并不乐观,粮食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2021年入夏以来,干旱、洪涝、山火等极端天气频发,制约了美国、巴西、加拿大等粮食出口国产量的提升,加重了伊朗、苏丹、阿富汗、索马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多国的粮食安全困境。2021年,全球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较2020年增加约7360万,其中亚洲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约增加3750万,非洲约增加2150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约增加980万。[3]FAO et al.,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Repurposing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to Make Healthy Diets More Affordable, Rome: FAO, 2022, p.26.此外,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黑海地区的粮食运输严重受阻,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2022年6月全球谷物价格指数平均为166.3,虽环比下降4.1%,但仍同比上涨27.6%。[4]“The FAO Food Price Index Drops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Month in June,” FAO, July 2022, 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从供给、获取和利用三个衡量粮食安全程度的指标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供给角度看,粮食供需差额不同,但整体供应趋紧。这可从地区主粮生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化中管窥。在小麦方面,从2018/19年度到2020/21年度,中东、非洲、南美、南亚等地区的小麦消费量均高于生产量,且除南亚外,其余三地的小麦消费量始终保持增长趋势;但同时,这三个地区的小麦生产量却直线下降。[1]“Grain: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ebruary 2022, 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circulars/grain.pdf.在大米方面,南美、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在2018/19、2019/20、2020/21三个年度的大米产量能够满足当年的消费需求,而中东、非洲、中亚和东欧等地区则存在大米“赤字”问题,尤以非洲最为严重,其消费量和生产量差额在上述三个时段均达上千万吨。[2]Ibid.在玉米方面,从2018/19年度到2020/21年度,南亚玉米生产量和消费量处于紧平衡状态,南美、中亚和东欧等地区玉米生产量整体下降,消费量持续增长,但供给有余,而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玉米消费量超出生产量上千万吨,供需矛盾尖锐。[3]Ibid.总体上看,中东和非洲的三大主粮均面临严重的供不应求,南亚、东南亚、南美、东欧等地区则在三大主粮的某一方面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粮食进口成为这些地区弥补差额需求的主要途径,而这也弱化了地区国家的粮食安全主动权。
从获取角度看,粮食进口量大,但脆弱性群体的粮食获取力较低。在东南亚,泰国、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的粮食进口量相对较少,而印尼和菲律宾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文莱和新加坡是世界上对外粮食依存度最高的国家。[4]姚毓春、李冰:《生产、贸易与储备:东南亚粮食安全与中国—东盟粮食合作》,《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第42-44页。在中亚,除哈萨克斯坦外,其余四国粮食自给率较低,尤其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粮食缺口最大,需进口弥补供给不足。[5]姜晔:《“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亚农业合作前景》,《农民日报》2015年5月23日,第3版。西亚北非的小麦进口量长期处于世界前列,2019年和2020年,均有14个阿拉伯国家的小麦进口额超1亿美元。[6]“Wheat Imports by Country,” World’s Top Exports, https://www.worldstopexports.com/wheat-imports-by-country/.南亚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从2018/19到2020/21持续上升,增量分别达567.8万吨和344.3万吨。[1]“Grain: World Markets and Trade.”撒哈拉以南非洲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连续三年(2018/19—2020/21)保持在上千万吨。[2]Ibid.较高的对外粮食依存度增加了粮食进口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其粮食安全极易受国际粮价变动或粮食出口国政策的影响。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诱发“粮食民族主义”,粮食出口国为确保本国粮食供应而实施出口限制政策,制约了进口国的粮食获取力。此外,粮食进口量仅体现国家层面的购买力,并不能反映家庭和个人的获取力。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妇女、儿童、老人、小农等脆弱群体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每当粮食危机爆发便首当其冲,这在粮食进口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进口国购买的粮食并未真正惠及粮食体系中边缘群体,粮食获取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具有较强阶级性和等级性。
从利用角度看,营养不良和粮食损失与浪费严重。一方面,实现膳食营养,在吃得好的同时也吃得健康,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但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粮食数量和质量不安全、环境污染严重、瘟疫等疾病频发、清洁饮用水不足等诸多问题仍未解决,影响了民众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尤以发展中地区最为显著。从2015年至2021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营养不良发生率分别增加了约4.4、1.1和2.8个百分点。[3]FAO et al.,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Repurposing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to Make Healthy Diets More Affordable, p.14.若具体到东非、中非、南亚、西亚等各区域,营养不良发生率则更高。另一方面,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食损失和浪费严重,反映了国家在粮食收获、加工、运输、仓储和节粮等方面的弊端。据联合国环境署《2021粮食浪费指数报告》估算,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东南亚、南亚、西亚、东欧等区域的家庭年均粮食浪费量约为108公斤、69公斤、82公斤、66公斤、110公斤、61公斤,[4]Hamish Forbes and Tom Quested et al., Food Waste Index Report 2021,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1, p.58.粮食浪费已成为多地区的共性问题。对这些区域而言,在粮食供需差额较大的背景下,粮食损失和浪费无疑将加重国家粮农治理负担,阻碍区域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
综合来看,粮食不安全已呈区域性聚集,并成为地区动荡的重要诱因。事实上,2010年底的西亚北非大动荡与2008—2009年的世界粮食危机密切相关。[1]张帅:《埃及粮食安全:困境与归因》,《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114页。因此,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更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稳固执政根基的迫切需要,这也是各国重视粮食安全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的现实基础
中国长期积累的粮农治理经验和具备的农业基建优势,是其开展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资源。事实上,农业始终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着力点。2021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加快中东欧国家农食产品输华准入进程,争取未来5年中国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翻番,双方农业贸易额增长50%,倡议在中东欧国家合作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2]习近平:《凝心聚力,继往开来 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人民日报》2021年2月10日,第1版。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指出,“中方愿发起中国东盟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提高各国农业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3]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3日,第2版。同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减贫和农业项目,向非洲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在华设立一批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鼓励中国机构和企业在非洲建设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道”。[4]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1年11月30日,第2版。2022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上强调,中国将帮助中亚各国培养减贫惠农等领域专业人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5]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一起向未来》,《人民日报》2022年1月26日,第2版。可见,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的核心议题。需指出的是,现代意义的粮食安全合作已不局限于耕种环节,而是立足大食物观,统筹协调生态、科技、经贸、数字、信息、运输等诸多领域,打造粮食全产业链,以期粮食安全在供给、获取、利用、稳定等维度共同实现可持续。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明确了粮食安全之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与对象国建立的多元伙伴关系、构建的多样化合作机制、制定的多领域合作政策、实施的多类型合作项目,为全球发展倡议在粮食安全领域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伙伴外交的引领
建立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新伙伴关系的同时,中国也一直努力与既有伙伴国就深化或扩大多领域务实合作达成共识,升级已有的伙伴关系。[1]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2期,第55页。随着伙伴关系的增进,中国与伙伴国对双边关系的战略认知也在不断提升,这有助于拓展和加强既有合作领域,将发展知识转化为发展实践。伙伴关系和不同议题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双向溢出的良性互动效应,使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和伙伴外交的密切关联就是最佳例证。在粮食领域,任何一国都存在着希望突破“高政治”领域教条的限制而开展交往与合作的社会力量。这种源于社会和经济层面的粮食交往合作需求,恰恰是可以减轻“高政治”层面摩擦的一种力量;这一具有内生性的力量,是改善、维持或增强双边关系的重要资源。[2]査道炯:《从中美关系史视角看中国海外粮食获取》,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页。同时,伴随伙伴关系的创新,中国的伙伴类型日益多元化。伙伴外交的深入开展,为全球发展倡议在粮食安全领域的落地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中国—中亚关系方面,2022年1月,中国和中亚五国决定在兼顾彼此利益的基础上继续合力构建内涵丰富、成果丰硕、友谊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将粮农视为全方位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3]《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30周年的联合声明(全文)》,外交部网站,2022年 1月 26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201/t20220126_10633759.shtml。在中国—东盟关系方面,2021年11月,中国和东盟共同宣布建立有意义、实质性、互利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承诺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加强粮食安全合作。[1]《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21年11月 22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111/t20211122_10451473.shtml。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方面,2018年7月,双方决定将中阿关系提升至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把粮食安全列为经贸与发展合作的重要议题。[2]《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阿合作论坛网,2018年 7月 13日,http://www.chinaarabcf.org/lthyjwx/bzjhywj/dbjbzjhy/201807/t20180713_6836925.htm。在中非关系方向,2015年12月,双方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表示将共同应对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和全球性挑战。[3]《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外交部网站,2015年12月10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1512/t20151210_9868597.shtml。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已嵌入中国与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之中,伙伴内涵的差异性和区域伙伴对粮食安全在合作领域中的不同认知,决定了多双边粮食安全合作的不同发展方向及所要达到的不同发展预期。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不是“趋同性”合作,而是强调合作的“异质性”,重视地区伙伴国对粮食安全合作的不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从国际与区域的空间维度和安全与发展的场域维度创新合作议题和合作模式。这凸显了全球发展倡议所强调的务实行动指南,有益于将中国和地区国家所形成的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实践,共同探寻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
(二)合作机制的保障
在伙伴外交的引领下推动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需立足于一个兼具开放性、包容性、平等性的合作机制,将各国凝聚到这一机制当中,统筹各方发展需求,找到利益聚合点,从而加速合作进程,共享合作成果。这也是当前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在粮食安全领域落地的有效保障。
从全球层面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是中国开展粮食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中国既是参与者,也是引领者,依托自身粮农治理经验,并结合全球粮食体系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2021年9月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召开后,中国发布了《联合国粮食峰会:中方立场》和《中国粮食系统可持续发展路径报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要义的新发展理念,主张各国坚持“发展优先”原则,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和脆弱群体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提升粮食保障能力,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1]《联合国粮食峰会:中方立场》,农业农村部网站,2021年9月23日,http://www.moa.gov.cn/xw/gjjl/202109/t20210923_6377480.htm;《中国粮食系统可持续发展路径报告》,农业农村部网站,2021年9月23日,http://www.moa.gov.cn/xw/gjjl/202109/t20210923_6377473.htm。上述文件阐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正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要义,彰显了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立场和全球主张。
从地区层面看,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构建的区域机制,包括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东盟“10+1”、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均把粮食安全列为主要议题之一。[2]上合组织虽包括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非中亚国家,但该组织是中国开展对中亚国家整体合作的唯一重要平台,故将其纳入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粮食安全合作的区域机制中。以中国为一方,地区国家为另一方,上述机制在“1”和“多”的互动中发挥中国的体量优势和区域国家的数量优势,构建既兼顾本国利益又体现他国诉求的粮食安全合作框架。[3]张帅:《“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的中国农业外交——核心特征、机制创新与战略塑造》,《国际展望》2019年第5期,第105页。
在地区发展机制下,中国坚持系统导向,秉承整体合作观,将地区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和全局角度对粮食安全合作进行战略设计。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同意加强粮食安全公共政策领域的交流,支持开展作物品种选育等联合研发,鼓励企业开展农产品种植、加工、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外交部网站,2021年12月7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112/t20211 207_10463447.shtml。中国与非洲国家将以粮食产后减损等为试点,帮助非洲国家在既有生产能力条件下提高粮食供给保障能力。[5]《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外交部网站,2021年12月2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112/t20211202_10461174.shtml。中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计划在自愿交换粮食安全形势信息方面开展合作,有意进一步发展上合组织与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1]《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粮食安全的声明》,外交部网站,2021年9月 20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109/t20210920_9585669.shtml。中国和东盟国家同意继续实施《10+3大米紧急储备协议》,加强粮食安全合作,提升地区粮食安全。[2]《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外交部网站,2020年11月12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01 1/t20201112_9869266.shtml。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将在有机农业/生物农业、粮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开展农业领域经验交流,借鉴中国经验。[3]《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20年至2022年行动执行计划》,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20年8月10日,http://www.chinaarabcf.org/lthyjwx/bzjhywj/djjbzjhy/202008/t20200810_6836922.htm。可见,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各有侧重,这既是基于区域国家的发展需求和中国优势达成的合作共识,也是对既有合作领域的拓展和完善,能够在合作过程中体现中国在不同地区所积累的技术、知识、农资、基建等增量,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
(三)政策规则的导向
合作机制重在确立双方合作的根本遵循,明确合作的主要方向,规范合作行为,但具体工作的实施仍需通过农业、商务、科技等相关部门协调,达成合作协定。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已召开两届农业部长会议,并在2021年通过了《第二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联合宣言》,双方农产品贸易总额到2030年将力争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农业投资存量将力争突破50亿美元。[4]《第二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举办》,农业农村部网站,2021年2月25日,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2/t20210225_6362311.htm。在“八大行动”[5]在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同非洲共同实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框架下,中非于2019年召开了首届农业合作论坛,通过了《中非农业合作三亚宣言》,双方还将计划在“九项工程”[6]在2021年11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卫生健康、减贫惠农、贸易促进、投资驱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九项工程”,作为《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的首个三年规划。的指引下,举办第二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召开中国—非盟农业合作联委会第一次会议,确保双方关注的农业领域合作得到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已举办六届农业部长会,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农业合作协定》2021—2025年落实措施计划、《上海合作组织粮食安全合作纲要》落实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中国和东盟自2016年以来已召开五届农业合作论坛,同东盟国家达成30多项农业合作协议,与其中8国建立了农业联委会工作机制。[1]《中国—东盟深化农业领域务实合作》,中国新闻网,2021年9月9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1/09-09/9561967.shtml。中国和澜湄国家在2017年和2019年分别成立了澜湄合作农业联合工作组和澜湄合作农业科技交流协作组,并于2020年发布《澜沧江—湄公河农业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中国农业农村部在2019年还设立了澜湄农业合作中心,助力“丰收澜湄”集群项目的实施。[2]《深耕农业合作,共襄“丰收澜湄”》,新华丝路网,2020年9月9日,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426556.html。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已召开五次农业会议,在第五届中阿博览会现代农业合作大会期间签署了36项合作协议,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改善粮食安全状况。[3]《第五届中阿博览会现代农业合作大会将促进农业全方位合作》,光明网,2021年8月14日,https://difang.gmw.cn/nx/2021-08/14/content_35093020.htm。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已召开四届农业部长会,并在2016年发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部长会议昆明共同宣言》,各方还在2021年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支持举办第五届农业部长会,第十五届农业经贸合作论坛,以及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咨询委员会第十次、第十一次会议。[4]《2021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划》,外交部网站,2021年2月9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102/t20210209_9869308.shtml。
同时,中国还就粮食安全的具体议题签署合作协议,明确工作方案。在粮食进出口关税方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2022年的正式生效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机遇。根据RCEP规则,中国与成员国实现了关税减让,中国对东盟、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农产品进口零关税比重分别为92.8%、92.0%、88.2%、91.5%、86.6%,对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零关税比重分别在61.3%~100%之间、96.1%、62.6%、98.5%、57.8%,[5]《<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_new.shtml。这将重塑国际和区域农业经贸秩序,完善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在粮食质量安全方面,2021年,中国、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越南五国农业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一带一路”合作 共同推动建立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合作意向声明》,旨在推动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植物保护委员会建立并在区域内普及系列农药产品质量标准,以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兴粮、质量兴粮。[1]《中国、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越南五国联合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农药产品质量标准合作意向声明》,农业农村部网站,2021年7月2日,http://www.gjs.moa.gov.cn/ydylhzhhnyzcq/202107/t20210702_6370854.htm。在检验检疫方面,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已签署检验检疫合作文件95份,批准14国的173种食品、农产品等输华。[2]《海关总署:我国已与中东欧国家签署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文件95份》,人民网,2021年6月8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608/c1004-32125152.html。
上述协议构成了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的基本遵循,为在粮食安全领域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供了政策导向,体现了双方的发展需求和共同关切,凸显了“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协议的内容看,综合性协议以中短期为主,合作方可以根据各自在合作期内粮食安全境遇的变化和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动,在下一个合作阶段完善合作议题,提出新的发展方向,使时效性和创新性得到兼顾;具体议题的协议往往是长期性的,表明各方希望在粮食产销环节形成一个具有规范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发展政策,以便在区域或国际粮食体系中建立一条相互依托的粮食产业链,实现共同粮食安全。
除和区域国家达成合作共识外,中国还和联合国粮农机构签署协议,共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2015年以来,中国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举办了中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年度磋商会、全球农业南南合作高层论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全球农业发展对话会,并在2015年和2021年签署合作协定,先后启动第二期南南合作信托基金(5000万美元)[3]《中国设立第三期中国—FAO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网站,2020年9月23日,http://www.cnafun.moa.gov.cn/news/ldcxw/202009/t20200925_6353306.html。和第三期南南合作信托基金(5000万美元)[4]《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全球农业发展对话会召开》,农业农村部网站,2022年2月28日,http://www.moa.gov.cn/xw/zwdt/202202/t20220228_6389873.htm。。2017年,原农业部与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编制并发布《中国国别战略计划(2017—2021)》,双方将携手实现零饥饿目标,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1]《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发布五年国别战略计划 中国成为先行者》,新华网,2017年3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28/c_129520551.htm。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中国应急管理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分别签署了关于共同加强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的谅解备忘录[2]《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应急管理合作》,世界粮食计划署网站,2019年4月26日,https://zh.wfp.org/news/wfp-china-mem-mou。和关于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改善的合作谅解备忘录[3]《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签署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世界粮食计划署网站,2019年6月21日,https://zh.wfp.org/news-21。。2018年,中国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签署《关于设立中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的补充捐资协定》,支持发展领域的南南经验交流与知识共享等。[4]《中国向农发基金捐资 设立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央视网,2018年2月13日,http://m.news.cctv.com/2018/02/13/ARTIuHOEpgqe8gK25CD2si2v180213.shtml。
(四)合作项目的实施
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遵循“双边对话—部级对接”的合作逻辑,即先通过顶层设计明确粮食安全合作的主要关切,再由职能部门协商推动签署具体协议。在这种复合机制下开展的粮食安全合作加速了项目落地,这可从中国取得的合作成果中管窥。在非洲,截至2020年,中国已建立25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这是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主要通过“一省对一国”的合作模式,发挥农企和农业研究机构的主体功能,提升非洲农业从业者的综合素养,帮助当地农户增产增收,支持非洲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实现粮食安全可持续。[5]张帅:《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理念、模式与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6期,第161-162页。如在中国—布隆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种植的超级杂交稻“Y两优900”达到当地平均产量的3倍多,[6]《我援布隆迪水稻示范获创纪录超高产》,商务部网站,2016年11月7日,http://bi.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11/20161101649188.shtml。增强了当地的粮食供给安全。在中国—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种植的“中国1号”棉花品种,比苏丹“哈梅德”和“阿伯叮”棉种的亩产高5到6倍,[7]赵忆宁:《21世纪的中国与非洲》,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改善了粮食获取安全。在中亚,中国与地区国家设立了新疆中亚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交流中心、中哈现代农业产业创新示范园,在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和杜尚别联合成立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分中心,在陕西杨凌建立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1]张庆萍、汪晶晶、王瑾:《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合作(2001—2020年)》,《欧亚经济》2022年第1期,第95页。助力中亚粮食生产现代化生态化。在阿拉伯国家,中国依托中阿博览会农业合作论坛,于2015年成立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并以宁夏作为主要负责省份,借助在毛里塔尼亚、约旦、摩洛哥等国建立的分中心,以科技赋能农业,助力当地农业经贸发展,提升粮食获取力。[2]张帅:《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特征、动因与挑战》,《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第98页。在东南亚,中国在2020年设立了澜湄农业合作广西分中心,充分发挥广西区位优势,在澜湄国家开展了60多个项目,先后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区内实施了一批中国(广西)—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项目,试验站引进试验示范的农作物品种普遍比当地种植品种增产20%~50%,亩增收超过20%。[3]《澜湄农业合作规划、项目齐推进》,农业农村部网站,2021年3月4日,http://www.gjs.moa.gov.cn/ydylhzhhnyzcq/202103/t20210304_6362927.htm。在上述发展中地区,中国还借助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建立的南南合作平台,与发展中国家加强粮食安全合作,惠及苏丹、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刚果(金)、乌干达、纳米比亚、蒙古等近30个发展中国家的100万农户。[4]《“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农业农村部网站,2022年1月18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GJHZS/202201/P020220128632546567867.pdf。农业农村部也累计向23个国家派出225名农业专家,推动428项新技术转移,举办400余期援外来华培训班,培训逾1.1万人次外国农业官员、技术人员。[5]同上。
2016年农业部发布《农业对外合作“两区”建设方案》,决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重点区域组织开展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试点,[6]《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对外合作“两区”建设方案>的通知》,农业农村部网站,2017年11月25日,http://www.moa.gov.cn/nybgb/2016/shierqi/201711/t20171125_5919532.htm。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苏丹、老挝、柬埔寨、斐济10国被列为首批试点国。由于示范效果明显,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数量持续增加,成为服务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的新平台,逐步产生“以点连线、以线带面”的规模效应。示范区的认定强调企业实力和社会责任感、完整产业链、产业规划适应对象国经济社会发展、园区所在国政局稳定、治安良好、具备一定设施基础和服务流通体系等标准。[1]彭瑶、吕珂昕:《“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迈向“工笔画”时代》,《农民日报》2019年8月13日,第4版。在这种兼顾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因素的建设条件下,双方在粮食安全领域取得诸多合作成果。如湖北省负责的莫桑比克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的土豆亩产达1760公斤以上,比当地传统种植方法增产300公斤/亩,既改善了主粮安全,又增加了农户收入。[2]《湖北境外示范区有效解决莫桑比克主粮安全问题》,农业农村部网站,2021年3月4日,http://www.gjs.moa.gov.cn/ydylhzhhnyzcq/202103/t20210304_6362932.htm。四川省在俄罗斯建立的“四川楚瓦什农业园”,被列为中俄合作重点项目,已租赁8000公顷土地,将提升当地居民的粮食获取力。[3]《四川“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中俄项目全面铺开》,农业农村部网站,2020年11月23日,http://www.gjs.moa.gov.cn/ydylhzhhnyzcq/202011/t20201123_6356793.htm。河南省负责实施的“乌克兰—黄泛区农业科技示范区”,借力中欧班列,将中国农业机械运至乌克兰,以改善当地农业灌溉条件,推进高标准示范田建设。[4]《河南省级“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借力中欧班列,推动境外项目复工复产》,农业农村部网站,2020年7月17日,http://www.gjs.moa.gov.cn/ydylhzhhnyzcq/202007/t2020071 7_6348846.htm。
此外,中国还注重与对象国的政策沟通,对接对象国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其重大农业项目,助力填补粮农治理短板。在埃及,“一带一路”倡议与埃“2030愿景”深度对接,助力中埃粮食安全合作。中资企业在埃开展的荒漠钻井项目,为埃“百万费丹”(1费丹约合4200平方米)土地开垦计划提供支持,使埃及更多荒漠变为良田。在俄罗斯,丝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了两国农企合作。中粮集团既参与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农业项目,着力开展大宗粮食贸易,也在俄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中粮远东有限公司,投建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改善当地储粮条件。[5]《积极践行“一带一路”中粮开拓远东农业合作》,光明网,2018年9月12日,https://economy.gmw.cn/xinxi/2018-09/12/content_31128528.htm。在阿尔及利亚,中国电建集团承建了阿首批大型粮仓建设项目,于2018年建成当地最大粮食储藏设施,为阿节粮减损和粮食自给提供强有力保障。[1]《中企承建阿尔及利亚最大粮仓建设项目首个工程竣工》,新华网,2018年6月6日,http://m.xinhuanet.com/2018-06/06/c_129887836.htm。
项目实施是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的具化,使合作效应更加持久。一方面,中国将技术、基建、人才、知识、经验等软硬实力资源嵌入合作项目,并在实践中进行资源重组和再造,结合中国优势与地区国家现状,创造并培育符合当地气候环境的耕种模式和良种。另一方面,中国在域外国家建立的合作中心是双方开展粮食安全合作的固定载体,既能够加强与对象国农业官员的政策协调,也益于增进与当地农业研究者的智力交换,还可以强化与当地农民的民间情感。中国与对象国农业利益攸关方构建的这种多层次交往方式,促进了中国与对象国粮农治理经验的交流。项目实施所取得的成效是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的前期积累,为在全球发展倡议下增进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对外粮食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进一步深化粮食安全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粮食安全的关联性危机频发
粮食安全属于复杂系统问题,极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效应。一是因为粮食安全的关联领域多维且相互交织,除农业外,还包括生态、贸易、金融、卫生、生物、交通等多个领域。这意味着任一领域出现不稳定迹象都会成为粮食危机的诱发因素,同时也表明粮食安全的实现需以保障粮食生态安全、贸易安全、金融安全、生物育种安全、运输安全等综合安全维度为前提。[2]于宏源、李坤海:《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期,第86-88页。二是因为衡量粮食安全的指标多元且相互依存,包括供给、获取、利用和稳定等维度。[1]Tony Castleman and Gilles Bergeron, “Food Security and Program Integration: An Overview,”in Louise C. Ivers, ed., Food In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 New York: CRC Press, 2015, p.2.只有确保四个层面的共同安全,才能够实现粮食安全可持续。粮食安全的复杂性增加了粮食安全合作的制约。以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对粮食安全合作的冲击为例。在卫生安全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交通运输业停滞,粮食生产资料供应趋紧,粮食经贸往来受阻。由于疫情防控,中资农企在当地雇佣的劳工无法按时复工,海外多数项目被迫暂缓,影响了中国和对象国既有的合作规划。在生态安全方面,气候灾害的发生成为粮食安全合作的压力倍增器。自2021年以来,气候极端化日益严峻,全球生态环境遭受重创,尤以发展中国家受灾最为严重。干旱、洪涝、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及由此引发的蝗灾、水污染等次生灾害加剧了东非、南亚、西亚等多个地区的粮食生产压力。稳定的气候环境是中国在对象国种植粮食的保障,自然灾害的侵扰既增加了双方的合作成本,也对农业技术的适应性提出了挑战,还影响了良种的示范试验。
(二)农企资金压力大
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投资长且见效慢,可持续的资金链是确保项目运行的关键。自2014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和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已联合编著9本分析报告,持续追踪中资农企海外发展,尤其关注发展中地区中资农企的发展状况。从报告中各企业反映的问题来看,融资困难是普遍面临的困境。[2]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编著:《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8年度)地方篇》,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年版。这主要是因为国内银行贷款利率高,周期短,且多数省份的银行对农企规模和投资对象国设定了条件。资金运转不畅直接阻碍了合作规模的扩展和合作领域的创新,也降低了农企的海外竞争力,使其在海外粮食市场开发上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长整体趋缓,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多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甚至出现整体下滑。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东北非、南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地区、欧洲与中亚地区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4.0%、-5.7%、-6.7%、-2.0%、-5.6%。[1]“GDP Growth (annual %),”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view=chart.域外地区面临的经济困境加重了中资农企在对象国开展项目的经济负担。如在非洲的山西农企表示,当地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会耗费企业的运营资金,加重运营成本。[2]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编著:《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6年度)地方篇》,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在东南亚的江西农企反映,对象国农资缺乏、水利设施落后,增加了项目实施的负担。[3]同上,第138页。
(三)对象国营商环境欠佳
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需要对象国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保障政策的连贯性,遵守合作契约,上述任一方面出现波动都将增添合作阻力。当前,与中国开展粮食安全合作的部分国家仍面临政权更迭、民族和宗教冲突、资源争夺、央地矛盾、大国博弈等多重压力,地区营商环境不稳定。据美国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21年脆弱国家指数报告》,处于警戒线以上(指数高于60)的国家多数与中国开展了农业项目。[4]Natalie Fiertz, Fragile States Index Annual Report 2021, Washington D.C.: The Fund for Peace, 2021, pp.6-7.2019年苏丹动乱、2020年埃塞俄比亚冲突、2021年缅甸政局动荡等都阻碍了中国在当地农业项目的实施。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的主要国家,随着乌克兰局势恶化和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升级,中乌、中俄的粮食贸易也将受到波及。同时,由于粮食安全合作涉及对象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农民等多个利益攸关方,各方利益诉求不同也增加了合作的制约。如在粮食收获后,当地方政府需要增加粮食供给而外资生产者需要出口时,双方矛盾便会产生。来自江苏的农企曾反映,部分投资所在地设置了较高的农作物出口关税限制,阻碍农作物外运。[5]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编著:《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18年度)地方篇》,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在苏丹的中资农企表示,苏丹的政治结构具有“弱政府、强社会”特点,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有限,即便中央政府给予中方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中也百般为难,并且苏丹企业还借助“主场优势”试图将中资农企赶出苏丹。[1]张帅:《中国与苏丹农业合作的现状与前景》,《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第34页。
(四)粮食安全合作领域失衡
粮食安全合作主要包括产销领域的合作和预防领域的合作,前者重在农作物种植、种子试验和农产品销售等,其对粮食安全保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政局稳定和外界干扰因素较少的时期;后者重在粮食储藏和粮食信息交流等,其对粮食安全保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区动乱、气象灾害、公共卫生疾病等不可抗力发生时期。从既有合作来看,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多发生在产销领域,在预防领域的合作相对不足。一方面,中国和多数国家尚未建立粮食舆情共享机制,缺少在粮食安全形势等具体方面的信息沟通和互换,降低了各方在危机时期开展联动治理的综合绩效,不利于中国和对象国形成粮食安全共生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在粮食仓储等方面的优势还没有在合作中完全展现,参与对象国粮仓建设和冷链物流发展的项目较少,影响了中国粮食危机管控经验的海外传播,也无助于中国和域外国家共建粮食全产业链。
四、深化对外粮食安全合作的路径
2022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明确指出,粮食安全成为全球关注重点,世界饥饿人口不降反升,需进一步在粮食安全等领域加强多双边合作,应系统谋划合作布局,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聚焦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深入分析双方合作潜力。[2]《“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面对粮食安全合作困境,中国宜在机制构建、模式创新、风险预防、领域拓展等方面综合施策,以实现粮食安全可持续,助力联合国2030“零饥饿”目标的实现。
首先,塑造以粮食安全为中心的系统合作机制,降低突发扰动对粮食安全合作的威胁。粮食安全不是单维度的安全议题,它和卫生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金融安全、水安全等相互交织。粮食安全合作不应局限于农业部门,需推动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因此,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可考虑在农业部级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跨部门的系统合作机制。当前,中国已建立以农业农村部为召集方,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多部委参与的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中国和域外国家可以此为借鉴,由双方农业部牵头,将和农业密切关联的部门纳入其中,构建一个跨国的农业部际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宜建立“农业+”对话平台,应对突发扰动对粮食安全的冲击。如在卫生危机爆发时,启动“农业+卫生”响应机制,以双方的农业部和卫生部为中心,其他部委参与配合;在气候危机发生时,启动“农业+生态”响应机制,以双方的农业部和生态环境部为中心,并借助其他部委的力量共同应对。此外,中国和对象国可考虑在建立农业部际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将该机制与相关对话常态化,使其成为中国和域外国家共同应对粮食安全关联性危机的重要平台。
其次,创新合作模式,减缓农企的资金压力。在国内,中资农企需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合作模式出发,探索解决融资困难的路径。一方面,农企可在所处省份内寻找合作伙伴,形成企业集群,以共同出资的方式赴境外投资。另一方面,还可考虑依托区位优势,建立区域企业联盟,如长三角农企联盟、东三省农企联盟等,发挥各企业比较优势,形成合力,抱团“出海”。在此过程中,地方农业农村厅需为农企搭建协商对话平台,促其达成合作协议。在域外,对外粮食安全合作需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双边合作和三边合作,积极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主权国家政府及其具有境外业务的企业,通过与其产业制造能力、经济实力相当且资源禀赋与贸易指数具有互补性的国家及企业,在具有更多自然资源、更强贸易互补性的第三方国家/地区进行的经贸、金融、基建等方面的多边合作。[1]门洪华、俞钦文:《第三方市场合作:理论建构、历史演进与中国路径》,《当代亚太》2020年第6期,第9页。中国在海外市场开展第三方粮食安全合作存在诸多可能。中国和海湾国家可考虑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借助中国的技术优势和海湾国家的资金优势,充分利用非洲国家的水土资源优势,实现三方共赢。中国与韩国和新西兰可借RCEP实施之契机,在东盟开展农业基建合作,中日韩还可在“10+3”机制下,在东南亚开展大米储备等项目。中俄可考虑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在中亚开展粮食安全合作,助力中亚农地资源开发。
再次,建立海外风险评估体系,加强对投资目标国的危机预警。早期预警对海外中资企业极为关键,尤其是在农企普遍面临资金压力的背景下,及时准确的信息将帮助企业减少经济消耗。对此,可考虑从两方面着手构建海外风险评估体系。在政府层面,由于当前派出的农业外交官尚未覆盖全部合作国家,农业农村部宜加强对农业外交官的培养并增加外派名额,服务于海外舆情信息的搜集。此外,农业农村部还可考虑结合上一年度农企海外运营状况和对象国当下局势,编写农业海外投资合作风险分析报告,对本年度的合作风险做出预判,弥补当前报告在这方面论述的不足。在企业层面,农企可考虑设立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负责跟踪投资目标国的发展情况。企业在招聘人员时,不应只局限在农业相关专业,还需重视外交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专业人才。同时,农企在海外投资之前,需做好田野调查,向智库、高校寻求智力支持,并做好危机管控预案。
最后,深化粮食安全合作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既是中非“九项工程”、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1+3+6”合作[1]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首次集体会晤时,提出中拉关系务实合作“1+3+6”新框架。“1”是制定“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3”是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三大引擎”;“6”是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六大领域为合作重点。、中国与东南亚五国“3+5”合作[2]在2016年3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国确定了“3+5合作框架”,即坚持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协调发展,优先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领域开展合作。的共同关切,也是2016年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和《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以及2021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的主要议题,这为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下深化粮食安全合作领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粮食危机管控领域,中国可发挥自身基建优势,在域外国家推动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冷链物流发展,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并提升对象国在危机时期的粮食供给能力。同时,中国与对象国可借助互联网通讯技术,建立粮食舆情共享平台,强化危机时期的协同合作。在新经济领域,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可借“数字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之契机,在域外国家传播物联网技术和无人机播种技术,推动精准农业和数字农业的发展,保障粮食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还可在“双碳”目标下,与对象国开展生态农业合作,实现绿色产粮,确保粮食生态安全。在减贫兴农领域,可开展乡村振兴合作,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赋权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贫农等脆弱性群体,维护其粮食权益。
作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一环,粮食安全合作正逐渐成为多双边合作的新增长点。伴随全球粮食安全形势的恶化,全球粮食体系也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对此,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时提出了中国的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乌克兰危机等风险叠加的背景下明确了中国粮食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向和施策领域。[1]《王毅提出中方关于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新华网,2022年7月9日,http://www.news.cn/2022-07/09/c_1128817160.htm。中国宜持续发挥粮农治理优势,对接沿线国家的粮食安全需求,畅通中国和对象国的粮食市场,促进国家间粮食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实施,助力全球粮食体系转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