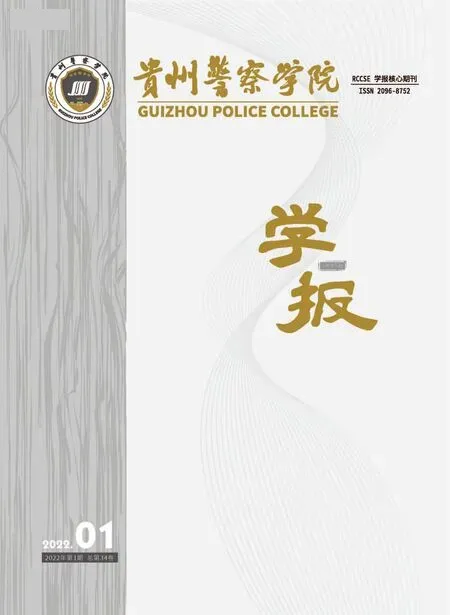公平责任适用困境的探析与纾解
尹宇杰(贵州梓熤律师事务所,贵州 贵阳 550001)
《侵权责任法》第24 条是关于公平责任规则的规定,即:“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民法典》第1186 条将该规则修改为:“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与《侵权责任法》相比,《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修改之处涉及条文约30 条,其中对公平责任的修改力度大。[1]新的规定虽然并未改变公平责任的一般性规则,但在适用条件、适用依据等方面进行了根本性修改,采用了与“无过错责任”规定相同的“一般性规则+封闭式例举”的立法例。[2]立法者修改条文的目的在于解决《侵权责任法》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问题。由于适用公平责任的困境主要源于其文字表述上的不确定性,所以修改的重点本应放在公平责任的适用情形上,即将公平责任适用的依据从法官的主观判断转变为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民法典》的规范模式似乎并未达致这一立法目的。
从既往的司法实践看,公平责任沦为了适用过错责任不利时的兜底条款,造成其适用上的随意性,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公平责任的构成要件与过错责任存在逻辑冲突,导致裁判者可以在不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的条件下将民事责任划分给行为人承担。站在整个侵权法的角度,公平责任不仅与过错责任产生了构成要件上的冲突,还与整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产生了在归责价值判断上的冲突。换言之,公平责任与过错责任之间在构成要件上的冲突只是一种延伸性的表现,其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之间在归责价值判断上的冲突才是导致公平责任陷入滥用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技术手段解决不了内核冲突,仅仅探索如何框定公平责任的适用条件,修正其文字表述上的不确定性并不能解决其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在归责价值判断上的冲突。
解决这种内核冲突需从以下角度着手:首先,分析公平责任之于整个侵权法而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即公平责任的法律性质及其功能之所在。然后,以此为线索分析公平责任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之间在价值追求上产生冲突的具体内容,即冲突双方的价值追求标的。最后,分析造成冲突的原因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一、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对于《侵权责任法》第24 条之规定,司法实践中常将其视为自由裁量权在侵权法中行使的依据,例如,人们关注较多的孙晓梅与赵建树健康权纠纷案①(2015)黑高民申二字第505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观点认为原被告之间发生的侵权纠纷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双方均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过错,故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4 条,由双方分担损失。、电梯劝阻吸烟猝死案②(2017)豫0105 民初14525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观点认为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直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4 条,由双方分担损失。等。在《侵权责任法》背景下,这种做法似乎合乎逻辑。因为仅从法条的字面含义理解,很难判断适用公平责任与适用过错责任的情形从逻辑上究竟是包含关系、并列关系还是交叉关系,适用过错责任的情形似乎也可以同样适用公平责任,区别只在于能否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总而言之,为了保护所谓弱者的利益,公平责任就是屡试不爽的正义之剑。立法者的本意是将公平责任作为只能在例外情形下适用的规则,但司法实践却将其作为原则性的裁判依据。这就形成了公平责任的最大问题,为法官滥用法律打开了方便之门,对人们的行为自由也是巨大的妨碍,[3]对整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造成损害,阻碍侵权法实现其应有价值。
诸多观点认为,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来源于其在文字表述上的不确定性,为此,学界提出了许多修改之建议,比如限制公平责任的赔偿范围,认为可分担之损失仅限于直接经济损失[4]、限制公平责任适用的主体[3]、限制公平责任适用的范围[1]。从形式逻辑而言,过错责任的含义为“有过错就有责任”,无过错责任的含义则为“无过错也有责任”,一般情形适用过错责任,法定的例外情形适用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从逻辑学上来看是一种周延的列举,不存在遗漏的情形。[5]而公平责任在文字表述上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后果是非例外情形下“无过错也有责任”,其与过错责任产生了构成要件上的冲突,导致其沦为“归责”的兜底条款,裁判者可以做到虽不属于法定例外情形,行为人亦无过错,但依然将责任归于行为人。这就让以“过错”作为核心价值判断要素的总体归责原则体系失去了意义。
现行《民法典》对公平责任进行了修改,采取“一般性规则+封闭性例举”的立法例,按照其修改路径推演,既然要有其他法律明确规定才能适用公平责任,那么则会导致公平责任无依据适用,无情形适用。由此可见,文字表述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公平责任与过错责任之间在构成要件上的逻辑冲突,确是造成公平责任适用困境的原因之一,但并非根本原因,仅从其文字表述上着手,亦无法冲破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反而会导致其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即无用的困境。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关于公平责任的具体适用情形已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分别为《民法典》第1190 条第1 款:“……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情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民法典》第1254 条第1 款:“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民法典》第182 条第2 款、第3 款:“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民法典》第183 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民法典》第1188 条:“……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6]但是,本文认为上述规定并非公平责任条款的具体规定。首先,适用公平责任需满足行为人、受害人皆无过错的两项前提,上述法条中仅有《民法典》第1190 条、第1188条考虑了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但都未兼顾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其次,除第1190 条、第1188条之外,其他3 项条文甚至都未涉及“过错”这一要素。换言之,上述5 项条文虽有涉及如何分担损失的含义,但并不符合公平责任构成要件。可见,就目前的立法而言,并没有任何一项条文可以作为公平责任的具体适用依据。
与过错责任相比,无过错责任之所以能采取“一般性规则+封闭性例举”的立法例,是源于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情形可以从事实类型上进行划分。这些特殊情形可以突破“有过错就有责任”的归责逻辑,是源于其本身具备的事实特征,如高度危险责任本身具备的危险性特征、产品责任本身具备的获利性特征。但是,公平责任的适用情形并不具备特殊的事实特征。在实践当中,能够适用公平责任的情形,并非源于其事实本身的特殊性,而是源于其事实发展过程的特殊性。由于这种特殊性并非类型化的,难以进行界定,所以采用“封闭性例举”的立法例会导致公平责任无类型化情形得以适用。本文认为,这也是《民法典》当下没有填充公平责任具体适用情形的原因。
由此可见,公平责任与过错责任之间在构成要件上的冲突只是形式上的冲突,其本质应是价值追求的冲突,所以即便能够将公平责任在文字表述上确定下来,也只能解决形式上的冲突,并不能解决本质上的冲突。
二、公平责任适用的国外立法例及其启示
就同样存在分担损失条款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公平责任并不是作为一般规则或某种归责原则来适用,皆集中在被监护人致损情形之中。如《瑞士债务法》第54 条①该条第1 款规定:法院可依公平原则判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部分或全部因其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意大利民法典》第2047 条②该条第2 款规定:负有监护义务之人不能赔偿损害的情况下,法官得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条件判定致害人给予公平的赔偿。以及《德国民法典》第829条之规定:“所谓衡平责任仅适用于监护人依法不承担责任时被监护人致人损害分担责任或在非因过错致自己丧失知觉或不能自由决定意思的精神错乱状态下致他人损害的赔偿的情形。”可见其适用范围非常局限,仅仅适用于极少数侵权行为类型,可以认为是将公平责任视为一种行为人的责任减免事由规定在被监护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行为之中。由于仅仅是将公平责任视为一种责任减免事由,其自然不会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产生构成要件上的逻辑冲突,也不会导致公平责任沦为适用过错责任不利时的兜底条款。
深入探析大陆法系国家适用公平责任的情形不难发现,其中的动机并非为了保护被害人,反而是为了照顾行为人。在被监护人致损的情形中,由于被监护人并非一个完全可能受监护人控制之物件,亦不属于任何危险情形,监护人从客观上无法形成对被监护人全天候的控制。如果全盘将损害责任附加于监护人,似乎显得过于苛刻,所以其价值追求的标的为实现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责任量上的平衡即公平。
与之相比,我国公平责任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裁判中适用公平责任的案件,立法者与裁判者的动机并非为了照顾行为人,而是考量如何将受害人的损失分担给行为人。换言之,大陆法系国家在适用公平责任时,考量的是如何实现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责任量上的公平。而我国在适用公平责任时,考量的是如何使受害人损失得以让行为人承担,以达到保护弱者的正义目的。这种动机上的相悖才是招致公平责任适用困境的根本缘由。
在整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中,过错责任蕴含的是一种无差别的公平价值,即无论情形如何,仅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为评价标准。而无过错责任同样也蕴含了无差别的公平价值,虽然形式上看起来,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也是在极力保护受害者的请求权利,但其中影射的观念并非是将受害人视为弱者。由于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中,行为人本质上可视为既得利益者,其利益的获得存在较大可能性侵害到他人,所以便不考量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其中蕴含的是一种利益的平衡,也就是公平价值。可见整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价值追求标的并不包含保护弱者或受害人的正义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侵权法追求的价值不包含正义;恰恰相反,侵权法中确立过错责任的起源便是基于对不法者的惩罚以及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也可视为保护受害者的正义举动。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过错责任或是无过错责任都以某种具体的标准作为价值判断要素,主张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固定在某一个客观存在的要素之上,即“谁有错,谁负责” “谁获利,谁负责”。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价值追求仅包含“公平”与“正义”中的“正”,但并不包含“正义”中的“义”。其意图将归责的标准固定在某一种价值判断要素之上,并不考量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其站在中立的立场衡量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或是否基于行为获利。但我国的公平责任条款并不完全支持这样的立场,其无法在难以证明“行为人具备过错”的情形下,对于受害人的损失袖手旁观,总是期望以某种形式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影射的是一种在主观立场上将受害人与行为人区别开来的态度,是一种对于“义”的价值追求。两者之间在价值追求上的区别导致了公平责任与过错责任之间产生了构成要件上的逻辑冲突,继而引发了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
三、公平责任适用困境纾解之前提
对于公平责任的定位,学界中素有争议,辨析公平责任的法律性质是突破其适用困境前必须解决的认识问题。
(一)公平责任法律性质之界定
对于公平责任法律性质的界定,侵权法学界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认为公平责任是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与其他归责原则有着同等价值、逻辑起点,能够弥补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不足;[7][8][[9]其二,将公平责任认定为责任成立后的损失分担,主张《侵权责任法》第24 条亦可在监护人的严格责任中作为责任减免事由适用;[10]其三,主张公平责任是因侵权构成要件欠缺而使责任无从成立时,对受害人给予的社会法意义上的救济,[11]可以认为公平责任的适用是一种“特殊的救济措施”;[12]其四,认为在满足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将公平责任认定为一种赔偿原则,本质是授权法官在个案中通过衡平手段合理分配损害,以达到公平正义之目的。[13]对于上述4 种关于界定公平责任法律性质的观点,在《侵权责任法》背景下,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但在《民法典》背景下,公平责任既非某一种救济措施也无关于侵权责任之成立。
首先,公平责任并非责任成立后的损失分担,原因在于其构成要件与其他归责原则的构成要件之间存在逻辑冲突。对于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皆坚持完全赔偿原则,当侵权行为满足归责构成要件时,侵权责任便成立,此时若无法定责任减免事由,行为人原则上将承担完全赔偿责任。[14]可以看出侵权责任的确立应当分三个步骤,首先需要满足侵权归责构成要件,其次根据事实情况选择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如恢复原状或金钱赔偿,最后考察是否具备法定责任减免事由。如果认为公平责任是责任成立后的损失分担,需要求侵权行为首先满足其他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从这一逻辑出发,公平责任的成立需要求行为人与受害人皆无过错,而过错责任的成立需要求行为人存在过错,无过错责任的成立则不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三者的构成要件存在逻辑冲突。这也反证了适用公平责任的情形与适用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的情形应当成立排斥关系。
其次,公平责任是否是侵权构成要件欠缺时的救济或法官的衡平手段。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公平责任确是侵权构成要件欠缺时的救济手段。如“何廷保等诉郴州某医院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医院的输血行为、供血站的运血行为对何廷保感染艾滋病的损害事实欠缺因果关系,但是鉴于双方均无过错,出于人文关怀,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4 条,酌定双方分担损失。①(2017)湘10 民终1668 号判决书。在上述案件中,适用公平责任就是在适用过错责任不利时的兜底行为,只要存在加害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皆可以将被害人的损失分担到行为人身上。这种适用方式似乎也符合大众朴素的正义观念,而这种价值观上的追求便导致公平责任成为了救济被害人的不二法宝。就像德国在出台《民法典》第829 条时那样,反对出台的观点认为“这种古怪的规定……将会留给法官公平的考量,而不是给他一个确定的法律规定。”[15]但在民法典时代的公平责任,其适用的依据从法官内心的主观判断转变为了法律明文规定的具体情形,这就将适用公平责任的情形与适用过错责任的情形区别开来。实务中不会再度出现由于欠缺适用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转而适用公平责任,以期实现救济被害人意图的情形。这就否定了公平责任乃是侵权构成要件欠缺时的救济或者赋予法官的衡平手段。
最后,公平责任亦非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原因在于公平责任缺乏成为归责原则的核心要素,即考量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公平责任的规定中,无法总结出适用公平责任需要证明的是何价值判断要素,反而体现的是不需要证明任何价值判断要素之含义,这与归责原则的内在要素相矛盾。如过错责任原则的内在要素为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内在要素为行为人客观上的获利。另外,如果认为公平责任能够独立成为一项归责原则,那么整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可能会面临崩溃的风险。构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目的是为所有侵权行为找到承担责任的主体,防止在侵权行为发生后无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出现。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几乎实现了这个目的,其以过错作为构建整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核心价值判断要素,再以无过错责任作为补充,已经可以做到覆盖绝大多数侵权行为。这种成功完全是建立在以“过错”作为衡量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核心价值判断要素的大前提之下,而公平责任的文义却蕴含着不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要素的归责含义,所以公平责任只能是一种损失分担规则而不能成为归责原则,否则整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就会存在两个逻辑对冲的归责原则。
根据以上分析,能够明确的是公平责任既不是一种归责原则,也不涉及责任成立的问题,在《民法典》施行后也不再是赋予法官救济被害人的衡平手段。其正确定位应当是一种体现法律原则的损失分担规则。已有学者提出,侵权法上的归责原则,实际上是归责的规则。[16]可以理解为归责原则既非法律原则,也非具体的法律规则,乃是通过分析法条本身的含义亦或是总结法条与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得出的某一种连接同类型侵权行为的价值判断要素,用以解决该类侵权行为如何确立侵权责任的问题。换言之,过错责任是一项法律规则,但并非归责原则,“过错”才是归责原则。而公平责任则是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公平原则在侵权法上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具体的法律规则。
(二)公平责任之功能界定
既然公平责任并非归责原则也非救济手段,其居于侵权法中的功能就需要另行分析。侵权法旨在转移或分散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损害,其所设之归责原则决定何种损害由加害人赔偿,何种情形下虽有加害人但仍由被害人自己承担。[17]但对于承担责任的形式与范围,归责原则却难以染指,这便是公平责任功能之所在。
首先,由于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导致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之间形成的归责原则体系无法囊括所有已经存在的或未来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类型。比如人类未能建成高楼之前,不存在高空抛物的侵权行为;人类未能利用核能源之前,不存在核事故致损行为;人类在没有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概念时,不存在监护人责任。如“肖友曹诉鞠玉发交通事故纠纷案”①(2017)湘0581 民初2737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观点认为无偿搭乘中宜采用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以公平责任原则为辅助的归责原则。“酒瓶不明原因爆炸致人受损案”②(2016)豫15 民终2227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观点认为原告因被告生产的白酒突然出现瓶身断裂而受伤的事实清楚,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无法证实被告存在过错行为,故根据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原被告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这两个案件如不适用分担损失的责任分配方式,将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价值。可见,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力量是有限的,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难以承担实现侵权法应有价值的任务,在未来公平责任会逐步填充自身具体的适用情形,弥补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局限性。
其次,归责原则解决的是确认由谁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但却无法解决责任分配的问题。即便目前的侵权立法正在努力构建由归责原则、承担责任方式以及责任减免事由组成的有机体系,但依然无法弥补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坚持完全赔偿原则的不足之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应当简单地由行为人承担全部责任或由受害人自担损失,总有一部分侵权行为在责任分配时不能采取先全部附加于谁再做“减法”的处理方式。而公平责任则是突破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默认的完全赔偿原则,从责任确立之时便进行了责任比例划分。
最后,公平责任的存在具有体系价值。“体系性的工作是一种永续的任务……法学体系必须保持开放。”[18]公平责任在整个侵权立法体系中承担着保持开放的任务,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类型的侵权行为开辟一条有法可依的路径,也为在责任分配方式上双重适用完全赔偿原则与不完全赔偿原则打下基础。
通过分析公平责任的功能更加确定了其并不涉及责任成立的问题,而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恰恰就源于此,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将公平责任视为一种“归责”的手段,作为责任成立的一般性依据。
四、公平责任正确适用的具体路径
从上文的探索路径可知,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并不能够通过限制其适用范围或者调整其文义表述得到解决,导致公平责任陷入适用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公平责任的内容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之间的价值追求冲突,解决其适用困境的方案应当着眼于公平责任的内容之上。基于这种思路,填充公平责任的正确内容以及以科学的形式将其设置在法条之中便是解决公平责任适用困境的办法,也是公平责任正确适用的具体路径。《民法典》将公平责任规定在“损害赔偿”一章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归责原则,或者像《侵权责任法》一样将其规定在“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一章中,算是对其性质和定位的一种纠偏。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完善其适用路径。
(一)分担损失应具备双向性特征
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仅仅居于受害人的立场而言,其位于侵权关系之中是唯一受损方。但是,若居于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双重立场,加害人也可能是受损方。如果仅仅是财产侵权事件,加害人在承担了全部侵权责任之后,对受害人之损失进行了全额损害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便得到了弥补,受害人不再是受损方,加害人将因为负担了侵权责任而成为了受损方。所以对于公平责任的分担损失功能,其损失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受害人,还应当包括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后的加害人。换言之,适用公平责任的出发点并不是为受害人的损失找到承担义务人,而是如何实现特殊情形下受害人与加害人分担损失量的平衡。
(二)扩大分担损失的范围
侵权法的立法目的本质上是为了实现矫正正义,但不意味其动机仅仅是一种报复,反而应当理解为一种救济。换言之,除了实现对加害人的处罚之外,更现实的是为了降低社会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对个体的损害,防止个体因面临社会风险而一蹶不振的情况出现。一次侵权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否有主体来承担了部分或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意味着一次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试想,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其权利受到侵害的确有可能因此遭受灭顶之灾,而加害人所负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可能同样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既然公平责任本就是建立在特殊情形之下的分担损失规则,有时这种特殊情形又难以证成加害人的过错程度,那么其分担损失的范围就应当站在社会总损失的角度,扩大到整套侵权责任的确定以及赔偿流程之中。站在这个角度,公平责任分担损失的范围就不仅局限于民事责任确立之前的损失,还应包括民事责任确立之后的损失。
(三)不应局限在无主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
回顾过往适用公平责任的案例,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这些案件往往是无法证成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或无法证成加害人具备过错的情形。换言之,这些案件皆无法为损害结果确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如果将公平责任的目的确立于在特殊情形下实现受害人与加害人分担损失量的平衡,以及防止特殊情形下个体因面临社会风险而崩溃的情形出现,那么其适用的情形还应包括可以确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情形。这时,需要从实证逻辑的角度予以解释。可以确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情形,其形式上满足了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无法定责任减免事由的前提下,原则上加害人应承担完全赔偿责任。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形成的周延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形式逻辑,而非实证逻辑,换言之,过错的量应当如何计算本身是一个无法精确的事实。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形成的逻辑圈可以解决如何囊括所有侵权行为的问题,但却无法解决精确计算过错量的问题。此时,公平责任的作用便显现了出来,某些特殊情形虽然符合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将被害人的损失全盘负担到行为人身上,难免会显得过于苛刻。某些侵权事件的发生本身也具备意外性,这种意外性便是干扰精确衡量过错量的变量,所以即便是可以确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亦可以基于实证逻辑的角度,为了实现受害人与加害人分担损失量的平衡目的适用公平责任。
(四)公平责任的适用不能以“过错”作为前提
基于“过错”建立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是解决侵权纠纷必须遵循的首要规则。构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目的是为所有侵权行为找到承担责任的主体,防止出现侵权行为发生后无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几乎实现了这个目的,其以“过错”作为构建整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核心价值判断要素,再以无过错责任作为补充,已经可以做到覆盖绝大多数侵权行为。这种成功完全是建立在以“过错”作为衡量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核心价值判断要素的大前提之下,而实现公平责任的分担损失功能则要求其必须脱离以“过错”作为确定侵权责任要素的规则,所以如果再以有无“过错”作为公平责任的适用条件,必将混淆公平责任与过错责任的适用情形,导致裁判者可以选择性地适用公平责任或过错责任,反而造成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伤害。
(五)公平责任不必以独立的条文存在
如果适用公平责任的目的是为了在特殊情形下实现受害人与加害人分担损失量的平衡,就预示了适用公平责任无需有固定的前提。换言之,法条只需要限定适用公平责任的具体情形,不需要限定其适用的前提。此时,由于已经将特殊情形独立设置为一项条文,那么公平责任的内容只需要在此情形之后阐述即可。比如,在监护人致损的情形中,如果需要以分担损失的方式解决损害问题,只需要在监护人致损的法条之中将分担损失的内容加以设置即可,而无需将公平责任独立设置为一项条文。
五、结语
公平责任与侵权责任原则归责体系之间在价值追求上的冲突是导致公平责任陷入适用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解决公平责任滥用问题的着眼点应聚焦到其本身的内容之上,将适用公平责任的价值追求从单方面保护受害人转变为实现受害人与加害人分担损失量的平衡,以此来解决公平责任与归责原则体系之间的价值追求冲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需关注公平责任的设置方式问题。由于公平责任并非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如果将其单独设置为一项条文,反而会引起误解,所以只需将其规定在适用的特殊情形条文之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