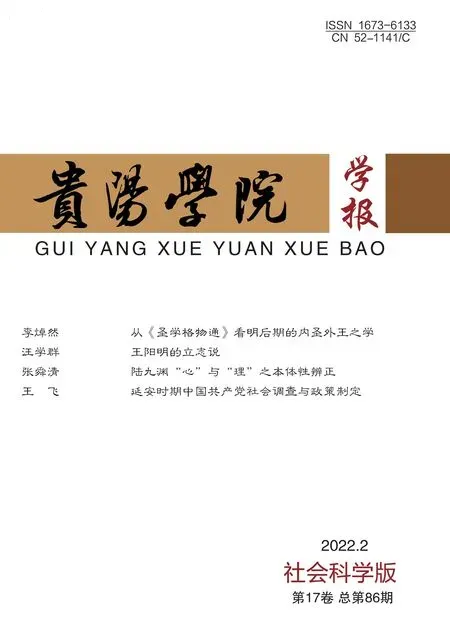从《奥赛罗》的创作评析斯图亚特时期的莎士比亚
孟俊一
(贵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5)
一
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时期的英国,社会相对稳定,艺术创新随之而起。就戏剧而言,伦敦的演员们,尤其是莎士比亚本人的剧团,正处在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人们追逐意大利时尚,就连王室与宫廷也深受影响。艺人们凭着自身的经验和信心演绎出一套标准,用于挑战教会等所制定的规范。剧作家们自信满满,一反模仿现实的传统,开始转向自我追问,于是便产生了辛辣的讽刺喜剧或晦暗的悲剧。莎士比亚这一时期(1603—1613)的创作包含了该时期所有主要的悲剧、罗马剧及最后一批传奇剧(《雅典的泰门》《亨利八世》)等,该时期(1609 年)其十四行诗也开始付梓。
在剧场方面,斯图亚特时期的舞台技术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即从仍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开放式舞台向早期现代封闭式剧场过渡,舞台被打造得像宫廷一样宏伟和华丽。普通剧院也在追赶时尚,安装了更多的“机械设备”。
这种封闭式的新派剧场,往往能够营造出一种亲密的氛围,那些精明老到的演员常常会带着观众连同他们自己一道去窥测那埋藏于个人心底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个新的充满怀疑和自我觉醒的时代,人们通常会试着去探索隐藏在意识背后的动机,这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风格,一种能够像表现行为一样表达思想的风格,能够把瞬间出现在大脑中的思绪记录下来的风格。”[1]那种扎根于传统社会模式的戏剧即刻被一种更具批判性、更倾向揭示个人并与大众娱乐严重背离的戏剧取而代之。莎士比亚的成功证明了:越是传统的艺人和剧作家,越能作出深入的探索。此时的莎士比亚正从社会问题的跟踪转向对普遍人性的研究。
斯图亚特王朝最初十年的戏剧流行讽刺和批评的风格。以意大利为背景的那种带有意大利风格的悲剧成为时尚;由马斯顿(《安东尼的复仇》创作于1599 年)、特纳(《复仇者的悲剧》创作于1606 年)和韦伯斯特(《马尔菲的女伯爵》创作于1613 年)引领的第二批复仇剧的浪潮显示了《哈姆雷特》的巨大影响,而此时的莎士比亚自己则从复仇剧的传统中走了出来。城市讽刺喜剧和悲剧则成了莎士比亚的主要戏剧形式,这是专门为那些阅历丰富的观众们创作的。从1604年到1608 年,莎士比亚创作了《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安东尼与克列奥佩特拉》《科利奥莱勒斯》等作品,每部作品的形式都与他在伊丽莎白时期创作的戏剧和历史剧截然不同。
斯图亚特时期的悲剧有两种声音,即英雄的声音和陪衬的声音。例如:哈姆雷特和掘墓人、苔丝德蒙娜和爱米莉霞、克列奥佩特拉和国人,他们每个人说出的话都不那么顺耳,他们的对话也都不能成为最后的定论,但是对立的双方必然是要妥协的。我们肯定奥赛罗的高贵,但爱米莉霞说他“愚昧无知”,我们也不会否定;贡纳瑞尔叫李尔“懒惰的老头”,而戈德莉娅却跪在这个疯子的面前叫他“王上”,二者都被认可。当然,我们首先必须明白并笃信秩序的重要,才能懂得上述所说的含义。
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及与他人矛盾冲突的复杂性显然是以群体成员之间精心设计的情节作为条件的。莎士比亚在斯图亚特时期的悲剧充溢着这样的场景,使观众对这些情节中的人物印象异常深刻。像李尔躺在荒野上、苔丝德蒙娜床边的奥赛罗以及麦克白和女巫们等强烈的舞台瞬间散发着巨大的象征力量,它们通常是画家们运笔的主题。然而,它们并不属于像早期的加冕仪式等仪式化的传统,也未承载有其他类似事件的记忆,但是立刻就会使人想到那因匠心独运的情节而被打上特殊印记的人的处境。与传统的形式不同,莎士比亚的悲剧乃是源于剧作家、演员和观众之间兴趣和爱好的平衡。
当然,讨论莎士比亚斯图亚特时期的成就不能流于空泛,不妨对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第一部悲剧《奥赛罗》进行辨析,使其典型特征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二
《奥赛罗》于1604 年11 月1 日首演[2],这部剧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一直以来都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保留节目。在斯图亚特时期,《奥赛罗》的剧中人物是除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之外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把这样的故事搬上舞台,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其勇敢而壮伟的角色颠覆了这类人物的传统形象。
那个时期舞台上出现的摩尔人都是半人半魔的形象,如《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里的埃隆就是一个浑身上下都被诅咒的摩尔人,他和马洛笔下的伊萨莫一样,有着魔鬼的自信和快乐,后来很多摩尔人或土耳其人的形象都如此,简直就是马基雅维利学说的翻版。他们是异教徒,目中无法;他们弑父,冷酷残暴;他们兄弟阋墙,反复无常,俨然是一群动作机械死板的魔怪。甚至在韦伯斯特的戏剧里,摩尔人也是以邪恶的“第二自我”[3]现身的。但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人们在这类形象身上所期待的性格特征全都转移到了伊阿古的身上。在这里,魔鬼成了英雄的陪衬,他和撒旦一样拥有邪恶的机智,他和密斯菲特一样怀着对美德的蔑视。然而,被出卖的奥赛罗并没有从他身上看出偶蹄这个魔鬼的征兆,“据说魔鬼的脚是分趾的,让我看看他的脚是不是这样”(第五幕,第二场)[4]265,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姑娘”的尸体,发出一阵动物般的哀嚎,所有仪式约束都无所谓了。奥赛罗作为接受了洗礼的摩尔人,用还愿的蜡烛作为世俗圣徒的象征,就像奥赛罗和伊阿古跪下来,缔结生死同盟的那个时候一样:
黑暗的复仇,从你的幽窟之中升起来吧!爱情啊,把你的王冠和你的心灵深处的宝座让给残暴的憎恨吧!胀起来吧,我的胸膛,因为你已经满载着毒蛇的螫舌。(第三幕,第三场)[4]157
然而,这部戏所依赖的则是失去爱情信物的魔法。如果爱情的一方是国王的子嗣,另一方是威尼斯议员的女儿,那么,这将是一个挑战传统观念的爱情故事,因为成功的悲剧要牵涉君主的成长、临政和陨落,政府和法律的变更,叛乱、内讧、王位接续、联盟等各种兴替以及其他种种错误或公共事务的转向。显然,这部戏并不关心伊丽莎白时代每个人都很在意的塞浦路斯的状况,如土耳其人的入侵、他们在纳彭托战场的失败以及后续的征服等。
当我不爱你的时候,世界也要复归于混沌了。(第三幕,第三场)[4]129
这部戏则把爱情而不是社会视为奥赛罗人生的主要法则。他告诉爱米莉霞:要是她是一个贞洁的妇人,即使上帝为我用一颗完整的宝石另外造一个世界,我也不愿用她去交换。(第五幕,第二场)[4]253
在她那灵魂与肉体交织的脆弱的网线上,那任何力量也无法打破和击碎的无瑕又辟邪的宝石正是其象征:这张网里有魔法。奥赛罗对于苔丝德蒙娜来说也是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完全为他高贵的德性所征服。”[4]49(第一幕,第三场)当她听说凯西奥被杀了,她哭泣道:“他被人陷害,我的一生也从此断送了!”言下之意,她自己不能被陷害,因为她把奥赛罗的错误和罪过揽在自己的头上。虽然她知道自己会被错杀,自己的死是无辜的,当爱米丽霞哭诉“哦,这是谁干的?”她却能回答“不是别人,是我自己”,因为正是她自己——她的另一个自己的罪过。奥赛罗的直觉很快就意识到了,他无法面对话中的真意,即他们的肉身是统一的,尽管他们的大脑和心灵并未完全合一,所以他勃然大怒,立刻加以否认:
她到地狱的火焰里去,还不愿说一句真话,杀死她的是我。(第五幕,第二场)[4]251
爱米莉霞立刻用同样的诅咒回敬:啊,那么她尤其是一个天使,你尤其是一个黑心的魔鬼了。(第五幕,第二场)[4]251
然而,天使和魔鬼是连体的,这正是两人疯狂话语背后的所指。
一个中年的异邦人,他受人尊重,他是这个国家的外籍居民,他在这里很幸运地找到了爱情,但是由于社会习俗的顽固,这份爱情显得异常脆弱,然而总督顶住社会的压力,对这一自由选择的行为表示认可。奥赛罗作为一名军人,他出于自愿,决定为威尼斯的大公们效力。就像苔丝德蒙娜一样,他属于一个全新的社会,人们服从个人的选择,并遵守契约。苔丝德蒙娜因此而坚守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忠诚,如果她把丈夫杀了,她要承担双重的罪名,即谋杀和背叛。对一个习惯发号施令并娶了高贵而仁慈的大公之女的人来说,不服从等于摧毁了他做人的基础。
角色新规则的引进是戏剧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关系上的变化。奥赛罗在第三幕和第四幕受到诱惑的安排开辟了一条戏剧创作的新途径,即心理机制的变化与恶化,这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核心内容,也是区别他晚期戏剧和早期戏剧的关键。
在凯西奥和奥赛罗那里,让高贵的品格感到羞辱本身就是一种补偿或者赎罪。所以,奥赛罗成了爱米莉霞诅咒、罗德利哥差遣和蒙太诺解职的对象:
且慢,在你们未定以前,再听我一两句话:
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第五幕,第二场)[4]269
这或许是一种自卫的恳求,而威尼斯人不再听从这位人犯的申诉。但是,要“他离开这个房间与他们同去”是不可能的。回想他在阿勒坡之战中,面对凶恶的土耳其人,差一点就以自杀而尽忠的做法,瞧着这饱受煎熬的生活和自身那“土耳其人”的自我,他清楚地把它与自己剥离开来。一旦执行法庭的判决,他黑面人的角色就终结了。奥赛罗是一个独断而果敢的战士,危机时刻更习惯运用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大脑。他的眼泪就像无药树上的果实,乃是死亡的象征,但是,它能治病。临近死亡,他勇敢地亲吻她的妻子,他再也不会觉得与她分离了:
别无他法:
现在我自己的生命也在一吻里终结。(第五幕,第二场)[4]271
莎士比亚一次次抬高奥赛罗的道德境界和智力境界。他只用几句话就平息了街头的骚动,他面对威尼斯元老院,举止高雅庄重,对勃拉班修的猛烈指控的辩白令人心悦诚服,并且满怀信心地从容接受军事重任。苔丝德蒙娜被他残忍杀害后,奥赛罗的极度痛苦的后悔表示也使观众对他产生同情[5]。
三
19 世纪的人们普遍认为奥赛罗是绝对高贵的,曾有批评家表示没有比奥赛罗这样更让我们喜欢的人物了,也几乎没有人会偏执到认为苔丝德蒙娜是罪人,因为她欺骗了她的父亲,她的命运是咎由自取。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声音,认为奥赛罗不应该自杀,他是因为缺乏洞察力而被离间。不过,艾略特的那段话很有影响,它为整个一代的批评家定下了基调:
我从来没有见过揭示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恐怖……在我看来,奥赛罗在做的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他在努力地逃避现实……他在夸耀自己,他在欺骗观众,但是,从一般人性的动机来看,他也是在欺骗自己。[6]
当然,艾略特是根据阅读的感受在谈自己的看法,他的阐释不可能搬到剧场上去,因为这在舞台上根本行不通。并且,上述观点跟伊阿古对奥赛罗的看法很接近,与莎士比亚原本的想法也很接近。这也是人们对这类故事通常应有的期待,尤其是那些去看戏的人。但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力量正是源于他打破常规。首先,这部戏里的冲突和随之引发的同情取决于主人翁不落俗套的性格;其次,在于其心理转换的速度,主人翁经历了漫长的心理变化,最终却陡然醒悟,因为斯图亚特时期的观众习惯于听到垂死之人在绞架上认罪伏法的戏白。
斯特沃德把伊阿古和奥赛罗两个形象看成是从“同一个也可以说是隐形的人物中提取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剧作家截取了人性中不同的面,把它们象征性地融入到一个人物中去,而不是奥赛罗把自己隐藏的一面投射到伊阿古的身上”[7]。另一方面,伊阿古远比奥赛罗更为重要和有趣,有多少个伊阿古,就有多少个人被他欺骗,他必须把出色演员那被人称道的每一种诡计都展示出来。他要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做得很成功,包括他的自我毁灭。他活着就是为了游戏别人的生命,给这个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有机体来一次毁灭性的转折。
上述不同观点的分歧说明,由于人与人的不同,人们对每一个角色的看法就可能存在差异,有可能会只从某个单一的角度而不是从总体的层面去凸显冲突。布莱德利通过《奥赛罗》发现,“使莎士比亚与神秘主义诗人、最伟大的音乐家和哲学家联系起来的基质中存在某种局限,一种对局部的压制”[8]149。但是,他没有认识到,象征的缺失或者说宇宙观的缺失本身何尝不是一种解放,没有了禁忌,没有了理性的羁绊,任凭情感的挥洒,这也是某些批评家们拼命反对的。莎士比亚背离了传统要求的金科玉律,所以他的定位也是摇摆不定的,必然取决于观众的自然反应。人们蜂拥而至,就是奔着“善良的李尔”和“这位悲情的摩尔人”而来的[8]163。然而,奥赛罗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呢?他说话总要带着命令的口吻,他的疯狂并没有带给他像哈姆雷特和李尔那样深刻的感悟。但是,那刺耳的命令声、那野兽般的喊叫以及主人翁的暴怒都应归入一种全新的、易于产生交感的演出技巧,女性观众会像苔丝德蒙娜本人那样醉心于这种来自异域的魅力。
奥赛罗勃然大怒,因为他的信物被用来抚慰他的好友的伤痛,苔丝德蒙娜慌乱中丢下了手帕,事后也想不起丢手帕的地方。在妓院那场戏后,她用“信仰,以及昏昏欲睡”来为自己神志不清的状态辩解;在死亡那场戏里,她在惊恐中看到奥赛罗那滚动的眼珠和战栗的嘴唇在渴望观众的解释和参与。争吵过后,伊阿古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如此奸诈的仆人完全控制了他的主人,凭着他扮演愚人的天赋而如鱼得水,这有可能正是莎士比亚在其黑暗时期所认同的角色,其地位并不亚于无条件宽恕他人的凯西奥和苔丝德蒙娜。
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中就曾有过如奥赛罗同样的情感发泄。他的一些十四行诗的情景与奥赛罗的悲情如出一辙,比如对黑肤女郎的厌恶或对他人赤裸裸的谩骂就很像伊阿古的语气。诗中那位隐形的主角不就是伊阿古和奥赛罗的组合吗?不就是他在谱写十四行诗吗?奥赛罗缺乏社会的安全感,他对自己的年龄也不自信,尤其是只会单调地使用天堂和地狱来打比喻,可以把他在舞台上的情景拿来和诗人对所爱之人变化无常的痛苦感受对比一下:
她的名誉本来是像狄安娜的容颜一样皎洁的,现在已经染上污垢,像我自己的脸一样黝黑了。(第三幕,第三场)[4]153
我曾经赌咒说你美,以为你灿烂,
你其实像地狱那样黑,像夜那样暗。[9]
过去的经历通过想象的蒸馏被埋藏在心底,伴随着往日的友谊以及那已反目成仇的爱情,如此叙事可能有助于《奥赛罗》带给人们的心灵以深刻的净化,虽然看不出情节的紧张和复杂,听不到无法解决的冲突的回响。但这部戏环环相扣,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所有的角色都安排在一个硕大的房间里,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这说明其背后蕴含着那个古老的生命之树的象征,它长着很多枝干,如约翰·唐恩所述:
没有一个人会是一座孤岛,独立自足;每一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块土,是主体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被海水冲走了,欧洲就会有所缺损,就像缺失了一块海岬,就像缺少了一个庄园,或者说你失去了一块领地;任何人的死亡都会让我有所减损,因为我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绝不要问丧钟为谁响起;丧钟为你而响。[10]
分割背后的统一,或许源自个人所体验的冲突背后的统一,它是由一部戏的节奏和情节发展的顺畅和力度以及编排和秩序支撑的,这种统一性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就像具有整体意识的演员所表达的那样,这种统一性是间接的、看不见的,通过大众的舞台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达。
四
然而,就像乔叟所做的那样,莎士比亚在其后期的作品中,把那些草根文人创作的角色拿过来,将所有剧场艺术的要求与整体的编排意识结合起来,意在表明,演员、观众和作者所共享的故事只有通过整体的情节才能表现出来。莎士比亚正是在这一点上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才能。
莎士比亚在斯图亚特时代写作的早期,反对由本·琼生所谓“悲剧统一性力量”所倡导的具有分析性和批判性的剧本,而是把自己的作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的基础上。莎士比亚反对约翰·弗莱彻纯粹、华丽的巴洛克戏剧等舞台表现,而他的创作坚守自爱,一脉相承,正所谓“恪守自己才能使万事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