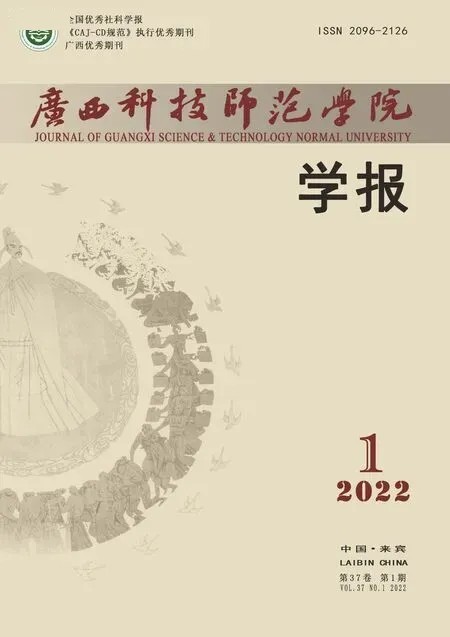论《红楼梦》现实空间的叙事功能
李 岚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0)
受编年体文学的影响,中国传统古典小说的研究重在关注时间性问题,而对空间叙事功能有待深入的发掘。但其实中国空间叙事意识源远流长,正如蒲安迪《中国叙事学》所言:“希腊神话以时间为轴心,故重过程而善于讲述故事;中国神话以空间为宗旨,故重本体而善于画图案。”[1]51“在中国文学的主流中,‘言’往往重于‘事’,也就是说,空间感往往优先于时间感。从上古的神话到明清章回小说,大都如此。”[1]57先秦时期的神话作品《山海经》,从书名上分析,我们会发现其蕴含着山与海的空间意识,在内容中更是展现了东西南北的方位空间、海陆空间等。随着古典小说的不断发展,空间叙事形式更加多样,空间叙事技巧更加灵活,《红楼梦》正是在古典小说不断发展的潮流中应运而生。作者充分运用现实空间将人物特点、结构线索乃至叙事节奏等要素系统地融合起来,从而实现其叙事意图。
一、《红楼梦》的现实空间
魏崇新在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红楼梦》分为三个世界:神话世界、大观园世界、大观园之外的现实世界。但从空间存在的虚构性与现实性角度看,魏崇新在《〈红楼梦〉的三个世界》中提及的神话世界所涉空间为“神界”,所涉人物有“仙人”,因此其当为虚有空间;而大观园世界与大观园外的现实世界所涉空间为“人间”,所涉人物为“凡人”,因此其当为现实世界。基于此,笔者将《红楼梦》的现实世界划分为南方空间与北方空间,即大观园空间与大观园外空间。不同空间有不同的特性,作者在书写不同的空间时着意捕捉其空间特点,从而使空间既真实又具有叙事性。
在书写南北空间时,作者注意到南北地域空间中特有的地名、语言、气候、服饰等特征,通过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描写使南北现实空间更具真实性。在《红楼梦》南方空间的叙事中,作者以文本互证的方式展现了多处古今地名交替使用的情况,如金陵与南京、维扬与扬州、姑苏与苏州等,故古今地名的沿用具有历史传承性。第二回借贾雨村道出了贾家金陵老宅“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2]13。此处说的老宅所在地就是金陵。而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一章,贾母生气说道:“去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2]234直接写出了老家地址南京,南京作为地名至今仍然沿用。贾雨村也说道去游览六朝遗迹,更是证明了贾雨村说的金陵与贾母说的南京便是现今六朝古都南京。而“吴语”的巧妙运用也突出了南方现实空间的真实性。第二十七回写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2]198“侬”在古诗文中作“我”,在吴语方言中表示“你”的意思。沈新林在《〈红楼梦〉中的吴语方言》中写道:“吴语中凡是用嘴接受某种物质的,都可以称‘吃’。”[3]如在“仍是吃酒谈笑”[2]7、“不吃酒”[2]53、“吃酒听戏”[2]77、“赌钱吃酒”[2]90中,“吃酒”的意思是“喝酒”。又如在“黛玉一面吃茶”[2]21、“斟了茶来吃”[2]44、“进里间来吃茶”[2]53、“吃茶吃水的”[2]179中,“吃茶”是指“喝茶”。“吃酒”“吃茶”等口语一直沿用至今。
在《红楼梦》北方空间的叙事中,“寒冷”的气候是其书写的典型特征之一。第四十九回写道:“到了次日一早……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2]337第五十回贾母说道:“这才是十月里头场雪,往后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费不迟。”[2]345大雪连下两日,达到一尺多深,若按清代裁衣尺度与现今降雪量级进行换算,十月里的第一场雪远超特大暴雪的级别。此外,《红楼梦》中描写冬季服饰时,经常出现“羊皮小靴”“鹿皮小靴”“鹤氅”“猩猩毡”“貂皮”等御寒衣物,这些都展现出北京冬天气候之寒,而地道的北京话也为北方空间增添了不少地域特色,使其更具真实性。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评价《红楼梦》语言特色为“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融会了古典书面语言的精粹”[4]。这不仅是作者创作时艺术技巧的体现,还是作者北京生活经历的投射。作品中人物称谓是典型的北方方言的表述,其中称贾母为“老祖宗”(在满族习俗中称年长女性为“男称”以表示尊重),以及用“爷”“奶”作为称谓以表示尊重,例如贾珍被称为“大爷”,贾琏被称为“二爷”,贾宝玉被称为“小爷”,李纨被称为“大奶奶”,王熙凤被称为“二奶奶”,等等。这里的“爷”“奶”不是指血缘关系,而是等级身份的象征,以“大”“二”“小”等量词来区分辈分。此外,儿化音的使用更是北京方言的特色,如“哥儿”“姐儿”“昨儿”“今儿”等儿化音在文中十分常见。
在书写大观园空间与大观园之外的空间时,作者注意到两个空间性质不同,大观园空间是纯雅的,大观园之外的空间是世俗的,进而在不同空间安排不同的故事情节。大观园是由贾府的后花园改造而成,整体空间环境呈现出竹林成荫、花鸟成林的特点,故在大观园中叙述的事件多是文人雅事与儿女情爱。第三十七回偶结海棠社,下雪对诗、中秋对诗、螃蟹宴对诗,尽情表现人物才华与文人雅趣。第二十三回宝玉偷读《会真记》时刚看到“落红成阵”便“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2]164,紧接着黛玉便出现在眼前,作者将自然环境与戏文相映成趣,进而营造了美好、单纯的情爱环境。相比而言,大观园外的空间是世俗空间,故叙事多是世俗肮脏之事:第十二回王熙凤在荣国府毒设相思局致贾瑞丧命;第十五回王熙凤在馒头庵依仗贾府与长安节度使的关系,受贿三千两银子,拆散金哥与原任长安守备之子的婚姻,最后导致二人双双殉情;第七回焦大大骂宁国府乱伦丑态;秦可卿丧事、元春省亲各种宴会等均可见贾府。
上述各种空间交替变化,将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巧妙融合,从而构成了红楼故事的大舞台。
二、《红楼梦》现实空间的表现形式
《红楼梦》中描写的现实空间类型多样,如居住空间、宴饮空间、花园空间、寺庙空间、农庄空间等。总体而言,其现实空间主要通过空间铺陈和空间转换的方式呈现出来,且空间铺陈与空间转换并不是独立存在,它们往往交替结合。
空间铺陈指对现实空间的地理方位、自然环境、陈列摆件等方面进行铺陈,从而呈现出某一空间特点。林黛玉从西角门入荣国府再向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2]21。她进入堂屋,堂屋上赤金九龙地大匾写着“荣禧堂”,堂屋内“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2]21。大紫檀案、三尺高铜鼎、墨龙大画、十六张楠木交椅这些壮大、华贵的摆设都显示出屋主人身份非凡,而十六张交椅更表现屋主人常在这里宴客,用林黛玉的话来表达对贾政院落装修的感受就是“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2]21,这便是通过空间方位、建筑陈列的铺陈呈现特定空间的整体布局。
空间转换是从一个空间转换到另一个空间,与空间铺陈密不可分。在林黛玉进贾府的过程中,作者正是通过空间铺陈介绍了不同人的不同居所的特点,又通过空间转换推动林黛玉进贾府这一情节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呈现了贾府的面貌,并对空间铺陈进行补充。第四十回刘姥姥进大观园,每转到一个空间,便有一处空间铺陈。她先去了林黛玉的潇湘馆,然后去了探春的秋爽斋,接着又去了惜春的暖香坞和宝钗的蘅芜苑,最后来到宝玉的怡红院。其中,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情节描写还伴有居住空间与宴饮空间的转换。居住空间凸显各处人物个性,也表现贾府华贵陈设的特征,而宴饮空间便是直接写出贾府奢靡的现象。作者正是通过空间的移步转换,从而使贾府形象更为立体。此外,秦可卿办丧礼的过程也体现出空间铺陈与空间转换交替,从居住空间到寺庙空间的转换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即小说从秦可卿之死的情节转移到王熙凤弄权害人之事上。
由此可知,空间表现形式推动了空间叙事的实现,《红楼梦》作者正是通过对现实空间的铺陈与转换来实现其叙事意图的。
三、《红楼梦》现实空间的叙事功能
《红楼梦》现实空间的叙事功能也是通过空间铺陈与空间转换实现的,其空间铺陈与空间转换对于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关系表达、叙事节奏调节以及叙事线索梳理都有映衬与推动的作用,《红楼梦》现实空间的叙事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借现实空间布局表现人物性格、关系、地位
蒲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写道:“大观园的空间布局,为《红楼梦》设定了一个特定的空间环境。怡红院、潇湘馆、梨香院、稻香村、栊翠庵等等的布置,在小说的每一步发展中都有空间上的意义。”[1]110不只是大观园,《红楼梦》现实空间不仅能表现人物性格,空间布局还能彰显人物关系与地位高低。
作者在描写林黛玉的潇湘馆时重在对自然地理空间的铺陈描写,突出清幽的特点。贾政在游园题对额时所见“有千百竿翠竹遮映”[2]112。第二十三回林黛玉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2]163此话既突出潇湘馆竹子之多,又呈现其幽静的特点。自古“竹”乃君子表征,苏东坡说:“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5]竹子象征着高雅的情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竹子中通外直的形貌也象征一种傲然骨气。竹子象征林黛玉孤傲清高的特点,也暗示其命运多舛。第三十七回探春开玩笑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2]255《红楼梦》中落泪桥段最多的当属林黛玉了,伤己落泪,生气落泪,怀乡落泪,感物亦落泪,一生为爱人宝玉落泪最多。
而作者在描写探春的秋爽斋时则更注重对人文空间的铺陈,突出阔朗的特点。秋爽斋中“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2]279,屋内放着“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2]279,一边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2]279,一边墙上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2]279,左右两边还挂有“颜鲁公墨迹”的对联,俨然是一个公子的房间。这将探春阔朗、精明能干的个性赋予在巨大的空间器具与繁多的文士物品之上,使得人物性格与空间环境相映成趣。此外,雪洞一般的衡芜苑与宝钗冷静稳重的个性,花团锦簇的怡红院与宝玉钟爱女儿的个性等,都可见现实空间铺陈与人物性格的关系。
空间距离也暗示了人物关系。第二十三回宝玉道:“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2]163宝玉岂是喜欢清幽之人?宝玉最喜欢热闹了,平日里都是和姐姐妹妹们混在一起的,今日之喜清幽,无非是应和林黛玉的,由此可见潇湘馆和怡红院相距很近。从贾政游园路线上看,他进园先见的是潇湘馆,而出园则是从怡红院后门出去便看见大前门了,也说明两人住处很近,都在大观园正门附近,其实也暗含两人的关系最亲密。而薛宝钗的居所却是距离贾宝玉最远的,怡红院在大观园进门处,大致在东南角,而衡芜苑在西北角,两处是遥遥相望的。地理空间的距离也是人物心理空间距离的隐喻。宝玉是不喜欢仕途的,而宝钗确是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女子,以仕途举业为重,思想的距离是宝钗和宝玉之间最根本的壁垒。空间布局也是人物身份的象征。从林黛玉进贾府的路线可见,贾府空间分三路,贾母居左,贾政居中,贾赦居右。作者在对贾母的居处进行空间铺陈时,写道“轩峻壮丽”[2]20。中国古代以左为尊,贾母居处正是居左,这体现了贾母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贾政居处正是贾府的中央,当作者对贾政居处进行空间铺陈时又与贾母处作对比,不同于贾母居处,贾政居处是“四通八达,轩昂壮丽”[2]21,这从空间方位上更凸显了贾政一家之主的重要地位。
(二)借现实空间转换调节叙事节奏
苗怀明在《〈红楼梦〉的叙事节奏及调节机制》中指出文本的“主次、疏密、详略、张弛、快慢的安排和搭配就构成了作品内在的叙事节奏”[6],现实空间转换便是叙事节奏调节的主要形式之一。
《红楼梦》作者通过南北空间转换描写来调节叙事节奏冷热。例如,薛家进京除了文中所写送妹待选、探望亲人、打点生意、游览风光的原因,还有叙事安排的原因。在临近进京前,作者安排薛蟠惹上人命官司,此时薛蟠是否要抵命、宝钗能否进京、香菱能否重回家中、雨村能否秉公执法都成为读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为了加快薛家进京步伐,作者将这摊难事留给薛家人解决。此时南北叙事空间发生转换,将一个极大的矛盾暂且留于南方空间,读者跟随薛家进入北方空间,因而既解决了紧迫的矛盾又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红楼梦》作者通过南北空间转换来调节叙事主次。《红楼梦》前四章通过黛玉进京、宝钗进京将主要人物转入主叙场。而第十二回作者突然安排黛玉奔丧情节,将林黛玉调离主叙场,其主要原因是为后文写凤姐和秦可卿做铺垫。在《红楼梦》中宝黛是主要人物,凤姐和秦可卿是陪衬人物,主次人物在同一时空中不写主要人物而重叙次要人物似乎是不合理的。此外,第九回宝玉上学前与家中长辈辞别后,又单单与黛玉辞别,可见二人关系不同别人,而黛玉习惯以尖酸之语调侃宝玉,宝玉也紧着上学没多理会,将两人从同一空间分隔开来,使原本即将发展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如果两人同在一个时空,小矛盾可能激化成大矛盾。如第二十九回黛玉因担心宝玉伤病前去探望,反不得进怡红院一事,逐渐发展为两人的大矛盾,甚至惊动了贾母,但这也是两人情感加速升温的阶段。如果第九回便做上述情节安排则会出现主次颠倒、情节发展过快的弊端。当第十二回黛玉要回扬州时,“宝玉大不自在”[2]82,宝玉表现出难舍之情,因距离远而产生惦念之感;而第十六回黛玉从南方空间回到贾府,用以慰藉宝玉经历秦可卿之死、秦钟大病的心痛,文中写到宝玉听了黛玉回来“方略有些喜意”[2]102。可见南北空间调动可缓和宝黛矛盾、增进二人情感,同时更是为了调节叙事重点。
此外,叙事节奏的调节还可通过小空间频繁切换构成大空间,小事件汇聚成大事件。正所谓“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7],使得叙事节奏波澜起伏,读之饶有趣味。林黛玉进贾府这一大空间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带读者领略荣国府全貌,她路过宁国府,进入荣国府,先到贾母处、贾赦处,再到贾政处,路过凤姐处,又回到贾母处。随着黛玉进入不同空间,看到不同院落装饰,见过各位长辈、姊妹,粗略为读者展现了各种人物性格与不同地位。同时,林黛玉进贾府这一空间展现也为下文叙述做了多方面铺垫。例如,黛玉在贾赦处见其房屋院宇,猜想是荣国府花园隔断过来的,小说夹批中也写道“为大观园伏脉”[2]20;小说写贾政在斋戒时夹批道“点缀官途”[2]22,这为日后贾政以仕途为业的思想做铺垫,也预示着贾政与宝玉价值观的对立;黛玉曾偶遇癞头和尚赠药方,宝钗也有癞头和尚赠冷香丸药方,宝玉又多次受癞头和尚点化,僧人形象有意无意穿插其中,展现人物间的联系,也暗示佛家“空”的思想。宝玉最终出家,可见“小浪”之下暗伏“大浪”。
(三)借地理空间转换暗示叙事线索
《红楼梦》的叙事线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逐渐萧条,贾家逐渐败落;另一方面,人物从南方空间转向北方空间,南方是贾家的根基,是繁荣的象征,贾府由南到北预示着家族的衰落、命运的悲剧。
从作者的人生经历看,也有由南到北的空间调动。曹家被抄后,从富足的南方转向北方,逐渐败落。而贾府正有与之相似的变化,贾雨村在演说荣国府时说贾家金陵老宅占尽大半条街,而文中出现的贾府则主要是北京贾府。贾家由南方空间转向北方空间,在北方空间中经历了元春省亲、农庄减产、家族被抄等事件,表现出收支不均,加上贾府内部奢侈、腐败,一代不如一代的儿孙,这些使得贾家逐渐萧条,展现了一条“北上而衰”的空间线索。
同时,人物命运也有“北上而悲”的空间线索。《红楼梦》首写林黛玉离家,林父言:“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2]17可见黛玉离家实属无奈。依傍祖母看似一件好事,但对林黛玉来说,北上便是从父母之爱的环境走向寄人篱下的环境。初入贾府,她处处小心谨慎,从南到北之路也是林黛玉走向悲剧人生之路。再看薛宝钗和香菱进京,各自都是无奈之举。薛宝钗进京是按当时规定“凡仕宦名家之女,皆报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人才赞善之职”[2]30。又逢薛蟠惹上人命官司,这又为进京加上另一个“不得不”的理由。同时,薛家到薛蟠这一辈已再无发展,薛蟠不务正业并不能支撑薛家繁荣,进京也可获得一些贾家的帮助。可见,他们进京不是在自身富裕的时候离开的,而是出现祸患才离开。此外,香菱进京更属无奈。香菱是悲剧人生的代表,幼年被拐子拐走,家人多方寻找未果,后来父亲出家,家中已经无人可以再寻找她了,她只能听天由命随主家生活。她的离家甚是无奈,无奈家中无人寻,无奈前路杳迷茫,无奈不能左右个人人生。
总之,作者在创作上以巧妙的笔法将现实空间作为叙事手段,不仅表现出典型空间中的典型人物、人物身份地位以及人物关系,并通过现实空间转换调节叙事节奏,理清叙事线索,实现了现实空间的叙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