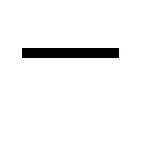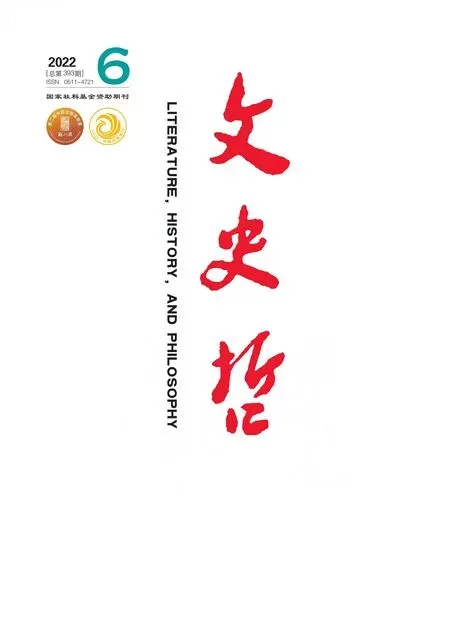中非文学的交流误区与发展愿景
——关于《雷雨》在尼日利亚的归化改编
朱振武
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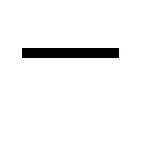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一家驻非中国公司的非洲工人罢工,不仅“触及了中非之间敏感的经济话题,也为国际媒体长期以来的‘新殖民主义’的论断提供着砝码与支撑”(2)刘东:《费米·奥索非桑的非洲、文学与中国》,2015年12月8日,http://www.oir.pku.edu.cn/info/1037/2782.htm.。奥索菲桑蓦然找到了《雷雨》与当下中非境遇的契合点,便将之改译为英文版《全都为了凯瑟琳》(AllforCatherine)(3)奥索菲桑改译的英文版《全都为了凯瑟琳》(All for Catherine)尚未单独出版,本文依据的是《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收录的杨梦斌译本。,后来又亲自执导,将其搬上北京大学的舞台。这部非洲版《雷雨》是第一部由非洲人翻译、改编并执导的中国戏剧作品,作为中国文学走进非洲的典型案例,个中得失及启示值得细思和深究。
一、《雷雨》在非洲的归化迻译与本土化改编
曹禺话剧《雷雨》(1934)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际上也是“知名度最高、影响面最为广泛的”中国现代戏剧(4)王伯男:《曹禺及〈雷雨〉的跨文化传播》,《上海戏剧》2014年第10期,第50页。,先后在二十多个国家上演。考察本剧的传播史,我们看到,如大多数中国文学作品一样,《雷雨》在国际上的百年传播与接受呈现出“亚洲热、欧美冷”的局面,更鲜少进入非洲观众或读者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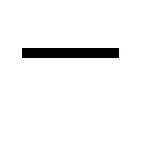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奥索菲桑首先从舞台表演的技术需求出发简化了《雷雨》的结构。一是大刀阔斧地删除了原著的“序幕”与“尾声”。这两处情节发生于正剧故事结束十年之后,周朴园前往医院探视罹患精神疾病的周蘩漪。作为正剧的延续,这两部分必要与否,自《雷雨》发表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议。在许多人眼里,“序幕”与“尾声”“不仅在情节上与正剧是游移的,而且在氛围上也显得与正剧的紧张激烈并不协调”(6)刘勇:《从戏剧冲突到命运冲突——曹禺剧作的诗性生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第99页。。早在1935年本剧于东京首次公演时,导演吴天就将其删掉,并解释说:“首尾都是多余的,因此大胆地删除了”(7)吴天:《〈雷雨〉的演出》,《杂文》1935年第2期,第34页。。奥索菲桑原本就有简化原创剧本的舞台设计以适应业余演出的习惯,删减这两部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舞台表演之需。二是他将原著的四幕合并为两部分,并压缩了戏剧时间。原著《雷雨》共四幕,其中第一、二、四幕均以周公馆的客厅为场景,第三幕的场景则转移到了鲁家。奥索菲桑将四幕合并为两部分,都以李伟业别墅的客厅为场景,原著的第三幕鲁家人(对应埃提姆一家)的对话也改在这里展开。《雷雨》的时间跨度是从当天早晨延续到午夜两点多钟,而奥索菲桑则将其压缩为当天上午和下午。英文版《全都为了凯瑟琳》和原著一样严格遵守“三一律”,但前者的时空结构更为简化。
奥索菲桑改变了《雷雨》发生的年代与国度,以此来增强中非文学的对话氛围。原著《雷雨》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奥索菲桑则将其转移到90年代下半叶(约1997年)的尼日利亚。他还修改了角色姓名以适应戏剧时空的变化,如周蘩漪改为王艳,周萍改为李龙,周冲改为李虎,如此一来,改编后的戏剧就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性。相应地,剧中人物周朴园由煤矿公司董事长变成了在尼日利亚经营水稻种植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李伟业,鲁侍萍变成了尼日利亚黑人女仆契卡(埃提姆太太),周宅仆人鲁贵变成了黑人奴仆埃提姆,鲁大海变成了非洲工人托尼,鲁四凤变成了李伟业家的女佣凯瑟琳(8)托尼是李伟业与契卡的私生子,凯瑟琳是契卡与埃提姆的女儿,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与《雷雨》原著中鲁大海和鲁四凤的关系一致。。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原著人物的社会背景与形象,使本剧具有了明显的非洲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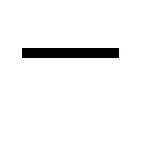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从中非文学交流史角度看,奥索菲桑迻译《雷雨》再次开启了中非文学交流的大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与非洲各国有着一致的反殖反帝诉求,中国始终高度重视中非关系。在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引领下,中非文化关系也开始起步。从1956年起,中国与埃及互派文化代表团。1957年之后,郭沫若两度访问埃及,写下了《金字塔》《埃及,我向你欢呼!》和《游埃及杂吟十二首》(一作《访埃杂吟十二首》)等诗歌。1962年,以茅盾为团长、夏衍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开罗参加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9)同行的还有杨朔、冰心、严文井、艾芙、叶君健等知名作家。参见张华、赵璞:《人文学术:东方与西方》,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页。。这些活动掀起了第一次中非文学交流的热潮。从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翻译引进了大量非洲文学作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非洲文学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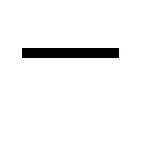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奥索菲桑至今已创作或改编戏剧50多部,其作品先后在非洲、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上演,无论是在非洲大陆还是在欧美西方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非洲著名作家,奥索菲桑首次主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对其进行一系列非洲化改编,为中国现代话剧与非洲戏剧提供了碰撞与对话的机会。他的改译变换了原著的戏剧时空与人物形象,把非洲本土较为尖锐的殖民问题、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等融入到角色的命运冲突之中,对原著的中国隐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非洲化转换,彰显了奥索菲桑艺术观念中强烈的非洲意识。这些改变固然有利于作品在非洲的传播与接受,但是改译者的归化策略可能带来的误读风险也不可忽视。毕竟,非洲在中国的形象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印象、政治话语及西方媒体报道的歪曲化渲染。
二、《雷雨》在非洲的误读空间与隐喻性转换
奥索菲桑将《雷雨》的文学隐喻转向非洲本土,使这部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话剧在新的时代与语境中焕发出别样光彩,但也正是这种顺应接受语境的翻译策略,同样会给中非文学交往创造误读空间。原著中女仆鲁侍萍被扫地出门是因为她与周朴园门不当、户不对,阶级差距是主因。而在奥索菲桑的译本中,仅用贫富差异和地位悬殊来解释契卡与李伟业之间的恩怨并不充分。虽然奥索菲桑有意保留了阶级差距原因,但种族差异或种族歧视也成为“棒打鸳鸯”的重要原因。英文改译本中的李伟业(对应周朴园)私通黑人女佣契卡(对应鲁侍萍)并使其怀孕。李伟业母亲抵达尼日利亚后“非常严厉地批评他居然和黑人搞在了一起”(12)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杨梦斌译,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39页。,并于除夕夜将契卡赶出家门,后来契卡生下了混血儿托尼(对应鲁大海)。多年后重逢,契卡回忆说:“……你是中国人而我是尼日利亚人。那时候你妈妈来了,你突然想起了我们的不同。你记起来我是个穷人你是个富人,是个富有的外国人”(13)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42页。。从这些细节看,李伟业抛弃契卡的原因既有种族因素也有阶级因素,但后者比重更大一些。
奥索菲桑显然比曹禺更加突出劳资冲突的尖锐性。托尼与妹妹凯瑟琳之间的对话表明,以李伟业为代表的资本家与以托尼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冲突。
托尼(恨恨地):你看,在这里的大多数外国企业主,尤其是像李老爷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不怀好意的。我见惯了过去那些年他们在种植园里的勾当,我很了解他们。他们假装自己是来帮助我们的,其实他们只是来把我们的国家敲诈干净。我恨透了他们。
……
托尼:别告诉我你是瞎子,凯瑟琳!甚至就拿这个房子,这个富丽堂皇的房子来说,你会说你不知道它是用那些大米磨坊里被压榨的工人的血建成的!(14)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02页。
这两段对话表明,托尼清楚地意识到外国资本对尼日利亚人民的压榨与剥削。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向凯瑟琳揭露了资本家的欺诈与伪善:
凯瑟琳:李老爷给几百个失业的人安排了工作。每年他都给几个我们绝望的青年提供奖学金。所以,如果他自己建造一个像样的房子,又有什么不好呢?(15)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02-403页。
托尼:他当然玩得起慈善家那一套,他们都那样做了,不是吗?这些有钱的外乡人。
……
托尼:来求一个自己心安,不是吗?在累死了那么多工人之后,做出这些善行!但是你看到过他生活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人民中间吗?决不会!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房产,这些闪闪发光的新豪宅,还用高高的栅栏围上,因为他们轻视我们!(16)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03页。
而且,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资本家不会因为肤色而有所不同,所有富人阶层、“大人物”都是一丘之貉,与穷苦百姓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凯瑟琳:不是还有些尼日利亚人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吗?
托尼:没有什么不同,亲爱的妹妹!我这不是在说他们的肤色。这是对你我这样普通人残酷的剥削,他们和我们的政府串通起来,用增加就业的名义来诈骗我们。所有的大人物都在骗我们,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这是那一小撮富人和穷苦的、无力的大众在对抗。(17)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03页。
托尼对资本的认识本质上是奥索菲桑思想的反映,上述几段对话就已经清晰地表达了奥索菲桑的阶级意识。此外,奥索菲桑还通过剧中角色托尼多次痛斥李伟业为富不仁、官商勾结、虚伪欺诈、剥削乃至屠杀工人的恶行,展示了本剧中劳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托尼:不,都是假的。你伪造了这张纸(即复工协议)来骗我们。所有的工人们都看到他们的同胞被你们的安保人员扫射——足足三十个啊!你知道的!——他们不能……不能像这样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就屈服,没有——不!你伪造了这个文件,你这下贱肮脏的骗子!(18)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44页。
托尼:……你们这些富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尼日利亚人,都无所不用其极地去赚钱,不管手段有多脏。偷、抢、杀——(19)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45页。
就连酗酒嗜赌、爱慕虚荣、奴颜婢膝、贪图小利和怂恿女儿凯瑟琳委身“龙少爷”(李龙)以攫取钱财的仆人埃提姆也背后怒骂“这些姓李的毫无道德,毫无顾忌”(20)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06页。。而在李伟业眼中,非洲工人懒惰、奸诈、不忠诚。他反复强调:“这些工人,对他们的老板是一点忠诚都没有——”“你问问这里大多数的老板们,他们都会告诉你,黑人是懒惰和不值得信任的!”“这里普通工人的心态都是你在剥削他,不管你给他们付了多少钱!他就是要……蓄意破坏你生意……”“我们所有开公司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的不忠诚。”(21)费米·奥索菲桑:《全都为了凯瑟琳》,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第417页。
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些非洲作家开始从阶级视角分析问题。他们描绘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甚至鼓动颠覆存在压迫与剥削的社会秩序。这类主题在非洲戏剧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东非的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 1938- )、米塞尔·吉泰·穆戈(Micere Githae Mugo, 1942- )、易卜拉欣·侯赛因(Ebrahim Husseni, 1943- )和穆科塔尼·鲁杰恩多(Mukotani Rugyendo, 1949- )为代表的作家,他们面向知识阶层创作西方式的严肃戏剧;另一种是奥索菲桑、博德·索万德(Bode Sowande, 1948- )、科勒·奥莫托索(Kole Omotoso, 1943- )和奥拉·洛第米(Ola Rotimi, 1938-2000)为代表的尼日利亚作家,他们面向普通民众创作通俗戏剧。这两类戏剧主题相似,即“揭穿资本主义的神话体系,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秩序”(22)Saint Gbilekaa, Radical Theatre in Nigeria (Ibadan: Cultop Publications Nig Limited, 1997), Introduction.;它们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启发、唤醒民众,并让他们相信自己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奥索菲桑同情被压迫阶级,谴责权力集团,甚至鼓动推翻现政权,具有明显的左翼思想倾向,而书写阶级对立与阶级冲突是其戏剧作品的常见主题。《阿尔廷的愤怒》(Altine’sWrath,1986)描述了不公正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阶级分层——以拉瓦尔(Lawel)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和他的妻子阿尔廷(Altine)所代表的被压迫者。《红色是自由之路》(RedIstheFreedomRoad,1983)讲述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与剥削,进而导致了被压迫者奋起反抗的故事。尼日利亚第二代作家普遍视“文学为社会变革的武器”,奥索菲桑就明显“继承”(heir apparent)(23)Muyiwa P. Awodiya, The Drama of Femi Osofisa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badan: Kraft Books Limited, 1995) , 25.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他不仅支持无产者反抗国家的结构性压迫,倡议穷人与被践踏者不再温顺地接受暴政和权威的枷锁,批判一切压迫者及其代理人,还试图让观众行动起来,变革腐朽的社会秩序。这种通过“激发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从而推翻和改变现状”(24)Muyiwa P. Awodiya, The Drama of Femi Osofisa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25.的做法是“革命性”的,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影子。从阶级立场来看,奥索菲桑对《雷雨》作如此改编是有其思想渊源的。
然而我们也看到,他的改编将富人与穷人、资本家与工人、中国人与非洲人放置到对立面,这很容易引发非洲读者对中国的负面想象。奥索菲桑本人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根据非洲文学研究者程莹的说法(25)奥索菲桑在中国访问期间,程莹在北京大学亚非系攻读非洲文学研究生,她作为陪同和翻译参与了奥索菲桑全部的讲座与交流活动。参见刘艳青:《中国:另一扇探索之窗——一位非洲作家的中国印象》,2011年11月23日,http://www.chinafrica.cn/chinese/abc/txt/2011-11/23/content_413281.htm.,奥索菲桑对《雷雨》的改编至少有六种不同版本。他将其早期版本寄给他的中国学生、同事和朋友,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沟通,他最终接纳了读者的意见,删除了李伟业关于“堕落的尼日利亚青年”(degenerate Nigerian youths)、“懒惰、惹事、偷盗的尼日利亚人”(lazy, troublesome, thieving Nigerians)等一些夸张而直截了当的评论(26)Cheng Ying, “History, Imperial Eyes and the ‘Mutual Gaze’,” 106.。即便如此,程莹仍然认为,“在这部旨在促进‘跨越地理和种族边界的相互理解’的戏剧中,仍然存在着刻板、夸张的中国形象”(27)Cheng Ying, “History, Imperial Eyes and the ‘Mutual Gaze’,” 97.。如果是出于不同艺术理念和文化基质的改编,尚能将误读限制在文学领域,但将种族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矛盾糅进剧本,就可能使误解突破文学界阈进入现实层面,从而对当下中非关系的相互体认产生一定消极影响。
的确,中非文学间的误读风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现实存在的。刘洪耀小说《混血儿》的主人公朱文惠在东非先后遭遇武装劫匪、非法监禁和军事政变,作品中的暴力、野蛮和混乱的非洲印象,既有作者对非洲现状的有感而发,也与西方媒体的大力渲染脱不开干系。赖翠玲的自传体小说《嫁到黑非洲》(1996)以切身经历述说了一段荡气回肠的跨国界、跨种族的爱情故事,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嫁到非洲》曾荣获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书写中国人与非洲黑人之间浪漫爱情的作品也曾饱受国内观众的质疑。中国香港电视剧《天涯侠医》(TheLastBreakthrough,2004),一部反映中国医生无私援助非洲并与当地人结下深情厚谊的作品,也被怀疑是医生因医术不精而不得不靠情感(empathy)疗法去医治病人(28)参看Karen Laura Thornber, “Breaking Discipline, Integrating Literature: Africa-China Relationships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2016): 708.。
同样,不少非洲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充满了话语偏见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色彩。小说《我们需要新名字》(WeNeedNewNames,2003)在涉及中国于津巴布韦开发项目的一章中,中国被描述成非洲人文与自然环境的破坏者,是一个“寻人吃的红色恶魔”,而欧美国家则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国家”(29)NoViolet Bulawayo, We Need New Names (New York: Reagan Arthur Books, 2013), 49.。阿迪契的《美国佬》(Americanah,2013)中,中餐、直发以及吃狗肉等皆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人被认为是“狡诈”(wily)的,中国的石油公司和其他外国石油公司一样都是“流氓”(riffraff)。《塔,国父不再》(Ta,O’reva(30)南非前总统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1918-2013)在科萨语中被尊称为“塔塔”(Tata),意为“父亲”。小说题名Ta O’reva源自宣传标语“Tata, Foreva!”,原意为“永远的父亲”,作者将标语修改后意义相反。,2014)初稿中的“烟消云散”(“All for nothing!”)一节,幻想中国控制了非洲大陆并于2031年将非洲合并成立“中非共和国”(Chica Republich)(正式出版时删除了这一章节)。短篇小说《兜售世界力量》(“Selling World Power”,2007)则暗示中国货币将取代肯尼亚货币,中国经济也将最终控制肯尼亚经济。这样的认识与评价既体现了某些非洲作家的偏听偏信,也反映了西方话语对非洲观念的影响与渗透之深。
三、中国文学的价值诉求在非洲的接受与龃龉
当然,奥索菲桑显然不是有意针对中国资本的,因为跨国资本在尼日利亚早已成为过街老鼠。1960年独立后,尼日利亚成为国际资本的逐鹿场。以石油产业为例,到1970年时,石油经济已经成为尼日利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尼日利亚政府虽然控制着石油资源,但其开采、提炼等生产过程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致使政府很快沦为西方跨国石油公司的买办。精英阶层与跨国公司相互勾结,从中收取巨额回扣,大量财富转移到私人手里,而普通民众却承担着石油污染的后果,致使人民对政府和跨国公司都非常不满。90年代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奥戈尼九君子”(Ogoni Nine)事件(31)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盛产石油,但这里的五十多万奥戈尼(Ogoni)人却无法分享这一资源带来的收益。他们请求政府公平分享石油收益并采取措施阻止环境恶化,但境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为争取正义和自治,避免环境进一步恶化,1990年10月,他们发起“奥戈尼人生存运动”(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MOSOP)。1993年1月,30多万奥戈尼人举行示威游行。1994年5月,4名奥戈尼酋长遇害。阿巴查(Abacha)政府将其归罪于“奥戈尼人生存运动”组织,逮捕了包括著名记者、作家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 1941-1995)在内的九位领导人。这九位领导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秘密执行。这起事件引发广泛的国际批评或制裁,尼日利亚被中止英联邦成员国资格三年。参见托因·法洛拉:《尼日利亚史》,沐涛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871页。,二是杰塞(Jesse)石油管道爆炸事件(32)杰塞地区盛产石油,但其他产业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困,一些穷苦百姓铤而走险,从石油管道窃取原油转卖谋生。1998年10月18日,杰塞石油管道爆炸引发火灾,附近整个村庄被毁,1000多人丧生。这起事故激化了民众的反政府与反跨国公司情绪,他们组织起来破坏输油管道,攻击政府及其支持者。参见托因·法洛拉:《尼日利亚史》,第199页。,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跨国公司的敌视情绪。
这种情绪通过新闻、戏剧与各种传言不断发酵,演变成敌视国际资本的话语环境,至于资本的主人是谁,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人们并不关心。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尼日利亚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企业开始在尼日利亚大量投资,中国资本逐渐成为国际资本的代名词,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的敌视对象。如此说来,虽然没有创作过批评国际资本的作品,但考虑到其左倾立场以及这样的国内语境,奥索菲桑在《全都为了凯瑟琳》中突出劳资之间的阶级对立就更容易理解了。
显然,奥索菲桑是一位突出主体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对非洲社会现实高度关切的作家。其创作深受第一代戏剧家索因卡、克拉克及奥拉·洛第米等人影响,曾对前辈们无视非洲现实问题颇多訾议,既有批评时政的,也有表达主体诉求的。如反对戈翁(Yakubu Gowon, 1934- )军政府的《闲聊与歌声》,讽刺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 1937- )政府的《谁害怕索拉林?》,批评谢胡·沙加里(Shehu Shagari, 1925-2018)文人政权的《午夜旅馆》(MidnightHotel,1986)以及批评巴班吉达(Ibrahim Babangida, 1941- )军政权的《阿林金丁和守夜人》(AringindinandtheNightwatchmen,1991)等即属前一类。奥索菲桑幼年丧父,在颠沛流离中读完大学,生活非常贫困。这一经历使他对尼日利亚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更加敏锐,对阶级矛盾理解更加深刻,对独裁统治与腐败政治的憎恨更加强烈,宣称通过“革命”建立人民的政权——“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逃出……悲惨的循环:必须把暴君从权力的楼梯上拉下来,底层人民必须获得权力,必须组成代表人口各部分的开明领导集团,以之取代现在的篡位者”(33)费米·奥索菲桑:《“秘密起义”:军人统治下的后殖民国家戏剧》,黄觉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年第4期,第123页。。奥索菲桑的这种创作意识在改译版《雷雨》中也有充分体现。
改编后的作品中,李伟业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资本家,家族在乔斯(Jos,尼日利亚城市)操持矿业多年,后来经营水稻种植公司又积累了大量财富,是一位典型的外国资本家。原著周朴园所代表的封建家长制对家庭的独断专行,在新版本中虽然都有所保留,但剧中他与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特别是改编之后中国老板与尼日利亚工人之间的劳资矛盾,构成了奥索菲桑作如此改编的内在动因。奥索菲桑的作品大都具有深刻的政治“启蒙性”,其创作就是为了唤醒民众,特别是唤醒知识阶层,并将他们培育为有担当、有作为的非洲社会领导阶层。可以说,在当下中非关系背景下,“中国如何自证‘双赢政策’,非洲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这些都是当前非洲文学的重要语境”(34)刘东:《费米·奥索非桑的非洲、文学与中国》。。高度关注非洲现实的奥索菲桑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启发中非知识界思考当下的中非关系,估计是奥索菲桑此举的重要目的和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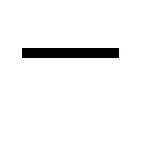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一般来说,译者的主体诉求难以离开特定社会语境的约束。经历过独裁政治洗礼的奥索菲桑深知,要想突破政治审查与限制,艺术家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以保护自身,并让对政府的批评与抗议“通过密道……抵达公众的视听”(36)费米·奥索菲桑:《“秘密起义”:军人统治下的后殖民国家戏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年第4期,第122页。,这就是他的“秘密起义”。奥索菲桑通过变换戏剧艺术的表达方式掩饰其创作的真实目的,让作品顺利通过审查并达到“公众视听”。可以说,他既具艺术自觉亦深谙避祸之道。他将原著《雷雨》中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冲突修饰为非洲工人与跨国资本之间的“新殖民主义”矛盾,将侍萍与周家的阶级差异涂抹上种族主义色彩,同时又让这些矛盾在人的命运冲突与悲剧面前显得不那么刺眼。奥索菲桑确实很好地把握了当下中非关系语境中雷池的边界。
另外,作为一位后殖民时代的作家,奥索菲桑及其他许多非洲作家的创作深受西方中心情结的支配。非洲文学呈现出“异邦流散”“殖民流散”和“本土流散”等三大流散表征(37)关于非洲文学的三大流散理论,详见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135-158页。。对非洲作家而言,跨越地理或文化空间的“异邦流散”司空见惯,然而,这些非洲作家为什么大多不来中国?个中有惯性思维使然,有空间距离使然,更有心理距离使然,但最关键的应该是其潜意识中深厚的西方情结使然。
非洲现代教育肇始于西方宗教的渗透与殖民统治。非洲高校直接以西方高校为模本,人文教育内容大多是西方的名家名作,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殖民语言在教育体系中广泛应用,使非洲知识分子更加亲近欧美文化。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政治腐败,政变频仍,政局动荡,一些非洲作家因言获罪,以致流亡欧美,成为异邦流散者。而在当下,一些新锐作家通过赢得西方设立的各种文学奖项提高曝光率,提高其知名度及其作品的销售量,“奖金的物质鼓励,非洲作家求知若渴;新鲜的精神刺激,非洲作家甘之如饴;广泛的国际认可,非洲作家更是翘首苦待”(38)赵白生:《非洲文学的彼岸情结》,乐黛云等编:《跨文化对话(第35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60页。,加上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及其话语的绝对控制,非洲作家喜欢聚集在欧美也就不难理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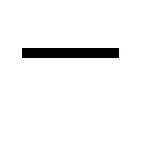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四、中国与非洲文学交流的困境与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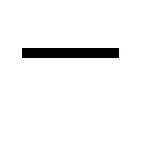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较长时间里,中非都曾难以摆脱西方的文化遮盖和话语建构,也曾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甚至以西人文论作为文学批评的依据和评判标准。中非之间的文学交流不光受制于西方话语,还受制于西方的出版渠道。中国文学越洋出海,更重视的是欧美市场,而且一定程度上以西方接受作为成功标准。而“西方媒介和语言的过滤决定哪些中国文学书籍将被配送到非洲国家,进而影响这些书籍在非洲的最终归宿”(41)凯瑟琳·吉尔伯特:《中国文学的非洲语译作太少了》,王会聪译,《环球时报》2016年11月23日,第6版。,许多中国文学译作就是这样经由美、英、法等国出版社进入非洲的。此外,中国文学的非洲本土语言译本严重缺乏,更不利于中非之间建立直接的跨文化对话。同样,非洲文学的优秀作品在过去也只能借道西方才能进入中国,决定非洲文学价值的同样不是非洲人而是西方人。如此一来,在中国、非洲、西方世界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他者”的三角:中国和非洲同为西方人眼中的他者,而处于中心地位的却是西方。
的确,很大程度上,中非文学中间依然横亘着辽阔的欧洲大陆,使中非文学交流与对话常常陷入边缘困境,使中非之间在美学观念上存在不少认识盲区。奥索菲桑对《雷雨》的改编就显示出他在中国传统文学知识方面的缺乏。他的改编有意观照中非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使英文版变成一部映射中非关系的“问题剧”,这恐怕是曹禺本人也无法认同的,也是许多学者不能苟同的。原版《雷雨》在东京首演后,曹禺曾表达不满,认为它“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42)曹禺:《〈雷雨〉的写作》,《杂文》1935年第2期,第34页。,是一首充满“幻想”的“诗”。曹禺其实更希望读者能读懂剧本对人类命运悲剧的诗意表达,而不是“斤斤以为艺术”“禽兽之不若”的“蒸母奸妹之剧”(43)罗亭:《雷雨的批评》,《杂文》1935年第2期,第36-37页。,也不仅仅是反映阶级斗争或封建大家庭罪恶的社会现实剧,它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命运冲突,是人类命运的冲突,是人类命运和宇宙关系的相互冲突,这种冲突本质上体现了曹禺对诗的追求”(44)刘勇:《从戏剧冲突到命运冲突——曹禺剧作的诗性生成》,第96页。。
奥索菲桑在改编中去除了“序幕”与“尾声”,与许多剧团将其删掉的原因如出一辙。根据舞台空间与表演的需要去掉这两部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考虑到曹禺戏剧的诗性追求,则“被删掉的序幕与尾声恰恰是曹禺最想要表现的东西”(45)刘勇:《从戏剧冲突到命运冲突——曹禺剧作的诗性生成》,第99页。。这两部分颇似《红楼梦》首尾处“大荒山无稽崖”顽石坠红尘的前情与历经温柔乡后的归隐之间的照应,也像极了《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魔”与“宋公明神聚蓼儿洼”的桥段。这些桥段与主体故事之间的关系看似不甚紧密,但这种叙事方式却频频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观阅期待。“序幕”与“尾声”是曹禺对中国传统叙事美学的继承,而奥索菲桑将其删掉固然便利了舞台表演,但也损害了原著的美学气象。而且,曹禺刻意营造的“白头发的老祖母讲从前闹长毛的故事”的氛围,为的是“在这氛围里是什么神怪离奇的故事都可以发生的”(46)曹禺:《〈雷雨〉的写作》,第35页。,为的是圆融过分偶然与巧合造成的情节突兀。在此处动刀的奥索菲桑显然还难以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表达方式,而这类知识空白会对中国文学的非洲之旅造成一定障碍,从而延缓和迟滞中非文学的有效交流。
奥索菲桑改变故事的年代和国度,改变人物的种族和国籍,放大非洲工人和外(中)国资本之间的冲突,这些都使戏剧冲突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一位中国老板与非洲黑人工人之间的矛盾,一位中国富家子弟与非洲黑人女仆之间的恩怨,这种改编在当下仍受西方话语严重制约的中非关系语境下,是否给新版本涂抹上一层“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这是值得担忧的。目前中非合作虽然硕果累累,但大多集中于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中非交往中人文关怀淡漠,对双方政治经济联系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缺乏关注,非洲人与中国人的私人关系不密切”(47)Karen Laura Thornber, “Breaking Discipline, Integrating Literature: Africa-China Relationships Reconsidered,” 697.,这一表述虽然角度不对,语意偏颇,但所言中非双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明显不够,交流意愿也还不算强,这点还是成立的。偏见、偏执与误解仍是时有之事。加之中国大批援助人员进入非洲后,西方那套“人权危机、环境污染、民族问题、专制独裁”等指责性话语的推波助澜,都易于引发非洲读者对这样改编的剧本做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解读,从而使中非双方读者都落入西方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话语的陷阱。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当下来看,中非文学都还处在西方价值与话语构建的边缘困境之中,要想突破这种困境并达到中非文学之间互知、互信、互鉴的目的,还需要双方坚持对自我的追寻与体认,需要摒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开辟直接的文学交流与对话渠道。奥索菲桑的改编表明,很多时候,在非洲读者眼中,包括《雷雨》在内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或许只是一起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作品的普遍价值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较为深刻的解读,因此,寻求文学对话的契合点对中非文化交流来说至关重要,这些都给中国文学“走出去”以深刻启示。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话题。研究者发表大量文章,从“走出去”的主体、策略、机制、路径、渠道、方法和意义等多个方面,对中国文学个案或文学文化出海作了有益探讨。这些成果较全面地梳理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现状,爬梳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对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实践大有裨益。然而,当前研究至少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默认将走进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评价作品成功“走出去”的标准,这从我们制定的目标语出版社的清单中就可以找到明证;二是对已经“成功”“走出去”的作品缺乏系统的、正反两方面的效果评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持续推动文学走出国门,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文学交流,在国际上营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进而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和文化多样性。很显然,归化过度不利于文学文化交流与互鉴,“心仪西方”更不能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状况,而不重视“走出去”效果则无法获知目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这些都会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根本目的的达成。奥索菲桑对《雷雨》的改译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也是双向的和立体的。
结 语
2016年9月20日,第23届开罗国际当代实验戏剧节(The 23rdCairo International Festival for Experimental and Contemporary Theatre)开幕,奥索菲桑受邀作为嘉宾出席,恰逢曹禺话剧《雷雨》(Thunderstorm)被选为开幕剧上演。这次演出由陈大联执导,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出演。演出结束后,埃及网络媒体金字塔在线(english.ahram.org.eg)发表通讯文章,认为本剧将“中国传统与当代文化、生活融为一体”,探讨了“僵化的传统主义与富人阶层的虚伪带来的灾难后果”,将“保守社会的严酷与奴性归因于权贵的腐败”,这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问题”(48)May Selim, “Chinese ‘Thunderstorm’ Brings a Haunting Past to Egypt’s Contemporary Theatre Festival,” Ahram Online, 21 Sep., 2016,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5/35/244383/Arts-Culture/Stage-Street/Chinese-Thunderstorm-brings-a-haunting-past-to-Egy.aspx.。应该说,这一评价符合人们对《雷雨》的一般认知,与陈大联导演“忠实”于原著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