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定义的伦理转向及其得失
韦庭学
尽管贫困有时候是一眼便可识别的现象,但是自从贫困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受到严肃对待以来,何为贫困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难题。长期以来,人们通常以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否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家庭或个体是否贫困。例如,联合国2015年根据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把国际贫困标准线上调至每人每天1.9美元。这里使用的是绝对贫困标准,它意味着收入低到“不足以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额度的生活必需品”(1)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London: Macmillan,1908),86.。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又根据自身的货币购买力对绝对贫困标准做出多样化认定。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一些欧洲国家率先解决了公民的食物、衣着、住房和医疗等基本需要问题,它们逐渐采用相对贫困概念来认定贫困。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主要考察特定社会中个体和家庭在多大程度上享有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相似的生活需要(2)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50-51.。例如,亚当·斯密在二百多年前曾以当时的欧洲人能否穿上亚麻衬衫为例,对相对贫困进行描述。他说,“严格来说,麻衬衫并不算生活上必要的……但是,到现在,通欧洲大部分,哪怕一个日佣劳动者,没有穿上麻衬衫,亦是羞于走到人面前去的。没有衬衫,在想象上,是表示他穷到了破脸的程度”(3)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03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部分发达国家在贫困治理中开始采用相对贫困标准。以英国为例,它把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60%”的家庭划定为贫困家庭,并对这些家庭(尤其是生活在这些家庭中的儿童)提供帮助(4)Paul Spicker,“Why Refer to Poverty as A Proportion of Median Income,”Journal of Poverty and Social Justice 20.2(2012):163-175.。可见,相对贫困概念关注的不只是生存问题,还涉及社会平等、公民尊严的获得,乃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伦理的视角对贫困进行分析和阐释。本文第一部分将首先考察传统贫困标准以及它们的理论基础可能存在的缺陷,探讨促使贫困定义伦理转向的客观原因;第二部分将主要考察西方学者从伦理维度对贫困概念所形成的新观点;最后,本文将对贫困定义的伦理转向在实践层面所产生的贡献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
一、传统贫困标准的缺陷
贫困的标准和定义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划分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大类别之中。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概念,最终通常都是还原到收入状况。随着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目标的多元化,一些研究者认为仅从经济收入维度来理解贫困存在诸多局限。因为收入多寡已不足以准确定义贫困现象。这一看似简单的理由背后涉及包括传统发展理念在内的诸多复杂理论问题。本节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促使贫困定义伦理转向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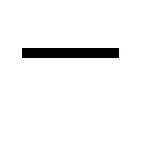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其二,贫困的考察对象不应当是集体或组织,而是个体。既有的各类贫困标准大多数都以家庭为单位。在上文中可以看到,即便像英国这样的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发达国家在制定贫困标准时也以家庭平均收入为单位,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也主张以家庭为对象考察和识别贫困。这一方法遭到了来自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严峻挑战。那些主张个人权利至上的研究者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方法忽略了因年龄差异、身体状况不同而对资源有不同需求的情况。例如,照顾老人和残疾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儿童比起成年人就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怀孕或哺乳的妇女需要更多的营养”(10)玛莎·C·纳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第41页。。马克思也曾表示,“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反之亦然。这就意味着,拥有相同收入的家庭,由于生活负担不同,极有可能出现一个家庭活得富足而另一个家庭则在贫困中挣扎的相反情景。因此,以家庭为单位所形成的贫困标准极有可能造成把部分急需帮助的人排除出受助行列的悲剧。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做法忽略了由观念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一些家庭成员获得了更多照顾,而其他成员没被公平对待的事实。“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包含争夺各种资源和机会的斗争。一些家庭成员得以在茶中添加牛奶,而另一些只能添加白糖;一些人获得上学的机会,另一些人则没有;一些人享受维持生命的医疗保健,另一些人则没有。”(12)玛莎·C·纳斯鲍姆:《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第53页。换言之,贫困是每个贫困者的亲身体验,根据个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和组织的状况来判断个体是否受贫困的困扰,这在某些情景下是不准确的。这种情况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没有完全获得认可的地方尤其突显。为此,努斯鲍姆明确主张各种政治、经济思想和公共政策必须关注女性在社会中权利被忽视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实,只有充分考虑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二等公民”这一现实,贫困和人类发展这些大问题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应对(13)玛莎·C·纳斯鲍姆:《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第3页。。
总体来看,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空间,一些人相应地认识到生存资料的基本满足并不就意味着摆脱了贫困。摆脱贫困意味着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而体面的生活包含着相应的伦理诉求。一些学者于是试图从伦理的角度对贫困进行重新定义和解释。
二、贫困定义的伦理化:从受社会排斥到可行能力被剥夺
贫困定义和标准的伦理化并不是当代学者的创新之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向前现代社会的贫困概念的回归性拓展。与现代社会普遍通过“贫困线”来识别贫困不同,在前现代社会中,贫困最初更多是在伦理和道德的层面被理解。在中国历史上,伦理解释是人们理解贫困的重要视角。孟子在建议齐宣王关于如何施行仁政时曾言,鳏、寡、独、孤之人乃“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14)《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3页。,并以周文王为例,建议齐宣王也要帮助穷人。虽然用当代人的眼光很容易看出孟子在此对穷人的划定一定也用了经济标准,但是他没有明确告诉人们,地主和富裕家庭的鳏、寡、独、孤者不是穷人。因而,有学者据此认为,如果根据孟子的表述来理解贫困,那么,这一概念“在社会问题这个层次上面也就等同伦理关系的问题”(15)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2页。,它指的是家庭结构不完整所造成的伦理缺憾。
贫困的伦理定义在西方世界也曾广受认同。根据英国著名社会经济研究者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的考察,在最早开启现代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之前贫困基本上还是一个道德概念。此时,社会对贫困的理解还带着宗教社会和道德社会的烙印。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地位获得确立,贫困和失业等概念才通过去道德化(demoralized)和世俗化的过程,在经济学意义上获得了它们的独立性(16)Gertrude Himmelfarb, 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4),100-101.。
当代社会从伦理、道德的视角来理解和阐释贫困,始于人们对“相对贫困”认识的细化和加深。在西欧发达国家,随着物质生活资料的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受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的限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政治家因此而宣称英国“几乎没有贫困”了(17)例如,在1976年和1986年,时任英国社会服务大臣分别指出,不断积累的富足已经让英国几乎没有贫困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些人虽然拥有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足够的条件参与到主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去。有人也把这部分人称为穷人。如此一来,贫困变成了一个可以根据具体社会状况进行建构的概念。它不仅与物质生活资料被剥夺有关,也蕴含着政治、文化、习俗和道德的内容。因此,有些研究者试图用更具现实解释力和道德感的概念,对贫困现象加以分析和阐释。在这些互竞的概念和方案当中,社会排斥概念较早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并逐步获得广泛的认可。
关于社会排斥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有研究者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保证个体和家庭获得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系统的崩溃和失灵”(22)Mark Shucksmith and Pollyanna Chapman,“R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xclusion,”Sociologia Ruralis 38.2(1998):230.,它和贫困一样,是一个多维和动态的概念。还有人指出,社会排斥是一部分群体“由于身体、社会、经济上的剥夺或歧视不能享有社会生活的福利”(23)Paul Taylor,“Democratizing Cities:Habitat’s Global Campaign on Urban Governance,”Habitat Debate 5.4(1999):2.。在对社会排斥概念的各种充满交叉和互竞的解释之中,希拉里·西尔弗(Hilary Silver)的工作获得了较为一致的认可。她在多篇具有较大影响的论文中把社会排斥定义为“在个体和社会层面上,社会纽带逐渐多维断裂的动态过程”(24)Hilary Silver,“The Process of Social Exclusion: The Dynamics of An Evolving Concept,”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95(2007):1.。对个体来说,它主要指无法参与到普遍的社会活动中,因而也无法建立起对自身有意义的社会关系;就集体层面而言,社会排斥反映了社会融合和凝聚力的不足。西尔弗还划分了社会排斥的三种范式(paradigm),即:团结范式、专业化范式和垄断范式。其中,团结范式指的是一个社会没有完全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纳入它的体系中,使每个人都变成社会的参与者。在西方和美国社会中,这方面的排斥主要涉及移民、少数族裔和生活在部分农村区域的边缘人群的生存困境问题。专业化范式指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市场经济把部分人群排除于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的现象,即专业化门槛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垄断范式主要指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自身的优势实现了不公平的利益最大化,从而造成其他人群选择受限,被排除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从上述分析来看,社会排斥和贫困概念之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社会排斥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团结不足、难以实现和谐的问题,而贫困更多关心的是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资料匮乏问题。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根据常识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可知,一个穷人或者一个贫困家庭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方面来看,确实难以融入社会的主流生活,穷人很难说没有受到社会排斥。这就引发了社会排斥和贫困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否存在联系的争论。持反对意见的论者认为,社会排斥是“一种平行、空间上的隐喻”,涉及的是人们融入或脱离主流社会;而贫困则基于一个“垂直的不平等模型”,它意味着有人“升入”或“掉出”某一社会阶层和收入分配结构(25)Daniel Beland,“The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Ideas and Policy Change,”Policy and Politics 35.1 (2007):123-139.。也就是说,社会排斥是一个“关系”问题,显示的是排斥者和受排斥者的差异和敌对。贫困则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贫困意味着贫困者成了匮乏的牺牲品,而社会排斥则不然,至少部分富人群体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情景并不鲜见。赞同的研究者则认为,对贫困和社会排斥做出区分是多余的,因为“社会排斥是一个比贫困更加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与贫困有密切关联的物质剥夺”(26)Ali Madanipour et al.,“ Concepts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Local Economy 30.7(2015):7.,用社会排斥代替贫困概念是理所当然之事。还有研究者对社会排斥和贫困这两个概念进行对比之后,认为两者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社会排斥和贫困一样是一个多变的概念,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其次,在社会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文献中,有很多论者把社会排斥视为贫困的同义词交替着使用,它们的共同点多于差异;最后,在关于相对贫困的一些概念分析中可以发现,贫困也涉及社会中一些群体占优,而另一些群体处于劣势地位的关系问题,它与上文提到的社会排斥聚焦于“关系”的探讨是一致的(27)Hartley Dean,“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12.。
学术界的争论和研究成果在部分西欧国家的社会政策制定中得到了体现。例如,欧盟委员会看到了传统贫困概念的缺陷,但是也没有主张完全抛弃这一概念并代之以社会排斥。在2010年,作为2020欧盟战略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在制定社会发展目标时要求,“到2020年,至少要减少2000万成员国公民处于或面临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风险”(28)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datasets/-/t2020_50.。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排斥与贫困处于并列地位,成为人们更加充分地理解社会贫困的重要补充工具。
如果说用社会排斥解释贫困源于法国,并成为欧盟的重要政策指导概念的话,那么,“可行能力被剥夺”就不但是英语世界的学者和政治家理解贫困的新视角,而且也成为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分析人类贫困的重要方法和理论。
可行能力路径(capability approach)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试图用来代替功利主义(增加算术总额)和罗尔斯的社会基本善的基本观点的一种正义理论。在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和其他学者进一步阐释之后,它成为当今人们理解和分析贫困、平等、人类发展和女性主义等核心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可行能力路径的核心价值是强调积极自由对个体的重要意义。森和努斯鲍姆认为,如果国家只是放开其干预之手而缺乏其他积极的行动,那么,对公民而言权利只不过是空头支票。所以,他们一再强调,判断一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的重要标准是看他是否具备“去做某事或成为某人的自由”(29)玛莎·C·纳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第46页。。一个人是否能够做什么或追求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他们的可行能力以及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可以说,可行能力和功能性活动构成了可行能力路径的两个基本评价机制。其中,可行能力指的是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30)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63页。。通俗来说,它是个体享有的实现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实际机会和潜能。功能性活动则反映了“一种或多种能力的积极实现”(31)玛莎·C·纳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第18页。。例如,受到正常的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获得自尊心、能够融入社会等等,都是实现功能性活动的表现。功能性活动是可行能力获得实现的结果。与前者相比,后者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例如,一个富人可以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在他身上实现的功能性活动和一个穷人是一样的,但是两者在可行能力方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状况。因此,森和努斯鲍姆都强调可行能力的优先性和重要性。
关于可行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可行能力的发展并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后天的社会环境在可行能力的培育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可行能力必须是低阶的能力,而非高阶的能力。正如人们不会期盼每个人都具备成为科学家或者奥林匹克冠军的能力一样。在此意义上,可行能力必须是基本的。努斯鲍姆在森的基础上列出了十项基本可行能力清单,并宣称这个清单对辩驳保持开放。
从20世纪80年代起,可行能力路径成为人们理解贫困的重要理论资源。最典型的表现是,森对可行能力进行阐述之后明确提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3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85页。。他认为,对贫困的这一定义将使人们对贫困的实质,以及人类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开展反贫困事业有新的认识。努斯鲍姆虽然没有对贫困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但是她一再强调十项基本能力在“最低限度水平上”获得满足的重要性。她认为,只要人们的任何一项核心能力未能获得满足,“这就应当被视为一种不公且悲剧性的处境并急需得到关注”(33)玛莎·C·纳斯鲍姆:《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第58页。。在她眼中,可行能力不能获得最低标准的满足无异于贫困。
从可行能力视角来看,贫困被定义为人的生活受到了严重束缚和摧残。这一定义不再局限于强调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它还抓住了人类生活的多元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还原性,试图从更加广阔和具体的视角来确认最低标准的人类生活应当是怎样的。
这一理论因为对贫困的认识和理解有新的突破而受到了较为广泛地认可。在森和努斯鲍姆等人的可行能力路径理论影响下,联合国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以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人类贫困指数(HPI)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2007年,在森和其他经济学家的倡导下,牛津大学创建了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该研究机构以森的能力方法为基础,“致力于建立和提出应对并减少多维贫困的更加系统方法和经济结构”(34)https://ophi.org.uk/about/.。这一机构提出的测量贫困的方法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纳,该署于2010年起在每年的《人类发展计划》中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35)多维贫困指数(MPI)围绕着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和十个具体指标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状况。代替人类贫困指数(HPI)发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多维贫困状况。
三、贫困定义伦理化的新意与局限性
贫困定义和标准的伦理转向充分表明,人类的反贫困事业在世界局部区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物质财富极度或相对匮乏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普遍认为贫困是关于“吃不饱饭”的问题。相应地,反贫困的工作往往只考虑穷人的“吃饭”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人,穷人除了有“吃饱喝足”的需要外,他们也有获得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克思曾经说,“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这就意味着,作为政治动物,人应当追求有价值的生活,国家和社会也要创造条件让公民追求有价值的生活。根据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渴望可能最为强烈”,而“如果……需要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与此同时,马斯洛也提醒人们,需求层次的秩序是会出现例外、重叠甚至是颠倒(37)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34页。。换言之,我们绝不能以为仅当对食物的欲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人才会出现对安全的需要;或者,只有充分满足了对安全的需要后,才会滋生出对爱的需要。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需要有可能是以平行或超常规的顺序出现的。正是因此,对穷人而言,很多时候生存、温饱问题和自尊是同等重要的,有些人甚至把尊严看得比物质需要的满足更重要。如果我们能理解穷人的上述心理,也就容易明白为何在社会交往中总是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可见,贫困定义的伦理转向将使人们认识到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一样,对贫弱者造成的伤害不容忽视。它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在国家政策的安排中,还是在社会舆论导向上,都要充分考虑那些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但依然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之处境。
另外,贫困概念的伦理化将促使反贫困策略向多样化方向转变。例如,如果以尊严得不到满足或社会排斥来定义贫困,那就需要考虑贫困感对人产生的伤害。尽管贫困感有时是一种充满主观情感因素的判断,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客观处境对他的心理认知具有深刻影响。以“城一代”为例,由于承担着房贷和各种生活压力,当他们与作为“城二代”“城三代”的同龄人相比时,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自己贫穷且低人一等。但是当他们回到农村,看到一些家长为了上中学的孩子一周100元的生活费而发愁时,或者看到一个病人因为付不起几千元医疗费而放弃做一项重要的手术时,他们的贫困感往往就不再像生活在城里时那么强烈。通过这个案例可知,人的贫困感是会随着情境不同发生变化的。可以说,降低社会成员的贫困感,将是未来反贫困事业中的一项长期任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为贫困唱赞歌,通过宣扬“贫穷是财富”来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要致力于通过改变社会现实来降低公民的贫困感,因为人们的社会情绪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体验息息相关。由此看来,如何进一步落实机会公平、权利平等和同工同酬等理想目标,将是未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从宏观层面上看,除了“东西、南北差距”问题依然需要重视外,如何在相同地区、相同行业和相同群体内部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将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人们的比较和攀比心理一般都始于和身边人或同行业、同龄人的对比,而且这种对比对他们的影响是最深刻的。这正如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犀利地指出的那样,“近亲、同事、与同养之人”之间很容易滋生攀比和嫉妒心理,“帝王除了受帝王的嫉妒外不受他的人嫉妒”(38)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31页。。
尽管从伦理的视角对贫困进行阐释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原初定义,并因而促使反贫困策略走向多样化,但是这一转向所带来的难题和困惑亦不容忽视。一方面,它将使得对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的认定更加困难。以可行能力方法为例,沃尔夫(Jonathan Wolff)和兰姆(Edward Lamb)等人曾评价说,根据该方法,“我们没有获得关于什么时候一个人是否处于贫困的清晰概念(方法)”(39)Jonathan Wolff et al.,“A Philosophical Review of Poverty,”15 .参见https://www.jrf.org.uk/report/philosophical-review-poverty.。换言之,虽然森和努斯鲍姆把贫困视为可行能力的缺失看起来新意十足,但是这一方法(理论)没有为我们提供一套易于操作的贫困认定标准。可能有人会反驳道,联合国发展署的人类贫困指数(HPI)和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就是基于可行能力方法的贫困认定方案。但实际上,无论是HPI还是MPI,它们都只是包含了可行能力方法的部分内容,而没有体现出它的全部要求。由于对各类数据的获取并不都是容易的,即便是受到广泛认可的MPI也依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状况。例如,对中国多维贫困测量所使用的数据基本上滞后于中国的真实状况多达10年之久(40)王小林:《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55期,第50页。。另一方面,贫困概念的伦理定义未能注意到个人选择和文化观念等主观因素对认定贫困可能产生的干扰。根据可行能力理论,当个体不具备一些基本能力且不能享有相应的功能性活动时,此个体就是贫困人口。这一论断在操作上将面临诸多难以应对的挑战。例如,一个不参与世俗生活的僧侣,我们能说他贫困吗?某些时代和地区的一些女性受到宗教和许多政治禁令的限制,但是她们却可以享受奢华的生活,谁会说这些人是贫困人口呢?至于社会排斥,有些人因为个性的缘故无论处境如何变化都觉得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社会的仇富心理会使一些富人认为自己不被社会接纳和认可。把这种现象认定为贫困并动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去应对,似乎难以获得普遍认同。尊严更是一个直觉概念,在很多语境中它的定义并不是完全明确的。一件事情让一些人获益匪浅,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意味着失尽尊严。可见,“贫困是尊严的缺失”的认定同样有失严谨。
一些研究者曾指出,公共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应该具有可操作性,易于利益相关者理解并受到广泛认可,即使这样的政策与被精心论证过的道德理论产生矛盾,道德理论也要被排在第二位(41)Jonathan Wolff,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hilosophical Inquiry(Oxford:Routledge,2011),3-6.。例如,欧洲发达国家的许多研究者都主张以社会排斥来代替或者补充贫困概念,但是在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反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目标基本都与收入和消费因素有关,即“贫困风险率(the at-risk-of-poverty rate)、物质匮乏指数和生活在工作强度极低家庭的人口比例”(42)Ali Madanipour et al.,“ Concepts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Local Economy 30.7(2015):11.。依此来看,在具体的反贫困工作中以收入标准界定贫困,似乎依然是最具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方法。
四、结 语
贫困定义的伦理转向无形中增加了贫困识别难度,并带来了缺乏可操作性和其他一些问题。把贫困的定义拓展到“可行能力被剥夺”和“被社会排斥”等维度,体现了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人们对好生活的理解。这一理论动向,把那些在传统社会中较少受关注或难以实现的生活价值(例如,个体自尊心的满足和社会团结),提升到了公共领域的重要位置。对时下的中国而言,关注和吸收贫困定义的伦理转向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实现美好生活及共同富裕的理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该矛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对“美好生活”和“平衡、充分发展”有客观且合理的认识。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个人追求的多样化,对什么是美好生活和实现怎样的发展等问题,人们可能无法列出一个完全获得公认的清单。但无法给出完美的清单,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可以相信的是,在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大多数人将会追求一种更具全面性和立体感的生活。这意味着“美好生活”除了包括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之外,还在安全、归属感的获得、自尊心的满足和自我实现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正如上文所言,这些要求将不是以“词典式次序”被提出,而是以平行甚至超常规次序的面目出现。因此,政府和社会在对公共产品进行建设的时候,不应当局限于经济维度,而是也应当从伦理视角寻找更多的理论资源。
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共同富裕成为国家和社会追求的理想。共同富裕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解决贫富分化和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一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如果把消除社会排斥和追求社会团结贯彻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之中,那么,我们所实现的将会是一个后富者活得更加舒适,而先富者过得更加心安的共同富裕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