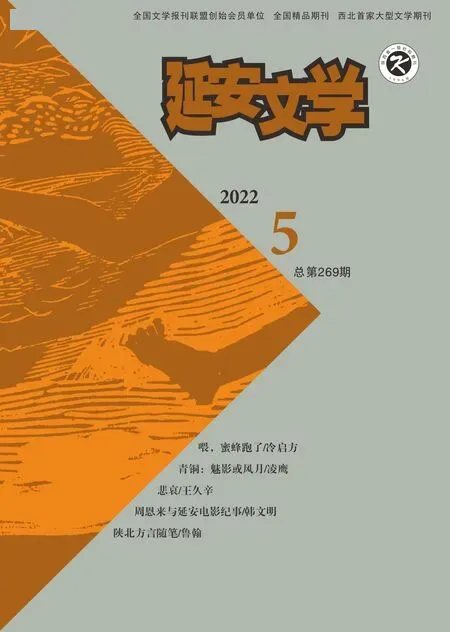星斗满天
杨代富
鸡叫三遍过后,深邃的夜空还稀疏地闪着几盏星星,月亮走远了,远山幽幽笼着黛色,太阳还沉沉地打着呼噜。母亲醒来了,轻轻地下了床,拿上手电,担着那对沉重的木桶,到村子南边水井担来一担满满清凉的水。母亲行走的步履太过匆匆,水从桶里蹦落下来,歪歪斜斜洒了一路。母亲把水放稳后,就劈柴烧起灶火,炊烟浓浓地从灶门涌出,呛得母亲眼泪都溢了出来。她忍不住蹬在地上,抹了一把眼睛,然后再站起来,眯着眼,一瓢一瓢地把潲水从大脚盆舀到堂锅中。她找来吹火筒,弯下身子,鼓着圆滚的腮帮,噗噗地吹将要熄灭的灶火。火的红光忽闪忽闪地映在母亲脸上,母亲显得很娇美。母亲开始切猪菜,用背篼把猪菜倒进堂锅里,然后稍稍喘了口气,用木瓢舀了半瓢清凉的井水,左手扶着没来得及挺直的腰,站在土灶旁边,咕咕地喝起来。
为了赶早去扛木方,整个夏天,这样的场景母亲不知上演了多少遍。母亲永远是这个场景中的主角,她给人的感觉总是火急火燎的。其实,每次母亲起床下地的时候,我也就醒了,经常也是跟着一同起来。有时候母亲起来担水,有时候烧火扫地,有时候去园子里割红薯藤来煮猪潲,都是在星星还亮着的时候。
我问妈你不怕鬼吗?“怕什么鬼。还得空怕鬼?忙都忙不过来。”母亲水波不惊地说,要我好生看火,然后又扑进夜幕里。
母亲不怕鬼,我猜想,肯定是有星星陪伴着的缘故,母亲的胆子一定是星星给壮大的。无论母亲走得多快,星星都在天上悄无声息地跟着,你到哪里,它也跟到哪里。不,像一盏灯,一盏高高的油灯,只是光发得暗一点而已。
听母亲说起过,小时候她是最胆小的。有时候晚上出门倒洗脚水都不敢,被外婆骂得老火了才麻起胆子把脚迈出门外。但眼睛刚一触碰到阴森森的夜幕,就顿时感到背皮发麻,头发都立竖起来。母亲赶紧泼掉水后,头也不回地跑进堂屋里,吓得脸色煞白。
“这花娘,当真未得出息!”外婆恨铁不成钢地数落母亲。
母亲把猪潲和饭菜都煮熟时,天还是灰蒙蒙的,只有东边的天空低低地涂着一抹暗暗的白痕。
父亲割牛草回来了。他什么时候去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他磨镰刀的声音。他放下担草的杠子后,就忙着去整理扛木方用的绳索。
扛木方,是那时整个夏天村子里最流行的挣钱的活。那段时间,花街路、乌牛大冲、唐烁溪、高椅和冉劝,到处都有人砍树锯木方,褪去了皮的白白杉木堆得满地都是,柴油机一天到晚“嘭嘭嘭嘭”地吼着,喷着刺鼻的浓烟,如簸箕大的锯片飞速旋转,锯木发出“哧哧”的刺耳声音,充斥着整个山谷、溪涧或是村落,盖过蝉鸣的声音。
母亲早就把饭菜摆好,用方形手帕包了两包圆鼓鼓的饭团。我们三人,围坐在饭桌边,不怎么说话,埋着头,急匆匆地吃着。两个幼小的弟妹还躺在床上,正甜甜地酣睡。
母亲把猪潲从锅里量出来后,到房间跟弟妹们交代一番,再到隔壁姨妈家去了一趟,回来,我们就一起出发了。
天边那抹白痕渐渐发酵扩大,父亲催我们快点走。出了村口,发现不少人陆陆续续走在大路上,大多是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大家都是赶早去扛木方的。原以为我们是去得最早的了,想不到人家比你还要早。“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此刻忽然从脑海里冒出这句话。这是我第一次跟父母去扛木方,想不到会这般热闹,心里充满了新奇和兴奋。我这才突然记起,昨夜整个晚上,好像我们村子就没有几家合眼过,几乎每家都是亮着灯盏的。“个个都要去扛木方,家里活路一大堆,白天做不了的只有晚上做,哪个还得空睡。”母亲说。
去扛方板的路上,人们步履匆匆,脚步噗噗哒哒,显得杂乱无章,手电的光在脚下晃动,像一条蜿蜒游动的长龙。偶尔有青蛙从田埂跳进水里,扑通一声,用手电一照,只见它一双手静静地扒在浮漂上,露出两只眼睛,一动不动。有的青蛙急得跳错方向,跳到你脚背上来,冰冰凉凉的,如被电击一般,吓得人大叫起来,赶紧踢脚踢腿,青蛙早被吓得不见影踪。走着走着,有时也突然从路的里坎窜出一条蛇来,有人“妈咿”地发出一声尖叫,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倒吸一口凉气,用手直拍胸口,走出很远了,心仍咚咚直跳。
大家边走,边说着话,相互探听木方多不多,在山上,还是在村子边,价钱如何。说这个地方才两角钱一斤,那个地方要多一点,到五角,但路程要远很多。我低着头,裹夹在他们中间,认真听他们谈论,偶尔母亲会提醒我,走路注意点。
我们加快脚步,赶超一拨又一拨人;一拨又一拨人,也一次又一次赶超我们,后来,大家都小跑在路上,像行军打仗的队伍。走了大约六七里远,天才开始泛光,周遭的草木矜持地立着,不再显得朦胧,鸟也醒了,偶尔鸣叫在深涧中,显得清脆而悠远,稀疏的几颗星星,还亮在天上。
当太阳跃出地平线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离家约二十里远的苗家村寨。这个苗寨叫乌潮,是一个宁静的小小村落,朝辉的暖色均匀地涂抹在房屋的木墙上,玻璃窗反射着明亮的光芒。房子前面的晾杆上,挂着一匹匹青褐色的土布,一条不大的小溪清浅地从村脚流过。村脚溪的左畔,是一个比较大的空坪场,堆着和散放满木方,白白的木屑填塞了一二十米远的溪段,三台锯木机安放在空坪场中间,边上堆满了一堆堆圆滚的等待锯成木方的杉木。木方中间站满了人,有的在观望;有的在挑选木方,然后堆在一起,标上记号;有的在忙着捆木方和登记。柴油机喷着浓烟发动起来,锯木机“哧哧”地发出尖叫声,锯木师傅“叭叭”地把木方娴熟地掷在一边。一切井然有序。
听母亲说,有次她们去卑炸扛木方,也是天还未亮就去的。去到那里一看,才发现木方少,扛的人多,有的木方还架在烤棚里烘烤,还不许扛。大老远跑来,不可能白来一趟。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走上前去,将木方卸下来扛走。锯木师傅无法,劝阻无效,只好默认大家扛走。菊英六妈见状,赶紧召集人去抢。菊英六妈长得高大,负责从烤棚里把木方抢出来,大妹四妈、银兰三妈则负责把木方输送出来,我妈负责在外面守着木方莫让别人抢走。由于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没多久,她们每个人都抢到了要扛的木方。但大多数人,都是自顾自,单打独斗,前脚刚把木方抢出来,后脚就被他人扛走。有的忙活了好半天,到最后弄得一块木方都没到手。有的在一旁哭,有的在指手划脚吵架,口水飙得到处都是。烤棚里的木方抢完后,人们就挤到锯木师傅身边。锯木师傅用抓勾把杉木端上锯木机架子上,刚送出锯盘一两尺远,就有人伸出手来争抓木方。第一块刚被人拿走,第二块就有其他人伸手过来,而且是越来越靠近锯盘。锯木师傅厉声骂道:“你们不要命了,为了一块木方?”骂归骂,但没有人退缩。锯木师傅无法,怕出事故,只好停机吃饭。人们只好干等,有的去亲戚家找吃饭,有的吃从家里包来的饭团。有的老早就到了,白白耽搁一天,一块木方也没扛到。
母亲说,那次她们去秦崩扛木方,也是守到下午天快黑了,才扛到木方。
秦崩是母亲老家格朗村的一处大山,全是原始深林,延展得快接近青山界了。去秦崩的路非常不好走,没有现成的,只有条毛毛小路伸至山脚,之后就得撕山往前走了。山又大又陡,树木密密匝匝,荆棘丛生,怕蛇,又怕野蜂。母亲说。
“未晓得莫去。”我天真地说。
母亲剐我一眼:“莫去,讲得倒轻巧,去哪里找钱?一家人开口天天要吃,拿哪样子买粮食?”
那时,我家有六口人,我排行老二,哥刚上初中,三弟和妹还没读书。对于家庭负担的沉重,还小的我,是体会不了那么深的。
生生的一座大山,硬是被我们这伙扛木方的踩出一条路来。母亲说,木方扛下山不久,天也就黑了,有力气的,扛到格朗来休息,她只好在高坡跟木生的媳妇过夜。木生以前是母亲家的邻居,他家的田都在高坡,离村子六七里远。因种田实在太辛苦,来回往返够呛,他只好从格朗搬到那上面去住,独独的一户人家,显得有些孤零。
木生两口子对母亲很热情,但那一夜,母亲始终是刨躁的,心急得像猫抓,留我们几个孩子在家,家里活路一大堆,想想一晚都睡不打瞌。刚刚闭合眼睛,一会儿又醒转过来,起来到门外看,还没见天亮,远处村庄的灯火稀落,没有听到狗叫,也没有夜鸟从头顶飞过,青蛙的叫声倒是非常殷勤,没看见月亮,头顶满是星星。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扛着木方离开了木生家。
这次来人虽多,但木方管够。大家都在抓紧挑选适合自己扛的木方。父亲选一块木方要我扛着试试,太轻了,又换了一块。
在太阳还有一丝清凉的时候,我们出发了,快步追赶前面的人们。由于乌潮那时不通公路,这些木方都要翻山越岭扛到二十五里远的地方上车。
一拨拨的人把木方扛走,一拨拨的人才急匆匆赶来。开始我能小跑,父亲和母亲也都是小跑,所有的人也都小跑,肩上的木方有节奏地一颤一颤。过完一段平路之后,一堵坡耸在眼前,灰白的山路一弯一扭成之字形从坡头滑下来。到九十九拐了。开始爬坡了。由于之前行走速度过快,体力消耗不少,汗弄湿了衣襟,脸上也爬满了湿黑的汗路,汗水还故意跑进眼睛里去,弄得眼睛又涩又辣。我不停地用小手揩着汗水,不时停下来,把木方在左右肩之间频繁挪移。太阳一改它温和的面孔,火辣辣地瞪着圆鼓的眼睛,喷着滚烫的热浪,路边的草木也蔫头耷脑,没有一点精神,风也不知藏到了哪里,空气似凝沉不动。
父亲的步履开始显得沉重,小腿上的青筋根根暴突,蚯蚓似地弯扭着,衣服全湿了,一阵阵浓重的汗味扑鼻而来。母亲无力地伸着脖子,茫然地望向坡顶,脚步显得蹒跚。我开始想哭,不停地换肩,在心里骂着太阳,走完一道弯,就把木方立在路上,小歇片刻,用眼光狠狠地盯着太阳,等父亲赶到身后,才又扛起来走。
“怎么还不到坡头?”我带着哭腔问母亲。
“快了。”母亲无力地回答。
爬上几段坡路后,我又问,母亲还是说快了。我生气地把木方丢在路边,我的小嘴裂开一道弧形口子,揩着满眼涩辣的汗水,无声地哭。
母亲把木方放下来,说歇会儿吧,然后用手帕揩我脸上的汗。我生气地把脸别过一边。
“你一小段小段地想,先到这个弯拐,到了再想上面那个弯拐,一段一段地走,你就没这么累了。不要一下子就想到坡头。”母亲告诉我行走的技巧。
“我早试过了,未起作用,肩膀还是辣火火的,腿都抬不动。”“你才扛这一趟,就讲抬不动腿。我们天天扛,都还抬得动腿。这点苦都受不了,今后的苦还要多,哪还受得了?”母亲开始生气起来。
“你们是大人。”我辩解道。
“好了,休息这么多,人家都走远了。”母亲软下脾气,把木方放到我肩上,我极不情愿地继续向前挪步。
当我们来到坡头的时候,已经有好些人停在那里休息。坡头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平整山坳,好几棵高大的树木立在上面,树下是几根两脚木凳或石块,坳口下来不远处有一眼泉水,泉水奔涌着,旁边放着个缺了口的瓷碗。
我们放下木方,找了一片树荫,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太阳立在头顶,此刻,我已没有勇气正视它了。
我站在泉眼旁边,舀上一碗泉水,大口大口地喝,顿觉劳累消减一半。我把水舀上来给父亲喝。父亲把水直接倒进嘴里,喉结滚动几下,就没了;一碗不够,又舀了一碗。当水喝完之后,父亲张着嘴,痛快地发出“啊”的一声。母亲也喝了一碗。这时,才感觉山坳口有一丝风微微吹来。
母亲解开饭团,父亲用柴刀砍来小木条当筷子,母亲把饭用小木条铲开,然后先放一坨在我手上,我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饭的时候,母亲讲了个笑话。说是那年正月间的时候,她和菊英六妈、大妹四妈、银兰三妈她们去乌细溪扛木方。银兰三妈、金花、水花她们仨娘崽带了八个煎粑粑。到乌细溪银兰三妈提议说:“先拿我的粑粑来吃吧,路上再吃你们的。”大妹四妈说:“哎嗨,莫挂欠,先吃我们的,你的留着。”其他人也跟着附和。银兰三妈显得有些无奈,但又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又默默地担着那八个粑粑,到乌累歇气的时候,才解开来吃。大家边吃边笑。银兰三妈说:“你们狡猾死,把你们的粑粑吃完了,你们倒是轻松,还得人情,才要我担这八个粑粑一路,害得我累死,明天老子一个粑粑都未煎来,干脆净吃你们的。”
“哪个要你笨死,煎这么多来。”大妹四妈提高嗓门,笑着大声说。
母亲边讲边笑,全然没有了刚才劳累的样子。
当我们把木方扛到公路边的时候,太阳已经收敛了它锐利的目光,悬在西边山头不远的天空。公路上堆满木方,人们把木方斜放在公路旁,疲惫地站着或坐着,有的甚至有气无力地躺着,焦急地等待木方过秤。
在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轮到父母称木方。我一天的劳动,换回了二块五角钱。这是我第一次挣钱,我高兴得忘记了身上的酸痛。我把钱交给母亲,要她拿来买米。母亲夸我懂事,晓得为家里出力分担了,她感到很欣慰,我也觉得心里美滋滋的。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溜下天边,浓重的暮色覆盖了整个天际。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的时候,村子显得静悄悄的,人们差不多都已入睡,唯有满天的星斗在不停地眨巴着眼睛。